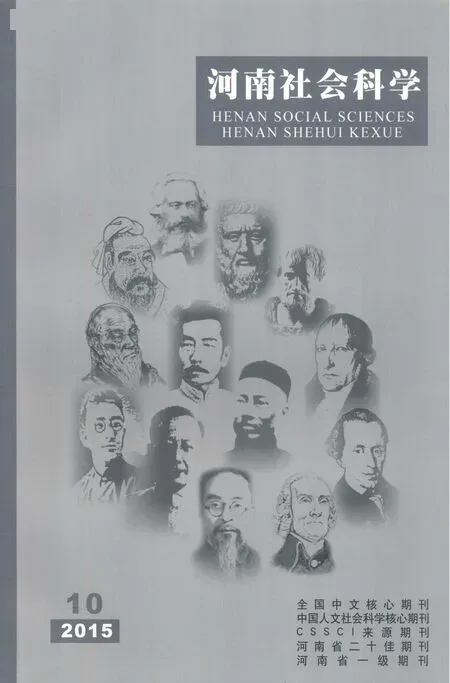论言语交互行为中的逻辑直觉与情感直觉
2015-03-26焦肃东
焦肃东
(南京大学 哲学系,江苏 南京 210013;南京艺术学院,江苏 南京 210013)
“语言”与“言语”是一对紧密相关、互为因果的概念,按中国传统的说法,“言”既为“语”,“语”可成“文”,中国传统文化中对于“言”的价值追求是向“文”的无限接近,“出口成章”“口吐莲花”“锦心绣口”等典故均表达了对言语行为实践价值境界的诉求。言语是人类相互交流的工具,在日常的使用中人们往往使用“语言”一词来涵括这一交流工具的所有方面。正因如此,在“语言世界”中,我们对言语概念的层级和不同层级的功能与使用效应的研究不深,挖掘不够,以至于造成各种类型的语言误解和交流障碍。言语背后是深刻的文化传统绵延,文化的走向和相对时间内的文化取向都对言语产生深刻影响,而语言的使用主体在具体的言语交互行为实践中,对文化走向与取向所决定的言语内容生成机制和言语交互的过程性控制机制的深入研究和把握则成为避免语言误解、破除交流障碍的关键。
西方语言哲学研究受语言转向的深刻影响,对于语言本体的研究与剖析带动了言语交互行为理论研究和言语交互实践水平的进步。在“语言转向”中,英美理想语言派的罗素、卡尔纳普、塔斯基等人认为,要深入研究语言的纯粹逻辑形式和功能,强调语言指称的准确性、表述的清晰性和意义的可证实性研究;而日常语言派的奥斯汀、塞尔及后期维特根斯坦等则认为,要强化词语的多重含义、表述的间接功能、意义的延展性来消解语言的纯粹逻辑形式功能,他们更加关注言语行为与世界的关系、关注语言的意向性、关注主体的“语言游戏”,简而言之,他们的研究更聚焦于“言说”本身,正如海德格尔所言:“语言之生存论本体论的基础乃是言说。”[1]
瑞士语言学家索绪尔则从人类言语活动(langage)中明确地区分语言(langue)和言语(parole)这两个不同性质的研究对象。他认为语言是一种表达观点观念的符号系统;而言语则是言语活动的个人部分,它是人们彼此言谈的总和[2]。言语其中包括:(a)依赖于个人意志,反映个人思想的个人的组合,即句子;(b)同样依赖于个人意志,实现这些组合的发音行为[2]。索绪尔还指出,可将语言研究分为内部语言研究和外部语言研究。内部语言研究关注语言自身的结构体系,外部语言研究涉及语言与文化、民族、历史等人文语言环境要素的关系。从上述评析不难看出,随着对语言和言语研究的深入,西方学者不论是在语言的逻辑性与非逻辑语言的存在,还是在语言的内部结构本身和影响语言的外部因素等诸多涉及语言和言语的方面有共识,但也存在很多分歧。在基本厘清关于语言和言语的观念前提下,本文将在传统“言语行为理论”的基础上,关注“言语交互行为”的过程、层级研究,以逻辑直觉和情感直觉在其中的作用和运行机制为切入点,尝试从言语的整体性和实践性视角探究言语交互行为过程在不同层级呈现出的规律和特点。
一、言语交互行为理论溯源
言语行为理论的先驱J.L.奥斯汀认为,使用语言是为了述说或描述事件和报道世界,话语可以和世界对照来考察其是否与事实相符,从而判定其真假。这一传统哲学家对语言本质的认识是不周全的,重要的是弄清楚“总的言语情景中的全部言语行为”[3],语言的重要功能在于完成各种言语行为。说话人意图和对言外之力的理解成为他言语情景中的重要分析要素。他将言语行为分为:话语行为(Locutionary Act)——说出词、短语和分句的行为;话语施事行为(illocutionary Act)——表达说话者的意图的行为;话语施效行为(Perlocutionary Act)——通过某些话所实施行为的效果。他认为,这种分析将涉及交流的双方,涉及一个或多个主体言语行为的连贯和相互关系。约翰·塞尔在继承和批判奥斯汀的分析方法的基础上,进一步解释和区分了话语的命题内容和施事行为,从言语行为应满足的“合适条件”(felicity conditions),即从成功实施言语行为必须满足的必要和充分条件——话语的目的(基本条件)、表现的心理状态(真诚条件)、话语与世界的关系、合适方向(先决条件)和命题内容(命题条件)[4]中——抽象出施事行为的构成规则:(1)命题内容规则:规定话语的命题内容部分的意义;(2)先决条件规则:规定实施言语行为的先决条件;(3)真诚条件规则:规定保证言语行为真诚地得到实施的条件;(4)基本条件规则:断言行为规定言语行为按照规约当作某一目的的条件[5]。在此基础上,塞尔又把施事行为化分成五类:断言行为(assertives)、指令行为(directives)、承诺行为(commissives)、表情行为(expressives)、宣告行为(declarations)。这些理论研究为早期言语行为的分析提供了解释模式和分析工具。
为了弥补早期言语行为理论在现代语篇分析和交际功能话语连贯性分析方面的不足,增强言语行为理论的解释力,后期学者拓宽了奥斯汀和塞尔理论言说的范畴,引入了“交互”(interactive)这一具有当代理论创新性和应用实践性的概念。埃德蒙森指出,在会话中每个参与者都在实施某个“言外行为”,这个行为的实施过程应该带有话语交际的重要特点,即发话人的意图与听话人的理解相互联系和相互作用,称为“交互行为”(interactive act),“言外行为”和“交互行为”共同构成话语的基础[6]。克雷格则认为,“言语行为”会影响交际中人们的思想,使发话人的意图与社会中其他“行为”互动或合拍,这也就形成了所谓“交互关系”或“交互行为”,在会话中人们主要对“交互行为”进行反应,其次才是对“言语行为”的反应[7]。由此可以看出,言语交互行为的研究是在当代语言更重视主体的互动性和交际性的背景中应运而生的,理论本身更加关注言语交互行为发生的过程性和交互过程中的言语内容结构的层次性。
二、言语交互行为的层级划分和直觉生成
海德格尔在《存在与时间》中谈及语言问题时说:“言说就其本身而言就是时间性的。”而言语交互行为本身就具有即时性和瞬变性的突出特性。正是具有了这样的特性,其规律性就更难把握,个中原由在于现代言语交互行为实践中言语所具有的复杂的交互层级。在言语交互行为实践中存在着从交流到竞争,进而上升至审美层次的不同层级。(1)交流层级,即言语行动最基本的传递信息、交互沟通层级;(2)竞争层级,即言语博弈和利益互换层级;(3)审美层级,即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传达与言语交互行为的艺术化层级。依此“层级论”出发,寻求研究言语行为实践的规律性进路,可使交互主体在不同层级对言语交互行为进行科学的把握。
言语的即时性和瞬变性体现在言语交互表达过程中。传授双方在言语交互中具有强烈的共时性,否则就无法形成对话场。双方在场域内,言语的生成是在瞬间完成,而且受到场域内各方的影响可能发生不可预测的调整和变化,言语生成有赖于言语主体快速的反应机制和反馈系统。因为这种言语反应机制和反馈系统其自身的模糊性和不稳定性,所以,直觉思维将对言语生成起主导性作用。当代心理学家研究将直觉思维分为三种不同类型:第一类是关注人际关系和情感交流敏感性的社会情感直觉;第二类是关注问题解决和任务决策的应用性直觉;第三类是关注预测未来能力的自由直觉[8]。这种直觉思维的划分方式涉及的人类主体的自我行动和创造行为以及群体交互行为,超越了单纯的直觉“感性说”和“初级原始说”,客观理性地划分了直觉思维在不同情境和应用性背景下的作用机制。依此分类,在言语交互行为过程中,社会情感直觉、应用性直觉、自由直觉对于不同层级的言语生成都会产生不同的作用:应用性直觉将主导信息的传递交流和决策的产生,自由直觉则主导假设性言语和想象性言语,社会情感直觉在其中调节言语的应景度和面对不同言语对象的言语分寸。这种在长期的言语实践中形成的自成一体的言语感知交互体系,通常称其为语感或言语直觉。言语直觉使言语生成中的主体快速反应机制和反馈系统形成成为可能,而言语直觉则可视为逻辑直觉和情感直觉的交互产物。
三、言语交互行为中的逻辑直觉运行机制
何谓逻辑直觉?逻辑直觉在本文对言语交互行为的探讨语境中是指:在即时的言语生成过程中对言语结构和内容因果关系的直观性把握,它决定了言语生成内容的合逻辑性和言语效用发挥的合目的性。乔姆斯基在转换生成语法学说中将语言的结构分析分为语言能力和语言应用行动两个部分,与索绪尔不同的是,他更加关注语言的创造过程,并力求为语言的生成寻求严密的逻辑基础。而他所假设的人所具有的“天赋语言能力”理论,虽然遭到后期很多语言研究学者的批评,但他在语言的初期生成理论描述中,实际上倾向于人们在处理言语交互行为过程中的逻辑直觉系统和情感直觉系统所发挥的作用。逻辑直觉直接控制着言语生成的逻辑形式,而这种逻辑直觉的生成则有赖于人类主体长期言语交互行为实践中所积累沉淀的语言应用型经验,快速的言语反应机制则是建立在对惯常使用的逻辑形式的“自发性”判断和选择,这种自发性的速度往往会超过言语主体的意识反应速度。当言语主体遭遇言语交互的具体情境时,大脑中会迅速形成新的“暂时神经联系”。根据巴甫洛夫等人的研究,这种新的“暂时神经联系”往往可以在大脑优势兴奋中心的边缘抑制区以“突然拓通”的方式形成,因此,主体就可能没有意识到形成的过程,而直接领悟出了结论[9]。
在言语传递信息和交互沟通的基本层级,逻辑直觉对于言语生成内容的控制呈现松散型特点,在此层级中,由于言语主体对于言语效应的目的是模糊的,换言之,即言语主体对于言语生成内容所期望取得的言语效应并无明确的目标。如“今天天气不错”,此句传递了简单的信息,达到了交互沟通中的问候功用,但使用主体并无明确的功能预设和效果预期。这个言语层级的言语交互行为类似于奥斯汀在言语行为理论中使用的“phatic act”(发语行为)的说法,“phatic”一词是波兰裔英籍人类学家Malinowski(1884—1942)首先使用的,指的是用于建立气氛和维持社会接触而不是用于交流信息或思想的谈话,如对天气的评论和询问健康状况的用语。奥斯汀借用这一术语是为了表示机械地说出一个语句而不知其意的谈话。“不知其意”对于言语使用主体来说,有些言过其实,在言语交互行为的这个基础层级中,应该理解为“意在言外”,即完成程式化交流或礼节性沟通,言之本意并不重要或居于次要位置。
在言语的言语博弈与利益互换层级,逻辑直觉对于言语生成内容的控制呈现紧密型特点,在此层级中,言语交互双方在有限时间的限定场域内,有争胜目的和利益需求,对言语所产生的效应具有明确的目标。因此,在相对有限的言语交互中,对话场域内的主体力求将言语的各部分功能发挥到最大值,对于由各部分组合所形成的整体言语系统所发挥的作用追求利益的最大化。逻辑直觉在这其中对于言语系统中的句序、词序和语段之间的逻辑关系及事实信息、观念信息、模糊信息等呈现共时性紧密控制,逻辑直觉对有效信息及对方言语方式进行即时判断、推理和演绎论证,对交互信息中不同命题的有效性进行瞬间的判断和回应,以达到“一语中的”“言之有理”的预期。如在谈判、辩论言语交互中,不同的言语主体在进行言语交互之前,都将进行言语内容材料的梳理和自我言语推进的逻辑论证准备,但在言语的对话场域中,原先的材料信息选取和逻辑论证推进程序将因对方的实际言语行动进行适时的调节与变化,这种“调节与变化”有赖于逻辑直觉的激发,对瞬间变化的言语场信息重新进行逻辑定位,从而生成全新的逻辑论证推进系统,保证言语效应的预期实现。
在言语交互的信息与情感的双重传达与言语交互艺术化层级,逻辑直觉对于言语内容的结构层级控制呈现弹性机制。在此层级中,言语交互的对话场域内的双方或各方对于言语效应的目的性要求更为隐性,目的本质与上述两个层级中的目的有根本性区别,其目的性在涵括上述言语层级目的的同时,往往具有公共性和示范性的价值诉求。对话场域内的言语主体的角色具有明显的“非个体化”特点,言语主体的身份和角色决定了言语交互的内容和方式,其言语内容更具公共性,言语方式更具示范性。这个层级类似于奥斯汀言语行为理论中的“话语施效行为”层次:“说话者在说了什么之后通常还可能对听者、说者或其他人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一定的影响。”[10]正如教师、主持人言语交互行为,言语主体的职业角色定位对其传递信息的质量和言语效应的预期实现有更高要求,逻辑直觉在言语发话主体前期相对充足的逻辑论证系统推进方式准备的前提下,对于对话场域内的另一方(接受主体)的认知水平、信息反馈及接受程度进行适时的弹性控制,并及时调整传递方式和表达内容的逻辑论证推进程序,以期对接受主体的感情、思想和行为产生影响。
四、言语交互行为中的情感直觉运行机制
情感直觉在本文对言语交互的探讨语境中是指:在即时的言语生成过程中对言语情感分寸和表达内容的直接性把握,它满足了言语主体对内容的情感性需求并强化言语效用发挥及对言语对话场域内的主体的情感影响。情感直觉在言语交互中的功能与逻辑直觉不同,如果说逻辑直觉是面向言语主体对自我和自我表达的观照,那么情感直觉则是面向言语主体对他者和他者表达的观照。言语主体除了对言语对象的话语作出内容价值判断外,同时对言语表达方式的恰当性产生相应的瞬间情感,并能够准确地把握对方所传递的各类情感。情感直觉既受到言语情境的制约,又受到言语主体情感识别偏好的影响,是言语主体以形象联想、模糊识别和情感活动为主的瞬间言语综合心理反应。情感直觉对于言语中的情感因素进行分寸把握和程度判断,有赖于言语交互中的情感体验实践和情绪感觉记忆。
在言语交互行为过程中,情感直觉的运行机制大致为:言语交互方发出或接收言语信号,在主观情感偏好的影响下提取认知范畴内的信息价值,并依赖于主体自身在长时间社会组织交互活动中形成的情感控制惯性,从而确定在言语交互行为中传递情感的方式与强度,接收和处理言语表达所产生的反馈信号,从言语情感分寸的把握与识别到言语表达反应的方式选择,再到言语交互过程中的即时修正,以认知为基础,记忆为中介,意志控制为导向,在瞬间整合离散信息,完成整体性的言语交互行为。凭借情感直觉,言语主体可以在接受言语符号刺激的瞬间不加分析地直接把握住语言符号所表达的全部抽象意义和情感色彩,能够下意识地辨别词与词之间在意义和情感色彩上的细微的差别,能够从语句或语段的开头预测出整体语句或语段的趋向。情感直觉在逻辑直觉发挥作用的同时,对事实性和观念性信息进行“二度创作”,来加强言语交互中的言语效用发挥,向更高境界的言语交互行为层级迈进。
五、结语
言语交互行为是具有创造性的言语实践活动,它所关注的是言语行为的“正在发生”和“走向何处”。过往对言语交互行为的研究过多关注于言语行为的静态分析,而忽略了言语行为过程的动态研究,而在此动态过程中言语直觉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言语直觉作为一种人类主体使用语言的应用型思维,是人脑对思维迅速指向客体对象(听话人身份识别、被描述实体、事件及言语交互本身)的核心及其交互关系的即时性突发式判断和反应,其特征在于生成言语内容(段落布局、句式排列、用词选择、语态调节)的直接性。言语交互行为过程中的言语应对的时间性要求和互动言语场域的形成有赖于“言语的直接性”,而这种言语交互的直接性则有赖于交互主体对逻辑直觉和情感直觉的把握和应用。对于言语交互中的逻辑直觉和情感直觉的研究有利于提高人类主体言语交互的层次和语言应用水平。
[1]恩斯特,卡西尔.语言与神话[M].于晓,等,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8.
[2]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M].高名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3]J.L.Austin.How to Do Things with Words[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2.
[4]J.R.Searle.Expression and Meaning:Studies in the Theory of Speech Acts[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1979.
[5]J.R.Searle.Speech Acts:An Essay in the Philosophy of Language[M].London: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1969.
[6]Edmondson.W.J.Spoken Discourse,A Model for analysis[M].London:Longman,1981.
[7]Craig.R.T.“Goals in discourse”Contemporary issues in Language and Discourse Processes[M].NJ:Lawrence Erlbaum Associates,Inc,1986.
[8]Raidl.M.H,Lubart.T.I.An empirical study of intuition and creativity[J].Imagination,Cognitive and Personality,2000/2001,20(3):217.
[9]孙伟平.从爱因斯坦模式看逻辑思维和直觉思维的互补关系[J].学术界,1992,(5):9—14.
[10]杨玉成.奥斯汀:语言现象学与哲学[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