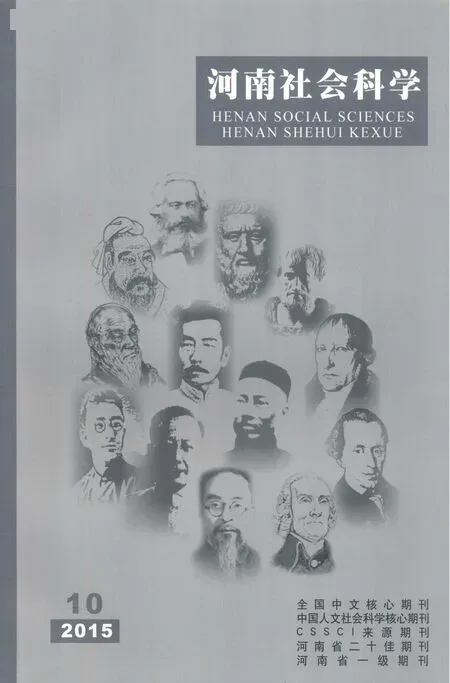叶燮诗性智慧的立论依据与精神旨归
2015-03-26李铁青
李铁青
(曲阜师范大学 文学院,山东 曲阜 273165)
诗性智慧在中西方的文化传统中是重要的精神内核和思想根基之一,对于中西文化比较与会通具有重要价值。作为一个重要范畴,诗性智慧由意大利著名学者维柯在《新科学》中首次明确提出。维柯以科学的态度一一探析了“用诗性文字来说话的诗人”[1]所创造的诗性玄学、诗性逻辑、诗性伦理、诗性经济、诗性政治等“要费大力气才能懂得”的诗性智慧,并对诗、诗人、诗性、哲学、哲学家、智慧等范畴都进行了阐述。由此,结合中国文化宝库中丰富的诗性智慧资源以及诗与哲学、诗性与智慧和思想密不可分的历史传统,笔者对诗性智慧的内涵界定为:一是诗性智慧是诗与哲学以及智慧的统一,是诗与思的统一,即以“诗”的方式表达“思”的意蕴,将智慧之“思”与诗之“诗性”有机结合,力求实现诗化的智慧与智慧化的诗的完美呈现;二是诗性智慧是天人合一的生命存在方式的有机统一,关注人的生命存在价值和意义。
叶燮(1627—1703)作为一名集诗性、智慧、德行于一体的清代文论家,以“诗”的方式表现哲学、智慧之思的深度,身体力行诗化的人生,力求诗与思的统一,不但诗文创作颇丰,而且写成了系统严谨的诗论大著——《原诗》等,展示出了一种积淀与突破贯通的诗性智慧,启人深思。本文就试着穿越历史,还原文化情境,以积淀与突破为基点来探析叶燮诗性智慧的立论依据与精神旨归。
一、对积淀与突破的思考
关于积淀与突破,学界曾进行过深入研究,在对各家的探索与争鸣加以分析和思考之后,笔者认为,积淀与突破孕育着巨大的文化价值。“文化谓‘积’,由环境、传统、教育而来,或强迫,或自愿,或自觉,或不自觉。这个文化堆积沉没在各个不同的先天(生理)和后天(环境、时空、条件)的个体身上,形成各个并不相同甚至迥然有异的‘淀’。于是,‘积淀’的文化心理结构(Cultural-Psychological Formation)既是人类的,又是文化的,从根本上说,它更是个体的。”[2]但仅有积淀,文化不足以传承、接续和创新。如果文化积淀通过各种方式的积累、吸收、深化,只是停留在量变的基础上,那就有可能是一种无超越意义的复古或历史的倒退。因而,文化的突破也就势在必行,突破是量变基础上有超越价值的质变,是推动文化发展和繁荣的历史原动力,是对传统的创新和复古的批判,是一种思想启蒙和解放。“因此,文化的突破必须是在深沉厚积基础上的突破,积淀应该是在不断变革求新的过程中的积淀……文化的积淀与突破,是人类文化自身的矛盾运动,是文化发展的内在动力。”[3]
由此,积淀与突破实际上为我们提供了一种有价值的研究路径和有益的启示,即以此来理解一个人、一种理论或范畴的立论依据与精神旨归。正如陈炎所说:“‘积淀’与‘突破’之最重要的意义……说到底,它涉及人在个体与群体、感性与理性、历史与未来、创造与享受等错综复杂的关系中,对于自身存在及其意义的理解问题,即涉及所谓‘价值之源’的问题。”[4]从这个意义上讲,叶燮作为一个文化个体,面对丰富历史文化资源与时代、现实的激发,将积淀与突破合理贯通来审视、思考,既是其实现个体价值的途径,也是其融入人类整体文化宝库的必由之路。其诗性智慧既是积淀前人研究的“照着讲”,也是有所突破创新的“接着讲”,其中孕育着巨大的文化价值。
二、积淀与突破:叶燮诗性智慧的立论依据与精神旨归
(一)价值论与方法论相统一的积淀:叶燮诗性智慧的立论依据
1.对《诗经》等文学经典的积淀
文学经典的学习和继承是任何从事创作和研究的人所绕不过的一个“存在”。经典不仅可以提供丰富资源的支撑,显示巨大的价值之用,具有价值论的意义,而且本身就可以成为立论的依据,具有方法论的意义。由于文学“名著中包含了人的心智赖以获得洞察力、理解力和智慧的最好材料”[5],叶燮通过对历代文学经典的积淀,诸如对历代作品中所蕴含的风格特征、语言形式、结构等丰厚养分的不断累积,为其诗文创作和理论建构打下了坚实的基础。例如,《原诗》开篇即引《诗经》作为其论述诗歌正变盛衰的依据,如“诗始于《三百篇》……诗有源必有流,有本必达末;又有因流而溯源,循末以返本”“不读《三百篇》,不知汉魏诗之工也”等。更重要的是,《诗经》作为文学经典,体现了诗性之美与哲思之美的有机统一,其中既有语言精妙、引人想象、意象丰富、怡情悦性、比兴并用的诗性之美,也有关注生命体验、文化意蕴丰富、忧患意识浓郁、雅正中和与可观、可群、可怨的哲思之美。除《诗经》外,叶燮诗文、诗论中所引用的《离骚》《论语》《孟子》《古诗十九首》《史记》以及杜甫、苏轼等的文学经典中都有大量的诗性与哲思统一的诗性智慧,这些都为叶燮诗性智慧的产生和发展提供了充足的立论依据。
2.对古代哲学、文论范畴、命题的积淀
叶燮非常注重对古代哲学、文论的学习积淀,通过对以往诸多范畴、命题的吸纳,赋予其新的内涵和意蕴,形成了丰富的诗性智慧。在叶燮的诗文、诗论中,如意、道、变、理、情、言、象、性、法、性情等哲学范畴,形神、虚实、有无、体用、本末等哲学命题,都为其建构理论、展示诗性智慧提供了依据。例如,《易经》中的变、天人合一、仰观俯察、观物取象等哲学范畴、命题都给叶燮以巨大影响,为其论述提供了有力支撑。正如有论者指出,“在哲学上,叶燮思想更为复杂。他以儒为主,又综贯佛老,兼及诸子百家,可说是包罗万象……在方法论上,叶燮受到儒家的《易经》,道家《老》《庄》,特别是佛家思辨方式的影响,具有一定的辩证因素”[6]。就其文论思想来说,他对历代文论范畴、命题基本上都进行了有所创新的继承。如诗言志、文质观、温柔敦厚、成一家之言、作诗者在抒写性情、三不朽、陈言之务去、诗穷而后工、诗中有画与画中有诗等。以“诗言志”为例,叶燮说:“《虞书》称‘诗言志’。志也者,训诂为‘心之所之’,在释氏,所谓‘种子’也。志之发端,虽有高卑、大小、远近之不同,然有是志,而以我所云才、识、胆、力四语充之,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正是有了对“志”的分析、继承,叶燮才进而提出富有新意的“才、识、胆、力”说来丰富其理论阐述。
此外,他还通过对历代文论的系统分析,在积淀和扬弃历代文论的基础上,“一一剖析而缕分之,兼综而条贯之”,丰富其诗性智慧。虽然他认为“诗道之不能长振也,由于古今人之诗评杂而无章,纷而不一……如钟嵘、如刘勰,其言不过吞吐抑扬,不能持论”,“最厌于听闻、锢蔽学者耳目心思者,则严羽、高棅、刘辰翁及李攀龙诸人是也……诗道之不振,此三人与有过焉”。但可贵的是,他在对刘勰、严羽等文论批判的基础上进行了积极的继承和借鉴,取其精华而为其所用。在其诗文、诗论中,叶燮一再引用钟嵘、刘勰、严羽等的理论思想、观点、词句,或作为立论的依据,或作为批驳的依据。由于所持的立场、言说方式等不同,评述虽然说有些过激,但从诗道不振的现实弊病和忧患意识出发,他还是对钟嵘、刘勰、严羽等文论中优秀的思想进行了有益的吸纳,为其理论体系的构建和诗性智慧的拓展提供了启迪。例如,刘勰文论的系统性、理论性等对叶燮创建诗论体系的启发,严羽的“以识为主”“妙悟”“本色”“极致”“入神”等对叶燮的影响。又如,叶燮就强调“惟有识,则能知所从、知所奋、知所决,而后才与胆力,皆确然有以自信;举世非之,举世誉之,而不为其所摇”,主张在文学创作中要“妙悟天开,从至理实事中领悟,乃得此境界也”“夫惟神,乃能变化”等。
3.对历代文艺家伟大人格的积淀
人格与文艺创作关系密切,对创作者诗性才情的形成和哲学思维能力的提升等有巨大影响。叶燮在《南游集序》中说:“然余历观古今数千百年来所传之诗与文,与其人未有不同出于一者,得其一,即可以知其二矣。”接着他通过对李白、杜甫、韩愈、欧阳修、苏轼等诗文的分析,认为他们“无不文如其诗,诗如其文,诗与文如其人。盖是其人,斯能为其言;为其言,斯能有其品……近代间有巨子与人判若为二者,然亦仅见,非恒理耳。余尝操此以求友,得其友,及观其诗与文,无不合也。又尝操此以称其诗与文,诵其诗与文,及验其人其品,无不合也”[7]。通过对历代文艺家伟大人格的积淀,叶燮将人格与诗文之品统一、“诗以人见,人以诗见”的创作见识融入其诗性智慧,以此为立论依据,推出了大量与人格相近的范畴,如《原诗》中提到的“胸襟”“品量”“面目”以及“性情”“才、胆、识、力”等,丰富了对于人格、人品与诗文之道的理解,将人格与远见卓识、性情、才学、胆识、胸怀等统一起来,重视伟大人格的生成和内在涵养的提升,力求以独立之思想、自由之精神来审视世界万物。
4.对自然之道的积淀
“古者包牺氏之王天下也,仰则观象于天,俯则观法于地,观鸟兽之文,与地之宜,近取诸身,远取诸物,于是始作八卦,以通神明之德,以类万物之情。”[8]人处于天地之间,在认识、改造自然的同时,自我在自然中得以复观。中国古代先哲们很早就认识到自然的重要性,在俯仰之间,在远取与近取中,人与自然得以合一。如孔子所说的“多识于鸟兽草木之名”,以及刘勰提出的“江山之助”等。诗文是有限与无限的统一,自然、宇宙中的日月、山川乃至一草一木等都无不蕴藏着浓浓的诗情画意,给诗人以创作灵思。
仅在《原诗》中,叶燮使用“自然”“天地”二词就有十多次,如“盖天地有自然之文章”“克肖其自然”“天地间自然之文”“自然之法立”“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文章者,所以表天地万物之情状也”等。叶燮通过对自然、宇宙之道的认识,不仅增长了见识,开阔了胸襟,还以此立论,生发出对于“理、事、情”、诗文之“法”等的创见。此外,叶燮还十分注重在亲身实践的游历中对自然之道的体悟,他遍游名山大川,其诗文中如黄山、泰山等曾出现过多次,许多理论的阐述就以对山川之体悟立论。叶燮通过游历对自然之道和“江山之助”有了更为深刻的理解,在仰观俯察中对自然之道加以把握,体悟自然之道所孕育的诗性智慧。恰如《原诗》中所说的“托意于仰观俯察,宇宙万汇,系之感忆,而极于死生之痛”“则其仰观俯察、遇物触景之会,勃然而兴,旁见侧出,才气心思,溢于笔墨之外”。
5.对深厚家学的积淀
叶燮家学积淀深厚,曾有叶氏一门“七叶成进士”的佳话。其父叶绍袁不仅“处世接物,坦易乐与,而是非必以直。凡地方公事不便者,力言之当事,不市恩,不避怨”[9],而且对儒道释等思想都有较深研究,编著有《午梦堂集》。其母沈宜修也工诗善文,家学传承甚好,著有《鹂吹集》,是明代吴江派代表人物沈璟的侄女。根据相关研究,“叶绍袁具有较高的佛学修养……其妻沈宜修也‘究心内典,竺乾秘函,无不披觌;楞伽维摩,朗晰大旨,虽未直印密义,固已不至河汉’。在他们夫妻二人的带动下,这个家庭‘精心禅悦,庭闱颇似莲邦’,‘儿女扶床学语,即知以放生为乐’”[10],而且“叶绍袁对苏轼特别崇慕……甚至梦寐之中都企盼能与苏轼一见……叶绍袁对杜甫诗中家国深忧的境界也感同身受”[11],这可从叶燮的思想根源于儒道释及论诗以杜甫、韩愈、苏轼为宗得到印证。并且,“吴江沈、叶二大家族于明末清初世代联姻……这种累世婚姻,将家族间的文化、教育方式打通融合,从而影响到文学创作,形成相近的文学创作模式及创作风格。沈、叶二氏才媛中创作成就较高的是沈宜修及其三女——叶纨纨、叶小纨、叶小鸾”,其中叶小纨创作有杂剧《鸳鸯梦》,“算是中国戏曲史上第一位有作品传世的女作家”[11]。无疑,世代重视读书、修身、心怀家国的深厚家学积淀及父母、兄弟姐妹博学有识、皆能赋诗善文的良好家庭氛围对叶燮日后的思想和人格的形成等都产生了巨大影响。
(二)通古今之变与成一家之言相统一的突破:叶燮诗性智慧的精神旨归
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通古今之变与成一家之言相统一,力求创新和突破,就成为叶燮诗性智慧的精神旨归。
1.通古今之变的历史意识和救弊意识合一的突破基点
叶燮通过对历代经典的积淀,面对现实中存在的是非不辨、蛊惑人心的“虚妄”之学和“遁于考订证据之学”的弊处,对俗儒、盲目复古者、随波逐流者等流弊诸多的近代之人进行了无情揭露,显示出他对于中国古代优良文学传统的深切呼唤和对于流弊的深恶痛绝。例如,叶燮在《原诗》中不无忧虑地说:“后生小子,耳食者多,是非淆而性情汩,不能不三叹于风雅之日衰也!”“今之人岂无有能知其非者?然建安、盛唐之说,锢习沁入于中心,而时发于口吻,弊流而不可挽,则其说之为害烈也。”一方面,叶燮的通古(这里的通古一是继承前人的精华,一是对前人的错误观点进行批判)都是为了解决当下亟待解决的问题,针对近代论诗者的流弊而展开的。另一方面,叶燮清醒地认识到其时论诗者与诗人的种种流弊,指出不但“乃近代论诗者……徒自诩矜张,为郛廓隔膜之谈,以欺人而自欺也。于是百喙争鸣,互自标榜,胶固一偏,剿猎成说”,而且“大抵近时诗人,其过有二:其一奉老生之常谈……其一好为大言,遗弃一切,掇採字句,抄集韵脚”。因此,他通过对古今诗歌发展的观照和对当时诗坛现实的批判,将宏阔的历史意识与强烈的救弊意识有机统一,构成其诗性智慧的突破基点。
2.成一家之言的突破意识
身处集大成的清代,面对丰富的历史文化资源,又亲睹清初诗坛的流弊与纷争,叶燮在深厚积淀的基础上大胆创新,以强烈的成一家之言的突破意识完成了对诗性智慧的建构。一是重视创作主体或审美主体之“神明”。叶燮在诗文论述中,曾多次使用“神明”。例如,《原诗》中论述创作之法时指出,“法在神明之中、巧力之外,是谓变化生心”;论述创作主体的才、胆、识、力时说“此四言者所以穷尽此心之神明”;论及鉴赏诗歌及作诗时说“诗而曰‘作’,须有我之神明在内,如用兵然”“故以我之神明役字句,以我所役之字句使事,知此,方许读韩、苏之诗”;在《集唐诗序》中论及审美客体与审美主体之关系时说,“凡物之美者,盈天地间皆是也,然必待人之神明才慧而见”,以说明审美客体的美有待于审美主体的创造性发现。综合起来,叶燮所论述的“神明”实际上就是主体的一种突破意识、创新精神。二是大力标举“成一家之言”并要求辩证对待。在《原诗》中,叶燮大力标举“成一家之言”,期望“夫作诗者,至能成一家之言足矣”,提倡“立言者,无力则不能自成一家”“欲成一家言,断宜奋其力矣”等。此外,叶燮还要求辩证对待“成一家之言”,而不能盲从和不加分辨地承袭。在《与友人论文书》中,他主张“谓文章一道不可以一律论,要各成一家之言而止”,反对“用其私智,而能成一家之言,以自鸣于古今者”,认为“仆尝论古今作者,其作一文,必为古今不可不作之文,其言有关于天下古今者,虽欲不作而不得不作,或前人未曾言之而我始言之,后人不知言之而我能开发言之,故贵乎其有是言也;若前人已言之而我模仿言之,今人皆能言之而我随声附和言之,则不如不言之为愈也”[7]。叶燮认为要“成一家之言”,就必须在通古今之变和进行深厚积淀的基础上有所创新和发现,具有强烈的自我突破意识,而不是无所依据地机械承袭前人、不知与时俱进和妄言独辟一家。
3.对至文、至境不懈追求的突破目标
在《原诗》中,有多处对于“至”的表述。例如,“天地之至神也,即至文也”“此天地自然之文,至工也”“为至文以立极”“自当求其至极者”“此天地万象之至文也”等。在《原诗》中,有人对叶燮加以发问(此处也可认为是叶燮的自我发问):“或曰:‘先生发挥理事情三言,可谓详且至矣……诗之至处,妙在含蓄无垠,思致微渺,其寄托在可言不可言之间,其指归在可解不可解之会,言在此而意在彼,泯端倪而离形象,绝议论而穷思维,引人于冥漠恍惚之境,所以为至也……若夫诗,则理尚不可执,又焉能一一征之实事者乎?’。”何谓“诗之至处”以及如何实现,那就需要通过对天地自然间的“‘意象’以及由它所形成的‘境界’的有无互立、虚实相生,一句话,赖其为可能性的言说方式;此不可言说者之被领会,又端赖领会者入于意象之境,结合自身的存在体认,而因有见无,由实至虚”[12]。需要审美主体具有超出一般人的感悟能力以感性、诗性思维去带动逻辑思维,共同参与到认识事物的活动中来,如“诗人”那样来把握“不可言之理,不可述之事”,去开拓创新,而非如“人人”一般去“一一征之实事”。例如,他对于杜甫诗歌《冬日洛城北谒玄元皇帝庙》中“碧瓦初寒外”的解读,“然设身而处当时之境会,觉此五字之情景,恍如天造地设,呈于象,感于目,会于心。意中之言,而口不能言;口能言之,而意又不可解。划然示我以默会相象之表,竟若有内、有外、有寒、有初寒。特借‘碧瓦’一实相发之,有中间,有边际,虚实相成,有无互立,取之当前而自得,其理昭然,其事的然也”。这种审美性解读充分强调主体“当时之境会”的审美体验,给了读者以想象的空间,使读者对于审美意象经由了一个“呈于象,感于目”而达到“会于心”的过程,领会到不可言说但已心领神会的艺术至境。
4.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举、理性思辨与诗性语言统一的突破方法
“诗歌是寓于形象的思维”“诗是直观形式中的真理……因此,诗歌就是同样的哲学,同样的思维,因为它具有同样的内容——绝对真理,不过不是表现在观念从自身出发的辩证法的发展形式中,而是在观念直接体现为形象的形式中”[13]。叶燮通过“立象以尽意”,在对大量具体、生动、可观、可感的形象进行感知的基础上,以具有丰富、无限意蕴的象征、审美意象来实现对思、道的言说可能性,运用比喻、象征等方法将他的理性思辨寓于诗性的语言之中,实现理论思维与形象思维并举,使其作品和论述中既有哲性之思,又富有诗性和诗意。叶燮认为,“我今与子以诗言诗,子固未能知也;不若借事物以譬之,而可晓然矣”。例如,在论述诗歌本源时,以河流、江海为喻:“从其源而论,如百川之发源……从其流而论,如河流之经行天下,而忽播为九河。”在论述唐代诗歌时,以春秋为喻:“又盛唐之诗,春花也……晚唐之诗,秋花也。”在论述诗歌创作时,以建造“大宅”为喻,并细分为基础、取材、善用、设色、变化五个步骤。可以说,运用这种形象性的比喻使得人们能够直接获取感性的信息,调动起了主体在具体语境下的想象力和感悟力,把诗性与哲性、灵性连接了起来。著名学者叶维廉就曾说,“疑问句的分析方法,与凶巴巴而来的权威性的肯定句的分析是不同的;疑问句有待读者的点头,叶燮把心感活动非常技巧地还给读者”“叶燮给了我们非常有效的说明性的批评而无碍于美感经验呈示之完整,这正是由于他了解到诗的‘机心’”[14]。
三、结语
亚里士多德在《诗学》第九章中曾说过“诗是一种比历史更富哲学性、更严肃的艺术”[15]的著名论断,指明了诗更注重表现带有普遍性的事情。别林斯基也说过:“一切感情和一切思想都必须形象地表现出来,才能够是富有诗意的。”[13]历史总是有惊人的相似,他们对诗歌与哲学、形象、想象与思维等的阐述,或许对于我们理解诗与哲学、智慧以及诗性智慧都不无裨益,这或许是一个新的课题,自不在本文论述范围之内。回归到对叶燮诗性智慧立论依据与精神旨归的分析、解读,不难看出,叶燮总是在积淀与突破之间诗意地呈现他对万事万物以及文艺创作的深刻阐述,总是力求诗与思的统一,探析诗歌与哲学、智慧的合理融合。
今天,面对如此丰富、深厚的古代诗性智慧,我们在认知、理解、现代转换的同时,更重要的是要将积淀与突破统一起来。依然引用叶燮的话来说,那就是既要明确地认识到“人之智慧心思,在古人始用之,又渐出之,而未穷未尽者,得后人精求之,而益用之出之”(《原诗》),也要学会“能因时而善变,如风雨阴晴寒暑,故日新而不病”(叶燮《黄叶村庄诗序》),更要做到“后人无前人,何以有其端绪?前人无后人,何以竟其引申乎”(《原诗》),努力实现“端绪”与“引申”的统一,尽力克服不知积淀、一味创新突破的“执其源而遗其流”和“得其流而遗其源”的错误观念,在根基深厚的积淀中突破,在有益的突破中积淀。
[1][意]维柯.新科学[M].朱光潜,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9.36.
[2]李泽厚.历史本体论[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2.130.
[3]侯传文.积淀与突破——论上古东方文化的转型[J].青岛海洋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1,(1):79.
[4]陈炎.再论“积淀说”与“突破说”——兼答朱立元、陈引驰先生[J].学术月刊,1995,(1):88.
[5][美]罗伯特·M.赫钦斯.美国高等教育 [M].汪利兵,译.杭州:浙江教育出版社,2001.164.
[6]蒋凡.叶燮和原诗[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5.13—17.
[7]吴宏一,叶庆炳.清代文学批评资料汇编[C].台北:成文出版社,1979.267,271—273.
[8]周易[M].郭彧,译注.北京:中华书局,2010.304.
[9]丛书集成续编(第124册)[G].上海:上海书店出版社,1994.770.
[10]蔡静平.明清之际汾湖叶氏文学世家研究[M].长沙:岳麓书社,2008.105.
[11]刘延乾.江苏明代作家研究[M].南京:东南大学出版社,2010.422—423.
[12]曹顺庆,李清良,傅勇林,等.中国古代文论话语[M].成都:巴蜀书社,2001.153—154.
[13]中国社会科学院外国文学研究所外国文学研究资料丛刊编辑委员会编.外国理论家作家论形象思维[Z].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79.56—58.
[14]叶维廉.中国诗学[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92.8.
[15][古希腊]亚里士多德.诗学[M].陈中梅,译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8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