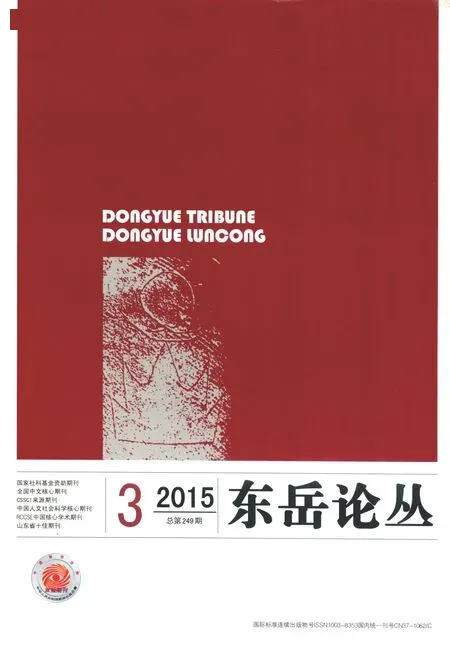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2015-03-22唐明贵
唐明贵
(聊城大学 哲学系,山东 聊城 252059)
苏轼《论语说》的诠释特色
唐明贵
(聊城大学 哲学系,山东 聊城 252059)
《论语说》初成于贬官黄州期间,在诠释过程中,苏轼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呈现出了疑经改经、杂采众说、阐发性命之说和掘发政治意蕴的诠释特色,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苏轼;论语说;诠释特色
苏轼(1037年~1101年),字子瞻,号“东坡居士”,累官至端明殿学士兼翰林侍读学士,礼部尚书。他于儒家经典多有涉猎,尤其是对《论语》颇有研究。贬官黄州期间,他就曾撰成《论语说》初稿。《黄州上文潞公书》说:“到黄州,无所用心,辄复覃思于《易》、《论语》。端居深念,若有所得,遂因先子之学,作《易传》九卷。又自以意作《论语说》五卷。”①迁居海南期间,完成定稿。《答李端叔三》中有言:“所喜者,海南了得《易》、《书》、《论语》传数十卷,似有益于骨朽后人耳目也。”②书成后,自宋及明初,该书一直流传于世。明正统六年(1441年),由杨士奇清点当时明皇室内阁藏书而编修的《文渊阁书目》著录“《论语东坡解》一部二册”。及至万历丁酉(1597年),焦竑刻《两苏经解》时,已不见有《论语说》了,其序称“《子瞻论语解》,卒轶不传”③。可见此书在明万历时期已经难觅了,因此《两苏经解》中没有苏轼《论语说》。从清人张佩纶以至今人卿三祥、马德富、舒大刚、谷建,都有辑文问世,且舒氏还将卿氏、马氏三人所辑合并于《三苏全书》中。④兹以这些辑本为据,探研苏轼诠释《论语》的特色。
一、疑经改经
在中国经学发展史上,由中唐开始,出现了一股疑古惑经思潮,尤其是在宋仁宗庆历前后达到了新高潮,由疑古惑经逐步发展到疑经改经。苏轼也深受其影响,在《论语说》中,他对《论语》经文提出了质疑,并作了某些改动。如《阳货》“鄙夫可与事君也与哉?其未得之也,患得之。既得之,患失之。苟患失之,无所不至矣”,苏轼注曰:“‘患得之’当云‘患不得之’,阙文也。”此说得到了后人的认同,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七指出,“东坡以‘患得之’当为‘患不得之’,盖阙文也。予以为然。”⑤杨伯峻《论语译注》“患得之”下出校记曰:“当作患不得之。”又进而解释曰:
王符《潜夫论·爱日篇》云:“孔子疾夫未之得也,患不得之;既得之,患失之也。”可见东汉人所据的本子有“不”字。《荀子·子道篇》说:“孔子曰,……小人者,其未得也,则忧不得;既已得之,又恐失之。”(《说苑·杂言篇》同)此虽是述意,“得”上也有“不”字。宋人沈作喆《寓简》云:“东坡解云:‘患得之’当作‘患不得之’”,可见宋人所见的本子已脱此“不”字。⑥
又,《子张》篇“曾子曰:‘吾闻诸夫子:孟庄子之孝也,其他可能也;其不改父之臣与父之政,是难能也’”,苏轼怀疑其中的“孟庄子”是为“孟献子”,王若虚对此提出了批评,《滹南遗老集》卷七曰:“东坡曰:‘闻孟献子之孝,不闻庄子也。’遂疑为‘献’字之误。夫圣人以为孝则固孝矣,而必求他证而后信,不亦过乎?”⑦
除改易经文外,苏轼还对《论语》的章句提出了自己的意见。如《子罕》最末两章“可与共学”、“唐棣之华”原本都合为一章作解。《朱子语类》卷三十七朱熹曰:“汉儒有反经之说,只缘将《论语》下文‘偏其反而’误作一章解,故其说相承曼衍。且看《集义》(指《论语精义》)中诸儒之说,莫不连下文。独是范纯夫不如此说,苏氏亦不如此说,自以‘唐棣之华’为下截。”即从苏轼、范祖禹始,就以“唐棣之华”为界,将传统延续下来的一章分为两章。朱熹认同这种章句安排,并在《论语集注》中加以采用,沿用至今。又,《尧曰》首章,苏轼注曰:“此章杂取《大禹漠》、《汤诰》、《泰誓》、《武成》之文,而颠倒失次,不可复考。由此推之,《论语》盖孔子之遗书,简编绝乱,有不可知者。如周八士,周公语鲁公,邦召夫人之称,非独载孔子与弟子之言行也。” 此说也得到了后人的认可。朱熹《论语或问》卷二十曰:“苏氏疑此章有颠倒失次者,恐或有之。”王若虚《滹南遗老集》卷七曰:“予谓东坡之说为近人情,故从之。”⑧
由此可见,苏轼对《论语》经文章句的改易,大都得到了后人的赞同,并对后世产生了一定的影响。
二、杂采众家之说
苏轼治学主张会通诸家,尤其倡导儒佛道三家汇合。在苏轼看来,儒佛道三教宗旨无异,必定会殊途同归。他说:“孔老异门,儒释分宫,又于其间,禅律相攻。我见大海,西北南东,江河虽殊,其至则同。”⑨为此,他首先用道家之说与《周易》、《论语》等儒经互相发明, 以论证二者之间的一致性。苏轼说:“道家者流,本出于黄帝老子。其道以清静无为为宗,以虚明应物为用,以慈俭不争为行。合于《周易》‘不思不虑’,《论语》‘仁者静寿’之说。”⑩不仅如此,苏轼还认为儒、佛之间亦有其一致之处。他说:“宰官行世间法,沙门行出世间法;世间即出世间,等无有二。” “儒释不谋而同”,“相反而相为用,儒与释皆然。”苏轼这种杂糅佛老的思想在《论语》诠释中多有体现。如《为政》“《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章,苏轼注曰:
《易》称:“无思”,“无为”,“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凡有思者,皆邪也,而无思则土木也。何能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此孔子之所尽心也。作诗者未必有意于是,孔子取其有会于吾心者耳。孔子之于《诗》,有断章之取也。
这里,苏轼阐释了孔子用“思无邪”三字来评价《诗经》的真正命意。因为人非土木,不能无思,孔子之所“尽心”处,正在于如何能使“有思”之人无“邪思”。不过,在王若虚看来,“苏子此论流于释氏,恐非圣人之本旨”。
苏轼在其他地方对此段文字的解释更是融儒释道为一体,如他在《思无邪斋铭(并叙)》说:“东坡居士问法于子由。子由报以佛语,曰:‘本觉必明,无明明觉。’居士欣然,有得于孔子之言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无思则土木也,吾何自得道,其惟有思而无所思乎?于是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于是得道,乃名其斋曰‘思无邪’,而铭之曰:‘大患缘有身,无身则无病。廓然自圆明,镜镜非我镜。如以水洗水,二水同一净。浩然天地间,惟我独也正。’”在《虔州崇庆禅院新经藏记》中,苏轼又说:“吾非学佛者,不知其所自入,独闻之孔子曰:‘《诗》三百,一言以蔽之,曰:思无邪。’夫有思皆邪也,善恶同而无思,则土木也,云何能便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乎!呜呼,吾老矣,安得数年之暇,托于佛僧之宇,尽发其书,以无所思心会如来意,庶几于无所得故而得者。谪居惠州,终岁无事,宜若得行其志。而州之僧舍无所谓经藏者,独榜其所居室曰‘思无邪斋’,而铭之致其志焉。”这里,苏轼指出,要想做到“有思而无邪,无思而非土木”,只有“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摄心正念,而无所觉”,才能最终“得道”。其中的“幅巾危坐,终日不言。明目直视,而无所见”是借用道家的养生方法;“摄心正念,而无所觉”一语来自于禅宗“无念为宗”。《坛经·定慧品》云:“无念者,于念而不念。”又云:“于一切境上不染,名为无念。”以无念为宗,无念即正念。无思无为,无念无心,一切顺其自然,物我为一,正所谓“寂然不动,感而遂通天下之故”,由此得道。我们从中不难发现,苏轼从儒家出发,尝试着借用道家的方法来印证佛家的“本觉必明,无明明觉”思想,这不仅反映了其试图吸取儒、释、道三家的思想来解决“有思”、“无思”问题的努力,也反映了其思想的驳杂与兼容。
另外,在《论语说》,苏轼还引用了他家学说以诠释之。如《学而》“弟子入则孝”章,苏轼注曰:“泛爱众而亲仁。仁者之为亲,则是孔子不兼爱也。”这里的“兼爱”显然是承受了墨家思想的影响。《宪问》“士而怀居,不足以为士矣”章,苏轼注云:“管仲曰:‘畏威如疾,民之上也。从怀如流,民之下也。’”这句话出自《国语·晋语》,是姜齐引用管仲的话。管仲是早期法家的代表人物之一,苏轼引用其说来解释经文,实际上就把早期法家的思想引入了对《论语》的诠释中。
366 Retrospective analysis on influencing factors of intraoperative indexes of robot-assisted laparoscopic radical prostatectomy
三、阐发性命之说
北宋时期,为了复兴儒学,王安石等人把古礼中的内圣方面加以发挥,开创了儒家的性命之学,他们希望以此来提高儒家思想形而上的水平,使之更加精深,从而提高儒家思想的吸引力,对抗佛教的进攻。后来由二程等理学家进行开拓与发挥,使之成为理论焦点。受时代思潮的影响,苏轼在《论语说》中也对性命之说做了探讨,并提出了独到的见解。
首先,性是所以成就善者,但善不是性。在诠释《阳货》篇“性相近也,习相远也”及“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章时,指出:“《易》曰:‘一阴一阳之谓道。继之者善也,成之者性也。’成道者性,而善继之耳,非性也。性如阴阳,善如万物。万物无非阴阳者,而以万物为阴阳则不可,故阴阳者视之不见,听之不闻,而非无也。今以其非无即有而命之,则凡有者皆物矣,非阴阳也。”这里,苏轼用了一个形象的比喻:万物都是由阴阳构成,但是万物并不是阴阳。善与性的关系亦如此。在苏轼看来,性是纯然的本体,“视之不见”,“听之不闻”,是无形的,但不能说没有,而善或恶则是有形的,这种无形不能为有形所代替。
其次,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苏轼进而指出:“性可乱也,而不可灭,可灭非性也。人之叛其性,至于桀、纣、盗跖至矣。然其恶必自其所喜怒,其所不喜怒,未尝为恶也。故木之性上,水之性下。木抑之,可使轮囷下属,抑者穷,未尝不上也。水激之,可使喷涌上达,激者衰,未尝不下也。此孟子之所见也。孟子有见于性而离于善。”“人性为善,而善非性也。使性而可以谓之善,则孔子言之矣。苟可以谓之善,亦可以谓之恶。故荀卿之所谓性恶者,盖生于孟子;而扬雄所谓善恶混者,盖生于二子也。性其不可以善恶命之,故孔子之言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夫苟相近,则上智下愚曷为不可移也?曰:有可移之理,无可移之资也。”他否定了历史上曾出现过的性善论、性恶论、性善恶混论、性三品说,指出人性不能有善恶,而只能趋向于善恶。
最后,性同而才异。在苏轼看来,过去儒者对“性”的理论之所以莫衷一是,原因就在于他们把“性”与“才”混为一谈。他说:“昔之为性论者多矣,而不能定于一。始孟子以为善,而荀子以为恶,扬子以为善恶混。而韩愈者又取夫三子之说,而折之以孔子之论,离性以为三品,曰:‘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以为三子者,皆出乎其中,而遗其上下。而天下之所是者,于愈之说为多焉。嗟夫,是未知乎所谓性者,而以夫才者言之。”在苏轼看来,性对于每个人而言都是一样的,并没有什么圣人性善和小人性恶之分。善恶仅是性所能之,而非性所固有。人类的“性”是一致的,但“才”则有高下。他说:“夫性与才相近而不同,其别不啻若白黑之异也。圣人之所与小人共之,而皆不能逃焉,是真所谓性也。而其才固将有所不同。今夫木,得土而后生,雨露风气之所养,畅然而遂茂者,是木之所同也,性也。而至于坚者为毂,柔者为轮,大者为楹,小者为桷。桷之不可以为楹,轮之不可以为毂,是岂其性之罪耶?天下之言性者,皆杂乎才而言之,是以纷纷而不能一也。”苏轼认为孔子中人以上、中人以下,以及上智下愚等说法,都是就才而言,并非言性。“孔子所谓中人可以上下,而上智与下愚不移者,是论其才也。而至于言性,则未尝断其善恶,曰‘性相近也,习相远也’而已。”因此,讨论人性问题,首先要辨明性与才之不同。
总之,苏轼否定了人性先天就有善恶的说法,并试图用才与性相配合,对先儒的人性论进行整合,这对于中国传统人性思想的发展,无疑具有重要的意义。
四、阐发《论语》中的政治意蕴
苏轼本人为官四十载,关心国家治乱,这在《论语》诠释中也多有阐发。如《八佾》篇“定公问:‘君使臣,臣事君,如之何?’孔子对曰:‘君使臣以礼,臣事君以忠’”章,苏轼解曰:
君以利使臣,则其臣皆小人也。幸而得其人,亦不过健于才而薄于德者也。君以礼使臣,则其臣皆君子也,不幸而非其人,犹不失廉耻之士也。其臣皆君子,则事治而民安。上有廉耻,则临难不失其守。小人反是。故先王谨于礼。礼以钦为主,宜若近于弱,然而服暴者,莫若礼也;礼以文为辞,宜若近于伪,然而得情者,莫若礼也。哀公问:(略)不有爵禄刑罪也乎?何为其专以礼使臣也!以爵禄而至者,贪利之人也,利尽则逝矣。以刑罚而用之者,畏威之人也,威之所不及则解矣。故莫若以礼。礼者,君臣之大义也,无时而已也。汉高祖以神武取天下,其得人可谓至矣。然恣慢而侮人,洗足箕踞,溺冠跨项,可谓无礼矣。故陈平论其臣,皆嗜利无耻者,以是进取可也,至于守成,则殆矣。高帝晚节不用叔孙通、陆贾,其祸岂可胜言哉!吕后之世,平、勃背约,而王诸吕几危刘氏,以廉耻不足故也。武帝踞厕而见卫青,不冠不见汲黯。青虽富贵,不改奴仆之姿;而黯社稷臣也,武帝能礼之而不能用,可以太息矣。
苏轼在这段文字中,阐发了礼为君臣之间之大义的政治原则。君以礼使臣,则臣要么是君子,要么是廉耻之士,如此一来,则临难不失其守,事治而民安。君以利使臣,则其臣要么是小人,要么是健于才而薄于德者,如此一来,则临难失其守,民乱而国危。在他看来,奔着爵禄而来的臣子,是贪利之小人,利尽则人去;迫于刑罚而至之臣,是畏威之人,一旦刑威式微,则会离散而逃。因此,只有用礼来处理君臣之间的关系,才能达到君安臣忠,国家兴旺。他还借用历史上汉高祖和汉武帝的例子对此予以了证明。
有大人之事,有小人之事。愈大则身愈逸而责愈重,愈小则身愈劳而责愈轻。綦大而至天子,綦小而至农夫,各有其分,不可乱也。责重者不可以不逸,不逸则元以任天下之重。责轻者不可以不劳,不劳则元以逸夫责重者。二者譬如心之思虑于内,而手足之动作步趋于外也。是故不耕而食,不蚕而衣,君子不以为愧者,所职大也。自尧、舜以来,末之有改。后世学衰而道弛,诸子之智不足以见其大,而窃见其小者之一偏,以为有国者皆当恶衣粝食,与农夫并耕而治,一人之身而自为百工。盖孔子之时则有是说矣。夫樊迟亲受业于圣人,而犹惑于是说,是以区区焉欲学稼于孔子。孔子知是说之将蔓延于天下也,故极言其大而深折其辞,以为:“上好礼则民莫敢不恭,上好义则民莫敢不服,上好信则民莫敢不用情。夫如是,则四方之民襁负其子而至矣。焉用稼?”而解者以为:礼、义与信,足以成德。夫樊迟之所为汲汲于学稼者,何也?是非以谷食不足而民有苟且之心以慢其上为忧乎?是非以人君独享其安乐而使民劳苦独贤为忧乎?是非以人君不身亲之则空言不足劝课百性为忧乎?是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君子以礼治天下之分,使尊者习为尊,卑者安为卑,则夫民之慢上者非所忧也。君子以义处天下之宜,使禄之一国者不自以为多,抱关击柝者不以为寡,则夫民之劳苦独贤者又非所忧也。君子以信一天下之惑,使作于中者必形于外,循其名者必得其实,则夫空言不足以劝课者又非所忧也。此三者足以成德矣,故曰:三忧者,皆世俗之私忧过计也。
苏轼在这里翻版了《孟子·滕文公上》中的“劳心者治人,劳力者治于人。治于人者食人,治人者食于人。天下之通义也”的说法,指出,劳心者“身愈逸而责愈重”,劳力者“身愈劳而责愈轻”,二者各有其分,绝不可乱。统治者只要“以礼治天下之分”,“以义处天下之宜”,“以信一天下之惑”,则足以臣服四海。
由于具有上述诠释特色,所以尽管苏轼《论语说》早已亡佚,但在《论语》诠释史上具有一定的地位和影响。
首先,在诠释过程中,苏轼主要是利用《论语》中的某些思想资料,结合时代主题和自己的心得体会,融会贯通,综合创新,进行创造性的发挥,旨在打破成见、自出新意,对于阐述己意无关的字词之义的训诂、名物制度的考证则少有关注。在多数情况下,苏轼仅仅将《论语》经文作为阐发个人思想的引子,所引申和生成的思想虽可自成体系,但业已脱离经典原文,所表达的只是苏轼本人对于当时社会与人生、历史与现实问题的种种看法。这种做法,体现了宋学的基本精神。清儒钱大昕曾从学术发展的角度对此予以了高度评价:“当宋盛时,谈经者墨守注疏,有记诵而无心得,有志之士若欧阳氏、二苏氏、王氏、二程氏,各出新意解经,蕲以矫学究专己守残之陋。”正是这种新的治学风气的出现,才使宋代义理之学得以蓬勃发展。
其次,由于苏轼博综淹贯,谙熟经史,识见超卓,故其经解颇有独到、高妙之处,往往能超越汉唐旧有注疏而别出新见。如苏轼在当时孟子学说受到普遍追捧的情况下,面对日益强大的理学,不盲目附合,以与理学迥异的性命论审视孟子的人性论,批评孟子的人性论,在性与善、性与才的问题上提出了自己的见解。无怪乎苏门秦观曾评价说:“苏氏之道,最深于性命自得之际。”又,在《论语》诠释中,他还不遗余力地掘发其中的政治意蕴,在治国理民方面为统治者出谋划策,充分拓展儒家的外王之学。朱熹曾说:“苏氏之学,上谈性命,下述政理。”上述所为,不仅表现出苏轼在重构儒学体系时特立独行及其独立思考的精神,而且也反映出宋代文化发展多样化的特色。后世学者,对于苏轼的“驳杂” 虽多有抨击责难,但对其在《论语》学方面的成就与造诣也不得不予以肯定。朱熹在论及《论语说》时,就曾指出:“东坡天资高明,其议论、文词自有人不到处,如《论语说》,亦煞有好处。”朱熹的《论语》著作之于苏轼《论语说》,在总共20篇中,只有《先进》和《微子》两篇未有论及;在总共499章(节)中,共有62章(节)论及,占总数的12%,有12章(节)所解为朱子《论语集注》直接征引;其中除了少数予以批评外,绝大多数都是肯定、借鉴和吸取的内容,内容涉及章句、训诂、考证和旨意等多个方面。因此,我们可以说,苏轼《论语说》对朱熹《论语》学体系的形成有着直接的影响。
[注释]
③焦竑:《两苏经解·序》,《两苏经解》, 明万历二十五年毕三才刻本。
④舒大刚:《苏轼〈论语说〉流传存佚考》,《西南民族学院学报》, 2001年第6期。
⑥杨伯峻:《论语译注》,北京: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186-187页。
[责任编辑:杨晓伟]
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中国‘四书’学史”(13&ZD060)和国家社科基金项目“宋代《论语》诠释研究”(11BZX047)的阶段性成果之一。
唐明贵(1971—),男,聊城大学哲学系教授。
B244
A
1003-8353(2015)03-0107-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