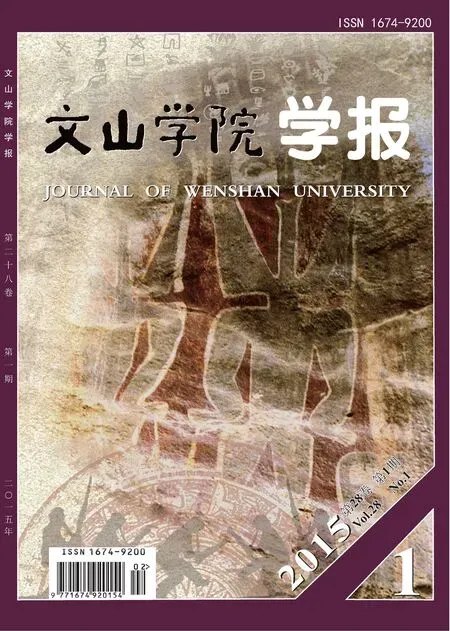广南方言的形成与归属
2015-03-21牟成刚
牟成刚
广南方言的形成与归属
牟成刚
(文山学院 人文学院 ,云南 文山 663000)
广南方言的形成与汉族移民的迁入有着重要的关系。根据移民史料记载,该方言应滋生于宋代,发展形成于明代,体系成熟于清代。根据调型来看,广南方言当属云南方言滇中片,但其词汇、语法及语音的部分特点又与滇中片存在一定的差异,联系广南与广西的历史关系来看,广南方言在早期很可能会受到广西汉语方言一定程度的影响。
广南方言;移民;形成;调型;方言归属
广南方言是典型的西南官话,1989年的《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把广南方言划归云南汉语方言滇南片,2009年的《西南官话分布区(稿)》也持此观点。笔者认为这有待商榷,因为无论从听觉还是语言事实方面,都能够明显感觉到广南方言与滇南片其他方言的不同。一般认为,西南官话的形成与移民和早期的行政格局关系密切,广南方言自然也不例外,本文将从语言、移民和早期行政格局的角度,对广南方言的形成和归属重新进行探讨。
一 、汉族移民与广南方言的形成
广南方言的形成和广南地区的汉族移民紧密相关。广南境域古属“西南夷”部分,据《广南县志》记载:“公元前3世纪,境内及附近地区为句町部族居住地,以僚、濮为主的部族组成句町国。”[1] 9西汉元鼎六年(公元前111年),汉武帝开南中,在今广南设置句町县,汉昭帝始元4年(公元前83年),朝廷册封句町部族首领毋波为句町王。此后,直至宋、元之前,广南的建制及管理者虽一直受历代朝廷册封,但朝廷因对广南实施的都是羁縻政策,很少派汉族人到此管理视察,因此,这段时间进入广南的汉族人数是很有限的。即使有少量汉族零星流落入境,也会很快就融入当地的土著民族之中。没有一定规模的汉民族迁入,汉语方言自然是难以形成的,这样看来,宋、元之前在广南显然不具备汉语通行的条件。
宋代是汉民族以驻军的形式小规模落籍广南的开始,地理上呈点状式分布。宋仁宗皇祐五年(1053年),宋朝枢密院副使狄青率宋军于广西南宁昆仑关与“南天国”仁惠皇帝侬智高起义军大战,“狄青追智高至科岩(即今广南县的阿科一带)”[2] 23,最终“狄青宣抚广南,平侬智高”[3] 13,侬军失利退至特磨道(即今广南)。至和二年(1055年),朝廷再派杨文广等率军进入特磨道追歼侬军获胜,侬智高败走大理国,宋军留下镇守特磨道。此时,宋军中的部分汉族官兵领命从俗,落籍广南,繁衍宗支,是为广南最早的汉族先民。时至现在,广南尚有“宝月关”“六郎城”“六郎洞”等历史遗迹。宋代汉民族的迁入给广南带来了汉语,但因落籍的汉族不多且呈点状分布,当时汉语仅在落籍汉族内部及与之相近而受影响的周边少数民族小范围内得以使用,可这预示着汉语在广南开始滋生出现。
汉民族较大规模迁入广南居住的时间当在明代,形式上以驻军屯垦和官府有组织的移民迁入为主。根据《明史》记载,明洪武十四年(1381年),朱元璋令傅友德为征南将军,蓝玉、沐英为左右副将军,统率大军30万人南征云南,平定云南后,明朝廷便在云南实行卫所屯田制度,整个云南建立二十二卫,广南卫便是其中之一。这些戍守边疆之兵及其家属子女就地屯田,不能随便离开,于是广南卫和其他二十一卫一样,汉族军民便因此而就地逐渐落籍下来。明太祖朱元璋命沐英镇守云南。洪武十六年(1383年),沐英为促进云南地区的开发,到江南征召了一大批工匠到云南,据《滇粹·云南世守黔宁王沐英附后嗣略》记载,这次官府组织的移民数量多达250余万人,被分配到包括广南在内的二十二个卫,从而使得广南的汉族移民进一步得到充实。沐英重视用兵边疆,开发云南,据《明史·沐英传》记载,沐英在滇百业俱举,广南卫开垦荒田40578亩,人民安居乐业。据清李熙龄《广南府志》记载,洪武二十六年,维摩十一寨叛乱,后广南侬氏家族聚部多次起事,沐英子沐昂、沐春多次出兵平定安抚,汉军因此又再次部分落籍镇守[2] 24-25。此外,据明正德《云南志》卷二《烈女传》记载,永乐初年,朝廷曾调云南广南卫的一些军队去戍守交趾(今越南),后来交趾恢复独立,明朝令原隶属广南卫的一些军队撤回昆明,但一部分汉兵因家属已落籍广南而选择重回广南定居。汉族军民屯田戍边,使得大量汉族进入广南并定居下来。明朝后期,军屯制度渐废,广南诸多军户便落籍为民。明代的军民屯田制度,为当时的汉族与当地少数民族杂居提供了可能。同时,明代汉族或军或民大批量迁入广南定居,使得当地汉语的地位得到了巩固并推广,可以说,这一时期是汉语在广南的发展成形时期。
但广南因地广人疏,清代至民国初年,汉民族仍大批量地不断涌入广南,但这时期的移民主要以民间的自发搬迁为主。据清李熙龄《广南府志》记载,广南幅员辽阔,周遭二千余里,“楚、蜀、黔粤之民,携挈妻孥,风餐露宿而来,既视瘴乡如乐土,故稽烟户,不止较当年倍蓰”[2] 54。又,民国《广南县志稿》第五册《农政志·垦殖》记载:“在二三百年前,汉族人至广南者甚稀,其时分布于四境者,附郭(按:府城周围)及西乡多侬人(壮族支系),南乡多倮倮(彝族),北乡多沙人(壮族的另一支系)。其人滨河流而居,沿河垦为农田,山岭间无水之地,尽弃之不顾。清康、雍以后,川、楚、粤、赣之汉人则散于山岭间,新垦地以自殖,伐木开径,渐成村落。汉人垦山为地,初只选肥沃之区,日久人口繁滋,由沃以及于脊,入山愈深,开辟越广。山间略为平广之地,可引水灌田者,则垦之为田,随山屈曲,垄峻如梯,田小如瓦。迨至嘉、道以后,黔省农民又大量迁入,于是垦之地数以渐增,所遗者只地脊水枯之区,尚可容纳多数人口。(后至之)黔民无安身之所,分向于干瘠之山,辟草莱以立村落,斩荆棘以垦新地。”由此可见,清代有大量的汉族从不同的地区涌入。他们当初看重的是广南地广人疏、偏安一隅的环境,后人口繁滋,便逐渐向山里迁居,从而与少数民族形成“大杂居、小聚居”的居住格局,进一步推进了汉族之间以及汉族与少数民族之间的交往。同时,经商迁入的汉人为了互相联系,支持照顾,建立了相应的同乡会馆,根据《广南县志》记载,当时重要的会馆有五个,即“川黔会馆”“岭南会馆”“江西会馆”“三楚会馆”“两湖会馆”。各会馆招收同籍人入馆并在当地经商定居。总体上看,清至民国初年,各地汉族因各种原因迁聚广南,聚群性地散居各地,致使原不同地区的汉语方言相互影响、相互融合,并最终形成体系成熟稳定而且具有鲜明特色的广南汉语方言。
此后,民国中晚期至今,虽也有部分汉族移民迁入广南,但因规模不大,数量有限,且居住地相对不固定,故对业已形成且体系成熟的广南汉语方言系统并不会产生太大的影响。
二、 广南方言的特点与归属
(一)已有的观点及其局限
广南方言属典型的西南官话。1989年出版的《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把云南方言划分为滇西、滇南、滇中、滇东北共4片,广南方言属于滇南片[4] 8。最近,李蓝在2009年发表的《西南官话的分区(稿)》把云南片划分为滇中、滇西和滇南共3个小片,广南方言仍属于滇南小片[5] 79。但通过对比分析,笔者认为,把广南方言划归滇南片有待商榷。
根据《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的分片,滇南方言片的地理范围主要指红河州、文山州各县市的方言。语音特征上,滇南方言“这一片多数县、市的上声为中平调(33)或半高平调(44)。而去声为低降调(211),这是滇南方言区别于其它三片的显著特点之一”[4] 16。且不说把去声调值211看成是滇南方言区别于其他三片的显著特点之一的观点是否恰当①,单就广南方言的声调来说,就没有一条声调语音特征是符合滇南片方言的语音特点的。滇南方言的上声调型为平调型可以说是其重要的语音特征之一,但广南话的上声调读高降调型(53调值),因此,从调型上把它划归云南方言滇南片显然是不恰当的②。其实,关于这一点,《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也是有所觉察的,如该书在滇南方言片的语音特点部分就提到,本片“除了河口县城区通行粤语,广南县方言语音较为特殊外,其它各县的语音较接近”[1] 16。
(二)广南方言的特点及其与滇南片方言的差异
实际上,广南方言无论语音、词汇还是语法上都与滇南方言具有一定的差异。分述如下:
首先,语音方面。中古日母字在广南方言今读有着较为规律的文白异读现象,文读音为零声母,白读音为z母,但蒙自、建水、文山、马关等这些具有典型滇南方言特征的方言点中一般都只读z母。例如“人”字,广南话白读音为in31,文读音为zən31,但建水话就只读zen42。同时,广南方言上声调的调型和调值与典型的滇南方言不同,典型的滇南方言上声调是平调型(中平调44或半高平调33),广南方言是降调型(高降调53)。
其次,词汇方面。广南方言有一些比较独特的词汇,非常能体现当地的方言特色。例如,文山、建水等称妻子为“婆娘”,但广南方言称“妻子”为“老婆”。此外,广南方言称“杀”为 “铴”(“杀鸡”当地称“铴鸡”),也是其他典型的滇南方言所不具备的。
最后,语法方面。广南方言有一个常用的助词“歇”,表示动作的完成和性质状态的实现。例如,文山、建水等说“吃了饭”“烧红了”,但广南话称“吃歇饭”“烧红歇”。同时,普通话中的“很”可以放在“得”字后面做补语,构成“形容词+得+很”的结构,形容程度高。但这一结构在广南话中完全可以用与之相应的“形容词+不+得”的否定形式代替,例如:苦得很=苦不得(意思是“很苦”或“非常苦”)。此外,广南有一个表示强调肯定的语气词“啂”,如“这本书是他呢啂”(肯定这本书是他的,而不是别人的)等。
据此可以看出,相对滇南片其他方言点来说,广南方言以上这些特点是比较具有地域特色的,即典型的滇南片方言点中基本上不具有这些特征。同时,广南方言也不具备滇南方言的突出特征(如上声调读平调型,调值为中平33调或半高平44调)。这样看来,把广南方言划归云南方言的滇南片是值得商榷的,应该重新考虑其划片归属。
(三)新的划片归属及理由
李蓝根据声调的类型把云南方言分为滇中、滇南和滇西3个方言小片,并指出滇中小片以昆明话为代表(阴平44、阳平31、上声53、去声212),滇西小片以保山话为代表(阴平32、阳平44、上声53、去声25),滇南小片以开远话为代表(阴平55、阳平42、上声33、去声12)[5] 79。广南话的调值是阴平44、阳平31、上声53、去声212,无论从调值还是调型来看,广南话与滇中片的昆明话都是一致的,而与滇西的保山型和滇南的开远型相去甚远。因此,根据这一标准,广南方言显然应该划归滇中片才合理。
《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中从声母、韵母和声调三方面对滇中、滇南、滇西、滇东北4个方言片的特点进行了归纳和界定。上面从声调的角度已经论述证明了广南方言属滇中方言片的昆明型。根据《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的分析,下面再从声母和韵母的角度,分析广南方言与云南方言滇中方言片和滇南方言片的关系,看它们是否能成为划片的标准。
首先,声母方面。滇中方言片和滇南方言片声母上的特点各有4条,其中能分n、l和有v声母是二者和广南方言共同具有的特点。滇中方言片和滇南方言片的不同点是:第一,滇中方言片绝大多数县市能分ʦ、tʂ组声母,滇南方言片则恰好相反,即绝大多数县市ʦ、tʂ组声母合流读ʦ组声母;第二,滇南方言片的文山一带有ŋ声母③,滇中方言片则没有ŋ声母。广南方言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今读合流为ʦ组声母和保留有ŋ声母,表面看好似与滇南方言更密切,但它与滇中方言的区别也是可以解释的。根据研究,“中古精知庄章四组声母合流为ʦ组是其在西南官话中最为晚近的历史层次类型”[6] 81,tʂ、ʦ组合流读ʦ组是语音演变的一大趋势,符合语言演变的经济原则,滇中方言片现在“近半数县、市有z声母”[4] 15就体现了这一演变趋势。滇南方言除红河州的河口话、泸西话和文山州的丘北话之外,其他方言点今读都有z声母,但据《云南方言调查报告》记载,调查于1940年的文山城内话tʂ、ʦ组两分,有ʐ声母而无z声母。滇南方言ŋ声母的存在主要为古音残留,因为相对于滇中来说,滇南一带更靠近南方,传统中的南方地理环境比较落后闭塞,语言的演变相对于滇中一带来说要慢一些,而广南更是直接与广西连壤,故其保留古音也就无可厚非了。其实,根据葛中选《泰律篇》(1618年)的记载,当时滇中方言通海话疑母尚有残存读ŋ声母的现象,直至清代沾益人马自援著的《等音》(1673年)中“疑母[ŋ]残余继续存在”[7] 245。可见, 中古疑母读ŋ声母在滇中方言今读中完全消失的现象也是晚近演变的结果。因此,从声母的区别角度来看,滇南方言片和滇中方言片并没有一个严格的区别标准,故广南方言自然也就不能根据《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中声母的片区特点来判定其归属。
其次,韵母方面。绝大多数县市无撮口呼、无卷舌音韵母ɚ是滇南方言片和滇中方言片的共同特征。它们不同点是,滇南方言绝大部分能分“单、当”和“弯、汪”的读音(文山话:单з55≠当tŋ55;弯з55≠汪uŋ55),而滇中方言约半数左右的县市不能分这两对字的读音(昆明话:单з44=当з44;弯з44=汪з44)。广南方言能分这两对字的读音(单44≠当taŋ44;弯u55≠汪uaŋ55),表面看似与滇南方言片同而与滇中方言片异,实际上,这一条同样不能成为滇中方言片和滇南方言片划分的标准。因为鼻音韵尾的弱化演变在汉语方言中也是比较普遍的,特别是云南汉语方言因受少数民族语音的影响,鼻韵尾弱化的情况就更加突出了。至今,滇南方言片尚有个旧、蒙自、建水、屏边等对上面的两对字都不分,开远能分“单、当”二字的读音,但不能分“弯、汪”二字的读音,元阳、红河、绿春能分“弯、汪”二字的读音,但不能分“单、当”二字的读音,这样看来,滇南片方言也有约一半左右的方言点不能分(或不能全分)“单、当”和“弯、汪”这两对字的读音。因此,能否区别“单、当”和“弯、汪”这两对字的读音显然不能作为区别滇南方言片和滇中方言片的标准,广南方言当然也就不能以此来判断自己的归属。
综合来看,《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中关于云南汉语方言的内部方言片区划分标准中,所列的声母和韵母标准是共性较多而差异较少,因此把声母和韵母拿做划分片区的标准显然是不太好把握的,即使有个别声韵母特征相对突出,那也是较为晚近方才发生的语音演变结果,用之做方言的划片标准并不恰当。这样一来,能做云南方言内部划片的唯一标准那就是声调的调型了。在云南的汉语方言区域之内,从上面的调型分析来看,广南方言的调型与昆明型一致,故广南方言应划归云南汉语方言中的滇中方言片。
三、余论
现把广南方言划归云南汉语方言的滇中方言片,首先是根据调型调值,其次是照顾现行的行政地理区划,再次也考虑到了未来本地方言的发展趋势。但值得注意的是,广南方言相对滇中方言片来说,它还具有自己的一些方言特点,如上面所列的中古日母字在广南方言今读中有着较为系统的文白异读,保留有ŋ声母。此外,还有“妻子”称“老婆”、“杀”称“铴”、有助词“歇”等等,这些都是滇中方言片很少或根本就不具备的方言特点。笔者认为,这或许与广南特殊的地理位置和早期的行政归属有一定的关系。
广南的地理位置与广西接壤,历史上与广西关系密切,据《广南府志》记载,“广南处滇极边,唐宋时隶邕州(即今之南宁)羁縻”,直至元代方才划归云南行省管辖。境内的西洋江、驮娘江和清水江属珠江流域水系,它们往东南汇入右江直通南宁。西洋江为广南最大水系,东汇右江,可以直达两粤,旁通黔楚,如果“顺流而下,三四程即抵南宁”[2] 31;境内宝月关,石磴嵯峨,为两粤要冲,从“维摩(元置广南维摩州)取道广西州治,直走会城,仅七百里”[2] 32。由此而观,广南到广西的水陆交通都极为方便,宋代狄青率部平息侬智高起义,便是从广西进入广南的。吴三桂引清军入关,会同多尼等进攻南明,明朝永历皇帝朱由榔(1623~1662年)携带同胞妹妹安化郡主由广东肇庆西逃至广南,中间也是途径广西而来的,安化郡主病逝广南,当地至今仍完好保留着安化郡主墓,并且年年祭拜。时至现在,广南当地人们都还经常到离之更近更方便的广西百色、南宁看病购物。地理条件的便利,历史上人们交往的频繁,广南的汉语方言就势必会受到广西相邻汉语方言的影响。
中古日母字在广南方言今读中有着较为规律的文白异读现象,白读为零声母,这说明早期的广南方言中并没有z声母。据《广西省志·汉语方言志》记载,中古日母字在广西官话方言今读中有多种读法,但多种读法中并未提及有z声母,如“桂林官话和永福百寿官话,今读声母为零”[8] 381。据此推断,中古日母字在广南汉语方言中的白读音层次,很可能与广西官话方言有着极为深层次的渊源关系(或者是语言接触造成的,或者具有同源关系)。理论上推断,广西官话方言对广南汉语方言的这种影响,随时间向前推得越早其影响就应该越大,但由于目前对广西官话方言较为系统详细的研究材料还比较有限,而广南方言受普通话和周边县市方言的影响也在不断地发生着区域性的演变,故要弄清楚二者之间的确切关系,还有待从两地人们的交往、语言的接触甚至移民等方面做进一步的调查和对比分析研究。
注释:
① 我们认为,这里把去声读为低降调(211)看成是滇南方言的显著语言特点显然是不妥的,因为纵观《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的声调记录,云南去声调的调值除云龙、剑川、永胜、凤庆、永德、镇康读45外,其它县市主要读为211、212、213共三类,通过调查,这三个调值在当地方言中并不具备区别意义的作用。
② 路伟等《滇南方言的特点和范围》(红河学院学报,2003年第1期)指出:“(滇南方言)划分的结果和方言实际有出入。一方面把红河州和文山州的各县都囊括其中,如把不属于滇南方言的弥勒县和泸西县,文山州的丘北县、广南县、富宁县和麻栗坡县划分到滇南方言中来。”(第64页)
③ 红河州的河口话(云南话)和金平话有ŋ声母,文山州的丘北话无ŋ声母。
[1] 广南县志编委会.广南县志 [M].北京:中华书局,2001.
[2] (清)李熙龄.广南府志[M].台北:成文出版社,1967.
[3] (宋)王铚.默记[M].北京:中华书局,1981.
[4] 云南地方志编委会.云南省志·汉语方言志[M].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1989.
[5] 李蓝.西南官话的分区(稿)[J].方言,2009(1):72-87.
[6] 牟成刚.中古精知庄章组声母在西南官话中的演变[J].文山学院学报,2013(1):76-84.
[7] 陈长祚.云南汉语方音学史[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2007.
[8] 广西壮族自治区地方志编委会.广西通志·汉语方言志[M].南宁:广西人民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 田景春)
The Formation and Belonging of Guangnan Dialect
MOU Cheng-gang
(School of Humanities, Wenshan University, Wenshan 663000, China)
The formation of Guangnan dialect is signifi cantly related to the migration of Han people. According to the immigration records, the dialect is created in the Song Dynasty, formed in the Ming Dynasty and systematically formed in the Qing Dynasty. Guangnan dialect belongs to Yunnan middle region type, but its lexicon, grammar and pronunciation features are different to a certain degree from the type based on the tone types. It is possibly infl uenced to a certain degree in the early times by Guangxi Han dialect concerning the historical relation between Guangnan and Guangxi.
Guangnan dialect; immigration; formation; tone types; dialect belonging
H172.3
A
1674-9200(2015)01-0065-05
2014 - 01 - 06
云南省教育厅科研基金项目“滇东南汉语方言音韵研究”(2013Y205)阶段性成果。
牟成刚,文山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文学博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