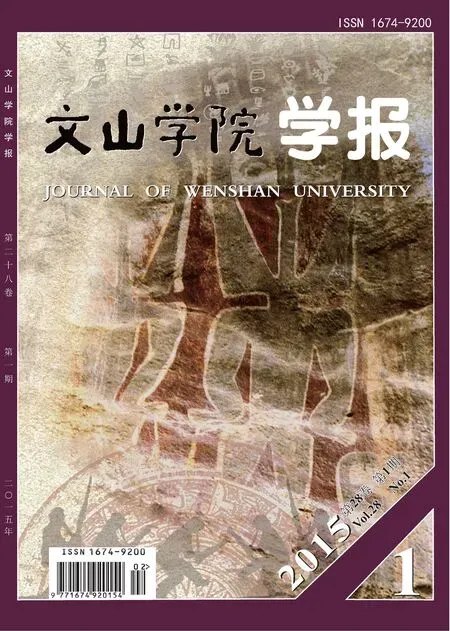民主改革视野下边疆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研究综述
2015-03-21王燕
王燕
民主改革视野下边疆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研究综述
王燕
(云南大学 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云南 昆明 650091)
民主改革作为国家与地方的互动策略之一,无疑是中央治理边疆的重要举措。文章从国家的视野出发,把民主改革纳入国家的治边思想及理论体系中来讨论,从历史的角度对治边思想作历时性梳理,以期更加深刻地理解民主改革的内容、类型及其体现的边疆观。
国家权力;治边思想;治边实践;民主改革
民主改革,全称“以和平协商土地改革为中心内容的全面社会改革”,是20世纪五六十年代发生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的一场以土地改革、解放奴隶、农奴和废除劳役及高利贷为主要内容的全面社会改造。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标志着现代民族国家框架和形式的实现,中央运作权力,通过各种方式进行民族国家及国族的建构,从关乎民生的土地入手,在内地汉族地区实行土地改革,在少数民族地区及边疆地区实行民主改革,使边疆与内地在社会制度上首先实现“边疆—内地一体化”,从而实现统一多民族国家的现代建构。
民主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开展的一系列民族工作之一,从现代国家和传统社会互动的视角看,它体现了国家意志和权力在少数民族地区的深入;从边疆治策视角看,民主改革及实践是中央边疆观、治边思想及理论的重大实践。少数民族地区发生的巨大变化一方面肯定了民主改革的高瞻远瞩,而时下少数民族地区面临的各种民族问题又启发我们不得不去回溯这场巨大的社会运动,甚至是文化运动。由于目前学术界对民主改革的研究甚少,以致我们对民主改革的内容、类型及实践缺乏足够的了解。因此,无论是从国家的治策视角,还是从少数民族社会变迁的视角,对民主改革做宏观上的把握无疑是一个突破口。
一、古代边疆治理理论及实践的研究
近二三十年来,我国古代边疆以及治理边疆方面的研究取得了长足发展,研究领域主要涉及边疆民族史、边疆移民史、边疆地方史、边疆地理等,但大多属于宏观方面的专题性研究,从历史的视角把边疆思想和治边实践纳入治边体系中作历时的、宏观与微观相结合的比较研究还比较少。因此,通过文献的梳理,对古代治边思想进行历时性的把握显得尤为必要。对古代边疆治理的研究,以方铁和周平两位先生的研究见长。方铁侧重于从历史的视角对古代治边思想进行探讨,周平则从政治学的视角对民族治策进行思考,在史实论证和理论建构上各有千秋。
方铁在其系列文章中对古代治边思想及实践进行了归纳分析,认为历代封建王朝统治者的基本治边思想是“守中治边”“守在四夷”,这也是制定各项边疆治策理论的基础。[1]作者因此在梳理史料的基础上总结了古代封建王朝对边疆的观念及治边实践,例如,早在先秦时期,诸侯国政治家便提出“五服”或“九服”说,由此看出统治者对边疆及边疆民族的态度。这种思想一直延续了两千余年,至明清统治者仍深受其影响,只是在不同的朝代更替中,统治者出于国力强弱、统治需求等对之有不同程度的继承和发展。
但通读先秦至清末的相关民族政策,“守中治边”“守在四夷”的治边思想,正如方铁先生所言是历代封建统治者的主流思想,而在不同的时期,由于对边疆的认识和开发不同,统治者的治边思想和策略又会有所不同。经过对先秦到清末的治边策略的粗略归纳,中国古代的治边思想经历了这样的发展过程:先秦时期主要是“内诸夏而外夷狄”的思想;到了秦汉时期,由于统一多民族王朝的建立,开始了对边疆地区的设治,表现为“守中治边”的消极保守思想;唐朝时期由于国力强大,唐太宗对边疆实行积极的开发和管理,提出“四海如一家”、君民一体的思想;到了宋朝,由于统治者的主要精力在北方,对西南边疆地区持“守内虚外”的保守克己思想;元朝较以往朝代少了“华夷有别”的民族歧视思想,统治者以西南地区为基地进行积极的开发和治理;明清时期,对边疆有了较为深入的认识,尤其是到清朝末期边疆统治危机的出现,这一时期统治者所持的治边思想既有继承的一面,也有创新的一面,表现为“守中治边”的保守性和“治同内地”的开拓性。
周平先生的研究侧重于政治学的视角,在对当代民族政策进行研究的过程中渗透着对王朝国家的边疆治策分析,指出我国的边疆治理模式经历了一个从族际主义到区域主义再到族际主义的过程,提出了今天我国边疆治理的模式建构。[2]在边疆治理的价值取向上,把何者放在首要地位,以何者为主,有很大区别。以处理族际关系为主的边疆治理方式,是族际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以处理区域性问题为主的边疆治理模式,是区域主义取向的边疆治理。两种不同取向的治理模式都是为了解决好边疆问题,但是二者存在着功能差别,因此导致了不同的治理效果。从秦统一中国到18世纪中叶的边疆治理,基本上是族际主义的边疆治理,18世纪中叶以来,区域主义的边疆治理模式形成,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来的边疆治理,则主要采取了族际主义的方式,今天,随着边疆形势的变化和边疆问题的转型,边疆治理应该构建一种区域主义的治理模式。
之所以形成以上不同的治理取向,与中央或中原王朝怎样看待边疆是分不开的。自秦朝以降,形成了“守中治边”的基本治边倾向,强调“守中”之地与四夷之地的区分,重视中心区域的治理,通过治理中心区域来影响边缘地区,“欲理外,先安内”,“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①;而对少数民族地区则采取怀柔之策,使臣服的少数民族镇守疆土,“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②。因此,形成了以夷制夷的羁縻政策。到了清末,西方国家逐渐强大而清王朝走向衰落,在西方入侵的情况下,为了保持国家的历史疆域,清政府与沙俄于1689年和1727年先后签订了《中俄尼布楚条约》和《布连斯奇条约》,王朝国家第一次意识到边界和边疆的意义。在此条件下,一种以国家边界为基础的边疆观念逐步出现,通过王朝中央直接控制边疆的体现区域治理内涵的边疆治理方式就逐步萌生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致力于民族国家的建设,在“边疆稳定、民族团结”的宗旨下先后实行了民族识别、民主改革、民族区域自治等一系列民族工作,体现了一种族际主义取向的治理思想。
周平关于边疆及边疆治策的研究,其特点和优势是站在管理学和民族政治学的学科视角,结合今天民族治策的理论实践整体把握我国的治边理论。这样,一方面使其研究更具有了现实的指导意义,另一方面将民族治策纳入政治学和管理学视野更能体现和容易理解国家治策的政治诉求。正因为如此,使得周平先生的研究存在着一个明显的不足,就是缺乏实证资料,尤其是今天治边情况的实证研究。因此,从民族历史的角度,对今天边疆治策现状作历史的回溯,用史料去补充、回应周平先生的研究就显得很有必要了。
二、边疆治理制度的近代化转折研究
正如上文所提到的,18世纪中叶以后,我国的边疆治策出现了近代化的转折。18世纪中叶正值清王朝中期,此时的中国还未进入近代发展阶段。但西方国家经历了长期的资本主义发展,已经进入近代化时期。在清朝政府不得不与之打交道的过程中,甚至受到列强的挤压和冲击,17世纪沙皇俄国将势力扩张到中国西北和东北地区,使中国意识到边疆和边界的重要性。在这种情况下清政府高度重视边疆的治理,近代意义的边疆观念逐步形成。边疆治策的近代化转变主要表现在:一方面加强对新疆、西藏、蒙古的直接统治;另一方面通过“改土归流”削弱少数民族政权对边疆的统治,把中央政权的力量直接深入到边疆少数民族地区,强化对边疆的统治。
关于边疆治策的近代化研究主要有苏德、吴福环、苏发祥、周平等人。苏德探讨了清政府在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推行一体化政策的历史原因、结局及影响。[3]在统一边疆的过程中,清政府对新疆、蒙古和西藏等边疆民族地区实行“因俗而治”“分而治之”的政策,建立起了以伯克制度、盟旗制度和政教合一制度为主的多元化管理体制。但是,进入近代以后,由于国际和国内的形势剧烈变动,清政府为了确保对边疆地区的统治,抵御外来势力的侵犯,不得不改变“因俗而治”的传统政策,在西北边疆改变以往的多元管理体制,逐步建立行省体制,以达到“治同内地”的目标。文中对清政府“一体化”政策推行的结局做了评价,认为该政策有利有弊,成败参半:利在新疆建省的成功,使新疆与内地政治一体化,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巩固国防,开发和建设西北都是有重要意义的;弊在“一体化”政策没有考虑到民族社会内部各阶层的利益,加上传统“因俗而治”的深远影响,引起了民族地区上层人士至平民百姓的抵制和反抗。
从文中可以得出这样的经验:清政府推行的“一体化”政策为什么没有取得最终的成功,除了与清政府后期国力的衰落,无力致力于边疆治理有关外,恐怕与“一体化”政策实行过程中的缺陷有关。“边疆—内地一体化”不仅是政治上的一体化,还是经济、社会、文化各方面的一体化,在实行的过程中,如果只考虑到政治方面的因素,而忽视了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的错综复杂的情况,在政策推行过程中不仅收不到预期的效果,甚至会播下民族关系不和的种子,引发族际冲突。
吴福环在《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一文中对新疆建省的历史背景和原因作了分析,指出1884年新疆建省,将边疆与内地划一治理,是清政府治边政策的重大转变,是国家统治方式近代化的标志之一。[4]新疆建省之所以是近代化的重要举措,是因为它吸取利用了西方近代资本主义的国家观念和理论,把国家的法律、管理措施等在其疆域内实施,国内一切地区概莫能外。
苏、吴二人都对清政府推行的“一体化”管理体制持肯定态度,视之为边疆治理的近代化转折。由于这是在清政府内忧外患之际采取的措施,有急功近利之嫌。联系民主改革,我们从中得到的启示是:边疆建省和民主改革在实施目的上基本是一致的,都是为了实现“治同内地”;但由于二者所处的国家性质不同,清王朝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政府采取的方式有所不同,导致了二者在实施后果上截然不同的效应。
针对该问题,利用磁力驱动机构的原理,设计了一款专门针对密封容器内部多相物料料位进行实时和可持续监测的带磁力驱动清洗装置的密闭容器多相物料料位监测装置[5].容器内部的机械清洗机构的表面为聚氯乙烯材质,能够避免被强酸、强碱或化工生产中常见的腐蚀性物质损坏.清洗机构通过外部磁力驱动,不需要在容器壁上穿孔,避免了容器内压力变化,和有害物质的外泄.
三、民主改革及相关实践
如果说清朝末期拉开了边疆治理的近代化帷幕,那么,新中国成立后,中央政府对边疆的治理则将治边理论推向新局面。尽管如此,时下还面临着各种各样的民族问题。因此,对中央政府的边疆治策作历史的回顾和研究现状的分析,是研究当代少数民族历史和把握时下民族问题的突破口。
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实现了国家主权的独立和民族的解放,从而实现了民族国家的构建。至此,中国已经有了全新意义上的国家边界,并形成了全新的边疆观念。中央政府高度重视边疆的治理,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初期,国家面临着国际国内各种各样的困难和挑战,民族稳定和民族团结是当时民族工作的中心。在这样的条件下,中央实行了“慎重稳进”的边疆少数民族民主改革方针,帮助边疆各族人民“用自己的腿走路”,胜利完成了民主改革,走上了社会主义道路,实现了历史性的飞跃。
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实行的民主改革,涉及西藏、青海、四川、云南及甘肃等省份,由于云南地处祖国的西南边疆,民族众多,云南的民主改革体现的边疆治理思想及实践是比较明显的。根据中央“慎重稳进”的方针,云南省委决定暂不进行土地改革,而是采取了一系列措施,为边疆的民主改革做准备,主要包括:军事进驻,清匪肃特,建设巩固的国防;疏通民族关系,加强民族团结;实行区域自治,帮助各族人民当家做主人;努力发展生产和卫生事业,大力培养民族干部。[5] 3-13以上方针及措施体现了中央从少数民族自身情况出发,以加强民族团结为宗旨的边疆治理思想,但正如周平所言,这时的治边模式是一种族际主义的治理模式。
民主改革的车轮已经走远,但作为一场深刻的社会运动,它在少数民族地区所产生的影响还在继续。由民主改革带来的民族地区社会、经济、文化等各方面的变迁,目前已经引起了学术界的关注,但研究甚少,主要有西南民族大学的学者对四川彝区的研究、云南大学的学者对小凉山彝族和德宏州德昂族等的研究。
四川民主改革的研究,主要以蒋彬、秦和平、杨正文等人为代表,他们通过对四川凉山彝族民主改革资料的收集和整理,对民主改革与彝族社会文化变迁做了研究,且形成了系列成果。
云南民主改革的研究,在文献资料方面有当代中国出版社出版的《当代云南简史》和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出版的《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两书,这两本书对云南民主改革缘由、方式、类型、过程及结果都做了详细的叙述,并收集了大量的文献资料、历史资料、专题资料及回忆资料,是研究云南民主改革和当代边疆民族治策的重要文献。
在研究论文方面,有云南大学学者嘉日姆几、李晓斌、高志英等人分别对彝族、德昂族、独龙族等的研究。
李晓斌对民主改革的研究体现在其《国家意志与云南文化变迁特点——以1949年至1960年间的变迁为例》一文中,作者从外源力与内源力二元聚合的视角,探讨1949年到1960年间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特点。文中指出,国家力量是这一时期云南少数民族文化变迁的重要推动力,但政策内容的差异性、少数民族文化的不同特性、民族分布的特点以及地区间的社会发展与社会形态的不同使文化变迁呈现出程度上的差异和文化变迁模式的不同,形成了国家意志的统一性与文化变迁的差异性特点。[7]但是,文中涉及的时空跨度比较大,且从整体上来把握云南的少数民族文化,没有集中到某个民族工作的时间段上,因此,民主改革的微观研究一方面可以论证其观点和理论,另一方面可以填充文中的研究空白。
高志英从民主改革的背景出发,对云南省独龙族的教育观念变迁做了研究。高志英从边疆、特少、“直过”这三个典型的维度来研究一个典型的民族,这一方法对于我们今天研究边疆治策具有启发意义。而其对教育观念的探讨告诉我们,民主改革引发的不仅是社会制度的跨越,同时还是其他一系列文化事项的跨越。因此,用历史的眼光来观察今天边疆民族的文化事项,更能以现状解决现状,以现状追溯历史。[8]
除了上述的研究外,还有其他高校、研究机构和学者对民主改革进行了研究。如陈玉屏、李成武、达布希拉图等,这些研究的一个共同特点是,从整体上来理解民主改革的思想及意义,属于宏观上的讨论和研究。
四、结 语
民主改革是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中央在少数民族地区进行的一场社会运动,对少数民族地区的发展具有深远的影响,将民主改革置于宏观的边疆治理体系来探讨,有利于把握民主改革行之有效的方针、方式、类型等。本文通过对治边思想及理论研究实践作历时的梳理,凸显了民主改革在整个治边体系中的地位和作用,为今后进一步从边疆治策的角度研究民主改革打下了基础。
注释:
① 贞观三年(629年),靺鞨谴使入贡,太宗曰:“靺鞨远来,盖突厥已服之故也。昔人谓御戎无上策,朕今治安中国,而四夷自服,岂非上策乎!”(宋)司马光编著:《资治通鉴》卷一九三《唐纪九》贞观三年十二月条。
② 明朝大臣桂彦良说:“天子有道,守在四夷,言以德怀之,以威服之,使四夷之臣,各守其地,此为最上者也。”桂彦良撰:《上太平治要十二条》,载(明)陈子龙等选辑:《明经世文编》卷七。
[1] 方铁.古代“守中治边”、“守在四夷”治边思想初探[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6(4):1-8.
[2] 周平.中国的边疆治理:族际主义还是区域主义?[J].思想战线,2008(3):25-30.
[3] 苏德.试论晚清边疆、内地一体化政策[J].中国边疆史地研究,2001(3):1-11.
[4] 吴福环:我国边疆治理制度近代化的重要举措——论新疆建省[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5 (4):38-40.
[5] 中共云南省委党史研究室编.云南边疆民族地区民主改革[M].昆明:云南大学出版社,1996.
[6] 嘉日姆几.云南小凉山彝族民主改革时期家奴的安置措施及其影响[J].思想战线,2010(4):101-108.
[7] 李晓斌,杨晓兰.国家意志与云南文化变迁特点——以1949年至1960年间的变迁为例[J].西南边疆民族研究,2010(7):58-64.
[8] 高志英.20世纪中国边疆“直过”民族教育观念变迁研究[J].华东师范大学学报:教育科学版,2007(3):37-43.
(责任编辑 杨永福)
Review on the Theories and Practice of the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WANG Yan
(Research Center of Borderland Minorities in Southwestern China, Yunnan University, Kunming 650091, China)
As one of interacted models between the state and local, democratic reform is absolutely an important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strategy for central government. The paper discusses the democratic reform from the frame of state's governing thoughts and theories, and combs governing thoughts on the borderland areas from the history perspective in order to obtain a profound understanding of the contents, types and frontier views of the democratic reform.
state power; thoughts on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 practice of borderland administration;democratic reform
D63
A
1674-9200(2015)01-0048-05
2014 - 05 - 10
王 燕,云南大学西南边疆少数民族研究中心2013级中国少数民族史博士研究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