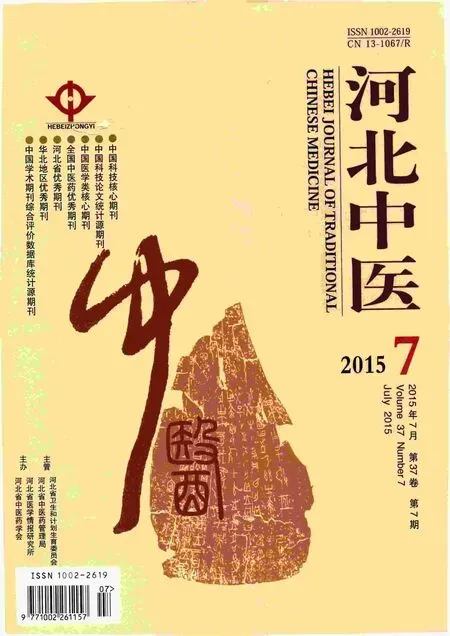基于“久病入络”理论探讨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医病机※
2015-03-21张全乐张红霞黄立冬
张全乐 张红霞 黄立冬
(京东誉美中西医结合肾病医院肾内科,河北三河 065201)
难治性肾病综合征(refractory nephotic syndrome,RNS)是指经正规激素治疗,出现经常复发、肾上腺皮质激素依赖和肾上腺皮质激素抵抗之一的原发性肾病综合征(primary nephrotic syndrome,PNS)[1]。RNS临床上极为常见,占PNS的30%~50%,是目前临床治疗比较棘手、预后较差的肾病[2-3]。RNS经久不愈可诱发多种致命并发症,后期常进展慢性肾衰竭,最终发展为终末期肾病,其治疗缓解率与肾脏存活率呈正相关性,临床主张中西医并用[4]。我们通过研究中医学经典文献并结合临床实践,发现根据RNS“难治性、缠绵性、反复性”的病证特点,运用中医“久病入络”理论阐释其发病病机,指导辨证论治,执简驭繁,验之于临床,可明显提高疗效,初步探讨如下。
1 “久病入络”理论源流
“久病入络”之学术思想源于《内经》,发展于汉·张仲景,成于清·叶天士。《素问·缪刺论》曰“夫邪之客于形也,必先舍于皮毛,留而不去,入舍于孙脉,留而不去,入舍于络脉……”《灵枢·终始》曰“久病者,邪气入深”,《素问·调经论》有“病久入深,营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的记载,最早指出了久病可入深的发展趋势,从而为“久病入络”学说奠定了理论基础。
“久病入络”自《内经》之后,历代均有发挥,日趋成熟。汉·张仲景《伤寒论》及《金匮要略》论述了中风、肝着、血痹、虚劳等病证的发生与络脉空虚、络脉瘀阻的病机有关,并首创活血化瘀通络法和虫蚁搜剔通络法,对久病入络理论的发展起到了承前启后的作用。
至清代,叶天士继承和发扬了前代的学术成果,将《内经》中有关“络”的生理、病理认识加以深化,引入到内伤杂病的病理阐释中,明确提出“久病入络”学说。强调“初为气结在经,久则血伤入络”(《临证指南医案》),从全新的角度揭示了疾病(多属内伤、脏腑病变)久延不愈,由经及络、由浅入深、由气及血的演变规律,认为络病分虚、实,总以络脉阻滞为特征,提出“大凡络虚,通补最宜”,“络以辛为泄”,并创立了辛味通络诸法,至此“久病入络”学说形成了较完整的理论体系。络病多属缠绵难愈的慢性病,“久病入络”理论启发了新的辨证思路和用药规律,为后世在内伤杂病理论和治疗学上的研究提供了重要借鉴。
2 “久病入络”与RNS的发病
2.1 RNS具备“久病入络”之病证特征
2.1.1 时间性、反复性、缠绵性久病,即痼疾。久病入络,是指一些日久不愈,或因失治误治,初病不愈,反复发作、病情缠绵的慢性疾病[5],正所谓“百日久恙,血络必伤”,“病久入血络”,“久发、频发之恙必伤血络,络乃聚血之所,久病血必瘀闭”(《临证指南医案》)。RNS指PNS经正规激素治疗,出现肾上腺皮质激素抵抗(规范化激素治疗12~16周无效)、经常复发(缓解后6个月内复发2次或1年内复发3次以上)和肾上腺皮质激素依赖(经激素治疗获得缓解,但在激素撤减过程中或停用激素后14 d内复发者)之一的PNS[6],符合“久病入络”的时间性、反复性、缠绵性特点。
2.1.2 难治性、进展性久病入络揭示了一般疾病可由新至久、由浅入深、由气及血的难治性、进展性特点,“初为气结在经,久病入络,以经主气,络主血……”(《临证指南医案》)。RNS是目前临床治疗比较棘手、预后较差的肾病,经久不愈可诱发严重感染、急性肾衰竭、血栓及栓塞等致命并发症,后期常进展为肾小球硬化和肾间质纤维化,导致慢性肾衰竭,最终发展为终末期肾病,其病理过程正是反映了由气及血、由功能性病变到器质性损伤的慢性进展过程。
综上,RNS发病具有渐次深入、病位深疴、病情顽固,病期冗长、反复发作的特点,符合中医“久病入络”的基本特征。
2.2 RNS发病与“久病入络”存在共同结构分布和生理、病理基础
2.2.1 肾脏血液循环与肾络结构层次的一致性
现代医学之肾脏血液循环表现为:肾动脉由腹主动脉分出后,经叶间动脉、弓形动脉、小叶间动脉、入球小动脉进入肾小球,组成第1个毛细血管网,即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其决定肾小球的滤过功能。肾小球毛细血管网再汇集成出球小动脉,离开肾小球后分支形成第2个毛细血管网,即肾小管周毛细血管网,其包绕于不同区域的肾小管,影响其重吸收功能。肾小管周毛细血管网汇合成静脉,经小叶间静脉、弓形静脉、叶间静脉、肾静脉进入体循环[7]。肾小球毛细血管丛实际上是一团盘曲成球状的动脉性毛细血管网[8],介于入球和出球动脉之间,每一个入球小动脉进入肾小球后可以分成5~8个分支,每一分支再分成20~40支襻状毛细血管小叶,其滤过面积约1.5 m2[7],最终各小叶毛细血管相互汇合成一条出球小动脉离开肾小球。肾小球毛细血管的结构较其他部位的毛细血管复杂,由内皮细胞基底膜、上皮细胞组成,构成肾小球特有的滤过屏障[8]。肾脏血液循环特征性的两级毛细血管网,是血液循环进行的管道,亦是代谢的通路。
肾络是网络于肾中之络脉,即“脏腑隶下之络,属布散于肾之阴络”(《临证指南医案·便血》),是肾脏组织结构有机组成部分。“经脉为里,支而横者为络,络之别者为孙”(《灵枢·脉度》),“孙者言其小也,愈小者愈多矣”(明·张景岳《类经·经络类》),“十二经生十二络,十二络生一百八十系络,系络生一百八十缠络,缠络生三万四千孙络,孙络之间有缠袢”(清·喻嘉言《医门法律·络病论》),络脉是经脉的分支,孙络是络脉的分支结构。“夫经脉之血……脉而络,络而孙”(《灵枢·痈疽》),“中焦出气如露,上注溪谷,而渗孙脉,津液和调,变化而赤为血,血和则孙络先满溢,乃注于络脉,皆盈,乃注于经脉”(《黄帝内经素问集注·调经论》),则进一步指出气血运行由经脉至络脉,分支散布于孙络,再经络脉汇集于经脉的过程。由此得出,自经脉分支而出的肾络,逐层细分为系络、缠络、孙络等不同级别层次,愈分愈细,其脉气亦逐渐细小,呈网状扩散,与肾动脉依次分出叶间动脉,直至肾小球、肾小管之毛细血管网,具有相同的结构层次分布。
2.2.2 RNS发病与肾络病证的生理、病理同一性肾脏血供极其丰富,是全身血流量最多的器官,过剩的血流量主要是为了维持肾小球滤过,以达到及时清除代谢废物、稳定内环境的目的[8]。中医学则认为,“络为聚血之所”(《灵枢·经络》),“血气之输,输于诸络”(《灵枢·卫气失常》,“络脉所行……以为流通之用”(《类经·经络类》),“经脉者,所以行气血而营阴阳”(《灵枢·本脏》),肾络属经络之分支,是运行全身气血、感应传导信息的通路系统,通过孙络充盈灌注,有溢奇邪、通营卫作用[9],正所谓“盖大络之血气……以通营卫者”(《黄帝内经素问集注·气穴论》)。然络脉渗灌血气、互渗津液的生理功能,赖营卫气化而实现[10],具体表现为“营者,水谷之精气也;卫者,水谷之悍气也。精者清,悍者浊。营出中焦,卫出下焦,谷气分布,则清升浊降。故浊者降至下焦,随卫气流行脉外;清者由中焦变化,随营气而行脉中”(《灵素节注类编》引《痹论》)。此所谓,“肾者水脏,主津液”(《素问·逆调论》),人体水液运行至肾络,在气化蒸腾作用下,浊者下注膀胱化为尿液排出体外,清者回归入经脉,复宣发输布全身。这与肾小球是血液与组织细胞之间物质代谢的基本形态功能单位、肾小球毛细血管网滤过、肾小管毛细血管网重吸收、血液回流重吸收存在生理上的同一性。
肾络空间结构特点决定了血液进入肾络后,具有面性扩散、运行缓慢、津液互换、末端联通、双向流动、功能调节、终而复始、如环无端的运行特点。RNS主要是肾小球疾病引起的临床综合征[6],主要环节在于肾小球滤过膜损伤,即肾小球毛细血管形态和(或)功能性的损伤,表现为对蛋白及细胞通透性改变,对水、电解质及酸碱平衡等调节能力障碍,导致低蛋白血症、高脂血症,形成高凝状态和球蛋白补体成分变化引起的营养不良、免疫功能缺陷[7]。这符合中医“血络者……血气有所留积,则失其外内出入之机”(《黄帝内经灵枢集注·血络论》)之论述。
综上,RNS发病与“肾络”具有相同的组织结构分布和共同的生理、病理基础,从中医学分析本病证当属络病。
2.3 基于“久病入络”探究RNS病因病机肾络逐级输注,络体细小狭窄,气血流缓,面性弥散,既是气血津液输布之枢纽,又是邪气致病场所,临床多瘀易积,易蕴毒留邪。“病久入深,荣卫之行涩,经络时疏,故不通”(《素问·痹论》)。RNS病位深疴或失治误治,导致病情顽固,反复发作,缠绵难愈,经气之伤渐入血络,从其病证发病特点入手,“久病入络”可作为中医药对RNS病因病机阐释的切入点。“邪之所凑,其气必虚”,RNS以蛋白尿难消为突出表现,蛋白尿乃机体水谷精微物质的外泄,“精气夺则虚”(《素问·通评虚实论》),RNS亦属“精气下泄”、“虚损”之范畴。其病机总以“正气亏虚,肾络瘀阻”为要,病位在肾络。
2.3.1 “正气亏虚,肾络瘀阻”是RNS的基本病机虚损病名见于《肘后方》与《景岳全书》,主要指脏腑亏损,气血阴阳不足的虚证,脏腑亏损归因责之脾肾。“不因虚邪,贼邪不能独伤人”,正气亏虚是RNS肾络瘀阻之病理基础,具体论之如下。
“血随气行,气为血帅”,“元气既虚,必不能达血管,血管无力,血必停留而瘀”(《医林改错》),导致肾络瘀阻,肾络气化输布失司,终致气机升降失常,津液渗灌转输失调,精气下泄见蛋白尿。又元气根于肾,一元之气分阴阳二端[11]。RNS患者存在使用激素前后药源性阴阳转化规律,致使阴阳偏胜偏衰、阴阳互损贯穿始终[12]。“劳伤之人阴阳俱虚,经络脉涩,血气不利”(《诸病源候论》)。分而论之,“阳虚者多寒”,“寒邪客于经脉之中,则血泣,血泣则不通”(《灵枢·痈疽》)。寒性凝涩滞,寒邪侵犯经脉,使经脉收引,血行迟缓,甚至血液凝滞,导致肾络瘀阻。此即《内经》“血气者,喜温而恶寒,寒则泣不能流”所谓是也。阴虚生内热,热盛则伤津耗液,使血液黏稠凝滞,“血受热则煎熬成块”(《医林改错》),炼血成瘀,终致脉络涸涩,瘀塞肾络,精气下泄。正所谓“阴阳不和,则使液溢而下流于阴,髓液皆减而下”(《灵枢·五癃津液别》)。
“夫人之虚……而独举脾肾者,水为天一之元,土为万物之母,二脏安和,诸经各治”(《病机沙篆》),指出虚损以脾肾为要。虚在脾,脾土运化失司,水液不能正常输布,湿浊内生,弥漫三焦,发为水肿。“肾如薪火,脾如鼎釜”,脾肾两脏相互滋生、相互影响。虚在肾,则脾运化失常,水液代谢紊乱,精微化生障碍,湿浊因而内生。湿为阴邪,其性黏滞重浊,伤气滞气。“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灵枢·百病始生》),湿邪积聚凝结于肾络,又有“水病血亦病”,脉络不利,积而为瘀之因,导致肾络瘀阻,脉络损伤,气血津液输布失常。即所谓湿浊入络,凝血成瘀。
“凡经脉直行,络脉横行,经气注络,络气还经,是其常度”(《临证指南医案》)。RNS病程迁延日久,久病损耗,病本为虚[12],导致肾络之气不充,络虚失荣,血失通利;血行迟滞,肾络瘀阻,津液渗灌转输失调,精气下泄,加重蛋白尿,所谓“血气有所留积,则失其外内出入之机”(《黄帝内经灵枢集注·血络论》)。随之肾中精气愈亏,无以养络,则正虚络阻日益为甚,如此形成恶性循环。RNS病机变化总以“正气亏虚,肾络瘀阻”为要,肾络瘀阻贯穿于疾病发展全过程。
2.3.2 “浊毒内蕴,伏积肾络”是RNS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毒者,邪气蕴结不解之谓”(《金匮要略心典》),指出浊邪为毒邪之源,毒邪为浊邪之渐。RNS临床表现为水肿,水湿之邪属阴,湿性黏滞,重浊趋下,留积肾府肾络。“湿气不行,凝血蕴里而不散,津液涩渗,著而不去而积皆成也”(《灵枢·百病始生》),湿浊留滞,蕴久化热,“血受烧炼,其血必凝”(《医林改错》)。湿热夹瘀胶固难解,“湿热久停,蒸腐气血而成瘀浊”(《金匮玉涵经二注》),日久酿毒。又湿郁蕴热,湿热留恋久稽,每每耗伤正气,伤阴损阳,“阴阳二气偏虚,则受于毒”(《诸病源候论·时气阴阳毒候》)。毒盛湿热鸱张,灼津生痰,痰湿重浊,黏稠不化,终成脂浊。水湿、湿热、瘀血、痰浊等既是病理产物又是致病因素,四者互结互病,积久蕴毒,败坏形体,腐蚀肾络,继而加重病情,形成恶性循环。正所谓血从湿而聚,从热而结,毒邪从瘀而生,毒瘀互结,久羁缠绵,蚀伤络脉,沉疴难愈。
综上,RNS之久病入络既可以是肾络营卫气血的功能失常,也可是肾络结构的损害,二者相辅相成,互为因果,相互影响。一方面“外邪留著,气血皆伤,其化为败瘀凝痰,混处经络”(《临证指南医案》),造成肾络瘀阻,津血互渗交换障碍,气化升降出入失司,分清泌浊功能失常,精气下泄,正气愈虚;另一方面肾络气血津液流通受阻,经络瘀滞,形成血瘀、痰凝、湿阻等病理产物,聚而不化,久积陈朽,日久相互搏结,郁而蕴蒸,蕴结成毒,壅塞络道,腐蚀肾络,进一步加重肾络形体败坏而难愈,正所谓无邪不成毒,毒从瘀起,变从毒起。现在医学认为的RNS病理机制主要有体液免疫介导(包括原位和循环免疫复合物的形成并沉积)、细胞免疫介导及肾脏固有细胞参与的免疫损伤[8],可视为浊毒内蕴,伏积肾络。由此而知,RNS病本为虚,“正气亏虚,肾络瘀阻”是其基本病机,“浊毒内蕴,伏积肾络”是其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
3 小结
“初病气结在经,久病血伤入络”(《临证指南医案》),久病入络是现代难治性复杂性疾病具有共性和进展加重的原因。叶天士在前人络病理论指导下,提出了疾病日久不愈,由气到血,久病入络的命题。RNS以蛋白尿、水肿为突出临床表现,病情缠绵,或疾病失治、误治,日久不愈,易于反复,符合“久病入络”之病证特点。通过分析发现肾小球滤过膜通透性变化是RNS形成蛋白尿的基本原因[13],肾小球微循环障碍与肾络病证具备结构层次和生理、病理的一致性。故认为RNS属气血阴阳亏虚之虚损证,病本为虚,经气之伤渐入肾络,“正气亏虚,肾络瘀阻”是RNS的基本病机,“浊毒内蕴,伏积肾络”是RNS发生发展的关键环节,所谓“毒热炽盛,蔽其气,凝其血而陷也”(《重订广温热论》)。RNS病理变化既可以是肾络营卫气血的功能失常,也可能是肾络结构的损害,二者互为因果,相互影响,正所谓“肿之生也,皆由风邪寒热毒气客于经络,使血涩不通,瘀结而成肿也”(《诸病源候论》。“五脏有疾也,应出十二原,十二原各有所出,明知其原,睹其应,而知五脏之害矣”(《灵枢·九针十二原》),“盖经络不明,无以识病证之根源,究阴阳之传变”(《医门法律·络病论》),指出内脏有病,可循其经脉,明知其原。“经脉者,所以决死生,处百病,调虚实,不可不通”(《灵枢·经脉》),以“久病入络”理论为切入点,分析RNS发生、发展及演变规律,阐释其发病病机,对临床辨证论治RNS具有重要意义。
[1]《环孢素A在肾内科的应用》专家协作组.环孢素A治疗肾小球疾病的应用共识[J].中华肾脏病杂志,2005,21(9):556-557.
[2]李小会,雷根平,潘冬辉.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的中西医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3,14(1):87-89.
[3]聂莉芳,陈荣源.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西医结合治疗的研究进展[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06,7(7):424-425.
[4]郭华伟.中西医结合治疗难治性肾病综合征研究进展[J].山东中医杂志,2008,27(9):645-647.
[5]吴以岭.络病学说形成与发展的三个里程碑(二)[J].疑难病杂志,2004,3(3):149-151.
[6]李学旺.成人原发性肾病综合征治疗专家共识[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1:1-7.
[7]王海燕.肾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41,936,941-948.
[8]黎磊石,刘志红.中国肾脏病学[M].北京:人民军医出版社,2008:10,256-271.
[9]孙广仁.中医基础理论[M].北京:中国中医药出版社,2002:156,158,160-161,190-193.
[10]吴相春,贾振华,魏聪,等.《内经》营卫关系探析[J].中国中医基础医学杂志,2011,17(2):127-129.
[11]罗伯托·刚萨雷斯,牛欣.基于现代医学基础的正气的诠释[J].中华中医药杂志,2012,27(6):1541 -1543.
[12]张全乐,张红霞.基于“阴阳互根、互用”理论探究难治性肾病综合征中医证治[J].中国中西医结合肾病杂志,2014,15(3):273-275.
[13]叶任高,李幼姬,刘冠贤.临床肾脏病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08:178.
(本文编辑:石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