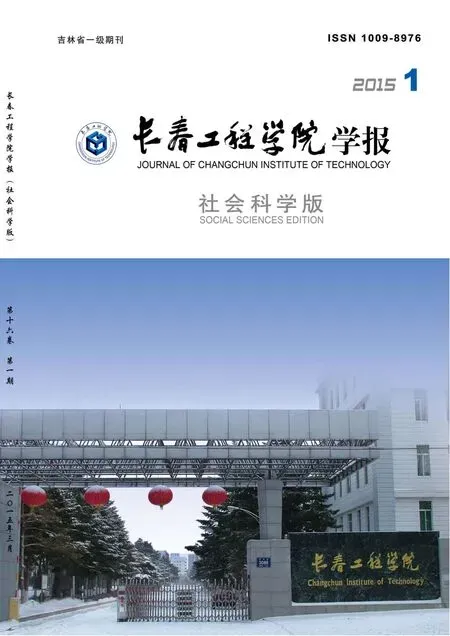《幸运的吉姆》之伦理解读——兼与《围城》之比较
2015-03-20刘洋
刘 洋
(合肥工业大学外国语学院,合肥 230009)
二战后的英国文坛,文学的现实主义回潮成为最为引人瞩目的现象之一。“英国涌现出一批具有较强艺术性、现实性的严肃的现实主义小说,这其中最有影响力的现实主义作家群就是被称之为‘愤怒青年’的作家们。”[1]
“愤怒青年”于20世纪50年代横空出世,给当时沉寂的文坛注入了一针兴奋剂。作为英国文坛承上启下的一代,在40年代现代主义大潮消退之际,在小说创作面临往何处去的历史关头,他们回归英国文坛传统,扎根现实主义的土壤,并将其创作手法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加以扩展和丰富,为其后六七十年代英国后现代主义小说的兴起铺平了道路,在这股文坛大潮中,作为“愤怒青年”这一群体作家的突出代表,金斯利·艾米斯(Kingsley Amis)以其代表作品《幸运的吉姆》,而尤其为人们熟知。
本文在文本细读的基础上,试图从伦理批评的角度来对这部作品进行解读,并将它与钱钟书的《围城》进行比较,从而加深对这部作品的理解。
一、《幸运的吉姆》之伦理解读
小说内容可以说是一个男版现代灰姑娘的故事。在一所二流大学任教的吉姆,为了保住饭碗,不得不费力讨好敷衍系主任威尔奇教授。在威尔奇教授的一次舞会上,吉姆邂逅了教授之子贝尔特朗的女友克莉斯廷·卡拉汉,并很快就爱上了她,于是,围绕着争夺卡拉汉,吉姆展开了一系列与情敌贝尔特朗的“战役”,并最终在情场上抱得美人归,大获全胜;而在另一个领域的战役——工作饭碗问题上,由于搞砸了系里的演讲,吉姆被学校辞退,但却意外地由卡拉汉的舅舅戈尔阿夸特提供了一份待遇优厚的工作,从而转危为安,可见,无论从事业上还是爱情上,吉姆都确确实实是“幸运”的。
而作者的刻意安排也使得吉姆的“幸运”更加凸显出来。在小说第五章,吉姆无意中看见威尔奇教授之子贝尔特朗和有夫之妇卡洛尔偷情的场面,由于贝尔特朗不忠在先,从而使吉姆争夺贝尔特朗女友卡拉汉在伦理道德上比较合情合理,既符合道义,也符合读者的阅读期待,而在小说结尾,吉姆的现任女友玛格丽特也被证实是一个工于心计的而又有些神经质的女人,从而使得吉姆下定决心离开她,这样,从两个方面,作者为吉姆与贝尔特朗女友卡拉汉的恋爱扫清了伦理上的障碍。
书中对吉姆命运起着关键性作用的戈尔阿夸特,作为工商界的富豪,他的伦理价值观与大学教授和校长们格格不入,在舞会上,戈尔阿夸特第一次登场,就说:“现在看来,我已经成功地躲开了你们的校长。”[2]3“我要是给他(指大学校长)抓住了还能逃得脱吗?”[2]53而对吉姆,他却主动与他喝酒聊天,并说:“我们是同病相怜啊。”[2]69并问他:“你上的是什么学校?”吉姆回答:“地方普通中学。”戈尔阿夸特点了点头。[2]75在这段对话中,我们看到,戈尔阿夸特对吉姆是感兴趣的,欣赏的,这种欣赏是主要是出于价值观上的认同,从而为吉姆的幸运埋下伏笔。事实上,在吉姆搞砸演说从而被学校辞退这件事上,戈尔阿夸特也是有份的,他让吉姆喝了太多的酒,但话说回来,他早就看出吉姆与学校里的所谓文化精英的气质格格不入,而这一点吉姆也是心知肚明的。在这场学界与工商界的不同价值观的冲突中,吉姆选择了离开学界,投身工商界。而这个选择绝不是单向的,以戈尔阿夸特为代表的工商界也选择了吉姆做他们这个阶层的文化代言。在共同的反对精英文化的斗争中,双方找到了契合点。这一点也体现在他对贝尔特朗·威尔奇的评价上,他对吉姆说:“他要的工作就是现在给你的呀!我一见到威尔奇,就知道他不中用,像他的画一样。”[2]120这也代表了实用至上的工商界对所谓的精英的嘲讽鄙夷的态度。
吉姆,威尔奇父子和富豪戈尔阿夸特之间的关系成三足鼎力之势。戈尔阿夸特为代表的工商界伦理道德和威尔奇父子代表的学界伦理相对立,而站在十字路口的吉姆在谋求学界聘任未果的情况下,被戈尔阿夸特看中,从而投身工商界,这看起来偶然的,但又是必然的。共同的反文化倾向使得二者不谋而合。
吉姆作为反文化的代表,体现了英国战后50年代的一股新浪潮,一股反对所谓的精英文化,主张大众文化、通俗文化的浪潮。通过吉姆之口,作者对威尔奇教授为代表的“文化精英”进行了辛辣的讽刺。小说刚一开始,即是威尔奇教授的无聊的冗长的关于音乐的谈论,连吉姆都忍不住怀疑:“他是怎么当上历史教授的呢?是凭出版过的著作吗?不是。是凭格外优秀的教学效果吗?根本谈不上!那么凭的又是什么呢?”[2]244而在小说结尾,吉姆终于得以对他所痛恨的威尔奇教授发出胜利的狂笑,应该说,这一声狂笑既是以作者为代表的那一代愤怒的青年的心声反映,也符合了读者的阅读期待,隐忍多年的郁闷一朝得以宣泄,从而使小说圆满收场。
在本书中,作者通过吉姆的眼光,揭露了大学这所象牙塔背后不为人知的一些故事,论文炮制,粗制滥造,剽窃抄袭,附庸风雅,趋炎附势,对各色知识分子进行了形象而辛辣的讽刺,而对与之相对应的主人公吉姆,作者是持比较欣赏的态度。在与代表旧的道德秩序的威尔奇教授的明争暗斗中,吉姆取得了胜利,向威尔奇一家发出胜利的大笑,这笑声是成功后的喜悦,更是对旧的权威秩序的一种公开的反抗和挑衅,在传统的道德观念和个人欲求的对立中,吉姆毫不犹豫地选择了后者。
当吉姆最终报得美人归,赢得好工作时,面对威尔奇教授一家时的狂笑,相信不仅发自吉姆之口。也反映了作者的心声。在吉姆这个角色上,寄托了作者对战后这批年轻人的共同的理解,他们大都出身社会中下层,受过中高等教育,但在历来等级分明的英国社会难有出头之日,所以他们怀着既怨恨又羡慕的心情发出所谓的愤怒或抗议。作为那个时代的代言人,吉姆那一声狂笑既宣泄了愤怒,也流露出那一代年轻人成功不易的怨意。
吉姆作为一个现行社会秩序(或他所在的学院秩序)的反叛者,在他身上,充分体现了人性复杂的一面。这种复杂性鲜明地体现在他对威尔奇和玛格丽特的态度上。对于自负的威尔奇教授,他虽然十分鄙夷,却无法流露出一点不耐烦,只能小心迎合,但同时,他对威尔奇教授也体现了性格上的反叛的一面,如坚持当面询问他的工作聘任问题;对于玛格丽特,他处在伦理两难的境地,一方面他并不爱她,想离开她,但另一方面又觉得对玛格丽特负有某种道德上的义务,从而左右为难。幸运的是到最后,工作与爱情这两个问题都得以解决,他才能对这种以威尔奇为代表的旧的权威,“文化精英”发出胜利的,宣泄式的狂笑。
作为一个小人物,吉姆并不是传统意义上的正面英雄人物,他是作为一个反英雄式的人物而存在,他视传统道德律令为粪土,尽情张扬个人欲求。他在舞会上见到美丽的克莉斯廷,即对她展开了追求的攻势。作为平民阶层,他与精英阶层贝尔特朗第一次见面就发生了口角。贝尔特朗与他就对富人征收重税意见针锋相对,作为既有利益的一方,贝尔特朗是反对征收富人重税的,而处在社会中下层的吉姆自然对现有利益的一方不满,因而觉得对富人征收重税理所应当。双方观点的分歧表现了战后新一代崛起的年轻人对现有社会制度、等级观念的不满,表达了他们强烈的想要实现个人欲求的愿望。
全书屡次出现在吉姆身上的一个词是愤怒,如“愤怒地回敬”,“狄克逊噙着怒不可遏的泪花”,“心中愤怒的怒火不禁油然而生”[2]245,等等,应该说,吉姆除了幸运,就是愤怒了,这股愤怒在他与威尔奇教授的交往中一直存在,但他一直隐忍不发,而在几乎每次与威尔奇之子贝尔特朗的接触中,他们都会争吵,后来甚至发展到闹剧一般的斗殴,这一方面是因为他是吉姆情敌所致,另一方面,贝尔特朗作为社会的有闲阶层和既得利益者,在他身上体现出的那种自负和傲慢是吉姆最为痛恨的,而吉姆的愤怒正体现了那个时代青年的心声,使其成为“愤怒青年”的代言人。
但由于小说的圆满结局很大程度在于外界力量的介入,不禁让人对小说的真实性打上一个很大的问号,应该说,这种大团圆似的圆满结局是与狄更斯时代小说的传统是不谋而合的,但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它被赋予了新的含义。在本小说中,反映了对现存道德秩序、等级观念的鞭笞和愤怒,而在之前的狄更斯时代小说中,传统道德说教的意味可能更浓厚一些,从这个意义上说,本小说又可以理解为一部反道德小说,体现了对从维多利亚时代积累传承下来的传统的道德观念的反叛。
二、《幸运的吉姆》与《围城》之比较
小说的主题可以理解为反文化,即反对当时所谓的精英文化,作品的魅力在于其幽默性,吉姆的所想与所言的巨大差距产生了强烈的喜剧魅力,此外,语言的魅力还体现在夸张性上。无论是在内容上还是在表现手法上,该小说都让人很容易就联想到钱钟书先生的《围城》,因为这两部小说有着惊人的相似。两部小说的字里行间,都隐隐约约打上了作者的影子,带有一定的自传性;都对精英阶层的装腔作势、矫揉造作进行了嘲讽,带有一定程度的反智主义倾向;就题材而言,都可以归为由文人创作的校园小说范畴,描写的都是男主人公在大学这个“小世界”里的经历;两位主人公都至少有一位男性朋友帮助,吉姆的朋友是阿特金森,而方鸿渐的朋友是赵辛楣,并且这二人相比较男主人公,都更加果断富有实干精神;甚至在一些次要角色上,也能看到类似之处。如《围城》中的李梅亭和《幸运的吉姆》中的约翰斯一样,都是比较阴沉,喜欢背后搞点破坏。同样类似地,在这两部作品中,都对大学教授这个群体进行了或是辛辣的讽刺或是温和的揶揄,具有强烈的讽刺或喜剧效果。
从对待爱情的态度来看,二者既有类似点,也有不同点。类似点在于对自己并不爱的女性,都觉得负有道德上的义务,都有些优柔寡断。吉姆对女讲师玛格丽特的态度和方鸿渐对苏小姐的态度如出一辙,正是这样一种暧昧的态度,让他们在追寻真爱之旅上备受打击,但不同在于吉姆有不达目的誓不罢休的劲头,而方鸿渐则一有挫折就容易灰心丧气进而放弃,正是由于这一点上的不同,二人的爱情结局截然不同,吉姆收获了适合他的爱情,抱得美人归,而方鸿渐则一错再错,娶了他并不心爱的孙小姐,婚后生活郁郁寡欢,与吉姆相比,呈现出悲喜两重境界。
从两位主人公人生轨迹的比较来看,也是意味深长的。吉姆栖居于一所普通大学的历史系,教职能否保住要看威尔奇主任脸色,人生轨迹低而平缓地开始,到与学校闹翻,人生轨迹到了最低点之际,突然天降喜讯,另有高就,而人生轨迹得以猛烈上扬。方鸿渐则是海外留洋回来,意气风发,人生轨迹高调开始,却无奈在当时动荡的大背景下一路走低,最终家庭、事业均是一蹶不振而结束。一出喜剧,一出悲剧,吉姆和方鸿渐迥异的人生轨迹带给我们同样深刻的人生思考。如果说吉姆的幸运系作者刻意安排所致,却也不可否认他自身的某些性格特点使得他并不适合呆在校园里,比如说他的反叛性,比如说他会主动追求已有男友的克莉斯廷,并收获真爱,而方鸿渐性格里的懦弱和犹豫,却使他在面对他真正喜爱的唐小姐时,始终不够积极主动,而与唐小姐遗憾地擦肩而过,所以方鸿渐的悲剧既是国家时代的悲剧,也是他自身性格的悲剧,
在与《围城》比较之后,可以看出,吉姆的幸运在于他体现了英国上世纪50年代的时代脉搏,因而为那个时代所亲睐,成为了那个时代的代言人,意气风发,收获了爱情与事业的双丰收,以喜剧收场;而方鸿渐则不然,他书生气十足,却总是感觉处处不得志,无论事业上,还是爱情上,他都是比较被动消极,随波逐流,在20世纪30年代动荡不安的中国,像当时很多中国人一样,他的命运是以悲剧结尾的。他与吉姆的遭遇呈天壤之别,正是时代命运与个人性格差异所致。虽然创作处于不同的时代,体现的是各自的时代特色,但在幽默性和夸张性上的出色表现,使得这两部作品都成为讽刺文学的经典,并且对后续的作家和作品均产生了深远的影响。
[1]瞿世镜,任一鸣.当代英国小说史[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8:32.
[2]金斯利·艾米斯.幸运的吉姆[M].南京:译林出版社,1998.
[3]阮炜.社会语境中的文本:二战后英国小说研究[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8:55-68.
[4]聂珍钊,等.英国文学的伦理学批评[M].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7.
[5]钱钟书.围城[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1.
[6]侯维瑞,李维屏.英国小说史[M].南京:译林出版社,2005.
[7]王守仁,何宁.20世纪英国文学史[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15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