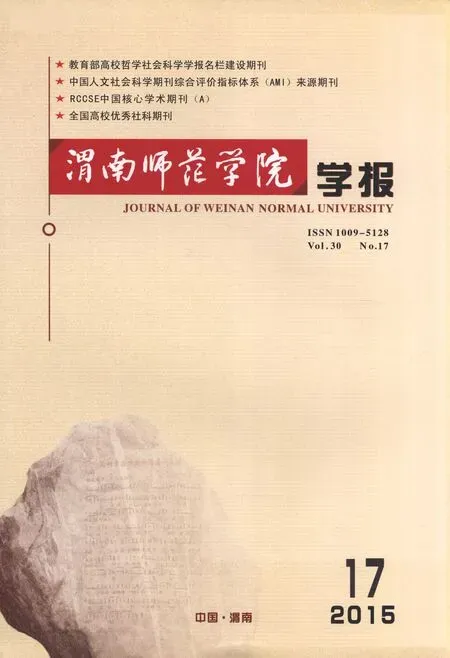电影艺术中的隐喻手法
2015-03-20孟丽花
孟 丽 花
(渭南师范学院 传媒工程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新闻与传播研究】
电影艺术中的隐喻手法
孟 丽 花
(渭南师范学院 传媒工程学院,陕西 渭南 714099)
隐喻作为文学的修辞手法进入电影艺术中后,衍生出了众多的构成元素。电影作品在视觉上可以运用物件细节、仪式以及特殊的场景构成隐喻,含蓄而形象地揭示主人公的性格,预示人物的命运。《天云山传奇》中熄灭的蜡烛,《菊豆》中的挡棺,《小城之春》中颓败的小城都是典型的视觉隐喻。除此之外,电影作品中常见的隐喻构成元素还有音乐和音响,尤其是音响的巧妙应用,可以含蓄地点明作品的主题意蕴。《大红灯笼高高挂》就通过捶脚的音响隐喻了男权掌控之下囿于院落的女人的悲剧命运。在电影中运用隐喻应该遵循含蓄生动和雅致双重原则。
隐喻;物件;仪式;音响
隐喻原本是文学中比喻修辞的一种,又称为暗喻,与明喻相对。明喻一般用“像”“似”之类的词语连接本体和喻体,隐喻使用“是”“成为”“变为”或“等于”之类的词连接本体和喻体。“艺术创作中意义和可供观照的意象结合在一起而只提意象一个因素的表达方式”[1]237就是隐喻。不论是传统的文学艺术、绘画艺术还是现代的电影艺术,都会运用隐喻手法,增强作品的艺术感染力和表现力。
一、隐喻手法:从文学到电影
传统的文艺作品惯用隐喻手法,以含蓄隽永的方式衬托人物品格或是传达主题意念。
以诗歌为例,《七步诗》就是运用隐喻手法的典范。“煮豆燃豆萁,豆在釜中泣。本是同根生,相煎何太急?”传说这首诗是曹植在曹丕的逼迫之下所作,曹丕要求曹植在七步之内成诗,不然就要取他性命。曹植诗中字字在说豆与豆萁,实际上句句直指曹丕,对同室操戈手足相残加以诘问。这首诗之所以流传广远,隐喻手法的巧妙应用功不可没。
著名的乐府诗《孔雀东南飞》也多次运用隐喻手法,开篇的“孔雀东南飞,五里一徘徊”,结尾的“东西植松柏,左右种梧桐。枝枝相覆盖,叶叶相交通”。其中的孔雀、松柏、梧桐都已经由生活中的物经由艺术作品的情境上升为有所隐喻的“意象”。意象“是由表象概括而成的理性形象,是事物的表层与主体对其深层之理解的辩证统一”[2]221。创作主体对隐喻本体的深层理解表现为隐喻的喻体。
传统文学理论中涉及隐喻手法的书籍著作颇多,隐喻手法属于赋比兴中的“比”和“兴”。尤其是“比”中的隐比,就是今天所说的隐喻。梁钟嵘所著《诗品序》中对赋比兴有这样的界定:“故诗有三义焉:一曰兴、二曰比、三曰赋。文已尽而意有余,兴也;因物喻志,比也;直书其事,寓言写物,赋也。”宋代朱熹在《诗集传》中也论及比兴手法:“赋者,铺陈其事而直言之也。比者,以彼物比此物也。兴者,先言他物以引起所咏之词也。”以李商隐的《登乐游原》为例,诗中的“夕阳无限好,只是近黄昏”,就符合比兴手法的特征,以黄昏中的夕阳比拟人生暮年,虽然仍有温暖美好的余热,但人生终点在望,让这温暖和煦沾染上了一丝迟暮惆怅之意。
这是文学艺术中的隐喻手法。电影作为19世纪末期诞生的新型艺术样式,在探寻本体艺术语言、丰富叙事手法的过程中,向传统的姊妹艺术借鉴了诸多艺术技巧,其中就包括隐喻。由于艺术语言的差异——文学以文字为媒,建构间接的艺术形象,电影则是借助于视听元素以更为直观具体的方式完成人物形象塑造和主题传达,电影艺术中的隐喻与文学中的隐喻有一定的差异,即需要借助于某种声音元素或是视觉元素来构成隐喻,但本质上是同一种艺术手法。
二、电影隐喻的视觉构成元素
让·米特里认为:“当我们看到银幕上的花束时,我通过呈现给我的影像想到实物。这个实物作为内在的真实,作为排除一切意向性的事物投入我的意识。”[3]344电影艺术最初的30余年是默片,如何通过视觉元素构成隐喻就成为早期电影导演们关注的核心问题之一。电影艺术中的隐喻手法也称为隐喻蒙太奇,是苏联电影艺术家爱森斯坦最早明确提出的一种表现蒙太奇技巧。在表现俄国1905年革命的电影《战舰波将金号》中,爱森斯坦把隐喻蒙太奇付诸实践。作品以长达六分钟的篇幅,运用快速剪辑和重复剪辑的方式展现沙皇政府的军队如何对手无寸铁的平民百姓进行血腥屠杀,形成了电影史上影响深远的著名段落“敖德萨阶梯”。之后导演切入了三个石狮子,分别是沉睡的狮子、苏醒的狮子、怒吼的狮子,来含蓄而生动地表达对于沙皇政府这种惨无人道的行径的控诉。这三个石狮子是爱森斯坦和摄影师基赛在沙皇的行宫前看到的三个大理石雕塑,经过巧妙的剪辑之后,原本普通的雕塑具有了艺术生命,这就是隐喻手法的微妙之处。由此也可以看出,某一种物件能否构成隐喻蒙太奇一方面与物件本身的含义有关,此处的狮子不同于一般的雕塑,狮子本身就是力量的化身,倘若换成猴子、孔雀之类的,就难以传达出愤怒;另一方面,隐喻蒙太奇的构成有赖于前后语境也就是场景,狮子由沉睡到苏醒再到怒吼,到底隐喻的是愤怒、控诉还是凶残,观众会通过镜头前后的语意逻辑来理解。爱森斯坦之后的电影后继者把隐喻技巧发挥得淋漓尽致,探索出了多种多样的隐喻元素。
构成隐喻的常见视觉元素有:物件、仪式、场景等。
物件是指出现在镜头中的物品,通过与相邻镜头的组合,这一物品能够承载更丰富、深刻的含义进而构成隐喻蒙太奇。“隐喻是建立在事物之间可互相转化和互相关照基础上的,它们之间的审美价值来自于其中的张力。”[4]在谢晋导演的《天云山传奇》中,有这样一个情节段落:在政治运动中被错划成“右派”的知识分子罗群,如今衣衫褴褛,在赶马车之余仍不忘继续自己关于开发天云山的研究,妻子冯晴岚当年顶着种种压力选择站在孤立无援的罗群身边,近20年里两个人患难与共,过着物质清贫但精神丰腴的生活。如今罗群终于要平反了,由于积劳成疾,冯晴岚的生命却走到了尽头。导演是这样来表现她生命的最后一刻的:
(1)特写,过肩镜头,冯晴岚用微弱的声音告诉丈夫自己想再看看他。
(2)特写,罗群的手拿起眼镜替她戴上。
(3)特写,冯晴岚戴上眼镜之后的脸。
(4)近景,仰拍镜头,罗群的脸渐渐模糊。
(5)特写,冯晴岚闭上了眼睛,头倏然歪向一侧。
(6)大全景,临窗的桌子上,冯晴岚的照片旁边,一支即将燃尽的蜡烛熄灭,袅袅的余烟飘起。
(7)特写,冯晴岚破旧的背心。
(8)特写,案板上没有切完的腌菜。
(9)特写,挂着补丁的窗帘。
上述情节段落中,出现的物品较多,有眼镜、照片、蜡烛、背心、腌菜、窗帘。其中的蜡烛具备构成隐喻蒙太奇的特质。一方面,俗语说“人走如灯灭”,蜡烛熄灭寓意着冯晴岚辞世。另一方面,蜡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是一个特殊的意象,李商隐的《无题》诗中有云:“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蜡烛和春蚕都被认为是奉献精神和无私品格的化身。因此,镜头中这支即将燃尽的余烟缭绕的蜡烛正是主人公冯晴岚高尚品格的隐喻。在罗群落难继而患病的日子里,她冒着大雪,以柔弱的身躯用板车把罗群拉回了家,用尽自己所有的心力为罗群搭起避风的港湾,这种精神品格恰好与洁白无私的蜡烛一致。因此,这里的隐喻手法用得巧妙。借助于物件进行隐喻的影片不胜枚举,吕克·贝松导演的《这个杀手不太冷》中与莱昂朝夕共处的绿色盆栽、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中桌角的那盆兰花都是主人公品格命运的隐喻。陈凯歌导演的《黄土地》中,也有成功的物件隐喻,“黄河隐比了传统文化的洪流”[5]21。
除了具体可观的物件之外,仪式也成为构成隐喻的常用手段。尤其是在张艺谋导演的作品中,民俗仪式往往成为隐喻人物命运遭际的主要手段。通常人们认为在电影作品中增加民俗仪式等内容,能够增强作品的可观赏性。实际上,仪式的艺术价值远不止制造视觉奇观这么表面化,它还是一种含蓄生动的隐喻手段。以《菊豆》为例,“挡棺”的段落就明显印证了这一点。
《菊豆》是张艺谋导演在1990年拍摄的影片,改编自刘恒的小说《伏羲伏羲》。作品在染坊主杨金山和他的年轻的妻子菊豆、远房侄子杨天清三个角色之间铺陈情感纠葛。年届五旬的金山为了延续香火,以二十亩地的彩礼娶了菊豆,续弦之后的金山不愿承认自身的生理问题,虐打久未有孕的菊豆。与菊豆年纪相仿的单身汉天清对这个年轻美丽又悲苦的婶子暗生情愫,两人最终珠胎暗结。起初,金山喜出望外,后来知晓真相的金山,以让儿子天白喊生父天清为哥的方式,聊以报复。金山百般阻挠、诅咒菊豆和天清,但最终中风瘫痪,有心无力。金山死后,杨家族人要求菊豆守妇道,保贞节,不准改嫁,而且为了证明杨家世世代代清清白白,杨天清必须搬出染坊大院。按照民俗,族人安排了挡棺的仪式,要求遗孀菊豆和晚辈天清在葬礼上为金山拦路挡棺,而且要挡七七四十九回,以示孝心。在这一段落中,导演用重复剪辑的方式以较长的篇幅展示了这个充满封建色彩的仪式。开始使用的是客观镜头,以平拍视角展示哭得撕心裂肺的菊豆和天清扑在棺材前大喊着“你不能走啊!你等等我!”然后双双被扶灵人压倒在地,厚重的棺椁从两人的头上高悬而过。渐渐镜头转化成主观视角的大仰角,华丽厚重的棺椁一次次漫过菊豆和天清的头顶,直到两个人完成了挡棺,精疲力竭地跪倒在路上。这一挡棺仪式不仅仅是还原式的,展示富有地方特色和年代感的风俗仪式只是表面的由头,挡棺仪式的真正艺术价值在于对菊豆命运的隐喻。菊豆是一个典型的受到“三从”精神枷锁奴役的悲剧性女性。在家从父,所以年轻美丽的菊豆才会被父亲以近乎售卖的方式嫁给并不般配的杨金山;出嫁从夫,菊豆嫁到杨家,始终遭受杨金山的折磨与压制,即使金山死了,在葬礼上,菊豆还不得不上演一出贞洁烈妇“恨不能随夫君西去”的戏码。至于夫死从子,一方面挡棺段落中已经有所体现——当菊豆和天清号哭着挡棺的时候,端坐在棺椁上方的正是天白,金山死了,天白接过金山手中的权杖,继续左右着菊豆和天清的情感;另一方面,后续的故事情节也印证了儿子杨天白对菊豆命运的掌控。天白对自己的生父是天清这一事实愤懑不已,最终选择棒杀天清。菊豆眼见父子相残,最终一把火烧了染坊。所以,天白从血脉上是天清之子,但从精神层面上来讲,他完全承继了杨金山的衣钵,成为压垮菊豆命运的最后一根稻草。因此挡棺的仪式在作品中以含蓄的方式完成了对人物命运的隐喻。
与此相类似的隐喻性仪式还有《大红灯笼高高挂》中的点灯、封灯。同样通过富有民俗色彩的仪式对人物的命运进行隐喻。
此外,电影作品还可以通过场景构成隐喻。费穆导演的《小城之春》中颓败的小城、残破的院落,吴永刚和吴贻弓联合导演的《巴山夜雨》中那条承载着形形色色的人物、供各色人等进行思想交锋的客轮,都是历史上某个年代的隐喻。
不论是物件、仪式还是场景,都是视觉性元素,电影作品还可以通过听觉元素构成隐喻。
三、电影隐喻的听觉构成元素
电影在1927年进入有声时代,终于告别了“伟大的哑巴”这样一个遗憾与赞誉并存的称号。在有声时代,导演可以充分发挥人声、音乐和音响的艺术表现力,其中音乐和音响都可以构成隐喻。以音响为例,创作者恰当地运用音响同样可以与相连镜头形成隐喻蒙太奇。与前三种构成元素物件、仪式、场景一样,能够构成隐喻蒙太奇的音响也早已超越了客观还原的浅表层面,具备了传递更深层的思想内涵的艺术功能。《大红灯笼高高挂》中就有典型的音响隐喻。四姨太颂莲甫一入府,就察觉到陈府的与众不同。每日黄昏,姨太太们在各自院门前垂手而立,等着管家宣布哪个院子“点灯”——点灯就意味着老爷今晚要在此处就寝。院子里亮起红灯笼,这位姨太太就会接受曹二婶的捶脚服务。在争风吃醋钩心斗角之际,颂莲看透了二姨太卓云两面三刀的伪善面目,在给她剪头发的过程中,失手伤到了卓云。卓云向老爷告状,老爷以二院持续多日点灯的方式安慰卓云。正当头裹纱布的卓云享受着曹二婶的捶脚时,颂莲上门来道歉。卓云一面作出一副豁达宽容的姿态,一面娇嗔地让曹二婶轻点捶。颂莲不悦,回到自己的院子。此时,琅琅的捶脚声清晰可辨。丫鬟雁儿正坐在破旧的矮炕上,闭目假想自己被捶脚,被颂莲的呼喊声惊醒,颂莲要求雁儿为自己捏脚,乖张的雁儿极不情愿,讥讽道:有本事你让曹二婶给你捶啊!整个过程始终伴有琅琅的捶脚声。从持续时间和音量上可以判断,这里的音响已不是写实的营造环境真实感的声音元素,萦绕在卓云、颂莲和雁儿耳畔和心头的捶脚声其实是陈府里掌握所有女人命运的老爷的化身。“在设计音响和利用音响的时候,要注意的是,由于电影音响的自在隐喻性,一定要使音响与其他电影元素紧密结合起来,不可失当。”[6]
由此可见,在电影作品中,构成隐喻手法的元素是多元的,既可以是物品、仪式,也可以是音响、故事场景等。使用隐喻手法能够含蓄而生动地传达主题意蕴。当然,在使用隐喻手法构建隐喻蒙太奇的过程中,有一些基本的原则需要遵守。
四、隐喻手法的应用原则
在作品中应用隐喻手法,首要的原则是含蓄生动。在电影艺术的初创时期,导演们对这一手法的认识相对有限,往往出现一些生硬直白的隐喻蒙太奇组接。查理·卓别林1936年自导自演的喜剧片《摩登时代》中就曾把工人放工的镜头与拥挤的羊群出圈的镜头相连,这一镜头段落的隐喻意义很明确,那就是对工人生存境遇的同情,但这种隐喻手法稍显生硬,羊群、羊圈与工人、工厂之间缺乏现实的连接点;《天云山传奇》在表现冯晴岚辞世时使用蜡烛则很自然,符合当时的故事情境和环境特点。因此,在选择构成隐喻的元素时,要考虑这一元素即喻体与本体之间的关联是否自然和谐,避免生搬硬套、牵强附会。
另一个原则就是雅致。隐喻手法往往取的是喻体形而上的文化寓意,而不是形而下的物质属性。流行歌曲中有这样一句歌词:“咱俩的感情像条鞋带,把你和我俩人绑在一块。”把美好的情感比作仅仅具有形而下的物质属性的鞋带,这种比喻就是失败的,当然这里是一个明喻,但原则上都应该力求雅致。
[1] 朱立元.艺术美学词典[K].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2.
[2] 王炳社.艺术思维学[M].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3.
[3] 李恒基,杨远婴.外国电影理论文选(上册)[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6.
[4] 王炳社.论艺术隐喻的本质、特征与方法[J].西北农林科技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2):84-87.
[5] 刘成汉.电影赋比兴[M].北京: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
[6] 王炳社.电影隐喻略论[J].电影文学,2010,(8):4-6.
【责任编辑 马 俊】
The Metaphorical Montage in the Movie
MENG Li-hua
(School of Media Engineering, Weinan Normal University, Weinan 714099, China)
Metaphor is often used to be one ordinary skill in literature. Nowadays, it has become one important skill in the narration of movies. There are several kinds of elements which could be used as metaphorical image, such as special object, ceremony and scene. These images reveal the characters of the roles and herald their destiny. The candle in the movie Tianyunshan Legend, the ceremony of stopping the coffin in the movie Ju-dou and the decadent city in the movie Spring in the Small City are examples of visual metaphor. The sound also constitutes metaphorical montage. The clang of beating the feet in the movie Rising the Red Lantern reveals the tragedy of women. Metaphorical images should be vivid and elegant.
metaphor; object; ceremony; sound
J904
A
1009-5128(2015)17-0077-04
2015-03-23
渭南师范学院科研计划项目:中国西部电影创作与当代文化价值观建设研究(14SKYM18)
孟丽花 (1983—),女,山东临沂人,渭南师范学院传媒工程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影视剧理论与创作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