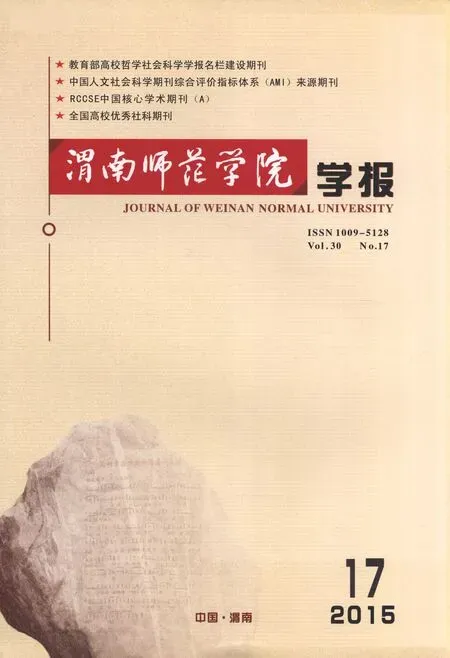变换分析与句法结构价值
2015-03-20王红生
王 红 生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语言文化与文学研究】
变换分析与句法结构价值
王 红 生1,2
(1.南开大学 文学院,天津 300071;2.宝鸡文理学院 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陕西 宝鸡 721013)
语言的本质是关系,变换分析不是方法上的问题,而是基于语言的联想关系而将意义相似的不同语法形式联系起来分析句法结构之间关系的一种理论分析原则。能相互变换的句法结构的不同语法形式所表达的语法意义内容不能简单地视作是“同义”,而只能看作是在意义内容上相似,这些表达相似意义内容的能相互变换的语法形式在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中相互对立而取得各自价值。
变换分析;联想关系;价值;理论原则
一、两种语法“变换”思想
变换分析,汉语学者一般将之视作一种重要方法来研究汉语句法问题。我国学者吕叔湘的《中国文法要略》里已经有变换分析的思想,这种分析思想得到朱德熙的特别肯定,并说“《要略》应该说是研究汉语句法结构变换的先驱”[1]。可是,吕先生的这种思想并未引起当时汉语学者的充分重视,也就谈不上这种方法在当时的语法研究中有什么重要影响。真正影响汉语学者的语法“变换”思想(包括变换分析本身的理论基础、研究程式、方法要求等)主要来自美国的语言学,其理论主要贡献者是海里斯和乔姆斯基。这两个人曾经是师生关系,但一个是描写语言学派的,一个是生成语言学派的,虽然都用transformation来表达他们的语法思想,但他们的transformation思想却有本质不同。为示区别,中国的学者一般把海里斯的transformation译作“变换”,而把乔姆斯基的transformation译作“转换”*可见陆俭明《八十年代中国语法研究》(商务印书馆2004年)第24页,或《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年)第83页。。客观地讲,汉语句法分析实践中,人们更多用的是海里斯的transformation思想,却不是乔姆斯基的。本文所说的“变换”主要是来自前者,而不是后者。为了全面、深入探讨变换分析在语法研究中的意义,在论述本文的主题之前,有必要先简单评价一下乔姆斯基的语法“转换”思想,这主要是基于两种考虑:其一,海里斯和乔姆斯基的transformation思想虽然有本质不同,但二者都重视transformation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且后者明显来自前者,只是他们的语言观(或语法观)不同,从而将这种分析注入了截然不同的理论色彩;其二,本文的目的是要进一步研究“变换”这种句法分析的理论依据、理论效能,并要详细探讨这种分析所带来的语法研究新任务,以及对汉语语法研究的意义,而乔姆斯基的语法“转换”思想的成败或修订发展过程,或许能够启示我们对这一问题的深入思考。
乔姆斯基的生成语言学产生以后,语言学者对这种新语言学毁誉参半,本文不加细评这种学说,只说它的“转换”思想。乔姆斯基认为,一种语言中全部无限的句子可以用一套有限的规则生成。乔姆斯基早先采用的规则主要是短语结构规则和转换规则,他规定在运用转换规则之前,必须先使用短语结构规则。短语结构规则也叫短语结构语法,这种规则写成:①S→NP+VP;②NP→Det+N;③VP→V+NP。短语结构规则只能生成一种语言的一部分句子,乔氏在“经典理论阶段”把用这种规则生成的句子叫“核心句”(包括简单句、主动宾陈述句等),如:John saw Mary等等。可是,仅靠短语结构规则不能生成一种语言的全部句子,还得用转换规则,它是在短语结构规则的基础上制定的新一套规则,乔氏在“经典理论阶段”把用这种规则生成的句子叫“非核心句”(包括疑问句、祈使句、命令句、被动句等)。如被动句Mary was seen by John是由核心句John saw Mary用转换规则(移位和添加by的规则等)变来的等等。到了“标准理论阶段”,乔氏提出了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两个概念,而表层结构是从深层结构通过转换实现的。比如,John saw Mary,Mary was seen by John等是从相同的深层结构变来的,它们的逻辑语义结构相同。这个阶段的“转换”是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中介,表层结构决定于深层结构,表层决定语音,深层决定语义。可是,语法学者后来发现,表层结构其实也对语义有影响,有的学者甚至主张取消深层结构这样的概念,例如:everyone in the room knows two languages,two languages are knows to everyone in the room这两句,深层结构虽一致,但语义并不同(two languages有定和无定的区别),这种区别就在于表层不同。这样,乔氏对他的理论又做了重新修订,到了“扩展的标准理论阶段”,虽然还保留了“深层结构”和“转换”这样的概念,但他把句子的语音和语义规则的解释倾向于全都放在表层结构了。徐烈炯对乔姆斯基各个阶段的“转换”思想有详细论述*见徐烈炯《生成语法理论》,上海外语教育出版社1988年版。,可以参考。
从乔姆斯基对“转换”的论述可以看出他的思想特征及发展趋势:其一,“转换”连接的是一组相互联系的句法范畴,而这些句法范畴以“转换”为中介。用这种观念建立语法学体系,可以使语法论述形式化、简洁化、程式化,这是它的优点。但是,将“转换”用在这些句法范畴中,其语言学基础却值得怀疑。比如,人们说话、使用语言的过程是否经历过这样的心理“转换”?比如,一个汉人说“小王打碎了花瓶”,是不是这个汉人心中先有个心理“转换”过程,然后才有“花瓶被小王打碎了”这样的句子?恐怕不是。事实是,一旦有表达的需要,认为汉人会直接说出“花瓶被小王打碎了”这样的句子的,并不见得一定会有这样的“转换”。这种心理过程可能是虚构的。第二,乔姆斯基设立的、用“转换”所连接的看起来相对的语法范畴——比如核心句和非核心句——在语言中是否存在也值得怀疑。比如,在一种语言系统中,我们很难规定哪些是核心句,哪些是非核心句,如果认定有核心句和非核心句的区别,这种区别的标准和依据是什么?恐怕很难确定。如汉语的“小王打碎了花瓶”“花瓶被小王打碎了”,我们据什么理由说前者是“核心”句,后者是“非核心”句呢?其实,这两种句式在汉语中都存在,它们在汉语句法系统中是地位平等的成员,重要的是它们既相互联系也相互对立。胡明扬曾根据西方语言学的变换思想,将具有相互转换关系的、类似于“核心句”和“非核心句”这样的语法概念称作“基本句式”和“派生句式”,不过,他也承认这种划分“可以有不同的理解”。[2]“派生”本是个语言历时变化的概念,而“基本句式”和“派生句式”是语言共时秩序中并存的句法形式。如果这些范畴是人为设定的、非语言真正有的,那就是虚拟的语法范畴。其三,从乔氏思想的发展过程来看,“表层结构”的地位更加凸显。先是从表层谈转换关系,后来设立个“深层结构”,谈深层结构和表层结构的转换关系,后来发现有的语义没法用“深层结构”解释,又将研究的重点放在“表层结构”上了,这样,乔姆斯基绕了一大圈,又回到原先的起点上了,这是个非常有趣的现象。实际上,“表层结构”已经包含了“深层结构”的内容,而“深层结构”的内容却未必能完全能解释“表层结构”的内容,难怪有的学者提出“深层结构”可以取消的观点。
本文介绍乔氏的transformation理论,为的是把“变换”思想在语法研究中的作用引向深入,并非完全否定转换生成语法的成就。我们虽然不全同意乔氏的transformation说,但对乔氏重视transformation在语法研究中的重要作用却是肯定的。长期以来,人们一般都把变换分析叫“法”,即“变换分析法”,即把变换分析看作方法问题。需要知道,如果仅把变换分析看作方法,那就有一些附带特点。比如,人们一谈到方法,就意味着可用不可用,或者说这种方法只能用在某种特定场合,别的场合便不适用。也许有这种定位,人们很少进一步讨论变换分析的语法学性质问题。深入认识变换分析在语法研究中的地位和作用,我们在这方面还探讨得不够。本文以为,确定一种语法分析的性质是基于对语言本质的认识,如果语言本质决定了必须考虑一种语法分析,那这样的语法分析就应视作是语法研究的理论原则,而不能仅把它看作方法问题。“理论原则”和“方法”有根本区别,前者是语法研究中必须要考虑的,并非可用不可用,后者则是可用可不用。如果确定一种分析是理论原则,这种语法分析可以从语言的本质属性的认识上找到它的依据。基于此,笔者更愿意将变换分析看作语法研究的一种理论原则,而不是方法论的问题。本文要从语言的本质属性说起,论证语法变换分析的语言学依据,说明变换分析是基于语言的本质属性而决定了的分析原则这个问题,并且初步探讨一下由此而得出的一些语法研究需要重视的问题。
二、语言的系统性与变换分析的理论基础
第一个全面、深入、科学论述语言本质属性的是现代语言学之父、瑞士语言学家费尔迪南·德·索绪尔。索绪尔认为语言是一种符号系统,系统的主要表现是关系,而语言学则是一门研究关系的学问,这跟传统语言学重在研究言语是大不相同的。
索绪尔说,“在语言状态中,一切都以关系为基础的”,他提出了语言的两种关系:句段关系、联想关系。“一方面,在话语中,各个词,由于它们是连接在一起的,彼此结成了以语言的线条特征为基础的关系,排除了同时发出两个要素的可能性。这些要素一个挨着一个排列在言语的链条上面。这些以长度为支柱的结合可以称为句段。”“另一方面,在话语之外,各个有某种共同点的词会在人们的记忆里联合起来,构成具有各种关系的集合。……它们不是以长度为支柱的;它们的所在地是在人们的脑子里。它们是属于每个人的语言内部宝藏的一部分。我们管它们叫联想关系。”“句段关系是现场的;(in praesentia):它以两个或几个在现实的系列中出现的要素为基础。相反,联想关系却把不在现场的(in aesentia)要素联合成潜在的记忆系列。”[3]170-171这种论述可概括为:句段关系以语言符号的“线条性”为基础,是两个或两个以上要素按照一定的规则的组合起来的结构,是显性的,可感、可观察的;而联想关系则是将有相似点的要素凭借记忆联想在一起,它不是显性的,而是潜存在一群人的大脑里。重要的是,在语言系统中,语言的这两大关系——句段关系和联想关系——有着连带关系,只有将这两大关系联系起来才能正确地认识语言系统。索氏说:“事实上,空间上的配合可以帮助联系配合的建立,而联想配合又是分析句段各部分所必需的。”每个组合都“有两个联想系列作为它的支柱”[3]178-179,也就是说,我们靠句段关系来建立联想关系,而每个句段关系必得以联想关系为基础才能形成。语言就是这两大关系相互起作用所成的网络系统。上面介绍的这两种关系的概念,索绪尔是以“词”为对象来说明的,实际上,包括句法结构在内的语言一切要素,都是在这两大关系的范围内展开的。语言研究应是在对语言的这种本质属性的认识的基础上来确定自己的理论原则。
从哲学上讲,任何事物都是形式和内容的统一体,句法结构也是如此,它是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相结合的表达线性结构关系的整体。这里的“形式”是语法形式,如语序、虚词、形态变化、重叠等等;这里的“意义”是语法意义,即词与词之间的关系意义。句法结构的形式和意义没法分离,形式离开了意义就不是表达语法意义的语法形式,意义离开了语法形式也算不上是语法形式表达的语法意义,分析句法结构应坚持形式和意义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应避免孤立地看待形式或意义。
索绪尔认为语言符号具有任意性,这是为一般学者认同的。同样,我们也要指出,句法结构的组成部分——形式和意义——的结合也是任意的。也就是说,一个民族的语言的语法结构采取什么样的形式来表达什么样的语法意义完全是这个民族的约定和习惯,没有理据性可言,正如陈望道所说的:“文法是一种民族的社会习惯,它是经过长期的历史积累而形成的。”[4]13比如,为什么汉语是SVO型语言,而波斯语是SOV型语言,为什么英语的第一人称代词做宾语用宾格形式,而汉语没有这样的变化,说不出什么理由,完全是讲两种语言的不同民族的习惯造成的。分析句法结构实际上就是要分析结构形式和意义凭着任意性原则相结合的对应关系以及结构整体之间的相互关系。
从理论上讲,分析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也得从索绪尔论述的两大关系入手,才能全面分析这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本文只限于论述跟变换分析相关的句法结构之间的关系,而这种分析却主要是基于句法结构的联想关系。胡明扬在谈到句法系统、句式转换之间的关系时说:“系统性表现在……各种各样的句子相互之间通过各种有规则可循的转换关系或者说变化方式构成一个整体,而不是杂乱无章的一个无序的集合。因此,古往今来,不论是传统语法,还是习惯语法,还是生成语法,还是功能语法,不论是暗含的还是明说的,都有一个基本句式体系,而其他句式则是通过有限的不同手段形成的相关的变式。确立基本句式和变式就是要反映语言的系统性,或者像很多人所说的那样,是为了‘以简驭繁’。从基本句式到变式有一套转换规则,而这些转换规则还可以归结为少数几种类型,这样,千变万化的各种句子形式就构成一个有规则可循的、互相联系在一起、互相制约的系统。”[2]胡先生这里所说的“系统”, 跟克里斯特尔列出的现代语言学两种常见的定义之一“任何一组数目有限的、有形式和语义联系的单位,单位之间既是相互排斥的又是相互定义的”[5]351-352相符,相当于索绪尔所说的“联想关系”。
对一种语言的句法结构来说,只要在某一点上——形式上或意义上——有相似的都可以建立起联想关系来,这也意味着同一个句法结构可能处在多个联想系列中。认识一个句法结构的语法性质,不能限于这个结构所处的一种联想系列,而要全面考察这个结构所处的各种语法联想系列,这样才能发现这种结构的语法特征。为了方便说明问题,我们以汉语学者曾举过的用例来说明这个道理。比如:
[A] [C]
门口站着人 → 人站在门口
前三排坐着来宾 → 来宾坐在前三排
床上躺着人 → 人躺在床上
黑板上写着字 → 字写在黑板上
墙上挂着画 → 画挂在墙上
门上贴着对联 → 对联贴在门上
山上架着炮 → 炮架在山上
[B] [D]
门外敲着锣鼓 → 门外正在敲锣鼓
外面下着大雨 → 外面正在下大雨
大厅里跳着舞 → 大厅里正在跳舞
隔壁打着电话 → 隔壁正在打电话
操场上放着电影→ 操场上正在放电影
教室里上着课 → 教室里正在上课
山上架着炮 → 山上正在架炮
就语法结构的形式说,[A]、[B]都是“NP[处所]+V+着+NP”式的,[C]是“NP+V+在+NP[处所]”式的,[D]是“NP[处所]+正在+V+NP”式的。从语法形式和语法意义两方面可以建立不同的联想关系。就语法形式而言,所有[A]和[B]的语句都是“NP[处所]+V+着+NP”式的,它们可以基于语法形式相同列成一个联想序列;从语法意义的相似点说,[A]、[C]和[B]、[D]的语法形式分别不同,但可分别构成两个不同的意义联想系列,[A]、[C]都表示了“存在、静止”的语法意义,[B]、[D]都表示了“活动”的语法意义。如果仅考虑形式上的联想关系,是难以解决[A]和[B]内部语法上的差别性的,还要从不同形式表达的意义的联想关系上去判断。其中,“山上架着炮”之所以有歧义,就是因为它处于两个不同的意义联想序列——[A]、[C]和[B]、[D]——中。从这个例子可以看出,变换分析的实质是根据句法结构的联想关系来确定句法结构的语法性质,它突破了仅仅从表面上相同的语法形式建立联想关系的局限,而且考虑到从语法意义的相似点上将不同的语法形式联系起来,而这些不同的语法形式的变换正是基于语法意义上相似的联想关系。
三、变换分析的相关句法形式 有各自的语法价值
语言中存在大量相互联系、可以相互变换的句法形式,这是变换分析的基础,但仅仅看到它们的相似是不够的,语法还要研究这些相互联系的各个句式之间的差别。陆俭明认为“变换分析法”的客观依据是“句法格式的相关性”,“这种相关性的前提条件是,句法中所包含的各个实词之间的语义结构关系一致”,即不同句式是“同义句式”。[6]84-86这里的问题是变换分析的相关句式是否能算作“同义”?我们知道,语言学中的“意义”是个复杂的问题,什么算作“意义”,“意义”包括哪些、不包括哪些要素,这是个复杂的问题。陆先生这里所说的“同义”的“义”,实际上只是命题意义或者逻辑语义,而不是句法形式表达的完整意义。对于传统所认为的变换“不改变句子的意义”的看法,胡明扬曾指出:“这里的‘不改变句子的意义’应该理解为‘不改变句子的命题意义’,因为实际上语法形式方面的任何变化都会引起语义内容不同性质和不同程度的变化,或者是语用方面的变化,或者是修辞方面的变化等等,仅仅是命题意义基本上没有重大变化而已。这一点似乎在语言学界意见还比较一致。”[2]我们说,意见一致是一回事,将所看到的意义差别作为语言研究的一个重点来做是另一回事。从理论上讲,句法结构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一种形式和一种意义相对应,形式不同则表达的意义不同,不同的意义则选择不同的形式来表达,语法就是要研究不同形式和不同意义的对应关系。如果两种形式表达的意义完全相同,那么语言会自动淘汰一种,而选择其中的一种,如果一种形式表达两种不同的意义,那么语言会产生另一种形式来区别。在一种语言系统中,存在着大量相互联系、可以相互变换的句法形式,这些形式之所以能并存,说明它们有各自的功能和地位,也说明它们在表达的内容方面肯定存在差别,而这些差别则是我们要认真研究的。本文要用索绪尔的语言价值学说对这个问题做初步的探讨。
“价值”这个概念本是经济学的术语,索绪尔将它拿来探讨语言学问题,而认为语言是一个纯粹的价值系统。他所说的“价值”是什么含义呢?索绪尔认为,一切的价值由两方面组成:“(1)一种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交换的不同的物;(2)一些能与价值有待确定的物相比的类似的物”“要使一个价值能够存在,必须有这两个因素。例如,要确定一枚五法郎硬币的价值,我们必须知道:(1)能交换一定数量的不同的东西,例如面包;(2)能与同一币制的价值,例如一法郎的硬币,或者另一币制的货币(美元等等)相比。同样,一个词可以跟某种不同的东西即观念交换;也可以跟某种同性质的东西即另一个词相比。因此,我们只看到词能跟某个概念‘交换’,即看到它具有某种意义,还不能确定它的价值;我们还必须把它跟类似的价值,跟其他可能与之相对立的词比较。我们要借助于在它之外的东西才能真正确定它的内容。词既是系统的一部分,就不仅具有一个意义,而且特别是具有一个价值;这完全是另一回事。”[3]161就语言符号而言,价值表现之(1)实际上发生在符号内部,是能指和所指的交换关系,可是,光凭这一点还不能决定语言的价值:而(2)则是发生在语言系统的不同的符号之间,是符号外部关系之间,这才是更为重要的。在索绪尔看来,“价值”是建立在语言系统、关系之上的,他说:“语言既是一个系统,它的各项要素都有连带关系,而且其中每项要素的价值都只是因为有其他各项要素同时存在的结果。”“任何要素的价值都是由围绕着它的要素决定的。”[3]161-162也就是说:就单个的语言要素来说,其价值不仅跟符号内部相对待的声音或概念有关,更是由语言系统、由外部的关系决定的,没有系统,没有要素之间的关系,也谈不上语言要素价值的问题。索绪尔是从符号的概念、物质(声音)以及符号整体三方面来论述“价值”的,他认为前两者“消极”地表现为“差别”,后者“积极”地表现为“对立”。“价值”学说是索绪尔语言学理论核心观点之一,正如冯志伟所讲的:“价值的概念是索绪尔语言学说的基本概念,它是‘系统’的概念所派生出来的概念之一。”[7]26索振羽[8]、徐思益[9]370-390等较为详细地讨论过索绪尔的价值学说,可以参考。索绪尔也指出,在语言系统中,价值不仅应用于像“词”这样的符号,而且“也可以应用于语言的任何要素”[3]162。句法结构也要考虑它的价值。句法结构既然是形式和意义的统一体,要确定某个句法结构的价值,光看到其形式和意义之间的交换关系是不够的,还得在分析这个句法结构跟其他的结构的相互关系才能确定其价值。
变换分析的基础是句法结构的联想关系,是基于语法意义的相似将不同的语法形式联想在一起来进行变换,这里所谓的“语法意义的相似”是说相关句式表达了相同的命题意义或逻辑语义。如果只看到句法形式和这种命题意义或逻辑语义的交换关系(像上面所说的索绪尔论述“价值”之(1))是不够的,还要将语言系统中的这些相关句式加以比较(像上面所说的索绪尔论述“价值”之(2)),才能得出结构的价值。变换的相关形式之所以能在语言系统中并存,不仅在于它们表达了命题意义或逻辑语义,更重要的是它们表达了各自的价值。逻辑与语言有密切关联,但逻辑毕竟不等于语言,逻辑意义也不等于语言意义。比如一个词,仅仅说它的内容是“概念”,这是逻辑上的,而不是语言上的,仅说句法形式的内容是命题意义或逻辑语义,这也是逻辑上的,不是语言上的。如果说能相互变换的不同句式是“同义句式”,这是就逻辑上说的,而没能真正触及语言的“意义”。如何认识句法形式的“意义”呢,这就跟索绪尔所谈的价值有密切关系。
变换分析前后的句法结构形式是有差别的,这一点非常明白,但变换前后的语法意义有什么差别,这里需要着力说明。只要论述了变换前后语法形式的意义差别,才能确定各个语法形式在语法系统中的价值。上文提到,“意义”在语言学里是一个复杂的问题,对于“语法意义”也是如此。徐思益认为:“语法意义存在于语素、词、短语、句子等语言层级单位的关系之中,是从语言层级单位中抽象出来的关系意义、结构意义和类意义,而不是指单位本身的具体的实质意义。”[10]189这种对“语法意义”的界定——“关系意义”——无疑是科学的。但是,句法结构表达的“关系意义”可能是多方面的,而不是仅限于某一方面,比如逻辑意义。句法结构体现的逻辑语义关系当然是“关系意义”,属于“语法意义”的范围,但并不是意义唯一的构成要素,若看成是唯一的,那就跟逻辑没什么区别。
我们以为,所谓的语法意义是指一种语言语法系统中不同语法形式所表达的有差别的关系意义。只要是表达了不同的语法形式之间有差别的关系意义内容,都应进入我们考察语法意义的范围。这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一个句法结构的意义受制于它的组成成分的价值。不同语法形式的差别成分表达着不同的语法意义,从而使句法结构的语法意义也有了差别。比如,[A]→[C]的“门口站着人→人站在门口”,前者的动词“站”用了表示汉语时体范畴的后缀“着”字,后者没用“着”字,这说明“门口站着人”,“人站在门口”的价值并不完全相同,意义上有差别。其二,句法形式表达的语法意义,即关系意义涉及的内容是综合的、多层面的,比如句法、逻辑语义、语用等等,为了得出不同句法形式所表达的意义差别,就得着眼于这些多层面的意义,通过比较找出其间的差别,进而得出各个句式的价值。我国学者胡裕树、范晓自从提出语法分析的句法、语义、语用“三个平面”的语法观以来[11],这种新型语法得到了汉语语法研究者的重视,也引起了学者们的热烈讨论。其中讨论的重要问题就是语法研究应不应该考虑语用问题,应多大程度上考虑语用问题、应考虑什么样的语用成分等等。我们以为,只要表达了一种语法形式的内容,无论其涉及什么样的层面(包括语用的),这些表达内容的差别只要用不同句法形式差别反映的,就是重要的。如果把“意义”限制在逻辑语义范围,那变换句式只能认为是“同义”的,若能打破人为设定的障碍,将句法形式表达的多层面意义等都看作是句法形式表达的内容,通过比较才能确定它们的价值,并得出这些形式表达的意义。这一点上,语音学上的经验值得语法学借鉴。语音学上为了得出一种语言语音系统的不同音的特征,从发音部位、发音方法等多方面综合考察,来确定每个音在系统中的区别特征。句法结构跟语音一样,它们都是多面体,仅仅着眼于一个层面,那就容易得出其同,但难发现其异。比如,“我没见过这个人”变换成“这个人我没见过”,变换前后的语法形式(语序)不同,其组成成分完全一致,逻辑语义关系也一致,它们的意义差别就在语用意义上。我们说,前者的话题是“我”,后者的话题是“这个人”,二者的话题不同。如果我们不考虑语用意义,笼统地认为它们是“同义”的,那就看不出变换前后句式的价值,也得不出相关句式表达的“意义”。可以说,语法意义到底包括了哪些,这不是语法学者先验地预设好的,而是从语法形式的对立关系中去发现,只要能体现一种语言语法系统中不同语法形式的意义内容差别的,包括语用意义在内都应考虑。
四、结语
绝大部分汉语学者将语法学上的变换分析叫作“变换分析法”,而将之与层析分析法、语义特征分析法、配价分析法等并列。我们之所以分析变换分析是方法还是理论原则,是因为它关系到这种分析是不是语法研究中必须考虑的重要问题。比如层次分析,过去一般的学者都叫“法”,即所谓的“层次分析法”,而朱德熙认为层次分析不是“法”的问题,他认为层次性是语言的本质属性之一,进行语法分析离不开层次分析,不是一种可以采用也可以不采用的方法。[12]我们同意朱先生的看法。理论原则与方法不同,它并不是可用可不用的问题,而是由对对象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决定的,并由对象的本质属性找到它的依据。笔者以为,语言研究中的变换分析不适合叫“法”,而应把它看作语法分析的理论原则,这种理论原则是基于对语言的本质属性的认识做出的。根据索绪尔的语言学理论,认为语言的本质是关系,变换分析主要是基于有意义相似的不同语法形式的联想关系,它是由语言的本质属性——关系性决定的,而不是一个可用可不用的方法问题。另外,变换不仅使我们看清了句法形式之同,也看到其异,变换前后的不同语法形式不能简单地视作是“同义”,而只能看作意义相似,这些不同形式在一种语言的语法系统中有各自的价值。
[1] 朱德熙.《汉语语法丛书》序[M]//吕叔湘.中国文法要略.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2] 胡明扬.基本句式和变式[J].汉语学习,2000,(1):1-5.
[3] [瑞士]费尔迪南·德·索绪尔.普通语言学教程 [M].高名凯,译.岑麒祥,叶蜚声,校注.北京:商务印书馆,1980.
[4] 陈望道.文法简论[M].上海:上海教育出版社,1997.
[5] [英]克里斯特尔.现代语言学词典[K].北京:商务印书馆,2000.
[6] 陆俭明.现代汉语语法研究教程[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
[7] 冯志伟.现代语言学流派[M].西安:陕西人民出版社,1999.
[8] 索振羽. 德·索绪尔的语言价值理论[J].新疆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3,(2):123-129.
[9] 徐思益.论语言价值系统[M]//语言研究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0] 徐思益.再谈意义和形式相结合的语法研究原则[M]//语言研究探索.北京:商务印书馆,2009.
[11] 胡裕树,范晓.试论语法研究的三个平面[J].新疆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85,(2):7-15.
[12] 朱德熙.语法分析和语法体系[J].中国语文,1982,(1).
【责任编辑 朱正平】
Transformation and Chinese Syntactic Value
WANG Hong-sheng1, 2
(1. College of Chinese Literature and Language, Nankai University, Tianjin 300071, China;2. School of Literature and Media Communication, Baoji University of Arts and Sciences, Baoji 721013, China)
Linguistic essence is relation.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is not a problem of the method, but an analysis principle that is based on linguistic associative relation. The principle makes different grammatical forms which express a similar grammatical meaning associated to discuss the relation of different syntactic structures. The different grammatical forms that can be transformed are not regarded as synonymous structures, but only the similar meaning. These different grammatical forms transformed each other of similar meaning are contrastive and each owns itself value.
transformation analysis; associative relation; value; theory principle
H043
A
1009-5128(2015)17-0050-07
2015-06-17
王红生(1979—),男,陕西大荔人,南开大学文学院博士研究生,宝鸡文理学院文学与新闻传播学院讲师,主要从事比较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