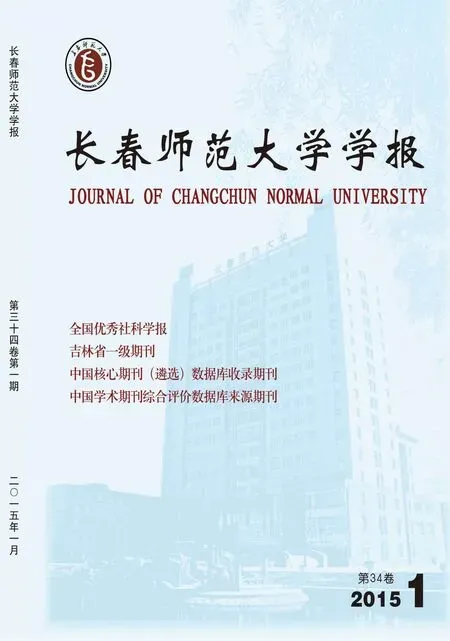论智利军人政权时期的技术专家
——“芝加哥弟子”与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2015-03-20吴恺夫
吴恺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论智利军人政权时期的技术专家
——“芝加哥弟子”与智利的新自由主义改革
吴恺夫
(中国社会科学院 拉丁美洲研究所,北京 100007)
在智利1973-1990年长达十七年的军人统治时期,存在着军人政府和以“芝加哥弟子”为代表的技术专家的联盟。“芝加哥弟子”在制定经济发展政策时扮演了关键的角色,在军政府的护持之下推进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成功地在智利建立起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为民主化转型后20余年经济改革的深化和稳定的增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
智利;军人政权;技术专家;芝加哥弟子
1973年,智利军队发动“911”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开始长达17年的政治高压统治。在经济领域,智利军人政权接受了以“芝加哥弟子”为代表的一批技术专家的观点,开始推行新自由主义的经济改革,成功地在智利建立起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制度。回顾和总结“芝加哥弟子”在军政府统治时期的行为与影响,对理解智利的现代化发展历程具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阿连德革命”的失败与军政府的战略选择
1970年,由智利六个左翼政党组成的“人民团结阵线”(Unidad Popular)在社会党人萨尔瓦多·阿连德(Salvador Allende)的领导下赢得大选。阿连德就任总统之后,迅速开展一系列改革措施,试图用经济国有化、土地改革、收入分配调整等手段实现向社会主义的过渡。但是,改革的措施触动了智利中、右翼集团的利益,也引起了美国的不满与干涉,加之阿连德政府的调整失误,到了1973年智利陷入了政治僵持、经济崩溃和社会动乱的局面。终于在1973年9月11日,智利军队在以奥古斯托·皮诺切特(Augusto Pinochet)将军为首的右翼军官团领导下发动政变,推翻了阿连德政府。
1973年上台的智力军人政权由三大军种和武装警察司令组成的军事执政团(Military Junta)控制。此时的军政府亟需为政变提供合法性与正当性的理由,但智利军人并没有系统性的意识形态,在军事执政团内部存在着意识形态的分歧和派系的竞争。在这种情况下,智利军队首先采用南椎体国家军队中流行的“国家安全学说”扮演官方意识形态的角色。“国家安全学说”的出现与冷战的国际环境特别是古巴革命有关。拉美军人认为自己是拉美社会最训练有素、最现代化的社会集团,是西方基督教价值观的捍卫者,因此有责任抵御国际共产主义的威胁,恢复政治秩序,为新的经济增长创造条件,必要时可以对社会和政府实行全面的控制[1]。在这一学说的支持下,智利军队公然抛弃宪政民主制度,解散国会、搁置宪法、禁止党派活动,对反对派和异议人士开展长期的制度化的镇压,“意图是消灭智利生活中的整个政治和社会运动。”[2]在这个过程中皮诺切特将军运用各种手段独揽权力:1974 年颁布第806号法令成为共和国总统;1978年1月通过精心策划的公民投票,获得75%的民众支持,继续担任总统职务;同年7月,逼迫军官团内的对手空军司令古斯塔沃·利将军(Gustavo Leigh) 辞职,从此确立起个人统治的绝对权威。
在“国家安全学说”之外,军政府受到以右翼法学家雷梅·古斯曼(Jaime Guzmán)为代表的“法团主义”思想的吸引。这种思想试图帮助军政府效仿西班牙佛朗哥政权,建立一种带有法西斯主义色彩的排斥民主政治的威权主义政体。在以古斯曼为代表的右翼势力的支持下,皮诺切特将军制定和颁布了1980年宪法,用以取代1925年宪法。这部被军政府称为“自由宪法”的宪法为了增强军政府的合法性,对智利未来政治经济的发展作出两个承诺:一是明确向民主过渡的期限,到1988 年将举行公民投票以决定是否继续由军方执政,如果获得通过,军队将再掌权8 年,如果未获通过,军队将在1990年还政于民;二是承诺保护私有产权,规定除因国家的普遍利益、国家安全、公用事业、公共安全以及环境保护等因素的影响,私有产权不得侵犯。
但是,无论是“国家安全学说”还是“法团主义”,都很难为智利的政治和经济改革提供明确的方向。首先,无论是好战的反共主义还是带有法西斯色彩的法团主义思想,都无法获得国内各个政治集团的全面拥护,也很难得到美国和国际金融资本的支持。其次,这些学说也可能被其他政治集团利用以削弱军人对权力的垄断。最重要的是,这些学说无法为亟需扭转严峻的经济形势的军政府提供新的经济发展模式。
军政府执政之初,军事执政团任命费尔南多·莱尼斯(Fernando Léniz)和劳尔·赛斯(Raúl Saez)执掌经济部,领导经济团队,推行稳定计划。莱尼斯等人采取了一系列措施,包括缩减公共开支、降低工资、控制货币发行、减少流动资金、取消价格控制、降低关税以及返还阿连德政府时期征收的私人企业等。但是,由于执行不力,加之受1973年第一次国际石油危机和国际市场铜价下跌等因素的影响,失业人口继续增加,经济困难无法得到缓解。在经济稳定计划受挫的同时,莱尼斯和赛斯对军政府的政治高压持有不同意见,认为军政府若能减弱对政治反对派的镇压、释放政治犯,会有利于寻求外部经济援助[3]。军事执政团无法容忍莱尼斯和赛斯的经济团队对其统治的异议,开始寻找其他经济稳定方案,这就为“芝加哥弟子”登上历史舞台创造了条件。
二、“芝加哥弟子”
“芝加哥弟子”起源于20世纪50至60年代深受凯恩斯主义影响的拉美结构主义经济思想和以现代货币主义为代表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思想对拉美经济发展中产生的问题的辩论。二战以后,以劳尔·普雷维什(Raúl Prebisch)为代表的拉美结构主义思想影响了拉美的许多国家的经济决策。拉美结构主义主张政府要通过积极干预经济完成进口替代工业化,这个政策伴随着贸易保护主义、操控汇率,并且要求采取土地革命、收入再分配等手段刺激消费需求、扩大国内市场。随着西方主要资本主义国家的经济相继出现“滞涨”的局面,主张实行自由市场经济、反对国家干预、强调市场机制作用的现代货币主义向占据统治地位的凯恩斯主义经济政策发起了挑战。在美国经济学家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的大力倡导下,现代货币主义以芝加哥大学为大本营,逐渐由理论进入实践阶段,开始影响与西方经济有着密切联系的拉美地区。
为了传播芝加哥学派的新自由主义理论,1955年芝加哥大学经济系主任西奥多·舒尔茨(Theodore Schultz)来到智利,与基督教大学签订了一个学术计划,选取一批学生到芝加哥大学经济系接受研究生教育[4]。这批学生得到了弗里德曼等人的直接指导,成为现代货币主义的信徒,确信引入完整自由市场竞争经济是解决智利发展问题的有效方式。完成学业后,大部分学生回到了智利,迅速在学界、经济界和政界产生影响。在他们周围,逐渐形成了一个拥有基本相同的经济学观点的技术专家群体,这就是“芝加哥弟子”的主要来源。
1968年,“芝加哥弟子”为准备参加竞选的右翼政治家豪尔赫·亚历山德里((Jorge Alessandri)起草了一份经济计划,主张开放的自由市场经济、取消垄断、鼓励私有化、调整社会保障制度、减少政府对经济的干预。他们的主张遭到工商业阶层的反对,被亚历山德里搁置。阿连德政府上台后的经济混乱状态使“芝加哥弟子”看到了希望,于是从1972年起开始举行定期研讨会。智利全国制造业协会主席奥兰多·赛恩斯(Orlando Saenz)为他们提供了资金,并建议他们为未来可能的经济改革作理论准备。此时,“芝加哥弟子”起草的经济方案被称为“砖石计划”(The Brick),并且通过一份右翼报纸《水银》(El Mercurio)引起了长期以来关注经济事务的海军上层的注意,就此将“芝加哥弟子”引入政府的决策部门。
“芝加哥弟子”认为,智利以往所推行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战略实行高关税的贸易保护政策、过多的国家干预以及阿连德时期激进的国有化政策,使生产资源无法有效配置,压制了私营企业的积极性,造成工业发展规模狭小、效能低下、国内市场狭小。“芝加哥弟子”认为应该彻底否定阿连德政府的政策,实行彻底而激进的自由市场经济改革。“芝加哥弟子”为军政府提供的计划不仅着眼于经济,而是通过经济改革促进智利政治、社会、文化改革,进而产生有利于军政府的结构性变化:缩减国营经济和公共部门的规模将会削弱反对派的经济基础,将资源重新引向私人资本将会巩固军政府的政治基础,经济自由化改革会提供新的经济增长手段以减轻政府对非竞争部门的财政支持,允许市场力量来调节工资将削弱劳工运动在政治上讨价还价的能力,旧的政治效忠形式将被削弱, 而新的无阶级形式和民族形式将会发展。 “芝加哥弟子”相信,运用自由市场的力量可以调节国家和社会的运行,消除通货膨胀这个最大的经济不稳定因素。不过,施行这样的变革不可避免地会引发激烈的意识形态冲突和利益纷争,因而需要在严格的威权主义控制之下才能完成。
芝加哥弟子为军政府描绘的是一个理想的政治、经济和社会改革蓝图,满足了军政府解决经济困难、巩固长期统治的“合法性”需求。对于军人来说,“芝加哥弟子”作为训练有素的技术学家,能够保障政府决策取决于技术与科学原则而非意识形态与政治,与军人的价值观相契合;对于工商业阶层和中产阶级而言,“芝加哥弟子”提供经济平衡和社会秩序的许诺也是颇有吸引力的。更重要的是,“芝加哥弟子”改革方案来自美国学界,有助于得到美国政府的政治支持以及跨国公司和国际金融资本的经济支持和直接投资。
1974年1月,军政府解除了经济部长赛斯的职务,同年7月任命豪尔赫·考阿斯( Jorge Cauas)为经济部长。“芝加哥弟子”在政府和相关机构中逐渐获得越来越多的职位,并开始逐步掌握经济政策的制定与实施的权力。1975年3月,“芝加哥弟子”在智利基督教大学策划了一个经济研讨会,邀请了弗里德曼、阿诺德·哈柏格(Arnold Harberger)等一批芝加哥学派的经济学家。弗里德曼在会见皮诺切特将军时完全支持其弟子们的经济改革计划,这促使后者下定了决心。仅仅一个月后,“芝加哥弟子”中的领袖人物塞尔吉奥·德·卡斯特罗(Sergio de Castro)取代莱尼斯,成为财政部长,开始全面推行“经济复兴计划”,这成为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开始的标志。
三、智利新自由主义改革的主要措施和成效
从1975年起,以“芝加哥弟子”为核心的经济团队从现代货币主义的理论出发,在智利进行了具有浓厚新自由主义色彩的经济改革。这场变革不仅表现在经济层面,而且涉及政治、社会和国家的作用等各个方面,为智利经济的持续增长奠定了基础。其改革的内容和成效如下。
(一)价格自由化
为建立市场调控机制,使经济摆脱国家的直接干预,经济改革首先采取价格自由化政策,即放松对价格的控制、减少政府定价的范围、对价格补贴的幅度进行调整。然后在政府监督的情况下对私人部门生产的商品价格实行自由化,使资源在市场机制引导下进行合理配置,以提高企业的生产效率;同时开放国内市场,实行贸易自由化,以平抑国内物价。从1973年到1978 年,受国家控制价格的商品从原来的2万余种减少到8种,商品流通领域基本实现自由化[5]。
(二)金融自由化
智利在金融领域中的改革主要以市场的作用取代政府的干预,建立一个不受国家干预的自由化金融市场,使金融工具能够在经济改革中发挥积极作用。为此推行的改革措施主要包括:放松利率管制、归还过去政府接管的私人银行并将国有银行私有化、放宽信贷控制、取消外汇管制。
智利的金融自由化改革经历了一个曲折的过程。资本大量流入和固定汇率政策使智利比索汇率被高估,加上1979年第二次石油危机和墨西哥债务危机的影响,使智利难逃债务危机的厄运,酿成1982-1983年经济危机,也导致了财政部长卡斯特罗被解职。经过几年的整顿和调整,“芝加哥弟子”的第二位领袖埃尔南·布奇( Hernán Büchi)在1985年2月被任命为财政部长,开始扭转在危机时期的资本管制和保护主义取向,健全金融体系,加强金融监管,使开放资本市场的措施与其他各项宏观经济政策和改革措施紧密配合,取得了较好的效果。
(三)贸易自由化
智利的贸易自由化主要是改变内向型的进口替代工业化发展模式,大幅削减关税、降低或撤消非关税壁垒,以提高生产率和资源配置效率,推动宏观经济政策的调整。1973年智利的平均关税为94%,至1979年6月实现10%的统一关税。债务危机期间关税有所上调,但自1985年起关税又逐步下调。在调整关税的同时,智利基本取消了非关税壁垒,促进了贸易自由化的发展,同时运用财政刺激手段扩大出口。
(四)经济私有化
进口替代工业化模式使国家充当了发展经济的主角,但大多数国有工业企业在政府补贴和贸易保护下效率低下、亏损严重,难以起到推动经济增长的带头作用。“芝加哥弟子”推动的私有化改革,其目的是转变国家职能,将经济领域中的国有企业向私营经济转移,实现所有权的广泛分配,充分发挥私营经济的积极性,建立更有效的发展模式。智利私有化进程主要分为两个阶段:
第一阶段为1974至1980年。在把阿连德政府时期征收的企业和土地无偿退还原主之后,军政府采取了激进的私有化改革,导致生产资本和金融资本很快集中到几家大财团手中。债务危机爆发后,私人企业由于资金短缺而大量倒闭,对经济造成极大冲击。政府不得不再次干预,将私有化的银行和企业又收归国有。
第二阶段为1985至1989年。军政府在总结前一时期私有化经验的基础上,采取程序化、规范化的手段重启私有化进程,对企业股权的转让采取了灵活多样的形式,并允许外国资本参与。这次私有化进程进行得较为顺利,取得了明显成效,极大地减轻了政府的财政负担,降低了国家对经济的干预和参与,企业管理水平和经济效益得到普遍提高,一个以活跃的私营经济为主导的比较稳固的经济体制得以建立。
经过以上的改革措施,智利在1984-1989年期间出现了经济持续稳定发展的局面。1984-1989年国内生产总值平均增长5.5%,其中1988年增长率为7.4%,1989年高达9%。鉴于二十世纪八十年代拉美各国经济普遍不景气、经济增长率平均仅为1%,可以说由“芝加哥弟子”领导的经济改革总体上是成功的[6]。但在其实践过程中也暴露出局限性以及负面影响,广大中下阶层人民为经济的恢复和发展付出了巨大代价。
四、结语
由“芝加哥弟子”领导的新自由主义经济改革,为智利经济的稳定和发展奠定了良好基础,而皮诺切特军政府也凭着在经济方面的良好表现得以用和平的方式完成了民主化的政权转移过程。虽然“芝加哥弟子”的领袖布奇作为右翼政治集团的代表在1989年的大选中未能赢得选举,但是1990年智利恢复文人制度以后的历届政府并没有改变“芝加哥弟子”奠定的自由市场经济路线。这不但保障了智利经济发展的成果,也为民主化转型后20余年经济改革深化和稳定成长创造了有利的条件。智利成功走出“中等收入陷阱”,成为本地区率先迈入高收入国家行列的经济体之一[7]。
智利改革成功的关键在于军人政权和文人技术官僚实现了有效的协调与合作。一方面,军政府特别是皮诺切特将军本人极力保护“芝加哥弟子”不受工商业资本家、地主阶级、军队内部的反对力量以及其它利益集团的干扰,放手让“芝加哥弟子”去改革,并以强力的方式将决策者的意志和计划渗透到全国。在1982-1983年债务危机爆发之后,一旦经济情况有所好转,皮诺切特将军又重新让智利向新自由主义改革轨道回归。 另一方面,由卡斯特罗、布奇率领的“芝加哥弟子”充分发挥专业素养,全心全意地推进新自由主义改革,在债务危机爆发之后及时吸取教训,调整激进政策,推进审慎的改革。
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往往是一个被“压缩”的过程,意味着在同一历史时空下,不仅要完成早期现代化国家经历几百年才得以完成的民族建设、国家建设、经济建设和社会建设等各项任务,而且还要满足社会各个阶级、阶层和集团因受到先进国家示范效应的影响而成倍增加的对参与政治、分享资源和提升福利的要求。因此,一些发展中国家改革的失败很大程度上在于其无法调和其内部始终存在的巨大的压力和矛盾。发展中国家在从传统社会向现代社会过渡或转型的过程中,其发展战略的选择具有特殊的重要性。智利军政府统治时期军人与技术专家共同推进的新自由主义改革的经验表明:在发展中国家的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有权威的能够对社会发展进程实施有力领导的中央政府,是社会变革时期能够以较低成本获取快速平稳发展的根本保证;改革的冲突在所难免,其成败往往取决于政府的发展能在多大程度上吸收、消化改革的正、负面作用。
[1]Alfred Stepan.Rethinking Military Politics: Brazil and the Southern Cone[M].Princeton: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 1988:14.
[2]莱斯利.贝瑟尔.剑桥拉丁美洲史:第八卷[M].北京:当代世界出版社,1998:364.
[3]Carlos Huneeus. The Pinochet Regime[M].Boulder: Lynne Rienner Publishers,2007:279.
[4]Patricio Silva. Technocrats and Politics in Chile: From the Chicago Boys to the CIEPLAN Monks[J].Journal of Latin American Studies, 1991,23(2):385-410.
[5]王晓燕.智利—拉美新自由主义改革的先锋[J].拉丁美洲研究,2004(1):30.
[6]Kees Koonings and Dirk Kruijt, Societies of Fear: the Legacy of Civil War, Violence and Terror in Latin America[M].New York: St Martin’s Press:171.
[7]郑秉文,齐传钧.智利:即将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首个南美国家—还政于民20 年及其启示[M]∥拉丁美洲和加勒比发展报告(2010-2011),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1-41.
2014-08-07
吴恺夫(1983- ),男,吉林长春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拉丁美洲研究所博士研究生,从事国际政治研究。
K153
A
2095-7602(2015)01-0069-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