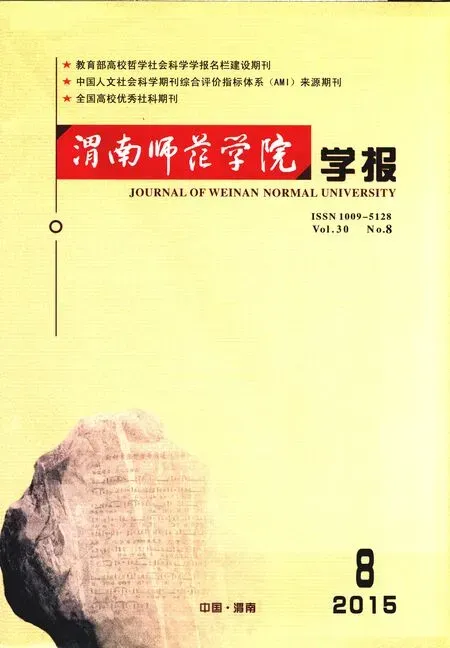庞德汉诗英译的审美观照
2015-03-20陈雪雪
陈雪雪,李 艳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70)
【外国语言文化研究】
庞德汉诗英译的审美观照
陈雪雪,李 艳
(兰州城市学院 外国语学院,兰州730070)
宗炳在《山水画序》中提出的“澄怀味象”对审美主体所作的要求,为译者在诗歌翻译中保持“不即不离”的审美观照心理距离提供了参考。从客观和主观两个角度探析庞德翻译审美心理距离的保持,并通过分析庞德的《华夏集》译文,阐释译者在审美观照过程中保持适当审美心理距离的必要性。
澄怀;味象;审美心理距离
汉学家埃兹拉·庞德的成就之一在于将中国的古典诗歌和儒家经典翻译成英语。《华夏集》的翻译更使他蜚声海内外。我们知道,庞德从1931年开始着手翻译中国古诗到1954年《论语》英译本出版,他都不曾真正地学习过汉语。他不通中文。这就使得国内外学者对其译文的不精确之处大加批评。然而,与此同时庞德所译的汉诗又因其含蓄凝缩、文字洗练、意象鲜明、诗情藏且不露而大受欢迎,其中不乏经典。这说明庞德在翻译过程中能够充分地发挥审美主体性去领会原诗的诗意、诗情,从而在译文中最大限度地再现原诗的艺术精神。本文将从翻译过程中译者的审美观照角度来探讨庞德是如何在译文中既保留了诗人的艺术审美特质,又能够让读者对异质文化审美经验欣然接受。
一、 诗歌翻译中的审美观照心理距离
诗歌作者的创作是对于物象进行审美感知并再造、外化审美感知的过程。在创作时作者对物象直接发生了审美心理活动,因此这里的审美感知可以被称为一度感物。诗歌读者审美感知的对象是诗歌作者再造的审美感知即审美意象,是间接感物。所以这种感应是一种二度体验,我们可以称之为“二度感物”[1]。我们要注意的是不光创作过程中作者的情感会不可避免地介入到审美意象中去,读者在欣赏诗歌时也势必会将自有的审美经验投射其中,其审美感受的结果可能与原诗作者的期待不同,甚至相差很远。作为一般读者,即便是和原诗作者的审美体验有天壤之别倒也无妨。而译者作为特殊的读者:既是诗歌审美主体,又充当着沟通原诗作者与译文读者的桥梁,这就要在自身的审美主体性与原文作者的审美主体性之间保持平衡。译者只有保持审美主体间的平衡,才能保证展现在目的语读者面前的译文最大限度地达到与原文近似甚至相同的审美感受。也就是说,译者要恰到好处地运用已有的审美经验来感知、体悟、理解诗歌,而如何“恰到好处”就取决于译者在审美观照过程中所保持的心理距离了。
在分析美感经验的心理距离时,朱光潜先生就指出:“创造和欣赏的成功与否,就看能否把距离的矛盾安排妥当,距离太远了,结果是不可了解;距离太近了,结果又不免让实用的动机压倒美感,不即不离是艺术的一个最好的理想。”[2]17在诗歌翻译过程中,译者作为审美主体,势必要调动其审美主体性进行审美观照。我们发现,译者在审美观照过程中对于原诗的审美经验介入也可能会出现这两个极端:要么过分调动译入语文化范畴内的审美经验介入,这样会“距离太近”;要么过分调动译出语文化范畴内的审美经验介入,这样又会“距离太远”。刘华文也在《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一书中谈到:
就汉诗英译来讲,翻译主体要么以译入语文化为重心的“我者”身份出现,采取“我本感应”的翻译倾向,要么以译出语文化为重心的“他者”文化身份出现,采取“他本感应”的翻译倾向。前者很容易把原诗同化为译入语文化的一部分,让原诗失去自己的文化个性和独特性,而后者则有可能让译入语文化产生排异性,使他我相互排斥和对立的关系彰显在译诗中。[3]184
试想,如果译文与译入语文化审美距离太远,即刘华文所谓采取“他本感应”的翻译倾向,那么译文读者很可能无法用已有的审美范式进行审美感应,从而无法达到审美共情,造成对译文的审美“排异”,使译文不能达到原有的审美期待。然而如果译文与译入语文化审美距离太近,即刘华文所谓采取“我本感应”的翻译倾向,译者常会因此强调传达原诗语言层面的信息而过分同化了原诗的异质审美因素从而忽略了对原文审美风貌的再造,结果是译文读者虽然毫不费力地理解了原诗所传达的文字信息,却无从感受原诗中异质审美因素带来的“原汁原味”的审美感知,或者因为过分地达意而使诗歌的美感意境无从表达。因此译者一方面要避免因为过分保留原文审美异质因素而忽略了译文的“达意”,阻碍了译文读者获取审美经验;另一方面要警惕因为过分追求“达意”的实用目的而忽略了译文的“达美”,消解了原文的审美诉求。因此,为了避免诗歌翻译中偏取一种的审美感应模式,并在译文中最大化地保持原文的审美效应,译者的审美经验介入只有保持“不即不离”的审美距离,才能为两种文化、审美主体之间的相异与相同找到最佳契合点,产生共鸣,进而使译文读者得以充分而有效地感知原诗的艺术精神和魅力。然而译者又该如何保持这种“若即若离”的审美心理距离呢?
二、“澄怀味象”与庞德的翻译审美观照
晋代的著名画家宗炳(375—443)在《画山水序》中提出“澄怀味象”这一美学命题就为我们解决这个矛盾提供了很好的参考。他说:“圣人含道映物,贤者澄怀味象,至于山水,质有而趣灵。”宗炳提出的“含道映物”和“澄怀味象”都是体验山水之美所必须的审美态度。这里的“澄怀”是对审美主体的要求,主体在审美感知过程中要做到澄净心怀,排除外界功利关系的纷扰,做到以虚静澄明的心态去审美观照,去实现“味象”。“味”是品味,体验即审美观照;“象”则指审美对象。所以“澄怀味象”这一审美命题要求审美主体在审美观照时要摆脱已有世俗社会的制度、规范和名缰利锁,做到心体自由,能够“超然物表”地反映审美对象。但是这里的“澄怀”并非指一味脱尽实际生活,也不是完全忘我,而是一种坚持审美无利害的审美观照,即主体对审美对象排除欲念、远离利害关系。[4]
庞德认为单纯的字面翻译无法再现原诗的审美经验,诗歌翻译“不仅要求是词和精神的翻译,而且还要有‘认同感’,那就是说,现代读者在某种意义上必须认同和意识到古人的精神内容,并从他们的思想与语言中吸取某些时髦的东西。”[5]17庞德的翻译思想与中国古典诗人所强调的“不着一字,尽得风流”“言有尽而意无穷”的审美诉求在根本上是不谋而合的。所以庞德《华夏集》的翻译并不强调对原诗词义的忠实、对等。他重视译诗的意象、氛围、节奏与原诗的贴合。庞德在翻译《华夏集》时不通汉语,对中国古诗韵律就更是知之甚少,他依靠美国东方研究专家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粗糙的笔记来翻译。然而厄内斯特·费诺罗萨的笔记只有每首诗的原文、日文读音,单个字的释义与解释,且多出自日文翻译。这样看来字词层面的准确翻译是不可能实现的,然而从另一方面,却“给他探索自由诗结构以最大的自由。结果《华夏集》的语言在他所有译文中最简朴、最不受古语影响。换言之,大大出乎意料的是,它的语言最当代化,尽管在时间和文化上存在极大差别。庞德的译文保留了古风和异国情调,主要是通过诗歌中实质性的内容获得的。或者说通过诗歌中狭窄的意象成分以及保留中国地名(虽然通过日语转译)获得的”[6]。
需要承认,不通中文会给庞德的翻译工作带来很大的困难。而这种语言上的不通却让庞德在审美观照中作为审美主体做到了“澄怀”,使他能够自然地“涤除”审美过程中来自语言层面的规范与限制。我们知道诗歌作为一种以语言为媒介的审美客体,欣赏者往往容易用已熟练掌握的关于语言的理性的、语法的、逻辑的知识分析并解读它。这样一来,诗歌的翻译者就容易陷入语言分析的表层认知而无法自拔。这种对作品看似明晰、确定的指认,却极大地破坏了对作品内涵的无限阐释,漠视了外延模糊的作品的艺术精神,而无限阐释的可能性正是文学作品的魅力所在。另一方面,在译者陷入文字分析泥潭的同时,译者的想象力、理解力受到了限制,不能够“透明”地体味、感应原文所呈现的审美体验。这样的译文只能是僵硬、呆板,没有生命力的附属于原文的鬼魂。因此我们说庞德的不通中文从客观上使得他能够摆脱语言层面的现实意义的困扰与羁绊,从而做到无利害地对原诗进行审美观照。我们不妨举例说明。如李白的《长干行》,诗中第一句:“妾发初覆额”中提到的发型表明了主人公“两小”的年龄特征,并借此回忆了童年的天真烂漫。这让缺乏中国传统文化知识的庞德费了一番周折。他先将“覆额”翻译成“bangs”,但最后将其译为:“While my hair was still cut straight across my forehead”。庞德在翻译时直接将词典中对 “bangs” 的释义“hair cut straight across forehead”作为译文。然而这种语言上的直白却恰好转达了原诗的状态与意境,通过这种动态简朴的语言让读者仿佛看到了当时场景。再如李白诗中写到“十五始展眉,愿同尘与灰。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庞德译为“At fifteen I stopped scowling/I desired my dust to be mingled with yours/ For ever and for ever and for ever/ Why should I climb the look out?”译文显然删除了“常存抱柱信,岂上望夫台”这两个典故。但译文用了三个“ever”表达了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信念,激活了原诗的灵魂,要比某些非常忠实的译文更加优美动人。这几行诗译笔流畅,真正得原作之神韵,将妻子对丈夫的一往情深表达得让人回味无穷。
如果说不通中文客观地使庞德能够“虚怀以待”,主观上庞德也拥有一个“以玄对山水”的审美心胸。20世纪的西方社会,由于工业的迅速发展和进化论的出现,原有的价值体系受到了挑战,旧的道德标准和行为规范正在崩塌。人与社会、人与自然、人与人、人与自我的关系等各种现代资本主义工业社会的矛盾日益尖锐。而包括第一次世界大战、经济危机、苏联十月社会主义革命、第二次世界大战等在内的这些20世纪重大的历史事件则对上述矛盾的激化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人们对于资本主义社会报有的热情和理想被失望、消沉和不满所取代。大多数人的梦想在破灭,世界似乎被周期性的金融危机带向更大的灾难。这都使得西方知识分子开始重新审视资本主义的价值体系。庞德也是怀疑者之一。他说:“西方人事实上已经最大程度上摧毁了西方最好的思想。官方的基督教是污水沟,天主教走向了虚无……整个西方理想主义是一片丛林,基督教神学一片丛林。要想把这片乱七八糟的丛林削成一点秩序来,没有比《大学》这把斧子更好了。”[7]89可以看出,庞德把复兴欧洲文明的希望寄托在了中国传统文化身上。对中国文化的浅显认知和向往,对西方文明的怀疑与批评,使他能够有意识地摒除已有的西方文明的审美价值观和审美经验。庞德的这种有意识地避免西方审美经验的介入和对东方审美异质因素的知之甚少,从主观上实现了心体自由,超越了来自西方社会和东方社会的世俗约束,保持了“心体清纯”,使译文最大地“忠实于原文的‘意义’与‘气氛’”[8]。
当庞德从客观和主观两个方面做到心体自由,排除干扰,就能以虚静的心胸关照汉诗的本真审美意象,从而实现“味象”。“味”除了品味,玩味之意外,还有想象、回味之意。
汉诗往往给人留以想象空间,令人回味无穷,这要归功于中国古诗特有的意象组合方式。中国古典诗歌在意象呈现上使用了和中国画一样的散点透视。中国画画家可以将万里河山同时呈现在一幅画卷之中,诗人也可以摆脱时空的限制将各种景象的意象并置于寥寥数语之间。而这种意象上的统一安排常使诗歌给人以强大的气势,从而能够烘托出一种情感和客体事物交相呼应的统一的艺术境界和审美体验,引起读者的无限联想和遐思。中国诗人杜甫有两句诗就表现了这种一目千里,把握全境的空间意识:“乾坤万里远,时序百年心”。这样一来,中国古典诗歌的翻译更是要求译者充分发挥其审美想象、审美联想、审美整合等一系列心理能动去体验原诗所表现的审美境界。试想,如果在审美过程中沿用西方的一点透视去理解王维的辋川诗绝句“北坨湖水北,杂树映朱栏,逶迤南川水,明灭青林端”,将会造成怎样的空间混乱。而庞德正是在“澄怀”的审美心胸基础之上,自由充分地发挥审美想象,准确体味到了汉诗的艺术风味。我们试举例说明:
送友人
李白
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
此地一为别,孤蓬万里征。
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
挥手自兹去,萧萧班马鸣。
Taking Leave of a Friend
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
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
Here we must take separation
And go out through a thousand miles of dead grass.
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
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
Who bow over their clasped hands at a distance,
Our horses neigh to each other
As we are departing.
Rihaku
这首诗描绘了诗人与友人依依惜别的情景。我们看到,庞德的译文中个别词句翻译得并不准确,如“孤蓬”“挥手自兹去”等,然而从译文中我们可以看到译者凭借其想象力将原本看似并置的意象进行整合,并再造成有机的整体。原诗第一句“青山横北郭,白水绕东城”被译为“Blue mountains to the north of the walls,white river winding about them.”译文中庞德成功地将“青山”“北郭”“白水”“东城”等意象整合在一起,不仅再现了原诗的审美意象,也为译文读者勾勒出了生动的场景。再如“浮云游子意,落日故人情”的翻译:“Mind like a floating wide cloud,sunset like the parting of old acquaintances.”虽然细推敲起来译文的翻译与原文意义稍有出入,但是庞德在译文中成功地发挥其审美想象,将“浮云”“游子”“落日”“故人”之间的联系建立起来,还原了原诗情与景相互交融的艺术意境,使译文读者能够体会汉诗以景状情,以情写景的审美追求。
三、结语
“澄怀味象”这一中国古代绘画命题为当代译者如何恰当地发挥审美主体性提供了美学参照。通过对其翻译行为的分析,我们看到庞德翻译中国古典诗歌时,西方的价值观、审美经验并没有过多地干扰到他对中国诗歌的审美体验。庞德从客观和主观两个层面在翻译审美过程中保持了“澄怀”,保持了译者审美主体性和原诗作者审美主体性之间的平衡,从而为我们进一步探索译者的审美心理距离提供了例证。
[1] 李健.“应会感神”:宗炳的感物美学[J].深圳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8,(1):120-126.
[2] 朱光潜.文艺心理学[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5.
[3] 刘华文.汉诗英译的主体审美论[M].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05.
[4] 张晶.审美静观论[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3,(2):113-120.
[5] Hugh Kenner.The Pound Ezra[M].Berkeley:University of California Press,1971.
[6] [美]杰夫.特威切尔.庞德的《华夏集》和意象派[J].张子清,译.外国文学评论,1992,(1),86-90.
[7] Cookson Willia.Ezra Pound,Selected Prose,1909—1965[M].London:Faber and Faber Limited,1973.
[8] 蒋洪新.庞德的《华夏集》探源[J].中国翻译,2001,(1):56-58.
【责任编辑 贺 晴】
th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Pound’s Translation of Chinese Poem
CHEN Xue-xue, LI Yan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Lanzhou City College, Lanzhou 730070, China)
Zongbing assumed that aesthetic subject should “purifying the mind and appreciating the world” in Preface of Painting Landscape, from which a poem translator could draw inspiration to keep an appropriat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n this paper, the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kept by Pound in poem translation is analyzed from both subjective and objective perspectives, and the necessity of maintaining a proper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is proved through an examination of the English translation in Cathay by Pound.
purify the mind; appreciate the world; aesthetic psychological distance
H059
A
1009-5128(2015)08-0053-04
2014-09-22
陈雪雪(1981—),女,甘肃兰州人,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翻译硕士,主要从事翻译理论与实践研究;李艳(1978—),女,甘肃天水人,兰州城市学院外国语学院讲师,文学硕士,主要从事外国语言学及应用语言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