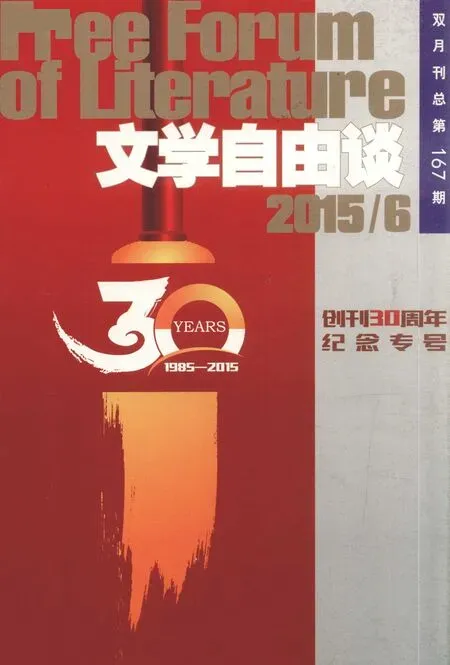我与刊物共成长
2015-03-20唐小林
唐小林
我与刊物共成长
唐小林
自1997年从遥远的四川来到深圳打工之后,我工作之余最大的爱好就是读书。早在打工之前,我就知道《文学自由谈》是一本文学评论杂志,但对于这样一本名刊,我却从未读过。偶然有一天,我在深圳宝安区图书馆里看到这本杂志时,却仿佛有一种他乡遇故知的感觉。于是,我立即从书架上取下来,随意地翻看到了扉页上的这样一段文字:“诚如本刊之刊名,《文学自由谈》竭力于表达文坛民意,试图告诉您一个相对真实的文坛。一切作家、作品,一切文学事件、文学现象,都可以一视同仁地成为本刊质疑、评点的对象……”
在当今众多的报刊都在忙着和名人攀亲的时候,《文学自由谈》却公然宣称:“不论您是名人,还是非名人,只要您在文学的范畴之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自圆其说,本刊都对您提供说三道四,显才露智的版面。”如此不合时宜的宣言,却令我满腹狐疑:这究竟是不是一种出于自我宣传,吸引眼球的广告策略?但当我从《文学自由谈》上读到那些无名作者,如阎德喜的《对第四期〈文学自由谈〉的随想》(2009年第5期)这样的文章时,我固有的想象完全被颠覆了。我自认为是读过一点书的人,但在几十年的阅读生涯中,还从来没有看见过有哪一家报刊能够有如此的勇气和胸襟,让一个无名的读者来对自己的杂志说三道四。不仅如此,《文学自由谈》还出人意料地对敢于挑刺的阎德喜表示热烈欢迎和由衷敬意。同时我还看到,《文学自由谈》在当今的文学期刊中,有一种鲜有的争鸣气息。这集中体现在它的品牌栏目“反弹”中。有时我甚至觉得《文学自由谈》的编辑们常常是在“犯傻”,别的刊物一旦受到学界和读者批评,常常都会讳疾忌医,不是遮着就是掖着,而他们却居然把读者批评自己刊物的文章也照样刊登出来。这种学术自由,兼容并包的胸襟,成就了《文学自由谈》海纳百川、有容乃大的高贵品质。
2006年2月,我先后在书店里买到了韩石山先生的《谁红跟谁急》和李建军先生的《时代及其文学的敌人》两本书。这是开启我的文学批评写作之路,让我爱不释手,反复阅读,不断获益的两本书。之后,我惊喜地发现,韩石山和李建军原来都是《文学自由谈》的主要作者。一本刊物的品位和高度,完全要看它拥有什么样的作者阵容。正是因为有了像他们这样一些从不与世俯仰、随波逐流,具有独立之精神、自由之思想的真正的知识分子风格独异的文章,才使《文学自由谈》在学界和广大读者中赢得了口碑。作为一个酷爱文学,但仅仅读过高中的人,我从未想到过要写文学评论,但阅读《文学自由谈》越多,我学到的东西和获得的阅读享受就越多。《文学自由谈》的许多作者,都是我在写作上心仪的老师,如李国文、陈冲、陈歆耕、李美皆等,而当我得知李美皆正是从《文学自由谈》脱颖而出,继而成为一名著名的文学评论家时,我的心中暗暗有了一种想法:如果我也能写出像李美皆那样的精妙之作,《文学自由谈》的编辑老师们同样会发表我的文章吗?于是,我做出了一个“重大”的抉择:我要认真学习和研究李美皆的文章,并且仔细分析《文学自由谈》上发表的众多文章,究竟为什么会受到读者的青睐。为此,我特意去书店买来了李美皆的文学评论新著《容易被搅浑的是我们的心》。通过李美皆的写作,我从《文学自由谈》看到了希望。于是,我立即去邮局汇款,邮购了好几年的《文学自由谈》旧刊,并订阅了当年的最新杂志。我下定决心,要用三年的时间,“攻下”《文学自由谈》。
为了能够使这一梦想变为现实,我从深圳的各大书店购买了大量的文学理论书籍,但写作什么样的稿,才会让《文学自由谈》的编辑老师们从众多的自然来稿中看得上眼呢?对此我想,倘若我投去的稿件,编辑认为写得不好,再投去的稿件,他们仍然觉得不好,第三次看到我名字的时候,也许编辑就会直接将我的来稿扔到字纸篓里去。经过一段时间的反复思索和精心写作,我把自己认为是最拿得出手的文章投寄给了《文学自由谈》,但接连好几次之后,一直是石沉大海。渐渐地我在心里产生了一种莫名的烦恼和抱怨:那么多作者投稿,或许那些编辑们根本就没有认真看过我这位无名作者投去的文章。然而,就在我对《文学自由谈》抱着一种极大的怀疑的时候,2010年夏天的一个中午,当快要下班的时候,我突然接到主编任芙康先生的电话,通知我说,我的文章即将在近期发表,要我将文章的电子版发到指定的邮箱。顿时,我心中的疑虑和对《文学自由谈》的误解和抱怨立刻涣然冰释。在《文学自由谈》发表了第一篇文章之后,我写作的热情迅速空前高涨。遗憾的是,我投给《文学自由谈》的这些文章,却再一次石沉大海。这一次,我没有像之前那样,把怨气一股脑洒在《文学自由谈》身上。因为我知道,别说是我这样的初学者,就是那些著名的学者和文学评论家,稿件达不到发表水平的,《文学自由谈》照样会为其亮起红灯,绝不会因为他们是熟人、名家就放行通过。
为此,我特别钦佩已故的著名学者何满子先生,即便是像他这样名满天下的文坛耆宿,其稿件也同样被《文学自由谈》退过稿。何老的稿子难约,因为凡是与编辑生疏的报刊,他从不投稿。而当《文学自由谈》的高素凤老师几经周折,终于拿到了何老的文章,却万万想不到,这篇被何老自称为“投石问路”的文章,却被《文学自由谈》附上意见退了稿。胸襟开阔的何老,却不以为忤,反而对《文学自由谈》有了好印象,觉得《文学自由谈》选稿有主见,尊重作者,可信可交。不久,经何老穿针引线,好几位与胡风案有牵连的文坛旧人,都成了《文学自由谈》的作者。这种以诚相待,编者与作者的良性互动,成就了当代文坛一则难得的佳话。在当代文坛,某些报刊使尽手段,卑躬屈膝地向名家约稿,可说早已成为了家常便饭。名家向杂志无理耍大牌的现象,也是屡见不鲜。试问当今的各种文学报刊,有几家敢像《文学自由谈》这样,将向名家的约稿又退了回去的?一位著名大型文学杂志的编辑就告诉过我,他们杂志曾经向某位文坛大腕约过稿,但这位大腕的小说却实在是写得太一般。但为了杂志的生存,该刊不但没有退该大腕的稿,而且还为约到该大腕的稿,专门举行了一个特别庆贺的饭局。在饭局上,另外一些著名作家们对该大腕的这部稀松平常之作,无不表现得激情澎湃,欣赏备至,甚至赞不绝口。可是当该大腕一离开饭局之后,同样是这些著名作家,却立马在背后对该大腕嗤之以鼻:他又不缺钱花,这样的小说,也好意思拿出来发表,忽悠读者?正因如此,我们从当今文坛上常常看到,那些耍大牌的著名作家,往往都像是天子下诏一样,任何一家报刊都只能无条件接旨。他们的稿件,即使写得很差,编辑都只能装傻,甚至连一些明显的错别字和语病,乃至知识性错误,在发表时都没有谁敢去动一动,更不要说退稿了。在文坛的生态早已被严重破坏的今天,某些文坛大腕确实把自己当成了报刊杂志的衣食父母,谁还敢去得罪?
作为一个从未受过专业训练,并且长期远离故乡,漂泊在深圳的打工者,当我的文章不断在《文学自由谈》和其他众多的报刊杂志发表之后,接二连三的脏水,也随之一盆又一盆地向我泼来。在这些“脏水”中,最让人感到可笑的就是那种不讲学理,只讲歪理,泼妇骂街式的侮辱。他们首先质疑我的写作动机是为了出名,其次给我定的罪名是不懂文学,再其次就是蛮不讲理。仿佛文学这玩意儿只有他们才能玩,而我就是一个罪恶滔天、罄竹难书的门外汉。有的人甚至在文章中气势汹汹地攻击我“制假造假”,并质疑我的“谬论”将把中国文学引向何方?有位“博导”居然公开撰文批判我:“媒体发表了唐小林的一篇大作:《是专业批评家,还是“吹捧专业户”?》。文章的基本观点就是,文学批评只要从正面评论作家作品的质量,那就是‘吹捧’。”看到这位“博导”欲加之罪,满肚子戾气的文章,不禁让我这个从未进过大学校门的人大吃一惊。我与这位“博导”素来无冤无仇,我的文章为什么会使其如此恼怒呢?而另一位名牌大学的“博导”,对我的文章同样恨之入骨,甚至不惜有辱斯文地公开辱骂我的文章是“狗屁文章”。是因为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过批评学院学术体制的《装腔作势的“组合轴”》,从而触犯了学术体制下某些人的既得利益,还是我的文章说出了许多人不敢说出的文坛真相,戳到了某些人的痛处?一位被我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公开批评过的著名文学评论家,对我的文章大为光火,在大庭广众之下愤怒地说:“我是从来不看《文学自由谈》的,连有人批评我的那篇文章也是别人在电话里告诉我的。”一方面大声宣称自己不看《文学自由谈》,一方面又对《文学自由谈》耿耿于怀,怒不可遏。有谁会想到,当今某些当红的文学评论家,居然是如此的弱不禁风,其“学术”连一丝半点的质疑都经受不起。这恰恰说明,《文学自由谈》并非像当前众多温吞水似的杂志,而是像一剂苦口的良药,虽然常常会使某些人感到难以适应,乃至反应强烈,但这一切都是出于编辑们良好的愿望——热切地为中国的文坛切脉问诊。我的文章之所以能够得到《文学自由谈》和众多读者的认可,是因为《文学自由谈》认定的是“在文学的范畴内持之有故,言之成理”,而绝不是花拳绣腿,或者只看作者的名头有多大。据我所知,有的文学理论刊物,居然无厘头地公开声明,投稿者必须是副教授以上职称,或者必须拥有博士以上文凭。按照这样的逻辑,鲁迅先生都没有发表学术论文的资格,因为他连一张本科文凭都拿不出;沈从文先生更是不允许写小说,因为他的最高学历,也仅仅是小学毕业。在言之有物的《文学自由谈》上,我们绝对看不到那种一大堆具有高级职称的“知道分子”在对文学瞎扯淡,大量制造学术垃圾。
自从我的文章在《文学自由谈》和《文学报》“新批评”大量发表之后,很多著名作家和学者都给予了我热情的鼓励。一位鲁迅文学奖获得者告诉我说:“《文学自由谈》是我很喜欢读的一本杂志,因为它敢于在文坛上发出自己的真声音,让我们看到许多其他刊物上看不到的东西,说出了许多我们想说,而又不便说出的心里话。圈内人都知道,如今某些著名作家写的东西实在是太差了,他们依靠一两篇作品成名之后,就不再认真读书和潜心写作,而是一味在消费自己的名气,而某些评论家的瞎吹捧更是太离谱了!文坛的风气真的很令人担忧!如果我们这些人说他们的作品不好,别人还会误认为是同行之间的互相嫉妒。因为你与文学这个圈子没有多少瓜葛,不需要瞻前顾后地考虑人际关系,所以你能无所顾忌地放开来写。”而另一位著名学者也告诉我说:“你在《文学自由谈》上批评著名学者XXX的文章写得非常好。”我觉得,对于当下鱼龙混杂的中国文坛,我们有必要进行一次认真的清理。文学批评家们要做的工作,就是要把那些名不副实的作家和鱼目混珠的作品认认真真地清理出来。对于那些浪得虚名,与某些当红作家上下其手的空头批评家,我们更需要毫不客气,勇敢地指出来。只有这样,中国的文学才会真正有希望,而绝不是像如今这样看似到处莺歌燕舞,文学大师满天飞,却只有高原而没有高峰。
早些时候,我曾在网上看到有的作者对《文学自由谈》大发牢骚,其理由是他多次投去的文章都没有发表。但我要现身说法地告诉这些作者,《文学自由谈》是一份拥有文化良知的杂志,他们绝不会像某些杂志那样去推敲人际关系,专门考虑怎样去创收。对于文章品质一向严格要求,且不收取任何版面费,《文学自由谈》多年来难能可贵的坚守,铸就了它在文学理论界良好的口碑。一个作者向《文学自由谈》投稿没有发表,原因可能是多方面的,作为一个作者,我们不妨反躬自省,我们的文章是否质量都很高,而即便是质量很高,但碰巧在此之前,该刊或者其他报刊已经发表过类似的文章,也有可能成为稿件不被录用的原因。尤其值得一提的是,在《文学自由谈》这份“由名人奠定品牌,由非名人保持锐气”的刊物上,我们每期都可以看到众多名人高质量的文章,同时也可以看到一些名不见经传的无名作者充满锐气的文章。如近来引起文坛关注的作者谢端平,仅仅是一位在深圳打工的业余作者,在向《文学自由谈》投稿之前,他几乎没有发表过多少文学评论,但就是这样一位毫无“人脉”的无名作者的稿件,却在众多的自然来稿中引起了编辑的关注,使其从众多的自然来稿者中脱颖而出。因为有了《文学自由谈》的热情扶持,谢端平对日本著名作家村上春树的批评,及其系列文章才越来越引起文坛的关注。在谈及此事时,谢端平尤为感激地说:“像《文学自由谈》这样,对一位无名作者的来稿只认质量,不讲关系和人情的刊物真的不多。”我们深深地感到,有《文学自由谈》这样热心发现和扶持文学新人的杂志,真是我们这些无名写作者的福气。
在我看来,一份具有独立思想的杂志,从来都不会人云亦云,低头向世俗妥协的。《文学自由谈》的“胆量”,来自于它有一个远见卓识,以文学事业为大任的优秀团队。与众多文学理论刊物一边倒,清一色的采用表扬稿相比,《文学自由谈》最令人尊敬的是它开阔的胸襟,及其活跃的争鸣气氛。即便是经常在《文学自由谈》上发表文章的名家,也从来不会像在其他刊物一样,享有不受批评的豁免权。细心的读者也许可以看到,在“反弹”里发表批评名家文章的,很多都是那些并不为人熟知的无名作者。而在《文学自由谈》上经常发表文章而被批评的名家,也从来就没有因为受到无名作者的批评,借机对《文学自由谈》耍大牌,甚至以不再为其“赐稿”相威胁。正是因为有了这样一批心胸豁达的文坛名家的鼎力支持和真诚的理解,才奠定了《文学自由谈》在当代中国文坛独特的品牌地位。
有的读者说,像唐小林这样一个没有任何关系的无名小卒,居然能够在《文学自由谈》这样著名的杂志上发表如此之多的文章,这样的现象,在当下的杂志大多习惯于依赖名人,对当红的文学名人高唱赞歌的大环境中,还有几家杂志能够像《文学自由谈》这样,不怕得罪那些当红的作家和文学批评家,直陈其写作的弊病,敢于揭露文坛真相的?有读者在其博客中写道:“天津出版的《文学自由谈》与众不同,敢于硬碰硬,说真话不讲一点情面,甚至支持无名小卒唐小林。”这位热心的读者甚至担忧,那些被我批评过的报刊和作家对《文学自由谈》不满,继而对我进行封杀。但我相信,那些受到批评的报刊和作家并不会个个都是鸡肠鼠肚,即使有个别当红作家对某些批评家的批评表示强烈不满,甚至对批评家大泼脏水,但这种颟顸的做法,最多也只能是给文坛留下笑柄。真正有出息的作家、评论家,从来就不会如此惧怕批评,一旦遭受到批评,就双腿打颤,一病不起的。鲁迅先生早就说过,批评必须坏处说坏,好处说好。《文学自由谈》上的那些批评文章,都是言之有物的文学批评,只是某些被批评的名家,曾经得到了太多的鲜花和掌声,还不习惯这种良药苦口的批评。如同别林斯基所说:“不管一本杂志多么坏,多么萎靡不振,可是只要偶然登载一篇精彩的批评文章,这篇文章就会被人阅读,登载它的这一期就会被人从尘封积压的地方翻出来重见天日;杂志具有强大的力量,首先应该归功于批评。如果没有批评,杂志就像是没有脸的人像,解剖学的标本,而不是活生生的有机的生物。为什么会这样?这里有许多原因:被损害的自尊心,个人利害关系,但最主要的是:对于教养的渴求。”能否坦然地面对批评,这取决于被批评者自身的教养。在当今的文坛,某些当红作家常常误以为,自己比评论家要高人一等,是他们的作品养活了评论家。正是因为如此匪夷所思的想法,他们在评论家的面前,常常从骨子里表现出一种趾高气扬的傲气。有的作家甚至公然宣称,某大牌作家“是一个可以在批评面前获得豁免权的作家。他有毛病又怎么样?要求XX完美是野蛮的。”在他们看来,批评家的工作,纯属是轿夫一样服务性的职业,或者像作家的三陪小姐一样,只能让作家开心。而某些批评家毫无节操,丢人现眼地对某些当红作家肉麻的飙捧,更是让文学批评的声誉雪上加霜。三十年来,《文学自由谈》上那些一针见血,敢于直陈某些作家创作弊病的文章,更是赢得了同行们发自内心的尊重。
《文学自由谈》是我的写作梦想开始的地方,它使我在文学批评的写作上迈出了坚实的步伐,并且越飞越高。让我感到欣慰的是,我发表在《文学自由谈》上的《谢冕的名气还能透支多久?》,有幸入选了《2014中国随笔排行榜》一书。《文学自由谈》就像是一座引领我通向文学批评的桥梁,它让我的文章从深圳走向天津,继而又飞向了远在上海的《文学报》著名的“新批评”。倘若没有《文学自由谈》为我树立起的信心,我的写作即便没有放弃,但我在艰难的打工之余牺牲休息时间,费尽心血写出的那些文章,或许至今都还在一家又一家编辑部之间艰难地“旅行”。从《文学自由谈》出发,我在写作的途中,感受到了贴心的温暖和关怀。我曾在《一个圈外人的感想》中说:“在长期的阅读中,我越来越感觉到中国的文坛可能出了问题。比如,某些作家稀松平常的作品,居然被众多文学批评家捧上天,在各种文学理论刊物上换汤不换药地反复研究。我觉得,当今的中国文坛,‘哥们’义气越来越严重,而且正在掀起一股又一股新的造神运动。面对这股‘妖风’,我决定以民间观察和圈外人的方式,来表达我对中国文坛的感想,揭露某些作家和文学批评家,为了一己私利而长期互相同谋的做法。”我也非常清楚,我写作的那些文章,即便是国内有多如牛毛的文学期刊和报纸,但要想真正发表出来,却犹如蜀道之难。我在内心里非常庆幸和无比感激的是,在步履维艰的写作中,我能遇到像任芙康、黄桂元和陈歆耕这样独具慧眼的主编。在我看来,中国的文学批评家之所以没有在与某些著名作家的勾肩搭背中被完全腐蚀掉,举起白旗,全军覆没,正是因为还有像《文学自由谈》和“新批评”这样的文化阵地,还有一批像韩石山、李建军、陈冲、李美皆这样敢于逆流而上,不愿低首下心地充当某些当红作家吹鼓手的文学评论家。再多飞溅的唾沫,也不能阻挡他们以百倍的勇气,筚路蓝缕,为当下中国文学开出一条血路的决心。
是《文学自由谈》为我提供了宽广的平台,让更多的读者听到了一个无名作者对中国文坛发出的声音。这本努力表达民意,特立独行、充满激情的刊物,在三十年的风雨历程中,始终保持着一股令人敬仰的锐气。在《文学自由谈》庞大的作者阵容中,有着无数在当代文坛上卓具影响的文学批评家。由他们奠定品牌的这本杂志,早已深深地镌刻在了每一个热爱它的读者的心里。作为《文学自由谈》的一位读者和作者,我只有在今后的写作中更加努力地写出更多让读者喜爱的文章,才能无愧于默默无闻的编辑老师们对我热情的扶持和鞭策。因为有了《文学自由谈》,才使我在长年漂泊的岁月里感受到了内心的无比充实,并且享受到了写作带给我的难以言喻的快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