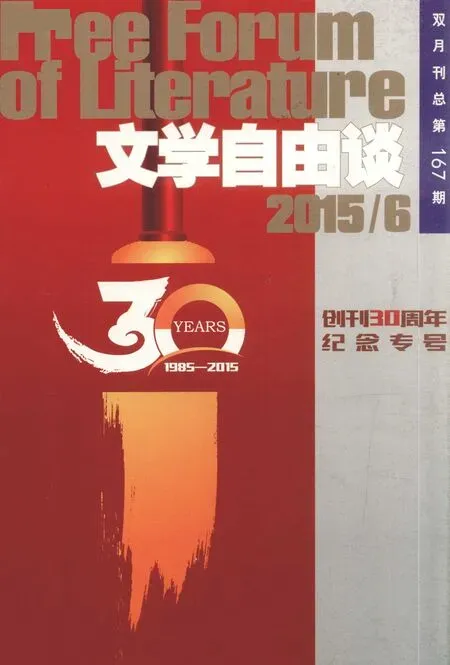岁月感与《文学自由谈》
2015-03-20黄桂元
黄桂元
岁月感与《文学自由谈》
黄桂元
我相信,世界上有一种人,其岁月感仿佛与生俱来。这或许也意味着,谈论“岁月”,未必就是老年人的专利。玛格丽特·杜拉斯的《情人》,女主人公在第一页就说:“18岁,我就老了。”我虽然在《文学自由谈》供职不足十二年,但回望它曲曲弯弯的来路,内心便有了可称为“岁月感”的那种滋味,令人恍兮惚兮。
还是从“上个世纪”谈起吧——我们已经习惯了用“上个世纪”来界定一些并不久远的陈年往事,仿佛那些往事距今已有百年之遥,而我们每个人都是仍在苟活的垂垂老者,于是岁月感也由此如影随形,纠缠不休——《文学自由谈》诞生在公元1985年秋季,如今已是三十华诞。三十年前我恰值而立,大学毕业仅仅三载,在一个党政机关当差,一部分工作便是阅读,但多与兴趣无关。那时我已有作品发表,对所谓文坛却懵懂无知。随着作家梦的渐行渐远,我开始担忧一辈子就这么交待给了那些无尽无休的速朽公文。不觉之间,《文学自由谈》这份由市文联办的小开本刊物进入了我的阅读视野,我很快为之吸引,为之遐想,为之挂肚牵肠。或许我的天性对一本正经的文章不感兴趣,而喜欢读自由言说的批评文字,但我从没有想到有朝一日会与这本刊物有任何交集。
一天下班后,我找到处长,吞吞吐吐地谈了离开的想法。处长大吃一惊,不明白我怎么会突然提出这么个古怪的要求,而且我的理由还很书生气很不合时宜,比如想有自己的阅读和写作啦,学以致用啦,专业对口啦。处长面容变得严肃了,规劝我:“是不是你学了中文,就觉得在这里屈才啦?告诉你,我们这里才真正是中文系毕业生最合适的对口专业,不是什么人想来就能来的,里面的学问大得无边!”我蔫巴巴垂下脑袋。处长和善地笑一下,拍拍我的肩膀:“小伙子,别三心二意了,你还年轻,文字也不错,把眼光放远些,老老实实地好好干!”
我“老实”了两三个月,内心又开始蠢蠢欲动。我大着胆子直接找到部领导,语无伦次地摆了一堆离开的理由:我十五岁就发表习作,读大学前还当过两年文学期刊编辑,到大学毕业时已有若干诗歌、散文和评论发表,希望组织上能考虑我的具体情况,最好能让我的工作与文化更靠近一些。部领导很和善,大约已经看出“烂泥扶不上墙”,干脆放行。一些同学、同事知道后,曾苦口婆心地劝我迈出这一步要慎重,三思而行,有朋友甚至直言,早知今日,又何必在宣传部兜这么大个弯子才回去搞文学?到文联就能搞出名堂来?三十多岁的人了,水往低处流人往高处走,老农村妇都懂的道理啊!我苦笑着。我承认我的选择有些冒险,但跟我能不能在文学上搞出名堂扯不上关系,不过是我的那根文学“筋”总在作怪,这已经是没办法的事了。
就这样,我的工作关系由巍峨庄重的市委深宅大院转到了市文联。那时文联只有三十来号人,因为基建,没有固定的办公场所,只临时租借了一座八国联军时期的百年旧楼,里面墙皮剥落,光线昏暗,空气潮湿,我每天拎包踩着吱呀松动的楼梯,到只有两间窄屋的一家杂志编辑部重操旧业,但只有我能感觉出此时此刻自己的心正在快乐地呻吟。从大机关的干事摇身一变成了普通杂志的编辑,昔日光环在瞬间熄灭得干干净净。如果说这种落差在世俗眼里毫无反应,那是骗人,但无论如何,我体会到了个人性情回归文学轨道的轻松。终于可以踏下心来进入阅读和写作了,那些澄明的文字引领我的日子远离喧嚣,安于平静,进入灵魂的一种自在仪式。我最初在《艺术家》供职,后来,两家刊物都由南开大学中文系毕业的任芙康师兄执掌,这个事实也构成了我文学人生的一种宿命。那时候我开始涉足文学评论,但多属于被动式写作,削足适履,中规中矩,唯独给《文学自由谈》写稿无任何顾忌。老任在我眼里是个神奇人物,他把自己独特的办刊理念坚定不移地注入这本刊物,并为其打上了鲜明的个性印记。他给我的定心丸是:不要有框框,写自己内心想写的,但要读着有趣。2004年春末夏初,我被调到《文学自由谈》做老任的助手,几乎是在他耳提面命的情状下,完成了“读者——作者——编者”的文学人生三部曲。
《文学自由谈》是一本积极介入文学现场的小开本批评刊物,始终倡导一种即时、及物的近距离文学批评。它的办刊思路和使命很简单,就是以文学批评而不是以学术研究的姿态,搭建一个可以听到各种不同声音的批评平台,它的三十年历程见证了新时期以来的文学发展轨迹。许多年来,我们所受到的教育是“多数人的想法永远是对的”,而在这里,你可以根据独立判断说“不”。进入这样的写作语境,意味着你选择了一种“偏离”或“游离”,很容易被视为另类。这三十年岁月,全球化、互联网、大数据给当今中国社会方方面面带来的变化之巨,非天翻地覆、沧海桑田不足以形容、描绘,而再看《文学自由谈》,似乎还是最初的模样:办刊宗旨一意孤行一如既往,小开本,随笔化,现场风云,问题意识,逆水行舟,我行我素,文风锐利,笔墨生趣,诠释的是一种以不变应万变的批评气质和文学向度。
有一个词已经被世俗用滥了,但请原谅我一时还找不到更适合的可以代替之,这就是——坚守。在我看来,一本文学批评刊物,在普通读者中或许可以是小众,但如果在作家中依然是小众,被束之高阁,不受关注,就不大正常。批评刊物不应办成文学研究刊物,只给圈内少数受过专业理论训练的人士来读。比较专业的文学研究刊物当然需要,但不可强求一律。这三十年的文学批评,从文学自觉回到学术自觉,当然是中国文学的进步,但同时也付出了一些代价。如今的文学理论刊物,多与经费实力充裕的高校互为养殖,彼此借力,这也决定了,置身其间的是一个新的、以前不曾出现过的学术环境。这个环境由什么构成?基本上是由大学体制构成,或者说,现在的学院评价体系已经深深影响甚至牢牢左右了文学批评期刊的办刊方针。应该承认,在大学评价体制下,期刊的非学理化倾向确实得到了有效扭转,但也正像一些有识之士指出的,有不少学院派批评基本上是伪学理的,文本并没有细读,很快就过渡到理论,他们津津乐道的理论常常是与文本游离的,与作家的写作是“两张皮”,使人望而生畏,然后是望而生厌,不被作家当回事,也就成了常态。当文化研究成为批评的一个主要方法之后,阐释变成了主流。以文化研究带动批评的深化固然值得肯定,以丧失批评趣味为代价却是不可取的。学者的思考可能更厚重,现场批评则更需要有血有肉、生香活色的体味,好读,有趣,而趣味正是一些故弄玄虚的理论家最缺乏的东西。
对于气象万千的文学现场,批评刊物需要接文学地气,与作家的写作息息相关,永远保持对文学现场的一种关切,一种介入,就像法国批评家蒂博代说的,文学批评应该表达一种“自发的批评”的声音,要热烈地爱,还要清醒地说;它最需要的不是学者日积月累的卡片,而是机智、敏感、生动、迅速的即时反应,是刚出炉的滚烫的现场批评。它的天职是抵制理论的无味缠绕、虚假的廉价捧场和无关痛痒的点赞喝彩,而注重文学话题的当下性、前沿性,起到文学现状晴雨表的作用。很显然,这一类现场批评本来就不是为传世、为后人写的,却可以为未来的经典作品研究和文学史研究作筛选和铺垫,因而是必不可少的。这类文章大多数会消失于文学史的视野,却起到了文坛哨兵和轻骑兵的有效作用。没有现场批评就没有学术的进一步深入,或者说,没有成千上万的充满争议的见仁见智的现场批评,就没有后来的文学史研究。所以蒂博代认为,不同的声音要比单一的声音好,对话要比独白好,争议要比一潭死水好。文学批评期刊应该体现一种大自在大境界,汇拢各种面貌,各种声音,各种性情,各种趣味,力求向当代文坛强调一种海纳百川、吞吐万象的批评气度,营造一个区别于一般理论刊物路数的独特存在。有位诗人的一句话深得吾心:对于创作而言,团结是一种力量,不团结也是一种力量,这才是正常的。欧美文学、俄罗斯文学的鼎盛时期哪有那么多大团结?百花齐放,百家争鸣,才是最真实、最生动、最有包容性的大合唱,才是最高意义上的和谐。这个过程中,批评者可能由于来不及深入思考而出现某种偏颇和疏漏,产生一些误解甚至情绪化的谬见,也无须大惊小怪,说到底,这是来自现场的还来不及冷却下来的直接感受。《文学自由谈》开辟了一个场域,为之带来一种活力四射的互动——与作家的互动,与读者的互动,但很可能不是与少数专家的互动。它明白,文学批评如果失去了对发展中的文学进程的有效性,其存在的意义就会大打折扣。
这些年,我越来越能体会芙康为刊物付出的心血和辛劳。时下,中国并不缺少思想厚重、学理规范、言说严谨的文学理论刊物,《文学自由谈》的出路在于求新立异,另辟蹊径。《文学自由谈》的三十华诞之际,也恰逢我退休之时,巧合的是,年富力强、底蕴厚重的潘渊之、董兆林组成的刊物核心团队也毕业于南开大学中文系,我相信这一定有一个不同寻常的隐喻。我为曾经拥有一段与《文学自由谈》荣辱与共、相濡以沫的岁月而欣慰,也为刊物未来的岁月祈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