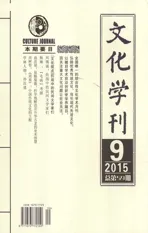从《盐铁论》看西汉儒学的演化
2015-03-20叶根虎
叶根虎
(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从《盐铁论》看西汉儒学的演化
叶根虎
(安康学院,陕西 安康 725000)
关于汉代选择儒学作为国家主流意识形态的原因,古今学者多有论述,但鲜有从《盐铁论》展开论述。本文以《盐铁论》为主,以其他汉代史籍为辅作为研究材料,认为西汉儒学在与政治的交互关系中,经历了由“儒学”向“儒术”的演化;同时,执行法家政策的政治家们也参与到对儒学的选择性阐释与改造中,发掘出“秋杀”一词,为法家政策找到儒学的理论根据,使儒学成为一种富有包容性的学说,逐渐被官方接纳与认可,最终成为统治中国数千年的主流意识形态。
儒学;儒术;秋杀
盐铁会议召开于汉昭帝始元六年(公元前81),根据当代学者考证,《盐铁论》成书时间“应该不早于公元前66年,其大体时间约早公元前66年之公元前 49年之间,是盐铁会议后20年著成的”[1],属于西汉著作,在考查西汉的儒学演化上,有着时间上的切近性。《盐铁论》的性质,经当代学者考证,并非桓宽臆造之书,[2]“基本上忠实了盐铁会议的论辩记录”[3],具有极高的史料价值,以此为材料,当可以得出相对科学可靠的结论。
一
首先看盐铁会议的背景。为什么偏在昭帝始元六年召开盐铁会议?导火线是杜延年向霍光建议“年岁比不登,流民未尽还,宜修孝文时政,示以简约宽和,顺天心,说民意,年岁宜应”,于是“光纳其言,举贤良,议罢酒榷盐铁”,[4]似乎是为了让百姓休养生息。但细读霍光本传,很容易得到另外的答案,即帮派斗争的需要。武帝后元二年春(前87年)崩,将昭帝(时八岁)托付给大臣霍光、金日磾、桑弘羊、上官桀,但后来上官桀、桑弘羊与燕王旦都因种种原因怨恨霍光,并组成集团,反对霍光。在昭帝 14岁时,即始元六年(前81),三人趁霍光休假,向皇帝奏报霍光的违制之举,认为其有篡逆之心,应予以罢免。此次由于皇帝的支持而未能成功,但“后桀党与有谮光着,上辄怒曰……”[5],可见党派斗争从未停止。斗争的结果是上官桀“(始元二年)正月壬寅封,五年,元凤元年,反,诛”;[6]“二月乙卯,搜粟都尉桑弘羊为御史大夫,七年坐谋反诛”;[7]始元七年即前80年,即召开盐铁会议的第二年,向霍光告发这次谋反的正是杜延年。从这个角度看,杜延年的进言很难说是为百姓,还是为同党出谋划策。可见,前81年盐铁会议的召开,是上官桀派与霍光派于前81到前80年一系列激烈斗争事件中的一件。这个激烈的帮派斗争的背景,是我们理解《盐铁论》内容必须要考虑的。
二
参加会议的人明显分成两个派别,即雇佣文人贤良文学派和桑弘羊。他们实际上可以代表两种思想路线,一种是掌握儒学,想靠儒学取得仕进的文人,一种是推行法家路线的当权派。这次激烈的思想交锋都曝露出各自存在的问题,但却都对推进儒学与政权结合,并成为国家意识形态起了很大的作用。
先说贤良文学们展现出的儒家学说。儒家面临的问题是怎样在国家意识形态方面有影响,将其融于国家行政体制中,即儒家如何当权。武帝时设立了《易》博士,《书》欧阳氏博士,《礼经》博士,《诗》三家博士,但博士只是“具官待问”[8]而已,根本没有掌握实权。儒家在朝廷拥有显赫地位的仅高祖时的叔孙通和武帝期的公孙弘。而公孙弘本人也只是“习文法吏事,缘饰以儒术”,[9]倾心于吏事,于儒学不甚用心。武帝朝所诏用的贤良赵绾、王臧草明堂位未就,就被赵太后视为方术之学,设法赐死。[10]儒家在朝廷中没有倾心推行儒学并有广泛社会影响的人物,这对儒学的长久发展不利。
儒家的优势在于国家有意识地扶植儒学,如设经学博士,“至武帝初立,魏其、武安侯为相而隆儒矣”,[11]儒学的影响在逐渐扩大,儒学的势力也在慢慢成长。由于儒家长久以来重视教育,在文化传播上有影响力,如儒家提出的理想治世图景,《礼记》中的大同,无为而治的黄帝等三王之世,以及被董仲舒美化的上古大治之世,“上下和睦,习俗美盛,不令而行,不禁而止,吏亡奸邪,民亡盗贼,囹圄空虚,德润草木,泽被四海,凤凰来集,麒麟来游”,[12]甚至具体到“成康之隆,囹圄空虚四十余年”。[13]这些思想甚至成为整个社会的共同理想,连武帝本人的诏书中,也宣称以儒家的治世图景作为行政的终极目的。
朕闻昔在唐虞,画象而民不犯,日月所烛,莫不率俾,周之成康,刑错不用,德及鸟兽,教通四海。海外肃眘,北发渠搜,氐羌徕服,星辰不孛,日月不蚀,山陵不崩,川谷不塞,麟凤在郊薮,河洛出图书,呜乎,何施而至此与![14]
有诏书确认,说明儒家的思想在社会上已被普遍承认,为什么儒家在国家政权中缺乏影响力?因为,在统治者看来,儒学本身“迂远难行”,这成了儒学进入国家行政机构的最大障碍。秦始皇准备封禅时,儒生进言“蒲车上山,埽地而祭,席用葅秸”,[15]被始皇认为难施用而废黜儒生。这种情况在武帝时又上演了一遍。在草封禅议上,武帝对儒生寄予厚望,结果儒生拘于古《诗》《书》而不敢创新,又有派系之争,武帝给他们封禅礼器予以示范,结果依然让武帝大失所望。武帝甚至连“采儒术以文之”的作用都没有达到,于是“绌偃、霸,而尽罢诸儒不用”,[16]儒生在武帝那里失宠。在《盐铁论》中,大夫们也认为儒者言论“信往而乖于今,道古而不合于世务”,[17]理论与现实差距过大,真正原因,是上层怀疑儒者的行政能力,怀疑儒学在面对具体行政事务时的通变能力。在《盐铁论》中发现,儒者的代表贤良和文学也确实暴露出了这样的问题。
丞相曰:先王之道,轶久而难复,贤良、文学之言,深远而难行。夫称上圣之高行,道至德之美言,非当世之所能及也。愿闻方今之急务,可复行于政,使百姓咸足于衣食,无乏困之忧,风雨时,五谷熟,螟螣不生,天下安乐,盗贼不起,流人还归,各反其田里,吏皆廉正,敬以奉职,元元各得其理也。[18]
丞相提出了几个具体问题,包括流民多、盗贼多、官吏贪污等,以及思考有没有办法解决这些问题。但贤良立即反击:“先王之道,何远之有”。接着举历史事例来证明施行仁义,成效卓著,运用的说辞与先秦士人用的大致相同,对具体问题无一涉及,这只能说明他们的学识与眼界还在古儒学那里。大夫也问:“诸生上无以似先王,下无以似近秦,令有司可以举而行当世,安蒸庶而宁边境者乎?”[19]
文学又开始重复仁义,并无新见。大夫们在给皇帝的奏章中称“贤良文学不明县官事”,[20]这固然有法家长期把持政权、儒家对政权运作不熟悉的原因,但也说明儒家缺乏一种把儒学与国家具体行政事务相结合的理论,可以套用当今俗语,即缺乏把儒学理论与具体的汉朝国情相结合的理论创新。
其实,儒学早已在寻求改变。早在陆贾的《新书》中,就有了“书不必起仲尼之门,药不必起扁鹊之方,合之者善,可以为法,因世而权行”[21]这样的求变思维。至《春秋繁露》,有“绌夏、亲周、故宋”[22]之说,运用三统循环说解释历史,同时大讲灾异,实际上是儒学系统对汉代具体情况作出的“常用于常,变用于变”[23]的努力。后董仲舒对儒学进行了大改造。在《春秋繁露》及《汉书·董仲舒传》中,董仲舒确立了两个文化根基,一是天人感应,二是《春秋》。这套理论将王的权力解释为根植于“天”,剥夺了王权的个人属性,即把王权的性质由王本人所拥有的私权,改变为王代“天”执政,实际上成为天地宇宙所共有的公权。这为儒家参与世俗政权留下了空间。同时以天道阴阳与四季更替比于行政之德刑,同时广开天人相与的模拟象征思维模式,为行政行为提供了宽广的可与实际情况相适应、相契合的解释理论,也为具体的行政行为开展留出了空间。①由于篇幅所限,董仲舒的具体理论贡献,容笔者另文详述。这套理论,比较完满地完成了时代留给儒家的课题,完成了“儒学”向“儒术”的转型。[24]在这一转型过程中,阴阳理论与天人相与理论,成为儒学与时代特征相结合而形成的新儒学。
但为什么这套理论在《盐铁论》中没有被贤良文学提及?王利器先生在《盐铁论校注·前言》中列举了大量例子,说明“他们是地地道道地继承了董仲舒的衣钵”。[25]纵观《盐铁论》,贤良文学们言论的主题有三点:(1)攻击武帝的政策;(2)宣扬董仲舒的“正其谊不谋其利,明其道不计其功”,即宣扬纯道德,反对利欲;(3)宣扬仁义,反对任法。可见其的确是经过事先准备。吴慧先生也认为“贤良原已被称为‘子大夫’。文学之所以得‘咸取列大夫’,这种不寻常的‘恩遇’,很可能就是攻击桑弘羊卖力所得的报酬。估计霍光等人在事先已封官许愿,同他们在会下已达成了这笔交易的”。[26]那么,论调其实早已确定,会上只是施展,以及个人的临场发挥。但这恰恰说明了纯学理在面对世俗政权时的弱势地位。学术只有作为工具,作为“器”,才能慢慢被政权接纳。董仲舒的学说最终被接纳,当然还与推行法家政策的政治家在为自己寻找行政理论根据时的选择性阐释有关。
三
法家政策在武昭时期,面临的问题是,由于长期对匈奴的战争,已经使“中国以空虚,边民大困贫”;[27]边费不足,颁布的盐铁、酒榷、均输政策,已导致“一官伤千里”;[28]用什伍连坐之法来控制人民,使“一人有罪,州里惊骇,十家奔亡”;[29]告缗法导致“逋流皆在大家,吏正畏惮,不敢笃责,刻急细民;细民不堪,流亡远去,中家为之绝出,后亡者为先亡者服事;录民数创于恶吏,故相仿效,去尤甚而就少愈者多”。[30]从富裕大户到贫穷百姓,都加入到逃亡行列。而出钱出粮捐官除罪,这些出钱买得官职的人,想方设法谋取利益,导致“公用弥多而为者徇私,上下兼求,百姓不堪,抏弊而纵法,故憯急之臣进,而见知、废格之法起”,[31]直接导致了人民的武力反抗,也迫使皇帝选用酷吏对人民实行镇压。这种政策反而导致矛盾更加激化,吏民益轻犯法,盗贼滋起。国家发兵征讨,这些人散乱失亡,复又啸聚山林,至无可奈何。沈命法又使府吏避匿盗情不报,致使盗贼数量更多。总之,纯法家政策已难以为继。对于这种混乱局面,从皇帝到大臣都在寻求解决良方,于是召开盐铁会议,放下身段向儒者求教,而儒生并没有给召开会议的官僚以满意的答复,倒是大夫们对儒家,尤其是董仲舒的那套集阴阳、数术和五行于一体的理论很感兴趣。细究其言论,得知这种兴趣来源于三点。
第一,这套理论可以为具体的行政行为找到依据。如“大夫曰:五行,东方木,而丹章有金铜之山;南方火,而交趾有大海之川;西方金,而蜀、陇有名材之林;北方水,而幽州有积沙之地。此天地所以均有无而通万物也”,[32]大夫们以此来论证自己均输政策的合理性。
第二,可以把失败的行政行为委之于“天数”,为推诿责任找借口。“水旱,天之所为,饥穰,阴阳之运也,非人力。故太岁之数在阳为旱,在阴为水。六岁一饥,十二岁一荒。天道然,殆非独有司之罪也”。[33]
第三,终极原因,可以为法治的存在找到理论依据,其实是争取法家在政权中存在的合理性,保存法家在政权中的位置。在《盐铁论》中,大夫和贤良文学可以展开对话与沟通的,是在谈论阴阳五行与行政的对应,其中大夫有一段。
大夫曰:金生于巳,刑罚小加,故荠麦夏死。《易》曰:“履霜,坚冰至。”秋始降霜,草木陨零,合冬行诛,万物毕藏。春夏生长,利以行仁。秋冬杀藏,利以施刑。故非其时而树,虽生不成。秋冬行德,是谓逆天道。《月令》:“凉风至,杀气动,蜻蛚鸣,衣裘成。天子行微刑,始貙蒌,以顺天令。”文学同四时,合阴阳,尚德而除刑,如此,则鹰隼不鸷,猛兽不攫,秋不搜狝,冬不田狩者也。[34]
大夫的这段话,首先是说明了四季有生养刑杀,所以为政应仿效天地之阴阳,即四季,依次行政,仅有生养而无刑杀是不对的。把当时流行的俗语“春生夏长秋收冬藏”中的“秋收”换成“秋杀”,则刑法、刑罚就有了天地自然的依据。其次,对儒家所尊奉为宝典的经书广征博引,这里面体现出的这些执政的官僚们对儒家文化的改造与创新,实际上并不亚于儒家自己的创造。由于他们是出于行政目的而利用儒家文化,因此对文化的创造更有目的性和针对性,这种目的性和针对性有时就会转化为创新性。宣帝说:“汉家自有制度,本以霸王道杂之,奈何纯(任)德教,用周政乎!”[35]王利器先生也认为:“王霸之分,方兴未艾,其实汉宣帝所举的一个‘杂’字,就全部道出了这个问题实质之所在”。[36]这与汉武帝的“取儒术以文之”的倾向一致。盐铁会议后,仅废酒榷,未废盐铁,说明盐铁会议的实质是派系斗争。政权在寻找能支持行政行为的理论,而理论也逐渐向政权靠拢,这就是儒学在演化过程中的形态。
《盐铁论》中,无论贤良文学,还是御史、大夫,都对儒家学说广泛引用,且大夫、御史对阴阳五行与行政对应的强烈兴趣,皇帝诏书中对阴阳的谈论,都说明将选择董仲舒阴阳化的儒学作为武帝以后国家的主导意识形态,这是剧烈政治斗争的结果,是整个汉代政治家和知识界的共同选择。
[1]黑琨.《盐铁论》成书时间考[J].四川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3,(3):76-79.
[2]龙文玲.《盐铁论》四十二至五十九篇非桓宽臆造——以《盐铁论》引书用书之考查为中心[J].首都师范大学学报,2012,(6):113-119.
[3]王永《盐铁论》之名义与作者之著作目的考论——兼论所谓“臆造“问题[J].贵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9,(3):69-75.
[4][5][6][7][9][10][11][12][13][14][35][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2664.2936.691.791.2618.3608.2515.2520. 2510.160-161.277.
[8][15][16][27][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3117.1366.1397.3141.
[17][18][19][20][25][28][29][30][31][32][33][34][36]王利器.盐铁论校注(定本)[M].北京:中华书局,1992.130.455.507.463. 9.69.580.192.132.42.428.557.22.
[21]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86.44.
[22][23][清]苏舆着.春秋繁露义证[M].钟哲点,校.北京:中华书局,1992.53.
[24]葛兆光.中国思想史(第1卷)[M].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1.256.
[26]吴慧.桑弘羊研究[M].济南:齐鲁书社,1981.480.
【责任编辑:周 丹】
I206.2
A
1673-7725(2015)09-0203-05
2015-06-25
叶根虎(1979-),男,陕西渭南人,讲师,主要从事中国文化与文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