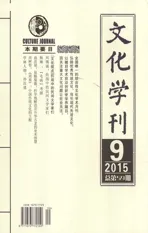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文化与媒介空间
2015-03-20李静
李静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1990年代以来中国的消费文化与媒介空间
李静
(河北师范大学文学院,河北 石家庄 050024)
当今社会是“媒介化”的社会,媒介空间作为无限开放的符号空间,给消费文化的空间生产提供各种原型符号构成,提供跨地域、跨文化的借鉴机缘,且具有“权力”性质,是建构集体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1990年以来的中国媒介空间分布及空间表征呈现出自身的特质:媒介空间走向多元开放局面,空间元素娱乐化、欲望化,在改造吸收西方消费文化的同时,又努力为中国文化传统争取更多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化复兴之路提供机遇。
1990年代;消费文化;媒介空间;社会空间
消费文化提供新的社会活动空间,空间的转换不仅改变人们的日常生活,且改变人们的社会关系、生活方式及生存方式。在消费文化的空间生产和空间消费过程中,一个重要的环节和领域不容忽视,那就是在空间生产消费的运作中,空间作为所指“符号”的意义如何传达?消费者的空间欲望如何与空间生产出的无限欲求呼应对接?消费社会的商品符号和消费文化的生产体系将如何建立?这一切都需要大众传媒(大众传播媒介)扮演的特殊角色得以实现。
“媒介空间”概念最早由约翰·哈特雷(John Hartley)提出。澳大利亚电视学者麦克·金认为,“媒介空间”的理论思想直接来源于前苏联符号学家尤里·劳德曼的“符号空间”……“尤里·劳德曼的‘符号空间’原来是指符号内容的‘普遍性’,这种普遍性保持并滋养意义系统的再生产,正如生态空间保持着生物与生命一样”。[1]“符号空间”具有生命性的传承机能及功能,即它本身包含着可供全人类持续、普遍传播的符号文本,及所有在文本中记忆着的一切事物的历史文化传统,因而,在人类文化传播中,“符号空间”具有潜在的再生性或再生能力。约翰·哈特雷由此而认识到,“媒介空间”存在于“符号空间”,媒介传播本质上就是符号传播。他认为:“媒介的整个宇宙——既是实际的,又是虚幻的,存在于所有媒介形式中(纸质媒体、电子媒体以及荧屏媒体)、所有的种类中(新闻、戏剧)、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中(从艺术到娱乐)、所有的语言形式和所有的国家中”。[2]这样,处于传播状态的各种媒介犹如一个个生命体,其外在形式中都生存着向外普遍联系的生命空间。
第一,媒介空间作为无限开放的符号空间,能为消费文化的传播提供其他国家的所有媒介形式、种类,所有的欣赏趣味、层次,所有的语言、形式,从而给消费文化的空间符号生产提供各种原型符号构成,提供跨地域、跨文化的借鉴机缘。
第二,媒介空间作为符号空间,具有“权力”性质,即可以“借助象征性内容的生产和传送,干预事件进程、影响他人行为甚至制造事件的能力”。[3]具体说来,媒介本身就是一种社会机构,它不仅掌握社会资源,也遵从特定的组织原则、运作规范及法律、惯例的操控和规制,它拥有自身的利益和权力边界,因此,它一方面要维护宰制性社会力量的特定利益,另一方面需要树立其自身的权威并努力使之自然化和合法化,这是同一过程的两面,也是媒介“符号权力”这一术语的内涵所在。媒介权力是通过怎样的形式来实施的呢?通过生产媒介空间,而媒介空间具有区隔作用,即它可以在媒介冲破原来的时空壁垒,在广泛地域中同步传送和接受信息时,制造特定的社会类属、位阶和界线,并使之逐步内化到社会成员的日常生活中,影响他们对媒介、自我、群体及社会的认知与体验。在此过程中,某些特定的社会类属、界线和位阶得到象征性的呈现与强调。
媒介空间的符号权力背后决定因素是什么?在对消费文化的众多研究中,鲍德里亚指出,当代社会是一个不断生产出各种消费符号的世界,消费文化强调的不是商品的使用价值,而是其符号价值和意义,正是通过符号编码或符号逻辑的作用,商品才被赋予了意义,而生产符号意义的工具和决定力量在于资本和媒介。[4]就资本与传媒的关系而言,传媒话语权的大小与资本的雄厚程度有直接关系:一般来说,资本实力越强,传媒话语权就越大。媒介为维持自身的话语权,也要受资本的控制和支配。但是这并不意味着媒介空间仅仅是一个受制于资本的传播工具,不能保证自身独立性,完全为资本服务。从另一角度看,前文提到媒介空间本身就是一个社会机构,具有维护自身权力合法性和自然性的需要,所以,它不仅可以通过制造消费需求为社会资本的扩张提供必要的环境,甚至引导资本流向,且为自身获得雄厚资本——传媒的成功运作在公众心目中的形象,其本身就是一种能产生经济效益的资本。二者事实上是一种相辅相成、互为促进的关系。
第三,媒介空间作为符号空间是建构集体认同的重要文化资源。媒介空间利用符号权力来形成消费的“想象共同体”,获得消费文化的认同。如通过媒介信息接受活动——参加节目、收听广播、观看新闻、插播广告、看报纸,媒介空间的参与者和接触者获得共同的文化感受和想象,而与此同时,参与者或接触者看到同样的节目或报纸也同样在地铁、理发厅、或者邻居家里被消费时,更是持续地确信那个想象的消费世界就根植于日常生活中。在这种周期性的消费中,电视、报纸、电脑等介质创造出一种同是阅读、收听和观看的符号权力空间,“虚构静静而持续地渗透到现实之中,创造出人们对一个匿名的共同体不寻常的信心。”这是媒介空间“想象共同体”形成的重要基础。它悄悄潜入人们的日常生活,媒介信息成为人们对自我、集体和社会定位的重要参照系,成为人们对拥有相同经验的其他社会成员的感知。从这个层面看,消费社会媒介的空间生产具有重大的意义:媒介空间的重心发生转移,“全球的大众传播内容都在向消费主义靠拢,即传媒着眼于公众物质消费和精神消费的创造,在传播中重视对物的符号意义的强调及其所营造的‘消费社会’的氛围”。[5]媒介空间也成为消费文化的一部分,借助对各种文化和信息的组合与融汇,构织一个庞大而诱人的仿真符号世界,不但俘获人们的心,模糊现实和仿真的界限,且唤起人们对预设生活模式不断追求。在这里,传媒空间不知不觉中扮演了组织大众生活方式和体验方式、建构社会现实和未来世界的重要角色。
联系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消费语境,如前所述,中国从抑制消费以便优先发展重工业的现代化战略,转向有利于消费主义兴起的、以低廉劳动力成本参与全球分工和竞争的全球化战略,中国消费革命的主要支撑力“是国家的经济发展政策”。由于国家刺激消费的同时采取“对外开放”的政策,全球化作为外因也起到一定作用,从而掀起消费主义文化在中国兴盛壮大的热潮。而这种消费热潮的进一步扩散必须由大众媒介空间来完成。20多年来的改革开放,中国传播媒介的规模迅速扩大,在总体水平上同发达国家的距离大大缩减。当下中国已形成以报刊、广播电视、互联网、手机通讯为主体,技本先进,多层次、多功能、多手段,基本覆盖全国城乡并面向世界的传播空间。广大受众面对一个可进入或可接触的媒介空间,其利用媒介权力将涉及到人们吃、穿、住、用、行等方方面面,它们和商家一起不断设法创造出消费时尚,赋予商品、消费活动与服务以丰富的文化与精神内涵,让人们在消费时能够获得一种心理上的满足,创造出消费观和生活方式的信息模拟世界。但基于中国消费文化后发速生的特点,1990年以来的中国媒介空间分布及空间表征呈现出自身特质:媒介空间走向多元开放局面,空间元素娱乐化、欲望化,在改造吸收西方消费文化的同时,又努力为中国文化传统争取更多话语权,为中国现代化复兴之路提供机遇。
1992年之后,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居民消费水平显著提高,中国已进入耐用消费品生产和消费时代。而生活必需品的生产与消费则退于次要地位。中国城镇居民生活开始进入富裕阶段,农村居民也已解决温饱问题,开始向小康生活迈进。实行社会主义市场经济后,中国媒介空间生产速度快速提高,尤其是最近几年,中国部分城镇居民的媒介消费水平已达到或接近西方发达国家的消费水平。新兴的媒介空间充满活力,各种反映改革开放、现代生活、异域文化的节目应接不暇,媒体空间在世界资本市场的主导下,更注重消费文化在日常生活中的影响力和渗透力,电视、电影、电脑、电话成为大众消费文化的空间表征。以电视为例,随着中国电视媒体空间的普及,观众身不由己地陷入电视制造的“神话”之中。首先,通过传播广告和购物性节目,为受众提供消费信息并激发受众的消费欲望,引导受众进行商品消费;其次,电视通过对消费趣味、身份等的夸耀和想象,定制社会时尚消费“模板”,是现代生活方式的拟像,直接影响受众的生活方式和价值观念;再次,电视空间中也通过推介、传播西方消费文化和当代娱乐文化,构建全球文化的符号想像,并创造出新的意义认同空间。从一定意义上讲,电视媒介空间代表了现代消费文化的符号空间。
1994年,中国正式成为国际互联网国际大家庭中的一员,18年来,中国网络媒体迅速崛起,发展速度十分惊人。截止2011年底,网民规模达到 5.13亿,互联网普及率达到38.3%,手机网民规模达到3.56亿,网络规模稳居世界首位。[6]中国互联网成为社会转型中最具活力、最有影响的媒介形态之一。如新浪新闻的发展原则是“更快、更多、更精”,对于刚刚开始利用互联网获得新闻的网民来说,这种原则与他们的需求相吻合。新浪在一些重大突发事件上的反应速度提高了它的地位。渐渐地,许多人养成媒体阅读新浪新闻的习惯,在突发事件来临之时更是如此。[7]阅读网络新闻与电视新闻已形成两种不同媒介空间消费方式。对大多数网民而言,他们已远离电视而养成登陆自己喜欢的门户网站阅读新闻的日常消费习惯;传统的纸质媒介(书籍、报纸)和电子媒介(广播、电视、电影)为适应市场竞争也纷纷创办网站,尤其是报纸的网络版已成为纸质版实现品牌推广和服务增值的有效手段。网络空间的发展极大地改变了网民的生活方式和体验方式。值得注意的是,随着电视、网络媒介空间的发展,西方消费文化在中国广为传播,对受众的消费观念和价值取向影响深远,形成以功用主义为旨归,以满足享乐和个人情感诉求为目的的媒介消费文化观念。
需要注意的是,1990年代以来的大众媒介是一个多种力量相互制衡的空间,除消费文化外,国家意识形态、市场经济和文化传统等多方势力都作用于它,是在一个多元力量相互角逐的场中建构中国特色的社会空间。从大众媒介空间的主导力量来看,随着知识分子的边缘化,大众传媒失去精英意识的依托,大众迅速取代精英阶层的地位成为媒介空间的主导力量。但由于媒介时代的大众决定着政治、经济与文化介入的方式,作为主导群体的大众,一旦失去必要的媒介引导,在向西方现代化靠近的同时,就有可能媚俗化或沦为商业化的附庸,发生远离中国特色现代化道路的危险。因此,虽然市场资本逻辑在中国现代化进程中占据支配地位,但国家话语权力仍然要利用媒介空间,对西方现代化进行改造,而不是一味地模仿照搬,同时吸收中国儒家文化传统,构建具有本民族特色的大众传媒文化。
首先,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是形成良好的传媒文化发展态势的必要条件。政府通过政策,保护媒介产业的健康成长,挖掘中国文化的丰富资源和美学理念,融入到符合国际流行标准的形式中,并推动全球一体化发展。对内,引导大众建构民族—国家认同,对外,使“他者”充分接触该文化,进而认同、接受。安托尼·史密斯认为,“民族认同感的刻意建构,必定寄生于更深层次的集体认同感之上,这种认同感为居于一个特定地方的人们所共有,包括了‘感情和价值观,这是就某种连续感、共同的记忆和共同的命运感而言的。’”[8]其关键是重建人与人的伦理关系:“人类要由抽象的存在而成为具体的存在,兼不泯失其特殊性与普遍性,则舍将人与人之关系,化为互为真实存在之伦理关系,亦无道路。而中国社会之重建,其中最重要之事,亦即在对此传统思想中之伦理关系之价值,重新自觉的认取,而加以扩大推广,以使一切人与人之根本关系,皆成一意义之伦理关系。”[9]其次,知识分子也要发挥工具理性批判的作用,在儒家精神支撑下,开掘中国文化传统现代性的一面,同时沟通中西文化关系,这是形成符合媒介空间传媒特性的文化形态的重要保证。德国学者卜松山认为:“中国传统中有一些具有世界性价值的因素,能够成为全人类的共同的基本伦理的一部分。特别是‘仁’即人类之爱(人道主义)的思想,它既是天赋的条件,又需要后天的修养,以达到人与人、人与万物为一家的目的。”。[10]中国文化的“现代性”集中体现在儒家的“和谐”思想上:在自律个体的道德向度上,是以“仁”为核心的推己及人;在社会规范向度上,是以“礼”为中心的协调方式;在与自然相处的向度上,是以“天人合一”为精髓的非对抗方式;总体上,“儒教是一种关注人性和把正确的人际关系当作社会基础的哲学”。(尤姆)[11]这种以人为中心,注重人与万物之间的和谐精神,相对于西方的现代性来说,体现出真正具有“现代”的面向。“中国人在现代化的道路上给传统的‘天人合一’思想赋予新的内容,在现代的意义上对它作出与自然的和谐统一的新诠释,重新认识到其自身传统中的人道主义内容。”[12]
总之,1990年代以来媒介空间的建构将人们引入开放和多元的局面,引入一个符号化、幻想化的世界,让人们在商品的符号世界中幻想、消费、享受和审美。而西方传媒消费主义的负面影响也应引起我们的高度警惕。为此,中国政府的持续强势干预、大众民族一国家认同感的强化、媒介产业的全球化扩张、中国知识分子全球化意识的凸显、媒介文化与儒家文化的异质同构性等,都在为中国构建本民族特色的传媒文化铺垫一条光明之路。19世纪 20年代,梁漱溟预言:“在世界未来,将是中国文化的复兴。”。[13]
[1][澳]麦克·金.亚洲电视节目的国际化[A].张凤铸,主编.全球化与中国影视的命运[M].北京:北京广播学院出版社,2002.364-365.
[2]John Hartley.Uses of Television[M].London:Routledge,1999.218.
[3]Thompson,J.The Media and Modernity[M].Cambridge:Polity,1995.17.
[4]段祥贵,麦永雄.“模拟与仿真”理论与消费文化研究——兼论鲍德里亚的象征交换符号观[J].阜阳师范学院(社会科学版),2006,(2).
[5]潘知常,林玮.大众传媒与大众文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2.205-206.
[6]百度文库.2012年中国网民规模达 5.13亿互联网普及率为38.3%[EB/OL].(2012-03-16)[2015-06-10].http://wenku.baidu.com/view/244ff9e7524de518964b7d9e.html###.
[7]彭兰.中国网络媒体的第一个十年[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83-84.
[8][英]约翰·汤姆林森.全球化与文化[M].郭英剑,译.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146.
[9]唐君毅.中华人文与当今世界[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96.
[10][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0.33.
[11][美]拉里·A.萨默瓦,理查德·E.波特.跨文化传播(第四版)[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4.128.
[12][德]卜松山.与中国作跨文化对话[M].北京:中华书局,2000.35.
[13]梁漱溟.这个世界会好吗:梁漱溟晚年口述[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19.
【责任编辑:周 丹】
G206
A
1673-7725(2015)09-0109-05
2015-06-15
本文系2014年度国家社科基金项目“1990年代以来中国小说的‘空间转向’研究”(项目编号:14BZW121)的阶段性研究成果;2013年度河北师大社科博士基金项目“文学审美的‘第三空间’—1990年代以来的中国小说研究”(项目编号:S2013B01)的研究成果之一。
李静(1974-),女,河北石家庄人,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当代文学与思想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