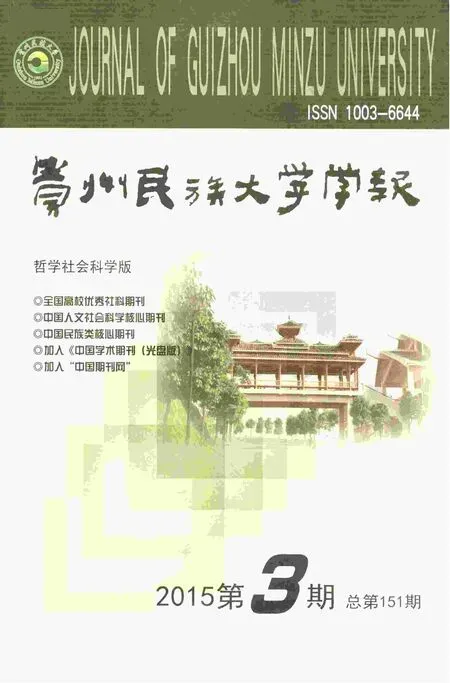蒲剧展演情境中的“神话主义”
——以山西稷山的《农祖后稷》为研究对象①
2015-03-20王志清
王志清
(重庆三峡学院(百安校区)文学院,重庆 404120)
神话学者杨利慧在梳理了“民俗主义”、“民俗化”、“传统化”等民俗学界诸多概念的知识谱系后创造性地使用了“神话主义”这一概念,“神话主义”即“用来指现当代社会中对神话的挪用和重新建构,神话被从其原本生存的社区日常生活的语境移入新的语境中,为不同的民众而展现,并被赋予新的功能和意义。将神话作为地区、族群或者国家的文化象征而对其进行商业性、政治性或文化性的整合运用是神话的常见形态。”[1]其当下正在进行“当代中国的神话传承——以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的考察为中心”这一国家社科基金课题的专项研究,从民俗学和神话学的视角对中国神话传统在当代遗产旅游和电子媒介领域中的利用与重构状况展开了细致的民族志研究,将神话主义植入了神话系统的整体脉络中予以整体观的审视,先后提出了神话主义的性质、神话主义的文本类型、神话主义的生产、神话主义的光晕等见解。
笔者结合个人调研后稷神话的田野实践,从戏剧这一杨利慧老师公开发表的相关成果中尚未涉及的领域提取典型案例,“嵌入性”①地思考《农祖后稷》的“民俗过程”②,进而对杨利慧所倡导的神话主义的研究予以呼应。山西稷山县的《农祖后稷》是编创人员融汇了后稷感生神话、后稷农业事功传说,并塑造了部分“于史无征”人物形象的一部蒲剧作品,是“融汇传统的文本、援引传统的文本、重铸传统的文本”[2]三者融为一炉的综合性文本。杨利慧在遗产旅游情境与电子媒介研究领域分析并归纳了神话主义的类型化特征,以及在不同领域“各归其类、各美其美”的特质,蒲剧展演情境中的神话主义亦呈现出“移位的神话母题”与“凸显的地域名称”两个特质。前者在当代电子媒介中比较突出,后者在遗产旅游情境中得到强调,而二者在蒲剧的展演情境中形成有机整体,建构了神话在戏剧领域特有的艺术光晕。
一、后稷感生神话与《农祖后稷》中移位的卵生母题
后稷被视为华夏农业文化的始祖,载录后稷事迹的《诗经》的《生民》、《史记》三家注等经典文献都提及后稷所居“邰”地。对比历史地理,于是后稷故里的认定问题就涉及到当下陕西的岐山县、杨凌区、武功县;山西的稷山县、闻喜县等地,以上地区构成了一个地理与文化意义上的“后稷文化圈”。学术界关于后稷故里的地望之争由来已久,“关中说”与“晋南说”各抒己见,历史学、文献学、考古学等各领域都有专题论述。当下后稷文化圈内的各地区都将后稷故里之名作为本地的重要文化资源予以关注,稷山县文化部门亦围绕着后稷文化进行了一系列“组织叙述”活动。所谓“组织叙述”是现代传播学中的一个重要概念,“组织”主要是指具有一致的利益和价值观念的人们共同体,其适用范围既可以指国际组织、国家、政党、群团等具有同一目标、行动纲领、制度、纪律准则等的具体“组织”,也可以指具有相同利益诉求和价值观念的群体,如社会的阶级、阶层、民族、教派、家族等。所谓“组织叙述”就是反映“组织”的目的、志趣、价值观、维护“组织”利益的话语表达形式。稷山县文化部门于2005年伊始,先后成立了后稷文化研究会;创办了全国唯一的后稷研究刊物——《后稷文化》;邀请作家张雅茜创作出版了《稷播丰登》一书;稷山县报社与县志办编辑出版了《稷人说稷》、《稷山风情》等书籍;申报并成功获批《后稷传说》为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
2010年3月28日开始,由稷山县蒲剧团演员为班底的《农祖后稷》先后在稷山、运城、太原等地公演。该部作品的创作过程历时两年,稷山县委、县政府数次邀请山西大学、山西科学院、陕西师范大学等单位的多位专家、教授来稷山举办后稷文化研讨会,在《史记》、《诗经》等大量史料的基础上数易其稿,群策群力地创作出了《农祖后稷》这一大型蒲剧作品。该剧由运城戏研所所长任国程任编剧,国家一级导演韩树荆任导演,由山西稷山县蒲剧团精心排练演出。自《农祖后稷》公演以来,山西日报、山西晚报、山西经济报、三晋都市报、运城日报、黄河晨报以及人民网、中新网等10余家新闻媒体对其进行了报道,根据媒体信息了解,“《农祖后稷》人物设计、服装道具、音乐设计、布景等均与剧情完美结合,充分展示了中华民族悠久的传统文化和历史文明,以及后稷故里的特色文化魅力,开启了中国农耕文化的又一扇窗口。据有关专家说,从演出效果来看,该剧集思想性、艺术性和观赏性于一体。观看演出的群众普遍反映,这是一台‘全新感受的视听盛宴’。”[3]
关于《农祖后稷》这一由远古神话改编创作为蒲剧作品的知识生产过程,从民俗学的视角可以理解为“民俗过程”,后稷感生神话遭遇了神话主义所强调的“神话的第二次生命”。《农祖后稷》共分九场,讲述的是在远古蛮荒时代,后稷在汾水河畔、稷王山下的小阳村神异卵生、随母亲姜嫄在小阳村历经磨难长大成人,与狩猎部落族人即传统势力进行斗争,选育“五谷”教民稼穑,终使华夏民族跨入农耕文明新时代的故事。其中将分别捍卫农耕与狩猎两类生计方式的人物作为矛盾斗争的两派,并且戏剧化地增加了狩猎代表猎虎与农耕代表后稷围绕着头人女儿蒋鹰发生的情感故事。剧中人物分别为姬弃(帝喾之子,即后稷,小生);姜嫄(帝喾元妃,姬弃之母,正旦);姜鹰(姬弃恋人,狩猎部落头人姜豹之女,性情刚烈,正义,小旦);羲和(天象专家,须生);姜豹(天神山狩猎部落头人,性情暴烈,头脑简单,二净);姜妻(彩旦);猎虎(姜豹亲随,欲娶姜鹰,奸巧诡诈,小丑);邰王(有邰国国君,大净或老生);帝尧(须生);巫师(姜豹巫师,杂);还有其他演员如当地四位老人、众猎户、男女青年、“天兵天将”、侍卫等人。
剧本将后稷感生神话中的姜嫄“履迹而生”、“三弃三收”等内容和情节进行淡化处理,突出采用了后稷感生神话中的卵生母题,卵生母题是构成戏剧冲突的一个重要因素,各类人物角色围绕后稷的神异出生方式展开了戏剧的序幕、发展、高潮与结局。笔者按照情节发展的时间顺序逐一列举卵生母题在《农祖后稷》中的出现情况,逐次递进的情节发展彰显了后稷神话的“民俗过程”。
在序幕部分交代了姜嫄生产肉球的前戏,第一场戏中长大成人的后稷进行农耕实验时遭遇当地猎户反对,争执过程中提及后稷的神异降生经历,抨击后稷尝试农耕与神异降生事件均为妖孽所为。第二场中姜妻面对后稷与姜鹰自由恋爱的状况,采用蒲剧中彩旦的自白演唱方式交代了当地人关于后稷神异降生情况的舆论评价以及本人的焦虑心态,该场戏还出现了猎虎欲娶姜鹰,安排手下冒充巫师指责后稷怪异出身的情节。第三场戏中通过后稷与姜鹰的对话,后稷知晓了自己神异降生的经历。第四场中姜嫄后稷母子对话,姜嫄将后稷为帝喾之子的身世问题全盘托出,后稷知晓了自己神异降生事件的来龙去脉。第九场戏中姜嫄向帝尧述说身世,帝尧认亲后惩罚了迫害后稷的猎虎等一干人,其中冒充巫师的那位老人在供词中交代了其当年作为姜嫄侍从向太后密报后稷神异卵生,从而遭致姜嫄被贬的事件。
如果单纯审视《农祖后稷》剧本内容本身,其非常符合苏联神话学家家叶·莫·梅列金斯基所倡导的文学领域内的“神话主义”,即“借助古典神话因素进行创作的现代文艺手法”[4],而对剧本的编创与舞台展演过程进行“嵌入性”地思考,整个知识生产过程更契合杨利慧所倡导的神话主义。
综观神话主义在该戏剧作品中呈现,凸显后稷卵生母题这一作法与编创作者的神话观密切相关。笔者询问编创作者之一的地方文化学者黄建中,其如何理解后稷感生神话中的卵生母题。黄建中拿出了其撰写的专著草稿《后稷大传》,列举第二节的神异诞生部分阐明自己的观点,其在文中列举了学术界解释后稷被弃原因的十七种说法予以评述,认为其中的“不哭说”和“怪胎说”两种说法比较合理,“根据现实生活中的生育情况分析,可以推测后稷出生时全身为一层肉膜所覆盖,出生后没有一般婴儿那样的啼哭,有点像肉球。和哪咤出生是一种情况,以为是个怪胎,只好弃之。这种情况从医学上讲,现在叫‘蒙头衣’。孩子出生后,身上为一层肉膜所包裹。古人迷信,认为是怪胎。其实只要撕开这个膜,孩子就出来了。哪咤出生后,他的父亲认为是妖怪,用宝剑挑开后才发现不是妖怪是个孩子。后稷很可能是这种情况,因为《生民》中讲,把后稷扔在冰池上后,有群鸟来临,可能是鸟儿啄破了肉膜,后稷才出来,然后哭了起来。《诗经》原文为,‘鸟乃去矣,后稷呱矣。’这时姜嫄一看真是个孩子,不是妖怪,这才赶忙抱回去了。如果真是这种情况,后稷出生时被困于蒙头衣中,好象一个肉球,呼吸困难,不能哭泣,形同假死,都可以讲通了,或许这才是最接近于历史真实的情况。”③黄建中评述各种说法后认为“怪胎说”可以用科学知识解释,比较可信。于是将卵生母题纳入了《农祖后稷》剧本。
黄建中编作为编创作者必然考虑观众因素,虽然后稷感生神话有《史记》等经典史籍白纸黑字的确切记载,其考虑到普通观众未必持有和学者一样清晰的神话观,未必能够充分理解神话与历史之间“主观真实与历史真实”的辩证关系。“履迹而生”、“三弃三收”等内容产生也会促使观众产生历史真实与神话真实孰真孰假的认识困惑,由此造成的麻烦可能会影响该部戏剧作品的演出效果。所以将普通观众不能用科学常识予以清楚解释的“履迹而生”、“三弃三收”等情节内容进行淡化,考虑到“卵生母题”能用科学常识迅速进行解释,于是在剧中将“卵生母题”予以彰显,作为戏剧的核心元素进行精心设计。《农祖后稷》剧本的知识生产过程亦是后稷感生神话在当代的一次“民俗过程”。
二、“凸显的地域名称”与《农祖后稷》呈现的宣传策略
稷山县政府近年以来一直将后稷文化作为当地文化名片予以推广,于是在政府倡导这一大背景下,当地或外地的相关人士创作或撰写了大量与后稷相关的各类文学作品及研究论文,其中主题先行、硬伤频现、学术规范欠缺的文章为数不少,稷山县文化部门严把质量关,建立了规范审核机制进行筛选。蒲剧剧本《农祖后稷》采用移位的卵生母题合理处理了神话与历史关系,这是其在诸多作品中脱颖而出的一个重要理由,而姜嫄之卵的所落之地——稷王山下的小阳村——后稷故里的定位也非常契合当地政府的“组织叙述”。
以“民俗过程”的视角来看,神话主义属于神话生命史中的“第二次生命”,杨利慧在梳理电子媒介中呈现的神话主义时强调了神话的顽强生命力现象,“诸多神话形象、神话母题和类型、反复出现的口语媒介、文字媒介和电子媒介中,形成了‘超媒介’形态的文化传统。通过新媒介的形成,观察这些既古老又年轻的神话主义现象,既可以看到根本性的人类观念的重复出现,也可以洞见当代大众文化生产和再生产的复杂图景。”[2]《农祖后稷》中移位的卵生母题与后稷降世之地都与此同理,《农祖后稷》与《史记》等历史文献比较,当下的卵生母题已经褪去了其族源神话的政治色彩,移位到一个区域文化特色浓郁的地方戏剧——蒲剧之中,衍变为一种历史资源和文学素材,其神话内蕴在新的附着载体和社会环境中焕发出新的生命力。卵生母题作为后稷感生神话中一个最小的情节元素,从已经尘封的历史文献里游离出来,既顽强地保持着独立特性,又通过不同的组合衍生出诸多奇幻的故事情节,其中姜嫄之卵所落之地——做为后稷故里的小阳村——参与建构着后稷神话的“第二次生命”。
神话主义在《农祖后稷》中即鲜明地体现在“凸显的地域名称”方面。“口承神话在流播的过程中日益地方化,是神话变异的一个规律。”[5]106-109“后稷文化圈”内各地区都将后稷神话、传说及其相关文化作为自己地区的“标志性文化”[6]予以积极宣传,不同地区的民间叙事、作家作品、地方文化学者著作、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等诸多文本中的叙事指向都凸显了地方性。民间叙事作品如岐山县的《珍珠泉传说》、武功县的《远志传说》、敦化县的《姜嫄河》、扶风县的《后稷教稼》、闻喜县的《稷王山与冰池村的来历》等风物传说,它们就将当地的周珍珠泉、姜嫄河、揉谷乡、稷王山、冰池村等真实地名列入其中,此举将《诗经》、《史记》中置于历史——时间序列的姜嫄与后稷等专名经过“再语境化”[7]256后,落实于具体的真实空间存在,置于风物传说的地方——空间系列。还有岐山县周公庙、稷山县稷王庙等文化遗产旅游景点都将具有地区倾向的作家作品作为底本供导游讲解,将后稷感生神话的姜嫄祈子之所、后稷被“三弃三收”之地与岐山县的周公庙、稷山县的小阳村等具体地点都进行了亦真亦幻的文学性建构。地方文化学者黄权中的《武功觅古揽胜》、黄建中的《后稷大传》等著作都对后稷的故里之名进行史料论证与积极宣扬。尤其是在当下积极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热潮中,各地展开了关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新一轮“地望之争”。武功县的《农业始祖后稷传说》于2009年被列为陕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闻喜县的《稷王传说》于2009年被列为山西省第二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而稷山县《稷王的传说》于2012年也被列入山西省第三批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扩展项目)。
各地都将后稷文化作为地方文化资源予以彰显,进而为各类文本打上了鲜明的地方烙印。“嵌入性”地思考各地参与的新一轮“地望之争”,这是一次整体性地进行了从后稷神话到后稷传说的“民俗过程”,其中稷山县的“组织叙述活动”不是采取专注于藏之名山式的静态遗产保护方式,而是采取“走出去”的策略,通过舞台展演等公之于众的途径进行稷山县为后稷故里的宣传。
从剧本初稿的创作与修改过程到邀请各路学者的献计献策;从晋剧团的精心排练到稷山县政府的专项资金支持,不同主体围绕着打造稷山文化品牌这一根本目标呈现出不同的面向,剧本作者努力塑造后稷丰满的人物形象、设计剧烈的情节冲突,追求稷山作为后稷故里的宣传效果。例如对感生神话中的“三弃三收”情节就进行了淡化处理,仅仅通过姜嫄的自白进行轻描淡写的交代,有意回避了闻喜县流传弥久的关于后稷落难之地的传说——《稷王山与冰池村的来历》。应邀而来的各地学者亦从自己熟悉的研究领域出发,在尊重史实的前提下打造“历史拼图”,对后稷神话进行重构与分析,为论证稷山为后稷故里而提供证据支持。地方政府则将后稷这一远古神话人物作为地方文化资源,出于经济效益、宣传等现实目的考虑,期望剧本创作人员将后稷这一神话人物与稷山县的文化品牌联系起来,将其符号化,赋予其特定意义,为扩大稷山县的知名度服务。不同利益群体的“组织叙述”活动促生了系统化的蒲剧《农祖后稷》,建构了后稷神话在稷山的“第二次生命”,上演了一幕“谁不说咱家乡好”的舞台演出。
综合而言,不同利益主体通过“组织叙述”活动,使后稷神话在当代社会得以挪用和重新建构。卵生母题贯穿于后稷神话的前世今生,正是通过它的有机串联从而历时性地形成了绵延的后稷神话生命史,“青山处处埋忠骨”的新一轮“地望之争”则共时性地丰富了后稷神话系统。共时性与历时性纵横交错,“移位的卵生母题”与“凸显的地域名称”交映生辉,蒲剧领域内的后稷神话以其特有的艺术光晕为神话主义的整体性研究提供了个案支撑,中华民族整个神话系统的“生命树”[8]添枝加叶,为神话学的理论大厦建构添加砖瓦之力。
注 释:
①社会学家翟学伟通过对“嵌入性”概念的历史性回顾,发现“嵌入性”即是“指一种社会行为的发生需要同一种社会背景、价值、脉络相配合,而不应把它看成一个可以独立运行的要素。”参见翟学伟:《中国社会中的日常权威——关系与权利的历史社会学研究》,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第2页。
②芬兰民俗学家劳里·杭柯(Lauri Honko)提出“民俗过程”(Folklore Process)的观点,“民俗过程”的概念即是一个整体性的理论框架。他把民俗的生命史细腻地划分为22个阶段,其中12个阶段属于民俗的“第一次生命”(First life)或者从属于它,剩下的10个组成了它的“第二次生命”(second life)。参见[芬兰]劳里·杭柯著户晓辉译《民俗过程中的文化身份和研究伦理》《民间文化论坛》2005年4期。
③根据笔者2010年9月访谈黄建中的田野笔记内容整理。
[1]杨利慧.遗产旅游情境中的神话主义——以导游词底本与导游的叙事表演为中心[J].民俗研究,2014,(1).
[2]杨利慧.当代中国电子媒介中的神话主义[J].云南师范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4,(4).
[3]杨明友 段杨慧.首部农耕文化历史剧《农祖后稷》问世[J].后稷文化,2010,(4).
[4]张碧.现代神话:从神话主义到新神话主义[J].求索,2010,(5).
[5]杨利慧.女娲的神话与信仰[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7.
[6]刘铁梁.“标志性文化统领式”民俗志的理论与实践[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05,(6).
[7]杨利慧.民间叙事的表演——以兄妹婚神话的口头表演为例,兼谈中国民间叙事研究的方法问题[A].参见吕微 安德明主编.民间叙事额多样性[C].北京:学苑出版社,2006.
[8]刘魁立.民间叙事的生命树——浙江当代“狗耕田”故事情节类型的形态结构分析[J].民族艺术,2001,(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