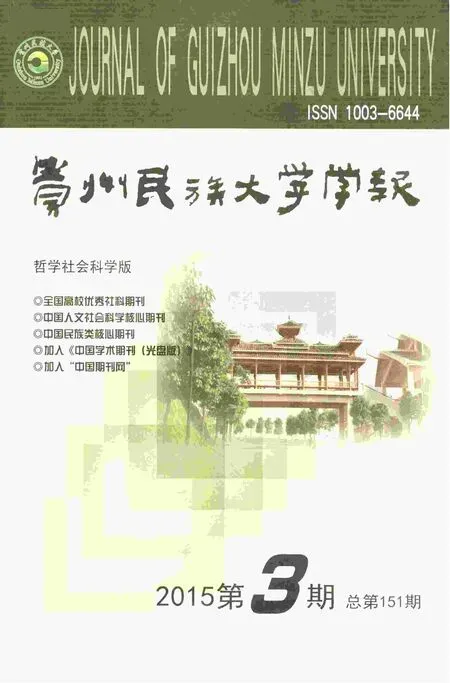民间文学的层积性研究①
2015-03-20王继英
王继英
(贵州民族大学文学院,贵州贵阳 550025)
层积性是地质中的一种历史积压现象,人们正是根据这种现象推断物体所经历的时间。而民间文学是口传作品,有很多作品经过若干代的流传,一直传承到现在。但是这些作品在流传的过程中,每经过一个时代都要被改变一下,而且每次改变都会在作品中留下一点印迹,透过这种历史印记的积累,我们大致可以推断出其作品从产生到形成所经历的时间。我们把这种研究方式称之为层积性研究。
在民间文学中,这种层积性在神话、传说、民间故事以及史诗中都有表现。为了节省篇幅,这里只举一首侗族的创世史诗和民间故事中的幻想故事为例。侗族这首创世史诗标题叫《人类的来源》,是一首讲述人类来源的史诗。据史诗描述:古时候有四个龟婆,在溪旁孵四个蛋,不料有三个蛋坏了,剩下一个好蛋孵出了侗族的第一个女性祖先——松桑。后来,这四个龟婆又在山岭孵四个蛋,不料又有三个蛋坏了,剩下一个好蛋孵出了侗族的第一个男性祖先——松恩。松桑松恩结合,生下十二个孩子,即龙、虎、蛇、雷、熊、猫、狐、猪、鸡、鸭、丈良、丈美。这十二个孩子中,除了丈良、丈美是人以外,其他都是动物或自然物。后来,这十二个孩子长大,都想当老大,于是争吵不休。为了解决争端,他们决定在山上比试本领,看谁的本领大,谁就当老大。在比试中,其他动物都依据各自的生理特点,施展了自己的本领,如龙翻江倒海,虎张牙舞爪,蛇伸缩蜷曲等。而丈良、丈美是人,他们的生理特点决定了他们不可能具有像其他动物那样的本领。但他们有计谋,能够哄骗动物们上当,然后放火烧山,把各种动物逼出共有的领地。因丈良、丈美在放火烧山时,伤害了其他动物,动物们个个义愤填膺,发誓要报复丈良、丈美。但是由谁来实施具体的报复行动?动物们想来想去,想到了雷(侗族称雷婆),它们认为雷婆的本领最大,由她报复丈良、丈美,定能达到目的。雷婆也不拒绝,她自恃本领高强,开始制定报复丈良、丈美的计划。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丈良、丈美也暗暗做了准备,他们从河里捞来青苔,铺在屋顶上,待雷婆下来站在屋顶上准备用火铲铲他们时,不料脚下一滑,摔倒在地,丈良、丈美上前把她捉住,关在铁笼子里。不过雷婆很狡猾,趁丈良不在时,悄悄跟丈美要了一瓢水喝,最后竟借着体力的猛增破笼而出。在逃回天上之前,她为了感激丈美的救命之恩,从嘴里拔下一颗牙瓣送给她,并要她赶快把这颗牙瓣种在地里,等牙瓣长出苗来,结出一个大葫芦,就躲在葫芦里,说完哗啦一声不见了。雷婆逃回天上以后,即发下洪水淹灭人类。丈良、丈美躲在丈美种出的葫芦里在水上漂着,等葫芦随水势漂到天上,丈良、丈美就冲出葫芦,与雷婆展开了殊死的斗争,最后终于在各种小动物的帮助下,慑服了雷婆。他们强迫雷婆造出七个太阳来把洪水晒干,丈良、丈美也因此回到了地上。由于太阳太多,丈良、丈美无法生活,于是他们又与长腰蜂商量,要他上天去帮砍掉五个太阳,留下两个,一个做太阳,一个做月亮。现在气候问题总算解决了,接下来是如何繁衍人类,因为经过洪水之后,人类只剩下丈良、丈美兄妹俩。如果他们不结婚,天下就没有人类了。所以兄妹俩心里很矛盾,结与不结,纠结了很久,最后经过滚磨占卜,才终于结为夫妻,生育人类。据说现在的人类都是丈良、丈美繁衍出来的。[1]P1-11
在我国南方,类似这样的史诗内容,其他民族也有,只是说法各不相同罢了,这说明我们选择侗族这首创世史诗作为了解其层积性的对象,是有一定的代表性的。从这首史诗的内容,我们可以看出,里面大约有四个历史印迹:一、兄妹结婚,二、龟婆孵蛋,三、十二兄弟争当老大,四、人雷大战。而且从历史上看,这四个历史印迹分属不同的历史时期,其中以兄妹结婚最早,它是人类刚刚脱离动物状态而进入人的状态时出现的。因为兄妹结婚本质上是古代人类血缘婚的反映,它是人类从动物式的杂婚迈向人类婚姻的第一步,这种婚姻的最大特点是排除辈份婚,而允许同辈的兄弟姐妹之间互婚。而龟婆孵蛋是在兄妹结婚之后出现的,这种现象的出现与氏族的分化有关。我们知道,在古代社会,氏族社会发展到一定的程度,就要发生分化,加上这时人们对血亲之间通婚的弊害已有了一定的认识,分化更是成为必然的要求。但是氏族分化以后,必须要有各自的标志,否则,人们无法在分化后的氏族之间作出区分。对于古代人来说,他们最初是用什么来作为氏族的标志?毫无疑问,是用人们在狩猎活动中经常接触的动物。美国印第安人把这些作为氏族标志的动物称之为图腾。侗族创世史诗中的四个龟婆就是以龟为氏族标志的四个女人,她们通过族外群婚生育了两个侗族最早的祖先——松桑和松恩。松桑、松恩结合,生下十二个孩子。这十二个孩子中,有十个是动物,两个是人。现在问题是:这十个动物孩子是真正的动物吗,还是如前所述的氏族图腾标志?我们的看法倾向于后者。因为侗族既然在氏族开始分化时,就有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现象,所以在后期出现与社会有关的动物,就不可能再是物我不分状态下的动物,而应该是以各种动物为标志的氏族或部落。从历史发展的过程看,这时的动物作为部落的标志可能性比较大。由于十二兄弟中的动物是各氏族或部落的标志,所以十二兄弟之间争当老大,就不可能是家庭的兄弟之争,而应该是古代各部落互相兼并的反映。而古代各部落互相兼并一般是发生在原始社会的晚期,这时由于生产力的提高,人类的生活资料开始出现剩余,加上这时各部落的势力强弱不一,于是开始出现了掠夺性的部落兼并战争,侗族创世史诗中十二兄弟争当老大就是这种兼并战争的反映。人雷大战是紧接着十二兄弟争当老大之后发生的。如果说,十二兄弟争当老大是部落兼并战争的反映,那么,人雷大战就是部族战争的反映。部族战争一般是建立在部落联盟的基础上,是各部落联合起来进行的,这种战争的规模非常之大,战争的场面也非常之惨烈。事实上,这种战争在侗族创世史诗《人类的来源》中也有体现,例如雷婆报复丈良、丈美是众动物兄弟推举出来的,这里就有部落联盟的影子。还有,丈良、丈美乘着葫芦上天去与雷婆展开殊死的斗争时,一路上收罗了很多求救的小动物,最后在这些小动物的帮助下,丈良、丈美战胜了雷婆,这里也是部落联盟的体现。据《列子·黄帝》中记载,“黄帝与炎帝战于阪泉之野”时,就曾“帅熊、罴、狼、豹、、虎为前驱,雕、鶡、鹰、鸢为旗帜”。[2]P84所以丈良、丈美与小动物们一起战胜雷婆,也应该属于这种情形。还有,与十二兄弟争当老大相比,丈良、丈美无论是活捉雷婆,还是雷婆发洪水淹灭人类,或者是丈良、丈美带着被救起的小动物们去与雷婆展开殊死的斗争,其战争规模都要大得多,也惨烈得多,战争的结果是人类被全部淹灭。对于古代人来说,要发生这样的战争,只有在部落联盟的斗争中才有可能出现。除了以上这些历史印迹以外,在侗族《人类的来源》中,还有兄妹结婚不合伦常道德观念的表现,有水灾和旱灾的发生,这些都是侗族《人类的来源》每次被改变时,留在作品中的历史印迹。
在侗族《人类的来源》中,这些历史印迹的构成情况是这样的:先是人类所经历过的血缘婚作为一种历史传闻,传到已有兄妹结婚不合伦常道德观念的时代。但是由于这个传闻的内容有悖于后来禁止血亲通婚的规定,以致人们很难接受它,但是人们又不能回避它,因为它涉及到了人类历史的源头。所以为了使这个历史传闻能被已有兄妹结婚不合伦常道德观念的人们所接受,他们只有以原始社会时期曾经发生过的各种历史事件为依据去对其进行重新解释。我们上述提到的以各种动植物为氏族的标志、各种动植物标志下的各部落之间互相开展兼并战争、各部落联盟之间爆发大战等历史印迹,就是作为解释的依据而累积在史诗中的,它们与作为解释对象的人类血缘婚结合在一起,显示了这首史诗的整个发展过程。在这个过程中,人类的血缘婚是史诗产生的开始,以后一直到氏族的分化,到族外群婚,到父系家庭的建立,到各部落互相兼并,到部族战争等,其中到部族战争时,已经是原始社会的末期。说明这首史诗从产生到形成经过了一个非常漫长的过程,它就是在这个漫长的形成过程中把原始社会时期各个历史阶段的历史印迹累积在里面的。
幻想故事是我们用以说明民间文学具有层积性的第二个例子。我们之所以要选择这类故事,主要是因为这类故事中有很多内容都与原始社会生活有关,然后又经过不断地改变,使它里面累积了很多明显的历史印迹。例如幻想故事中的人与异物结合的故事就属于这样的故事。在幻想故事中,人与异物结合一般有两种情况:一是异物变成美女嫁给贫穷善良的小伙子,如《田螺姑娘》和《龙女的故事》等;二是善良的姑娘嫁给异物,如《蛇郎》和《青蛙郎》等。过去人们在研究这类故事时,都认为是人们为了表现惩恶扬善的思想感情而创作的,其实从历史发展的角度看,这类故事的出现是有历史根源的。这个历史根源就是它来自古代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例如摩尔根在《古代社会》一书中介绍卡米拉罗依人的婚级改革时就说过:“鬣蜥氏的慕里原来只许和另一组三氏族中的布塔结婚,现在他可以和属于袋鼠氏的旁系姊妹玛塔结婚了。同样,鬣蜥氏的库比现在可以和袋鼠氏的旁系姊妹卡波塔结婚。鸸鹋氏的孔博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布塔结婚,鸸鹋氏的伊排现在可以和黑蛇氏的伊帕塔结婚。”[3]P56在这里,鬣蜥氏、袋鼠氏、鸸鹋氏、黑蛇氏,都是用不同动物标志的氏族。他们的婚姻是在两个不同动物标志的氏族之间进行,即鬣蜥氏的男女与袋鼠氏的男女之间通婚;鸸鹋氏的男女与黑蛇氏的男女之间通婚。我们把这种现象称之为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摩尔根这里介绍的虽然只是卡米拉罗依人的婚姻现象,其实这种现象普遍存在于古代世界各地各民族中,只不过由于世界各地各民族进入文明社会的时间先后不一,有的民族很早就把这种婚姻现象演变成了不同姓氏的族外婚,有的民族直到很晚还保留着这种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
由于古代普遍存在着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这就使人与异物结合的故事有了产生的依据。也就是说,在人与异物结合的幻想故事中,无论是动植物变成美女来嫁给贫穷善良的小伙子,还是善良的姑娘嫁给动植物,都不是凭空想象的,它是先有了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古代族外婚,然后在长期的误传中,把本来是不同动物标志下的氏族之间的男女通婚理解成了人与异物的通婚,人们就是依据这个理解去表达了各种与此有关的观念。从历史上看,人们最初是用人与异物的通婚去解释某民族的来源,民间文学理论界习惯把这种文学作品称之为婚姻神话。例如云南白族虎家族的《七妹嫁虎》和鄂温克族的《狐狸姑娘》就属于这样的神话。在这两个神话中,前者是讲述一位姑娘嫁给老虎,生出虎家族的后代[4]P167;后者是讲述狐狸姑娘嫁给猎人,生出鄂温克人[5]P227。后来,随着社会的发展,人类开始由母系社会转向父系社会,这时人类的生产力有了极大的提高,生产的产品开始出现剩余。但与此同时,人类的私有观念也在慢慢滋生,最后竟发展成了强烈的占有欲。这种强烈的占有欲表现在家庭中,就是财产的侵占;表现在社会上,就是部落与部落之间具有掠夺性的战争。这种侵占和掠夺性的战争频繁发生,就使社会陷入了极度的混乱,为了维护社会的秩序,人们开始在侵占和被侵占者之间、掠夺和被掠夺者之间产生了善和恶的观念。在人们看来,只有大量提倡善行,反对恶行,社会才能保持公平公正。但是这种提倡对于已经形成趋势的侵占和掠夺来说,显然是无济于事的,它只能作为一种愿望表现在人们的幻想里,于是原来在神话中用作解释某民族来源的那种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现在又成了人们在幻想中用以表现其惩恶扬善观念的依据。在这种幻想里,人们主要是把原来作为氏族标志的动植物变成一种可以变化的神物,然后通过它们与善良者结合,以帮助他们摆脱贫困或战胜压迫他们的邪恶。人们惩恶扬善的幻想故事就是这样创作出来的。
由于民间文学中人与异物结合的幻想故事,是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为依据创作出来的,这就使它成了一种层积性作品。在这种作品中,其历史印迹的累积是这样的:先是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变成一种人与异物结合的形式出现在作品中,然后人们用这种形式来表现惩恶扬善的观念,而惩恶扬善的观念一般是出现在私有观念大量产生时的原始社会晚期,所以这里就含有了两个重要的历史印迹。不但如此,有些人与异物结合的幻想故事还反映了阶级斗争,他的具体表现是:异物出于对贫穷善良者的同情,变成美女来嫁给他时,不料遭到了统治者的嫉妒,他们想方设法要剥夺贫穷善良者的幸福。于是异物变成的美女又运用各种神力与这些统治者展开了针锋相对的斗争。例如侗族的《郎付和三公主》就属于这样的幻想故事。在这个故事中,郎付是一个贫穷善良的樵夫,他的妻子是东海龙王三公主,郎付自从娶了龙王三公主后,过上了幸福的生活。但是好景不长,郎付的幸福生活遭到了曾到此游玩的皇帝的嫉妒,他为了达到占有龙女的目的,给郎付出了三道难题:一、要郎付给皇帝送去一百条鲤鱼,要条条两斤半重,不多一钱,不少一两;二、要郎付交出三百条红蛇,三百条绿蛇;三、要郎付以物质的形式交出一个非物质的东西“莫奈何”。最后,在龙女的帮助下,郎付一一对付过去了,并且还消灭了皇帝。[6]P46像这种有阶级斗争反映的内容,一般是人类进入阶级社会以后才出现的,它是人们在阶级社会中改变该幻想故事的思想内容时留下的历史印迹。此外,有些人与异物结合的幻想故事还反映了封建礼教,这种幻想故事最有代表性的是《白蛇传》。这个幻想故事是人们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为依据去表现青年男女对自由恋爱的追求时,不料遭到了以法海为代表的封建势力的迫害而产生的。说明这类幻想故事到封建社会时,还在被改变,以致其历史印迹不断累积下去。
从以上这两个例子我们可以看出,民间文学的层积性是非常明显的,特别是那些从古代流传下来的民间文学作品,其层积性就更加突出。但是民间文学作品的层积性要经过仔细的鉴别才能看出来,因为民间文学是口头创作、口头流传的,里面的层积性容易发生变形。这种变形一般有几种情况:一、历史时期的重组,例如侗族《人类的来源》中的兄妹结婚,这本来是人类最早发生的历史事件,但由于侗族人民是立足后来的社会观念(兄妹结婚不合伦常道德)去解释它的,结果把这种现象产生的时间不是往前推,而是往后移。二、由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常常把一些历史事件作变相描述,例如侗族《人类的来源》中的部落兼并战争和部族战争,这本来是非常激烈的斗争场面,但是由于后人不知道这是古代以动植物为标志的部落之间开展的战争,结果把它描述成了的人间游戏或人与自然的斗争。三、为了达到表现某种思想观念的目的,而对一些历史事实作了改造,例如幻想故事中人与异物的结合。在幻想故事中,人与异物的结合,本来是古代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的反映,但是由于人们对这一段历史的无知,加上又想用它来表现惩恶扬善的观念,于是把本来是以动植物为氏族标志的族外婚描述成了人与异物的结合。这些变形的历史印迹极容易给我们造成一种错觉,使我们对民间文学作品的内容产生错误的理解。所以为了弄清各民间文学作品的层积情况,我们必须先对里面的各种历史印迹进行仔细鉴别,然后再根据其出现的先后,去描述其在作品中的层积情况。
总之,民间文学的层积性研究是民间文学研究中一个重要方法。运用这种方法,不仅使我们看到民间文学产生和发展的过程,而且揭示了民间文学与历史的关系,说明民间文学不仅在创作过程中与历史发生了联系,而且在发展过程中也与历史发生了联系,只有这样来认识,我们才能真正看到民间文学的历史价值。
[1]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民间文学资料集[Z].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文学艺术研究室,1981.
[2]杨伯峻.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79.
[3]路易斯·亨利·摩尔根.古代社会[M].北京:商务印书馆,1983.
[4]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5]中国少数民族文学(下)[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
[6]杨通山等.侗族民间故事选[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