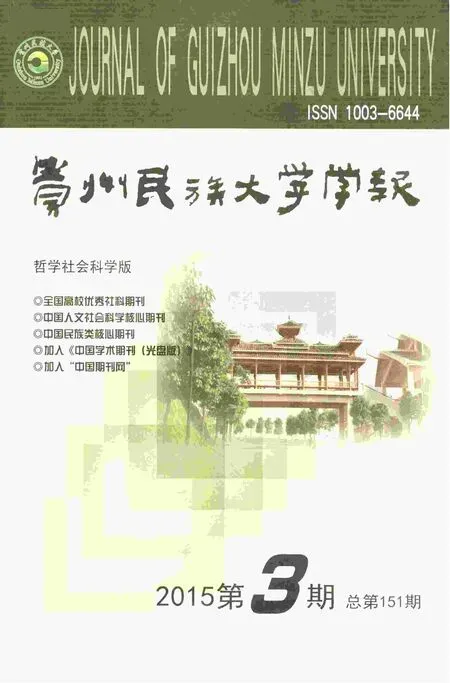近拒远交与远近无交:边缘族群三撬人婚姻圈的解体与困境①
2015-03-20余达忠
余达忠
(三明学院生态文化研究中心,福建三明 365004)
家庭是社会的最小组织单位,而家庭主要是通过两性婚姻建立起来的。在以一夫一妻制为主要两性关系的社会中,婚姻在繁衍人口、建构社会秩序、维护社会发展中发挥着至关重要的作用。更多的时候,在社会关系中,婚姻不仅仅是两性关系的契约,更是人们在社会关系中达成的一种文化契约,是社会关系和社会利益的重要部分,具有一种制度性的力量和影响力。婚姻本身就是一种制度形式。唐利平说:“婚姻的缔结不是生理本能的驱使,而是‘文化引诱的结果’,直接受到各种社会习俗、道德、规范和制度的影响和制约。”[1]作为一种社会关系和文化契约的婚姻,在承担人口生产使命的同时,更多地折射出各种社会力量、社会人群间的博弈,是社会中各种文化人群的文化表达形式。不同的社会,会形成不同的婚姻规范;不同的文化人群,会有不同的婚姻制度。对于婚姻起支配和决定作用的,主要不是两性关系中的“性”,而是两性所置身的社会中的各种关系,政治、经济、文化、地域、族群、阶层、宗族等。陈庆德、刘锋说:“婚姻是立于生产的基点,对人类性行为的制度规范。婚姻的制度性规范的中心事实或核心指向,是‘生育’这一‘性’的基础性功能。而文化的渗入,使性的功能不断地被建构出来,这样便产生了联姻机制与性经验机制在重叠中的差异。”[2]社会生活中的各种要素都会对人类的婚姻形态产生影响。对于人类婚姻的研究,既要着眼于社会现实中的各种社会关系和利益,又要着眼于人类的整个发展历程,重视人类发展进程中的婚姻变迁。
在一个具备最基本社会组织形态的社会中,选择和缔结什么样的婚姻,起决定和支配作用的,主要是人们结成的社会关系,是人们在社会中所进行的一种文化选择。这种在一定地域中构成的社会关系和文化选择,决定婚姻中必然存在一个有形或者无形的婚姻圈。就是说,从婚姻成为婚姻开始,人们就不是随心所欲地缔结婚姻,而必然有一定的规范和制约,这种婚姻规范和制约,就构成婚姻圈。婚姻圈既可以是一个地理空间,又更是一个文化空间,是各种社会关系的一种复杂形态。
一、边缘族群三撬人
三撬人(又写作三锹或三鍫)是生活于黔东南苗族侗族自治州黎平县、锦屏县交界区域的一个独特族群,计20余座村寨,6 000余人口,是20世纪80年代贵州省认定的23个待识别民族之一,承认其作为待识别族群的政治身份与文化身份。20世纪90年代,随着民族识别工作的强力推进,贵州省民族识别工作领导小组取消了三撬人待识别民族身份待遇,将之认定为苗族,少数三撬人根据意愿认定为侗族。
三撬人生活的黔湘桂交界地区,从来就是一个多族群互动地区。长期以来,苗族、侗族一直是这一区域的主体民族,而在苗族、侗族中,又存在许多不同的支系,尤其是苗族,虽然同属苗族中部方言区,但其中又分为不同的土语区,不同的土语区分属不同的支系,主要通过服饰和颜色区别,由此就构成了明清时代所谓之“百苗”——在明清时期的泛苗化中,侗族在更多的时候也被看成是“苗”之一种或几种。生活在这一区域的人数更少的三撬人,在历史上,也被称为三撬苗或锹里苗。光绪《靖州乡土志》卷2释:“苗里,俗名锹里。”[3]——锹里的核心区域在今湖南靖州三锹乡——而锹里正是三撬人历史上的居住区域。有清一代,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进入大发展时期,三撬人由锹里迁徙至清水江支流乌下江、八洋河流域的崇山峻岭深处,与汉族、苗族、侗族杂居,大部分三撬人独立立村建寨居住,少部分与汉族、苗族、侗族同村共寨居住。三撬人主要以山地耕种和林木砍伐为主要生产方式。最初,三撬人以佃种山场为生,渐渐通过现银购买和劳股折价等方式获得土地而得以安身立寨。相对于处于社会政治文化生活主流的汉族,相对于人数更多,居住时间更早,族群身份更明确的苗族、侗族,无论在政治上、文化上、还是经济上、地理区域上等,三撬人都属于是一个边缘族群,在各大族群的边缘取得生存地位。三撬人划入苗族或侗族后,其边缘性并没有改变,反而处于一种更边缘化状态。
三撬人有自己的祖源历史,是清初由于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而由湖南靖州锹里地区迁徙而来。三撬人有自己的语言“三撬话”。“三撬话”不同于苗语、侗语,是介于苗、侗语间的语言。苗语有三个方言区,即东部方言区、中部方言区和西部方言区,每个方言区又分为许多土语区,黔东南苗族均操中部方言区苗语,各土语区间的苗语可以互相交流,但三撬话与各土语区的苗语不能交流,与苗语的同源词汇约在30% ~40%,三撬人普遍会说当地苗族的方言土语,但当地苗族不会说三撬话。三撬话与当地侗语的同源词汇约在40~50%,三撬人普遍会说侗语,但侗族人不会说三撬话。长期以来,周边汉族、苗族、侗族一直将三撬人看作一个独立群体,三撬人自己也说,三撬人就是晓得三样话的人。①在黎平锦屏交界区域,汉、苗、侗、三撬是分得很清楚的族群概念。即便三撬人被认定为苗族(侗族)后,在族源、文化、语言、习俗、婚姻等诸多方面,仍然维护着对于三撬的认同,周边汉、苗、侗族群,依然一如故往地称之为三撬。
人类学家弗里德里克·巴斯为《族群与边界》一书作序时说:“一旦(把族群)定义为归属性和排他性的群体,族群单位的维持性本质便很清楚了:它取决于边界的维持。”维持族群的边界有地理边界,但更重要的是社会边界。他强调“维持族群间的联系不仅隐含了认同的标准和标志,而且隐含了允许文化差异存在的互动的架构”。“在族群边界存在的地方,他们更多地依赖微妙和特定的机制,主要与某些地位和组合不可行性有关。”[4]47,48,59著名台湾学者王明珂也认为:“族群由族群边界来维持:造成族群边界的是一群人主观上对他者的异己感(the scnse of otherness)以及对内部成员的根基性情感(primordial attachment)。”[5]P4三撬人作为一个族群,为自己划定了严格的族群边界。除前面强调的祖源历史、三撬话是其族群认同的重要标志外,其族群的重要边界还包括其婚姻制度和习俗。
二、近拒远交:三撬人的婚姻规范与婚姻圈
在婚姻上,三撬人实行严格的族群内婚配制。20世纪80年代初,根据相关民族政策,黎平县的三撬人积极向各级政府申请将之列为单独民族,经贵州省民族事务委员会和黔东南州人民政府同意,由黎平县牵头,成立了三撬人族属调查工作组。工作组于1982年5月,根据三鍫古歌描述,在黎平大稼乡啤嗟村(三撬人村落)的“翁九老”塘中,挖掘出一块立于乾隆已巳年(乾隆14年,公元1749年)的款约碑。碑文全文如下:
尝思朝廷有国法,鍫里有里规。兹余三鍫自先祖流离颠沛于斯,迄今已近百年。为铭志先祖之习俗,故三鍫各寨里长约集,宰生鸡而誓志,饮血酒以盟心,计照规约于后:
(一)务须击鼓同响,吹笙共鸣,同舟共济,痛痒相关,一家有事,阖里齐援。
(二)男女婚姻务须从父从母,原规结亲,不准扒亲赖亲,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来拌水,亦不准水去拌油,倘男不愿女罚银三十三,若女不愿男罚银六十六。
(三)倘遇外来之侮,阖里应齐心以击,尤对客家与苗家,更应合力以抗之。
恐嗣后无凭,刻有坐卧碑各一块,永远存照。
大清乾隆已巳年孟春榖旦日立②
这块款约碑包含了丰富的信息。一是生活于黎平锦屏交界区域的三撬人是从锹里地区迁徙而来的,在三撬人迁徙至黎平锦屏交界区域之前,就有了“三鍫”的称谓——“三鍫”是三撬人共同认同的文化符号——即三撬人作为一个文化上的人群共同体,在迁入黎平锦屏交界区域前就已经形成了。居住于黎平锦屏交界区域的“三鍫”是一个有着高度认同感的人群共同体,大家“击鼓同响,吹笙共鸣,同舟共济,痛痒相关,一家有事,阖里齐援”,结成一个整饬有序的群体一致对外。二是三撬人在清朝开国初期迁入黎平锦屏交界区域,迁入的原因是清水江下游区域的山地开发。由乾隆已巳年上溯一百年,正是清顺治时期。笔者在黎平最大的三撬人村落岑趸村田野调研时发现,最早落寨的吴姓先祖的碑文落款亦为顺治年间;其他三撬人村寨的大量的开寨传说也大都指向康、雍、乾时期,说明三撬人迁徙到黎平锦屏交界区域不是一次完成的,而是在一个较长的历史时段内完成的,而这个时期,正是清水江流域山地开发进入全面发展的时期。学者张应强对此论述:在这个时期,“整个清水江流域,尤其是下游沿江傍河地区,种粟栽杉、伐木放排、当江市易,已经成为主要的区域性社会经济活动,而许多相应的社会经济制度也就逐渐形成和发展起来”。“几乎所有的人群与村落都以不同的形式,不同程度地卷入到与木材采运有关的社会经济活动之中”。[6]P46,49三撬人正是在这个背景下落拓于黎平锦屏交界区域,从事山地耕种和林木栽种砍伐。三是三撬人一直实行严格的族群内婚配制度,在族群内以族姓为单位建立起婚姻圈。三撬人实行严格的同姓不婚制,婚姻严格限定在族群内不同姓氏的宗族间进行。“原规结亲”是三撬人婚姻中必须遵循的基本准则,“原规”即在三撬人族群内部不同宗姓间进行婚姻分配,“水各水,油各油,不准油来拌水,亦不准水去拌油”是对“原规”的最通俗明白的诠释,说得更直接些就是不准外族群的女子嫁入三撬,也不准三撬女子嫁给外族群男子,必须最大限度保证三撬人血统的纯正性。这是族群根基性认同的典型形式。四是三撬人的婚姻有一系列的规范和礼俗,“从父从母,原规结亲”是三撬人婚姻规范和礼俗中最普遍的形式。“从父从母”显示三撬人的婚姻普遍以父母之命,媒说之言为基础,在婚姻上的自由选择度比较低。在锹里地区发现的三锹人的碑文对此有明确表述。2008年5月,湖南大学教授胡彬彬与靖州三锹乡乡长王华,在三锹乡地笋村发现立于清道光21年的“群村永赖”款约碑,这是由锹里众寨共立,由州官州府颁布的款约碑,不仅是民间款约,而且有了法律地位。碑文对锹里的婚姻礼俗作了详细规范,强调婚姻要“由父母选择,凭媒约特聘”,反对“舅霸姑婚”,反对勒索财礼。其众寨所波及的范围,“西至今贵州天柱县远口镇、锦屏县劳坪、三江、铜鼓、敦寨;南及贵州隆里镇、高屯及黎平县黄柏,湖南通道县弄冲、播阳、临口、木脚;东部及湖南城步县长安营、绥宁东山、乐安、寨市、黄桑坪;北至湖南会同县广坪、太阳坪、地灵等,地域涵括了今天湘黔两省八县中的许多自然村(镇)落。这些自然村落虽有部分在清代中期后划入了贵州省的行政版图,或与靖州同省相邻的其他县域,但在苗族族内的领属关系上,却依然从属于‘锹里’。”[7]五是三撬人从来将自己与客家(汉)和苗(含侗族群)严格区分开来,认为自身是与苗、侗、汉不同的文化共同体。“倘遇外来之侮,阖里应齐心以击,尤对客家与苗家,更应合力以抗之。”这里暗示,在历史上,在与苗、侗、汉族群杂居互动中,由于各种社会利益关系,尤其是资源竞争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各族群间存在深深的过结和鸿沟。
从乾隆以来的二百多年,三撬人的婚姻圈一直得到较好维持,其男女婚配,基本上在三撬人族群内进行。三撬人与苗、侗、汉族群杂居,没有形成连片的居住区域,三撬村落间的空间距离,一般在7、8公里以上,两个或几个三撬村落挨邻的情况很少,三撬村落周边,多半是其他族群村落,还有许多三撬村落是族群孤岛。黎平县乌勒寨,位于黎平锦屏交界的乌下江北岸山麓,周边均为侗、苗、汉族群村寨,距最近的三撬村寨的距离都在20公里以上;美蒙坐落于黎平、锦屏、剑河三县交界的最高峰青山界主峰下,其西北面是青山界主峰,其东面、南面是汉族、苗族村落,距离最近的三撬村落九桃和小瑶光都在30公里上;由黎平的岑趸到锦屏的岑梧,距离达到百公里。三撬人居住的这种格局,就形成了三撬人婚姻中“近拒远交”的现象,即不与周边的苗、侗、汉族群村落发生婚姻联系,而选择与更远距离的三撬村落结亲。邓刚在三撬村落调研时也深有同感:“所谓‘近拒’就是指不与三锹人村落四周的苗寨、侗寨或汉寨通婚,‘远交’当然指的就是与相隔较远的三锹人村寨通婚。在访谈中,岑梧人告诉笔者,他们以前和高表、美蒙、九佑、乌山、乌勒这些村寨结亲较多。这些‘三锹人’村寨中,距离岑梧最近的九佑有约10公里远,而其他村寨则有数十公里之遥。对于这种‘近拒远交’通婚模式,除了听到‘只觉得我们锹家的好’这一关乎‘原生性情感’的解释外,从村民的其他说法中也能到隐约体会到经济和文化的差异也是岑梧村民只与‘三锹人’结亲的原因之一。”[8]三撬人这种“近拒远交”的婚姻模式,一直维持到新中国成立,划定民族成分后,才有所改变,但大部分三撬人,还是维护传统婚姻圈,以在族群内选择婚姻为主流。据成立于1981年的“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调查工作组”调查,1982年,岑趸全寨245对夫妻中,有226对夫妻是族群内婚姻,只有19对是与周边苗、侗族群婚配,且是20世纪60年代后发生的,大多是文革后期和改革开放初期发生的③。
三、市场化与三撬人婚姻圈的解体
学者王沪宁在研究村落家族文化时说:“资源总量制约着社会选择组织形式,一个社会没有足够的资源总量,它就只能选择较为古老和简单的组织形式。资源总量的多寡与生产力发展的水平密切相关:生产力发展水平高,社会的资源总量就多;生产力发展水平低,社会的资源总量就寡。”[9]P32三撬人的婚姻规范和婚姻圈,本质上是三撬人作为一个弱势族群在多族群互动环境中,为资源竞争而采取的一种被动策略。至少在清代中期,清水江中下游区域都还处于原始自然氏族向封建宗族转化的进程中,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整个社会的资源总量极为有限,社会的组织结构简单古朴,是以氏族或者宗族为基本架构组织起来的,各个氏族或者宗族间,因为同处一个共同的地理空间内,必然地要结成种种社会关系,但总体上,由于生产力发展水平不高的局限,整个社会始终呈现出一种封闭性和保守性,其社会化是一种低水平的社会化,这就决定生活于这一区域的各族群,必须凝聚为一个团结整饬的共同体,形成高度一致的族群认同,才能在社会资源竞争中获得基本的地位和话语权。香港学者陈志明说:“社会化的不同类型及强度都会引起对其类型不同的冲击及族群情感的强度。社会化的经历也包括生活在异族人中及生活在民族国家中的经历。”[4]P288族群认同既包含一种主观性的认识和想象,更包含客观性的社会化现实关系。作为这一区域的后来者和弱势者,三撬人处于族群互动中的最低层级,必须通过不断的妥协和隐忍才取得生存地位,而整个社会环境的封闭性和保守性,低层次的社会化,使得三撬人在放低生存底线的前提下,必须进一步强化其族群凝聚力和认同,由此获得一种平衡。就是说,在一个封闭和保守的社会里,如果生产力发展的水平不高,社会资源又相对匮乏,在族群互动中一般很难形成族群间的融合,反而会促进族群边界的生成和强化。维护族群边界,与其说是这种环境中各族群的一种文化保护和文化自觉,更不如是族群的一种生存策略。族群认同的工具论观点,在这里得到典型表现。三撬人在这个区域中要被容纳,除了生存上的不断妥协和隐忍,就是强化族群的存在感,让族群成为资源竞争环境中的一种内在力量,为在这一区域中的生存给出精神和文化上的支持与表达。布迪厄说:“婚姻策略的基本和直接职能是提供确保家族再生产,即劳动力再生产的手段”;婚姻关系也表现为“倾向于满足物质和象征利益并根据一定的经济和社会条件安排的策略的产物”。[10]P235-236二百年来,三撬人的婚姻圈一直能够维持下来,根本原因不在于三撬人的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有多么强烈,而在于在一个相对封闭和保守的社会环境中形成的社会关系,在于整个社会的社会化发育程度,而社会化发育程度的高低,则与社会生产力发展水平的高低和社会资源总量密切关联。
清代雍正开辟苗疆后,清水江下游地区得到开发,形成了以木材交易为主的市场,商品经济得到一定程度的发展,但整个社会始终还是处于封建商品经济的初级阶段,而控制商品市场的主要是汉族及汉化程度相对较高的沿江集镇,而远离沿江集镇的广大山区,那种实质上的封闭和保守并没有因为木材交易的出现而发生根本性改变。三撬人村寨合力订立款约碑,从另一个侧面说明,在封建商品经济冲击下,其族群认同和族群意识出现一定程度的动摇了,但这种动摇距离其婚姻圈的真正解体,还有相当大的距离。必须是三撬人直接置身于市场中,在高度社会化的市场中感受到竞争的压力和市场的诱惑,其婚姻圈才会发生根本性动摇并最终解体。
三撬人婚姻圈的解体终于在20世纪90年代中后期到来了。
从20世纪90年代开始,农村劳动力大量涌向城市,尤其是向沿海城市迁移的打工潮席卷全国,将大量世世代代生活于粘着于土地的农民吸引到城市,中国农村固守千年的那种封闭性和保守性,由于打工潮的引领,轰然间消解了,一个新的世界,充满依赖性的现代世界在中青年农民眼中打开来。他们一方面对现代生活充满一种新奇感,为五彩斑斓的世界所诱惑和鼓动;另一方面,他们又鲜明地感觉到与现代生活的巨大的差距,与“城市”、“城市人”的差距 ,有一种深刻的自卑感。这两方面既激发起他们对于新生活和未来的梦想,又产生一种深深的身份的焦虑——对于年轻的打工者,他们已经不适应那种传统的农耕生活,更不愿意再像父辈那样在土里讨生活,但他们也同时不属于城市,或者还不能融于城市和现代生活中。正是基于这样的现实,20世纪90年代后期,三撬人村寨中的中青年纷纷走出寨子,开始他们无尽的盲目而又目的明确的打工之旅。正是这股席卷整个农村的打工潮,导致正在动摇消解的三撬人的传统婚姻圈轰然坍塌。
从时代发展来看,现代社会是一个开放的体系,是一个市场化的社会。20世纪中后期开始的全球化进程,使整个世界呈现出一种从未有过的开放性,各个地区间,无论是中心区域还是边缘地区,都建立起一种紧密联系。著名学者吉登斯说:“全球化是一系列过程,它意味着相互依赖。对它最简单的定义就是:依赖性的增强。”[11]P4三撬人婚姻圈坍塌的最直接的表现就是女性不再固守传统观念与习俗,不再在三撬人村寨间选择配偶,而是在一个非常开放的社会体系内进行婚姻选择。现代社会的市场化,不但让这些一直生活于传统闭塞乡村的三撬女性有了价值的观念——打工的方式,让她们直接看到了通过自身劳动所创造和获得的价值,而且社会的开放性和市场化,还让她们发现了自身性别所蕴藏和体现出来的价值——她们可以通过婚姻获得和享受更好的生活,或者说,婚姻是她们改变自身命运的一种途径。越来越扩大开来的市场化,不但让三撬族群的青年女性们可以摆脱宗族对于她们身份的控制,而且为她们提供了一个从来没有的全新的生活平台。在这个平台中,她们发现了自身的性别价值,并且唤醒了她们作为人的本性——对于更好的生活的向往与追求。社会学家在研究20世纪70~80年代美国白人妇女的婚姻时,提出一种“上嫁”(marrying up)模式理论,即社会地位和收入较高的黑人男子娶社会地位较低的黑人女子,社会地位较低的白人女子满足于自身经济地位和消费水平的提高,而事业上成功的黑人男子则可以在社会上炫耀自己娶到白人女子。[12]P441在人类婚姻史上,女性婚姻中的“上嫁模式”一直存在。当三撬青年女性走出村寨后,她们成了最先不恪守婚姻传统的叛逆者,纷纷借着性别优势——实行自由婚姻后,女性在婚姻上的优势明显于男性——选择外寨、外族群优于本寨、本族群的男子为配偶。女性纷纷外嫁直接导致三撬人婚姻圈的解体,是三撬男性陷入婚姻困境的直接原因。在岑趸村,嫁在本寨的女性不到五分之一,近一两年很少有女性嫁在本寨了。美蒙村,已经有五六年没有女性嫁在本寨了。中仰村,80%以上的女性嫁给外寨外族群的男子。岑趸村干部吴汉仁做过统计,全国只有新疆、西藏、青海等五六个省市没有岑趸姑娘嫁去了。正是大批三撬女性外嫁,而外村寨、外族群女性又不愿意嫁予三撬村寨,因此就出现了三撬人婚姻生态的严重失衡。
四、远近无交:市场化中三撬人的婚姻困境
由于传统婚姻圈的解体,三撬人陷入亘古未有的婚姻困境中。
2014年8月,笔者调研了黎平锦屏两县重要的三撬人村落,着重考察三撬人的婚姻问题,发现其男性面临的婚姻挤压已经到了畸形地步,其婚姻生态的失衡已经成为严重社会问题。
大稼乡岑趸村是黎平县域最大的三撬人村寨。全村都是三撬人,计240户,1 017人,村寨内部交往语言为三撬话。近年来,村寨常年在外打工人数在700人左右,留守村寨人数约300人,多半为老人、小孩和不能外出的妇女。据笔者与村委会干部统计,全村26岁至50岁未有配偶的男性达78人,涉及65户,几乎每3户人家中,就有1户有超龄而未有配偶的现象,其中35岁以上未有配偶的成年男性达31人。全村分为潘、吴二姓,各姓又分为多个房族,而有些房族中,婚姻生态失衡尤为严重。潘贵龙房族计20户,74人,26岁以上至50岁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达18人,占总人口的24%,涉及16户家庭,其中30岁以上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达15人——这15人中,12人从未有过配偶,3人有过短暂婚史,40岁以上还未有配偶有4人。
河口乡中仰村是锦屏县域最大的三撬人村寨。全村312户,1 448人,分为陆、龙、潘、张几姓。全村26岁至55岁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计58人,其中,35岁以上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达31人。
美蒙村是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最高峰青山界下的三撬人村寨,全村100户,433人,分为张、杨、龙三姓。全村26岁至50岁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有21人。
九佑是一个自然寨,分为二个村民组,256人,26岁至50岁没有配偶成年男性19人,其中林昌忠家四个儿子,最小的1988年出生,均未有配偶。
三撬人的婚姻困境呈现出三种现象。一是三撬人的婚姻困境主要表现为成年男性找不到配偶,基本上没有女性找不到配偶的情况。用岑趸村主任吴汉生的话说,只要是女的,哪怕长得很丑,身体有残疾,也会有人娶。二是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的年龄主要集中在26岁至40岁之间。岑趸村78名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中,41岁以上为11人,年龄最大为48岁;中仰村58名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中,41岁以上10人,年龄最大为55岁,上50岁的3人中,1人为妻子去世多年,1人为婚后妻子跑了十余年;美蒙村21名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中,41岁以上只有1人;九佑寨19名没有配偶的成年男性中,41岁以上有4人,最大年龄48岁。由此看出,三撬人村落中出现的这种婚姻生态失衡,主要发生在近15年间,即从1998年以来。三是三撬人的婚姻困境是一种普遍现象。早先,三撬人近拒远交,只在三撬村落间进行婚姻选择,婚姻圈坍塌后,对于三撬男子而言,就成了远近无交,无论在就近村落,或者远方他乡,三撬男子都难以找到配偶。本人走访了大部分三撬人村寨,几乎都存在男子面临巨大的婚姻挤压。三撬人村落最集中的锦屏县河口乡和黎平县大稼乡领导,在接受我的采访时都说,在他们乡辖境,三撬村寨中的单身汉是最多的。黎平县人大文教卫委主任潘健康是三撬人,对大稼乡三撬村寨很熟悉,也深有同感,说看到那么多老单身汉,让人纠心,也很无奈。
现代社会是一个市场化的社会。而在当下这个开放的、社会化程度极高的市场化社会中,作为边缘族群、弱势族群、贫困族群的三撬人,显然在各方面都处于不利的地位,这是全球化和市场化时代表现出来的一种新的不平等现象。
导致三撬男性婚姻困境的最直接的原因是贫困。
有研究认为,经济因素对婚姻挤压的平衡作用仅体现在城市或发达地区,反而加剧了落后地区的婚姻挤压,中国婚姻愈加成为排斥贫困地区男性的社会制度问题。[13]贵州是全国最贫困的省份,而黔东南则是贵州的贫困地区,三撬人居住的村落,则又是黔东南州内最贫困的村落。大稼乡是黎平县最贫困的乡镇,岑趸是大稼乡最贫困的村寨。大稼乡书记吴涛告诉我,真实来说,大稼乡村民的年收入,就在2 000元,基本温饱都不能解决。锦屏县最贫困的乡镇是河口乡,而三撬人主要集中分布在河口乡。首先,三撬人的贫困与其所占有的资源总量密切关联。作为农业耕作族群,三撬村落的土地资源非常奇缺。岑趸村1 017人,田土面积441亩,人均0.43亩;中仰村1 448人,田土面积668亩,人均0.46亩;美蒙村433人,田土面积280亩,人均0.64亩。在笔者所调查的三撬人村寨中,人均田土面积最多的是岑梧,达0.8亩,其他村寨都在0.4~0.6亩间。三撬人全部居住在高海拔山区,其耕种的田亩都是塝上田、冲头田、冷水田、望天田、锈泥田,单位面积产量亩产700斤左右——700斤出田谷,大约产大米390斤。人均0.5亩田土,年均粮食不到200斤,不能维持基本温饱。其次,三撬人的贫困与其居住环境密切关联。三撬人居住区域属于中山峽谷地貌,山势陡峭,山体切割强烈,从谷底到山顶,海拔落差达700米以上,自然坡度均在40度以上,很不适宜人类居住开垦。春夏季节,暴雨山洪会造成程度不一的滑坡和泥石流,而冬季,北风冷雨又极易形成凝冻。岑趸村建筑在一道山岭顶端由几匹山汇聚形成的一个浅浅的山坳处,村委所在地水塘海拔960米,而两边列筑的人家,海拔高度则在1 000米以上。中仰村筑列在大坪山巅所形成的一个狭窄盆地上,海拔高度860米。美蒙村位于锦屏、黎平、剑河三县交界处最高峰青山界下,是距青山界主峰(海拔1 400米)最近的村寨,海拔高度980米。所有三撬人村寨,没有一座村寨居住在海拔700米以下。由于海拔高,环境恶劣,无论垦山还是耕作,都极端不利,其劳动力成本之高难以想象。这样恶劣且封闭的环境,显然不能吸引外面女性嫁进来。第三,交通也是造成三撬人贫困的重要因素。由于环境恶劣,山势高峻,山体破碎,坡度陡峭,落差巨大,三撬人居住区域的交通非常不便。一是居地偏远,三撬人几乎都居住在高山大谷中的高山之上,距离中心区域,尤其是距集镇路途遥远。岑趸村距乡政府所在地大稼10公里,中仰距乡政府河口陆地距离40公里,水上距离15公里,美蒙村距河口28公里,岑梧村距平略镇平略15公里。所有三撬人村寨,距县城都在60公里以上。二是路况差。黎平锦屏两县,有20余座三撬人村寨,没有一座三撬人村寨进村道路为水泥路或柏油路,都是狭窄陡峭的泥土路,一般车辆不能通行,遇上雨雪天气,则任何车辆都不能通行。三是居地高峻险窄,出行困难。由于三撬人居住地海拔高,坡度陡,无论是乘坐交通工具出行还是步行出行,都极为困难,就是与周边村寨交往,也困难重重,在村寨内串门,也要上坡下坎,很是吃力。在现代社会,交通在决定生活状况中,具有越来越关键的作用。
当整个区域都处在一个封闭的体系中的时候,三撬人的婚姻圈会一直维护下来,其男性自然不会陷入婚姻困境中。但当开放和市场化成为社会的一种生活方式和制度形式的时候,长期以来,由于种种原因一直处于边缘、弱势、贫困状态的三撬人,在市场竞争中显然处于不利地位,这种不利,会从另一方面加速其边缘化、孤立化,当然,其陷入婚姻困境也就似乎成为一种必然,一种不能回避和必须直面的现实。
一个高度社会化的开放社会,一个实行市场化的社会,应该为陷入婚姻困境的三撬人找到一条破除困境的出路,这是社会的正义和良心的要求,是时代的使命。
注 释:
①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调查工作组: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识别调查材料,黎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全宗号147号。
②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调查工作组: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识别调查材料,黎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全宗号147号。
③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调查工作组:黎平县三撬人族属识别调查材料,黎平县民族宗教事务局档案,全宗号147号。
[1]唐利平.人类学和社会学视野下的通婚圈研究[J].开放时代,2005,(2).
[2]陈庆德,刘锋.婚姻理论的建构与遮蔽[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6,(5).
[3]光绪《靖州乡土志》卷2.
[4]徐杰舜.族群与族群文化[A].哈尔滨:黑龙江人民出版社,2006.
[5]王明珂.华夏边缘:历史记忆与族群认同[M].杭州:浙江人民出版社,2013.
[6]张应强.木材之流动——清代清水江下游地区的市场、权利与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6.
[7]胡彬棚.靖州“群村永赖碑”考[J].民族研究,2009,(6).
[8]邓刚.“三锹人”与清水江中下游的山地开发——以黔东南锦屏县岑梧村为中心的考察[J].原生态文化学刊,2010,(1).
[9]王沪宁.当代中国村落家庭文化——对中国社会现代化的一项探索[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1.
[10][法]皮埃尔·布迪厄.实践感[M].蒋梓骅译.南京:译林出版社,2003.
[11][英]安东尼·吉登斯.全球时代的民族国家[M].南京:凤凰出版传媒集团、江苏人民出版社,2010.
[12]马戎.民族社会学——社会学的族群关系研究[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13]何生海.婚姻地域挤压的社会学分析[J].贵州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2,(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