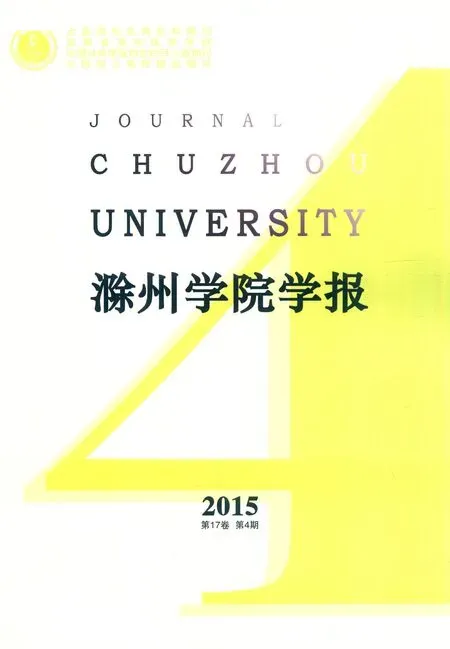“继承”与“发展”
——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2015-03-19孙四化
孙四化
“继承”与“发展”
——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研究
孙四化
随着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对“人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与保护,我国的“非遗”保护工作也取得了许多成就,同时也存在需要进一步研究与关注的问题。本文旨在就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过程中取得的成绩和存在的问题进行了阐述,分析了如何针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做出重点保护,在继承和发展的过程中,注重其“活的灵魂”的保存。
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活的灵魂;继承与发展
皖南地区泛指安徽省长江以南地区,包括现在的芜湖、宣城、马鞍山、铜陵、池州、徽州(黄山市)六市。皖南地区是安徽省重要的经济和文化中心,也是中国著名的鱼米之乡,它历史悠久,富饶发达、人杰地灵。悠久的历史孕育了灿烂的文化,时至今日,祖先留给皖南人民大量丰富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就是最好的例证。这些遗产在当地文化遗产保护的工作人员及相关部门努力下,得以传承和发展,但许多音乐种类仍然在逐渐失传。因此本文是在对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调查的基础上,对其在传承中积累的成功经验进行总结,对其存在的问题进行剖析和阐述,并提出了更加系统的保护措施。
一、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特点
与其他非物质文化遗产有所不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具有高度的精神性、对受众的依赖性和易逝性等特点。
(一)高度精神性
多数非物质文化遗产往往具有明确的、与众不同的实用性或者装饰性,但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加注重的是精神上的依赖与品格。在人创造音乐的过程中,体现出来的是人的精神及对于生活的向往,因而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可以被看作是精神产物,是人在生活中、在不同的场合表达自己情绪、精神内涵、不同于物质需求的精神层面的特殊的艺术形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人借以音乐来抒怀,跨越时间、空间、地域来表达自己的诉求。因此,在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中,要重视起高度精神性的特点。
(二)对受众的高度依赖性
文化的创造和生产是人的需要的体现,只有当一种文化得到多数人的认可和依赖,才能够生存并发展下来。这就体现了非物质文化遗产对于受众群体的依赖,而在这一特点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显得尤为突出。“供求”是文化得以延续的根本,就像一个理论只有适应社会的发展需要,被人们需要,才会存在一样。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存方式取决于社会受众的依赖程度,它需要根据受众的多少来调节自己的生存方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生存的最主要方式就是依靠演绎来获得经费,获得观众的喜爱,获得继承的生命力。如果受众过少,演出无人观看,就会直接影响到演出的数量和继承人的热忱。受众的高度依赖性,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赖以生存的根源。
(三)易逝性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艺术形态是易逝性极强的时间艺术,它稍纵即逝,极难保留。这便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的难点。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中,多数均是可见、可触的,只有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转瞬即逝、无形无踪的。[1]尽管现在科技发达了,可以使用影像影音来将其记录下来。但是,单纯的刻录影音并不能有效的延续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更不能够全面的将民间音乐的大量内容记录下来。所以,仅仅依靠现今的技术来记录影像,只能够算是建立档案,而非真正的“继承”和“发展”。
二、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概况
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历史悠久,不仅具有重要的历史价值,因其音乐的独特形态,更加具有与众不同的艺术价值。
(一)民间音乐
繁昌民歌,主要指流传于安徽省繁昌县境内的民间歌谣,它是安徽省政府首批省级非物质文化遗产。繁昌民歌曲调优美,内容丰富语言朴实生动。贵池民歌,以贵池罗城民歌为代表,既有江南风格,又有北方音乐特性,具有较高的艺术研究价值。徽州民歌,在历史上,徽州历来就是安徽乃至全国的文化重镇。悠久的历史造就了徽州独特的文化,徽州民歌是徽州文化的缩影,它品种多样,有号子、山歌、小调及佛教、道教歌曲等,其演唱的内容更是丰富多彩。
文南词,流行于安徽省东至县、宿松县等地古老的汉族戏曲剧种,被誉为中国戏曲的“活化石”。2006年,文南词被列为安徽省首批非物质文化遗产项目。2008年,文南词入选第二批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
青阳腔,形成于安徽省池州市青阳县,因青阳属池州府,故又称池州调或徽池雅调。2006年,青阳腔获准第一批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自明清开始便被誉为“徽池雅调”“天下时尚”,红遍全国,影响了多种戏曲的形成和发展。
贵池傩戏,是安徽贵池古老稀有的汉族戏曲剧种之一,贵池傩戏至今仍然保持着古朴粗犷的原始风貌,被誉为戏曲活化石,因此贵池地区被誉为“中国傩文化之乡”。除此之外,徽剧、目连戏、花鼓戏等皆是深受广大人民群众喜爱的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精粹。
民歌的主要操纵者是农民,戏曲音乐的受众也也大都在民间。近些年来,由于城市化进程的加快,年轻人多外出打工,留在农村的多为年过半百的老人,缺乏新一代有影响力的民间传承人,民间音乐,尤其是民歌的传唱已经岌岌可危,亟待保护。
(二)宗教音乐
皖南地区北有九华山,是我国四大佛教胜地之一;南有齐云山,则是四大道教胜地之一;中部有黄山,山上也有众多的道教遗迹。[2]因而宗教音乐在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占有重要的地位。宗教音乐中的佛曲、偈、真言、拜愿等形式曲调平缓,歌唱虔诚,伴奏清明。器乐以鼓为主,配以碰铃、木鱼、二胡等。此类宗教音乐并不是单一的音乐种类,而是结合了与宗教、文化息息相关的各种因素,还混合了地理环境和人文因素,所以完好的保护并发展皖南地区音乐的原始形态,不能够单独的靠着“保存”二字。应进行深入的研究,并充分认识保护对象的历史、现状和价值所在,解决为什么要保护和如何保护的途径与方法问题,否则将会使“非遗”保护工作流于一般。[3]
三、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现状
(一)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的经验成果
2006年,在以“保护为主、抢救第一、合理利用、传承发展”的工作方针指导下,安徽省委省政府正式部署并启动了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资源的普查工作。皖南地区的各级政府也纷纷行动起来,成立了专门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实行领导责任制,抽调专人办公,全面负责非物质文化遗产普查、保护、传承、发展工作。经过多年的艰辛努力,皖南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与发展取得了显著成绩。首先,入选国家级名录有就有当涂民歌、繁昌民歌、徽州民歌、池州傩戏、徽州目连戏、徽剧、青阳腔等,是安徽省国家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中数量最多的地区之一。其次,国家级、省级、市(区)级、县级的四级传承人保护体系逐渐形成,尤其是各级传承人的传帮带作用发挥的非常出色,这对于激发年轻人参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和保护起到了积极作用。其三,各地相继出台了很多地方性的保护法规。2014年,《安徽省非物质文化遗产条例》已经在安徽省第十二届人民代表大会常务委员会第十三次会议通过并施行。这些法律、法规的出台对整个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了保障的作用。其四,皖南地区的很多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成立了传承基地和传习所,这使得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承有了传承的场所和基地。
除此之外,安徽省群众艺术馆及民间艺人、高校研究所对于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也做出了极大的贡献。2014年安徽大学召开了全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论谈会,并召开了文化遗产宣讲活动,深受学生及社会欢迎。
(二)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中存在的问题
皖南地区沉淀的历史文化是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的动力源泉。尽管皖南地区政府及民间音乐工作者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与发展做出了诸多努力,但是由于在具体的实施和工作中存在各种因素,仍然是有着许多民间技艺在历史与时间的冲刷中渐渐失色。所以,在看到皖南地区取得的成绩时,也需要认清事实,总结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和发展中遇到的问题和经验教训,好在今后的工作中有的放矢,正视自己的不足。
1.政府重视程度不够。我国响应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关于“保护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号召,自2002年正式启动“抢救和保护中国人类口头和非物质遗产工程”,并相继出台了一系列关于加强文化遗产保护工作的文件,这些文件将对我国无比丰富的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起到政令性和实施性的保障。[4]皖南地区的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在列入党政重要工作日程的同时,更应该放在我省社会、经济、文化的整体规划上来,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能够作为皖南地区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重要工作而得到广泛的重视。近年来,由于资金不足与实践经验匮乏,在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工作上仍有所欠缺。所以在政府的重视程度上以及资金的投入中仍需加强。市、县级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中心、办公室、委员会等,均存在着人员紧缺、资金不足的情况,对于专职人员的培养及长效机制的建立也出现了工作的断层,这就导致了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工作的力度不足。
2.继承人及专业音乐人才的培养缺失。继承人的培养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的基础性工作。由于市场需求、经济发展、时尚元素冲击等诸多原因的影响,近年来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人的培养不尽人意,专业音乐人才就业前景不容乐观,因此也导致了戏曲人才的流失和继承发展的桎梏。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传播及传授形式一半都是靠口口相传才能够得以延续。但是这种民间的原始传承方式在当今快速发展的社会环境中,很难将其真正继承和发展起来。
3.传播途径阻塞。戏剧表演是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主要形式,可是现今快节奏的社会,慢节奏的戏剧表演已经很少出现在人们的视线当中了。说到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始终都移不开人和社会,然而随着社会的发展和人们对生活的追求的变换,传统的民间艺术的生存空间与传播途径已经被压缩的几近消失。
4.对青少年兴趣的培养不够重视。想要培养社会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就要培养人们对于民间音乐的爱好。而青少年的兴趣培养,不仅是人们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传承的根本方法,更是培养继承人的根本措施。然而在调查中我们发现,皖南地区在这一方面所作的努力显然不够。首先,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进课堂做的不到位,有的仅仅是一种走过场;其次,各处青少年宫和少年艺术馆中更多的是迎合大众品味的流行音乐,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几乎在这些场所中难觅身影;其三,电视广播是青少年非常喜爱的娱乐形式,然而,各个市县的电视广播节目中有关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宣传明显不足。
四、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继承与发展的建议
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作为人类所创造的有灵魂的非物质文明,是悠久历史中传承下来的“活的灵魂”。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这一特性,在继承与发展中需要充分考虑其在文化生态系统中的定位。基于对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继承与发展中的成果与不足,提出以下建议。
(一)“继承”——不断加强保护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1.政府主导——改善传承环境。地域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是政府所需要面对的冗长而繁重的工作,如何有效的管理,建立怎样的长效机制,都是需要以政府为主导来开展进行的。皖南地区政府需要根据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区域性、民间性、独特性的特点来制定因地制宜的相关政策、法规和科学可行的战略规划和实施计划,采取政府组织、部门分工协作的具体方式。[5]同时政府须组织整合财政分拨,加大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的资金投入,组织促进民间音乐团体进行表演宣传,加大宣传和保护力度。
2.以人为本——确立主体地位。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是依靠口口相传的形式来继承与发展的,这种既“看不见、摸不着”,又没有办法大众化传播的文化形态,是依靠人与人的接力来实现传承的。传承人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活的血液和生命力。[6]在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中,首先确立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并在对传承人地位的肯定的同时,给予帮助与保护,在社会的冲击和文化的交杂中保护传承人的主体地位,加强培养工作,才能够壮大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队伍。
3.寓教于乐——发挥高校优势。对于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来说,高校音乐专业的优势可见一斑。高校的师资力量是对于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提供充分指导的力量源泉,同时高校音乐专业的建设和长期高素质人才培养机制的建立,都是民间音乐艺术教育传承的最好保障。政府、民间音乐组织应该和高校形成良好的互动,三者团结在一起,以艺术实践的形式开展民间艺术的推广与宣传,寓教于乐,培养学生对于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兴趣与爱好,并通过对于师生教学相长的活动,推动地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
(二)“发展”——为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注入新血液
1.鼓励多元化——开辟新型道路。现今社会,国内的民间艺术接受了国外、时尚等诸多文化因素的冲击,这就考验了皖南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时代性。笔者认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生命力不应该仅仅驻足于“继承”,“发展”才是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在时代潮流中生存下来的硬道理。政府应主导文化多元化,引导民间艺术团体适应市场经济的需求,不只是将目光局限于传统的演绎形式。民间艺术团体可以和各地社区机构合作、成立地方民间艺术基金以及推出民间艺术次生产品等多元途径来发展民间艺术,发展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
2.开辟新模式——培养发展意识。在多层次的文化冲击中,要做到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继承与发展,就要有针对性的做出宣传政策。宣传过程中的重点,是要加强社会上每个人的主体意识,不只是将自己作为非物质文化遗产的保护者,更要把自己摆放在主人位置,形成有深度、有广度的宣传、保护新格局。依靠各种媒体来进行宣传,通过广播电视来培养人们对于民间艺术的兴趣,在公办的舞台演出中推出民间艺术的表演来推广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认知度,同时辅以网络媒体、民间庙会等多层次的形式来开展广泛的宣传工作。
五、结语
纵观当今社会,全球对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的重视并非一种偶然,它是人类从工业文明社会转向生态文明社会的信号。一方面是如何兼顾原样地保存和借助不同的艺术形式加以雕琢,符合当代人的审美品位,另一方面就是,借以不同的演绎方式,让更多的人通过不同的艺术形式来体味传统音乐文化的内在魅力,最终实现对优秀的传统民间音乐文化最为理性的保护与发展。
[1] 刘承华.“保存”与“生存”的双重使命——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特殊性[J].星海音乐学院学报,2008(4):3-4.
[2] 周显宝.人文地理学与皖南民间表演艺术的保护[J].文艺研究,2006(4):76-78.
[3] 樊祖荫. 对当前"非遗"保护工作的几点思考[J].音乐与表演(南艺学报),2015(1):1-2.
[4] 蓝雪霏.关于非物质音乐文化遗产"保护"的学术探讨[J].音乐研究,2008(2):6-9.
[5] 李爱真.徐州地区音乐类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的成果经验与存在问题探究[J].音乐创作,2011(4):155-157.
[6] 田青.鲁迅错了吗?--兼谈"非物质文化遗产"概念的内容[J].音乐研究,2006(1):6.
责任编辑:李应青
孙四化,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讲师,硕士,研究方向:作曲及技术理论(合肥 230011)。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科研究重点项目(SK2015A261);安徽大学艺术与传媒学院青年人才基金项目(2014yjrc01);安徽广播影视职业技术学院优秀青年人才基金项目(yrxm201307)
2015-03-11
J692;G122
A
1673-1794(2015)04-0068-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