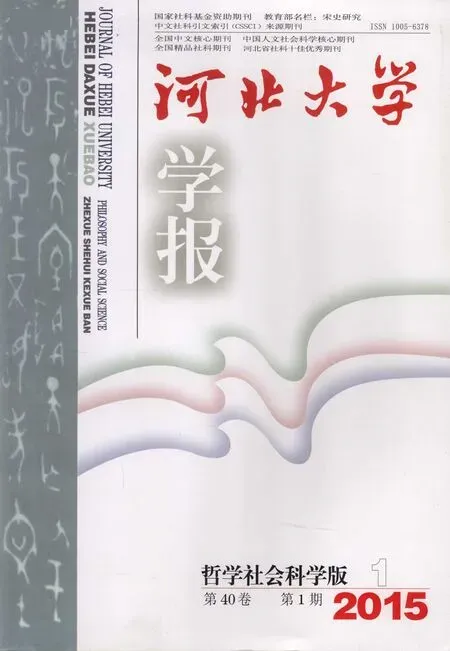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交际舞的散播与社会风尚嬗变
2015-03-19肖红松陈娜娜
肖红松,陈娜娜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2.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历史学研究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交际舞的散播与社会风尚嬗变
肖红松1,2,陈娜娜2
(1.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 北京 100875;2.河北大学 历史学院, 河北 保定 071002)
20世纪20年代,北平营业性舞场逐渐兴起,舞者队伍扩大,交际舞业“迅速极盛”。该行业在丰富城市娱乐生活的同时,却诱发了奢靡、享乐、纵欲等不良风气的蔓延,导致北平市政府一再禁舞。30年代初,北平舞业“盛极而衰”。北平的官方、民众、媒体在此间的诸般心态及举措反映了交际舞在该市散播历经波折,呈现出这一时期北平新旧观念并存、博弈的社会风貌,也说明北平的传统保守气质使其社会风尚的嬗变显现出相对迟缓的态势。从根本上说,该市的社会生态系统制约着其社会风尚变迁的深度与广度。
北平;交际舞;散播;禁舞;社会风尚
清末民初,交际舞蹈自西方国家传入中国,逐渐发展成为一项重要的城市娱乐活动。这一问题已为不少社会文化学者所关注,诸多相关成果相继问世①主要成果参见马军:《1948年:上海舞潮案——对一起民国女性集体暴力抗议事件的研究》,上海古籍出版社2005年版;《市政·舞厅——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年版;张艳:《激荡与融合:西方舞蹈在近代中国》,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左玉河:《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河北学刊》,2005年第5期;唐小兵:《象牙塔与百乐门——民国上海的大学生“禁舞”事件考述》,《开放时代》,2007年第3期;李从娜:《从〈北洋画报〉看民国时期都市交际舞业》,《中州学刊》,2010年第1期;杨阳、万妮娜:《民国时期舞女性质探析——以上海舞女为中心》,《社会科学论坛》,2011年第4期等。,但多聚焦于上海、天津等城市,对北平舞业的关注尚嫌不足。笔者以为对交际舞在北平的散播发展实有研究必要:一则,北平具有与津、沪等城市迥异的政治文化背景,该市交际舞业的发展亦有不同的轨迹。实际上,交际舞在进入北京后的很长时间内仅供上流社会消遣娱乐,直至国府迁都后,北平营业性舞场渐兴,舞者队伍扩大,该市的交际舞业才“迅速极盛”,但也随之陷入舆论漩涡,致使该市政府着手禁舞,北平舞业遂“盛极而衰”。从晚清以来的悄然蔓延到30年代初的激突式扩散与被禁,交际舞在北平之发展轨迹及其背后蕴藏地这座城市所独有的社会文化特征,均值得学者们探究、品味。二则,交际舞的散播牵动了北平社会风习的变迁,透过这一独特视角有助于我们了解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社会风貌,深化对转型时期近代中国社会的认识。本文旨在厘清北平交际舞业的整体发展脉络,解读舞业参与者与关注者之心态及应对,藉此揭示交际舞散播与北平社会风尚嬗变之间的关系。限于笔者水平有限,敬请各位专家指正。
一、北平“舞业之盛”
在1858年《天津条约》签订之后,北京东江米巷及附近地区成为西方各国使节及眷属、随员的聚居地。应娱乐社交之需而举办舞会是外国侨民延伸其西式生活习惯的自然之举,交际舞于北京社会的散播由此肇始。此外,斌椿、张德彝、郭嵩焘等曾在西方国家亲眼见识过交际舞的晚清官员们,通过文字或口述把相关见闻带回京城,为交际舞在北京上层社会的散播做了铺垫。1904年,清廷驻法外交官裕庚的女儿裕德龄、裕容龄为慈禧太后表演了交际舞[1]59-60,首次将交际舞带入宫廷。这时的交际舞仅在北京外侨、买办、少数皇族亲贵和涉外大臣的生活圈子中散播,几乎不为其他京城中人所知。民国初年,举办交际舞会开始成为北洋政府礼待外宾和与西方人联络感情的良方,每逢节日和重要宴会常有各种舞会举办,跳交际舞也逐渐成了上流人士的一种时髦娱乐。
1928年6月,国民政府迁往南京,各国驻华使馆人员及大量政商权贵随之南迁。受众的大量流失使当地交际舞业一度陷入危局。然而面对国府南迁所带来的冲击,交际舞的参与者(舞场经营者、舞客、舞女)与关注者(媒体、政府)皆采取了有利于自身发展的应对措施,促使“危局”变为“契机”。
其一,舞场经营者与媒体之间的互利互惠。国府南迁所致的交际舞受众的流失迫使舞场经营者降低“门槛”,以招徕更多顾客。如,京城首屈一指的高级饭店——北京大饭店曾登出广告:“本店每晚均有跳舞,每星期六晚备有特别晚宴并跳舞大会,不收入门券”[2]。王府井交通大饭店舞场也以“不售门票,添设消夜”[3]为号召吸引顾客。应该说,在舞场经营者打出“优惠”牌以维生意的过程中,报刊媒体是其所必需的宣传载体。与此同时,报刊除了能从舞场经营者那里赚取广告费外,还能用有关舞场、舞女的消息作为吸引读者的噱头,以增其销量。于是,舞场经营者和媒体之间相互扶持,共同促进了交际舞业盛势的到来。
其二,外侨消费实力犹存的同时,文人学者与青年学生逐渐成为舞客中的新主体。国都南迁后,北平的外侨人数除1929年略降之外,整体上呈逐年上升的趋势,到1937年达5000余人[4]统计表。由此推断,迁都后外侨仍是北平交际舞的主要参与者。因迁都而失去以往政治经济优势的北平更加注重维护其文化中心的地位,加大力度进行文教建设,这使得北平的文人学者、青年学生越聚越多。一方面,经过新文化运动洗礼的这些人,易于接受交际舞等西式娱乐;另一方面,在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两性社交尚不发达,正值青春年少的学生对接触异性有相当的诉求,而交际舞在满足这一诉求的同时又不似留连娼寮妓院那般显得不自爱。资料显示,有越来越多的青年学生活跃在北平各大舞场中,成为消费交际舞的新主力,但这也为交际舞业遭遇坎坷埋下了伏笔。
其三,舞女群体从无到有。1930年春,舞场业主们为发展营业起见,开始雇佣舞女表演舞艺、陪客跳舞、交际应酬,以招揽更多有消费能力的男性舞客[5]。北平舞女的来源有:外籍女青年——主要来自日本、朝鲜及俄国;外地女青年——主要来自上海、天津等“摩登”大都会;本市女青年——妓女、女招待及原属中上阶层但家道中落的女青年。舞女这一备受争议的群体在北平的出现并迅速扩大,既是该市舞业发展势盛的体现,又是刺激其舞业繁盛的重要诱因。
其四,北平政府对营业性舞场的态度暧昧。营业性舞场初兴时期,北平市政府出于繁荣市面和增加税收的考虑,并未对其予以严格管理。1931年5月,市府曾“通令各舞场限制时间至夜间二时为止,逾时不得延长”, 但不久后又“体恤商艰”,准许将跳舞时间延长到夜里三时,且对星期六日的跳舞时间不加限制[6]。在平市舞业日盛一日的情况下,市府出台了《舞场捐征收章程》[7],专门针对舞业征税。然而,该章程付诸实施后各舞场中拖欠捐税者屡见不鲜,市府却没有对拖欠者进行有效地惩治。北平官方对舞业的这种暧昧态度也助推了交际舞在北平社会的散播。
除迁都外,北平政局的另一变动值得关注。1930年春,商议恢复北平国都地位的扩大会议在北平酝酿,一度冷清的北平城复又冠盖云集。这多多少少刺激了各饭店开设跳舞场,招徕政商界人士。从1930年春到1931年5月,北平添设跳舞场的饭店已有30余家,几呈“有饭店皆舞场”之势[8]。
各群体针对时局的反应使交际舞在北平的散播有了突破性进展——从仅在高级饭店中附设舞场到“有饭店皆舞场”,舞场空间在迁都后的一两年之内发生爆发式扩张;从仅有上层社会人士参与到一般中产阶层乃至下层民众(主要指舞女)也参与其间,舞者队伍亦随舞场空间的扩张而呈现迅速扩充的态势。
二、消费舞女与舞女消费
文人学者、青年学子、外侨、富商、政客是北平舞场的主要消费者,舞女则是诱使这些消费者走进舞场的“金字招牌”。舞女们不仅可以吸引舞客花钱邀请她们伴舞,还可以带动舞客在舞场内进行各种消费,从而增加舞场的收益。而舞客在舞场里的消费情况是对舞女在舞场营业中所扮演之角色的最好诠释。对广大男舞客而言,最吸引人的消费莫过于通过跳舞与姿容秀丽、身材曼妙之舞女产生肢体接触和情欲交流。满场的情欲电波和暧昧气息在撩人心弦的乐曲中、令人目眩神迷的灯光下发酵、弥散,往往使舞客和看客们心荡神驰、沉醉不知归路。为制造令人意乱情迷的氛围,舞女们使尽浑身解数——摩登的妆扮,软软的腔调,动人的笑靥,流转的眼神,加上妩媚的舞姿,这一切都让男舞客们蠢蠢欲动,于是消费行为接踵而至。舞客到场跳舞,需以现金购买舞票,通常三张舞票售价一银元,每与舞女合跳一支舞,就给舞女一张票[9]。约三四分钟后一曲终了,舞客交给舞女的舞票即被消费完毕。若舞客舞兴未尽,还想与舞女共舞,则需另交舞票。
舞女在吸引舞客邀其伴舞的同时,还会极尽交际本事哄得舞客消费酒水或其他餐饮。其中当数香槟酒价格最高,每瓶七元到数十元不等。舞客若要招舞女陪坐,需开香槟酒,同时奉上至少五元以上的舞票[10]。报刊常以某舞客开香槟几瓶为噱头发布关于舞女的八卦消息,说明开香槟是一种彰显舞客身家阔绰、出手大方的举动,也是证明舞女本事、提高舞女身价的凭证。就舞场营业额而言,酒水进账往往与舞票收入持平或者远高于舞票收入之上,比如开明露天舞场每夜可售舞票400余元、水酒400余元;白宫舞场每夜可卖出舞票600多张,价洋200余元,水酒卖出400余元[11]。必须指出的是,不管是酒水进账还是舞票收入,舞女均功不可没。
舞客对舞女的消费并不限于舞场,还常见于舞场之外。如果舞客醉心于某位舞女,那么,他不仅乐于在舞场内为这位舞女花费舞票、酒水,还会在舞场外请她吃饭或进行其它娱乐消遣活动,再或者送她花篮、衣服、首饰等礼物,以讨得美人欢心。
除舞客对舞女的直接消费外,值得一提的是时人对刊发舞女消息之报刊的消费。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京社会风气相对保守,男女社交亦不公开。在这样的社会氛围中,舞女、女招待、女伶及妓女等特殊女性群体自然成为众人关注的焦点。报纸杂志争相刊登有关消息来吸引读者眼球,增加发行量。据查,当时报道舞女消息较为频繁的有《北洋画报》《北平晚报》和《晨报》等报刊。《北洋画报》常常将一些知名舞女的照片刊于报端,这些舞女均为姿色、 体态、舞技绝佳的“红舞星”,这使得无钱进入舞场、与舞女共舞的男人们可以通过观看舞女照片得到视觉上的享受。《北平晚报》的《广播无线电》专栏和《晨报》的《舞场消息》专栏,经常报道舞女生活的八卦新闻,没有作者署名,无人担负文责,舞女可以被任意书写塑造,使读者的猎奇心理和娱乐消遣心理藉此得到相当程度的满足。从受众群体的层面考虑,这些刊登舞女照片及消息之报刊的存在,使舞女的消费群体从有钱进入舞场消费的中上层人士扩展到了无钱入场消费但尚能购阅报刊的人们。
无论是舞场内的伴舞和酒水消费,还是舞场外的消遣和礼物消费;无论是实际接触到舞女的直接消费,还是对以舞女为内容的报刊的消费,其本质皆是在男权社会和男女社交不甚公开的背景下,男性满足自身对女性之诉求的途径,这类消费大可归入情色消费。舞女群体的兴起以及围绕舞女群体的情色消费,揭示了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社会男女社交的一种特殊状态,但也预示着该地的交际舞业将受到风化方面的严峻考验。
舞女在被消费的同时,也是北平社会中一股新的消费力量。如时文所述,“舞女乃一业,其收入以舞票为大宗。姿容秀丽之舞女,为一般舞客所欢迎者,彻宵达旦,无时或辍,每夜收入恒自二十元至三十元不等,此外月薪尚不计也。以舞女一夕之所入,实乡农半载年勤所不及,小学教员一月中所不能得者。……平庸之舞女,每夜收入恒在五元至十元间,每月计之,亦在二百元左右。”[12]由此可知,舞女群体收入不菲,使其有实力成为社会消费主体之一。对舞女而言,姿色是其吸引舞客的重要砝码,因此她们需要花费重金来妆扮自己。烫发染发,置办旗袍、洋装、皮大衣、高跟鞋、丝袜、丝手巾等服饰,购买口红、香水和各种首饰等,这些消费活动在舞女的日常支出和业余时间中均占很大比重。舞女的摩登装束不仅是吸引舞客的重要资本,也是各报刊八卦专栏的绝好佐料,如“时昌舞星高素贞,近由上海购置水晶色之舞裳一件,异常鲜艳。闻近日舞蹈时服此衣,舞家极为欢迎”[13],又如舞女萧美真“常着一素色长袍,白缎鞋,服装益趋‘少奶奶’化”[14]等等。
在消费舞女和舞女消费之间透露着北平社会两性文化和消费文化的新动向。在市风保守、两性之间尚缺乏正常交往渠道的情况下,既年轻貌美,又能与客搂抱跳舞、陪客欢乐的舞女自然而然地成为了北平不少青壮年男子寄托情欲的对象。通过消费舞女,他们对异性的渴望得到了一定程度的满足。“北平旧日风气素称朴素,晚近虽为军政商界少数人之骄奢淫逸,有所传染,然一般社会尚多保持旧观”[15],但舞女极尽所能诱惑舞客消费——买舞票、开香槟、购置衣饰相赠等,每一样都是钱花得越多越能彰显阔绰,越能博得舞女欢心。同时,对舞女自身而言,舞女这份职业使其有机会成为消费主体,为其追求华美衣饰和摩登生活提供了物质基础。总之,舞女群体的迅速扩大,推动了北平社会的情色消费、奢华消费和摩登消费。享乐、奢华、摩登的风气通过消费舞女和舞女消费在故都渐渐蔓延开来,这种风气与北平传统保守的气质发生冲撞。于是,交际舞被推进了舆论的漩涡,加之时局发生了变化,禁舞被北平市政府提上了日程。
三、日趋严峻的北平禁舞
交际舞这种男女相拥而舞的娱乐方式与“男女授受不亲”的中国传统伦理观念背道而驰,同时舞女群体的异军突起所带动的情色消费、奢华消费、摩登消费不仅有悖于北平古城的传统气质,而且有碍于政府对其“全国文教中心”形象的塑造。因此,历经短期顺境发展的北平交际舞业在1931年冬就遭遇了市府的第一条禁令,随后的局势日趋严峻,该市的交际舞业遂由盛转衰。
鉴于营业舞厅、舞女对北平社会风气和青年学子的不良影响,政教名流们大声疾呼查禁交际舞业。1930年5月,北京大学女子学院院长刘半农颁布《禁止女生入公共跳舞场布告》,严禁本校学生去公共舞场跳舞。1931年7月,中央监察委员张继在北平市长周大文的就职典礼上呼吁禁舞以维持风化[16]。此外,自然灾害和时局变化也是北平官方禁舞的促动因素。1931年夏季全国性大水灾和“九一八”事变促使河北省党务整理委员会呈请中央“禁止全国营业跳舞场以励风气”,并请北平市政府“查照转饬所属禁止”[17]。出于对以上因素的综合考虑,北平市府积极回应了河北所发出的禁舞号召,于1931年11月18日发布命令,查禁该市的华商舞场[18]。
对此,北平各华商舞场的经营者首先通过旅店同业公会向政府呈请“展期禁止三个月,以示体恤”[19]。此缓兵之法未果后,他们又利用禁令本身的漏洞——只禁华商舞场而不禁洋商舞场——想法取得外商庇佑,以求照旧营业。华盛顿舞场经理于连仲向社会局呈报歇业后,将该舞场转交美国人贾克经营。当警员前去调查时,贾克称他已将于连仲辞退,该房屋由法国人手中租来,整个舞场已与华商无关,所以该舞场得以继续公开营业。大华、柠曼两家舞场虽表示愿意停止舞业,专做咖啡、酒馆生意,但警员调查发现其接待的客人均为英、美、法、意等国军人,跳舞营业仍暗中进行。原由华商经营的正昌舞场虽在禁令压力下一度停业,但它很快由正昌面包房的法国人克拉砸司接办,恢复跳舞[20]。各舞场经营者的如此应对使北平当局陷入尴尬境地。市政府对华商和洋商的双重标准,导致此次禁舞在官方的“踌躇莫决”[21]中不了了之。
1933年7月,青年会会员阿拉勒开亚致函北平市府,称“北平之中国舞女,现为一希腊人名亚尼者及公安局职员王绍亭(译音)所保护,亚为三星舞场之业主,王为高夫舞场之股东,置政府禁令于不顾,诱惑男女青年学生演成不法情事……”[22]新任北平市长袁良以此为由头,开展了一系列严厉的禁舞行动。他针对1931年禁舞令姑息洋商舞场的弊端,于7月27日发布新禁舞令,明确规定“所有外人开设舞场应自八月五日起不得再有雇用中国舞女伴舞情事……倘敢故违,定行依法究办,决不姑宽。”[23]29日晚,市府派出警力在各舞场门前阻拦携中国女性的中国男舞客入场,此举引发了舞客与官方之间的冲突——“刘瑞华事件”发生。当晚,协和医院大夫刘瑞华(系卫生部长刘瑞恒之弟)及其友人携夫人到高夫舞场跳舞,被警察所拦阻。双方因言语不和发生冲突,警察将刘大夫打伤,并带往内一区审讯。经刘友人(前天津市长副官)和北平市第一区卫生事务所所长等人出面调停,此事和解。[24]这场风波过后,北平交际舞业的参与者仍在寻找新禁令的漏洞,即中国男舞客携其女性亲眷者、外国男舞客携外国女性者、外国男舞客携中国女性者都不在禁止之列。于是,在北平的中国舞女有的伪装成舞客的亲眷,有的则尽力结交外国人,仍操旧业。甚至有中国舞女更改国籍的传闻盛行一时。当然,也有中国舞女离平赴津,易地“货腰”;有的则堕入娼门,直接“卖肉”;还有的公然做起社会名流的小妾或情人[25]。总之,新的禁舞令亦收效不佳。
鉴于此,袁良在1933年8月12日再下禁令,规定各舞场在解雇华籍舞女后,不得另雇西籍舞女替代;除1912年9月以前由外商开设的舞场仍准予营业外,不得再开设新舞场;准予营业的外商舞场也须做到“不售舞票,不雇舞女,仅有欧美人士自携眷属或伴侣于酒阑饭后借跳舞为消遣,如华人携伴跳舞即当劝阻”,不得转以跳舞为营业[26]。这条禁令不仅加大了禁舞的力度,而且明确了对外商所经营舞场的处理办法,以示市府彻底禁舞之意。此令着实取得了一定成效:北平许多舞女远赴外地谋生——“红玫瑰、梁桂珍等三十五人赴香港;丁爱琴、赵凤舞等二十八人赴大连;王宝莲、李爱莲、张莉莉等五人赴天津,还有赴上海、广州者,共计七十人左右”[27];营业性舞场数量大减,只有三星、中西、电报三家符合官方“准予照旧营业”的条件,且不得雇舞女、售舞票。
从1931年11月的禁舞令到1933年7、8月的禁舞令,官方禁舞的态度愈发明确、严厉,北平交际舞业的声势也逐渐转弱。尽管如此,仍有一些从业者心有不甘,精心应对。据报载,洋商舞场仍照常营业且生涯鼎盛,并有新兴者如雨后春笋般相继而起[28]。三星、高夫各处时常有失业舞女到场参观,寻客伴舞,暗营舞业。警察一再告诫,其不仅置若罔闻,还大张鼓乐,任意跳舞[29]。此外,进舞场消费的中国舞客大有人在,一些舞场经营者却没有按照“如华人携伴跳舞即当劝阻”的禁令要求,加以劝阻。对此,北平市府再次强势出击,于11月18日派人赴各舞场突击检查,逮捕了大批中国舞女和舞客[29]。这一逮捕行动引起了广泛的社会关注。袁良市长对此事件的处置则表达了市府强硬的态度:一方面,他对误捕的舞客和良家女子并未致歉;另一方面,他对被捕者中的妓女从轻发落,对舞女却严格处罚、绝不姑息,所捕高丽舞女亦不例外[30]。
当局如此强势的举措和态度一度引发舞客的强烈不满。在大捕舞女事件中被捕的一位舞客——北大英文系教授蒯淑萍女士因不堪无辜受辱,在各大报刊上刊登启示,斥责市长袁良此举践踏人权,警告其必须正式道歉,否则将诉诸法律手段予以解决[31]。如此直接针对市长且言辞激烈的启示引起了媒体和舆论界的高度关注,但对峙双方最终和解。和解内幕,我们不得而知,但可以确认的是,风波平息后北平媒体对舞业的报道频率大幅下降。至1933年底,原本热衷报道各种舞讯的《晨报》《北平晚报》等报刊均鲜见与舞业相关的报道。通过对禁令的强化以及对政府强制力的使用,北平当局在相当程度上震慑住了舞场经营者,袁良政府的禁舞行动终见成效。援引北平市公安局对该市禁舞行动的总结来说,“本年(1933年,笔者注)内各舞场均停止营业”[32]15-16。
四、从交际舞业命运看北平社会风尚的嬗变
20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北平新旧势力并存。对于交际舞这一新式娱乐活动,有外侨、政商人士、新派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等趋洋趋新者乐在其中,也有守旧文人和政教名流呼吁禁止。纵观交际舞在北平的兴衰历程以及相关舆论的变化,可以看出北平社会风尚由传统、保守向现代、开放的转变。但通过与津、沪交际舞业的横向比较,又能看出其社会风尚的变迁相对迟缓。
20世纪二三十年代,北平的舞女群体随营业性舞场的兴起而涌现。在消费舞女和舞女消费之间,北平社会中根深蒂固的传统礼教——“男女授受不亲”等观念受到冲击,纵情声色、奢靡浪费、追逐“摩登”的社会风气日渐蔓延。舞女因此成了卫道士们讽刺、批判的对象。有的说她们“光着胳膊露着腿,绝像一只毛羽未全的鸡”[33];有的认为她们将金钱视为“高于一切的主宰者”[34]255,是从事银洋与肉体交易的人[35]10;有的视之为消磨青年意志,耗费青年资财,诱使青年荒废时光、精神、学业的祸水[36];还有的认为跳舞与北平“全国文化中心”的形象不符,不利于吸引学子前来求学,进而导致该市教育业的衰落[15]。这些卫道者从不同角度针砭舞女,成为呼吁市府禁舞的主力。虽然也有人对舞女群体做出较客观的分析,对其抱以同情态度或愿意为之宣传推广,但这种持中立或同情态度的人士尚在少数。总体而言,在舞女群体初兴并迅速扩大时,对该群体的贬斥之声远大于中立或同情之声。
北平舆论的转变也值得关注。舞业初兴时,舞场营业者和报刊经营者在逐利观念的驱使下频繁刊发舞业讯息——舞场广告、舞女消息、舞星玉照等铺天盖地,喧嚣尘上。市政府厉行禁舞后,这些宣传舞女的声音在权力的压制下迅速消尽。但随着官方禁舞行动的深入,社会舆论对北平交际舞业的关注点悄然改变——从集中关注跳舞、舞女对社会风化的影响逐渐变为对跳舞活动与禁舞行动的反思、争论。而这些争论又使时人对北平交际舞业和交际舞本身的认识渐趋深入、理性,这一点体现在舆论界对舞女同情态度的增强以及对官方禁舞行为失当的指责上。舆论焦点的转换及其内容的理性化是交际舞在北平社会深入发展的体现,而公众对这一带有异质文化特征的新事物的接纳与合理认识也是北平社会风尚从传统、保守转向现代、开放的一种表征。
然而,与同期内交际舞在津、沪等沿海开埠城市的发展情况相比,北平交际舞的散播显示了该市社会风尚变迁行进迟缓。首先,就交际舞发展的整体情况而言,北平舞业比津沪舞业起步晚、规模小、兴盛期短暂。有研究表明,上海首家营业性舞厅于20世纪初期就已出现[37]48,继上海之后,跳舞之风才在天津、北京等地开始流行[38]111。当1927年天津发生禁舞风波之时,北平舞业的兴盛时代尚未来临,北平舞女群体还有相当部分聘自津沪。从规模上讲,在公会组织方面,上海有专门的舞业公会作为舞业经营者和官方沟通的桥梁,而北平舞业则没有类似的同业组织,斡旋于舞场经营者和官方之间的是北平旅店同业公会;在宣传媒介方面,上海有《跳舞日报》、《影舞日报》等专门报道各种舞讯的报刊,北平则没有此类专门刊物,仅《北洋画报》及《晨报》的《舞场消息》专栏、《北平晚报》的《广播无线电》专栏等报道舞业讯息频繁些,但很快随市府禁舞而撤销。从兴盛期的持续时间上讲,北平的交际舞业从1920年代末的初兴到1933年底的“各舞场均停止营业”[32]16,历时仅四五年时间。尽管1931年河北省对国民党中央的禁舞呈请针对的是全国的营业性跳舞场,但在北平禁舞逐步强化之时,津沪舞业却繁盛依旧。如上所述,袁良政府禁舞的结果之一就是北平的众舞女纷纷转赴津沪等地,重操旧业。
另外,比较1931-1933年的北平禁舞与1927年的天津禁舞风波,发现两者最大的不同在于有无官方力量的介入。 1927年,天津福禄林饭店增设跳舞场,其他饭店亦尾随增设,跳舞之风充溢津门。当地名流以“伤风败俗”为由函请当局取缔,遭到拒绝后又以“破坏礼教”为由提起诉讼,仍被驳回。同时,禁舞派和拥舞派还在报刊上开展了两个多月的辩论。但此番禁舞风波终未取得实质性结果,津门舞风依旧强劲。相比之下,北平禁舞除了社会舆论的呼吁外,官方力量的强势介入是其成功的有力保证。禁舞令的一再强化、警力的动用以及市长的强硬态度使舞业参与者们最终屈服,北平交际舞业的繁盛仅是昙花一现。官方力量介入的成功与否,原因多元,城市的底蕴和民风是其中之一,北平传统、保守的风气为官方力量的成功介入提供了适宜的社会生态环境;官方力量对这种故有社会风气的维护又使交际舞在北平社会的散播阻碍重重。因此,尽管北平在西俗东渐的大背景下,呈现出新旧杂陈的社会面貌,但是在从传统、保守到现代、开放的社会风尚变迁之路上,它的脚步必然迟缓。
结 语
交际舞在西俗东渐的大背景下进入北京,又因时局变化由“迅速极盛”到“盛极而衰”。在此过程中,交际舞业对奢靡、享乐、纵欲等不良风气的带动使市政府明令禁舞。而伴随禁舞之深入所发生的社会舆论的转变则表明,民众对交际舞的认知逐步深入、理性。民众认识的深化是交际舞深入北平社会的体现,也体现了该市社会风尚由传统、保守向现代、开放的有限嬗变;而且与同期津、沪等城市的交际舞业状况相比,北平交际舞业的曲折命运显示出该市社会风尚的嬗变进程又是相对缓慢的。
纵观20世纪二三十年代交际舞在北平社会的发展历程,笔者以为交际舞这一有悖于中国传统“风化”的外来事物在文化底蕴深厚的北平社会频遇阻力,反映了在西方文化大量涌入、社会变革势不可挡的时代背景下,故都社会新旧观念激烈博弈,社会风尚发生了有限的迟缓的转变。从根本上说,是北平特有的社会生态系统制约着该地社会风尚嬗变的深度与广度。
[1]德龄.清宫二年记[M].顾秋心,译.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6.
[2]北京大饭店(广告)[N].星期三创刊号,1929-10-16.
[3]交通跳舞场今晚开幕[N].北平:新晨报,1930-04-01.
[4]北平民社.北平指南[M].北平:北平民社,1929.
[5]交通舞场增聘妙女[N].北平:新晨报,1930-04-21.
[6]跳舞夜内展至三时,星期日不限制[N].北平:晨报,1931-05-11.
[7]舞场捐章程公布[N].北平:晨报,1931-05-15.
[8]平市百影(三)跳舞场上[N].北平:导报,1930-11-14;北平舞女达五百余人[N].北平:益世报,1931-05-01.
[9]两年来上海之浪漫跳舞场(二)[N].北平:晨报,1931-04-02.
[10]金羽人.楼头观舞记[J].北洋画报,1933(20):969.
[11]北平舞场调查[N].大公报,1931-07-23.
[12]北平舞女生活[N].大公报,1933-02-03.
[13]舞场消息[N].北平:晨报,1931-05-17.
[14]广播无线电[N].北平晚报,1935-01-21.
[15]大灾中北平跳舞场问题[N].大公报,1931-09-03.
[16]北平市长周大文昨宣言[N].北平白话报,1931-07-01.
[17]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 准内政部咨以奉论禁止全国营业跳舞场请饬属禁止等因仰核议具复由1931-10-23[J].北平市政公报,(1931)119.
[18]北平市政府.函公安局 奉令禁止舞场营业一案业经布告周知兹计期限已满函请协助查禁并希见复以凭呈覆由1931-12-19[J].北平市政公报,(1931)131.
[19]北平市政府.批原具呈人北平旅店同业公会 呈为舞场奉令停业带恳展期禁止三个月以示体恤请核准由1931-12-10[J].北平市政公报,(1931)126.
[20]北平市政府.令社会局 遵令办理禁止本市舞场营业情形请核示由1932-02-25[J].北平市政公报,1932:136.
[21]如何禁绝跳舞?华洋商可一律待遇 社会局踌躇莫决[N].北平晚报,1932-04-19.
[22]北平市政府.训令社会公安局 据阿拉勒开亚请对于三星高夫两舞场加以限制等情仰会同遵照迭令分别处理具报由1933-07-12[J].北平市政公报,1933:205.
[23]北平市政府.布告 本市舞场自八月五日起一律不许雇用中国舞女伴舞违者重惩仰各遵照由1933-07-29[J].北平市政公报,1933:209.
[24]平市禁舞风波[J].北洋画报,1933(20):967.
[25]北平舞女之出路[N].天津:益世报,1933-08-16.
[26]市政府训令1933-8-12[J].北平市政公报,(1933)210;市府彻底禁舞[N].北平晚报,1933-08-14.
[27]平舞女各自西东[N].天津:益世报,1933-08-16.
[28]禁舞后的舞场[N].北平晚报,1933-11-19.
[29]昨晚大捕舞女[N].北平晚报,1933-11-19.
[30]处罚舞女办法[N].北平晚报,1933-11-12.
[31]为禁舞事敬告袁良[N].北平晚报,1933-11-24.
[32]平市公安一年来施政之检讨[J].市政评论,1935(3):1-2.
[33]最近之上海——披发鬼之发源地 跑狗和跳舞[N].北平:晨报,1931-08-09.
[34]华瑞.诗人与舞女[J].现代小说,1929(3):1.
[35]唐勉之.夜的卖笑者[J].中国漫画,1935(2).
[36]黄泽华.对北平跳舞盛行之感想[N].大公报,1931-07-06.
[37]马军.市政·舞厅——上海百年娱乐生活的一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10.
[38]左玉河.跳舞与礼教:1927年天津禁舞风波[J].河北学刊,2005(5).
【责任编辑 侯翠环】
The Spread of Ballroom Dancing and the Vicissitudes of Social Custom in Peking in 1920s-1930s
XIAO Hong-song1,2,CHEN Na-na2
(1. Department of History, 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 Beijing 100875;2. College of History, Hebei University, Baoding, Hebei 071002, China)
Commercial ballrooms sprang up gradually in Peking in 1920s, which was followed by an expansion of the number of people who participated in ballroom dancing. As a result, ballroom dancing thrived rapidly in this age-old city. This kind of business enriched the entertainment life of people living in Peking; meanwhile, it also induced the spread of extravagant, hedonic and orgiastic social atmosphere, which caused the government of Peking to give orders to forbid running ballroom business. Thus, commercial ballroom business recessed in Peking in early 1930s. The psychology and behavior of the local government, common people and media during that process reflected not only a zigzag spreading road of the ballroom dancing but also the social features that new viewpoints and traditional viewpoints coexisted and fought mutually in Peking at that time. What's more, that process also proved that the traditional and conservative temperament of Peking brought about a relatively slow vicissitudinous procedure of the social custom in this archaic city. Primarily speaking, it was the social ecological environment that restricted the depth and breadth of social custom vicissitudes in this city.
Peking; ballroom dancing; spread; forbidding the dance; social custom
2013-10-20
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重大项目《民国日常生活》(13JJD770017);中国博士后科学基金项目(2014M550641)
肖红松(1971-),男,河北安平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后,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社会经济史、华北区域史研究。
K26
A
1005-6378(2015)01-0096-07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1.01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