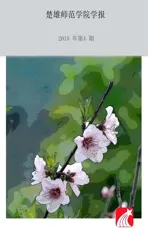沈从文笔下“老人”形象的精神解读*
2015-03-19严晓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严晓驰(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沈从文笔下“老人”形象的精神解读*
严晓驰
(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北京100875)
摘要:在沈从文的笔下,存在一系列老人的形象,如老水手、老船夫、老兵等。在这些老人身上,作者寄予了高尚的理想、健康的思想以及深厚的感情。老人历经人事的偶然与情感,虽达至生命的凝固,却仍表现出一种对生的执着,或不安于命运的安排,奋力抗争;或守卫生命的庄严,坚实地活着。同时,他们又是一种参照,联系着过去、现在和未来,作者在他们身上,注入了深深的爱与哀悯。
关键词:沈从文;老人;生命;明日
在《从文自传》中有一个章节叫《一个老战兵》,作者在回忆中写道:“在我那地方,学识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我一个姨父,带兵方面使我敬重的是本地一统领官,做人最美技能最多,使我觉得他富于人性十分可爱的,就是这个老战兵。”[1](P41)是不是得于这份年少时的记忆,在沈从文后来的写作中,我们常可以看到“老战兵”的形象。如《边城》中的老船夫,《长河》中的老水手,《灯》中的老兵,《会明》中的老火夫等,以及在其他篇章中着墨不多,但给人印象的老水保、老长工、老船匠、老纤夫等。在这些“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很多相同的部分,如他们的诚实善良、质朴纯厚,但在各个篇章中每个人的人生遭遇、生活处境又是那么的不同。
沈从文在《论技巧》中说:“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思想,必须先融解在文字里,这理想方可成为‘艺术’。”[1](P333)那么,在这些业已成为艺术形象的老人身上,作者又蕴含了何种“人类高尚的理想”、“健康的思想”,浸润、寄托着何种“宏博深至感情”?
一、人生偶然与情感的乘除
当我们走进沈从文笔下老人的世界,我们很快就会发现,这些老人都有着某种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灯》中的老兵,是“一个差不多用脚走过半个中国的五十岁的人,看过庚子的变乱,看过辛亥革命,参加过革命北伐许多重要战争,跋涉过多少山水,吃过多少不同的饭,睡过多少异样的床,简直是一部永远翻看不完的名著!”;《长河》中的老水手“身世如一个故事,简单而不平凡”;《丈夫》中的老水保“一个河里都由他管事”,“那些船排列在河下,一个陌生人,数来数去是永远无法数清的”,他且可以“明白这数目”,“记忆得出每一个船与摇船人样子”;《辰河小船上的水手》中的掌舵老水手,“三十七年的经验,七百里路的河道,水涨水落河道的变迁,多少滩,多少潭,多少码头,多少石头——是的,凡是那些较大的知名的石头,这个人就无一不能够很清楚的举出它们的名称和故事”。
这实在无可厚非,一个人活至近生命的终点,即使没有那么多传奇式的人生经历,只要他肯说来,那么他这一生即使再平凡也都将是一个传奇。《边城》中的老船夫,活了七十年,从二十岁起便守在小溪边,五十年来不知把船来去渡了多少人,这本身即已成一个传奇。《黔小景》中,两个商人问老店家“他住到这里有了多久,他说,并不多久,只二三十年”。照例,对这些老人的传奇人生经历,沈从文总是轻描淡写,然而这并不能掩盖这些老人经历
背后所隐伏的生命意识。在这些平凡老人的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一种生命发展的过程,他们各自对待生命的态度,而更为重要的是,从对他们坦白的陈述中,我们才明白,“在用人生为题材的各样变故里,所发生的景象,如何离奇如何炫目”。[1](P85)“这才真是一个传奇,即顽石明白自己曾经由顽石成为宝玉,而又由宝玉变成顽石,过程竟极其清楚。石和玉还是同一个人”。[1](P179)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人的一生可说即由偶然和情感乘除而来,人生中偶然与情感的乘除,会使一切改观。“你虽不迷信命运,新的偶然和情感,可将形成你明天的命运,决定你后天的命运”。[2](P298)而这一切在老人们身上得到最为集中的体现,他们既已行过人生的大半旅程,实乃历经了人生偶然与情感的乘除,这才真是他们的传奇之处。
《丈夫》中的老水保,本是个水上一霸,在年青时节因殴斗杀过一个水上恶人,因为杀人,同时也被人把眼睛抠瞎了。独眼睛的水保处治这水上的一切,到人上了年纪,“世界成天变,变去变来这人有了钱,成过家,喝点酒,生儿育女,生活安舒,这人慢慢的转成一个和平正直的人了”,并建设了一个道德的模范。而更让人感到人生飘忽的还是《长河》中的老水手,年轻时吃水上饭,到事业刚顺手,母子三人却害霍乱病死,特意把他单独留下。祸不单行,本想重新挣出一份家业的他,行船又出了事,于是对自己失了信心,离了家跑远了。大约经过十五年光景,这个在外面生活不甚得意的老水手回到了家乡,成了枫树坳上坐坳守祠堂的人。
“十年兴败许多人”,在老人们人生长河的种种变故里,我们看到了“时间”的古怪,一切人一切事全在“时间”下被改变。时间既无法停滞,生命本身也就不能凝固,总在发展中,因此,变化应当是一种常态。然而,人生的种种变故又像是一种近于偶然的势能,决定了生命发展的形式,也正因如此,命运总显得无常而不能自主。沈从文笔下的老人形象,一个个单独发展的生命个体,也就成了人类困于命运枷锁的象征。
二、超越的生存愿望
然而,沈从文寄予老人身上的思考并不局限于此。固然,非理性的情感与非必然的偶然,是“生命”有计划、按理性支配人生的巨大魔障,但是生命的发展,无从离开理性或意志。“一切奇迹都出于神,这由于我们过去的无知。新的奇迹出于人,国家重造、社会重造全在乎意志。种族延续、国家存亡在乎‘意志’,并非东方式传统信仰的‘命运’”。人生除了偶然和情感,还应当有点别的什么,“难道我和人对于自己,都不能照一种预定计划去作一点”。[2](P300)
“生命在发展中,变化是常态,矛盾是常态,毁灭是常态。生命本身不能凝固,凝固即近于死亡或真正死亡。”[1](P376)而对于老人,他们既已迈入人生的暮年,近于死亡,那么生命的凝固就不能不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正如作者在《长河》中所说的:“事实呢,世界纵然一切不同,这个老水手的生命却早已经凝固了”。可是老水手人老心不老,在命运的接连打击之下,他总是要想个办法脱身。老水手的重置家业、浪迹天涯,无一不是想凭借自己的“意志”去挣脱由偶然和情感形成的命运枷锁。即便当他最后成了一个坐坳守祠堂之人,生命的凝固也并没有让他失去对生活的积极态度。
传奇的人生经历和丰富的人生经验让老水手在面对外部世界的剧烈变动时,显得更加自信,也更加坦然。“慢慢的来吧,慢慢的看吧,舅子。‘豆子豆子,和尚是我舅子;枣子枣子,我是和尚老子。’你们等着吧。有一天你看老子的厉害!”、“好风水,龙脉走了!要来的你尽管来,我姓滕的什么都不怕!”老水手内心的呐喊,既是对恶势力的蔑视,也是对命运的无言抗争。这命运是“地方明日的命运”,也是身处其中的人的命运。老水手所想的,仍旧是“总有一天有些事会要你来作主的”。
生命凝固,近于死亡,却和老水手一样,想凭着自己的意志来安排命运的还有《边城》中的老船夫。十五年前,因着情感,老船夫的独生女丢开老的和小的,为一个军人吃了很多冷水死掉。面对人生的偶然变故,老船夫一言不语,在平静的日子里,将女儿留下的孤雏抚养长大。这些事对老船夫来说谁也无罪过,只应由“天”去负责,他口中不怨天,心里却不能完全同意这种不幸的安排。因此,当翠翠一天天长大,也开始因情感而困扰时,老船夫心情也变了,记忆中的隐痛让他担心翠翠会和她的母亲有着同样的命运。
按理说,“人太老了,应当休息了,凡是一个良善的乡下人,所应得到的劳苦与不幸,全得到了。假若另外高处有一个上帝,这上帝且有一双手支配一切,很明显的事,十分公道
的办法,是应把祖父先收回去,再来让那个年轻的在新的生活上得到应分接受那幸或不幸,才合道理”。可是老船夫不这么想,他以为死是应当快到了的,但无论如何,得让翠翠有个着落。他要把翠翠交给一个人,这个人要适宜照料翠翠,更重要的是,翠翠得愿意,只有这样,他的事才算完结。
为了翠翠的幸福,也为了求得人对自己命运的自主,老船夫四处奔波、探询,做着各种“安排”,直至死亡。但是他的“安排”却让他陷入了不被理解的痛苦境地,他成了一个好事、做作,为人弯弯曲曲、不利索的老家伙。也只有在死后,老马兵替他说出了生前一直忍着不说的话:“听我说,爷爷的心事我全都知道,一切有我。我会把一切安排得好好的,对得起你爷爷。我会安排,什么事都会。我要一个爷爷欢喜你也欢喜的人来接收这渡船!不能如我们的意,我老虽老,还能拿镰刀同他们拼命”。
沈从文在《短篇小说》一文中写道:“……一个人不仅仅能平安生存即已足,尚必须在他的生存愿望中,有些超越普通动物的打算,比饱食暖衣保全首领以终老更多一点的贪心或幻想,方能把生命引导到一个崇高理想上去。这种激发生命离开一个动物人生观,向抽象发展与追求的兴趣或意志,恰恰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1](P343)可以这么说,在老水手和老船夫身上,作者凝聚的正是这样一种崇高理想,即一个人历经人事偶然与情感的乘除,达至生命的凝固,却仍不忘追求生命的自主自为,为着自己的命运做一些抗争和安排,这些老人也正是人类一切进步的象征。所以,从这个角度来看,《边城》和《长河》实乃作者唱响的生命理想之歌。
三、生命的庄严
老船夫虽是一个在自然里活了七十年的人,但在人事上的自然现象,即偶然与情感的乘除,又实在不是他所能安排的。天保的意外去世,顺顺的冷淡,傩送的误解,翠翠的朦胧情感,都是老船夫无法预料和安排的。面对无常的命运,他再奋力抗争,结果也只能是“捏紧拳头威吓了三下,轻轻的吼着”,最终在雷雨交加的夜晚,伴随着白塔的坍塌而死去。
在《边城》的题识中,沈从文如此写道:“三月二十一看此书一遍。觉得很难受,真像自己在那里守灵。人事就是这样子,自己造囚笼,关着自己;自己也做上帝,自己来崇拜。生存真是一种可怜的事情”。[1](P218)这或者正是人之所以为人,出于自然而又异于自然处:自然似乎永远是“无为而无不为”,而人却只像是“无不为而无为”。[1](P265)如此看来,人类景象似乎只是一片寥廓的虚无。不过面对此虚无时,作者并不彷徨丧气,人“无不为而无为”,其庄严处也正在于此。老船夫活了七十年,守了五十年的渡船,他从不思索自己的职务对于本人的意义,只是静静地很忠实地在那里活下去。他担负了自己的那份命运,为自己,为亲人,也从不逃避为了求生而应有的一切努力,在这一切努力中我们也便感到了四时交替的严肃和生存的庄严。对他来说,做人就是“要硬扎一点,结实一点,才配活到这块土地上”!孔子说“未知生,焉知死”,人既必死,那么就应当在生存的时候知所以生。沈从文在这些近于死亡的老人身上寄托的正是这样一种精神:一个人只有稳稳当当地活在这块地面,不辜负日头,才不失其生命的庄严。
在《湘行散记》的《一九三四年一月十八》一文中,作者写他行船上行时,需要一个临时纤手,“一个老头子,牙齿已脱,白须满腮,却如古罗马战士那么健壮,光着手脚蹲在河边那个大青石上讲生意来了”。老头子和船上的水手大声嚷着而且辱骂着,只为着争一分钱。当他见小船已开出后,便不再坚持,“却赶忙从大石上一跃而下,自动把背后纤板上短绳,缚定了小船的竹缆,躬着腰向前走去了”。等他得了钱,坐在水边大石上一五一十数着,作者不禁感慨:“人快到八十了,对于生存还那么努力执着,这人给我的印象真太深了”。
《黔小景》中的老人,他一个人守着地处偏僻的客栈二三十年,俨然像尽着一份责任似的,寂寞而宁静地生活着。面对人事的变故,他似乎有着一份超然的从容——“那老人在旁边听到这两个客人的调笑,也笑着。但这两双鞋子,却属于他在冬天刚死去的一个儿子所有的”。而当死亡降临到他自己身上,他仍是那么从容不迫,在夜里坐在凳上安静地死去,没有留下任何言语。
表面看来,用沉默来接受一切人事的变故,不抵抗,不作解救之方,且仿佛无动于衷,这是一种消极地对待生命的态度。然而,明白偶然和情感在生命中的种种,只照分上派定的忧乐,结实、从容地活下去,这何尝不是一种艰苦的挣扎和战争。在作者看来,这“也
就是新的道家思想,在某一点某一事上,你得有点信天委命的达观,你才能泰然坦然继续活下去”。[2](P300)
确实,命运实非人的“意志”所能安排,但“一个人存心要活得更正当结实有用一点,决不会轻易倒下去的”。[1](P141)生命的庄严,就在那“无不为而无为”的哀悯中,就在这“存心”之中。这实在是沈从文思想的复杂之处,或者说,这是人类景象的复杂之处。对沈从文来说,他也不过是带着一份对于人事关系中,人甘心接受分定或希望挣扎而脱的爱与哀悯来“看”这一切。
四、民族及人类未来的远景
不管是对无常命运的抗争,还是守卫生命的庄严,沈从文笔下的老人时常闪现出耀眼的人性之光。但沈从文写这些老人,并不是简单地寄托对老人的赞赏或哀悯,他写老人总是寄望于一个“明日”,寄望于未来的一代。在沈从文看来,一个作家应当“把他的作品预备作为未来光明颂歌之一页,倾心于那个‘明日’,肯为‘大多数人如何可以活下去’打算打算”,[1](P318)而他自己也正是这样一个“常常为人生远景而凝眸”的作家。
《边城》中,傩送夸奖老船夫说:“……地方不出坏人出好人,如伯伯那么样子,人虽老了,还硬朗得同棵楠木树一样,稳稳当当的活到这块地面,又正经,又大方,难得的咧”,老船夫回答:“我是老骨头了,还说什么。日头,雨水,走长路,挑分量沉重的担子,大吃大喝,挨饿受寒,自己分上的都拿过了,不久就会躺到这冰凉土地上喂蛆吃的。这世界有的是你们小伙子分上的一切,好好的干,日头不辜负你们,你们也莫辜负日头”。老船夫对傩送的期许,是老一辈对未来一代人的期许,是对那个“明日”的期许。老人自己既已走过生命的长河,而他一生传奇式的经历、丰富的经验、做人优美的品性却将凝结成一种智慧传递下去。沈从文笔下的老人如老船夫一样,成为一种参照,通过他们,我们就能“温习过去,观照当前,悬揣未来”。
在篇首提到的《从文自传》中的那个老战兵,作者说他“做人最美技能最多”、“富于人性十分可爱”,而这又像是沈从文笔下所有老人的共同点。在这些老人身上,我们可以看到作者一直倾心于表现的一种“优美、健康、自然,而又不悖乎人性的人生形式”。他们善良、质朴、正直、诚实,忠诚、纯厚、勤俭、和平,爱说玩笑、富于童心……仿佛人性中所有美好的品性都能在这些老人身上找到,但这并不是作者刻意为之,作者“动手写他们时,为了使其更有人性,更近人情,自然便老老实实的写下去”。[3](P93)而在湘西的传统中,老人也常作为一种道德的模范而存在。如《边城》中写船总“必需一个高年硕德的中心人物”,顺顺那时虽只五十岁,“人既明事明理,正直和平又不爱财,故无人对他年龄怀疑”。
如果硬要说作者描写的有悖于现实情况,那么,只能说是作者所描写的是湘西的过去,老人所代表的也就是湘西的过去,是“这个民族的过去伟大处”。然而,“这地方到今日,已因为变成另外一种军事重心,一切皆用一种迅速的姿势在改变,在进步,同时这种进步,也就正消灭到过去一切”。[1](P4)骤然而来的风雨,把许多人的高尚理想,做人的优美品性都卷扫、摧残得无踪无迹。前一代人固有的优点,“年轻人几乎全不认识,也毫无希望可以从学习中去认识”。[4](P16)因此,作者温习过去,写出老人身上所保有的民族优美品性,为的就是不失去本来的一切,以求重造未来。正如作者在《长河》题记中所说的:《边城》中人物的正直和热情,虽然已经成为过去了,应当还保留些本质在年轻人的血里或梦里,相宜环境中,即可重新燃起年轻人的自尊心和自信心。[4](P17)
而对于这些老人自身,作者又是怀着一种不易形诸笔墨的沉痛和隐忧。在“目前堕落处”,沈从文笔下的老人总会陷于一种孤独的处境:老船夫的不被理解,老手水探询“新生活”的可笑之处,老纤夫的狡猾,老舵手的古怪,《灯》中的老兵仿佛永远处在另一个世界,《会明》中老火夫的呆傻、被戏弄。然而,可笑之处也是可爱之处,且一般人所谓的“怪”、“呆”、“傻”,或许倒正是目下认为活得“健康正常人”业已消失无余的难得品质。对于他们,作者寄予深厚的同情:“我望着这老兵每个动作,就觉得看到了中国那些多数陌生朋友。他们是那么纯厚,同时又是那么正直。好像是把那最东方的古民族的和平灵魂,为时代所带走,安置到这毫不相称的战乱世界里来,那种忧郁,那种拘束,把生活妥协到新的天地中,所做的梦,却永远是另一个天地的光与色,对于他,我简直要哭了”。可见,老人身上背负着一个民族的“过去”,但这种重负让
他们在新的环境下举步维艰。
另一方面,老人因其“体力日渐衰竭,情感已近于凝固,自有不可免的保守性”,这种保守性让他们保留治事、做人的优美、崇高风度的同时,也势必带来“习惯”的危害。“人类一出生便完全沉落在传统思想,种族习惯,和社会团体严格包围中。这些思想和习惯自其活动的开始,就给了本能和冲动一个扮演的舞台,一言以蔽之,就是给了他一个永久逃不脱的界线……”[1](P338)而生命愈长久,这种习惯的力量就愈大,老人最终只能生活在自己的习惯里,与“现在”脱节。如《会明》中的老火夫,在军队消磨了卅年,只为怀着对“革命”的忠诚,然而“为什么动手他却不问。因为上司早已说过许多次,自然是‘打倒军阀’,才有战事,不必问也知道。其实他的上司的上司,也就是一个军阀。这个人,有些地方他已不全呆了”。在沈从文看来,这种习惯不仅阻碍着主体精神的活力,也阻碍着人类的进步。他所关心的仍旧是“我们用什么方法,就可以使这些人心中感觉一种对‘明天’的‘惶恐’,且放弃过去对自然和平的态度,重新来一股劲儿,用划龙船的精神活下去”。[2](P175)
总之,不管是对老人的赞颂,还是对老人主体精神蒙昧的隐忧,沈从文的立足点始终是将“过去”和“当前”对照,思索“所谓民族品德的消失与重造,可能从什么方面着手”。眼前的许多事实虽不免令人失望,但就像老人传奇式的人生经历一样,对于民族及人类未来的远景作者并不灰心,因为“时间”将会对此作出证明。这些老人形象的意义正如沈从文所说:“我们得承认,一个好的文学作品,照例会使人觉得在真美感觉以外,还有一种引人‘向善’的力量。我说的‘向善’,这个词的意思,并不属于社会道德一方面‘做好人’的理想,我指的是这个:读者从作品中接触了另外一种人生,从这种人生景象中有所启示,对‘人生’或‘生命’能作更深一层的理解”。[1](P343)
参考文献:
[1]沈从文.从文自传[M].北京:十月文艺出版社,2008.
[2]沈从文.沈从文散文选[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4.
[3]沈从文.边城集[M].湖南:岳麓书社,1992.
[4]沈从文.长河集[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5.
(责任编辑徐芸华)
On Images of Old People Portrayed by Shen Congwen
YAN Xiaochi
(School of Chinese Langue and Literature,Beijing Normal University,Beijing 100875,China)
Abstract:In articles of Shen Congwen there are a series of images of old people,such as the old sailor,the old boatman and the old soldier.On those old people,Shen has placed noble ideals,healthy ideas and profound emotion.The old people,who have experienced personnel accidents and emotion,present persistence towards life or struggling against their fates or live steadily while guarding solemnity of life though they have come to solidification of life to certain degree.Meanwhile,they are playing a role of reference objects who are connecting the past,present and future.Towards them,Shen has imbued with profound love and sympathy.
Key words:Shen Congwen; old people; life; the next day
作者简介:严晓驰(1989—),女,北京师范大学文学院2013级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儿童文学。
收稿日期:* 2015-01-15
文章编号:1671-7406 (2015) 04-0039-05
文章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6. 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