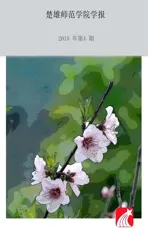以女性民俗视角重读《为奴隶的母亲》及其女性命运*
2015-03-19祝林辉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宝山200444
祝林辉(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宝山200444)
以女性民俗视角重读《为奴隶的母亲》及其女性命运*
祝林辉
(上海大学文学院,上海宝山200444)
摘要:以往的研究者基本上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解读柔石的《为奴隶的母亲》,笔者试图从女性民俗的视角出发,考察春宝娘是如何在典妻的民俗下被不断地塑造和加固性别角色及遭遇权利的不平等性,父权制社会对女性的压制又是如何通过民俗被合法化,但女性又以自身的丰富性和辩证性抗拒着凝固为绝对法则的民俗陋俗。同时,也看到作者的男性身份使得文本并未完全表达出女性在典妻民俗下的生命体验。
关键词:女性民俗;柔石;《为奴隶的母亲》;性别压抑
《为奴隶的母亲》这部小说曾产生了广泛的影响,并被不同的剧种如沪剧、甬剧、黄梅戏等改编上演,也曾被搬上银幕以及翻译成多种语言出版。从一开始,这部作品时常被从阶级性和政治性的角度来进行解读,新中国成立后,在“左”的思潮影响下,依旧是从阶级分析的角度来剖析该作品的深层意义。进入新时期以后,新启蒙主义又搭载着西方思潮和重返“五四”的顺风车,引入人性和人道主义的思考,跨越阶级分析的隔离墙,认为作品的女主人公春宝娘拥有伟大的母爱以及自我牺牲的精神;而性别视角则在90年代后才被运用于解读该作品,但是解读多围绕男女二元对立之下春宝娘的悲剧性命运,却很少有以女性民俗视角作为切入点,对《为奴隶的母亲》中女性的社会性别和女性意识等方面进行不同的分析。正如董晓平在《中国现代的女性观及当代变迁》中对女性民俗做出的思考,即“认为女性的解放地位要在民俗内部进行。”因此,要研究文本内女性民俗所揭发的女性问题,我们可以从女性主义角度出发,探讨民间文化体系如何赋予男性角色绝对优势的权威、价值和重要性;探讨典妻这样的女性民俗是如何不断地重塑、加固女性的性别角色及权利的不平衡性,又如何成为女性思想意识深处根深蒂固的一座衡量自我准则的坐标。同时,笔者认为女性在典妻这样的民俗中也呈现出辩证的状态,她并非是一成不变的顺从,而是以自身微弱的丰富性对抗着凝固为绝对法则的传统民俗,用女性独有的方式抗拒着这亘古不变的传统。
一
几千年的封建传统,儒家礼教的深入人心,形成了比较稳定的父权制社会,在此背景下,男性是传统社会的主导和中心,天然地拥有优越感。而女性则成为“第二性”,男性的附属品,这种意识促成了女性自觉的卑贱意识,又以民俗生活的方式不断得到加强和固化。典妻制度是人类买卖婚姻的一种风俗,盛行在浙江宁波、绍兴、台州等地,它和娼妓制度一样,都是正式婚姻制度的一种补充。一些有钱人家因为没有子嗣,就通过金钱购买妇女到自己家,等生了孩子之后妇女便回到原来的家庭。而女性民俗研究首先要关注的是民俗社会中与女性民俗有关的民俗事项,在此基础上思考民俗社会中女性性别规范的养成,女性和男性在民俗社会的活动中如何扮演其角色。《为奴隶的母亲》就是通过典妻这样的女性民俗,表现了春宝娘的悲惨遭遇。
“费尔斯通的《性的辩证法》中认为,使妇女的屈从形成系统的父权制,乃是根植于两性在生物学意义上的不平等。”[1](P101-102)他进一步认为,“只要自然生育依然是常规,而人工或技术辅助生育是例外,那么对妇女来说,并没有发生任何根本的改变。”[1](P103)在传统社会中,典妻的民俗利用的正是女性作为廉价的生育工具而被买卖,从而使春宝娘被封锁在性的工具、生育的奴隶这层意义上。这在当时却
被认为是天经地义的,这正是民俗在历史的长久积淀下所具有的潜移默化的作用。“年纪约三十岁左右,养过两三个儿子的。”“假如三年养不出儿子,是五年。”[2](P208)沈家婆最关注的就是春宝娘作为一个生育工具的使用价值,如果在规定时间内不能生育,还可以延长典妻的时间。春宝娘被典卖给秀才家三年并且生养个儿子的价格是100块大洋,这100块大洋归其皮贩丈夫所有。因此,典妻的民俗给了皮贩丈夫一条生存的出路,多少可以改变他“因为境况的不佳,烟也吸了,酒也喝了,钱也赌起来了。……但也更贫穷下去,连小小的移借,别人也不敢答应了。”[2](P207)性/社会性别制度是一套安排,社会通过这套安排把生物学意义上的性转变为人类活动的产物,父权制社会就是利用男女在生理和文化中的差异,逐步构建出类似于民俗这样一整套的意识形态规范,把妇女限定在顺从、消极的范围中。这样,典妻的民俗就正好可以最大化地利用春宝娘的生育价值,并且保证皮贩丈夫可以取得金钱利益,保证秀才可以取得子嗣的利益,而不用付出任何代价。春宝娘则毫无所获,自始至终她只是个物品,在重重的枷锁中,春宝娘面临着一个斑驳陆离的世界和一个逐渐被淹没的自己。
同样,秀才的正房太太也是当时典妻制度的牺牲品,作者叙述她不能生育,但是面对典妻习俗时,却也不得不忍受典妻甚至是“秀才娘子也喜欢”。可见,典妻民俗已经在潜移默化中内化为女性潜意识认可的一种传统习俗。她非常嫉妒春宝娘,想方设法地为难春宝娘,却不曾想到自己也是典妻习俗下的牺牲品,是父权制社会下苍白无力的受害者。
从皮贩丈夫到秀才,春宝娘所扮演的正是典妻习俗下出色的生育工具,是男人泄欲的对象和传宗接代的工具和奴婢。典妻民俗所具备的巨大惯性力量和性别不公,成为笼罩着传统男女性别等级的大雾,在雾中,女性看不清自身所处的位置,但是却时时刻刻呼吸着充满雾的空气,赤裸裸地展示着女性作为性工具和生育工具的一个符码。
在民俗强大的力量面前,春宝娘的精神日益分裂,所处的境况越来越糟糕:
“没有借你五块钱吗?”秀才愤怒地说。
妇人低着头停了一息答:
“五块钱怎么够呢?”
秀才接着叹息说:
“总是前夫和前儿好,无论我对你怎么样!本来我很想再留你两年的,现在,你还是到明春就走罢!”[2](P219)春宝娘在秀才眼里仍旧是前夫的女人,秀才是当时的一个知识分子,有着较好的修养和礼仪,但是在对待女人方面,仍旧是将春宝娘看作一个附属品似的玩物,孩子的母亲,生育的工具。典妻习俗下的女性,就是处于这样一种矛盾和焦虑中,在两边徘徊,无从附着。从这个角度看,春宝娘甚至连附属品都不是,她不属于秀才和皮贩丈夫中的任何一个,更不属于自己,她是在女性民俗精神虐杀下备受心灵创伤的一个受害者。典妻民俗按照既定的方向更改和涂抹着她,生产出一个矛盾的结合体。这个矛盾的结合体来自于两方面,一方面即如前所说的在两个丈夫中被抛弃和排斥,毫无归宿;另一方面,被两个孩子春宝和秋宝抛弃,或者说春宝娘不得已最终不属于任何一个孩子。
“别了,我底亲爱的儿子呀。你底妈妈待你是好的,你将来也好好地待还她罢,永远不要再纪念我了!”[2](P220)春宝娘无法让时间永远停滞,她最终必须离开一岁半的孩子,也许永远都无法见到他了,即使见到了也无法以母亲的身份带着母爱的关怀来到他身边。而当她回到皮贩丈夫家的时候,“一群孩子们,个个无意地吃了一惊,而春宝简直吓得躲进屋子他父亲那里去了。”[2](P221)春宝已经跟她非常生疏了,她感受到的就是典妻的民俗耗尽了她三年的光阴,慢慢地蒸发掉母子之间的情谊,夺去了她在这个世界上最后的也是唯一的寄托。春宝、秋宝、皮贩丈夫、秀才都抛弃了她,那么她还剩下什么呢?她连自己都不属于了。
典妻的习俗对女性人物的生命体验有着极大的漠视,在被不断地塑造和加固女性角色地位之后,在典妻民俗的车轮碾过之时,春宝娘是那样的无力与无奈:
这时,他底妻简直连腑脏都颤抖,吞吐着问:
“你为什么早不对我说?”
“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
“决定了么?”妇人颤着牙齿问。
“只待典契写好。”
“倒霉的事情呀,我!──一点也没有别的方法了么?春宝底爸呀!”[2](P208)春宝娘面对丈夫的决定,从未有过任何一个明确的显而易见的反抗,最多只是责怪他为什么不早说,责怪自己的命运不好,如此倒霉,典妻的命运会降临到自己的头上。可见,女性在强大的外力面前显得如此弱小,发不出自己关于生命体验的任何反抗的声音。在秀才家所受
到的折磨令她一天天地瘦黄下去,在典妻结束之后,返回皮贩丈夫家的时候,“暖和的太阳所照耀的路,在她底面前竟和天一样无穷止地长。”[2](P220)民俗作为一种民间伦理,将典妻以合法化的形式日益固定并推广开来,成为演绎、强化性别等级和奴化女性的一个场所。顺从的结果是自己一步步走向深渊,走进了残酷的男权社会通过残酷的典妻民俗撒下的大网之中。文本中有许多描述春宝娘的句子,例如“几乎昏去似的”、“讷讷地低声地”、“简直痴似的”、“一点儿也没有气力地。”反复出现的几句话是“话一句没有”、“话一句也说不出”、“声音时在她底喉下”、“无论怎样也说不出”等。一个人又如何能够改变自己的境遇呢?春宝娘找不到答案,也不会去寻找答案,然而春宝娘的反抗有着自己无言的特殊的方式。
二
民俗在春宝娘身上打磨而过,她不能发出声音,但是说话的喉舌却一直存在。正如学者所说:“不管男人如何图谋持续有效地管教妇女。威胁她们所有人,许多妇女都用行动证明,她们是不可控制的。”[3](P505)女性的欲望在民俗这样无孔不入的道德说教中处于压抑状态,女性的声音虽然很少发出来,甚至被淹没在一片男性的讨伐声中,但是却从未消失过。春宝娘用其微弱的行为抗拒着典妻民俗,只是这种抗拒是在男权社会意识形态的凝视和认同之下,才能获得表达的权力,所以,春宝娘当然不会也不能够赤裸裸地通过逃跑、暴力等方式。由于包括春宝娘在内的中国传统女性的整个生命过程基本上都是围绕着家庭展开的,也就是说,春宝娘的生命价值和对典妻民俗的抗拒也只能是在家庭中得以实现。
和鲁迅的作品《祝福》中的女主人公祥林嫂的隐忍、麻木不同,我们似乎可以从春宝娘身上感受到一种美,或者说是一种无声的反抗。春宝娘其实是作为生育工具而被典卖的,“母亲”的身份是最能够体现她的精神状态的。典妻民俗想要完全扼杀女性的主体性,但是母亲的真心诚意却弥漫于整个文本中,小说在写春宝娘离开的前一个晚上,说“她先将春宝底几件破衣服都修补好;春将完了,夏将到了,可是她,连孩子冬天用的破烂棉袄都拿出来,移交给他底父亲。”春宝娘对于孩子永远是主动地关怀,春宝娘的人性精神都在母爱的光辉中得到了体现。同样,春宝娘在两个丈夫的家里,都主动地为了孩子参与了很多劳动,包括离开皮贩丈夫前夜的修补、收拾房间,在秀才家洗衣喂猪、生儿哺乳。虽然这些都是家庭内部的事情,可以说她沦为男性的家务活工具,但是春宝娘是出于对孩子的关爱而主动地承担这些家务的。这就是主动与被动之间的差异,这时读者体验到的是一个拥有善良美、母性美的女性形象。小说中写到“竟说得这个具有朴素的心地的她,一时酸,一会苦,一时甜上心头,一时又咸的压下去了。”[2](P212)春宝娘的这些特征正是通过她与孩子相处,劳作中所透露出来的欢乐、幸福和生的意识表达出来的。
甚至,她为了自己的孩子偷偷地把秀才给她的青玉戒指给了皮贩丈夫,这对于春宝娘是一个非常艰难的抉择,一旦被发现后果将不堪设想,但是她还是偷偷地给了皮贩,也因此违抗了秀才的意志,毕竟戒指是作为传家宝传给秋宝的。试想,如果春宝娘为了自己考虑,顺从秀才,没有把青玉戒指赠送出去,那么,也许她就增加了长期留在秀才家里的机会,至少能够解决温饱问题。这个细节说明女性体内蛰伏的欲望、意志一直在涌动不息与蓬勃发展,尽管是不被认可、不被张扬的。典妻的民俗关闭了女性在男性面前自我表达的这扇门,但是却被女性推开了另一扇门,即在孩子的掩护下,自然的情感和自由的精神像涓涓细流一样从不中断。这当然不能够颠覆整个男权社会及其一系列的社会规则、意识形态,但也正因如此,她才终于没有“像织金云朵里的一只白鸟,最后霉烂在屏风里”。母性是春宝娘的精神归宿和情绪表达的一种方式,她并没有完全忘记自己的存在,这是一个可以“主动表达”的生育工具。
三
“女性研究并不是简单地研究妇女,而是确定女性为本位,从女性的视角看世界,以女性自身的体验为中心的研究。”[4]然而,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作者是否真正地从女性主义的角度,阐发了女性在典妻民俗中自身的体验而毫无男性视角的遮蔽呢?女性民俗作为传统的“集体无意识”是经过了数千年时间的积淀,才内化为女性自身的一部分。尽管文本通过典妻的故事讲述了一个为奴隶的母亲在女性民俗下的悲剧性命运,但是作者作为一个男性仍然带有传统的男权色彩,并没有给春宝娘真正表达自己的机会,也没有完全深刻地表达出女性人物的生命体验。
例如,在皮贩丈夫告诉她已经把她典出去了的时候,春宝娘虽然在场但实际上却是缺席
的,小说记叙了皮贩丈夫滔滔不绝地讲述自己典妻的原因和内心的不安,讲述自己是迫不得已的,为自己开脱罪责:
他气喘着说:“三天前,王狼来坐讨了半天的债回去以后,我也跟着他去,走到了九亩潭边,我很不想要做人了。但是坐在那株爬上去一纵身就可落在潭里的树下,想来想去,终没有力气跳了。猫头鹰在耳朵边不住在啭,我底心被它叫寒起来,我只得回转身,但在路上,遇见了沈家婆,她问我,晚也晚了,在外做什么。我就告诉她,请她代我借一笔款,或向什么人家的小姐借些衣服或首饰去暂时当一当,免得王狼底狼一般的绿眼睛天天在家里闪烁。
……
“昨天在你底面前旋了三个圈子,可是对你说不出。不过我仔细想,除出将你底身子设法外,再也没有办法了。”[2](P208)
笔者长篇累牍地引用原文,就是想说明文本不停地叙述皮贩丈夫的境况和他内心的不安与无奈,但是分配给春宝娘的文字少之又少,作为女主人公却游离在文本的结构之外。尽管春宝娘在强大的女性民俗面前,没有多少反抗的权力,但是这并不代表春宝娘内心里没有自己的真实想法和声音,春宝娘作为典妻习俗的受害者,应该有着自己深切的生命体验,这些却被作者忽略了。再如,在离别前的那个晚上以及秋宝过生日的晚上,春宝娘都不是文本的结构中心,对叙事进程的作用也是十分微弱的,这样,读者对春宝娘的真实内心想法也逐渐模糊。
春宝娘对典妻的态度也从未在文本中出现过,而且叙事者经常比较强硬地介入到春宝娘的内心——“他知道这个老妇人是猜忌多心的,外表虽则对她还算大方,可是她底嫉妒的心和侦探一样,监视着秀才对她的一举一动。”这里,“像侦探一样”的语言怎么会出自一个农妇口中呢?明显是作者自己的声音通过春宝娘的内心表达出来的。正如费孝通所说:“乡村社会中阻碍着共同生活的人充分了解的却是个人生理上的差别……正因为还没有人能亲身体会过两性的差别,我们对于这差别的认识,总是间接的,所能说的差别多少只限于表面的。在实际生活中,谁都会感觉到异性的隔膜,但是差别的内容却永远是个猜想,无法领会。”[5](P46)
总之,在《为奴隶的母亲》中,作者虽然叙述了在父权社会的压迫下,春宝娘处于压抑和身不由己的状态,但是并没有具体地表达出她更加真实的体验。笔者认为,这多少会影响到作品对典妻所代表的父权制社会的批判。
参考文献:
[1](美)罗斯玛丽·帕特南·童.女性主义思潮导论[M].艾晓明等译.武汉:华中师范大学出版社,2002.
[2]张福贵编.中国现代文学经典(一) [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7.
[3](美)凯特·米列特.性的政治[M].钟良民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
[4]易小松.民俗文化视野中的女性研究[J].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科版),2004,(3) .
[5]费孝通.乡土中国[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98.
(责任编辑徐芸华)
My Mother a Slave and Destiny of Women Re-read from Women's Customs Perspective
ZHU Linhui
(College of Liberal Arts,Shanghai University,Baoshan,200444,Shanghai)
Abstract:Rou Shi’s My Mother a Slave was virtually analyzed from the perspective of class,but the present author’s is a custom one,especially that of a woman.The feminist discussions herein include: how the feminist role of the heroine is constructed and consolidated by the custom of pawing wife; how the heroine is unfairly treated; how the patriarchal system legalizes the oppression of women through custom; and how women defy unreasonable customs that have already condensed into laws with their own diversity and dialectic characteristics.The author even proceeds to point out how the novelist,as a man,has failed to fully express the true life experience under the custom of wife pawning.
Key words:feminist customs,Rou Shi,My Mother a Slave,gender repression
作者简介:祝林辉(1989—),男,上海大学文学院2013级硕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
收稿日期:* 2015-02-26
文章编号:1671-7406 (2015) 04-0044-04
文章标识码:A
中图分类号:I207. 42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