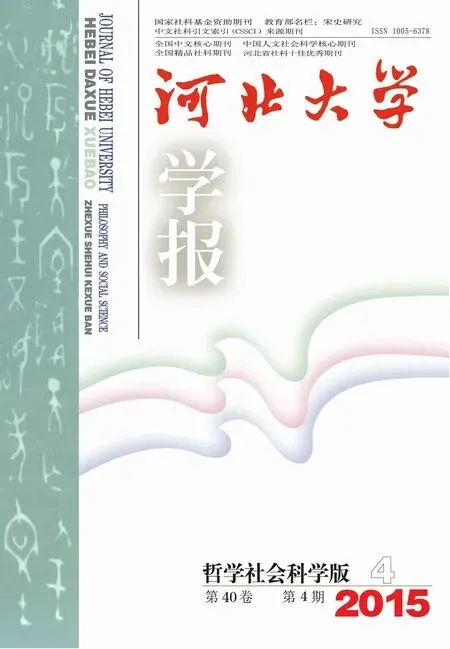近代直隶省会保定城的城市功能衍变
——以直隶总督署、莲池书院、保定军校为例
2015-03-19刘志琴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071002
刘志琴(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历史学研究
近代直隶省会保定城的城市功能衍变
——以直隶总督署、莲池书院、保定军校为例
刘志琴
(河北大学历史学院,河北保定 071002)
以清代与民国初期的直隶保定城(1669—1917)为研究对象,通过剖析保定城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城市建筑文化遗产,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城市建筑;城市功能;保定城
城市的建筑犹如城市的一张脸,不仅反映着当时城市的风貌,还蕴含着城市的历史文化,折射着城市历史演变的进程。本文以保定城的古文化建筑为研究对象,通过对保定城中的直隶总督衙署、莲池书院、淮军公所、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等具有时代标记和烙印的地标性城市建筑进行剖析,展示近代保定城在社会政治风云变幻中的发展轨迹及其“一文一武一衙署”的城市功能衍变特性。
一、直隶总督署与保定城的政治功能
《保定郡志》载燕昭王曾于今保定城东建“广养城”(明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十二·古迹),用来放牧战马,以备军需,“广养城去郡治东六里许周围五里南临河水,古老相传燕昭王牧马于此故曰广养”①《保定郡志》(明弘治版《保定郡志》卷二二·古迹)。其功能是为战备而建的军事后备之城,这是保定历史上修建的第一座城池,虽为“空城”,但自建立那天起,就是一座战备之城。可见,城池的出现就带有了军事的色彩。自此以后的各朝代,保定以一个军事重镇的身份成为朝廷所设的或攻或守的一个棋子。金元之后国家政治权力中心北移,保定城由边塞军事重镇变为京畿重地。这一由“边城”到“腹地”的变化确定了保定城的军事与政治地位,成为“冀北干城,都南屏翰”,“北控三关,南达九省,地连四部,雄冠中州”的战略重地。而其军事、政治功能衍生出其独特的文化功能,尤其在清代,保定城在其20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更是呈现出军事、政治、文化功能“叠加”的特色,而为“畿辅首善之地”①。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城后,保定这座“京畿重地”开始以直隶首府的身份出现在历史舞台上。自雍正元年(1723)特授李维钧为直隶总督以后至清末,便一直沿袭着“直隶总督”督管直隶全省的制度。直隶乃天子脚下的畿辅重地,直隶总督位高责重。作为统率直隶全省的省会城市,其政府办公驻地的建设便成为当时保定城市政建设的重点,所以直隶总督衙署的修建成为重中之重。
(一)直隶总督衙署的选址
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其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最初设在了保定城西北隅的原参将署(即参将署改为巡抚署)。雍正元年(1723年)原直隶巡抚升任直隶总督仍驻节保定,原办公场所直隶巡抚署也就改为直隶总督署。但其办公环境与地理位置较偏僻,遂选中了城中心的参将署作为新的直隶总督署所在地。“特谕道经保定,相度督署基址。当城之中,得参军旧署辨方而定植焉。”①李培祜、朱靖旬修,张豫垲:《保定府志·卷三五·工政略一·公署》,清光緒八——十二年(1882-1886)。
清参将署故址最早追溯到元代,曾是元世祖时期顺天路总管府治中周孟勘于至元七年(1270)修建的“宣化堂”。洪武元年(1368)保定路改为保定府,此地便是保定知府的衙署。明永乐元年(1403)朱棣称帝,定都北京,基于保定京畿之地的重要性,将位于北京的重要军事机构大宁都司署迁到保定,这里又成为了明代的大宁都司署。直隶总督署的前身是明朝的保定府署、大宁都司署与清代的参将署所在地。
(二)由直隶总督署的修建看保定城政治功能的强化
省政府重要职能部门直隶总督署的建成使用,使得保定城的城市功能发生了重大的改变。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在此时期已超越了它的军事功能而逐渐成为主导性功能,保定城完成了从军事功能向政治功能占主导作用城市的转变。这种城市功能的转变极大地促进了保定城市的发展并使其在全国的政治影响力日益彰显。
一方面,随着省会的设立,省政府各部门都陆续迁入保定。据(1934年)《清苑县志》记载:以直隶总督署为核心的行政衙署在保定城有几十个,如布政使司署、按察使司署、分巡清河道署、新道署、保定府署、清苑县旧县署、清军同知署、水利通判署、理事同知署、藩经历署、藩库大使署、按司狱署、按经历署、府经历署、仓大使署、府司狱署、督院笔帖署、督标中军协镇署、左营督司署、右营游击署、前营游击署、右营守备署、前营守备署、后营守备署、保定营守备署、保定营参将署、把总署、军器大库、新设火药局、驻防城守尉、府学、县学、典史署、布政使署等。省衙、府衙、县衙、道衙、军事机构等“齐聚”此地,保定城有了健全的政治管理机构体系。
另一方面,自清康熙八年(1669)直隶巡抚由正定移驻保定到宣统三年(1911)张镇芳止,在历时240多年的直隶省会历程中,共计202任的直隶巡抚与总督在此任职。直隶总督署落成后,自清雍正八年(1730)直隶总督驻此至清朝灭亡(1911)期间,直隶总督的“政绩”颇为显著。李卫、方观承、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人的政绩更可以说是影响了中国的历史走向。如李卫建立的莲池书院,改革了中国传统的教育制度,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说奠定了中国近现代教育的基础。在其影响下,近代的保定涌现出诸多的才子文人,也促进了近代各种新式院校的建立;曾国藩、李鸿章、袁世凯等的练兵制度由此改革了传统的军事教育制度及军队作风,建立起近现代化的军队。他们制定的决策及实施的举措对整个国家的政治、军事、文化、经济产生过重要的影响,他们的功过是非反映着清朝的兴衰与荣辱。在他们的政治生涯中,他们的“政绩”反映的是清朝历史的轨迹。所以有“一座总督衙署,半部清史写照”的说法。
二、莲池书院与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
(一)保定城强劲的政治功能成就了莲池书院
莲池书院建立以前,保定城历史上曾有二程书院和上谷书院,主要讲授程朱理学,后废除。清立国后,政府实行“文治”政策,雍正十一年(1733)谕令在全国各省会建立书院:
“各省书院之设,辅学校所不及,初于省会设之。世祖颁给帑金,风励天下。厥后府、州、县次第建立,延聘经明行修之士为之长,秀异多出其中。高宗明诏奖劝,比于古者侯国之学。儒学寝衰,教官不举其职,所赖以造士者,独在书院。其裨益育才,非浅戡也”。[1]
直隶要建书院,作为省会城市的保定自然是建立书院的首选之地。当时任直隶总督的李卫按照清廷的谕令,按照传统书院建立的规制,选取了有着浓郁文化特色的古莲花池“建为书院”②莲池书院(河北·创建篇)(雍正十二年(1734)),《畿辅通志》卷一一四,光绪十年刻本,第61-62页。古莲池中有元代贾辅建的收藏图书万余卷的万卷楼、元代文学家郝经居住的“中和堂”,其格局仍然规矩齐整,适宜建立书院。。书院于雍正十一年(1733)五月动工至同年九月落成。建立书院所用资金除政府拨付的千两帑金外,还通过士绅捐助、捐养廉银、税收等补充,“共费金钱若干万,动支公费若干”。应清王朝的“文治”政策而开设的保定莲池书院,在直隶总督署落成四年后(1733)建成,是保定城又一具有时代特色的城市建筑。
莲池书院自雍正十一年(1733)到光绪三十年(1904),历时170多年,成为当时享誉全国的教育学术重镇。书院聘请学界名士来此执教,同时广置图书于万卷楼。此外,直隶总督那彦成在道光十年(1830),将家中收藏的唐宋元明以来的墨迹珍宝献出并镌刻于莲池书院南墙,定名为《莲池法帖》[2]32,以备学子临摹。书院既是教授学生之所,还是编纂书籍之处。如书院于同治十年修的《畿辅通志》,成为当今重要的历史文献。莲池书院当时吸引了八方学子慕名而来,以致出现弟子盈门,“以待学者,犹不能容,或怅然而返”①黄彭年:《莲池书院记》,清光绪七年(1881),《陶楼文钞》卷三,清光绪十六年刊本。的场面。清朝皇帝曾多次临幸巡视,在此赋诗作画,保定也因书院而名声远扬。
书院培养了诸多名人,如历任工兵刑礼四部侍郎王发桂、任新疆布政使(方志学家)王树楠、清末状元刘春霖、民国教育总长(版本目录学家)傅增湘、国学大师吴汝纶之子吴北江、代总统冯国璋等[3]。这诸多从莲池书院走出的文官武吏及学术名宿,他们对中国近代的政治和文化产生了重大影响。特别是在清末,黄彭年、张裕钊、吴汝纶等任书院院长时,为应对时势所做的一系列书院教育制度改革,使莲池书院文化成为当时中西跨(国际)文化交流的前沿。如在书院开设西文(英语)学堂、东文(日语)学堂、实行军队与书院的联合办学、收取日本留学生等等举措,不仅使书院“一变为储才研籍之地”[4],更是使书院成为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交流的研习、传播与交流之地。清末曾经在莲池书院留学的中岛裁之、宫岛勗斋(即宫岛大八)等日籍学生,求学期间他们拜张裕钊、吴汝纶等为老师,学习中国的书法、文化,与老师和同学们结下了深厚的友谊,亦将中国文化广播东瀛。他们回日后建立的东京同文书院、善邻书院等在传播中国文化时所形成的张裕钊书法艺术流派(张氏书法流派)影响深远,成为中日人民友好文化交流的历史见证。莲池书院在跨文化交流与教书育人方面被誉为“教育英才,德意之厚,与天同功。”②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清雍正十二年(1734),河北《清苑县志》卷五,1934年本。
(二)莲池书院文化的传播奠定了近代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主导性地位
“于政体(而)得”③李卫:《莲花池修建书院增置使馆碑记》,清雍正十二年(1734),河北《清苑县志》卷五,1934年本。的莲池书院不仅仅是一个政治产物,其独特的文化魅力吸引着众多学人来此学习交流,也给保定城带来了文化、政治、经济的繁荣。保定成为畿辅首善之区而得到清政府的器重与皇帝的多次“巡幸”,同时也使得莲池成为当时著名的风景名胜之地。慕名而来的文人墨客及游人来莲池游览也将莲池书院的文风带向全国,莲池书院成为当时盛极一时的书院。“莲池有名,是因为有莲池书院,莲池书院当时在全国是很著名的。”④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曾巡视古莲池时所说。文弘:《河北书院发展概况》,见河北省出版史志编辑部:《河北出版史志资料选辑》1990年第7辑,第96页。
莲池书院及由此形成的书院文化,不仅使保定城的政治功能地位得到了提升,也使得保定城的“文化教养”功能得以发展,并逐渐转变为城市的主导功能。
鸦片战争后,天津开埠,清廷于天津设立“三口通商大臣”以“专办洋务,监督海防”。为进一步巩固与加强北方海防,同治九年十月(1870年11月)清廷谕令裁撤三口通商大臣,“所有洋务海防各事宜,着归直隶总督经管,照南洋通商大臣之例,颁给钦差大臣关防。”⑤章开沅:《清通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4.》,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34页。即“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
“直隶总督兼任北洋通商大臣”职位的设立,扩展了原来直隶总督“三辅资为政,屏藩卫帝京。修文敷教化,讲武寄干城”⑥《畿辅通志》卷一一,《帝制记·宸章陵寝京师 行宫》第2册,河北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320页。的权能,使得军事、行政、河道、盐业及三口通商大臣的职权集于直隶总督一人身上,由此也出现了直隶总督公务在地域上的分化,既要于省城保定管理省属事务,又要于天津管理海防事务。为此,清廷专门做出了特别的规定,允许直隶总督于天津设立另一座直隶总督衙署,在保定、天津之间“轮驻”:
“(直隶总督)……将(位于天津的,笔者注)通商大臣衙署,改为直隶总督行馆,每年于海口春融开冻后,移扎天津,至冬令封河,再回省城;如天津遇有要件,亦不必拘定封河回省之制。”⑦章开沅:《清通鉴同治朝光绪朝宣统朝4.》,岳麓书社2000年版,第234页。
因直隶总督的“轮驻”,保定城的政治职能渐被削弱,由新崛起的天津取而代之。但此时保定城却没有因“政治功能”的衰减而一蹶不振,反而一度曾出现了人口增加、城市面积扩大、商业经济发达的短暂的“复兴”的景象。其内在的原因,就是莲池书院形成的文化教养功能的作用与影响。
时任直隶总督的袁世凯于1902年在直隶省设立了我国最早的省级教育机构——直隶省学校司,又于1902年6月21日(光绪二十八年五月十六日)向清廷上《筹办直隶省城学堂折》,建议:“先将保定旧有畿辅学堂,分别修造,约可容住生徒一百三四十人,上月初旬工竣。……就该堂附近地方,扩基添造学舍,……约以四百人为定额。”[5]这是利用近代保定莲池书院的影响力与保定城曾经建立的旧有学堂的设备及保定城的文庙等其他可资利用的设施创建新式学堂,开展新式教育。据《清苑县志料》记载清苑县(保定城)“大中小学于前清光绪二十八九年即行开办。”①《清苑县志料·教育》卷五,1912-1949年。光绪三十一年(1905)直隶总督袁世凯与清苑知县罗正钧又先后颁布了《兴学告示》,保定所建各类新式学校在清末十年(即19世纪末20世纪初)如雨后春笋般蓬勃发展。保定城形成了新式教育的体系规模:建立了如畿辅大学堂、直隶高等学堂、直隶师范学堂、保定军官学堂、直隶农务学堂等多所高等院校。所办院校,既有综合类院校,也有专职类院校。在专职类院校中以军事院校为学科最全,形成当时完整的军事教育体系。成为19世纪末20世纪初军事高等教育的典范。与此同时,配套的师范教育、中等教育、小学教育等学堂亦纷纷建立,清末新教育的局势改变了保定的市面状况,兴学之风盛起一直延续到民初,声望远播。
清末的保定成为新式教育改革的阵地,成为教育之城,这些都与保定城的历史文化底蕴、与莲池书院的书院文化风气密不可分。“古莲花池者,不仅为保定名胜之巨擘,且为北方文化之渊泉”[6],可谓“教育城”之称。
保定城文化氛围的洞开促进了保定城文化教养功能的提升,其文化教养功能开始超越政治功能占而一度成为清末保定城发展的新的动力源。到1913年,省会迁往天津,保定的政治功能衰落,但保定的文化教养功能仍然在支撑着这座城市的发展。有着“教育城”称谓的保定用历史印证了“文化是城市核心竞争力和城市核心内涵的观念”[7]。
三、保定军校与保定城的军事功能
(一)保定军校设立的背景
以军事防御起家的保定城在其悠久的历史中,军事功能历来是其传统的城市功能。清代以来保定为直隶省会,由单一的军事功能转变成为集军事、政治、文化多功能的叠加与融合的城市。
清末面对危难的国情,清政府为提高防御力量,倡导清末新政的“筹饷练兵”之策,以增强国力、提高士兵素质。这“筹饷练兵”之策便成为曾经接连出任直隶总督的曾国藩、李鸿章与袁世凯那“一脉相承的扩张自己势力的要诀”[8]。他们借为朝廷训练近代新式军队之机,实行地方的自我保护,在其当政管辖之地,构建军事设施和军事院校,培养效忠于他们的军事人才,以达到掌控兵权的目的。保定成了他们“拥兵自重”之地。清末的保定随即出现了一批具有军事色彩的建筑设施。如曾国藩的“练兵大校场”、李鸿章的“淮军公所”和袁世凯的“保定军校”等。
曾国藩在其“经理直隶省练兵事宜[9]中,“仿湘军成规”[9]进行直隶练军。于直隶增设招募马勇千人,使原有兵额超过万人。将其分为四个营,并分练马队、步队,各营制定营哨制度,制定底饷、练饷、出征加饷制度,为提高军队素质多次到“到大校场检阅直隶练军”,“到教场看新兵操演”①等,改变了当时直隶省部队“营务积年废弛,各营兵数多寡悬殊,号令不一”的状况[9]。
继曾国藩之后的李鸿章,亦将“练兵”作为首要任务。“相国之治军也,虽无事如临大敌”[10]104。他的治军理念是“以洋为师”、“文武结合”。如建立新武学校(保定行营将弁学堂、保定军校的前身),聘请莲池书院院长吴汝纶来作主持[11]2320。还在保定古城区的西南隅修建了一处用来纪念、祭奠在镇压太平天国和捻军战斗中阵亡的淮军将士的“淮军昭忠祠暨公所”(简称淮军公所),“立祠直隶以祀北征以来将士”。[10]105李鸿章、吴汝纶二人商定以淮军公所之名委托莲池书院为其官兵教授日语和西文,以培养专业外语人才。于“保定淮军公所岁修生息余款中,岁提四百金,开一东文学堂,专教皖人在北者子弟”[12],这样可“中、东兼习”、“遍览广学……皖人文武子弟,倘有造就成才者,其为功效,比淮军公所之经理得法,更为远大”[13]255-256。此事议妥,李鸿章、吴汝纶感到双方合作非常愉快,“傅相(李鸿章)欣然乐从。”[12]吴汝纶推荐其“于东学、西学皆已卓立”[13]255的日本弟子中岛裁之做教习。
曾国藩的保定练兵、李鸿章的保定淮军训练为清末袁世凯于保定建立军事院校奠定了良好的基础。
(二)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与保定城军事功能的彰显
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简称保定军校),为中华民国初期重要的军事院校,其创建是以清末袁世凯军事教育体系的建设为前提的。
1.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军事学堂、教育体系及其影响。李鸿章死后,袁世凯承继其衣钵。他在任直隶总督期间不仅仍“以练兵为当务之急”,还上奏清廷请求“设军政司于保定,分兵备、参谋、教练三处,……建议设陆军学堂,由小学而中学而大学,计十二年毕业。而先设陆军速成学堂,以应缓急之用”[14]99。他上奏朝廷说:
“近值朝廷振兴戎政,屡下明诏,殷殷以储才为急。上自贵胄学堂,下至小学堂,皆以次第开办,惟此项大学堂尚属阙如。惟按照定章,必俟中学堂暨兵官学堂次第设立,再行兴办。诚恐缓不济急,而高等教习,急切尚难多选,仍不能不借才异地,在京延订亦多未便。臣谨遵照练兵处、兵部奏定办法,略事变通,名曰军官学堂,即在保定省城设立。……一俟在京师设立大学堂,则此项学堂立即停办。现在暂借从前将弁学堂房屋先行开课。惟学舍逼窄,不敷应用,容俟筹定的款,再行建筑。”[5]
由此在袁世凯的精心设计下,北洋陆军将弁学堂、北洋速成武备学堂、陆军速成武备学堂等系列军事院校设于保定。在此基础上,光绪三十二年(1906),又在保定城东关外(今保定军校广场所在位置)的原北洋速成武备学堂校址上,开办建立了保定军官学堂。其“斋舍、操场以及仪器、自修各室,皆取各国新制,复延聘外国军学家,以广教材。而师范(一曰武师范)学堂、经理学堂、军械学堂亦附设于其中”[14]。
清末的保定军官学堂隶属于北洋军政司,段祺瑞任督办,宣统二年(1910)正名为陆军大学,宣统三年(1911)改为陆军预备大学堂,1912年陆军预备大学改为陆军大学,迁往北京。
袁世凯在保定构建的系列军事学堂,虽主观上为发展自己实力而积蓄军事力量,但客观上这些军事院校的建成使得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再次彰显。新建的这些军事院校为民初保定军校的建立奠定了扎实的基础。
2.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及其意义。保定陆军军官学校(1912-1923),1912年由中华民国陆军部创办,简称保定军校。民国陆军大学迁往北京后,陆军部于1912年10月20日在其原址开办陆军军官学校。历任校长曲同丰、蒋方震、王汝贤,教育长张承礼。建校规制仿照日本的陆军士官学校,实行军官养成教育,生源为陆军中学的合格毕业生。学制2年,前半年为入伍期,后一年半为学习期。课程主要有学科、术科、外文。其“所聘外籍教官,以德日为主体”①根据曾国藩同治八年的日记所载整理,见《曾国藩全集·日记三》,岳麓书社出版1995年版,第1591-1700页。,其所用教具如枪炮仪器及要塞壕垒模型“悉为德国著名兵工厂制造”,“其内部构造与真者不爽毫发。原以拆卸便利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它如炮弹炸弹,重至千余磅,小至数磅。凡数百种,遍陈十余室。”①这些稀世袖珍仪器是“校内最珍贵之物”①,“供讲堂观摩研究之需”①。
学校校园由本部、分部、靶场、大操场四部分组成,占地1500亩。1918年2月17日曾在保定军校教场举行了华北地区的第六届运动会[2]40,可见该校规模在当时属一流。
保定军校的建立,在中国军事史乃至世界军事史上都产生了重大的影响。它不仅是“清末袁世凯在保定创办军事学堂的延续和发展”[15],也标志着中国近代军事教育的高潮。它源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但“与清末保定军官学堂相比,保定军校‘其程度之增高,组织之完备,则诚不可同年而语’”[15]。它不仅从近代建设军事院校的规模上最为宏大,还以最为先进的军事管理与训练制度强化了中国近代的军事国防力量,走出了闭锁多年的中国军事封建堡垒,由非机械化兵器的刀枪剑戟的冷兵器时代向具有近代意义的机械化兵器时代迈进,使中国的军事事业迈向近代化而与世界军事接轨。保定陆军军官学校的建立,将西方的军事教育体制融入中国,成为当时国内领先的军事院校,标志着保定城军事功能在近代达到高峰。从北洋行营将弁学堂到保定军校,为20世纪的中国培养了大量掌握近现代军事技能的高级军事人才。其中将军就有一千多名。如靳云鹏、熊秉琦、齐燮元、吴佩孚、李景林、孙岳、孙传芳、王都庆、王
承斌、商震、陈调元、李济深、蒋介石、张群、杨杰、季方、叶挺、赵博生、董振堂、边章五、季振同、张克侠、何基沣、邓演达、蒋光鼐、陈铭枢、熊式辉、万耀煌、黄绍竑、黄琪翔、张治中、傅作义、余汉谋、刘文辉、邓锡侯、陶峙岳、唐生智、郝梦龄、罗卓英、周至
柔、秦德纯、顾祝同、陈诚、白崇禧、钱大钧、刘峙、上官云相、薛岳、乔明礼、张寿龄等,可谓“名副其实的将军的摇篮”[16]。清末民初保定城以新式军事院校为主的军事特色建筑,为“一代英雄咤叱之场”①伯龙:《记保定军官学校》,《北洋画报》1933年第19卷第914期。,也是近代保定城军事功能彰显的重要标志。
总之,透过“一文一武一衙署”这些近代保定城遗存的典型城市建筑,我们可以了解近代保定城所具有的政治、文化和军事等城市功能特性,并由此看出近代保定城市发展衍变的历史轨迹。
[1]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六:志八十一·选举一[M].北京:中华书局,1977:3119.
[2]河北省保定市地方志编纂委员会.保定市志:第1册[M].北京:方志出版社,1999:32.40.
[3]司存喜.保定文化资源概览:下册[M].保定:河北大学出版社,2009:897.
[4]灊山.谈谈以往的莲池(节录)[J].《河北月刊》,1936 (2).
[5]天津图书馆、天津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所.袁世凯奏议[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87:547,1320-1321.
[6]于振宗.重修保定古莲花池记[z]//河北《清苑县志》:卷五.1934:866.
[7]涂文学.近代市政改革:影响20世纪中国城市发展的历史性变革[J].学习与实践,2009(9).
[8]李宗一.袁世凯传[M].北京:中华书局,1995:99.
[9]赵尔巽,等.清史稿:卷一三二:志一百七·兵三·防军、陆军[M].北京:中华书局,1977:3932,3934.
[10]吴汝纶.合肥淮军昭忠祠记[M].//吴汝纶全集1.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104,105.
[11]巴斯蒂.从辛亥革命前后实业教育的发展看当时资产阶级社会政治的作用[C]//中华书局编辑部.纪念辛亥革命七十周年学术讨论会论文集.北京:中华书局,1983:2320.
[12]吴汝纶.与方伦叔.[M].//吴汝纶全集3.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256.
[13]吴汝纶.与李季皋.[M].//吴汝纶全集3.吴汝纶.施培毅,徐寿凯,校点.合肥:黄山书社,2002:255,255-256.
[14]张一麐.故代理大总统冯公事状[M]//来新夏.北洋军阀(5).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93:99.
[15]李金铮.论保定陆军军官学校[J].近代史研究,1995 (1).
[16]李麟.游遍中国:河北卷[M].西宁:青海人民出版社,2003:95-96.
【责任编辑 王雅坤】
Modern Zhili Province Capital Baoding City's Evolvement of Urban Functions——Tale Zhi Li Zong Du Shu,Ancient Lotus Pond,Baoding Military Academy as Examples
LIU Zhi-qin
s:This paper's research object is Baoding city in the Qing dynasty and the beginning of the Republic of China(1669-1917).This paper analyzes Zhi Li Zong Du Shu,Ancient Lotus Pond,Huaijun Hall,Baoding Military Academy which are time marks and brands of urban constructions'cultural heritage in Baoding city,which expresses the change of Baoding city's political trajectory and“Yi Wen Yi Wu Yi Ya Shu”functions.
City's building;Urban functions;Baoding city
K2
A
1005-6378(2015)04-0076-06
10.3969/j.issn.1005-6378.2015.04.015
2015-05-12
刘志琴(1964—),女,河北深州人,历史学博士,河北大学历史学院、华北学研究所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