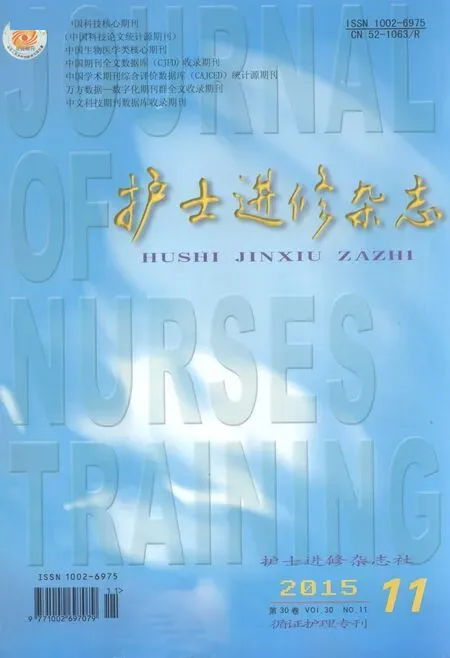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分析
2015-03-19王旖磊胡雁
王旖磊 胡雁
(复旦大学护理学院,上海200032)
循证护理(Evidence-based Nursing,EBN)是20世纪90年代伴随循证医学的发展而新兴起来的一门学科。作为一种科学的护理工作方式和工作理念,越来越受到护理人员的广泛重视。
循证护理实践是护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应通过开展循证护理培训,培养一批具有循证护理能力的临床护理人才[1]。而正确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成为指导人才培养的重要前提,笔者对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内涵进行分析,以期为构建适合我国国情的测评工具、培养高素质的循证护理人才提供借鉴。
1 能力的概念
能力,《辞海》[2]中定义为“通常指完成一定活动的本领。包括完成一定活动的具体方式,以及顺利完成一定活动所必须的心理特征。”吴晓义等[3]对能力的概念进行分析后认为,能力尽管是人们最熟悉、最常见的个体心理品质,但在学术领域中争议颇多,成为在实际应用领域中最难界定、最难测量的个体心理品质。一般而言,可从心理学视角、哲学视角、职业能力开发视角对能力进行多维度剖析。其中,职业能力开发视角的“能力”常与具体职位或工作情境相结合,由此发展而来的整合的能力概念目前正越来越得到多数人的认可[3-4]。整合的能力概念,最早由美国学者盖力(Larrie E.Gale)和波尔(Gaston Pol)提出,他们在《能力的定义与理论框架》一书中提到,“能力是与职位或工作角色联系在一起的,胜任一定工作角色所必须的知识、技能、判断力、态度和价值观的整合[3]。在该框架的基础上,曼斯菲尔德[5]提出,能力是指在具有相关压力和各种实际工作环境中,能够根据职业所要求的标准履行全部的工作角色。
2 循证护理的概念
2.1 循证实践 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源于循证医学。根据 Pearson L[6]的观点,循证实践可定义为在现有最佳证据的基础上做出临床决策的过程。Melny K等[7]认为,循证实践是一种以综合现有最佳证据、临床经验、患者价值观以及改善结局愿望为基础的方法论,或可理解为促进临床人员做出决策的一条途径。
2.2 循证护理的概念 循证护理,可定义为护理人员在计划其护理活动过程中,审慎地、明确地、明智地将科研结论与其临床经验以及患者愿望相结合,获取证据,作为临床护理决策依据的过程[8]。该定义已获得普遍认可。
2.3 循证护理实践的概念 通过文献检索,国内外一些研究者为了进一步表明循证实践在护理领域中的应用,已开始使用循证护理实践(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EBNP)这样一个词汇[1,9-10],为剖析循证护理与循证实践之间的关系提供了新的思考方向。
Pipe等[9]于2005年发表的文献中提到了“循证护理实践”的操作性定义,他们认为,“循证护理实践”应聚焦于患者的需求并提供优质照护,即在对患者实施护理过程中结合现有最佳证据及个人经验,并在最大程度上考虑患者需求。同时,他们还提出在循证护理实践中,护士常常需面临跨越证据与临床之间差距的挑战。
2.4 循证实践、循证护理以及循证护理实践的区别和联系 根据文献回顾及分析可见,循证实践的概念较广,包含了循证医学、循证卫生保健、循证护理等内容。由于循证护理在概念中尤其强调将证据应用于实践这一过程,循证护理(EBN)常常与循证实践(Evidence-based Practice,EBP)互 换 使 用[11]。Jennings等[12]提出,尽管这种互换很少遭到质疑,但是这可能导致误解。有学者对循证护理和循证实践的概念和内涵展开分析后表示,循证实践可能缺乏护理实践构成中的一些必要因素,例如循证实践对将质性研究作为证据存在质疑,在形成护理决策过程中缺乏护理及护理技术层面的哲学驱动力[13]。Kay Scott等[11]回顾83篇涉及循证护理或循证实践概念的文献后提取出11个核心元素,分别为识别研究、评估研究、将研究应用于实践、最佳证据、评估照护、解决问题、决策、应用专家经验、理论驱动、患者参与、过程。通过对这些核心元素的出现频率统计,结果显示:循证护理和循证实践均强调最佳证据的使用,并重视循证决策过程中结合临床经验的价值,相比于循证实践,循证护理还侧重以下三方面:(1)理论驱动实践(Theory driven practice):即如何将证据上升为理论指导实践。(2)患者参与(Patient involvement):体现护理专业积极促进患者权益的哲学观。(3)过程(Process):此过程不因做出决策而停止,而将延续至应用证据和持续评价环节。以上分析表明,循证实践、循证护理、以及循证护理实践在概念和内容上既存在关联又相互区分。
3 循证护理能力
3.1 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起源 近些年,为促进证据在临床上的应用,临床对培养具备循证护理能力人才的需求不断增加,“循证护理能力”一词开始被更多学者提及[1,14],正确理解循证护理能力的概念和内涵成为指导循证护理人才培养的重要前提。通过文献检索,尚未发现对“循证护理能力”概念权威或公认的界定,只在少部分文献中出现相关定义,例如 Maria Ruzafa-Martinez等[15]提出,循证实践能力是整合循证知识、技能、态度并建立任务,将之应用于临床情境的能力。与循证护理能力相关的名词包括循证护理实践能力[9]、循证实践能力[16]、循证能力[17]及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18]等。
笔者通过前期大量的文献阅读和思考,从整合的能力观出发并结合护理职业特点,初步将“循证护理能力”定义为:护士在完成循证护理实践活动过程中,为履行全部工作角色而具备的循证护理知识、技能、判断力、态度和价值观的整合。
3.2 循证护理能力的组成 由于循证护理来源于循证医学,在对循证护理能力组成进行分析时,参考循证医学能力组成的描述。例如加拿大McMaster大学循证医学中心[19]早在1992年提出开展循证医学需要临床人员具备新的技能,包括精确定义患者问题、有效的文献检索、严格的文献评价、选择最佳证据和实践模式、与同伴讨论以及将证据应用于患者,该过程可称为批判性思维训练(Critical Appraisal Exercise)。陈进等[20]认为,循证医学能力应涵盖循证临床实践五方面,即提出问题、查询证据、评价证据、应用证据和后效评价。通过检索,尚未在文献中发现关于循证护理能力组成的确切描述,仅在少部分文献中提及,例如Kessenich等[21]曾提出,循证护理能力涉及提出问题的能力、文献检索能力、评估能力和证据应用能力。笔者认为,需从概念或理论框架高度进一步指导对循证护理能力组成的探究并细化组成内容。Graham等[22]2008年提出的KTA模型(Knowledge to Action,KTA)为本文构建循证护理能力提供了理论指导,该模型由构建环(Knowledge creation cycle)和行动环(Action cycle)组成。知识构建环包括探究知识(Knowledge inquiry)、综合知识(Synthesis)、形成工具(Tools/producets)等步骤,再通过情景因素(Contextual factors)下,激发行动环。整体而言,该框架表明知识构建者和知识使用者在KTA过程中应保持密切合作[23],这一互动关系也符合将文献证据转化为临床证据的过程。据此,笔者初步提出循证护理能力包含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两部分能力,并进一步提出在评价循证护理能力的两部分即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能力时应区分其评价对象,例如知识整合部分更多针对研究者(可包括护理学者、研究生、高级实践护士等),可归纳为知识构建者(Knowledge producers);知识应用部分则更多针对实践者(可包括临床护理管理者、一线护士、高级实践护士等),可归纳为知识使用者(Knowledge users)。
需指出的是,循证护理实践,其对应的能力即循证护理实践能力应为循证护理能力中重要评价内容之一,其概念内涵渗透于知识整合和知识应用两个维度中,并在整合能力观的指导下与循证护理知识、技能、判断力、态度和价值观等共同组成循证护理能力。
4 影响具备循证护理能力的因素
Mcsherry等[24]提出,影响护理人员循证相关能力的因素可从态度(Attitude)、理解和自信(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支持(Support)三方面进行总结。根据这一提示,现就每一方面的分析分述如下。
4.1 态度 在整合的能力观中,态度(Attitude)是能力的重要组成之一,影响能力的进一步发展。Roy L等[25]提出,护理人员具备积极的循证态度或信念是开展循证护理的前提和基础。在我国,汪惠才等[26]通过对398名护士的调查发现,护士对循证护理的正确认识和积极态度,更有助于其正确、有效地制定循证护理决策。因此,护士具备积极的态度是开展循证实践、提升循证护理能力的重要前提。
4.2 理解和自信 护士对于循证护理的理解力及自信程度(Understanding and confidence)与其教育背景、经历有关。护理专业学历层次分级较多,不同学历层次对象由于在受教育程度、接受能力、基本技能上存在差异,导致护士在接受培训后对循证护理的理解、循证护理能力提高的程度上存在不同。Melnyk等[27]通过调查发现,尽管对循证护理持积极态度的护理人员比例较大,但由于缺乏循证护理知识,阻碍了循证护理实践行为的发生。故对于不同学历层次的对象,应根据实际情况开展不同程度的循证护理能力培训,促进循证实践行为。
其次,具备循证护理能力与对象的工作经验或经历存在一定关系,傅亮等[28]通过对512名护理学硕士研究生的调查中发现,年资较高、参与过循证相关研究或循证护理实践项目者,其循证行为得分显著高于其他对象。这可能与研究对象由于具备更多循证经历而对循证护理产生更多认识及更多自信有关。因此,在开展培训过程中,可考虑将护士、护生等纳入到循证相关研究或实践中,切身体验有助于提高循证护理能力。
4.3 支持
4.3.1 所在组织支持程度 护理人员所在组织是否支持循证行为、是否能够提供相关资源与循证护理能力的提升,以及能否持续实施循证实践行为有关。Retsas[29]通过对400名澳大利亚护士的调查发现,缺乏行政支持是阻碍开展循证护理实践的主要原因。由此,获得行政支持对于护理人员开展循证护理具有重要意义。
4.3.2 充足的时间实施循证护理 由于循证护理能力的提升需要一个过程,因此,是否具备充足的时间是影响因素之一。在国内,护理人员偏缺,护士工作负荷较重。万丽红等[30]通过对248名护士的调查显示,护理人员不足、缺乏时间是阻碍循证护理开展的第二位因素。因此,为了促进循证护理行为,提高循证护理能力,应大大提高床护比,给予护理人员更为充足的时间。
5 小结
伴随循证护理近些年在我国的快速发展,临床对于具备循证护理能力的高素质人才需求已日渐增加。在现阶段对循证护理能力这一概念进行梳理和分析,并提出可操作性的能力框架,可为构建针对我国国情的循证护理能力评定工具提供有效指导,同时,也为全面培养循证护理人才提供可行方针,以进一步推动循证护理在临床中的实践,为循证护理事业在我国的发展开拓新的高度。
[1]胡雁.循证护理实践:护理学科发展的必然趋势[J].中国护理管理,2013,13(1):3-5.
[2]辞海编辑委员会.辞海·缩印本[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1980:2013-2014.
[3]吴晓义,杜晓颖.能力概念的多维透视[J].吉林工程技术师范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06,22(4):1-5.
[4]Mei Ching Lee,TKaren L.Johnson,Robin P.Newhouse,et al.Evidence-Based Practice Process Quality Assessment:EPQA Guidelines[J].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2013,10(3):140-149.
[5]石伟平.职业能力与职业标准[J].国外教育资料,1997,(3):59-64.
[6]Pearson L.Providing the best for our patients:evidence based practice[M].Nurse Practitioner 26,2001,11(12):15.
[7]Melnyk B.M.,Fineout-Overholt E.Evidence-Based Practice in Nursing and Healthcare:A Guide to Best Practice[M].Wolters Kluwer,2013.
[8]胡雁.循证护理学[M].北京:人民卫生出版社,2012:10.
[9]Teri Britt Pipe,Kay E.Wellik,Vicki L.Buchda,et al.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Nursing Practice[J].Med Surg Nursing,2005,14(3):179-184.
[10]Kay Scott,Rob McSherry.Evidence-based nursing:clarifying the concepts for nurses in practice[J].Journal of Clinical Nursing,2008,18:1085-1095.
[11]刘晓华,张晋昕,成守珍,等.护理人员循证护理实践基本素质现况调查[J].中华护理杂志,2010,45(9):831-834.
[12]Jennings BM,Loan LA.Misconceptions among nurses about evidence based practice[J].Journal of Nursing Scholarship,2013,33(2):121-127.
[13]Ingersoll G.Evidence-based nursing:what is and what it isn’t Op-Ed[J].Nursing Outlook,2000,48(4):151-152.
[14]陈向韵.成人高等护理教学中循证护理能力的培养[J].护理研究,2004,18(1B):174-175.
[15]Maria Ruzafa-Martinez,Lidon Lopez Iborra,Teresa Moreno-Casbas,et al.Development and validation of the competence in evidence based practice questionnaire(EBP-COQ)among nursing students[J].BMC Medical Education,2013,19(13):1-10.
[16]Dragan Ilic.Assessing competency in Evidence Based Practice:strengths and limitations of current tools in practice[J].BMC Medical Education,2009,53(9):53-57.
[17]Holmboe E,Hawkins R.Methods for Evaluating the Clinical Competence of Residents in Internal Medicine:A Review[J].Annals of Internal Medicine,1998(129):42-48.
[18]Maureen P McEvoy,Marie T Williams,Timothy S Olds.Evidence based practice profiles:Differences among allied health professions [J].BMC Medical Education,2010,69(10):1-8.
[19]Evidence-Based Medicine Working Group.Evidence-Based Medicine A New Approach to Teaching the Practice of Medicine[J].JAMA,1992,268(17):2420-2425.
[20]陈进,李幼平,杜亮,等.医学生循证医学相关能力的评价[J].中国高等医学教育,2009(2):48-50.
[21]Kathleen Burr Oliver,Prudence Dalrymple,Harold P.Lehmann,et al.Bringing evidence to practice:a team approach to teaching skills required for an informationist role in evidence-based clinical and public health practice[J].J Med Libr Assoc,2008,1(96):50-56.
[22]Graham ID et al.,Lost in knowledge translation:Time for a map[J].Journal of Continuing Education in the Health Professions,2006,26(1):13-24
[23]Jo Rycroft-Malone.Models and Frameworks for Implement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 Linking Evidence to Action[M].Sigma Theta Tau International,2010:207-222.
[24]Chang AM,Crowe L.Validation of Scales Measuring Self-Efficacy and Outcome Expectancy in Evidence-Based Practice[J].Worldviews on Evidence-Based Nursing,2011,8(2):106-115.
[25]Roy L.Simpson.Automation:The vanguard of EBN [J].Nursing Management,2006(6):13-14.
[26]汪惠才,徐佩茹,胡娟,等.临床护士循证护理知识-态度-技能的调查分析[J].解放军护理杂志,2013,30(16):1-3.
[27]Melnyk B M,Fineout-Overholt E,Fischbeck Feinstein N,et al.Nurses'perceived knowledge,beliefs,skills,and needs regarding evidence-based practice_implications for accelerating the paradigm shift.[J].Worldviews Evid Based Nurs,2004,1(3):185-193.
[28]傅亮,胡雁,邢唯杰,等.护理硕士研究生循证护理行为现状及其影响因素研究[J].护理学杂志,2013,29(15):1-4.
[29]Retsas A.Barriers to using research evidence in nursing practice[J].J Adv Nurs,2000,31(3):599-606.
[30]万丽红,林细吟,梁嘉定,等.广东省循证护理现状分析及对策[J].中华护理杂志,2004,39(4):270-27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