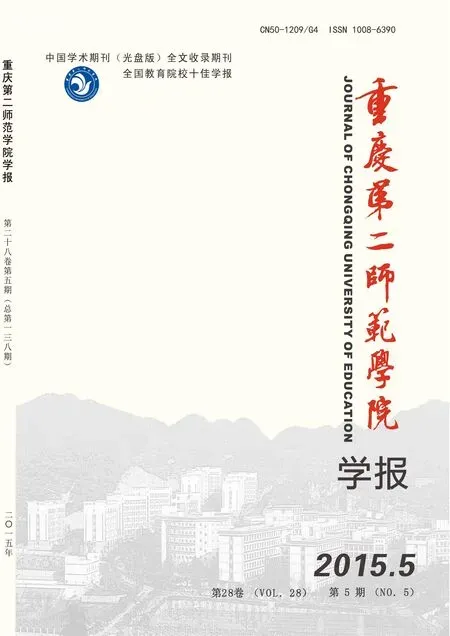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跨越对接存在的问题——渝东南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关资料的阅读与思考
2015-03-19赵心宪
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跨越对接存在的问题——渝东南地域文化民间信仰相关资料的阅读与思考
赵心宪1,2
(1. 重庆市文史研究馆;2. 重庆第二师范学院,重庆 400067)
摘要:“网络传说”不等于“民间传说”,“民间传说”有历史的规则,其所依存的地域文化应该有民间信仰与之对应。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跨越式直接对接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经意间忽视了民间信仰作为地域文化精神内核存在的历史价值。当代苗族蚩尤文化的传承和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对其祖先祭祀历史文化传统内在规律的遵循。
关键词:蚩尤传说;蚩尤文化;民间传说;民间信仰;祖先崇拜
收稿日期:2015-07-03
作者简介:赵心宪,男,重庆市人,重庆文史研究馆馆员,重庆第二师范学院教授,研究方向:中国现当代文学和少数民族文化。
中图分类号:G112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8-6390(2015)05-0037-06
一、《娇阿依传说》剧本与《雷神史话》比较阅读引出的话题
笔者近读题材源自网络贴吧“蚩尤传说”的原创剧本《娇阿依传说》,总有一种特别的感受,因为与阅读苗族祖先创世神话史诗《雷神史话》[1]所获得的崇高感比较,实在差异悬殊。为了更清楚地发现产生这种“特别感受”的问题之所在,笔者遂将两部与蚩尤传说相关作品的片段比对阅读的效果进行对照,问题产生的原因就渐渐清晰了(两部作品的节选文字读者可以自行查阅)。
湖南省花垣县滚岩寨世袭十四代苗祭司田德,不会汉话,不识汉文。他演唱的口述史诗《雷神史话》中的女雷龙雷鬼(幼时即小龙女),男雷神雷魅(幼时即小雷公),均为苗族神话人名。《雷神史话》顺次出现有关湖南湘西、渝东南可考的地名(苗语注音略去)很多,如湖南的常德、长沙、溆浦、麻阳、吉首、吉吼(吉首市乾州)、三叉(吉首市三叉坪)、等然(吉首市辖地)、官厚(凤凰县沃库乡)、堆整(凤凰县沃库乡)、高现(吉首市大兴寨)、高扁(吉首市小兴寨)、花垣、保靖、局迈(今花垣县长潭乡)、坪土(今花垣县吉筒坪)、茶洞(花垣县属)、坪块(重庆市秀山县)等64个之多。其中湘西地名60个,又集中于花垣县范围之内(共约37个)[1]。
与贵州松桃有关、可考,在《雷神史话》“踏地分域以及迁徙情况”部分,顺次出现的地名还有麻焦、盘信、间当、务卡、当烧、柳娃、柳補、云落、九江、平浪、蓼皋、斗贬、道西、卑中、马涧、当造、康金、板凳、板当、武浊、老堂、巴巴、咀贬、高嘎、亮亮、高巴、仁项、得将、占良、登现、代董、洛牛、仁广、孟溪等34个。[1]
口述史诗《苗族创世纪》上篇《雷神史话》出现的可考地名,集中于以花垣县为中心湘渝黔关联的武陵山区,而且,《雷神史话》“踏地分域以及迁徙情况”地名所及范围,在集中介绍贵州松桃30余属地之后,最终又回到湖南的花垣县,口述者突出花垣县在苗族创世史诗中所居核心地位的主体意识很清楚。但三苗、荆楚、荆蛮、武陵五溪蛮之后苗族的迁徙史是基本可证的。
《娇阿依传说》原创剧本,在文学想象中演绎苗族的历史传说,似乎“玩”得有些过了,展示文学原创灵气的同时,与苗族历史“隔”得有些离谱。如果说,蚩尤为炎帝之后,还有著名学者有关论述支持的话,娇阿依是蚩尤夫人的说法,就很难找到证据了。涿鹿之战蚩尤未死的苗族民间传说是有的,但苗族之名见诸史籍是在宋代。《娇阿依传说》原创剧本也道出“乌江画廊”景观的由来、关联上彭水历史悠久的“盐丹”矿产资源、阿蓬江、摩围山、阿依河传说,虽然一一都有当下自然、人文景观的实际对应,却显然不能成为黔中文化发源地的彭水——作为西南苗族聚居地之一历史由来的事实注解。笔者认为,以网络贴吧等形式流传的有关蚩尤传说等民俗文化题材的种种创作,都可以称之为“网络传说”,而“网络传说”与“民间传说”是不能随意等同的,“民间传说”有历史的规则,其所依存的地域文化更应该有民间信仰的对应。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跨越式直接对接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经意间忽视了民间信仰作为地域文化精神内核存在的历史价值。在笔者看来,当代苗族蚩尤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取决于对其祖先祭祀历史文化传统内在规律的深刻领悟与契合时代要求的遵循。
二、历史、传说、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的学理探讨与应用
古代中国,“历”“史”原是两个单音词。“历”属于动词,有经过、越过的含义;“史”的本义是记事,也是动词。后来专门担任记录、言事及掌握文书的职务称之为“史”,又进而把一切记言记事的册籍统称为“史”,如此这般,“史”由动词转换成名词。将“历”“史”二字组成一个词,还是近百年以来汉语发展过程中出现的事情。光绪二十八年(1902),江南书局为了适应当时开办新学的需要,编印了一部通史性质的教材——《历代史略》,推出“历史”一词,沿用至今。
史家认为,历史一词的广义泛指一切事物(包括自然界和人类社会)的发展过程,历史一词的狭义,则专指使用文字对于历史事迹记录和研究的成果,即史书。也就是周谷城先生《历史完形论》一书所说:“历史一名词,常代表着历史之客观存在与历史之文字的表现。”
“传说”一词作为一个科学名词,还是近代才有的,中国传统的说法应为“传闻”[2]。史学界对“传说”的定义有多种,著名史学家似乎都发出了自己的声音。
梁启超的《中国历史研究法》似最先从史学的视角解析“传说”的内涵:“当人类之渐起而形成一族属或一部落也,其部落之长老每当游猎斗战之隙暇,或值佳辰令节,辄聚其子姓,三三五五,围炉籍草,纵谈己身或先代所经之恐怖,所演之勇敢……等等,听者则娓娓忘倦,兴会飙举期间有格外奇特之情节可歌可泣者,则幡镂于听众头脑中,渝拔不去,辗转作谈料,历数而未已,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3]梁任公“其事迹遂取得史的性质”的判断,实际上强调了“古史传说”与我们记忆中光怪陆离的“鬼怪故事传说”、如今网络流行的“网络传说”本质上的区别。“古史传说”与“上古传说时代”的关联,是古史传说内容的特别界定。
徐旭升先生曾经对“传说时代”(上古)有一个通俗的说明。他说,世界上任何一个民族最初的历史,总是用“口耳相传”的方法流传下来的。在古文献中,保存有古代传说,而在当时尚未能有文字把它直接记录下来,用这种史料所记的时代,就叫做“传说时代”[4]。当然首先应该指称上古传说时代。中国的传说时代上限没有确凿的材料认定,下限定在盘庚迁殷以前(前1300年)已有文献可考。在文字的发展还达不到详细记录大段历史事实之前,先民们根据真实的历史人物、事件,经过加工(当有一定的虚构成分),通过口耳相传方式传播古代历史。这些口述的古史传说,多发生在氏族社会时期,常常与历史上的实有人物、事件和习俗有关。“这种关联,主要还不是表现为对风物和习俗的描述,更重要的是表现为以远古传说来解释风物和习俗的成因与流变。”[5]换言之,氏族社会时期历史上“实有人物”及其事件、习俗的历史文献记载,成为判断古史传说是否构成史学中的一部分,为史学认同的“古史传说”非常重要的前提条件。所以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一书,才会这样阐述“传说”与史学的生成关系:“传说对于史学的关系,恰恰在于它是远古的非史学的,它一方面提供了关于史学来源的最原始的资料,一方面又曾在相当长的年代里影响着文明时代的史学历史观点的发展和史学的面貌,史学要走出传说的投影,那是许多代史学家经过巨大的努力才能做到的。”[6]例如上古传说的黄帝、炎帝与蚩尤,是《史记》记载的历史人物,涿鹿之战是《史记》记载的历史事件,因为作为“上古传说”的记录,提供的是“关于史学来源的最原始的资料”——口述史的文字整理资料,有关它的见仁见智的阐释,影响史学家们难以痛快达成一致的历史共识(当然这也给文学创作带来广阔的原创审美空间)。这里特别强调的是,关于上古传说实质上就是口述史的观点,是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一书中论证过的史学见解:“传说,可以看作是最原始的‘口述史’,先民对于历史的记忆和传播,是通过这种原始的‘口述史’来实现的。这里说的传说,是最原始的‘口述史’,是指它所叙述的内容仍不能完全摆脱虚构的成分,但其中毕竟包含着不少真实的人物和事件,即使是虚构的成分,也并不是完全脱离历史的奇想。”[7]本文第一部分所引《苗族创世纪》上篇的《雷神史话》,应该是一个典型的例证;而《娇阿依传说》中的蚩尤传说故事,则是有点“完全脱离历史的奇想”了。
白寿彝先生《中国史学史》一书对“传说”还有一个界说,是值得我们进一步体会的:“远古的传说,主要是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8]这个判断是我们阅读少数民族历史文化资料非常重要的提示。白先生所说的“氏族社会里英雄人物的故事”,包括上古英雄人物率领部族对自然进行斗争,在原始农业等生产上维持生计的种种故事、生活习俗、社会风物,也包括氏族部落间原始战争中的英雄故事。这样,“远古的传说”,反映了社会生活的一部分,是氏族社会中“原始先民传述历史知识的最古老的形式”。或者说,上古传说中的英雄人物,是传说时代历史内涵中人物、事件、风物、习俗认识四要素之首。传说时代的历史,实际上成为上古英雄率领各自的部族“创造”生存可能的口述史。蚩尤是九黎部族时代的英雄,三苗时代、荆楚、荆蛮五溪蛮武陵蛮时代,所谓“生苗”“熟苗”时代的英雄是谁?又依据什么历史线索能够找到呢?这个问题在下文中将作适当分析。
由历史、传说而成为民间传说,会经历“质的转换”,一言以蔽之,由“史实”性质的历史内容,在发散思维推动下,艺术想象的自由飞腾中,变形、夸张、附会而成为民间审美的言说故事,成为民间文学中的历史、传说题材。查百度百科“民间传说”词条[9],有关解释概述如下:
关于民间传说学界存有两种看法。广义民间传说,俗称“口碑”,是一切以口头方式讲述生活中各种各样事件的散文叙事作品的统称;狭义民间传说是指民众口头创作和传播中描述特定历史人物或历史事件,解释某种地方风物或习俗的传奇性散文体叙事。
借鉴目前“传说学”的理论研究成果,可将上述有关民间传说概念的内涵界定,完善表述为如下文字:民间传说是围绕客观实在物,运用文学表现手法和历史表述方式构建出来的,具有审美意味的散文体口头叙事文学。在民间传说种种创作中,“客观实在物”始终处于核心地位,因此人们又将这个“客观实在物”,称为“传说核”。“传说核”可以是一个历史人物、历史事件,也可以是一个地方古迹(即“风物”中的一类——引者)或风俗习惯。因此,民间传说既不是真实人物的传说,也不是历史事件的纪实(其中可能包含真实历史的某些因素),而是民众的艺术创作、艺术产品。
民间文学的民间传说,采用历史素材,居于“传说核”的历史要素在民间传说作品中,是化身为历史表述方式给作品的文学表现手法导向的。或者说,民间传说围绕的“客观实在物”,是在与之对应的民间信仰的精神支撑下,才可能具备“传说核”的本质规定。也就是说,民间传说在不丢失与民间信仰的关联中,才可能既体现“民间”的审美话语风格,又表现出民间认同的民族精神特质。上文所引《苗族创世纪》上篇《雷神史话》如果改编为散文体形式,应该可能是具有“传说核”民间传说的例证,而《娇阿依传说》中的蚩尤传说故事,似乎已经丧失成为“传说核”的基础条件了。
重视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不可割断的深层联系,需要彻底破除创作认识魔障,就是单纯、习惯,又无所顾忌地将民间信仰视为“民俗”题材,迎合流俗意趣创作民间传说。李俊领的《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开篇就尖锐指出相关问题之所在:“民间信仰视为民俗,是当前学界普遍认可的看法。但民俗概念在解决中国民间信仰方面存在自身难以克服的局限。具体而言,传统中国民间信仰是一种多元并存的体系。其中有些信仰属于纯粹的民间习俗,与官方礼制无明显关联;有些信仰属于官方政治信仰或宗教信仰的衍生物;而有些信仰属于官方与民间共有的信仰;还有些信仰属于官方祭祀礼仪与民间祭祀习俗的综合体。简单地以一个西方舶来的民俗概念,界定传统中国民间信仰,难免力不从心。中国民间信仰,在国家礼仪制度发生显著变化时,也没有完全割断礼和俗的关联。应从风俗和礼俗的本土角度和话语看待民间信仰。”[10]这样的论断,解说民俗概念与中国民间信仰内在复杂性的扞格抵触,虽然很精彩,却是小众化的高头讲章。李文还步步深入提出四个问题:(一)“民间信仰是民俗还是风俗、礼俗”;(二)“民间信仰是不是迷信”;(三)“民间信仰是不是宗教”;(四)“如何对民间信仰进行科学研究”。这有助于我们剖析“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不可割断的深层联系”的论述,集中在李文第一部分最后的理论阐释和实例分析的应用中。作者指出:“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的大部分现象都可以归为礼俗。即近代中国民间信仰,在总体上是一种民俗现象,既有礼制的规范(或影响),又有民间的习俗。仅将其称为民俗,则在形式和内容上忽略了礼的一面,容易割裂礼教与俗化的内在联系。近代民间信仰的鬼神、祖先、祖师等谱系中,有较大影响力的部分,几乎都可以在官方祀典式惯例中找到根据。比如城隍、关帝、妈祖、泰山娘娘(碧霞元君)等民间广泛信仰的神灵都是如此。从祭祀的角度而言,尽管清代朝廷祀典总计78种,但朝廷通过封赠、赠额等方式认可的民间种类(祖师)谱系十分庞大,而且其中相当一部分被划入地方祀典。与之相应,一些不被官方认可的民间信仰现象往往遭到查禁,比如白莲教的神灵信仰。近代民间信仰作为民俗还有礼俗的一面。”[10]
《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第一部分的实例分析,就是北京妙峰山信仰作为兼有礼与俗综合民俗现象的解剖。田野调查所见,武陵民族区10万平方千米的人文地理空间,民族“民间信仰的鬼神、祖先、祖师等谱系”非常复杂。各少数民族“大杂居,小聚居”的生存格局,用西方的民俗学理论审视,总是感到特别困难。《重庆苗族的迁徙》一文,关于“渝东南苗族的定居”,有这样的阐述文字:“渝东南苗族为‘古三苗遗种’、‘盘瓠之后’,而世居土著、移民迁徙、避难落籍、募民垦荒等,也不失为苗族的来源。清《皇朝经世文编》载《郭青螺文集》云:‘考红苗蟠据楚、蜀、黔三省之界,即古三苗遗种也。’彭水、黔江、酉阳、秀山,正处在楚、蜀、黔三省交界处,说明此四县居住的亦多‘三苗遗种’。《水经注》卷37载:‘今武陵郡即盘瓠之种落也。’《后汉书》云:‘其在黔中、五溪长河间,则为盘瓠之后’。彭水、黔江、酉阳、秀山四县为古黔中、五溪地。所以,《方舆胜览》卷60说:绍庆府人皆‘盘瓠子孙’。湘西流传的《迁徙歌》中云:苗族从‘水乡’迁入武陵五溪地区后,‘一支去往平西(今秀山县——原注),一支去酉阳。’(《苗族史》1992年版85-86页)这两支苗民源于三苗。”[11]历史的复杂性在于,“世居土著、移民迁徙、避难落籍、募民垦荒等”成为渝东南苗民来源的依据,是数千年跨越巨大时空中形成的武陵民族区渝东南“大杂居,小聚居”的基本史实。特别是明清时期多次大规模“赶苗拓业”,自上而下国家意识名义推动的大移民,地区各民族文化融合进程的强力推进。《水经注》《后汉书》《方舆胜览》等典籍文献,甚至湘西流传的《迁徙歌》,有关渝东南苗民“源于三苗”“三苗遗种”的结论,当下还需要艰苦的田野调查科学认定。其中核心调查内容之一,就是渝东南“民间信仰的鬼神、祖先、祖师等谱系”文化遗存的现状。因为,言之凿凿的民间信仰存在,才是各民族精神个性辨识的最重要依据之一,才是各民族民俗文化多样性的具体特征之所在。
三、蚩尤传说在渝东南的传播与苗族聚居村落田野调查民间信仰的现状
上文分析口述史诗《苗族创世纪》上篇《雷神史话》出现的可考地名,有“集中于以花垣县为中心湘渝黔关联的武陵山区”的轨迹特点,而且,《雷神史话》“踏地分域以及迁徙情况”地名及其所及范围,“在集中介绍贵州松桃30余属地之后,最终又回到湖南的花垣县”,口述史诗《苗族创世纪》提供的苗族迁徙史信息的历史价值自不待言。这个信息加上20世纪80年代以后对苗族始祖蚩尤的广泛认同,相关民间信仰指向有了明确的核心内涵。山东大学民俗研究者指出,花垣县新世纪以来,正是因为三方面社会力量的愿景合成,才形成武陵民族区蚩尤文化建设蓬勃出新的现代传播态势的[12]。
地方精英知识分子,是让蚩尤传说在花垣县“参与到地方经济、文化建设中的主体”。苗族著名学者龙伯亚、李廷贵、龙炳文、伍新福、龙海清都发表过相关的论文,如龙海清的《关于给蚩尤公正历史定位的几个问题》、龙文玉等的《苗祖蚩尤与湘西苗疆——关于湘西苗疆的新认识和新建议》等文,很有影响。因为学者们发现,汉文献古籍所载与湘西地方民间信仰所载所言的蚩尤,存在很多不同,蚩尤的苗祖地位是首先应该正名的。与此同时,苗族同胞自身寻求一个始祖,以唤醒族群七次大迁徙之后,已经开始“微弱的民族意识和认同感”,历史也可以“用故事的眼光审视它”[12]以达成族群的民间信仰诉求。地方政府顺势而为,“在传说需要的地方风物支持下,保证其真实性和鲜活性;普通民众更需要借助外物的力量去追忆或者铭记。”近十年来,花垣县地方风物建设可谓一年一个样:
2000年,花垣县人民政府修建古苗河蚩尤文化园。2001年8月7日,花垣县举办中国花垣苗族赶秋节,塑巨型蚩尤塑像。2002年,古苗河风景区被批准为湖南省级风景名胜区。其中的三处景点“雄狮迎驾”“蚩尤巡疆”“天兵天将”依据蚩尤传说的内容设计。2008年10月23日,花垣县举办“花垣·边城边区民族团结联谊会暨苗族服饰、传统工艺品、特色饮食展示会”;活动中与凤凰县、保靖县、吉首市民族局和重庆市秀山土家族苗族自治县民宗委、贵州省松桃苗族自治县民宗委联合签署了《湘黔渝边区蚩尤文化学术研讨会协作书》,蚩尤文化的学术研讨正式进入到区域民族工作的日程中来。2009年2月3日,起草《中国·边城民族团结暨蚩尤文化研讨会实施方案》(征求意见稿)。最后决定,由省民委,省文化厅,州委、州政府主办“2009’中国·湖南(花垣)首届苗族文化艺术节”,由中国民俗学会、湖南省苗学会主办全国蚩尤文化研讨会。2009年6月9日,花垣县下发《关于成立“2009’中国·湖南(花垣)首届苗族文化艺术节暨全国蚩尤文化研讨会承办、领导小组的通知”(花办[2009]32号)。2009年8月1日,苗戏拟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同月又拟将“苗族古歌”(苗族古老话)列入国家级非遗名录,地方政府认为,古歌是一部有关蚩尤的口碑史。2009年10月26-28日,全国蚩尤文化研讨会正式召开,与会者参加蚩尤文化花园蚩尤公祭大典。2010年4月13日,花垣县拟将蚩尤传说申报进入第四批国家级非遗名录,申报资料包括《板塘苗歌选》《苗族古歌》和苗族精英学者后期编撰的种种专门著作。[12]
这里值得提及的武陵地域文化传播资料,还有花垣县民族事务局“十一五”时期有关文件中关于促使“蚩尤文化研究中心落户花垣,使之成为‘文化研究区域中心’,做大蚩尤文化的设想”。与花垣县同在武陵民族区的渝东南,蚩尤文化新世纪传播的路径及其影响当是不言自明的。笔者很认同关于蚩尤文化传播的如下见解:“这不是一个纯粹的学术问题,而是意识形态建构或者文化建设问题,属于性质世界和意义世界的范畴。”[13]蚩尤传说的存在,在武陵民族区的意义世界已经拥有不可漠视的现实价值。现在紧迫需要解决的问题,不是追问蚩尤传说在武陵民族区的意义世界的存在价值,而是从蚩尤传说发展扩大为社会各个层面广泛传播的蚩尤文化,蚩尤信仰民间形态的现状分析可能会得出什么样的结论及如何积极应对。民间传说与民间信仰的生成关联,是地域文化生成历史中始终绕不开的关键问题。简言之,没有民间信仰的中介文化形态存在,地域文化繁荣的最终目标将成为空想。
专家指出,地域文化传统中“民间信仰的关键要素,是人们定义民间信仰的主要方面——既是心理活动,也有行为表现拥有特定的神灵系统,也有秉持这种神灵信仰的信众”[14]。民间信仰作为一个完整的现代知识体系,自上而下由三个层面构成:1.神灵体系;2.社会组织系统;3.节庆庙会等仪式活动。通过这三个层面结构内涵的具体分析,可全面认识作为地域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的内在发展规律。因为,新世纪以来“作为社会历史和文化现象的民间信仰”,越来越受到学界的特别关注,“关于它的历史发展过程中的性质、地位、兴盛和衰落,成为宗教学、社会历史学、文化人类学和民俗学等多学科热点问题。从氏族部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民间宗教或民间信仰,自成生成演变的历史脉络”。[13]民间信仰作为文化中介的社会文化功能,在于其“具有历史内涵的多重性,植根民间的稳定性,口头叙事的多样性,文化取态的多元性,并存选择的灵活性”,因为它在特定地域文化的形成过程中,“既凝聚了人们敬天礼地的信仰根基,也满足了人们寻根问祖的需求”。[13]蚩尤传说中蚩尤信仰的历史与现实是应该设法去认真了解的。上古时代的蚩尤传说有一个地域文化发展中民间神话化的自然过程,在当下中国却整体跨越“从氏族部落社会到民族国家的不同历史阶段”,而民族国家的现代化历程,又将其迅速推入现代文化传播的世界语境中,其“文化层垒”的“速成”性质,竟将上古时代的传统文化与当下社会的现代文化“无缝”直接对接。笔者以为,对于这种复杂的文化现象,不可掉以轻心。近年有关武陵民族区民间信仰的两个田野调查研究报告,告诫我们这项工作持续开展下去的确刻不容缓。
一个田野调查研究报告,是向轼的博士论文《“苗疆”边缘地带族群性的维系与流变——重庆秀山半沟村苗族的个案调查》[15]。论文介绍了田野调查点选择的主要原因:“重庆市秀山县梅江镇半沟村,是重庆唯一至今保留着完整的苗族文化和苗语的村子。位于湘鄂渝黔交界处,距离历史上苗族聚集的中心地带——湘西和黔东南部只有大约五十公里的车程。半沟村约一千五百人,苗族村民约占百分之六十。其余村民皆为土家族和汉族。苗民迁徙而至大约有五六百年的历史,自称红苗,先从江西迁酉阳,然后再迁徙至此。其迁徙历程和在村里生活的历史充满了传奇色彩。这个村子跟小茅坡营村的不同之处在于,可以用‘族群半岛’来形容它的地理和社会环境,村子周边多数相邻地带都围绕着其他民族,但是却跟历史上苗疆腹地、苗族活动频繁的贵州松桃苗族自治县相隔不远(约二十公里),保持着紧密联系。据说,他们还跟松桃有着血缘关系。半沟村苗族本色没有丧失,为了本民族的发展,在族群内部,也延续着很多文化事项,如跨地域的‘踩花山’‘赶秋’‘牛王节’等,甚至苗族的各种风俗习惯都隐藏着一种深层的维系纽带。”关于半沟村苗族村民“深层的维系纽带”,惜乎论文最终没有提供答案。
有关半沟村民间信仰的祭祀活动,向博士的论文介绍甚详:“半沟村祭祀活动中,对祖先的崇敬和信仰无时不在。对祖先的祭祀意识,不仅在现实生活中处处体现,还通过一些仪式来强化。有生活式祭祖和还原式祭祖。生活式祭祖就是‘祭家先’,还原式祭祖就是‘打棒棒猪’。这两种祭祀活动都在室内的固定方位举行。”四月八祭祀活动却有苗族民间信仰的特别价值:“祭祀是为了祭祀民族英雄。一说是亚努,战死在贵阳的苗族首领。另一说是祭祀乾嘉苗民起义的松桃苗族领袖石柳邓。第二说因为四月八是牛的生日,把常年耕地的牛放假一天,洗澡还要系上红带子或红花,牵到一起来让它们打斗,人们也围着牛一起联欢。两说半沟村苗民都认可。”如今半沟村四月八活动,已经成为“各种文化意义的融合”,民间信仰精神价值取向泛化了:1.有祭祖、祭英雄的意识;2.牛的生日纪念;3.男女择偶的良机。关键是蚩尤信仰,无论是形式或者内容的一点蛛丝马迹,在半沟村的现实生活中实际上没有了。事实上,支配半沟村苗族、土家族、汉族民间信仰的共同活动,已经转变为土地庙祭祀。
另一个田野调查研究报告,是刘欣的硕士论文《作为文化经济、政治资源的蚩尤传说——以湖南省花垣县为例》[12]。作者2011年10月11日至16日,到湘西花垣县排碧乡岩锣村经历三天的田野调查,访谈过5位村民。石长山,91岁,曾就读国立11中高二部师范班,解放前在小学任教,随后参加过抗美援朝战争,“听说过乾隆时期农民领袖石贵宁的传说,因为这与岩锣村民由来有关。石岚音,78岁,由吉首小兴苗寨嫁入岩锣村,在吉首和花垣都生活过,没有听说过蚩尤的事情。石民德,79岁,石岚音丈夫,土生土长的岩锣村人。每年参加集体祭祖,苗语为“阿剖兜懂”(即各路大仙的总称),从未听说过蚩尤。老巴代,88岁,苗族法师,祭拜祖先都是太上老君那里发展而来。太上老君养了一个女儿,他的女儿又有很多姊妹,这些姊妹就是祭拜的祖先。石福生(原村支书),认为苗族的始祖就是蚩尤,说了一个关于蚩尤的传说故事:“蚩尤战败后,就沿着长江被赶下来,一路经过十一个省,一直南下到武陵、吉首,再后来由泸溪而上,就成了苗民的祖先。”石福生是村里的说唱艺人,他是在28岁当上艺人之后,才逐渐了解蚩尤的。
武陵民族区上述两个有关蚩尤信仰的田野调查研究报告要点,可以得出的结论不免让我们有些担心。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的强力推进,没有认真注意蚩尤信仰民间遗存问题的解决,蚩尤文化离开民间文化根基所在的地域文化源头活水,还能持续传播下去吗?反思历史,可能找到创生思路内在规律的指点。明代以来,“儒家行为规范在民间信仰当中也得到肯定,民间信仰的世界观与上层阶级的意识形态有很多重合之处,传统礼教把祭礼当作教化的手段,强化宗法制度中‘敬天法祖’的价值取向,民间信仰在许多方面以这种血缘根基的宗法制度为基础,都属于多神信仰,与农业社会的生活联系紧密。以天地崇拜为中心的自然崇拜,都将祖先崇拜作为核心内容。”[14]蚩尤信仰的精神实质,不就是苗族祖先崇拜的原始心理意识的表征吗?这应该被视为武陵民族区蚩尤文化的民间信仰原点。彭水郁山的蚩尤庙及其传说,应该不会早于明清时期,“庙”的建筑形式,已经成为多民族文化融合的产物。与苗族祖先祭祀的关联,是值得深入研究的问题。
总之,“网络传说”与“民间传说”是不能随意等同的,“民间传说”也有历史的规则,其所依存的地域文化更应该有民间信仰的对应。从蚩尤传说到蚩尤文化跨越式直接对接出现的问题,就是不经意间,忽视民间信仰作为地域文化精神内核存在的历史价值。在我看来,当代苗族蚩尤文化的可持续发展,在于其祖先祭祀历史文化传统内在规律的深刻领悟与契合时代要求的遵循。
参考文献:
[1]完班代摆.松桃印象[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8:181-183.
[2]潜明兹.中国古代神话与传说[M].天津:天津教育出版社,1991:4.
[3]梁启超.中国历史研究法[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8:6.
[4]徐旭生.中国古代的传说时代[M].桂林: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03:22-23.
[5]陈虎.论远古传说与史学的产生[J].山东社会科学,2002(2):99-104.
[6]瞿林东.中国古代史学批评纵横[M].北京:中华书局,2000:195.
[7]瞿林东.中国史学史纲[M].北京:北京出版社,2005:117.
[8]白寿彝.中国史学史[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6:129-131.
[9]百度百科.民间传说[EB/OL].(2014-05-19)[2015-06-15].http://baike.baidu.com.
[10]李俊领.近代中国民间信仰研究的理论反思[J].南京社会科学,2015(1):150-156.
[11]重庆苗族的迁徙[EB/OL].(2012-05-14)[2015-06-15].http://wmz.cq.gov.cn/llyj/5478.htm.
[12]刘欣.作为文化经济政治资源的蚩尤传说——以湖南省花垣县为例[D].济南:山东大学硕士论文,2014:34.
[13]尹虎彬.传承论的民间信仰研究[J].西北民族研究,2014(2):46-61
[14]赵世瑜.狂欢与日常——明清以来庙与民间社会[M].北京:三联书店,2002:13
[15]向轼.“苗疆”边缘地带族群性的维系与流变——重庆秀山半沟村苗族的个案调查[D].武汉:中南民族大学博士论文,2012.
[责任编辑文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