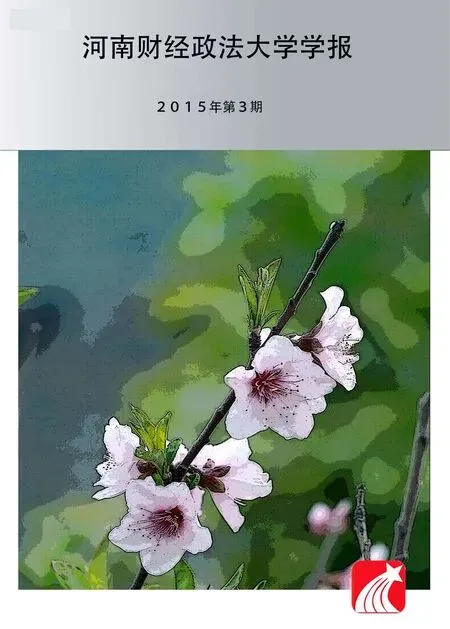海洋刑法学视阈下船旗国刑事管辖原则辨析
2015-03-17阎二鹏
阎二鹏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海洋刑法学视阈下船旗国刑事管辖原则辨析
阎二鹏
(海南大学法学院,海南海口570228)
以海上国际犯罪作为研究对象的海洋刑法学研究范式之提出意在突破传统教义刑法学的研究框架。从刑法之外研究刑法,使得从教义刑法学向一种普适刑法学的转变成为可能;作为国家主权体现的刑事管辖权在实然层面上会面临冲突是一种客观事实,不能将其作为否定船旗国刑事管辖是属地管辖原则之补充的理由;船旗国管辖原则只有在刑事司法管辖权层面下有其独立存在之必要,相应的,我国刑法之规定并无修改之必要。
海洋刑法学;船旗国管辖;刑事司法管辖权
传统刑法学者囿于知识结构上的局限,船旗国刑事管辖原则并未单独作为问题提出,但在海洋法与刑法的交叉学科背景下,这一问题并非不证自明,如何突破传统刑法教义学研讨的桎梏进而提供一种新的思考方向,实对当下学理及实践层面具有积极意义。
一、海洋刑法学之研究范式的证成
我国虽为海洋大国,拥有漫长的海岸线与广袤的海域,但受到存在数千年的“陆权思维”的影响所形成的大陆文化主导型社会,使海洋文化一直处于边缘地位,亦无法生发出与海洋文化相应之海洋文明①严格来说,海洋文化于我国历史上也绝非难觅其踪迹,“由于海洋的广袤,即使在以农耕或游牧为主的自然经济社会,其沿海地区居民也会发展出一定程度的海洋文化,只是不在所属社会中居主导意识形态。”(参见庄国土:《中国海洋意识发展反思》,载《厦门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2年第1期)。时过境迁,进入21世纪,海洋之于各国经济、社会发展之重要性已不言而喻,在“海洋强国”战略顶层设计的推动下,学理上对海洋之研究亦成为热点领域,“海洋意识”“海洋经济”“海洋文明”等成为共识性概念而为人们所接受,在此种大背景下,针对海洋权益的法律保护问题亦被学界所关注,渐成学理上的研究热点。此种研究态势之形成可归结为两方面的原因:一方面,自20世纪80年代以来,我国已成为一个高度对外开放和依赖外贸的国家,而且是典型的出口导向型和资源进口型国家,货物出口对GDP的贡献率一直占有很高的比重,而海运则为国际贸易中最主要的运输方式,我国绝大部分进出口货物均是通过海洋运输完成的,海洋俨然成为国家经济发展的命脉;另一方面,海上犯罪伴随开发利用海洋资源发展海洋经济应运而生,作为高度依赖海洋外贸运输的我国自然难以幸免,作为中国海洋运输主要通道的马六甲海峡,则是危险中的危险,据统计,每年海盗给全球经济带来的损失是160亿美元,其中仅马六甲海峡地区海盗袭击的损失就高达40亿美元,猖獗的海盗袭击活动将使这条世界上最繁忙的航道变成最危险的海峡之一[1]。海上犯罪不仅对我国海上运输安全造成了直接威胁,也直接影响了我国的经济安全,如何对此类犯罪制定行之有效的刑事规制对策在学理上必须做出回应。
海上犯罪的危害性及惩治的迫切性虽获得了包括我国在内的各国学者的共识,但在传统刑法学视阈下,其并未占得一席之地。与传统刑法问题相比,针对海上犯罪的研究明显薄弱。这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刑事立法上的滞后。目前的刑事立法明显侧重于陆上犯罪的法律规制,而较少从海上犯罪的自身特性出发寻求有针对性的立法规制对策。涉海犯罪的特性,决定了其与陆地犯罪“在证据的收集和保全上非常困难,在刑事犯罪的证据使用和犯罪起刑点上都不宜直接援引陆地上的刑事法律规范”[2]。在定罪的构成要件要素设定以及量刑的裁量基准上应与陆地犯罪进行区隔,从而实现罪刑均衡。但目前的刑事立法并未对涉海领域的犯罪独立进行规定,最典型的如海洋环境污染犯罪,1997年新刑法中虽然就已经规定了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从而囊括了污染土地、水体、大气三个方面的环境污染犯罪行为,但从1997年新刑法颁布实施之后,尚无一例因海洋环境污染事故而构成刑事犯罪的案件,司法实践中主要依靠行政处罚制裁海洋环境污染的现象已成为不争的事实。《刑法修正案(八)》虽对重大环境污染事故罪做出了重大调整,将其从结果犯转换为行为犯或危险犯,体现了刑事立法的进步意义,但遗憾的是仍未将污染海洋环境的犯罪与其他污染环境犯罪进行区隔。造成上述司法适用困境的原因,除了司法人员主观认识偏差之外,恐怕刑事立法设置本身的缺陷亦不可忽略;除此之外,我国刑事立法未能很好的与我国所签订之国际条约相衔接亦广为学界诟病。由于国际条约中所规定的犯罪类型在实践中尚需通过各国国内立法的形式得到确认,且国际条约中所规定之犯罪仅有犯罪行为之规定,没有刑罚之设定,因此,国内法之具体规定则成为适用国际条约的关键。目前,对于我国缔结或者参加的国际条约中所涉及的海上犯罪,有相当一部分犯罪行为在我国刑事立法中并未得到体现,最典型的是关于海盗罪的设定,《联合国海洋法公约》中明确规定了“所有国家应尽最大可能进行合作,以制止在公海上或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任何其他地方的海盗行为”,同时对海盗行为进行了详尽之规定,(a)私人船舶或私人飞机的船员、机组成员或乘客为私人目的,对下列对象所从事的任何非法的暴力或扣留行为,或任何掠夺行为:(1)在公海上对另一船舶或飞机,或对另一船舶或飞机上的人或财物;(2)在任何国家管辖范围以外的地方对船舶、飞机、人或财物;(b)明知船舶或飞机成为海盗船舶或飞机的事实,而自愿参加其活动的任何行为;(c)教唆或故意便利(a)或(b)项所述行为的任何行为。由于我国刑法典中并未设置与公约中对应的海盗罪,因此在实践中只能通过“分解”上述海盗行为比照最相类似之犯罪行为进行定罪的方式以实现对这些犯罪行为的规制,如将“非法暴力行为”“非法扣留行为”和“掠夺行为”按照故意杀人罪、故意伤害罪、抢劫罪、绑架罪、劫持船只罪等罪名定罪量刑,此种司法处理模式明显无法体现海盗犯罪的本质,对行为之定性也极易形成偏差[3]。同样的刑事立法缺陷与司法适用困境亦可能表现在像暴力危及海上航行安全罪、破坏海底管道和电缆罪、危及大陆架固定平台安全罪等国际条约中所规定之罪名的适用上。
其二,学理上传统刑法学研究方法之局限。所谓传统刑法学研究方法,笔者将之界定为以刑法规范之阐释为基础之规范刑法学(刑法解释学)抑或教义刑法学的研究方法。有学者从方法层面与结果层面刻意强调规范刑法学与教义刑法学之间的区别:方法层面上,前者主要采取“注释”的方法,后者则主要采取“逻辑推理”的方法;结果层面上,前者所形成之知识体系突出强调“以刑法规范为中心”或揭示“刑法规范的含义”为己任,而后者则强调刑法知识体系本身的逻辑性最大化特征[4]。或许从本质上而言,注释还是逻辑推理,揭示刑法规范含义抑或刑法知识体系本身的逻辑性可能并不冲突,对刑法条文规范含义的阐明可谓“注释”的方法,但其必然伴随着逻辑推理,同理,刑法知识体系本身的逻辑性亦可通过揭示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所体现,在此意义上而言,“法教义学实际上也可用来指称部门法学,质言之,部门法学就是法教义学,尤其在德日等大陆法系国家,民法就被直接称为民法教义学、民法解释学,刑法就被直接称为刑法教义学、刑法解释学”[5]。规范刑法学也好,教义刑法学也罢,两者之共同点使得传统刑法学的研究范式强调以“法条”为中心采取注释与逻辑推理的方法,去找寻刑法规范的真实含义,但较少关注法条本身在打击犯罪方面的实际效果,亦可能导致刑法学之研究成为一个封闭的研究范畴,从而忽视多学科、跨学科之研究方法在刑法学研究中的积极意义。
如果说对于犯罪现象之研究包含刑法之内的研究与刑法之外的研究的话[6],那么,海洋刑法学范畴之提出则意在突破既有之研究框架,从刑法之外对海上犯罪进行审视,从而使人们的关注重点自然而然的从国内的法律规范转向区域性甚至世界性的有法律约束力的公约等,最终从方法论的层面来看,使得从教义刑法学向一种普适刑法学的转变成为可能。海洋刑法学作为独立之研究范畴存在,就必须确立其独立之研究对象,学理上至今未形成关于海上犯罪的统一认识,其缘由亦可归结为多数论者未能从海洋刑法学作为独立之研究范畴出发思考问题。按照学理上的一般表述,海上犯罪有广、狭义之区分,前者泛指发生在海域上的所有犯罪的统称,后者则专指由海洋法国际公约所规定的海上国际犯罪。如果仅仅从与陆地犯罪在时空环境上的区别着眼,则广义的海上犯罪并无不妥,但仅仅从犯罪发生的空间环境出发,并不必然代表对两种犯罪的刑法规制会形成不同。如果从海洋刑法学作为独立范畴的角度出发,则其研究对象应限于“国际海上犯罪”,即具有了跨国性、涉外性、违反公约性基本特征的涉海国际犯罪,相较而言,国际海上犯罪更多的涉及国际公约之适用,导致对其的调整方法也与国内犯罪有别。
二、船旗国刑事管辖原则的认识误区评析
海洋刑法学视野下,刑法学研究视角被大大拓展了,若干被学界忽视的问题亦得以提出并进行研讨,针对海上国际犯罪之船旗国刑事管辖原则可谓其典型问题。
刑事管辖权亦称刑法的空间效力,是国家对其领土及其国民行使主权的具体体现,而刑事管辖原则则为刑事管辖权确立之根据,从当今各国的立法实践来看,一般在立法上将属地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保护管辖原则与普遍管辖原则进行组合式的规定,其中,属地管辖原则与属人管辖原则在学理上亦被视为各种管辖原则之核心,“从根本上说,国家制定法律的目的都是调整发生在一定领域内的事实或者行为(属地原则),或与一定的人有关的行为或事实(属人原则)”[7]。由船旗国中心主义这一国际惯例延伸而来的船旗国管辖原则,泛指各国对取得其国籍的船舶以及船舶上的人、物和发生的包括刑事案件在内的事实实行管辖的原则[8]。各国刑事立法中对于发生在船舶上的刑事犯罪之管辖权虽有所涉及,但船旗国管辖原则能否视为独立之刑事管辖原则及其与其他刑事管辖原则之关系则不无争议。
各国刑事立法对发生于船舶上的刑事犯罪之立法规定较为类似,以我国《刑法》第6条之规定为例: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内犯罪的,除法律有特别规定的以外,都适用本法。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或者航空器内犯罪的,也适用本法。学理上一般认为,本条后半段对于在中华人民共和国船舶内的犯罪,适用管辖权的依据是属地管辖原则,“挂有本国国旗的船舶与航空器属于本国领土,不管其航行或停泊于何处,对在船舶与航空器内的犯罪,都适用旗国的刑法,这便是旗国主义,是属地管辖原则的补充”[9]。该种学理主张虽然指出了船旗国管辖原则之于刑事管辖权之适用,但其是以将船旗国视为本国领土即以属地管辖为前提的,换言之,船旗国管辖原则并不具有独立之地位,仅为属地管辖的下位原则。上述将船舶视为“浮动领土”“浮动岛屿”的“领土拟制说”受到了学界的批判,批驳的焦点多集中于以下两方面:
其一,该种学说将船旗国视为一国拟制的领土将导致两个领土主权并存从而与领土主权之排他性相冲突的尴尬境地:“相互尊重国家主权和领土完整是当代国际法最重要的基本原则之一。由于国家领土的一个重要特征就是‘排他性’,因而在国家领土主权的问题上,相互尊重他国主权和领土完整这一国际法的基本原则,首先就表现为一国领域内不允许他国领土的存在。因此,在他国领域内的船舶决不能成为船旗国的领土”[10]。
其二,船舶领土化会无谓地制造刑事管辖权的国际冲突。如果各国都将本国的船舶视为本国领土,那么,船旗国对于在外国港口、内水或领海内的本国船舶上的犯罪都具有排他性的管辖权;而沿海国对港口、内水和领海内的犯罪行为根据领土原则也享有排他性的管辖权。这样船籍国与沿海国都对同一个犯罪产生了“排他性”的刑事管辖权,两个“排他性”的管辖权冲突是不可调和的,最终导致该冲突无法合理解决[11]。
上述两方面的批驳或许并无实质区别,刑事管辖权是国家主权之体现,在拟制领土说之下,所谓国家主权之冲突其实就是刑事管辖权之冲突。因此,上述批驳意见可归结为采纳拟制领土说的弊端是会导致刑事管辖权之冲突。其实,这样的批驳意见是不能成立的,一个显而易见的事实,各国刑事立法对刑法适用的空间效力问题上一般都对属地管辖、属人管辖、普遍管辖与保护管辖原则进行了规定,在错综复杂的刑事管辖原则之下,必然会发生刑事管辖权冲突的问题。如我国根据属地原则对发生在我国领域内的一切犯罪包括本国公民与外国公民的犯罪均享有刑事管辖权,而其他国家则完全可能基于属人管辖原则对本国公民在国外实施的犯罪享有刑事管辖权。换言之,各国对作为国家主权体现的刑事管辖权之设定在立法意义上并无考虑别国规定之必要,立法论上对同一犯罪可能存在不同国家的刑事管辖权是客观存在的,面对这种冲突,也并非无解决之办法。各国司法实践中普遍存在的刑事司法协助本质上就是为解决刑事管辖权之冲突进行协商的结果,按照学界的一般认识,国际刑事司法协助包括疑犯引渡、讯问证人和鉴定人、搜查、文件送达、刑事判决执行、刑事追诉等方面的协助。其中的疑犯引渡是指在他国犯了罪或者受到调查、被起诉、正在审判中的犯罪嫌疑人或被告人及被判有罪的罪犯在所在国受到原属国要求引渡犯人时,将疑犯引渡到所属国家[12]。换言之,对外国刑事法院判决之承认是刑事司法协助之前提,同理,所谓刑事管辖权的“排他性”也并不绝对,这不仅体现在上述实然层面上为解决刑事管辖权之冲突所延伸之刑事司法协助方式,而且在各国刑事立法中也有所体现。例如我国《刑法》第11条规定,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此条关于外交代表刑事豁免权之规定很明显是属地管辖原则的例外①如后文所述,在区分刑事立法管辖权与刑事司法管辖权的理念之下,此条之规定宜理解为属于刑事司法意义上对属地管辖原则之限制。,亦即上述情形下不适用属地管辖原则,从而也无刑事管辖权,这一条文亦是各国在平等互惠、相互尊重各自主权及遵循国际惯例的基础上形成的,在此意义上,一国刑事管辖权之行使是有限制的,而非“排他”的;更为重要的是,我国《刑法》第10条规定了关于对外国刑事法院判决之承认问题,即凡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领域外犯罪,依照本法应当负刑事责任的,虽然经过外国审判,仍然可以依照本法追究,但是在外国已经受过刑罚处罚的,可以免除或者减轻处罚。从世界范围来看,多数国家刑事立法中均涉及对外国刑事法院判决之承认问题,只不过在具体承认方式上有所谓的积极承认与消极承认之分,前者将外国确定的刑事判决与本国刑事判决同等看待,“具体言之,是指在本国具有刑事管辖权的行为,受到外国确定的有罪判决时,将该犯人移至本国后,执行外国所确定的有罪判决;如果刑罚在外国执行完毕,或外国法院虽宣告有罪但免除刑罚,或已作出无罪判决,则本国不再追诉”[13]。后者虽保留本国对已经在外国执行刑罚的犯罪人进行审判之权力,但在刑罚之执行方面亦考量其已经经过国外刑罚执行之事实。不论是积极承认抑或消极承认,均以承认外国刑事法院之判决为前提,不仅如此,从世界范围来看,“外国刑事判决的效力,经历了一个由完全否认到消极承认再到积极承认的发展历程”[14],此一事实说明,完全承认外国刑事判决与本国刑事判决具有同等之效力是各国刑事立法之趋势,也因此,刑事管辖权的所谓“排他性”并非事实。
三、船旗国管辖原则于我国刑事管辖中的理性定位
从根本上说,船旗国管辖原则来源于国际惯例,亦为当今主要之国际公约所承认,如我国已加入的《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2条就明确规定,船舶航行应仅悬挂一国的旗帜,而且除国际条约或本公约明文规定的例外情形外,在公海上应受该国的专属管辖。国际公约中的上述规定成为我国学者坚持将船旗国管辖原则视为刑事管辖中的独立原则之理由。其实,此一原则是否应在我国刑事管辖原则中占据一席之地,取决于其与作为管辖原则基础的属地管辖与属人管辖原则之间是否存在设定目标、内容上的重叠。
一方面,船旗国管辖原则是对属地管辖原则的限制。将具有本国国籍的船舶上发生的刑事案件赋予管辖权“貌似”是对“领域”的衍伸因而扩张了属地管辖的范围,但同时各国对船旗国管辖原则的立法承认又会使本国之属地管辖原则受到限制。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2条之规定,沿海国的主权及于其陆地领土及其内水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在群岛国的情形下则及于群岛水域以外邻接的一带海域,称为领海。此一规定将领海的法律属性等同于陆地领土,在一国领海内的犯罪自然得根据属地原则进行管辖。但该公约27条亦规定,沿海国不应在通过领海的外国船舶上行使刑事管辖权,以逮捕与在该船舶通过期间船上所犯任何罪行有关的任何人或进行与该罪行有关的任何调查,但下列情形除外:(a)罪行的后果及于沿海国;(b)罪行属于扰乱当地安宁或领海的良好秩序的性质;(c)经船长或船旗国外交代表或领事官员请求地方当局予以协助;或(d)这些措施是取缔违法贩运麻醉药品或精神调理物质所必要的。换言之,在上述四种情形之外的均属“无害通过”的情形,沿海国对其领海内船舶上的犯罪不具有刑事管辖权。故此,船旗国管辖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形成了适用上的限制。
另一方面,船旗国管辖原则不同于属人管辖原则。属人管辖原则是以行为人的国籍作为连接因素而适用一国刑法的根据,而船旗国管辖原则则是以船旗国的国籍作为连接因素确定其管辖权依据的。按照《联合国海洋法公约》第91条之规定,每个国家应确定对船舶给予国籍、船舶在其领土内登记及船舶悬挂该国旗帜的条件。船舶具有其有权悬挂的旗帜所属国家的国籍。国家和船舶之间必须有真正联系。尽管《联合国海洋法公约》对“真实联系”之标准并未明确规定,而“在国际法上,如何制定本国的登记政策是各国的内部的主权事务,国际法一般不对各国的船舶登记法进行干预”[15],船东一般都可以自由选择船旗国成为一种普遍存在的实践,但毫无疑问的是,同艘船舶只能有一个国籍,船旗国管辖正是以船舶作为整体进行管辖为基础的。至于船舶内的船员其国籍是否与船旗国国籍一致则在所不问,因此,对船舶内外国人实施的犯罪,船旗国对其行使刑事管辖权必然不同于属人管辖权。
从上述分析来看,船旗国管辖原则构成对属地管辖原则之限制,导致与属地、属人管辖原则的适用解决不同,但据此做出其属于独立的刑事管辖原则尚嫌武断。各国刑事立法中对享有外交特权和豁免权的外国人的刑事责任通过外交途径解决的规定亦可谓对属地、属人管辖原则之限制,事实上并没有人主张上述管辖原则也应视为独立之刑事管辖原则。其实,各国立法中对属地、属人管辖原则之规定所解决之问题乃是一国刑法适用的效力范围问题,由于“没有任何一个国家的刑事司法系统可以超越国家主权的管辖范围,在他国领土上自由地进行追诉犯罪的活动”[16],因此,一国刑法适用的效力范围最终与其具体管辖范围之间可能并不一致。就此,部分学者提出的刑事立法管辖权与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划分是有价值的,前者所要解决的是国家刑事管辖权的空间范围与对象范围之问题,后者则意指管辖权行使的具体权能和行使的方式问题。“国家的刑事立法管辖权是不可能放弃或转移的,它是一个静态的、稳定的立法规定;国家能够放弃或者转移的只是动态的、具体的、实然的刑事司法管辖权”[17]。由此看来,船旗国管辖原则果有存在之必要,也应限定在刑事司法管辖权层面,由于遵守国际公约之义务,使应然层面上的属地管辖原则受到限制,形成实然层面的船旗国管辖原则。
即使将船旗国管辖原则视为独立之刑事司法管辖内容,笔者也不赞成修改目前刑法之规定,前文已然述及,船旗国管辖原则构成对属地管辖原则之限制,将其视为属地管辖原则之下位原则并无不妥。从世界各国刑事立法来看,其中关于船旗国管辖原则之规定大同小异,区别仅在于立法条文中是否单独作为一条进行规定,如《德国刑法典》第4条单独规定,“在悬挂德意志联邦共和国国旗或国徽的船舶、航空器内发生的犯罪行为,无论犯罪地法律如何规定,均适用德国刑法。”而更多的国家则与我国立法规定类似,在同一个条文中将属地管辖原则与船旗国管辖原则进行规定,如《日本刑法典》第1条规定,“本法适用于在日本国内犯罪的一切人。对在处于日本国外的日本船舶或者日本航空器内犯罪的人,亦适用本法。”部分国家的刑事立法甚至直接将本国之船舶或航空器视为本国领域,如《意大利刑法典》第4条规定,“在刑事法律的意义上,共和国领域以及其他一切受国家主权支配的地点是国家领域。意大利的船舶或飞机,无论处于何地,均被视为国家领域,除非他们根据国际法受外国本地法的管辖。”上述立法规定的共同点均承认船旗国管辖原则对属地管辖原则之限制,相较而言,我国刑法之规定虽未如德国刑事立法那样将船旗国管辖原则单列一条做出规定,但在属地管辖原则的条文中单列一款做出规定,所表达的是同样的意思。况且,在学理上将刑事管辖权区隔为刑事立法管辖权与刑事司法管辖权的前提下,在对上述条款的理解适用上,各国实践并无不同,因此,并无修改我国刑法之必要。
[1]张湘兰.南海打击海盗的国际合作法律机制研究[J].法学论坛,2010,(5).
[2]赵薇.海上刑法的理论定位与实践价值[N].中国社会科学报,2010-09-07.
[3]郭玉川.我国刑法该如何规定海盗罪[N].检察日报,2009-01-23.
[4]周详.教义刑法学的概念及其价值[J].环球法律评论,2011,(6).
[5]林来梵,郑磊.基于法教义学的质疑——评“中国法学向何处去”[J].河北法学,2007,(10).[6]王牧.犯罪研究:刑法之内与刑法之外[J].中国法学,2010,(6).
[7]陈忠林.意大利刑法学原理[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56.
[8][11]邵维国.论海上国际犯罪的船旗国管辖原则[J].吉林大学社会科学学报,2007,(6).
[9]张明楷.刑法学[M].北京:法律出版社,2011.75.
[10]陈忠林.关于我国刑法属地原则的理解、适用及立法完善[J].现代法学,1998,(5).
[12]王金贵.国际刑事司法协助的主要形式与新发展[N].检察日报,2006-09-02.
[13][14]苏彩霞.我国刑法第十条之检讨[J].淮阴师范学院学报,2004,(4).
[15]张湘兰,郑雷.论“船旗国中心主义”在国际海事管辖权中的偏移[J].法学评论,2010,(6).
[16]张智辉.国际刑法通论[M].北京: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281.
[17]邵维国.刑事管辖权含义辨析[J].广州大学学报,2007,(11).
Research about Flag State Jurisdiction Principle from the view of Sea Criminal
Yan Erpeng
(Law College of Hainan University,Haikou Hainan 570228)
The purpose of sea criminal model on the base of international sea crime is to break through the traditional dogmatic punishment law and transcend it to general criminal law;The conflict of national criminal jurisdiction is a fact as reality,which shouldn’t be argued to deny it’s additional principle of territoriality;The flag jurisdiction principle is only necessary under the level of criminal jurisdiction,so the Chinese criminal law doesn’t need to change.
sea criminal jurisprudence;flag state jurisdiction;criminal jurisdiction
D924.1
A
2095-3275(2015)03-0025-06
2015-02-05
本文为2013年国家社科基金一般项目“海上非传统安全犯罪的刑事规制对策研究”的阶段性研究成果。
阎二鹏(1978— ),山西晋城人,海南大学法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法学博士,北京师范大学刑事法律科学研究院博士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