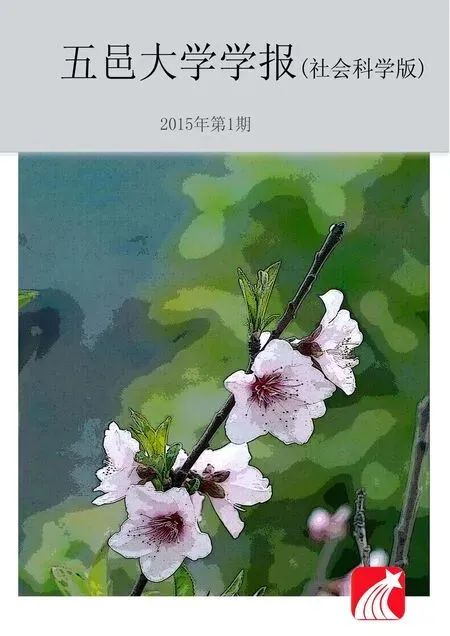论大唐文治与东南学士
2015-03-17潘链钰
潘链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论大唐文治与东南学士
潘链钰
(武汉大学 文学院,湖北 武汉 430072)
大唐文治局面之形成历经太宗朝秦府文学馆学士、弘文馆学士,则天朝北门学士以及玄宗时期的集贤院学士和翰林院学士之逐步推进。而此五馆学士中之东南学士与东南学术,对于学馆构建、政治顾问、礼乐制定、律史修撰等都贡献极大。有唐一代文治之隆盛,是由于太宗、则天、玄宗三朝重东南文士之文治积淀而成。东南文士在大国盛世文化构建中有着举足轻重的地位。
大唐文治;东南学士;文化强国
引 言
唐初关中、山东、江南三大地域不仅存在明显的地缘政治差异,同时也存在明显的区域文化差异。唐人称山东为“河洛”,称江南为“江左”。《新唐书》卷一九九《儒学传》中直引唐人柳芳《氏族论》说明以上三者之区别:“山东之人质,故尚婚娅,其信可与也;江左之人文,故尚人物,其智可与也;关中之人雄,故尚冠冕,其达可与也。”[1]论江左之人,以“文”概括,可谓尤确。文德贵政,因而唐帝国统治者未将治国大任全然交予尚雄之关中人与尚质之山东人,而是倚仗尚智之江左人,应该是正确的选择。后来的历史证明,东南文士对唐代文治政治局面之形成影响十分深远。
江左驻于神州东南,自六朝便是经济富庶、人才荟萃之地。得天独厚的地理位置,加上久远流传的“耕读传家”处世理念,造就了东南极为浓郁的文化氛围。而东南这种学术世家的传承实际自东汉后便逐渐兴盛。东汉后之学术不再以政治中心为传播重心,而以地方大族为传播倚靠。正如陈寅恪先生指出:“东汉以后学术文化,其重心不在政治中心之首都,而分散于各地名都大邑。是以地方之大族盛门乃为学术文化之所寄托。……故论学术,只有家学之可言,而学术文化与大族盛门常不可分离也”。[2]江左作为唐初政权根基的三点之一,与关中、山东相较自然势力不敌,但三者同在由隋入唐政权转变浪潮中贵气渐失的境遇里作出了不同选择。关中尚武,武力出雄能在乱世有建功,但政权渐稳阶段则极易引发皇权争斗危机,太平时期又有武无所用之尴尬,自然不会受到特别的重视。山东重婚,血缘关系一方面能带来政权中心的相对固定化,但固定化的另一面便是僵化,这会导致政治活力之丧失与骄逸心态之渐涨。太宗卓识,早在秦王时期便意识到这些问题,且因深谙世事累迁之律故慧眼识得江左才是唐政权稳固之重点。太宗的远见卓识,一方面开启了唐代以文治国的道路,另一方面也让东南文人在政权构建中极尽才能,为王权所用,为苍生谋福。从后历史的角度考察,东南文人学术的确在大唐文治建设过程中发挥了极为重要的作用,甚至可以说,东南文人造就了初唐、盛唐博雅隆盛的宏大局面。
一、 东南缘起:秦馆文臣之文治初萌
前文提到,东南文人对唐代文治局面之形成起到极为关键的作用。而唐代统治者倚靠东南文人及其学术文化风化天下巩固统治绝非一朝一夕之事,而是有着代际传承与循序渐进的过程。具体而言,唐代李世民在秦王府设立秦府文学馆,标志着唐代统治者力行推广文治天下的开始。自秦府文学馆,经由太宗弘文馆,则天朝北门学士,继而玄宗集贤院学士至翰林学士,这一系列的文治举动,几乎全部是东南文人在统治者支持下发展进行的。
乱世则隐是大部分儒者践行的原则,但战乱迫使文士居无定所,只能“客游”天下,希冀偶遇明主一展才华。而一如春秋战国吸才纳贤之风,隋后诸军事集团皆求贤若渴。李渊镇守太原时,便吸纳隋朝旧学温大雅等人进入幕府,李渊引温大雅为记室参军,专掌文翰,其弟温彦博为中书侍郎,二人深得李渊信任,兄弟同主一时成为美谈。在政治卓见上,唐太宗李世民于其父毫不逊色,在引用天下人才上更是青出于蓝。武德四年(公元621年),李世民筹建秦府文学馆,其中来自江南与山东之文学才彦占了三分之二。这样明显借山东江左之力平压自魏晋以来便形成的“关陇本位”之模式,一则因关中势力既受李渊厚重又尚武轻文不便统治,二则因李世民见识高远借鉴南北朝上流尤重江左文士之传统而自纳贤良于斛内,为日后的政治前途做了诸多重要铺垫。秦府文学馆学士中源于东南地区之名士者,如褚亮、蔡允恭、刘孝孙,还有官至贞观宰相的许敬宗,最为人所识的则是陆德明与虞世南。陆德明,苏州吴人。虞世南,越州余姚人。作为典型的东南文士,陆虞二人对唐初文治政治及文化构建贡献极大。秦府文学馆的开设让东南学士有了给李世民出谋划策之机遇,因而在历次战役中李世民都有着战功赫赫的表现,甚至在玄武门之变中,秦府文学馆学士也给予了不可小觑的帮助,这些在史书上有着清晰的记载,不再赘言。需要说明的是,秦府文学馆吸纳的各方才士多乃客游文人,也就是说他们的籍贯并非一定明确,再加上李世民在用人政策上虽有新启东南之态势,但并非完全摒弃关中旧贵族而不顾,他之倚重东南文士有着逐步提高的过程。
二、东南名盛:弘文馆学士之文治隆升
如果说秦府文学馆中太宗因关中旧士族之故而未对东南学士全然倚重,那么在接下来的弘文馆学士中,东南文人可谓极尽风光,以致史载关陇集团“恂恂然似不能言”。弘文馆学士设置于武德九年,距玄武门之变仅三月不足。作为第一个由中央设置的学士官,弘文馆学士是由太宗皇帝在朝职事官中遴选出来的,中间多有昔日秦王府文学馆学士,绝大多数乃是东南文人。《资治通鉴》卷一九二载:“至天下既定,精选弘文馆学士,日夕与之议论商榷者,皆东南儒生也。”[3]此处尤见太宗对东南文士之重视,而虞世南、褚亮等原秦府文学馆旧臣更是倍沐皇恩,甚至高祖李渊之葬仪皆由虞世南主定。《旧唐书》卷一八九上《儒学上》言道:“及即位,又于正殿之左,置弘文学馆,精选天下文儒之士虞世南、褚亮、姚思廉等,各以本官兼署学士,令更日宿直。听朝之暇,引入内殿,讲论经义,商略政事,或至夜分乃罢。又召勋贤三品以上子孙,为弘文馆学生。”[4]此等记载另详见于《文苑英华》与《资治通鉴》中,而弘文馆设置之速,尤见太宗对文治之重视。弘文馆学士参政对贞观时期政治制度构建及文化奠基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也是直接推进太宗朝文治化局面的中坚力量,而其中东南文士及其学术导向更值得大书特书。
首先是贞观时期经学的东南化倾向直接由弘文馆中的东南学士导引。太宗对南朝文化尤为倾慕,虞世南、褚亮、欧阳询等皆以南朝文人而受太宗重用,甚至内宫才女美人皆以南朝旧贵族为尚。在此等宏风之下,举朝崇尚南朝经术自不为奇。据宋人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卷三十“词翰书籍”的记载:“以经籍讹舛,盖由五胡之乱天下,学士率多南迁,中国经术浸微之致也。今后并以六朝旧本为正。”[5]由此可见,南朝文化作为中国学术的正统,应该是得到了唐代统治阶级认可。中国学术首以经学为重,东南文人又延续南朝学术传统,将南朝重《孝经》、《论语》之文化风气带入唐朝。高宗喜欢殿前听讲《孝经》便是南朝风气使然。尔后《孝经》、《论语》作为唐朝科举考试的必考项目亦是弘文馆中东南学士引导之力。至于太宗令孔颖达编撰《五经正义》亦多是东南文士之功,而这些在文学史经学史中屡被谈及。要之,东南文士久历经术传家之祖训,在学术传承与人格构建上,承接汉魏遗风,因而这种“根正苗红”的世家文风很容易便赢得倾向南朝文化的唐代统治者的偏爱,因此他们发挥东南文化之优势弘扬学术传统为贞观之治添彩便成了天造地设之佳话。
其次是弘文馆东南学士在贞观朝对礼乐法度的筹建对后世影响颇远。唐朝首次修订的《贞观礼》就是弘文馆学士之功。至于乐事本是太宗所善,而由褚亮等新做的乐章《大唐雅乐》,以太宗认可的“乐在人和”之主张歌颂太宗气象因而深得帝王夸赞。新礼与新乐之成型,给了朝野上下一个参照的模板,举朝皆以和雅为乐事,这直接促进了太宗朝文治局面的形成。参与修订新礼的魏征对礼乐新成之盛世局面喜不自胜道:“拨乱反正,功高百王,自开辟以来,未有如陛下者也。更创新乐,兼修大礼,自古作乐,万代取法,岂止子孙而已。”[6]此语虽略有拍须之嫌,但由此可窥太宗朝的确渐渐形成了一种“偃武修文”的盛世景象,这自然是太宗重用文士促成文治之必然结果。
在定律修史方面,东南学士同样颇有建功。太宗律令之基本原则是“死者不可再生,用法务在宽简。”[7]这体现了太宗以人为本的仁治思想。唐初立法正是在此等原则下由东南文士积极参与而成。太宗朝参与制礼的文人学士如房玄龄、虞世南、褚亮皆是深谙南朝文化的东南文人,因而唐初律令有南朝文化印记毫不为奇。值得提及的是,东南文人对太宗以人为本之治国理念躬行不悖,因而在定刑上从宽就简,定下了“死、流、徒、杖、笞”五等被后代王朝引以为遵的法典。正是东南文士不断努力实践太宗仁政之理念,以礼修法,一改过去动辄祸牵株连的残酷条文,因而太宗文治世景得到进一步推动和发展。今人法制史里也直接称赞道:“以李世民为代表的唐初统治者为了安定社会秩序,维护封建统治,在立法上采取‘以宽仁治天下,而于刑法尤慎’的原则”[8]。太宗文治之另一表现则是修史,在修史方面东南文人亦发挥了巨大的作用。唐代太宗前无官修历史,自太宗开创了“官府修史”与“宰相监修国史”两个制度,一来是太宗政治上的需要,二来是文治政治的必然。参与修史工作的东南文士如孔颖达、李延寿、房玄龄、李百药、岑文本、姚思廉、魏征、上官仪等开启了空前规模的官修史书活动。
三、东南因变:北门学士到翰林学士之文治转型
弘文馆是太宗时期文治政治的主要建功者。而武则天时期的北门学士,虽然同样是在政治目的下构建的文学臣馆,但相比起来,北门学士失去了往昔弘文馆开明温和的政治环境,在则天一朝虽然也为文治与政治做出了诸多建树,但在武则天高压统治下,北门学士显得羸弱而恭谨。无论是武则天还是武则天时期的政治都是历史上颇有争议的话题。在今天看来,武则天还是对大唐走向繁盛作出了极为重要的贡献。作为借政治革命而荣登帝王宝座的一代奇女,武则天很能审时度势地利用太宗朝延续的文治政治理念。武则天正是敏锐地看到关陇势力和地位剧烈下降以及东南文士和庶族阶层迅速崛起不可逆转之趋势,因而在政治革命中,一直用心提拔包括许敬宗、李义府、王德俭、崔义玄、袁公瑜等东南文士作为自己日后政治革新之资本。北门学士为武则天所用,为了政治目的而修撰了包括《少阳正范》及《臣规》在内的诸多文化与政治典籍。更值得一提的是,北门学士可以直接参与朝政,开了文臣直接进入禁中议政的先例,这是唐朝文人政治局面发展的重要转折。然而北门学士仅存18载,且在则天铁腕之下显得卑微羸弱,因而北门学士跟弘文馆学士相比有着明显的悲剧色彩。
武则天之后,唐朝经历了短暂的动荡,但从后历史的视野观看会发现,大唐文治之路不可逆转。唐太宗构建的文人治国方针在则天一朝没有衰弱反而逐步壮大成型,至玄宗则进一步巩固,因而继北门学士之后出现了集贤学士。玄宗时期,进士科作为王朝高级官吏之来源已经得到全社会的普遍认可与拥护。自开元后,“四海晏清,士无贤不肖,耻不以文章达。其应诏而举者,多则二千人,少尤不减千人。”[9]玄宗时期文人治国成为颇有积淀的政治运转模式,文治局面之稳固与浩大已全面超越则天时期,甚至与太宗朝“海内清晏、九州飨和”之景十分吻合。正是在这种情势下,由政治目的出发的修书运动浩浩荡荡地展开了。开元十三年四月,玄宗为奖赏《封禅仪注》之修撰,先将集仙殿丽正书院改名为集贤院,后又仿太宗厚待文学馆十八学士,画开元十八学士图于上阳宫,且亲题赞文。此等荣耀非北门学士能企及。然其政治目的不言而喻,玄宗改名诏书里其实暗示得十分明显:“仙者,补影之流,朕所不取;贤者,济治之具,当务其实。”[10]集贤学士受到重用,成为玄宗朝文治政治进一步推进和发展的重要力量。据两《唐书》记载,进士科出身的集贤学士共118名,其中山东江南两地占57名,关中30名,从中可以看出玄宗朝集贤学士中还是东南文士占了主导地位。玄宗一朝乃是史书记载的开元盛世,甚至是中国封建社会的顶峰时期。这种盛世与顶峰时期,并不一定指武功方面,最主要的还是指文治。一个国家之强大远非武力能够衡量,真正能使“万国来朝、百鸟朝凤”,根由实际在于文化之力,而文化之力首推经典书籍之盛。这一点,在开元时期得到了验证。开元十九年,集贤院历经十余年之努力,修撰成经史子集和道、释、杂术近9万卷。其中《初学记》、《大衍历》、《开元礼》、《唐六典》是集贤学士们的经典著作,成为后人沿袭使用的模范典籍。在这些经典著作成书过程中,东南学士与东南学术理念同样发挥了不可磨灭的功绩。比如《开元礼》之总编撰萧嵩是山东临沂人,而主要修撰人王仲丘是山东琅琊人。其他修撰人员则涵盖了包括贾登、张炟、施敬本、陆善经等一批东南学士。《开元礼》被宋元明清相继沿用,欧阳修曾赞曰:“唐之五礼之文始备,而后世用之,虽小有损益,不能过也。”[11]然而任何学士之最终命运皆在帝王之用,集贤学士在翰林院产生之后,迅速失去了往日光辉。天宝年间的集贤院已再无政治用途而完全变成了安置闲臣的苦闷场所。贞元八年集贤院寿终正寝。
翰林学士设置于开元二十六年,距安史之乱仅17年。跟以前的弘文馆学士与集贤院学士很不一样,翰林学士不负责文化整合而是“专掌内命”。从弘文馆开始的“临时草诏”到翰林学士的“专职草诏”,唐代文治与唐代学士之命运悄然发生了变化。学士掌诏虽然是文治发展的必然结果,但学士附庸政治的地位却随之变得不可扭转。翰林学士开始不再以地域划分与选拔,而是从官吏中直接选出拔萃者供皇帝任用。然而很明显,大唐文治之开始乃是任用庶族与平民以抵挡关陇贵族之腐朽,自秦府文学馆到集贤院,皇帝多用东南文人,用人以文才,但从翰林学士开始,皇权专制骤然加强,无高门无官史之人员很难再进入权力中心成为翰林执掌,文治局面悄然发生了逆袭,因而玄宗之后,帝国政治分野出现了新变化,朋党之争加剧,文士掌权随着附庸地位的稳固而不再呈现清晏局面。因而帝国根基动摇甚至大唐覆灭便成为了必然。
四、结 语
中国文化里自《易》便有刚柔之分。儒家主清刚劲健而道家重冲淡轻柔。乱世用武与盛世崇文亦是统治者习以为常的治国方针。盛世用文,而文则偏柔。文者,温柔敦厚,乃是儒道共同秉持之理念。文贵乎柔,甚至以阴柔为天下正。按照地理学之区分,的确有南人偏文而彬彬轻柔、北人重武而雄强刚劲的说法。东南文士,无论是唐初弘文馆学士还是则天北门学士,或是盛唐的集贤学士和翰林学士,其贵文尚柔之特征表现得十分明显。北门学士胡楚宾,“性慎密,未尝言禁中事”[12];集贤学士萧嵩,开元时官至宰相,是《开元礼》的主要负责人,但为人唯唯诺诺,从无见解。可见,文者贵柔实乃文人的表征。盛世不崇武力,文者贵柔便是一种比较和谐的处世方式。在唐代纵然翰林学士官居朝野之前,但少有革职查办之例。翰林学士大多谨言慎行,遵礼守法,体现出唐代文治开明的极大效用。从以上可知,在盛世局面下,崇尚文治重用文士的确是政治开明、文化兴盛的重要途径。唐人文化颇重东南已在前文深刻辨析,两宋倚重江南也是史有所载,明代江南富商云集,刊刻书籍成为典型的文化泽国,清代虽文化高压,但东南学士参与四库修撰之功不可不提。由此可见,盛世文化构建的东南情结在历史上屡见不鲜。这种学趋东南的文化心理至今仍然是华人最为明显的文化表征。
当然,我们说学趋东南,并非意味着西北或北方文化不如东南文化,只是指由唐至清几个盛世阶段,为学之盛偏向东南而言。从秦府文学馆学士到翰林学士,从太宗文治到玄宗专权,大唐学士的从政之路与东南学士的使命都在发生变化。封建帝国自身无法克服的矛盾,终将极盛一时的文治之路推向深渊。但不可否认,从贞观到开元,东南文人在大唐初盛时期发挥了不可磨灭的政治作用。
[1]欧阳修,等.新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5769.
[2]陈寅恪.金明馆丛稿初编[M].上海: 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131.
[3]司马光,沈志华,张宏儒.资治通鉴[M]. 北京:中华书局,2009:6437.
[4]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726.
[5]江少虞.宋朝事实类苑[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1:398.
[6]王方庆.魏郑公谏录:卷四[M].北京:中华书局,1985:25.
[7]吴兢.贞观政要[M].济南:齐鲁书社,2010:271.
[8]张晋藩,等.中国法制史[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81:245.
[9]杜佑.通典[M].北京:中华书局,1988:189.
[10]王溥.唐会要[M].北京:中华书局,1998:1006.
[11]王应麟.困学纪闻[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2008:1378.
[12]刘昫.旧唐书[M].北京:中华书局,1975:4803.
[责任编辑 李夕菲]
2014-11-21
本文是2012年度国家重大社科项目“中国文化元典关键词研究”(批准号:12&ZD15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
潘链钰(1988— ),男,湖北鄂州人,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中国古代文论研究。
I206.2
A
1009-1513(2015)01-0036-0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