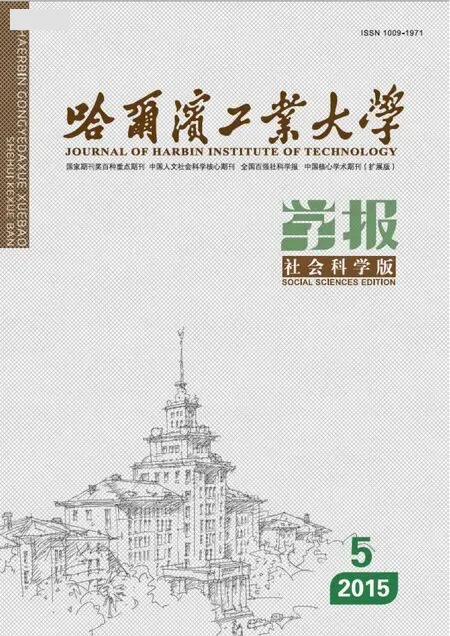鲁迅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
2015-03-17任传印
任传印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28 )
·文学与文化研究·
鲁迅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
任传印
(浙江大学 人文学院,杭州 310028 )
摘要:作为现代文学史上具有奠基性、开拓性的作家与思想家,鲁迅有着广博深厚的文化学养,包括对佛教、基督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的涉猎乃至深入研究,并由此塑造出具有独特性格和审美价值的宗教人物形象。鲁迅坚实的现代启蒙立场使很多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突出批判意识,彰显“立人”理想。鲁迅健旺的审美意识亦使宗教人物形象具有独特性格内涵与审美价值。从文学史视域来看,鲁迅塑造宗教人物形象的两种基本路向,即启蒙与审美皆有其代表性和借鉴意义。
关键词:鲁迅; 宗教人物形象; 启蒙立场; 审美建构
收稿日期:2015-05-20
基金项目:教育部人文社会科学研究规划项目“早期全球化语境与近现代中国文学重塑“中国形象”研究”(12YJA751023);浙江省哲学社会科学规划课题“民国佛教文学研究”(15NDJC142YB)
作者简介:任传印(1984—),男,山东德州人,助理研究员,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研究。
中图分类号:I266
文献标志码:志码: A
文章编号:编号: 1009-1971(2015)05-0097-07
Abstract:Lu Xun is a great writer and ideologist who is fundamental and ground-breaking in Chinese modern literature. His cultural accomplishment is extensive and profound including Buddhism, Christianity, Taoism and folk religions. Meanwhile, Lu Xun created a lot of images of religious figures that had different characters and artistic style. Because his modern enlightened attitude was steadfast, many images of religious figures expressed critical thinking and the thought of “fostering personality”.Second, Lu Xun' aesthetic consciousness is very strong, so some images of religious figures had much aesthetic value. In the view of Chinese modern literary history, these two types are all representative, the modern enlightened attitude is more obvious.
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有着或隐或显的诸多关联及体现,其中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是较为独特的现象。①笔者考察的宗教人物形象主要包括佛教、道教、基督教,同时因为中国民间宗教向来与佛道关联甚密,近现代亦复如是,所以兼及民间宗教人物。另外,宗教意义上的儒家尚无确论,笔者未将其纳入考察范围。作为现代文学的奠基人与开拓者,鲁迅以宽广深刻的文化学养与审美体验塑造了以知识分子和农民为代表的多种人物形象。学界对鲁迅笔下的诸多形象及其宗教观多有涉及,但对有独特性格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少有系统研究。鲁迅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与其宗教文化学养有关,也源于他对社会宗教现象、文化传统的反思以及独特生命体验的审美传达,在文学人物形象序列中有特定的历史与审美价值,同时折射出鲁迅及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的关联。
一、广博深厚的宗教文化学养
作为现代文坛巨擘,鲁迅有着天生我才的独特禀赋与宽广弘深的文化学养,对传统儒道文化、古典文学、现代自然科学、西方文学及哲学等皆有独到拣择。同时需要指出,他对佛教、基督教、道教及民间宗教等中西宗教文化亦有普遍涉猎乃至深入研习。首先,鲁迅与佛教的渊源递嬗增进,他自幼便依照绍兴民俗拜寺庙的“龙和尚”为师;②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载《鲁迅全集》(第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596页。1906年至1908年,留学日本的鲁迅得以亲近章太炎先生,乃师宣讲佛学对其有所影响,这在他早期的《文化偏至论》、《摩罗诗力说》、《破恶声论》等著作中有某些体现;③鲁迅早期著作如《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摩罗诗力说》等代表着他对文化与文学的思考,其中某些核心范畴如“自性”、“我执”、“自觉”、“有情”等皆有浓厚的佛家色彩。王乾坤在《鲁迅的生命哲学》中对此亦有述及。参见王乾坤《鲁迅的生命哲学》,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85页。自1913年至1918年间,忧患痛苦中的鲁迅广泛搜求佛教典籍文物,涉及般若系列、三论宗、华严宗、净土宗、僧传、佛教艺术等多方面内容,还认真抄写佛经、高僧传记等,对释迦牟尼的智慧深表叹服。*查鲁迅日记和书账中的佛教典籍,1913年约有7种,1914年约有93种,1915年约有2种,1916年约有7种,1918年约有3种,另外还有很多佛教拓本、碑铭、造像等。日记记载鲁迅研读抄写佛书,与佛教徒许季上、梅光曦等人有交往,1914年7月27日为佛教流通处捐款20元,1914年7月29日为母亲助印《百喻经》向金陵刻经处捐款50元,10月7日又增加10元,还向朋友等赠送佛经,这表明鲁迅与佛教有着很主动与密切的关联。参见鲁迅《癸丑日记》、《甲寅日记》、《乙卯日记》、《丙辰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270页。据许寿裳回忆,鲁迅说:“释迦牟尼真是大哲,我平常对人生有许多难以解决的问题,而他居然大部分早已明白启示了,真是大哲!”参见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岳麓书社2011年版,第39页。其次,本土道家文化对鲁迅的影响也是深刻的,如他自己所说:“就是思想上,也何尝不中些庄周韩非的毒,时而很随便,时而很峻急。”[1]对与道家密切相关的道教以及民间信仰,鲁迅也有深刻剖析,他书账中有关于道家与道教文献的记录,*参见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参见鲁迅《日记》,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中国小说史略》显示出他对佛教、道教、民间信仰及神话的熟悉。再次,鲁迅有着开放的人文视域和“拿来主义”的文化建构思路,故大力引介西方的人文理性、科学精神、文学艺术等以救治转型中国的沉疴痼疾,在早期著作《文化偏至论》与《破恶声论》中,他对基督教的历史影响和精神价值有相当深刻与辩证的认识,*张福贵等对此有所论述。参见张福贵《鲁迅宗教观的文化意义:思想启蒙与道德救赎的衍生形态》,载《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年第3期。后来的日记、书账及文学创作说明他对基督教文化仍有关注。*鲁迅书账中有关于基督教文献的记录,1916年2月为吴雷川的景教阅览所捐款4元,1925年2月21日晚买《新旧约全书》,1928年12月12日托人买《Holy Bible》,创作中对基督教也多有提及。参见鲁迅《丙辰日记》、《日记十四》,载《鲁迅全集》(第15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218页、第553页。参见鲁迅《日记十七》,载《鲁迅全集》(第16卷),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104页。总体而言,鲁迅与佛教的渊源最深,对道家、道教及民间信仰亦有深刻认识,对基督教也比较熟悉,深厚宽广的宗教文化学养成为他塑造宗教人物形象的基础。
同时需要明确,鲁迅的心路历程和价值诉求有着阶段性的迁变,其思想观念体系亦有很大张力。他曾坦言:“其实,我的意见原也一时不容易了然,因为其中本含有许多矛盾,教我自己说,或者是人道主义与个人主义这两种思想的消长起伏罢。”[2]但诸多矛盾没有动摇鲁迅毕生的核心理念与价值诉求,即现代启蒙意义上的“立人”。他在《文化偏至论》中说:“是故将生存两间,角逐列国是务,其首在立人,人立而后凡事举;若其道术,则必尊个性而张精神。”[3]我们亦可说,正是此种诉求,促使鲁迅不断进行心灵探索和文学创作,其所接受的宗教文化也在此视域中被审视、批评、拣择、转化,以期为“立人”理想和形象塑造提供借鉴。鲁迅的好友许寿裳也曾指出:“所以他对于佛经只当做人类思想发达的史料看,借以研究其人生观罢了。”[4]其实不唯佛教,鲁迅对道教、基督教等亦复如是,这种启蒙自觉强化了他笔下宗教人物形象的时代感。同时,作者的审美意识也很健旺发达,故启蒙立场与审美自觉或各自凸显,或融合而意涵丰富,这是鲁迅塑造宗教人物形象的两种基本类型,并影响到人物的性格与审美特色。
二、启蒙立场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
西哲康德说:“启蒙就是人类脱离自我招致的不成熟。”[5]这句经典之言如同嵌入西方启蒙运动大厦中的闪亮基石,同时亦是对人类整体历史进程的洞见。如果从宏观的民族国家和微观的个体生命这两个维度予以考量,近现代中国面临的便是系统性的启蒙工程。鲁迅在《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中也自陈其启蒙主义与改良人生的文学本怀。*参见《鲁迅全集》第4卷:《我怎么做起小说来》。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年,第526页。刘再复指出,中国近代政治思想家严复、梁启超等引领了民族国家意识,“五四”作家开启了个体生命意识,鲁迅是很典型的代表[6]。正是以个体生存与内曜充实作为核心价值,他肯定了希伯来宗教和印度佛教对人之精神需求的重要意义[7],检视了西方基督教、物质文明、科学民主等思潮偏至动进的利弊,并极力引介非物质、重个人的新神思宗,亦提出个体发扬踔厉以兴邦国的路径。鲁迅深知人类文明偏至以进的非中道特征,同时意识到中国处在本体偏枯、新疫传入的交伐苦境,因此其启蒙立场始终是立体多层面和富有张力的。借用《文化偏至论》中近于夫子自道的话说:“此所为明哲之士,必洞达世界之大势,权衡较量,去其偏颇,得其神明,施之国中,翕合无间。”[8]鲁迅笔下的宗教人物形象便在此视域中获得多维度的“权衡较量”,彰显不同的性格侧面。
首先是对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性塑造。早在《破恶声论》中,鲁迅就指出:“人心必有所冯依,非信无以立,宗教之作,不可已矣。”[9]其中对占寺办学亦有批评:“夫佛教崇高,凡有识者所同可,何怨于震旦,而汲汲灭其法。若谓无功于民,则当先自省民德之堕落;欲与挽救,方昌大之不暇,胡毁裂也。”[9]无独有偶,鲁迅对宗教人物形象的肯定性塑造也集中在对佛教高僧的赞扬,这不同于宗教徒在信仰意义上对宗教人格的建构和弘演,而是从重视个体生命自由和形上精神生活及建立现代民族国家文化自信的角度予以“拿来”,既是对佛教信仰人格的借鉴和吸收,亦暗含现代人的理性审视与距离感。如杂文《晨凉漫记》从张献忠异常残暴的性格入手,言及编撰代表中国人性质的“人史”, 特别勾勒出“舍身求法的玄奘”,不仅表达了对玄奘大师坚毅信仰人格的赞许,同时也是对国人性格弊病的深刻批评。再如《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批评了时人在内忧外患困局中的种种举措,如天朝自夸情结、依赖求助国联、盲目祭拜、怀古伤今等,犀利指认出其自我麻醉的国民劣根性,然后笔锋陡然上扬,简洁有力地指出尚有未失掉自信力的中国人:“我们从古以来,就有埋头苦干的人,有拼命硬干的人,有为民请命的人,有舍身求法的人,”[10]鲁迅着力称扬他所熟悉的法显、玄奘等高僧舍身求法的卓越品格,将之视为中国的脊梁,暗含双重的启蒙意义:一是从人文理性的角度肯定僧人宗教信仰的精神价值,与其极力引介新神思宗有着相近的命意,以此弥补国人对“诚与爱”的匮乏;二是着眼于近现代民族国家的独立自强,以微观层面僧人的宗教人格来启蒙和增进宏观层面中华民族的文化自信,实质上是以传统佛教资源支持和推进现代国人新的德性建构。美国社会学家爱德华·希尔斯指出:“任何叫做传统的东西都不是一个整体,它的每一个成分都要经过接受、修改或抵制这样一个过程。”[11]鲁迅对佛教历史人物亦有这样的拣择功能,虽然对高僧形象的勾勒只有寥寥数语,但往往能够“得其神明”, 从个体解放与民族国家的双重启蒙意义上进行复合式建构,如“舍身求法”、“民族脊梁”等性格塑造已成为佛教精神的经典写照,至今仍有重要的启示价值。
与肯定性塑造相异的是对宗教人物形象的否定式书写,这在根本上属于鲁迅毕生所致力的新文化建设、国民性批判及创作实践。如果说肯定性塑造集中于佛教高僧,那么否定式书写则涉及佛道人物与近代在华扩展的基督教信徒等,这在杂文创作中体现较明显。鲁迅努力秉持中道智慧,以建立现代理性自觉和精神生活为核心价值,从人文理性、科学精神、新的德性建构等视角对当时社会的宗教信仰弊病及国民性弱点予以审视,塑造相关宗教人物形象,性格类型约有三种。
首先,从现代科学理性视角对宗教人物的信仰行为予以审视评判。*曹振华认为,鲁迅并没有因提倡科学而否定宗教。笔者认为,鲁迅在《文化偏至论》、《破恶声论》等著作中确实强调了现代科学与传统宗教的不同功能及导向,同时他也从科学视角对社会宗教现象进行了审视,这在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方面亦有体现。参见曹振华《关于鲁迅宗教文化思想的几点思考——与王家平先生对话》,载《鲁迅研究月刊》,2000年第8期。如杂文《新秋杂识(二)》中以科学视角描述在盂兰盆节做法事的和尚与善男信女,兼及对民间信仰风俗的审视;《随感录三十三》以科学理性审视张鬼神之说的民间信仰生活;《寡妇主义》从现代生命科学规律出发,质疑中世纪教士的独身生活,如此等等。需要明确,佛教在中国逐渐本土化的过程中产生了较为复杂的民间信仰形态,有的与原始巫术相融合,因此形态内容参差多元[12]。邓子美指出,清末民初,中国传统农业社会中有大量下层民众的宗教需求远远落后于时代[13]。道教本自民间方术发展而来,与原始巫教等早期信仰的关联更为密切[14]。因此,鲁迅在塑造此类宗教人物形象的时候,既有对信仰体系的理性审视,也有对具原始社会巫术色彩的早期信仰的考察评判,进而表现出鲜明的现代人文理性与科学精神。
其次,由宗教人物形象塑造展开对传统思想文化弊病和国民劣根性的批判。毋庸置疑,社会中的宗教人物生存于中国的文化环境,宗教文化也浸染着历史沉淀的文化基因,西方传入的基督教亦须在适应本土文化的过程中发展,鲁迅的深刻与犀利使之能通过具体的宗教人物形象达到对民族文化基因或国民性的洞识。如杂文《补白》描述理学先生谈禅、和尚做诗,审视“三教同源”的文化现象,主旨并非否定不同信仰的对话,而是以此批评国人以现实利益为核心的善变、无特操性格。《查旧账》和古体诗《赠邬其山》勾勒某些名人的造寺、念经之举,缺乏精神生活意义上的宗教虔诚,实质也是对国人无特操性格的针砭。小说《端午节》以方玄绰的视角暗讽手握经济权的人失势学佛,同样是聚焦其善变性格。
再次,前述两种方式各有侧重,但也非泾渭分明。第三种方式则将对具体宗教人物的塑造与整体的国民性批判相结合,从宗教人物与社会环境本不相隔的角度说,这是理所必至的结果;从艺术创作角度说,这是更为丰富圆融的形态。如《论雷峰塔的倒掉》中的法海形象,基于民间流传的白蛇故事而来,与历史上真实的法海不同,*历史上的金山寺法海禅师为佛教发展贡献了力量。参见柴福善《法海本是降妖伏魔的高僧》,载《中国民族报》,2010年1月26日第7版。作者对其干预民间自由婚恋的行为及心理动机的剖析批评,既蕴含对宗教心理的思考,更是对封建宗法专制弊病的针砭,*学界亦有相关论述。孟凡东《法海形象演变的文化意义》。邱高兴主编《佛教与江浙文化(第1期)》,上海三联书店2013年版,第112页。表达出现代人文价值诉求。
此外,《吃教》从批评中国文人学士的“无特操”起笔,进至信仰领域,以“吃教”生动凝练地概括某些追逐现实利益而忽视精神追求的宗教人物,最终达到对国民“吃”的文化现象的艺术概括,可谓简约深刻。再如《庆祝沪宁杭克复的那一边》以庆祝沪宁杭的克复为主题,谈及对佛教大、小乘教的观感评判,鲁迅对大乘佛教义理有深刻研习,但在修持方面则赞同原始佛教的坚毅踏实之风,以此寓意对社会革命的洞见,也是将佛教人物塑造与社会思想、文化批判结合起来。
鲁迅关于宗教人物形象的作品数量较多,笔者不拟遍览详述,上述三种旨趣亦是基本归纳。之所以有如此状貌,根本在于作者的现代启蒙视角和思想力极大地强化了人物性格的思想内涵,然而这并不意味着宗教人物形象缺乏艺术特色。无可否认,那个亟待激浊扬清的时代强化着鲁迅的启蒙立场,杂文多产正当时,无论是肯定抑或批判,宗教人物形象在文本中多趋于简约、扁平与静态化,叙述视角亦彰显主体的坚毅与自信。这种浑厚简约之美有传统艺术风格,亦有现代审美自觉,而且作者的艺术思维健旺运化,如“舍身求法”、“民族脊梁”、“吃教”等已成为宗教人物性格的重要写照,在现代文学史和宗教文化史上有独特价值。
三、审美建构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
近现代中国的民族矛盾与现实忧患让文学面对着严肃、沉重的社会担当,这确实是艺术良知的应然,但社会性的凸显往往造成艺术审美的弱化。鲁迅曾在《杂感》中写到:“无论爱什么,——饭,异性,国,民族,人类等等,——只有纠缠如毒蛇,执着如怨鬼,二六时中,没有已时者有望。但太觉疲劳时,也无妨休息一会罢;但休息之后,就再来一回罢,而且两回,三回……。”[15]其实这近于他对自己创作心态的生动描述。如果说包括宗教人物形象在内的启蒙式创作是紧张的“纠缠”,那么“休息”之时,健旺的审美思维方获得更加充分的释放,生命的深层体验出离逼仄的战壕,展开超越的审美时空,创造出蕴含多重生命体验的散文、小说等,其中便包括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较之启蒙主义的创作路向,审美建构意义上的宗教人物形象数量不多,就人物形象在文本中的地位而言,主要有强势参与和弱势参与两种,前者主要包括《复仇(其二)》中的耶稣、《起死》中的庄子、《我的第一个师父》中的师父及师兄弟等,分别涉及基督教、道教和佛教。这既有偶然性,也显示出鲁迅对宗教人物形象进行审美建构的特点。
鲁迅青年时就呼唤中国的精神界战士及摩罗诗人,其实他自己正近乎于此。王富仁指出,鲁迅是中国文化的守夜人[16]。如果守夜不仅意味着铁塔式的等待,而是从既有的文化地藏中开启生命之光,那笔者更愿将鲁迅视为中国文化进程中具备克里斯玛特质的先知人物。*学界亦有相近观点。冒键《论鲁迅的巨人文化特质》,载《江苏社会科学》,1998年第2期。傅铿指出,传统的形成意味着克里斯玛特质的形成,破旧立新同样需要克里斯玛,甚至双倍于前者方可为之[17]。由此就不难理解鲁迅其人其文的坚韧、执着以及绝不宽恕的性格,更加理解其对国民性弊病的深刻批判,他因洞察中国文化与生命之罪而孤苦,同时又因试图疗救而受难。先知意义上的孤苦与受难应是鲁迅生命中最深沉和难以言说的体验,它无法、甚至也不应在启蒙话语中获得涌流,因此当他在书写作为自己“哲学”的《野草》时,就既偶然也必然地将这种体验投射到先知耶稣的受难形象中,深沉的人生体验由此转化为审美体验。鲁迅说这是对自己受难经历的“复仇”,其实也是在审美观照的意义上获得澄明与解脱。与《圣经》中的耶稣原型相比,基于启蒙者人生体验而来的耶稣形象具有更多的人间性格,*此处受祝宇红的启发。祝宇红《“本色化”耶稣——谈中国现代重写〈圣经〉故事及耶稣形象的重塑》,载《鲁迅研究月刊》,2007年第11期。核心内容是作者以回环往复的手法和深沉简约的语言,叙说痛苦、悲悯、诅咒、欢喜等诸多体验对立融合的受难过程:“丁丁地响,钉尖从掌心穿透,他们要钉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悯的人们呵,使他痛得柔和。丁丁地响,钉尖从脚背穿透,钉碎了一块骨,痛楚也透到心髓中,然而他们自己钉杀着他们的神之子了,可咒诅的人们呵,这使他痛得舒服。”“突然间,碎骨的大痛楚透到心髓了,他即沉酣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18]刘再复指出,丰富的人物性格不仅表现在横向的杂多,更重要的是纵向之深邃,表现出性格深层结构中的矛盾,写出人物性格深处的动荡、不安、痛苦、搏斗等[19]。耶稣形象富有张力与深度的性格可谓呼应着刘氏所说的艺术境界。这种宗教题材的象征式、独语式的人物塑造,创造性地化用了基督教的受难体验,从启蒙者与时代社会的现实关系层面聚焦至个体生命本味的内觉,涌动着主体复杂的自由意志。
鲁迅的杂文是简约深刻的启蒙话语,它当然也会渗入审美创造,影响作者对历史传统的审美式“新编”。如《起死》中的庄子被塑造为性格鲜明的道教人物,他佩戴道冠,会运用道教法术,祈请司命大神显示神威,但在与汉子关于衣服、白糖、南枣等现实生存权利的争执中,志在精神高蹈的哲学家却陷入无奈尴尬,最终以喜剧方式避走。李孺义指出,老庄道体论形而上学总体上要求人面向其生命的境界形态而去在,其全部意义辐辏于人的性体复归,它与个我的社会化生存分别对应“内圣”和“外王”,两者不能互相代替、移位或归属[20]。鲁迅将庄子塑造为“内圣”与“外王”价值错位的性格,就是以此反拨道家“齐死生”、“无是非”、“坐忘”、“心斋”等玄思在社会化维度衍生的误用和异化,为“立人”理想涤除历史积习中的悖谬因素。就艺术性而言,《起死》的对话体形式与《过客》相似,生动简约、富于夸张的言行描写、细节描写、环境描写及古今穿越的奇幻结构,木刻般突出了庄子性格的矛盾性和喜剧性,旁白叙事强化对人物性格的锤炼。需要指出,庄子哲学本有其深刻的人生悲剧感,后来被庸俗化和工具化是令人遗憾的精神萎缩[21]。从这个意义上说,作为对中国古典哲学家的文学重构,此时的庄子形象并非经典的历史文学意义上的再现,而是渗染着杂文的社会批判精神,鲁迅亦自陈“速写居多”,“不免时有油滑之处”[22]。这种写法体现出作者对传统文化的启蒙立场和艺术创造,同时也难免遮蔽道家人物本具之复杂性格。
精神界战士固然多冷峻与紧张,但也有静好的审美自在境界。鲁迅为现代文坛贡献出剑拨弩张、犀利深刻的杂文,也写下有着“闲话风”或“独语体”风格的诗文,以真诚、坦然、自由的言说状态进入审美世界,获得个体生命的意义体验[23]。如鲁迅在去世前不久,曾写下散文《我的第一个师父》,深情回眸童年,以幽默自然的口吻侃侃而谈,从自己生来担心养不活而拜和尚为师开始,以童少趣事、乡间民俗、寺庙生活等营构乡土生活环境,进而以多侧面的言行描写和典型事件如婚姻、受戒等,塑造出民间世俗性格的“龙和尚”及师兄弟们。作者基于现代启蒙立场而来的理性透视和价值评判依然时有闪现,从规范的佛教信仰视角指出师父是个俗人,但在批评的背后是对这位民间和尚朴素真诚的怀念。对师兄弟们的寺庙生活,亦有善意调侃:“我的师父,在约略四十年前已经去世;师兄弟们大半做了一寺的主持;我们的交情是依然存在的,却久已彼此不通消息。但我想,他们一定早已各有一大批小菩萨,而且有些小菩萨又有小菩萨了。”[24]这是与启蒙立场完全不同的创作风格:质朴传统的民间生活,平淡如水的传记语言,宁静含蓄的审美情怀。或许即将离世的鲁迅在自觉不自觉地汲舀夕阳之美,默默回眸辽远大地上的沧桑世情,重温其所在世界纯真美好的童年,酒神式的悲喜剧狂欢或有隐伏,日神的智慧之光徐徐展开,“龙和尚”及师兄弟们已非佛教意义上的僧人,而是从审美之维观照的生命存在,传达叶落归根的淡然平常心境。
至于弱势参与类型的宗教人物形象,在鲁迅作品中普遍处于边缘位置,缺乏充分的性格建构,宗教生活也很少体现,或者付之阙如。如《阿Q正传》中的小尼姑,相关情节与性格刻画都很薄弱,主要是衬托主人公阿Q胆怯又凶狠的二重性格;《祝福》中的柳妈是个吃素的民间善女人,小说中对她的民间信仰生活略有展示,但核心是刻画祥林嫂的性格与命运;《明天》叙述单四嫂子请民间宗教人物何小仙给孩子诊病,她为死去的孩子焚烧《大悲咒》等,重心是表现民间寡妇孤苦迷惘的命运;《奔月》里的道士提供飞升的丹药,以此推动后羿与嫦娥人生命运的演变;散文《从百草园到三味书屋》叙述老和尚捉妖的故事,旨在丰富充满好奇心和幻想的童年生活;《为了忘却的怀念》借用《说岳全传》里高僧坐化的故事,重点不是对佛教人物的批评,而是以幽默苦涩的语调衬托悲苦的现实境遇。从叙述学视角看,他们多属于功能性人物,而非具有审美价值的心理性人物[25]。因为对文本总体建构的参与程度相当弱,所以此类人物形象很难获得独特的美感,微观而论,往往缺乏艺术独立性;宏观来看,则从属于作品的整体风格。
四、现代文学史视域中的考察
近现代中国社会的转型主要是民族国家的独立和现代化进程的开启,在文化层面意味着终极关切的重构,也必然包括古代中国文学向现代形态的演化[26]。随着近代中西文化交流的深化以及梁启超等人对文学启蒙作用的重视,文学在社会变革中被赋予了往昔少有的先锋价值,于是新的审美理想、文学观念、创作主题、人物形象、叙事手法等文学要素渐次生成,旧的则逐渐消弭或边缘化,因此近现代文学是新旧并存、融合转换、递嬗趋新的动态过程。在上述文化与文学的演变视域中,可发现鲁迅塑造宗教人物形象在此类形象的近现代演变中的特定意义。
首先,鲁迅基于启蒙立场对宗教人物形象的塑造在现代文学史上有开创性、代表性和启示意义。众所周知,上古中国没有明确强劲的宗教传统,自魏晋以降,随着佛道文化的发展,文学中陆续出现佛道人物形象,如宗教文学、宋元话本、明清小说等,既有对宗教思想的弘演,亦有文学性的化用,批判性塑造则多从儒家道德理想的视域展开。在近现代社会转型时期,鲁迅作为新文化与新文学的开拓者,其基于启蒙立场的宗教人物塑造体现出现代人文理性和科学精神。与传统儒家道德理想和以善为美的原则不同,这是有时代新意的创作范式与文化视角,主要趋向以真为美的审美理想和新的德性生活建构,*此处受到陈伟的启发。参见陈伟《中国艺术形象发展史纲》,学林出版社2004年版,第300-301页。某些性格描写如“舍身求法”、“吃教”等可谓经典概括,为现代文学人物长廊增添了有特定意涵的形象群。
其次,从中国现代文学与宗教文化对话的角度说,启蒙立场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体现出作者以现代理性与传统佛道信仰及西方基督教的对话、互鉴。杨春时指出,中国的现代性自西方引入时便有片面性,存在着形上领域缺失的问题[27]。鲁迅具有稳健的现代意识与宽广深厚的宗教学养,这使他的宗教人物塑造富有张力和立体性,不仅能够检视社会信仰现象的弊病,而且重视卓越宗教人物的光华,开显形上层面的精神价值,在人物塑造上达到相当深刻和辩证的程度。如对高僧人格的推崇与“吃教”性格塑造形成对比,显示出中道智慧,这是同时代及后来很多作家欠缺的。如果说尚有遗憾,那就是以先生的宗教学养,完全可以塑造出如苏雪林《棘心》中杜醒秋式的人物,*乔以钢等学者指出,这部小说在思想和艺术上有诸多不足。从宗教人物形象塑造的角度说,杜醒秋富有特色。参见徐岱《边缘叙事:20世纪中国女性小说个案批评》,学林出版社2002年版,第60-66页。进而将这种精神对话推进到更深层面。需要指出,鲁迅对宗教人物形象的启蒙式塑造基于现代人文理性与科学视角,而科学与宗教的关系问题尚有很大探讨空间。*例如美国学者英格探讨了宗教与科学之间矛盾与融合的复杂关系,特别是佛教与现代科学有很大的对话空间。参见英格《宗教的科学研究》(上册),金泽等译,刘彭校,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89-94页。从社会文化发展偏至而进的意义上说,彼时传统文化惯性强大,集体无意识使得革新困难,故启蒙理性有利于个体人格建构与时代发展,亦能促进科学与宗教的对话,建构有时代新意的终极关切。
再次,虽然鲁迅在审美建构意义上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比较少,但强势参与类型的人物仍有代表性,不仅体现出他对古代艺术精神的继承,对西方文学与宗教的借鉴,更重要的是在性格内涵与艺术风格上有鲜明的独创性,如耶稣形象,为现代文学的返本开新与艺术探索提供了重要启示。后来其他作家如曹禺、无名氏等,以宗教人物形象塑造继续探索文学审美的终极关切,可谓新的开拓。需要指出,相对于少而精的审美化建构,启蒙立场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更为突出,而且该特点不同程度地渗透于审美建构,可谓历史担当与文学审美的必然性和合。
总体而言,无论中国还是西方,传统宗教与现代理性及审美自由都存在明显差异,因此面临着艰巨复杂的现代转型,更何况中国的现代化须将民族独立提上日程,因此宗教人物形象在现代文学中不是“显学”意义上的人物群像。但如果从社会转型和意义重构的角度说,中国现代文学应创造有卡里斯玛特质的新人物,这是文学审美的历史性担当,也是其对精神生命的承诺,因此宗教人物形象无疑是值得重视、开掘的焦点。从文化人类学的角度说,艺术与宗教同根同源,在契合人的原始思维和心理方面有很大的相通性[28]。今天的文学与文化需要在担当中创新,如果作家在审美创造的同时有深厚的宗教修养,便可吸纳宗教思维与信仰体验,以立体的宗教人物形象涵容人文理性、科学精神与宗教信仰等多面性格,增进文学先天不足的终极关切和人物的精神内涵,拓展独特的审美空间。就人之为人的自觉性与精神性而言,无论沧海桑田,神性总是存在,启蒙不曾瓦解,审美味象澄怀,鲁迅“立人”意义上的宗教人物形象塑造是现代意识与宗教文化的审美对话,对当今消费文化语境中生命超越维度的开显独具启示,有着重要的历史意义。
参考文献:
[1]鲁迅.写在《坟》后面[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2]鲁迅.两地书[M]//鲁迅全集:第1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81.
[3]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8.
[4]许寿裳.亡友鲁迅印象记[M].长沙:岳麓书社,2011:39.
[5][德]伊曼纽尔·康德.对这样一个问题的回答:什么是启蒙[G]//詹姆斯·施密特,编.徐向东,卢华萍,译.启蒙运动与现代性——18世纪与20世纪的对话.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61.
[6]刘再复.中国近现代三大意识的觉醒——在台湾联合报系的演讲(1996)[G]//叶鸿基,编.回归古典,回归我的六经:刘再复讲演集.北京:人民日报出版社,2011:317-319.
[7]郑欣淼.鲁迅与宗教文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4:3.
[8]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7.
[9]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9-31.
[10]鲁迅.中国人失掉自信力了吗[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22.
[11][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48.
[12]吾淳.从道佛二教与民间宗教的关系看中国社会的底层信仰——以现有研究为基础的考察[G]//中国社会的宗教传统:巫术与伦理的对立和共存.上海:上海三联书店,2009:124-135.
[13]邓子美.传统佛教与中国近代化——百年文化冲撞与交流[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1994:8.
[14]闻一多.道教的精神[G]//神话与诗.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2010:124.
[15]鲁迅.杂感[M]//鲁迅全集:第3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52.
[16]王富仁.中国文化的守夜人——鲁迅·自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2:3.
[17]傅铿.传统、克里斯玛与理性化——译序[M]//[美]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5.
[18]鲁迅.复仇(其二)[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78-179.
[19]刘再复.性格组合论[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10:103.
[20]李孺义.“无”的意义——朴心玄览中的道体论形而上学[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99:421-422.
[21]王乾坤.回到你自己:关于鲁迅的对聊[M].北京:中国文联出版社,2001:28.
[22]鲁迅.故事新编·序言[M]//鲁迅全集:第2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54.
[23]钱理群,王得后.鲁迅散文全编·前言[M].杭州:浙江文艺出版社,1991:1-28.
[24]鲁迅.我的第一个师父[M]//鲁迅全集:第6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602.
[25]申丹,王亚丽.西方叙事学:经典与后经典[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0:52-59.
[26]朱德发,魏建.现代中国文学通鉴(1900—2010):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12:1-33.
[27]杨春时.现代性与中国文学思潮[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9:8.
[28]蒋述卓.宗教艺术论[M].北京:文化艺术出版社,2005:4.
The Images of Religious Figures in Lu Xun's Literary Works
REN Chuan-yin
(School of Humanities,Zhejiang University, Hangzhou 310028, China)
Key words: Lu Xun; the images of religious figures;enlightened attitude;esthetic creation
[责任编辑:郑红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