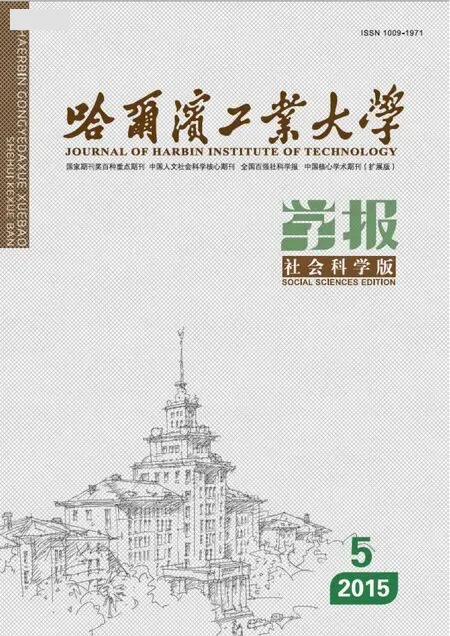清代佛教文学的文献情况与文学史编写的体例问题——《清代佛教文学史》编撰笔谈
2015-03-17鲁小俊
鲁小俊
(武汉大学 文学院,武汉430072)
清代佛教文学,指的是清代僧侣创作的文学,是中国佛教文学史的重要组成部分。清代佛教的发展情况,纵向来看,前中期较为兴盛,道光以后国势衰落,佛教亦式微。就宗派而言,禅宗和净土宗影响较大,其他宗派则相对微弱。明清鼎革之际,禅宗复兴,其中又以临济天童、盘山二系和曹洞寿昌、云门二支最为繁盛。清初以后,禅宗衰落,净土宗仍为佛教各宗的共同信仰。迨至近世,传统佛教日趋衰微,居士弘传佛学,成为中国佛教的中坚力量。清代佛教文学的发展历程与此相关联,又有自身的特点。《清代佛教文学史》试图对其做出符合实际的描述。
与清代佛教文学的实际成就相比,学术界的关注显得很薄弱。例如,日本学者加地哲定《中国佛教文学》(今日中国出版社1990年版)几乎没有涉及清代僧侣的文学创作。在已往的研究中,历来学者最重视清初,其次清末,又次清代中期。其中研究较多者,主要是清初遗民诗僧及清末的少数大家。孙昌武先生《中华佛教史·佛教文学卷》(山西教育出版社2013年版)第九章《宋代以后的佛教与文人》第九节《清代前期文人与佛教》,以及第十三章《近代文人与佛教》,其重心尚不是僧侣作家;陈引驰先生《佛教文学》(上海人民美术出版社2003年版)第九章《近世诗人与佛教》,涉及清代的只有一节《近代诗僧与苏曼殊》;龙晦先生《灵尘化境:佛教文学》(四川人民出版社1995年版)第六章《清及近代佛教文学》涉及的僧侣作家稍多,有弘智(方以智)、大错(钱邦芑)、正志(熊开元)、读彻(苍雪)、超源(莲峰)、达瑛(慧超)、清恒(巨超)、湛汛(药根)、慧琳(梅庵)、祖观(觉阿)、了禅(月辉)、昌仁(一庵)、敬安(寄禅)、苏曼殊等十四位,以及道元、再生、性道、静诺、慧机五位有诗文传世的比丘尼。
这一研究现状与清代诗文的研究状况有些相似而更显滞后。在整个清代文学研究领域,小说戏曲一直是大宗,诗文方面直到最近二十年才真正繁荣起来,而以诗文为主体的“佛教文学史”这类专题研究又更为晚熟。因此,以名家大家为主要研究对象,自然也是研究的初级阶段的主要特点。而这样的状况,显然不足以反映清代僧侣创作的实际情况。要了解清代僧侣的精神世界、生存状态、审美意趣、文学修养,必须对僧侣作家做整体研究,而不仅是名家大家。
较之于前面的几个时段,清代佛教文学文献的主要特点是:作家众多,创作繁荣,文献丰富。根据《清人别集总目》、《清人诗文集总目提要》等工具书提供的信息,现存清代僧侣别集的数量为300多种,有别集传世、可作专题研究的作家近300人(清代僧侣别集在《清人别集总目》中著录作者265人,著作360种,仍有失收的情况,如通琳《大觉禅师遗文》、济悟《鹤山禅师执帚集》等未曾收录;又有明人误作清人者,如智舷等。凡此种种,皆需深入清理)。其中较为重要的别集,多已收入《丛书集成续编》、《丛书集成新编》、《续修四库全书》、《四库存目丛书》、《四库未收书丛刊》、《四库禁毁书丛刊》、《清代诗文集汇编》、《禅门逸书初编》、《禅门逸书续编》、《北京师范大学图书馆藏稀见清人别集丛刊》、《上海图书馆未刊古籍稿本》等大型丛书,除去重复收录者,已经收入丛书的别集数量有60多种(这些可以视作常见文献)。这些别集包含的文体众多,除了通常所见诗文之外,语录、小参、示众、机缘、垂问、拈颂、偈等皆有涉及。此外,方志、山志、寺院志以及总集中的僧侣作品,数量也相当可观。例如《晚晴簃诗汇》,涉及的僧侣作家有260人,其中有不少诗人没有诗集存世。以上这些文献,是编撰《清代佛教文学史》的基础文献。
20世纪以来文学史著作的主流体例是纪传体,其突出特点是按照作家的“等级”安排章节,“一流”作家一章,“二流”作家一节,“三流”作家几个人合起来占一节或一段。纪传体的优势是可以清晰地展示重要作家在文学史上的地位,从而有助于把握文学史的大体走向。我在《清代佛教文学史》的上编部分,即借鉴了这一体例,对大汕、大错、今释、函可、函昰、敏膺、道忞、成鹫、元璟、读彻、敬安等约二十位作家予以专题讨论。
但文学史不仅仅是“大作家”的创作史,众多“小作家”也应该包括在内。纪传体的局限就在于容易把文学史变成重要作家和文学名著的历史,而缺少对更为广阔的文学世界的关注。与纪传体以作家(大家、名家)或作品(名著)为基本单位不同,编年体以时间点(年、月、日)为基本单位和叙述支点,其优势恰在于关注文学发展过程中有价值的细节。与此相关联,在对基本文献的占有和使用方面,纪传体可以只关注重要作家和重要作品,而编年体则要求对每个时间点上的文学事件和人物通盘考虑,即便是名家名著,也应置于当代文学的“话语体系”之中。因此我在《清代佛教文学史》的下编部分,采用的是编年体的叙述方式,旨在将众多“小作家”纳入进来,从而尽可能地反映清代佛教文学的整体面貌。
抛开“等级”观念,以编年的方式,对有作品存世的僧侣作家进行观照,所遇到的一个主要问题是,文学史不应该也不可能是“全体僧侣作家年谱合编”,那么,究竟哪些史实和作家应该被写入佛教文学史?这时,或许新历史主义的文学史观更为适用,即建构文学史的目标不是所谓还原或再现历史,而是用新的话语或文本表述新的“意义”。
具体而言,在下编的编年体部分,自然会涉及名家大家。而在上编部分,相关名家大家已有纪传体的叙述,对其生平和创作皆有较为充分的表述,因此在下编部分,将侧重叙述其“群体性”的文学活动。例如释敬安,除了在相关年份交代生卒、重要行迹等项之外,将突出其与其他僧侣、作家的交往,以及纪传体部分不便叙述的史实。如:
“光绪十二年(1886)六月,王闿运集诸名士开碧湖诗社,敬安与会。九月,复至长沙,敬安赴王闿运、郭嵩焘招集之碧浪湖重阳会。”
“光绪二十一年(1895)冬,敬安与王闿运等人集长沙浩园,又在上林寺为易佩绅作寿。”
在编年部分展现这类史实,可让我们对于具体时间点上,僧侣作家的行迹和交游有更直观的了解。再如:
“光绪二十年(1894)夏,大旱,敬安奉湖南巡抚吴大澂之请往黑龙潭求雨,愿以死解民忧。”
在陈述这一史实之后,再将敬安关注民生的其他诗作予以介绍和论述,从而与上编释敬安的专题形成“互见”。
又如,有些史实放在纪传体中可能有些突兀,放到编年体中则较为自然,且可见出前后之联系或变化。顺治二年(1645)除夕之夜,释通复写了一首诗,其中有“醉中身世还惊梦”之句。自注云:“律酒之为禁,在第五之条,所甚重也。予既啬于饮,又恡于戒,有所撰咏,且讳其字,自欺欺人,非两失乎!今得此句,即用表出,后有及之,纪自今始。”(《冬关诗钞》卷四)这首诗很可以见出作为僧人的通复,在面对“酒”时的特殊心态。近些年的文学史撰写,较多地注重细节和过程(参见蒋寅《进入“过程”的文学史研究》,《山西大学师范学院学报》2001年第1期),而编年体的独特优势即在于能够自如地处理这类文学史的细节问题。
至于上编纪传体部分没有专题论述的“小作家”(包括有别集传世者和仅在总集中存有作品者),皆归入下编编年体的部分。这样做旨在避免文学史的“空白”。在一定程度上,文学史家有点像说书人。譬如说书人讲究“有话则长,无话则短”,而所谓“有话”和“无话”则取决于说话人对事件重要性的主观判断。文学史家也是这样,常常在“重要的”文学发展阶段花费较多的笔墨,而在“不重要的”阶段言简意赅甚或付诸阙如。这样,文学史著作的页数与文学的历史过程并不一致,而这种不一致在通常情况下是必要的。但同时,这种不一致是否会遗漏某些可能不“重要”但很有“意义”的历史过程,则是我们不能不谨慎考虑的问题。譬如明代前期一百多年的小说发展状况,长期以来在通行的文学史著作中几乎是不占有页码的。而实际上,明代前期市井民间的小说创作和传播从未间断,这一点,最近这些年已经引起了不少研究者的关注。清代佛教文学史也是如此,清代前期和后期名家辈出,创作兴盛,在前面纪传体的部分,也是以这两个时期为重头戏;而中期则相对薄弱。我以编年体来解决这个问题,并不是说文学进程应该按照时间平均分配页码,而是指编年体本身要求对所有文学时间做平等的扫描和客观的记录,因而不容易出现所谓平庸的文学时代或文学史的空白时段(至于因文献缺失而无法纳入视野的时间点则另当别论),从而尽可能地避免有意义的文学史实的遗漏。在这一部分,我的基本原则是“大家求精,小家求全”。存世的众多清代僧侣别集,以及其他相关作品,则为编年体的佛教文学是叙述提供了充分的文献依据。
编年体的文学史叙述,也有其自身的问题。重视细节固然有助于建构“原生态”,但同时也容易忽略整体和大局。“近些年学界颇受法国年鉴学派的影响,细节的意义的确受到了应有的重视,但是有些学者经常忘了为什么要关注细节,往往是见木不见林,正像有人讽刺那些只重细节史的邯郸学步中人,他们知晓1789年巴黎的面包价格,但却不知道这一年爆发了法国大革命,忘却了年鉴学派也是具有‘长时段’和‘总体史’眼光的。”
(吴晓东《历史如何触摸》,《读书》2006年第12期)在历时态地展示清代佛教文学发展历程方面,编年体有其自身的缺陷,即不具备宏观把握历史事实的功能,历史进程被分散在各个时间点中而缺乏高屋建瓴的概括。因此,有必要借鉴纪事本末体的叙事方法,在适当的时间点对重要史实详其起讫,做历时态的叙述;同时在总论部分,加强宏观性的论述。这里将侧重两个方面:一是发展历程,二是文学谱系。就发展历程而言,清初佛教文学以遗民诗最为突出,无论是咏物、写禅境还是咏叹兴亡,悲凉情怀是此期佛教文学的主旋律。迨至清代中叶,由于社会结构的变化等诸多因素,佛教文学也体现出明显的世俗化特征。嘉道以后,国势日衰,佛教不振,但僧侣创作仍然有相当的势头,不可避免地染上了浓郁的近世色彩。就文学谱系而言,最突出的是以寺院为中心而形成的谱系。它不同于一般文学流派的流动性,而具有固定的地点依托,由此形成的世代相传的文脉,比之一般的文学流派更具有稳定性。其中镇江定慧寺、宁波天童寺、杭州灵隐寺等可为代表。而一般文学史著作中关于清代文学史的论述,皆称清代为古代文学的集大成时期。这一论断并非普遍适用。就清代佛教文学而言,并不具有集大成的性质。时代性、地域性、谱系性,是清代佛教文学最重要的特征。
概而言之,鉴于清代佛教文学文献的丰富性,《清代佛教文学史》采用了纪传体和编年体相结合的叙述方式,而在建构若干大判断方面,则借鉴了纪事本末体。目的在于尽可能全面地展示清代佛教文学的历史进程,至于能否达到预期目标,还有待于实践检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