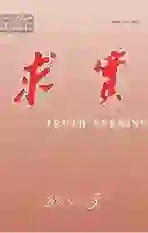析“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是现实的个人”
2015-03-16唐瑭陈红桂
唐瑭+++陈红桂
[摘要]《德意志意识形态》标志着历史唯物主义的成熟,但《形态》中把唯物史观的前提界定为“现实的个人”而非物质生产,这一方面基于马恩批判对象话语的相似性,另一方面基于马恩理论话语的现实背景。“现实的个人”包含了对“现实”(生产力、生产关系等现实进程)的关注和对“人类社会”的双重关注,搭建历史主体与历史活动的桥梁。马克思恩格斯从物质生产实践角度理解历史矛盾,在历史本质矛盾中思考“现实的个人”的解放意义,实现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统一。
[关键词]唯物史观;历史前提;《德意志意识形态》;历史主体;社会关系
[中图分类号]B03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007-8487(2015)03-0033-06
[收稿日期]2014-10-10
[基金项目]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社会科学基本科研项目(2010SJD710012)。
[作者简介]唐瑭(1983-),男,安徽泾县人,厦门大学哲学系师资博士后,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发展史与西方马克思主义研究;陈红桂(1978-),男,江苏高邮人,南京航空航天大学人文学院副教授,主要从事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
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以下简称《形态》)中提出“现实的个人是唯物史观前提”,而不是将现实的物质生产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这似乎说明“现实的个人”较之物质生产概念更为全面。从马克思恩格斯文本研究角度来说,在《形态》或更早的《评李斯特》中已经生发出从现实历史进程出发来研究现实问题的倾向,但是这种词句的出现并不意味着历史唯物主义真正的成熟。虽然我们普遍认为马克思恩格斯在《德意志意识形态》中已开始引入现实性因素,并已从人本主义思维逻辑转向了从现实出发的科学逻辑,但总的来说,“现实的个人”中现实因素还很淡薄,此时,这一概念给人更多的感觉是抽象意义上的个人,似乎与马克思此前批判的费尔巴哈“现实的人”并没有很大差距,从“现实的个人”入手,给人一种仍在人本主义框架中绕圈子的嫌疑。此时,“现实的个人”更倾向于一个想要向现实的个人靠拢的抽象的类本质概念,与以往人本主义者相比,这一历史前提的变革性似乎并不突显。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历史唯物主义的中心线索是物质生产实践,马恩却没有直接用生产或诸如生产资料之类的概念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而将“现实的个人”这样一个似乎还带有人本主义色彩的词语作为前提,因此,深入理解“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是现实的个人”,将深化对历史唯物主义的理解。
一、从马恩原初语境探讨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为“现实的个人”
马克思恩格斯的《形态》并不是一本简单的历史唯物主义的教科书,创作这本书的理论目的是用以批判当时的德国哲学。在马恩看来,“从施特劳斯到施蒂纳的整个德国哲学批判都局限于对宗教观念的批判。出发点是现实的宗教和真正的神学”[1](P21),这些哲学家的出发点都是宗教的人。马恩认为,他们“没有一个想到要提出关于德国哲学和德国现实之间的联系问题,关于他们所作的批判和他们自身的物质环境之间的联系问题”[1](P23)。所以,马恩希望扭转当时德国哲学脱离现实的哲学思考,而解决这个问题的关键就是提出“现实的个人”这一概念。
在马恩看来,“我们开始要谈的前提并不是任意想出的,它们不是教条,而是一些只有在想像中才能加以抛开的现实的前提。这是一些现实的个人,是他们的活动和他们的物质生活条件,包括他们得到的现成的和由他们自己的活动所创造出来的物质生活条件。因此,这些前提可以用纯粹经验的方法来确定”[1](P23)。并同现实的分工、所有制的探讨紧密联系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认为:“以一定的方式进行生产活动的一定的个人,发生一定的社会关系和政治关系。经验的观察在任何情况下都应当根据经验来揭示社会结构和政治结构同生产的联系,而不应当带有任何神秘和思辨的色彩。社会结构和国家经常是从一定个人的生活过程中产生的。但这里所说的个人不是他们自己或别人想象中的那种个人,而是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1](P28-29)那么,关于这一概念具体应该如何理解?在《形态》中,马恩又是如何展开来论述这一问题的呢?我们可以结合马恩的具体文本,深入论述这一问题。
第一,在《形态》中,马恩指出:“任何人类历史的第一个前提无疑是有生命的个人的存在。”[1](P23)这种界定本身并不稀奇,和其他探讨历史与人的关系一样,从“有生命的个人”出发来探讨历史的前提。但问题还不仅于此,马恩进一步认为:“我们的出发点是从事实际活动的人,而且从他们的现实生活过程中我们还可以揭示出这一生活过程在意识形态上的反射和回声的发展。”[1](P30)“它的前提是人,但不是某种处在幻想的与世隔绝、离群索居状态的人,而是处在一定条件下进行的、现实的、可以通过经验观察到的发展过程中的人。”[1](P30)这就将这种“有生命的个人”现实化了,而且同从事实际活动的“现实的个人”联系起来。这就比单纯的只是从生产力、生产关系的物质生产活动来思考历史的前提前进了一大步,因为,这类活动都失去了人的参与,变得愈加抽象;同时,现实化的人扬弃“有生命的个人”,使人从抽象的人转化成人与环境、人与历史的关系探讨,从关系层面重新建构唯物史观视域下的人,使其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唯物主义内涵。
第二,从历史本质层面尤其从历史本质矛盾中进一步拓展了对“现实的个人”的探讨。从历史本质层面思考历史与哲学的问题起源于西方哲学,自苏格拉底以来西方哲学家都喜欢将社会、国家、人统一在一起思考问题。柏拉图的《理想国》主要是从理念世界出发,外在于现实社会探讨现实社会问题,当然,他对理想国的构想在很大程度上参考了他一直崇尚的斯巴达的国家机制,但总的来说,还离现实太远,抑或说,这一学说建构出来之后,它在实现措施等各方面都与理念世界相关而离现实太远。柏拉图自身理论的一个悖论在于理念世界与可见世界之间没有一个可以沟通连结起来的桥梁,这也注定了理想国的理想性太强而缺乏现实可操作性。这也导致了柏拉图《理想国》以后的很多西方哲学家在面对现实生活的不完善时,总会回归到类似理想国的思路,试图构造一个人类社会的理想蓝图。马克思也不例外,但不同之处在于,马克思理想蓝图构造的参考点不同。马克思构想的社会的立脚点更加贴近现实,马克思从客观的历史矛盾中寻求历史与人的关系,他的历史本质论并不是抽象固定的,而是历史发生学意义上的,从生产与生产关系内在矛盾中探讨现实的个人与历史环境的关系。马恩认为,从“现实中的个人,也就是说,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因而是在一定的物质的、不受他们任意支配的界限、前提和条件下能动地表现自己的”,“但这里所说的人们是现实的,从事活动的人们,他们受着自己的生产力的一定发展以及与这种发展相适应的交往(直到它的最遥远的形式)的制约”[1](P29)中体现出来,关于社会、国家和个人的研究一直是整个哲学史上的一条线索,也是唯物史观研究的出发点。历史唯物主义真正实现了对传统哲学抽象性的扬弃,从社会历史矛盾中探讨了社会、国家和个人的关系,从唯物史观的视角下,探讨了“现实的个人”存在的历史必然性及其历史的可能性,将历史唯物主义矛盾所概括出来的历史的本质矛盾与历史主体紧密结合起来。
笔者认为,历史唯物主义之所以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重要的原因是唯物史观不仅仅是探讨历史矛盾,梳理历史规律,还有其强烈的人文关怀、价值使命。马克思恩格斯自始至终都是以对人类的现实关怀为依托,马克思主义从人本主义的抽象性向历史唯物主义的现实性转向,处于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恰恰衔接了这一过渡。其中,“现实”表明历史唯物主义开始从历史发展的客体向度说明问题。同时,马恩并没有忽视历史主体的革命意义,而“现实的个人”正好从历史唯物主义的主体向度说明了这一问题,所以,“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体现了历史的主体向度和历史的客体向度的统一。马克思的历史唯物主义不仅是客观规律学说,还是以历史为中介统一历史主体和历史客体的历史辩证法。或者说,马克思的唯物史观,正是从现实的个人而向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统一发展的。“现实的个人”因而是唯物史观的最初前提并贯穿其中,当然,“现实的个人”在唯物史观的具体发展中是有变化的,这将在下文具体阐述。
二、从现实革命角度理解“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历史前提的意义
马恩非常注重“现实的个人”同历史环境的结合,并深入讨论其间形成的一定的历史关系中的历史主体。在他们看来,“历史的每一阶段都遇到有一定的物质结果、一定数量的生产力总和,人和自然以及人与人之间在历史上形成的关系”[1](P43),“这些个人是从事活动的,进行物质生产的”[1](P29)。在这个探讨中,“个人”被凸显出来,因此,梳理“个人”概念发展史就显得尤为必要。
随着语言学的发展,“人”的概念在其历史上有了几层具体含义。如英语语境中的人格化的人(Person),原子个人(Individual),肉身性的人(Human)等,德语语境中与之对应的分别是Person,Individuun,Mensch。在这些关于“人”的概念的历史演变及其在各自具体语境的运用中,伴随着正当性、权利(Recht)、私有制(Eigentum)、占有(Besitz)、意志(Will)、劳动(Arbeit)等。从这些概念的演绎中,初步能够看出“人”中所伴随的经济关系。上文已经说过,“现实的个人”一定存在于具体物质生产活动中。“他们是什么样的,这同他们的生产是一致的——既和他们生产什么一致,又和他们怎样生产一致。因而,个人是什么样的,这取决于他们进行生产的物质条件。”[1](P24)也就是说,人不是抽象的存在物,而是现实的个人,并且他们的具体物质生产活动决定了人的具体内涵,人在具体的物质生产中获得了社会历史性存在的具体规定。
区别于那些“没有任何前提的德国人”,马克思进一步考察了历史的关系的四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人类生存的第一个前提,“这个前提是:人们为了能够‘创造历史,必须能够生活。但是为了生活,首先就需要吃喝住穿以及其他一些东西。因此第一个历史活动就是生产满足这些需要的资料,即生产物质生活本身”[2](P23),即人的最基本需要的满足。第二个方面是“已经得到满足的第一个需要本身、满足需要的活动和已经获得的为满足需要而用的工具又引起新的需要”[1](P32),即物质生活资料的生产。第三个方面是人的种族繁衍。“每日都在重新生产自己生命的人们开始生
产另外一些人,即繁殖。这就是夫妻之间的关系,父母和子女之间的关系,也就是家庭。这种家庭起初是唯一的社会关系,后来,当需要的增长产生了新的社会关系而人口的增多又产生了新的需要的时候,这种家庭便成为(德国除外)从属的关系了。”[1](P32-33)第四方面是社会关系的生产。“人们之间是有物质联系的。这种联系是由需要和生产方式决定的,它和人本身有同样长久的历史;这种联系不断采取新的形式,因为就表现为‘历史。”[1](P34)在这四个方面,是以生产为主线索,以“现实的个人”为前提,马克思恩格斯建构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场景,统一了自然关系和社会关系的生产。在物质生产的过程中,人们一方面和自然相连结,生产出了自然关系,另一方面人与人之间的生产关系也历史性地构成了,“现实的个人”成了历史活动的前提。
但是,这种历史活动的建构同现实的个人的结合,只是从广义历史唯物主义角度探讨了历史唯物主义的基本原理,马恩从生产过程中进一步深化了对该问题的理解,而且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矛盾中思考现实的个人同历史的关系,在他们看来:“已成为桎梏的旧交往形式被适应于比较发达的生产力,因而也适应于进步的个人自主活动方式的新交往形式所代替;新的交往形式又会成为桎梏,然后又为别的交往形式所代替。由于这些条件在历史发展的每一阶段都是与同一时期的生产力的发展相适应的,所以它们的历史同时也是发展着的、由每一个新的一代承受下来的生产力的历史,从而也是个人本身力量发展的历史。”[1](P81)在此,马克思恩格斯从社会的历史矛盾,即生产力和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来思考社会历史发展的动力,在他们看来,一切历史冲突都根源于生产力和交往形式之间的矛盾。人类社会正是通过这一矛盾发展出人类社会的历史,当生产力与交往形式相协调时,人类社会向前发展,当生产力同生产关系的矛盾不可调和时,实践将迫使无产阶级反对资本主义(交往形式),产生超越资产阶级社会的无产阶级革命意识,形成科学的共产主义运动。“它推翻一切旧的生产关系和交往关系的基础,并且破天荒第一次自觉地把一切自发产生的前提看作是先前世世代代的创造,消除这些前提的自发性,使它们受联合起来的个人的支配。因此,建立共产主义实质上具有经济的性质,这就是为这种联合创造各种物质条件,把现存的条件变成联合的条件。”[1](P79)这样,共产主义将不再是空洞的口号,而是同现实社会历史矛盾结合起来,并且以现实的个人为客观前提,现实的个人又同社会生产的历史矛盾统一在一起,马克思恩格斯真正实现了历史学科的科学性和革命性的辩证统一。
三、从哲学史的角度探讨“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历史前提的意义
笔者认为,马恩提出“现实的个人”在哲学史上具有革命意义。纵观马克思主义发展史,马克思主义的很多概念是建基于对德国古典哲学相关概念的扬弃,甚至在探讨“现实的个人”时,我们都会因为德国古典哲学的学缘关系,将其与费尔巴哈的“类本质”等概念联系起来。因此,非常有必要厘清马恩的哲学史背景,深化“唯物史观的历史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在哲学史上的变革意义。
马恩批判费尔巴哈强调类本质层面的人,其实,费尔巴哈也谈“现实的人”,但是,费尔巴哈的“现实的人”最终还是要落实到人与人之间“爱”的关系,费尔巴哈在摆脱了世俗的宗教之后又建立了爱的宗教。施蒂纳的“唯一者”可以说看到了与费尔巴哈的类的“人”不同的个体层面的人,他意识到费尔巴哈的人与神一样是一种抽象空洞的概念,人的具体性被淡化或弱化,因此,施蒂纳从现实生活中的“唯一者”入手,引入了活生生的个体人。但总而言之,施蒂纳的人依然是一种抽象的概念,他过多地关注“唯一者”而忽视了与“唯一者”相联系的他者以及其间关系的形式和内容,放弃了社会关系背后的历史矛盾线索。所以,马克思的“现实的个人”既不是费尔巴哈感性存在意义上的人,也不是施蒂纳的“唯一者”,而是具体到物质生产实践(感性活动)中的个人。
从整个西方学术史上看,三种具体的人——Human、Individual、Person在不同语境中揭示了不同的内涵,在《形态》中,人的意义对应着人格化的人“Person”。“唯物史观的前提是现实的个人”这一命题中的“人”是单子化的人,是“Person”。
为什么这样理解《形态》中的“人”?一方面,《形态》所创作的1846年,欧洲处于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在手工业资本主义时代,单个“person”成为经济的主体,而单子化的个人交往及其经济关系成为社会关系的主要内容。另一方面,马恩深受英国古典经济学家亚当·斯密分工理论的影响,在他们看来,分工是促进社会效率、提高生产能力的主要动力,分工也成为了促进民富、追求公平的基础。但是,现实的社会经济事实并不促成民富的理想状态,与同期的一般共产主义理论一样,马恩开始批判现实,寻求“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路径,并促使对资本主义经济现实的批判转向科学共产主义。所以,马恩强调:“共产主义对我们来说不是应当确立的状况,不是现实应当与之相适应的理想。我们所称为共产主义的是那种消灭现存状况的现实的运动。这个运动的条件是由现有的前提产生的。”[1](P40)
随着理论兴趣的转移,马克思文本对象的目标也发生了变化,但是,这条逻辑依然贯穿在马克思一生的理论批判之中。即使在马克思晚年的政治经济学批判中,马克思依然对“现实的人”做了更深入的研究,他坚持扬弃机器大工业所生发的古典经济学的技术性批判,从资本主义新的发展形式中解剖现实的人与人之间关系的内在矛盾,进一步完善了历史唯物主义。
“现实的个人”内涵也被赋予新的时代意蕴。1848年欧洲大革命以后,欧洲出现短暂的经济繁荣,机器大工业逐步取代手工业劳动,成为新兴生产力的新的标志。古典经济学家更多地看到机器大工业与具体个人之间的力量悬殊,从实证层面认同资本主义生产关系对人的剥削。马克思则从“阶级”的角度进一步研究历史活动的主体,从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中重新思考“现实的个人”。此时,“现实的个人”不再是分工意义上的单子化的人,而是具有总体性的“阶级人”,政治经济学的批判不仅为我们提供了科学认识社会的理论,更重要的是为无产阶级解放提供了理论武器。
笔者认为,如何正确理解“现实的个人”,成为能否正确理解历史唯物主义的关键。唯物史观着重于从资本主义社会的深层机制出发,这种研究对象似乎是与人无关的历史客观机制,但理论核心仍然是围绕着现实的人的解放展开的。无论是政治经济学批判,还是晚年的人类学研究,马克思都是为了探讨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路径,但是,这种解放不是抽象、空洞的口号与理想,更不同于当代西方左翼的激进解放,而是从理解资本主义的客观矛盾入手,从社会本质层面揭示了在一定历史关系中的“现实的个人”的解放。这样,作为唯物史观前提的现实的个人就具有了丰富的历史内涵,“现实的个人”同历史活动紧密结合在一起,体现了生产力与生产关系的内在矛盾。“现实的个人”作为唯物史观的前提,就真正实现了历史唯物主义的科学性与价值性的统一。
参考文献:
[1]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0.
[2]马克思恩格斯.德意志意识形态(节选本)[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责任编辑郑百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