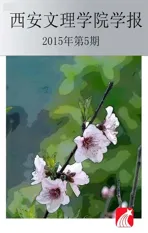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文化消费探析
2015-03-01柏悦
柏 悦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影视艺术文化研究】
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文化消费探析
柏 悦
(北京师范大学 历史学院,北京 100875)
从1929年历史上最严重的经济危机爆发到20世纪40年代中叶,美国一直笼罩在大萧条的阴影下。但此时电影业蓬勃发展,美国人对于电影的消费显露出极大的热情,从而折射出美国人奢侈的物质消费观受到极大的冲击,文化消费开始与物质消费出现分庭抗礼的局面。美国人的工作伦理也从此有所改观,娱乐休闲的地位大幅提升。这一切最终促成了美国大众消费的转型,美国人的消费观也在大萧条时代进一步发展塑成,现代化程度进一步完善。
大萧条;美国电影业;文化消费;大众心理
1929年秋,史无前例的股市大崩盘让富极一时的美国瞬间跌入到大萧条时代(本文主要是指20世纪20年代末到20世纪40年代初,共15年左右)。1934年6月仅加利福尼亚州就有高达70万名产业工人失去工作,其中洛杉矶就占了一半,而这些居民中的五分之一几乎不能靠“每月每家16.20美元”的补助来支撑日常生活。[1]种种类似事例不胜枚举,美国民众正处在朝不保夕的困境中,而大萧条对美国金融业、工业、农业等带来的重创更是难以言喻。但正是在这个最艰难困苦的岁月,大众文化消费尤其是电影消费成为了这个惨淡时代的一抹亮色,更为后来美国大众消费的稳定和繁荣奠定了基础。
一、大萧条时代电影消费兴起的背景
1920年代美国加州洛杉矶郊外的一个不知名的小镇好莱坞声名鹊起,这里聚集着星罗棋布的电影行业,被誉为美国人的造梦基地,也是金钱和奢靡的代名词。然而不到10年的时间,大萧条时代的来临让众多昙花一现的中小电影企业纷纷倒闭歇业,电影产业在摧枯拉朽般的重组之下最终被规制为垄断资本主义的模式。美国电影行业八个巨头由此产生,即后来为人所知的八大电影公司,也就是米高梅、派拉蒙、20世纪福克斯、华纳、环球、哥伦比亚、联美、雷电华。[2]23-29
电影行业与美国其他行业一样,也迈入了垄断企业的行列,直到把电影业作为产业优化运营推向完备。影片可以类比为流水线上制造出来的汽车,告别了手工作坊的小成本生产,直接进入大工业化时代。生产、发行和放映上的一体化,保证了电影产业从生产环节到流通领域都能最大成效地节约时间和金钱,将产品的预算、生产和流通相对固定下来,减少不必要的支出和风险。电影工业化的盈利模式不断被寻找和完善,电影业从此开始以最大程度挖掘其内在的商业价值。兜售电影的“商场”——电影院在大萧条时期显示出睥睨其他商业的傲人姿态。1929年,覆盖全国各个城镇的影院数量达到历史上的最高点——超过23 000家,是旅馆数的两倍,是百货公司数的三倍,[3]甚至多于银行,为30~40年代电影消费的繁荣奠定了最基本的保障。到了1941年,平均每12.5个美国人就拥有一个电影院座位。除此之外,电影院的规模装潢在一定程度上也发生了变化,邻家的小型电影院逐渐代替1920年代初期宫殿式的大型电影院,于是普通的工人阶级也可以坦然地进行消费。[4]
大萧条之后电影院的激励消费策略亦层出不穷,影院向观众附送诸如枕头、瓷器、自行车、丝绸、袜子、台灯、手表来吸引人们走入电影院,[5]或者开设如“大减价之夜”“十美分之夜”“家庭之夜”等午夜专场。[4]
电影业在大萧条中幸存并壮大除了内在的完善,还要得益于外在的政策扶持。具体来说,这与罗斯福在大萧条时期推行新政所带来的帮助和支持是分不开的。1933年成立的国家复兴局(National Recovery Administration)与美国电影业相互作用,一方面加强了发达资本主义中的统治阶级用以谋得最大利益的一整套财产关系,另一方面也使政府成为大商业组织的同盟。[6]电影业作为垄断资本主义中的后起之秀,必然受到政府的大力关注。1934年联邦政府成立了传播媒体委员会(Federal Communications Commission),专门负责管理广播电台及影视等大众传播业的运作,[7]以此加强了对电影业的监管。
二、物质消费与电影文化消费的此消彼长
美国在20世纪初完成的大规模、大批量现代化工业生产需要人们更新消费观念。大萧条前期美国人的热情都放在批量购买奢侈品上,一个车库中存放两辆汽车并不罕见,但此时消费市场已经表现出奢侈过度的特征,物质膜拜已经如日中天;勤俭持家、集腋成裘的良好传统也被一夜暴富的现象所打破,人们的消费观念已经彻底失去节制。富足的城乡公民的生活笼罩在物质享用主义的表象之中。“自一战结束以来,那些不断倾泻到美国家庭中的小器具——电烤箱、搅蛋器、烤架、烘饼烤模、咖啡渗滤器、洗衣机、电炉——连同家具和缝纫机的销售洪流,到30年代初期突然减速。汽油和汽车配件的销量一直不错,新车的交易量却像铅锤那样垂直下降,开一款去年流行的也不再不光彩。曼哈顿街头的出租车司机们,无奈地发现自己的收入已然从每天7美元降为2~3美元。”[8]21而就在物质消费走向低迷、出现巨大下滑的同时,人们却对电影消费产生了巨大的兴趣。尽管1/3的电影院没能等到1933年夏季的电影复苏就提前关闭,尽管在大萧条到达最低谷时电影观众数量经历了一个短暂的低潮,但在整个经济危机之中,电影观众数量仍旧保持着稳定的增长。每星期会有8 500万美国人走进电影院,每家影院一年放映100~400部影片,八大制片厂平均每周生产一部影片。1934年国家娱乐联合会(National Entrainment Association)对 5 000人进行调查统计,统计结果显示看电影是排名第三的娱乐活动,仅次于成本更为低廉的听广播和看报纸。[9]126仅以1939年为例,全国1.5万家电影院票房收入达到近7亿美元,平均每个家庭每年在电影上花费25美元。1936年《命运》杂志研究发现美国观影群体中青少年和儿童的比例高达36%,电影不再只是成年人娱乐休闲的专利。另外电影消费的阶级分布也越来越均衡,其中“28%属于富有阶层,27%的观众属于社会阶层较低的人群,19%的观众是穷人”,社会学家华特(W. Lloyd Warner)和伦特(Paul Lunt)发现很多身处北方的失业工人在1930年代中期在电影院消磨时光成为普遍现象,[10]8电影真正成为了全民娱乐,看电影这种往日便于区分阶级的高雅文艺活动越来越走向普通人。
人们在消费电影的同时,由电影所带来的周边消费也逐渐铺展开来,与电影消费相互刺激、相互影响。电影业不仅仅是对影片本身的消费,更促进了其周边消费,电影业的繁荣带来了大众消费狂欢的热潮。1920年代的电影院几乎不贩卖任何食品,因为那样做有违电影院高雅的艺术格调。如今电影院司空见惯的爆米花和糖果在当时被认为不符合上层阶级的品位,尤其爆米花在美国人眼中属于移民用马拉车带来的脏兮兮并且口味低劣的小吃,往往与下层阶级低俗的娱乐滑稽歌舞杂剧(burlesque)联系在一起。大萧条时期电影蜕变成为属于各个阶层的大众消费,电影院也“屈尊纡贵”地开始售卖糖果和爆米花,大众消费的标志——饮料界巨头可口可乐也逐渐出现在电影院的小卖铺里。[5]除了看电影过程刺激了周边的大众消费之外,电影的影响力还拓展到电影之外的消费上。1934年电影巨星克拉克·盖博在影片《一夜风流》中脱下了自己的衬衫,直接袒露胸膛,这一行为立即为全国的男士们效仿,只是因为一个电影明星在影片中的一个形象,就使得他们放弃由来已久的穿贴身内衣的习惯。[11]这看似是一则娱乐趣闻,但却给男士内衣的消费习惯带来了前所未有的改变。电影带来的消费效应已经蔓延到社会的各项相关消费之中。
三、对娱乐的重新认识与美国民众移情电影院
(一)对闲暇时光的重新认识促进文化消费
经济危机时期井喷式的电影文化消费与通货紧缩以及新政对娱乐休闲和设施场所的财政支出关系密切。[12]51除此之外,美国人对娱乐的重新认识也是促进文化消费的一个重要因素。美国的失业人口由经济危机之前的200万人增加到1 000万至1 500万,1932年失业率一度到达25%,美国民众陷入了前所未有的空虚之中,手中握着大把的闲暇时间却无处排遣。而实际上并不是失业加剧单独造成的结果,在此之前大机器的使用不仅让工作难度有所下降,而且使工作时间大为缩短,由19世纪的每星期70小时缩短到不足50个小时。可以断定的是“闲暇时光正在增加,并且必定会越来越多”,[12]19大萧条只是把闲暇时光增多这一本应循序渐进的现象以一种突发的形式呈现在美国人的面前。因为依照美国的传统,娱乐是不被认可的。从美国清教的宗教文化立场看来,宗教信仰让人们相信自身带有原罪,而娱乐则是撒旦诱惑堕落之人的手段,所以一切娱乐并不具备合理性和合法性,闲暇时间的娱乐遭到最大程度的挤压,只有工作与劳动才是生活的全部;只有通过劳动人才能得以拯救。与这种劳动神圣观相对应,娱乐成为人罪恶感的基本形式。“好的劳动技能取悦于上帝,又有益于劳动者。劳动者通过劳动在上帝那儿获得恩惠的奖赏,但这不是因为他们应该获得这份奖赏,而是因为上帝的慈悲把这种神圣价值馈赠于劳动者。”[13]53除此之外,14世纪之后的商业繁荣导致城市人文主义观念的崛起,18世纪工业革命从工业产生创造的角度进一步把这种人文传统巩固下来,使之成为人类社会的基本原则。
通过数据分析,结合产品总出成和综合售价两个方面的综合考虑,在毛鸡只重为5.10×500g时,有相对较高的总出成和最高的综合售价。所以,确定车间肉鸡屠宰中毛鸡的最佳只重为5.10×500g,对养殖端的毛鸡养殖的最佳只重范围提供一定理论依据,进而对屠宰车间的最大化价值生产提供一定的原料支持。
但是在娱乐休闲被罪恶化、被排斥的同时,相比预示着资本主义时代之前那种娱乐和劳动根本没有概念界定,混为一体的观念已经做出了跨越式的进步,“娱乐从劳动中分离成为罪恶实际上也是人们自由观念演进的变形形态之一。娱乐在特定的时空区域摆脱任何神灵和所有劳动伦理戒律的拘禁,表明人类的生活方式中已经有一部分不属于上帝而属于人类自身”。[14]接下来必然就会经历着原本工作伦理的丧失以及娱乐伦理逐渐凸显的阶段,美国著名文化批评学者丹尼尔·贝尔把那种悄然兴起的现象称之为大众享乐主义,“一场更为深刻的变革正在社会结构中进行。这是经济体系中动机和报偿方面的变革,镀金时代的财阀资产明显增加,意味着劳动和积累本身不再是目的,而是进行消费和炫耀的手段、地位及其象征,而非劳动和上帝的遴选,变成了成就的标志”。“大规模生产和高消费开始改造中产阶级的生活。实际上,讲究实惠的享乐主义代替了作为社会现实和中产阶级生活方式的新教伦理观,心理学的幸福说代替了清教精神。”“‘新资本主义’在生产(即工作)领域仍然需要新教伦理,但在消费领域却刺激娱乐和游戏的需要。”[15]
20世纪的娱乐与此前所有时代的娱乐最大的不同在于这种娱乐不是一种单纯的人性培育的方式,而是人性本身的直接呈现。判断一个国家进步与否的标志不再是单一的科技或者经济发展水平,人们如何有效、智慧地运用闲暇时间和工作之余将生活品质提升逐渐受到越来越多人的重视。休闲娱乐不仅仅是失业的产物,也是现代工业民主的永久性特征。[12]29闲暇时光是社会和政治复兴的关键。闲暇时光的运用能够成为复兴、修正现代化的催化剂,休闲娱乐已经变成美国民主的标志和未来的希望,尽管闲暇时光的过分充裕依旧与传统格格不入,但也不失为经济危机后复苏的解决途径。[12]30大萧条时期经济学家纷纷断言,对国家的首要意义已经不再是做一个公民,而是做一个消费者。消费是一个新的需要,故而大萧条时期蓬勃兴起的文化消费,尤其是电影文化消费就是一条绝佳的解决路径,既能让惶惶不可终日的美国人平复心理困境,又能为美国消费体系的完善增砖添瓦。电影是20世纪科学与艺术相结合的新兴产物,电影与现代科技同步发展,电影蕴含着与人互动的发展潜力和能力,他们因此也成为现代人发现和探讨自我、感知和认知世界的新手段。消费电影既是消费科技,也是消费艺术,是高级文化消费的重要组成部分。
(二)消费电影迎合大萧条时期美国民众心理
大萧条的突然降临还直接导致美国人的心理状态产生了极大变化,饱受打击的美国人没有暴行、没有反抗,没有再分配财富和挑战既定规则的倾向,整个社会只是笼罩在自我困扰和倍感耻辱的气氛之中。一些失业的男人加入失业组织,或者是特别津贴组织,或者其他形式的保护组织。但是还有更多的男人只是走上街头,日复一日地寻找工作,尽管他们知道根本就没有工作岗位。或者是他们不能再忍受这种无益的事(指漫无目的地在街上溜达),他们就躲在家里,沉默,破坏,不能去面对这个世界,甚至是他们的家庭。[10]8“1917—1918年间因战争紧张而销量激增的香烟,在大萧条的20世纪30年代再次充当了人们精神过敏症的安慰剂,其销量从1930年的1 230亿支增长到1936年的1 580亿支。”[8]21当人们在真实生活中感到哀苦无告时,只有更多地移情至银幕角色上。在一个生活无着、惊恐不已的脆弱时刻,电影更成了人们心灵的庇护港湾。支撑起整个家庭的男人们是这样,对于女人们来说也是如此,那些私人空间有限的,家庭住宅比较小的工作阶层妇女,她们“认为电影院提供了一个温暖的男女混合的环境,都比其他选择要安全”。[9]139
大萧条时代美国电影的种类异常丰富,恐怖片、动画片和歌舞片的流行都是为了迎合底层平民的审美趣味,“电影已经成功地将社会的愤怒和忧虑达成了一个小心翼翼的、艺术的转变,变成了欢笑”。[10]10电影是迄今为止最能再现梦幻和无意识的结构和逻辑的表现形式。人们明知银幕上的故事情节是虚构的,但却相信它的“真实性”。这一“真实性”是相对人们无意识之中的欲望产生的。美国人在电影中宣泄恐惧,暂时陷入无忧无虑的童话世界,以逃避艰难、希望渺茫的现实。因为电影这种舒缓精神的方式,“有其自身的魅力,它使人扮演着另一种完全不同的角色,是对未来的‘预先占有’……在游戏中,人世间的现实突然成为一种转瞬即逝的东西。人们随时准备接受令人惊异的和新奇的事情,进入一个运用不同法则的世界……人们甚至连身体都摆脱了世俗的负担,而合着天堂之舞的节拍轻松摇动”。[13]179好莱坞剧作家弗朗西斯·马里恩在1937年这样说道:“观众希望有趣的事情让他们兴奋,让他们消遣,让他们充满悬念,让他们能自我认同,哪怕激发他们的愤慨;他们哭着……‘给我安慰,给我快乐,给我悲伤,给我感动,给我梦想、欢笑、战栗和哭泣!’而更重要的事情是,观众希望电影‘让他们愉悦地回家’。观众期待电影为他们提供真实生活经验的替代品,而且电影故事要能包含让他们获得情感满足的元素。观众愿意看到影片对接近理想生活的展示,而不是他们已经知道的实际生活。观众希望看到可能限度内发生的有趣的事情;他们更喜欢在银幕上展示他们的白日梦”。[16]大众的审美情趣和生活方式也从此成为“美国文化”的主要内容之一。绍特斯利文(Kevin Shortsleeve)认为大萧条是迪士尼动画赖以成长的孵化器,低廉的电影票价和百万的失业者给迪士尼提供了一批现成的观众,而充满乌托邦意味的迪士尼系列影片分散了他们对于饥饿和贫困的注意力。[17]1
诸多批判现实主义的经典之作也都诞生在大萧条时期,左翼思想在美国商业片中一时间占据了主流,如艺术大师卓别林1931年的《城市之光》和1936年的《摩登时代》都是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众生的真实写照,直面了大萧条期间的贫富差距与失业问题,充满了对现实的嘲讽,对底层劳动人民的关怀,可谓直戳美国人的心理软肋。大萧条时代的电影担负维持美国人的价值观的责任——个人主义、去阶级化、发展和进步。
四、结论
从诞生之日起,电影就具有双重的身份:既是一种消费产品,又是消费的推动者。它不仅培养了消费主义,而且还与消费主义一道发展。从某种程度上说,电影还是消费主义的创造者。[18]162)电影制作人与其他商品供应商及政治家一样,他们都本能地注重人们潜意识里的需要和渴望。通常,这些需要和渴望都还处于朦胧状态,尚未成形,并且也没有明确表达出来。但是这些需要和渴望却一直在膨胀,膨胀着去接受诱惑。[18]163文化消费尤其是电影文化消费是一种奇特的凝聚力,可以将种族、信仰、语言和经济地位各异的人们联合在一起。在一个贫富分化严重、阶级分明的社会里,共同消费电影的行为可以使人们暂时忘却贫富和阶级上所存在的差异。作为一种变现为资本主义社会本身进步和民主化的形式,电影也变成了资本主义社会发展和变化的象征。电影一直在宣传自由、逃避和不安分的个人主义思想。[18]163-164
大萧条的出现制造了一种前所未有的落差,潜移默化地推动了电影文化消费。美国在此时还没有发展到成熟的消费主义,替代性消费表面上抑制了美国人消费观的发展,但实际上确立了消费的合法性。生产是积极人格,用消费代替生产是一种补偿心理,是填补人们心中潜在的幻灭感,这种幻灭感在大萧条时期更加凸显,电影中的角色和故事正是起到了这种补偿性功能。故而,经济危机时期美国人的消费并没有停滞,虽然是以一种全新的面貌出现,文化消费看似与物质消费相互对立,但实际上两个消费模式的共存才是现代化特征的最好体现,尤其电影文化消费属于一种精神消费,而且这种消费的成本很低,又富有现代化的特征,是一种比较平等的消费模式,它模糊了阶级差别。
[1] 王霞,孙冬梅,林琳.1930 年代大萧条下美国电影的资本结构与产业格局[J].当代电影,2004,(4):26-31.
[2] [法]达尼埃尔·鲁瓦约. 好莱坞[M].马韵文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96.
[3] [美]威廉·曼彻斯特.光荣与梦想——1932—1972年美国社会实录(上)[M].朱协译.海口:海南出版社,2004:101.
[4] Richard Butsch.American Movie Audiences of the 1930s[J].International Labor and Working-Class History, 2001,(59):106-120.
[5] Douglas Domery.Film and Business History: the Development of an American Mass Entertainment Industry[J].Journal of Contemporary History sage, London, Beverly Hills and New Delhi,1984,(19):98-100.
[6] [美]罗伯特·C·艾伦,道格拉斯·戈梅里.电影史:理论与实践[M].李迅译.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7:180.
[7] 齐小新.美国文化研究导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1:94.
[8] [美]狄克逊·威克特.经济危机与大国崛起[M].王水译.北京:北京理工大学出版社,2009.
[9] Philip Hanson.This Side of Despair How the Movies and American Life Intersected during the Great Depression[M]. Madison, N. J.: Fairleigh Dickinson University Press, 2008.
[10] Alan Brinkley.Culture and politics in the Great Depression[M]. Baylor University, 1998.
[11] 蔡骐,蔡雯.美国传媒与大众文化——200年美国传播现象透视[M].北京:新华出版社,1998:137.
[12] Susan Currell.The March of Spare Time: The Problem and Promise of Leisure in the Great Depression[M].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 Press, 2005.
[13] [美]托马斯·古德尔,杰瑞德·戈比.人类思想史中的休闲[M].成素梅,等译.昆明:云南人民出版社,2002.
[14] 蓝爱国,马薇薇.文化传承与文化消费——电影产业的文化道路[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9:14-15.
[15] [美]丹尼尔·贝尔.资本主义文化矛盾[M].赵一凡译.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89:123,132.
[16] [澳]理查德·麦特白.好莱坞电影[M].吴菁,等译.北京:华夏出版社,2005:8.
[17] Kevin Shortsleeve.The Wonderful World of the Depression: Disney, Despotism, and the 1930s. Or, Why Disney Scares Us[J].The Lion and the Unicorn, 2004,28(1):1.
[18] [美]比尔·麦吉本.消费的欲望[M].朱琳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7.
[责任编辑 石晓博]
American Movies Cultural Consumption in the Great Depression
BAI Yue
(SchoolofHistory,BeijingNormalUniversity,Beijing100875,China)
Despite the great influence of the great economic depression from 1929 to the mid 1940’s, American film industry was blooming, and Americans had great enthusiasm for movie consumption, which reflects American’s consumption conflicts between material and culture. American’s work ethic changed in which the status of leisure and entertainment dramatically rose. This contributed to the transformation, formation and further development of the consumption concept of American masses.
the Great Depression; American film industry; cultural consumption; psychology of the masses
2015-08-10
柏 悦(1987—), 女,陕西西安人,北京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主要从事德国近现代史研究。
G112
A
1008-777X(2015)05-0001-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