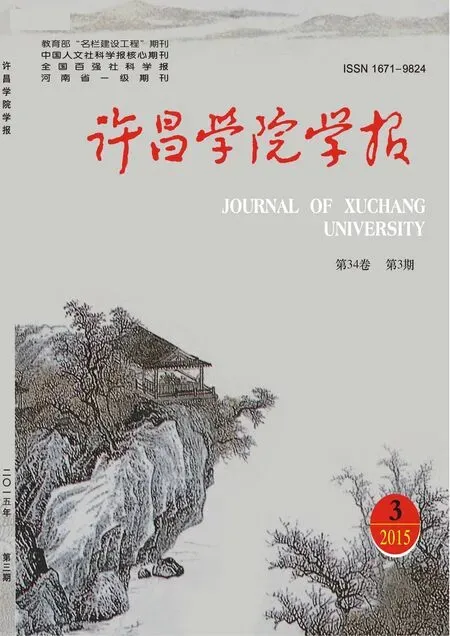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的质疑
2015-03-01霍伟
霍 伟
(信阳农林学院 人文社科部,河南 信阳 464000)
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的质疑
霍 伟
(信阳农林学院 人文社科部,河南 信阳 464000)
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认为,“蕴藉属性”是文学话语必须持有的,其他话语不具备的性质。但这一说法有失偏颇。“蕴藉属性”是话语的一种属性,它在文学话语中表现得更为突出;没有“蕴藉属性”的话语也能成为文学话语。
文学理论教程;话语蕴藉;文学话语
作为高校文学类的经典授课书目,童庆炳主编的《文学理论教程》(以下简称《教程》)在教材的编写、内容的创新方面与同类教材相比有很大进步,但并非完美无缺,如其中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的阐释就有失偏颇。本文拟就对这一问题进行详细说明,以期与同仁做一探讨。
一、何为“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是《教程》在探讨文学活动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时提出的。所谓“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属性”,是“指文学的审美表现过程与意识形态相互浸染、彼此渗透的状况,意识形态巧借审美传达出来”,[1] 61在这一“传达”的过程中,文学就有了话语蕴藉属性。具体来说,《教程》对于这个属性的阐释是次第展开的。
首先,《教程》引用福柯的话语理论,认为“话语”是一种语言与言语结合而形成的丰富而复杂的具体社会形态,而文学作为一种语言艺术,也是话语的一种形式。这种形式具有自己的内涵,它“是指特定社会语境中人与人之间从事沟通的具体言语行为,即一定的说话人和受话人之间在特定社会语境中通过文本而展开的沟通行为,包括说话人、受话人、文本、沟通、语境等要素。”[1]69接着,作者指出,文学作为一种话语,与日常话语、哲学话语等一般话语类型是有区别的,这主要体现在文学话语具有“蕴藉”的特点上:“文学作为话语,与日常话语、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新闻话语等一般话语不同,具有‘蕴藉’特点,从而具体表现为话语蕴藉。”[1]71最后,作者从中国古典诗学的角度对“蕴藉”做了阐发,认为它是“指文学作品中那些意义有余、蓄积深厚的状况。”[1]71包括含蓄和含混两种修辞形态。这就是所谓的“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
在《教程》中,作者尤为推崇“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认为“文学直接地就总是以话语蕴藉的形态而存在。而无论是作者还是读者,都只能通过这种话语蕴藉而参与到文学活动之中。”[1]72“文学的审美意识形态性只能以话语蕴藉这一特定形态表现出来,都只能蕴含在话语的含蕴或含混的意义空间中,无法离开这种话语蕴藉而独立存在。”[1]76“如果离开了话语蕴藉便不存在文学活动了。”[1]76
通过作者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的阐释,我们至少可以得出这两层意思:第一,“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是文学中所蕴含的那种含蓄、深醇的审美意蕴;第二,按照作者的意思,“话语蕴藉属性”是文学所独有的,日常话语、哲学话语等“一般话语”是不具有的;不具有“蕴藉”属性的话语不是文学话语。对于第一点,笔者认为是合理的,但对于第二点,笔者有诸多疑问。
二、对“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若干问题的质疑
(一)《教程》认为日常话语、哲学话语、政治话语、科学话语、新闻话语等“一般话语”不具有蕴藉属性,这是有失偏颇的,原因在于:
1.日常话语虽然简单明了,但并不乏蕴藉性。以现代汉语为例,如,甲夸赞乙的衣服洗的干净,说:“你的衣服洗的真打击我!”这里的“打击”一词明显不仅仅是字面的“受伤害”之意,同时蕴含了甲对乙的赞扬。在此,就不能说这句话没有蕴藉意义。再如“聪明绝顶”一词,如果对着一个头发稀少的聪明人说,就蕴含了“夸此人聪明、调侃此人头发少” 两层意思,也不能说这句话不包含蕴藉意义。
2.哲学话语的蕴藉性自不待言。如中国的哲学著作《庄子》,其中的“庖丁解牛”、“轮扁斫轮”等虽然是小故事,但却蕴含了大道理,所以在解读时,就不能仅仅了解其字面意思而不探究背后的意蕴,否则就违背了庄子以寓言来表现思想的初衷了。一些西方哲学家的著作也具有蕴藉性。尼采曾用“上帝死了”来象征无名时代西方世界信仰的崩塌,这不仅是对基督教神学的严正挑战,更写出了人类因信仰缺失而灵肉游离的状态。在《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中,他用万物的苏醒与离去来阐释消亡与新生、分离与相合的辩证关系:“万物刚刚苏醒;万物刚刚离去,命运之车轮永远循环在宇宙上方。万物刚刚复苏,万物就已死去,存在之时间,永远远去。”[2]如果仅从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根本得不到其真旨,只有体会其背后的意思才能看到尼采思想之所在。由此可见,把蕴藉性排除在哲学话语之外,不能不说是《教程》的疏漏。
3.政治话语也并不排除蕴藉性。举个简单的例子,在一次记者招待会上,一位外国记者曾对周总理说:“你们中国人走路都低着头,而我们美国人走路是挺胸抬头”,周总理立即针锋相对地说:“因为我们走的是上坡路,而你们走的是下坡路。”[3]很明显这里说的不单单是走路的问题,而是蕴含了中国的国际形象和尊严问题。中国政治话语的“蕴藉”属性可以追溯到春秋时期。在《左传·晋灵公不君》中,晋灵公为政不仁,臣子们又不敢加以制止,就巧妙地引用《诗经·荡》中的“靡不有初,鲜克有终”和《诗经·蒸民》中的“哀职有阕,唯仲山甫補之”,来警示晋灵公改邪归正。在此,如果只看《诗经》中这几句话的原义,是不能理解臣子们的良苦用心的。此外,我们之所以用“闪烁其词”来形容外交辞令,多半因为外交辞令的模糊性和多义性。可见,政治话语仍带有某种程度上的蕴藉性。
4.科学话语也具有一定程度上的蕴藉性。科学话语包括自然科学话语,如数学、生物学等自然科学的论著和论文,计算机语言,自然科学实验报告等;还包括社会科学话语,如社会学、语言学等社会科学的论著和论文,社会调查报告,心理分析报告等。科学话语作为理论思维的工具,具有充分的认识性、概念性、逻辑性、思辨性,但并不与蕴藉性绝缘,它常借蕴藉性来表达。比如,爱因斯坦曾经这样阐释他的“相对论”:“你同你亲密的人坐在火炉边,一个钟头过去了,你觉得好像只过了5分钟;反过来,你一个孤孤单单地坐在热气逼人的火炉边,只过了5分钟,但你却像过了一个小时。——唔,这就是相对论”。[4]59这样,就将复杂问题简单化了,巧妙地传达了“相对论”的要旨。所以,说科学话语不含蕴藉性是不符实际的。
5.新闻话语具有的蕴藉性是不言而喻的,比如有这样一则标题:“陈水扁的舌头牵动美国的神经”,形象地描绘了陈水扁和美国政府的微妙关系。这则新闻标题的精彩之处就是其言说的形象性、隐喻性。由此可见,笼统地将新闻话语排除在话语蕴藉性之外,未免牵强。
综上所述,笔者认为,“蕴藉属性”作为话语的一个属性,并不是文学话语的专利,日常话语、哲学话语等也可以具有蕴藉属性,只是说其在文学话语中表现得较为明显。由此可见,《教程》将话语的蕴藉属性缩小到文学话语的范畴,无疑是不妥当的。
(二)《教程》中将蕴藉属性作为文学话语必须拥有的特性,也不合文学事实。
按照《教程》的说法,蕴藉是“指文学作品中那些意义有余、蓄积深厚的状况”[1]71也是“一种内部包含或蕴藉多重复杂意义,从而产生多种不同理解可能性的话语状况”。[1]72简言之,就是文学作品中含蓄、朦胧、多义的审美意蕴。不可否认,大多数文学话语确实具有这样的审美特征,但如果用这种标准去衡量所有文学话语,那就与文学事实不符了,因为一些文学话语并不具有蕴藉性。如敦煌曲子词中的《菩萨蛮》:
枕前发尽千般愿,要休且待青山烂。水面上秤锤浮,直待黄河彻底枯。
白日参辰现,北斗回南面。休即未能休,且待三更见日头。
此诗用自然界不可能出现的事物来反衬主人公对爱情的坚贞不渝。“没有追求含蓄蕴藉之致,其抒情方式以直率、热烈、大胆、泼辣见长,遣词造句亦不加雕饰,形同白话,充分表现出拙朴、自然的本色”,[5]72可见,直抒胸臆同样能取得震撼人心的艺术效果。此诗并不具有蕴藉性,但我们不能说这不是一种文学话语。
再比如《乐府民歌·饶歌·上邪》:
上邪!我欲与君相知,长命无绝衰。山无棱,江水为竭,冬雷震震,夏雨雪,天地合,乃敢与君绝!
本诗是一位痴情女子对爱人的热烈表白,誓词热烈,感情直率,表现了她对爱情永恒的渴望与追求,情感意义较为单纯,但是我们不能否认它是一种文学话语。 可见,不是所有的文学话语都具有蕴藉属性。
“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是《教程》从古典诗学的角度提出来的,从某种程度上说,它只适合一部分文学作品。但通过以上论述可以发现,《教程》中用“只能”“必须”等字眼来涵盖一切文学话语,认为所有文学话语都具有蕴藉属性,就有了以偏概全之嫌。
《教程》中的这种“文学的话语蕴藉属性”与王一川先生所说的中国美学的“兴味蕴藉”传统有异曲同工之处。王氏的“兴味蕴藉”是“感兴传统的一个重要的方面或成果,是指作为感兴的集中呈现状态,艺术品往往在其兴象系统中蕴含深长的余兴,令观众或读者回味无穷。”[6]17“兴味蕴藉”还被王氏看做汉语文学的古典品质之一,认为“富于兴味蕴藉的文学作品,往往让读者感到余意无穷,为他们开拓出绵延不绝的兴味空间。中国文学历来讲究兴味蕴藉深厚,余味绵长,并把它作为衡量文学作品艺术成就的重要尺度。”[7]241王氏自己也确实用这种尺度去衡量和要求文艺作品,比如他对赵本山的小品批评和解析。[8]37但是我们看到,王一川先生并没有将这个尺度唯一化,笔者认为,这种说法与《教程》相比是较完备的。
总之,蕴藉属性作为话语的一种属性,不是文学话语的专利,其它话语也具有一定的蕴藉性,没有蕴藉性的话语也能成为文学话语。
[1] 童庆炳.文学理论教程[M].北京:高等教育出版社,2005.
[2] 尼米.查拉图斯特拉如是说[M].孙兴周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3] 老外交官动情会议:我最后一次见到周总理.http://www.ycwb.com/gb/content/2006-01/06/content_1050292.htm.
[4] 历史幽默[J].招商周刊,2004(5):59.
[5] 司马周.执子之手 与子偕老——三首别样的古典爱情诗词赏析[J].名作欣赏,2009(4):72.
[6] 王一川.感兴传统面对生活—文化的物化[J].文艺争鸣,2010(13):13-20.
[7] 王一川.文学理论(修订版)[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
[8] 王一川,冯雪峰.从中国美学兴味蕴藉传统看通俗艺术品位提升[J].北京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1):37.
责任编辑:石长平
On the Utterance Implication Property of Literary
HUO Wei
(Dept. of Humanity&Social Science, Xinyang Agricultural College, Xinyang464000, China)
Tong Qingbing claims in his book Literary Theory Tutorial that the property of implication is unique to literary utterances. This paper argues that this view is biased. The author thinks that implication is a property of utterances and it appears more prominent in literary discourse. Utterances without implication can also become literary discourse, so context can be a standard for judging whether the utterance has the implication or not.
Literary Theory Tutorial; implication of utterances; context
2014-09-28
霍伟(1986—),女,河南信阳人,硕士,助教,研究方向:文艺理论。
I0
A
1671-9824(2015)03-0064-03