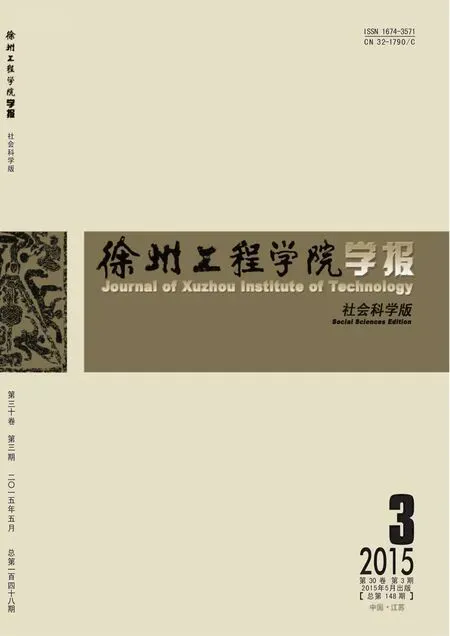瞿秋白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和传播——以其国共合作时期的几个纪念文本为考察中心
2015-02-28梁化奎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 徐州 221018)
瞿秋白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和传播
——以其国共合作时期的几个纪念文本为考察中心
梁化奎
(徐州工程学院 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江苏 徐州221018)
摘要:在中国早期马克思主义传播史上,列宁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概念并非是同步进入中国的。国共合作时期,瞿秋白在为纪念列宁而撰写的几个文本之中,其对“列宁主义”的场域指认和阐释,既有为同时代人所不及的突出贡献,也有囿于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不成熟的一面。总结瞿秋白这一时期的列宁主义传播之旅,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列宁主义,怎样对待列宁主义”的问题,同时有助于推进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研究。
关键词:瞿秋白;列宁主义;出场
从概念史角度考察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列宁主义谱系中的一些核心概念是如何接受、指认的,又是怎样研究、传播和运用的,是创新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问题研究的一条新路径。然而,对于这一极具学术性开拓空间的新的研究路径,目前学界还很少为人所关注。以瞿秋白的列宁主义传播之旅为例,国共合作时期,他在为纪念列宁而撰写的几个文本之中,其对“列宁主义”的场域指认和阐释,即为我们深入考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研判的经典案例。
一
任何思想和表达思想的概念,都不会凭空现身某一特定场域。在国内“出场学”首倡者任平先生看来,一种思想体系在某一特定场域的“现身行动”,亦可以说是一种哲学指义上的“出场”[1]。这一“出场”由于会受到“出场语境”、“出场路径”的制约,因而也呈现出一定的“出场形态”。由此看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出场,广义上的列宁主义与“列宁主义”的概念并非是同步进入中国的。就前者来说,从1917年12月28日杨匏安在广州《中华新报》上发表《李宁胜利之原因》一文,即首篇介绍列宁思想的文章,可以说列宁主义就已在中国传播了;而就后者来看,要厘清“列宁主义”的概念是怎样进入中国的,则要显得复杂得多。
在俄国语境中,“列宁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1903年,但其却是孟什维克派用来诋毁列宁及布尔什维克派的一个贬义词。列宁生前,褒义用法的“列宁主义”一词也已出现,并在列宁逝世后不久即为俄共(布)党内外所普遍接受。不仅如此,斯大林在1921年4月斯维尔德洛夫大学发表的题为《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演讲中,还首次系统论述了列宁主义,并为“列宁主义”下了个著名定义。他指出:“列宁主义是帝国主义和无产阶级革命时代的马克思主义。确切些说,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的理论和策略,特别是无产阶级专政的理论和策略。”[2]185与此同时,从1923年秋至1925年初,俄共(布)党内针对托洛茨基有关列宁的言论,接连发动了三次猛烈批判,谴责托洛茨基的言论破坏了党的威信,破坏了党的干部的威信,破坏了列宁主义的威信,因此要求其“无条件地放弃任何反对列宁主义思想的斗争”[3]534。再者,1924年6月,共产国际在莫斯科召开了第五次代表大会,大会向各国支部党提出了实现党的“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指出各国支部党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把“马克思列宁主义变成自己党员的共同财富”[4]54。会后,这些精神经由参加大会的各国党的代表,被带回到了各支部党。
在中国,“列宁主义”一词最早出现在李达的《马克思派社会主义》一文中,该文发表在1921年6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9卷第2号上。李达在文后所列的参考书中,指明参考了日本人室伏高信的《列宁主义批评》一文。不过,室伏高信所说的“列宁主义”,仍是在贬义所说的“列宁主义”,所以,并不能将出现在李达文本中的“列宁主义”一词,视作是“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出场。中共成立后,依据列宁在共产国际“二大”前后提出的关于民族和殖民地问题的理论,以及共产国际相应提出的策略思想,1922年7月,中共“二大”制订了反帝反封建的民主革命纲领,提出了建立“民主的联合战线”的方针;次年6月,在共产国际代表的指导下,中共“三大”讨论了以“党内合作”的方式同国民党合作,开展国民革命的问题。与此同时,在中国共产党的帮助下,孙中山也在商讨通过党内改组的方式实现国共合作的各种问题。1924年1月20日,中国国民党“一大”在广州召开,大会重新解释了三民主义,标志着国共统一战线正式建立。第一次国共合作的建立以及随之兴起的大革命运动,揭开了中国民主革命的新篇章,为列宁主义在中国的广泛传播,特别是“列宁主义”概念在中国的“现身”,找到了出场的通道,提供了行动的场域。
然而,就在中国国民党“一大”召开的次日,列宁溘然长逝。孙中山从俄共(布)来华特使鲍罗廷处得知这一消息之后,在1月25日召开的悼念列宁大会上,发表了《关于列宁逝世的演说》。他称赞列宁是一个“革命之大成功者”、“革命中之圣人”、“革命中最好的模范”,同时指出:“列宁先生之思想魄力、奋斗精神,一生的功夫全结晶在党中”,“现在有俄国的方法以为模范,虽不能完全仿效其办法,也应仿效其精神,才能学得其成功”[5]575-576。在这个悼念会上,鲍罗廷也发表说:“列宁虽死,列宁主义万岁。”[6]次日,鲍罗廷的这个演讲被登在了广州《民国日报》上。褒义上的“列宁主义”一词,就这样首次出现在了中国报刊上。从中共方面看,第一次国共合作时期,以追悼列宁及随后开展的年度性纪念活动为契机,中国共产党人持续掀起了研究、传播列宁主义的热潮。在这股热潮中,瞿秋白发表的多篇旨在传播列宁主义的纪念文章,集中体现了他对“什么是列宁主义”的场域指认和阐释。
二
1924年3月9日,中共上海地委等单位代表在南市小西门举行追悼列宁大会,瞿秋白第一个登台作了《列宁史略》的报告。据次日《申报》的报道,大会在“列宁主义万岁”的呼声中结束。在这次纪念大会出版的“特刊”上,瞿秋白发表了他的《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接着,他在3月25日出版的《东方杂志》第21卷第6期上,又发表了《李宁与社会主义》一文。正确解读瞿秋白在这两个文本中都说了什么,又为什么会那样说,既需要弄清其文本写作的背景,又需要能够理清瞿秋白此前认识思想发展的脉络。
第一,五四运动后,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在对俄国革命的持续关注、研究和宣传中,坚定地认同了“俄国人的路”,并将这个世界上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看作是能够“帮助中国脱离世界帝国主义压迫的世界正义之国”,“是可资借鉴的成功实践马克思主义之最佳样板”[7]。值得关注的是,瞿秋白发表上述两个文本之时,褒义的“列宁主义”一词出现在中文词汇中仅有月余,而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此时即便是在苏俄也还尚无一个公认的定义。这时,发生在俄共(布)党内、还在发酵中的争夺“列宁主义”定义权、阐释权的激烈斗争,则更不可能为中国共产党人所全面、真实了解。由于有这些原因,也可以说正是由于少有思想束缚,这为中国共产党人大胆探索“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问题,反而提供了一个相对宽松的政治环境。
第二,瞿秋白在新俄考察学习期间,列宁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正面形象。在中共早期领导人中,瞿秋白是见到过列宁次数最多,也是唯一同列宁有过合影的人。1921年6月,他曾以来宾身份出席了共产国际“三大”,会间与列宁相遇并作了简短交谈。这年十月革命纪念日,在莫斯科狄纳莫工厂举行的庆祝晚会上,瞿秋白第二次见到了列宁,聆听了列宁在庆祝会上的演讲。次日,他便以极其生动的文笔向人们描述了列宁的光辉形象(《赤都心史·赤色十月》)。1922年1月,远东各国共产党及民族革命团体第一次代表大会在莫斯科(后移至彼得格勒)召开,会间,由瞿秋白任翻译,列宁抱病接见了出席大会的中国代表张国焘、张秋白、邓培三人,向他们询问了国共两党进行合作的可能性。仅从这几点看,在中共早期马克思主义者群体之中,瞿秋白之所以能够“在塑造俄国正面形象方面贡献极大”[7],这同他对列宁及十月革命始终坚持的正面情感倾注,可以说息息相关。
第三,瞿秋白1923年初回到国内之后,其认识思想的发展深受列宁主义的引导和影响。这年6月15日,由瞿秋白任主编的《新青年》季刊创刊,并登载了由他翻译的列宁在共产国际“四大”上的演说《俄罗斯革命之五年》(今译为《俄国革命五周年和世界革命的前途》)。在这个演说中,列宁深刻阐述了应当怎样把俄国革命经验介绍给外国同志,外国同志又应当怎样学习俄国革命经验的问题。列宁指出,共产国际制定的一些议决案“俄国气味太重”,“纯粹反映俄国革命史中之经验”,外国同志决不能把它当做“神像一般挂起来祈祷”[8]。瞿秋白敏锐地察觉到列宁的这个演说之于中国共产党的重要意义,不仅及时将全文译出发表在《新青年》季刊创刊号上,且在列宁逝世之后不久撰写发表的《历史的工具——列宁》《李宁与社会主义》两个纪念文本之中,进一步益彰了这个演说中的一些重要思想观点。1923年12月20日《新青年》季刊第2期出版,瞿秋白在该期上发表了《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文中8次使用了“历史工具”或“历史的工具”的概念。对于这一概念,瞿秋白阐释说:技术进步及阶级斗争是“社会发展之最后动力”,“个性的先觉仅仅应此斗争的需要而生,是社会的或阶级的历史工具而已(如马克思、列宁)”,所以,“‘伟人’必定是某一时代或某一阶级的历史工具”[9]。
从瞿秋白上述两个纪念文本的写作背景,以及此前其认识思想的发展脉络看,在“列宁主义”一词刚刚出现在中文词汇中,而其作为一个政治概念的巨大能量和价值还尚未为人们所真正认识之时,瞿秋白在这两个纪念文本中所言说的“列宁”,实则是一个具有双重指向功能的语码符号。它既可以指向作为世界革命“总指挥者、总组织者”的列宁,也可以说它是在指称“李宁的主义和精神”;这样两个“能指”实则被瞿秋白有机叠用在了其纪念文本之中,这是瞿秋白以追悼列宁为契机、传播列宁主义的一个匠心独用。而他对“李宁的主义和精神”作出的提炼性概括,无论是从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来看,还是从中共早期的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来看,无疑都占居了十分显要的位置并作出了巨大贡献。
在《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中,瞿秋白将其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提出的“历史工具”论的观点,援用到了对列宁的认识评价上。他指出:“伟人不过是某一时代、某一地域里的历史工具。”列宁是资本主义发展到帝国主义阶段“世界社会革命的总指挥者、总组织者”,“是二十世纪世界无产阶级的工具”,“列宁的伟大不仅在于他的共产主义理想,而在于他能明悉社会进化的趋向,振作自己的革命意志,指示出运用客观的环境以达人类的伟大的目的之方法”[10]。不过在瞿秋白看来,并非人人都能“当得起”历史的工具。他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说,在伟大的历史运动中,英雄或天才之所以能“当得起”历史的工具,“他至少要能知道几分社会现象的必然公律”[9]。这里可以看出,瞿秋白所指称的“历史工具”,并非仅是对作为伟人的个体的简单指认,而是对那些洞悉、掌握了历史发展规律并在历史发展进程中所创造的理论学说的一种全面指称。在《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一文中,瞿秋白还深刻指出:“科学的公律正是流变不居的许多‘异相’里所求得的统一性”,如“中国革命与法国革命的环境形势大相差异,然而并不因此而不能求得革命的公律”[9]。由此推演,人们同样可以从中国革命与俄国革命的“异相”中求得“统一性”,即“求得革命的公律”。这才是瞿秋白在上述两个纪念文本中真正意欲向人们表达的。通过在不同场域对这一推演逻辑的反复操演,瞿秋白不仅从理论上回答了历史伟人及其理论学说的作用和价值,特别是其之所以能够“当得起”历史的工具的原因,同时这也成为他对当时国共合作阵营内已在泛起的反对“联俄”“联共”之声的一种有力回应。从这一目的出发,瞿秋白在《历史的工具——列宁》一文中高调宣称,列宁或说列宁的“主义和精神”作为“革命的象征”“革命组织的象征”,“不但是历史的工具”,而且是全世界受压迫平民的“一个很好的工具”[10]。
1924年夏,瞿秋白在上海夏令讲学会演讲了他的《社会科学概论》。在这一演讲中,瞿秋白进一步丰富了他对“历史工具”论的认识。美国学者德里克谈到这部讲稿时曾经独具慧眼地指出:“‘工具史观’支配了瞿的全书。”[11]28检视这一时期瞿秋白文本写作的思想方法进路,可以发现,从《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到《历史的工具——列宁》,再到《社会科学概论》,其中,“历史工具”论作为一个浸蕴了马克思主义唯物史观和唯物辩证法思想的、有着丰富哲学内涵的有机要件,实则起到了卯榫这一时期瞿秋白还在发展中的认识思想的重要作用。
《李宁与社会主义》是瞿秋白写于同月的另一篇纪念文本。此文的最大贡献是他在文中概括出了列宁作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理论家和实践家具有的四个鲜明特点。即:一是列宁“最能综合革命的理论和革命的实践”,“他不仅是坐言,并且还能起行”;二是列宁“最能觉察现实”,他能适时察觉社会、政治的“变机”,预料事势、政党、人物的“变易”,“最善于运用革命的原则,能应用主义到每个实际的事势上去,决不死守着纸上的主义”;三是列宁在马克思主义政党建设上具有的“组织力和训练力”;四是列宁对于夺取政权具有“百折不挠的意志和极伟大的自信力”,能灵活运用“相反相成的政略”。文章总结指出“李宁是实行社会主义的第一人”,因为他具有这样四个特点,所以他“能以妥协的方法行不妥协的策略:能组织集中革命的实力;能观察客观的政治动象;能运用革命实力探悉对付客观环境的方法去实行社会主义的目的”。正是在这些意义上讲,列宁“虽死犹生”[12]。
回望瞿秋白同时代的人,在时人对列宁和列宁主义所作的诸多评述之中,能与瞿秋白在上述两个纪念文本提出的许多精彩论述相比肩的,实不多见;他对列宁和列宁主义的指认和阐释,可以说代表了其时中国共产党人所能达到的最新高度。
三
就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外来影响因素看,1924年6月在莫斯科召开的共产国际“五大”最具关键影响。如前所述,在这次大会上共产国际向各支部党提出了布尔什维克化的任务,并强调指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就是指把俄国布尔什维克主义中过去和现在一切具有国际意义、普遍意义的东西,应用到我们的各个支部中去。”[4]30在大会通过的《共产国际及其支部的宣传活动(提纲)》中,还第一次把“马克思主义”与“列宁主义”合称为了“马克思列宁主义”,指出党的布尔什维克化“是通过对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灌输马克思列宁主义来实现的”,因此,共产国际及各支部党在当前的首要任务之一,就是要使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先进理论成为各国共产党及其党员的“共同财富”[4]54。
为贯彻、执行共产国际“五大”的精神,1924年十月革命周年纪念前后,中共进一步扩大了对列宁主义的宣传力度,其中一个重要表现,是当时中共主办的《向导》周报、《新青年》季刊、《中国青年》等宣传刊物,在此纪念日前后集束式地刊发了一批纪念文章。在这波研究、传播列宁主义的新热潮中,彭述之最早尝试回答了他对“列宁主义”这一概念的理解。他在《向导》周报上发表的《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一文中说,列宁主义作为一种“试验过的理论与策略”,“就是解放无产阶级,解放农民,和解放被压迫民族之理论与策略”,换言之,亦就是“无产阶级革命,农民革命和被压迫民族革命之理论与策略”。彭述之认为,这是列宁主义所包含的“根本点”[13]。这里,不能不令人惊愕的是,此时在苏俄,托洛茨基的言论正在受到来自斯大林、季诺维也夫、加米涅夫“三驾马车”及其掌控下的宣传舆论的猛烈围攻,而彭述之在该文中非但没有提到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定义,反而引述了托洛茨基论述列宁的一句名言作为开篇。这说明发生在俄共(布)党内争夺“列宁主义”定义权、阐释权的斗争,此时还尚未影响到中共党内。这使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对列宁的评价与其对“列宁主义”的指认和阐释,因此也更多带有个性化私人言说的特点。瞿秋白这年3月写作的前述两个纪念列宁的文本,事实上也就鲜明地反映出这个特点;而其文本话语所彰显出的思想力和活力也在深刻昭示后人,任何理论的进步和发展,都需要有自己的独立思考。
可是,上述传播特点在1925年初中共党内形成的新一轮研究、传播列宁主义的热潮中发生了明显转变。这年1月10日,中共中央发出 “通告”(第24号),要求各地在列宁逝世周年纪念日,“应在可能范围以内号召地方各团体开一纪念会”[14]316。 次日,中共“四大”在上海召开。通过这次大会俄共(布)党内谴责托洛茨基反对派的声音,以及共产国际“五大”通过的各项决议的精神,被明确传达到了中共党内。大会以“议决案”的形式表示,中国共产党“完全同意”共产国际“五大”作出的各项政策决定[14]321,“完全同意”俄共(布)领袖对“托洛茨基主义亦为投降主义之一派”的认定,“并且希望托洛茨基同志改正自己的错误而完全承认列宁主义”[14]325。这就明确宣示了中国共产党坚定地站在了“列宁派之俄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一边。大会以“议决案”的形式还建议,党的新一届中央执行委员会“应与共产国际发生更密切的关系”,以使中共在理论上和政策上能够得到共产国际“更多的指导”[14]328。
在宣传上,中共“四大”通过的关于宣传工作的“议决案”提出:为了“端正党的理论方向”,“党的宣传工作有重新整顿的必要”。同时强调指出,应将共产国际“五大”关于宣传工作的指示精神作为开展党内教育的理论根据,尤以共产国际关于共产党内“左的右的乖离倾向”与“宣传马克思列宁主义和各国党之布尔什维克化”的指示精神,更值得“特别注意”[14]374-376。这里,迄今仍在为我们所沿用的“马克思列宁主义”这一术语,首次出现在了中共中央文献之中,也是第一次出现在了中国。为重整党的宣传工作,“议决案”还提出了12项具体改进办法。如中央宣传部下设编译委员会,编译各种宣传列宁主义的小册子;集力办好《新青年》月刊,并使其更好地将“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见地运用到理论和实际方面”;党员对外发表一切政治言论,“完全应受党的各级执行机关之指挥和检查”[14]376-378,等等。
中共“四大”闭会的前一天,恰值列宁逝世周年忌日,中共遂以本次大会的名义发表了《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在这份简短的“宣言”中,中共高度评价了列宁的光辉业绩,指明了列宁主义对于中国人民和一切被压迫民族的解放斗争的指导意义,并强调指出,中国工农阶级和一切被压迫民众要想摆脱被奴役的地位,“只有站在列宁主义的旗帜之下”,“努力了解列宁主义,实行列宁主义”。“宣言”中还就“什么是列宁主义”给出了一个简短的定义。认为“列宁主义就是资本帝国主义专权时代的马克思主义,是消灭帝国主义的唯一武器”[14]396-397。不难看出,这个定义已显像有斯大林对“列宁主义”定义的影子了。在列宁逝世周年之际,亦即在俄共(布)党内争夺“列宁主义”定义权、阐释权的斗争已尘埃落定,胜利者的声音传入中国之后,中共方以“宣言”和“议决案”的形式,首次公开表达了它对列宁的党际评价与其对“列宁主义”的政党指认,并基此开启了列宁主义在中国传播的一个新阶段。
这里顺便要说的是,传统上,人们对中共“四大”的地位和贡献的认识,似乎早已习惯了从它明确提出了无产阶级在民主革命中的领导权问题和工农联盟问题来作诠释的,但上述考察已表明,在中国早期马克思列宁主义传播史上,中共“四大”具有重大节点意义。关于这一点,学界尚需要有更加深入地研究。
四
在中共“四大”上,瞿秋白当选为中央委员并进入中央局,任中央宣传委员。依据中共“四大”在宣传工作上提出的新要求,1925年4月22日,由瞿秋白任主编、改刊为月刊的《新青年》第1号出版了“列宁号”纪念专刊。专刊登载了三类15篇文章,共约12万字。一是中共“四大”发表的《对于列宁逝世一周年纪念宣言》与编辑部特写的《列宁逝世的第一周年》;二是由瞿秋白、陈乔年、郑超麟翻译或是“改译”的列宁、斯大林的文章;三是由共产国际领导人及其在中国的代表与中国共产党人撰写的各类纪念文章。瞿秋白在专刊上发表了《列宁主义概论》《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两篇文章,并为专刊的编印付出了大量心血。关于这期专刊的影响,从十年后(1935年2月)中国国民党中央组织部调查科编印的《中国共产党之透视》一书中,也可见一斑。据这份材料中透漏说:中共四次大会闭幕后,共党伪中央改《新青年》季刊为月刊,创刊号系“列宁纪念”号,“此为中国共党对于列宁主义之最初的亦系最具体之介绍”[15]63。
再从瞿秋白发表在专刊上的两篇文章看,《列宁主义概论》“改译”自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为什么要选择“改译”?1927年2月,瞿秋白在将该文收入其自编论文集时,在文后说得很明确:选择“改译”意在更“接近中国读者”[16]46。于是,瞿秋白把斯大林原文约7万多字、10个章节的《论列宁主义基础》一文,“改译”成了约万余字、7个章节。当《新青年》月刊第1号刊出此文时,瞿秋白曾在文后解释说,这篇文章只是译出了斯大林对于列宁主义论述的“大概”,斯大林文中对于列宁主义与民族问题、列宁主义与农民问题的重要论述,“因为本号另有专论,所以没有重复赘述”[17]。依照斯大林原文的结构和思路,译文在首节即回答了“什么是列宁主义”的问题,但是,瞿秋白并没有照搬原文,而是添笔加入了一些自己的叙述和思考。文中指出,列宁主义不等于马克思主义,列宁主义中有许多成分是马克思主义中“原来所没有的”,“或者虽有亦很不详尽,还未发展的”。如在无产阶级独裁制与农民阶级、无产阶级革命与殖民地民族革命之关系等问题上,列宁“便有格外详尽的研究,发见许多新的原则”。所以,作为执行无产阶级革命实践原理的列宁主义,是“无产阶级革命时的帝国主义时代的马克思主义”[16]。这样,斯大林对“列宁主义”的经典定义及其对列宁主义体系、功能的系统论述,便以“改译”的形式首次被最早介绍到了中国。这亦即意味着,“列宁主义”作为一个具有确切内涵所指的政治概念,至此完成了它在中国的“现身行动”,实现了它在中国的出场。
瞿秋白对斯大林的《论列宁主义基础》的“改译”,在其后中国革命中发挥了巨大影响作用。1927年1月,新青年社出版了《列宁主义概论》的单行本。进入苏维埃和抗战时期,国内对斯大林这篇文章的翻译和出版,虽有译者、版本和收录内容上的差异,但其书名大都沿用了瞿秋白所用的《列宁主义概论》这个最初译名。1929年11月28日,在福建汀州的毛泽东曾经致信中共中央,请求中央能给他们寄来《布尔塞维克》《红旗》《列宁主义概论》《俄国革命运动史》等党内出版物,以便对党员“赶急进行教育”[18]26-27。这里,在毛泽东点明急需的四本党内出版物之中,后两种即为瞿秋白之所译或所著。1938年8月22日,毛泽东在延安中央党校又向即将毕业的学员发表演讲说,同志们“以后要不断地学下去”,并向学员推荐说,“可以看看《列宁主义概论》”[19]。这表明毛泽东不但认真研读过《列宁主义概论》,而且此书曾给他留下了极为深刻的印象和影响。不仅如此,瞿秋白的这个“改译”本由于简明扼要,它因此也赢得了基层工人群众的认可。据杨之华回忆说,在白色恐怖严重的1935年,她曾在上海“一个工人家里的箱子中发现藏有这本书”,收藏者还对她说,这是他“最爱读的一本书,已经藏了好几年了”[20]。可见瞿秋白的这个“改译”本在中国革命历史上,特别是在传播列宁主义方面,的确曾经发挥过巨大影响作用。所以,讲到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史,瞿秋白的这个贡献,足堪予以高度肯定。
《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一文,是瞿秋白在俄共(布)党内斯大林同托洛茨基派的斗争已尘埃落定的背景下,为响应中共“四大”通过的《对于同志托洛茨基态度之议决案》而作。该文一开始便指出:以列宁为首的多数派“是无产阶级政治思想的最正确的指导者”,而托洛茨基派的主张则具有“退化到机会主义,以至于反革命,而成为资产阶级左派在劳动平民中的政治奸细”的“恶倾向”[21]。该文的重点,也可谓这篇文章的一个最重要的功效,是它对列宁主义与托洛茨基主义之间的根本不同点,作出了一种严格的区分划界。
首先,瞿秋白指出了两派在革命性质的判断,以及在如何看待农民阶级在革命中的作用,这样两个密切相关问题上的分歧。瞿秋白指出“多数派以为当前的资产阶级革命是农民的资产阶级革命”,在这一革命之中无产阶级应与“农民携手,取得政权”;少数派却“只见着农民思想里的反动方面”,否认农民阶级“可以成为革命中之一动力”。在瞿秋白看来,若是按少数派的主张进行革命,不仅会使无产阶级陷于“孤立”,甚至会“激使农民反动”,“而助长反革命的势力”。所以说,“杜洛茨基主义”既是“一种少数主义,亦是一种机会主义”[21]。在中共“四大”明确提出要争夺无产阶级领导权、强调建立工农联盟的大背景下,瞿秋白把对托洛茨基派的错误的批判,重点放在了应当如何看待农民阶级的作用的问题上,其用意显然在于提醒全党,应当充分警惕因忽视农民问题有可能导致的机会主义错误。然而两年后,中共恰是由于在这点上出了大问题,最终导致了轰轰烈烈的大革命的失败。
其次,瞿秋白批判了托洛茨基的“无间断革命”说。他指出:托洛茨基认为,无产阶级在资产阶级民主革命阶段,便可以不顾农民的利益需要,“单独向资产阶级进攻”,“进于社会革命”,“实行种种社会主义的政策”,“实行纯粹的无产阶级独裁制”, 如此“便会实现急转直下的无间断的革命”;列宁派则认为,“这革命仍是资产阶级性的”,“并不是根本推翻资产阶级式的私有制度”,而是要建立“无产阶级及农民之革命民权主义的独裁制”。在瞿秋白看来,列宁主义和托洛茨基主义的不同,并不在于主张“革命无间断的转变”与否,关键在于这样两点,即无产阶级政党“是否认农民阶级绝无独立的政治作用”, “是否当注意吸引农民阶级,使他积极赞助自己”[21]。
可以看出,通过上述对比分析,既表明了中国共产党对于列宁派及俄共(布)新任领导人的态度和立场,同时也起到了净化社会舆论环境的重要作用。这是瞿秋白的这种对比分析的价值与意义之所在。说到瞿秋白的革命理论活动,大革命失败后曾经留学过莫斯科中山大学的王凡西,在其回忆录中总结指出过一个特点。他说:“瞿秋白毕竟是一位较有深度的革命思想家,即使陷在斯大林主义的圈子里,许多意见还是要通过自己的思想,用他自己的话说出来。”[22]81瞿秋白发表在《新青年》月刊创刊号上的这两篇文章,即具有王凡西所说的这个特点,不仅如此,应该说瞿秋白的整个革命理论实践活动都鲜明带有这一特点。这也是瞿秋白不同于其他早期中国共产党人的一个重要之处。
而进一步就瞿秋白的这两篇文章看,无论是他对斯大林的经典文本的“改译”,还是对托洛茨基主义所作的批判,有研究者说,在1925年初的中共党内,“也只有瞿秋白能完成此项任务”[23]346。环视瞿秋白同时代的人,从他们当时的资望、能力和理论修养看,这样的说法实不为过。
五
中共“四大”后,中国国内政治形势急遽变化。1925年3月12日,一生以“革命”相呼号的孙中山先生逝世,中国国民党党内的分化随之渐呈出公开化。紧接着,以五卅运动为标志,国内掀起了反帝大革命运动的高潮,一时间,“‘打倒帝国主义’一语,在中国已成一种普遍之口号”[24]。与此同时,中共力量得到迅速发展,党员人数从中共“四大”召开时的994人,至年底已增至万余人。另一方面,力主反共、反对国共合作的国民党右派势力的活动,这时也猖獗起来。先是戴季陶出版了他的《孙文主义之哲学的基础》《国民革命与中国国民党》的小册子,公开宣扬阶级调和,反对马克思主义的阶级斗争学说;后有邹鲁等人在北京西山非法召开所谓的“国民党一届四中全会”,并宣布取消中国共产党人在国民党党内的党籍。1926年1月初,蒋介石则在中国国民党“二大”上攫取了党内的实权。
上述国内阶级关系以及各种力量对比的变化,也反映到了思想和舆论界。仅举一例看,1926年列宁逝世周年忌日,诗人徐志摩便曾公开发文,表示怀疑马克思的阶级和革命学说,进而提出:应当“给现在提倡革命的人们的议论一个彻底的研究,给他们最有力的口号一个严格的审查,给他们最叫响的主张一个不含糊的评判”。那么,诗人徐志摩又是如何“研究”、“审查”、“评判”革命的呢?在他看来,俄国革命并不是“马克思学说所推定的革命”;在中国,“阶级的绝对性更说不上了”,阶级斗争“还远得很”,现在就来谈这个问题,实在是“神经过敏”。文中攻击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是“第三国际式的革命”,“不是起源于我们内心的不安,一种灵性的要求,而是盲从于一种根据不完全靠得住的学理,在幻想中假想了一个革命的背景,在幻想中设想了一个革命的姿势,在幻想中想望一个永远不可能的境界。这是迂执,这是书呆”。对待列宁和列宁主义,徐志摩直言不讳地表示,“不希望他的主义传布”。在徐志摩的笔下,列宁不仅被说成了是“一个制警句编口号的圣手”,一个“话里有魔力”的“党魁”,也是一个“主张不免偏窄”、“议论往往是太权宜”的“危险”人物。徐志摩甚至对列宁进行人身攻击说:“他不承认他的思想有错误的机会;铁不仅是他的手,他的心也是的。”在这番攻击、诋毁之后,徐志摩终于说出了他最想说的话“不要轻易讴歌俄国革命,要知道俄国革命是人类史上最惨刻苦痛的一件事实”,“我们不要叫云端里折过来的回光给迷糊了”;“我们不要狂风,要和风,不要暴雨,要缓雨”[25]。
也是在列宁逝世两周年忌日,瞿秋白在《向导》周报上发表了他的《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一年后,他在将该文收入自编论文集时,标题后用括号表示本文系“改译”,但究竟“改译”自何人何文,因何需要特意注明是“改译”,现已无从考证。据杨之华回忆说,1926年春,瞿秋白因肺病严重住进了上海宝隆医院。住院期间,瞿秋白曾经吐露说:“中国共产党员连我在内,对列宁主义的著作读得太少了,要研究中国当前的革命问题,非读几本书不可。”而在入院之前,瞿秋白已在酝酿编译一套丛书,就是“针对当前中国革命中几个重要问题编译几本值得参考的丛书”,并已在着手准备,为此,正想找一个较安静的地方来实现自己的“心愿”[26]205-206。这样看来,《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很有可能正是从为编译这套丛书而收集来的材料中“改译”而来。这从该文松散的结构、略显零碎的内容,也不难看出一二。尽管如此,该文力求将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相结合,它在这一点上所作的努力表明,其在列宁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史上仍具有十分重要的地位。
首先,瞿秋白指出,列宁主义是唤起人民反抗帝国主义统治的强大思想武器,中国蓬勃发展中的民族解放运动,证实了列宁主义之于中国民众的意义。 因此,纪念列宁应当重在考察中国革命运动之发展与世界革命及列宁主义的关系。其次,瞿秋白指出,国民革命最近一年来的发展证明,“中国无产阶级是民族解放运动中的主干”,中国共产党“有指导群众的政治运动的能力”,但现时中国人民的反帝斗争“还很幼稚”,“还没有分别谁是朋友谁是仇敌的明确的觉悟”,因而不免有“许多动摇不定的政策”;在坚定革命意志、革命观点、革命政策方面,“列宁是我们的模范”。第三,瞿秋白指出,中国共产党最近最紧要的革命任务,就是要“努力赞助并领导国民革命运动”,“全力联合一切革命的民主主义的力量,使成一伟大的反帝国主义联盟”。第四,在革命路径的选择上,针对有人提出的“用和平的方法,阶级妥协的方法”就可以争得劳动阶级的解放的说法,瞿秋白指出,欧洲大战后各国政府实行的劳动政策,已经“完全证明这一说法的错误”;俄国革命的道路已在向人们表明,只有组织起自己的军队,才能扫除资产阶级的反革命,战胜帝国主义者的武力侵略。所以,国民革命要取得最后的胜利,就需要组织起自己的“人民的武力”[27]。
可以看出,《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一文,尽管是一篇“改译”之作,但文中所表述的一些重要观点,有力促进了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并深刻体现了瞿秋白对列宁主义在中国革命实践中的具体运用。
六
毋庸置疑,在中国早期列宁主义传播史上,李大钊、陈独秀、瞿秋白、恽代英等中共早期领导人都曾作出过重大贡献,但就大革命失败前其个体对列宁主义的传播力度和深度来看,其中“当首推瞿秋白”[28]。在这点上,一些海外研究者甚至给予了瞿秋白更高的评价。如澳大利亚学者尼克·奈特认为,“马克思列宁主义在中国的传播是从瞿秋白开始的”[29]7。台湾研究者姜新立在1982年提出,以瞿秋白“对列宁主义的了解”看,“到现在为止,中共尚无一人能超过他”[30]152。这些说法虽有所言过、失实,但从一个侧面也说明瞿秋白在传播列宁主义方面,确有为同时代人所不及的贡献。如在斯大林定义的“列宁主义”还尚未传入中国之前,瞿秋白便以“历史工具”论为立论点和阐发点,把“列宁”这个名字变成了一个具有双重指向功能的语码符号;他对列宁的革命理论和革命实践活动的特点作出的四点概括,实际上也是中国共产党人对于列宁主义的精神内涵和实质,所能作出的最早较为系统的解读。在这些纪念文本之中,瞿秋白还力求将列宁主义同中国革命实际相结合,其中一些思想观点,深刻体现了其马克思主义中国化思想,及其新民主主义革命思想的萌芽。
另一方面,在“列宁主义”一词在中国出场,并作为一个具有特定内涵所指的政治概念被确认、固定下来之后,“列宁主义”的言说事实上成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主导性话语。这也就是说,在中共早期意识形态结构中,居主导地位的,实则是“具有民族主义涵义的、列宁化的马克思主义”[11]226。马克思主义在中国早期传播的这一特点,固然适应了当时正处于迅速发展中的国共合作和大革命斗争的实际需要,但是因此也造成人们不适当地夸大了列宁主义的普遍指导意义,进而把“俄国人的路”看作是实现马克思主义理论原则的唯一路径和模式。这就极大束缚了人们认识思想的发展,并且深刻影响到中共早期革命话语的生产机制。所以,瞿秋白对“列宁主义”的指认和阐释,也不免有囿于时代和历史条件下不成熟的一面。如在民族问题上,提出应当承认蒙古、西藏具有“完全自决权”,主张效仿苏俄的联邦制模式,建立中国的“联邦共和国”[27]。而在如何看待阶级斗争的作用的问题上,对于阶级斗争在推动历史发展中的作用的过度解读,也使其惯常在左与右、革命与反革命、社会主义与机会主义两相对立的思维模式下,去观察周围的事物,去思考现实中遇到的问题,从而把任何利益冲突和意见分歧都看成是阶级斗争的表现。瞿秋白在《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一文中的一些认识,即带有这样的问题。这也深刻说明,中国共产党人这时对于列宁主义的理论品质和精髓,都还尚缺乏完整、统一的认识和把握。
从上述意义上说,总结瞿秋白的列宁主义传播之旅,尤其是他在国共合作时期对“列宁主义”的场域指认和阐释,也就不仅为我们深入考察列宁主义在中国的早期传播问题提供了一个可供研判的经典案例,而且可以帮助我们正确认识和把握“什么是列宁主义,怎样对待列宁主义”的问题,进而不断开拓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发展的新境界和新局面。
参考文献:
[1]任平.论马克思主义出场学的辩证视阈[J].马克思主义研究,2012(5).
[2]斯大林.斯大林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3]苏联共产党代表大会、代表会议和中央全会决议汇编:第二分册[M].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
[4]库恩.共产国际文件汇编:第2册[M].北京:三联书店出版社,1965.
[5]中共中央党史研究室第一研究部.共产国际、联共(布)与中国革命文献资料选辑:第2卷[M].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1997.
[6]鲍罗廷.列宁之为人[N].民国日报:广州,1924-01-26.
[7]林精华.俄罗斯问题的中国表述[J].俄罗斯研究,2009(5).
[8]列宁.俄罗斯革命之五年[J].瞿秋白,译,新青年季刊,1923(1).
[9]瞿秋白.自由世界与必然世界[J].新青年季刊,1923(2).
[10]瞿秋白.历史的工具——列宁[N].民国日报·追悼列宁大会特刊:上海,1924-03-09.
[11]德里克.革命与历史:中国马克思主义历史学的起源[M].翁贺凯,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
[12]瞿秋白.李宁与社会主义[J].东方杂志,1924(6).
[13]彭述之.十月革命与列宁主义[N].向导周报,1924-11-07.
[14]中央档案馆.中共中央文件选集:第 1 册[M].北京:中共中央党校出版社,1989.
[15]沈云龙.近代中国史料丛刊续编:第87辑[M].台北:文海出版社,1982.
[16]瞿秋白.瞿秋白文集:政治理论编: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9.
[17]瞿秋白.列宁主义概论[J].新青年月刊,1925(1).
[18]毛泽东.毛泽东书信选集[M].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
[19]毛泽东.当学生,当先生,当战争领导者[J].党的文献,1923(6).
[20]杨之华.一个共产党人——瞿秋白[J].党史资料,1953(1).
[21]瞿秋白.列宁主义与杜洛茨基主义[J].新青年月刊,1925(1).
[22]王凡西.双山回忆录[M].北京:东方出版社,2004.
[23]王观泉.一个人和一个时代——瞿秋白传[M].天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1.
[24]周伦超.论打倒帝国主义[N].京报副刊·救国特刊,1925-07-19.
[25]徐志摩.列宁忌日——谈革命[N].晨报副刊,1926-01-21.
[26]杨之华.忆秋白[M]∥忆秋白.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7]瞿秋白.列宁主义与中国的国民革命[N].向导周报,1926-01-21.
[28]孙淑.瞿秋白在中国传播列宁主义的历史功绩[J].南京大学学报,1995(4).
[29]Knight N.Marxist Philosophy in China: From Qu Qiubai to Mao Zedong[M].Springer,2005.
[30]姜新立.瞿秋白的悲剧[M].台北:幼狮文化事业公司印行,1982.
(责任编辑刘自强)
Qu Qiubai and the Initiation and Propagation of "Leninism" in China:
Based on Qu's Several Commemorative Texts in the KMT-CPC Cooperation Period
LIANG Hua-kui
(Ideological and Political Theory Teaching and Research Department, Xuzhou Institute of Technology, Xuzhou 221018, Jiangsu,China)
Abstract:In the history of the early spread of Marxism in China,the word Leninism and the concept of Leninism was introduced into China asynchronously.In several texts in honor of Lenin during the KMT-CPC cooperation period,Qu Qiubai identified and interpreted the domain of Leninism which showed,on one hand,his outstanding contributions over his contemporaries and,on the other hand, exposed his tentative understanding constrained by the time and historical conditions.Therefore,it is helpful for us to conclude Qu's propagation of Leninism during this period in order to advance the further research of Leninism in the early days of China and correctly understand and grasp the problems like "what is Leninism" and "how to treat Leninism".
Key words:Qu Qiubai; Leninism; initiation
中图分类号:D62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3571(2015)03-0011-09
作者简介:梁化奎(1965- ),男,江苏徐州人,徐州工程学院思想政治理论课教研部教授,硕士生导师,主要从事中共党史党建研究。
基金项目:江苏社科研究学会专项课题项目“‘秋白精神’的菁华:瞿秋白的探索精神研究”(13SXH-036)的阶段性成果
收稿日期:2015-03-30