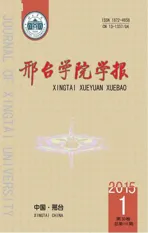中西移情说散论
2015-02-28王玉华
王玉华
中西移情说散论
王玉华
(邢台学院文学院,河北邢台 054001)
移情就是把自我本身的知觉、情感、意志、理念等等心理活动外射到物。在中西方美学史上,对移情现象的艺术实践和论述古已有之。
中西;移情;比较
何谓移情?我们先看唐代诗人韦庄的七绝《台城》:“江雨霏霏江草齐,六朝如梦鸟空啼;无情最是台城柳,依旧烟笼十里堤。”这首诗凭吊六朝古迹。诗人借景寄感,发世间盛衰兴亡、沧海桑田之慨。本来江南的烟雨、碧草、啼鸟、杨柳等自然景物不具有感知、灵性,因而无所谓有情与无情,但诗人将自然情感化、人性化。“人生有情痴,遇物牵所思”(白居易语),物之“无情”正是诗人主观情感的附会,恰恰表明诗人的“多情”。
由上可知,所谓移情就是把自我本身的知觉、情感、意志、理念等等心理活动外射到物,仿佛觉得外物也有同样的属性、情感,使自然事物生命化,无情事物有情化,故有人又曰移情为“情感的外射”,或“宇宙的生命化”。陶渊明之爱菊、周敦颐之爱莲、林和靖之爱梅,无不是作家将思想感情、个体品性、审美情趣灌注于自然景物之中,这些景物自然烙上作家的主观色彩,成为某种情感、思想与人格的意象。因此,法国美学家巴布甚至把移情叫作“象征的同情”,认为“引起移情的事物成为一种情趣、品性的象征。”
移情说于19世纪后半叶,德国美学家、心理学家立普斯(Lipps 1851~1914)提出。他在美学名著《空间美学和几何学·视觉的错误》、《论移情作用,内摹仿和器官感觉》、《再论移情作用》中详细论述了作为审美的移情作用。移情说是美学的基本原则,是解答一切美学问题的钥匙,因而此观念的提出在美学史上具有重要意义。李斯托威尔曾评论说:“这一理论,比起任何其他的理论来得到更为普遍的承认,在整个半世纪中,在欧洲大陆的美学理想中,取得了支配的地位。”移情说的崇拜者甚至将它与达尔文的生物进化论相媲美,而立普斯则被奉为移情说之父。
其实,在中西方美学史上,对移情现象的艺术实践和论述古已有之。荷马史诗中就有如下描写:“矛头站在地上渴想吃肉”、“矛头兴高采烈地闯进他的胸膛”、“那块无耻的石头又滚回平原”。古希腊文艺理论家亚里斯多德在《修辞学》中将此种“把无生命的东西变成活的”艺术手法称为隐喻。德国古典主义哲学家康德和黑格尔的美学理论中也曾涉及移情。康德在《判断力批判》中说:“对自然的崇高感,就是对我们自己的使命的崇敬,通过一种‘暗换’的方法,我们把这崇敬移到自然事物上去(对主体方面的人性观念的尊敬换成对对象的尊敬)”。这里康德提出“暗换”,即自然事物之所以显现出一种崇高情感,是因为我们把对自我内心的崇敬付予了自然界的对象。黑格尔也曾指出:“自然美是属于心灵的那种美的反映”,通过自然美能够“感发心情和契合心情”,自然景物与人类心情的这种“契合”是与人的生命力向自然的“渗入”分不开的。康德、黑格尔以“暗换”和“渗入”试图阐释移情,显然两人的有关论述已十分接近移情说。
中国最早的诗歌总集《诗经》中亦运用了移情。《小雅·采薇》:“昔我往矣,杨柳依依;今我来思,雨雪霏霏。”依依杨柳和漫天飞雪实际上寄寓了征人离家时难舍难分,以及经过战乱于归途中的欣喜和欢悦之情。后代的诗词歌赋中移情现象更多,“海水梦悠悠,君愁我亦愁”(南朝东府《西洲曲》)、“多情只有春庭月,犹为离人照落花”(张泌《寄人》)、“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元稹《行宫》)、“细看来不是杨花,点点是离人泪”(苏东坡《水龙吟》、“可堪孤馆闭春寒,杜鹃声里斜阳暮”(秦观《踏莎行·郴州施舍》)、“晓来谁染霜林醉,总是离人泪”(王实甫《西厢记》)。诗中景物皆是作家情中景物,清末王国维概括为“有我之境”,“有我之境,以我观物,故物皆着我之色彩。”这里只是信手撷取几例,如此移情于物、寄情于景的诗句在我国古典诗、词、曲、赋中俯拾皆是。
中国文学起源于古典诗歌,在美学思想上强调艺术中的情感。“诗言志”,诗歌要表达思想情感,就要籍于外物。谢榛在《四溟诗话》中说:“景乃诗之媒,情乃诗之坯,合而为诗。”古代诗词刻意去追求情景交融的意境,因而诗论家便将情与景这对范畴独立出来。在历代文论中,对二者的关系有大量的精僻论述。“托物见志”、“意与象通”,“登山则情满于山,观海则意溢于海。”宋代以后的诗论家更多的是强调彼此的有机统一,“意中有情,景中有意”(姜夔语)、“景无情不发,情无景不生”,对二者的认识上升到辩证的高度。
立普斯审美移情的主要特征是主体移情客体,主客融于一体。他举例:“我在蔚兰的天空里,以移情的方式感觉到我的喜悦。那蔚兰的天空就微笑起来,我的喜悦是在天空里,属于天空的。这和对某一对象微笑不同,我欣赏的审美对象的愉快就是‘我’自己的愉快,就我的意识说,我和它完全统一起来了。”立普斯的移情说具有双向性,在聚精会神地观照中,仿佛蔚兰的天空与我有同样的喜悦,主体又通过这种错觉与对象发生共鸣,把我的性格、感觉、情趣移注于物;同时又把物的姿态吸收于我,我没入大自然,大自然也没入我,物我交感,人的生命和物的生命往复回还交流,相互碰撞,相互振荡,相互改变。物体被主体的情志意识化,主体被客体的表象审美化,我和物的界限完全消失。主体与客体、个体与整体、形象和观念、现实和理想、生命与宇宙、瞬间与永恒、有限与无限等等得到交融、互渗、沟通。这种移我于物,又移物与我建构一种新的意象,达到美感最高层次,物我两忘,物我同一,呈现一种超物我、超时空、超功利的审美极致状态。
中国的美学理论中,对移情阐释比较深入的是晋代刘勰和明清之交的王夫之。刘勰《文心雕龙· 物色》“情往似赠,兴来如答”点出移情作用的双向性质。情与物的关系好似一种互相赠答的关系,主体的生命、情感外射于物,无生命的物不仅生命化而且情感化,反过来生命化的外物又激发、强化主体情感。他在《物色》的另一论述:“诗人感物,联类不穷,流连万象之际,沈吟视听之区,写气图貌,即随物以宛转,属朱附声,亦与心而徘徊。”也阐明心物两者的双向往复关系。王夫之在《诗绎》里也谈到:“情景虽有在心在物之分,而景生情,情生景,哀乐之触,荣悴之迎,互藏其宅”情景最初相离的,通过移情到情景交融的审美境界。
立普斯的审美移情是建筑在移我于物,由我及物的前提下。事实上,审美移情的发生也可以物移我情,由物及我。物象可以感发兴起人们的喜怒哀乐。《诗经·周南·关睢》“关关睢鸠,在河之洲,窈窕淑女,君子好逑。”河畔水鸟的啼鸣,触发了君子匹配佳偶的情思。诗六义之一的“兴”即是“引譬连类,感发意志”,也就是触类旁通。刘勰《文心雕龙·比兴》中“兴者,起也”,“起情,故兴体以立。”刘熙载《诗概》中对“兴”的理解“触物以起情”,都说明自然客体可以启发,感动主体的情感意志。
刘勰也充分肯定了主体的审美心理活动可以由客体的物引发。“物色相召,人谁获安,是发献岁发春,悦豫之情畅;滔滔孟夏,郁陶之心凝;天高气清,阴沈之志远,霰雪无垠,矝肃之虑深。岁有其物,物有其容,情以物迁,辞以情发。”四季自然环境的变化激发人们情感和心境的变化。陆机《文赋》”遵四时以叹逝,瞻万物而思纷;悲落叶于劲秋,喜柔条于芬春”。白居易:“外事牵我情,外物诱我情。”吴乔“情能移境,境亦能移情”都表明可以触景生情,由景起情。主体观照、审视某种事物,产生特定心境,又以此心境去看事物,这样他对事物的感觉就会染上主体所具有的特定感情色彩,加深他的主观心情。文学作品中有不少这样的例子可以佐证。王昌龄《闺怨》“闺中少妇不曾愁,秋日凝妆上翠楼,忽见陌头杨柳色,悔叫夫婿觅封侯。”孟浩然《秋登万山寄张五》“愁因薄暮丐,兴是清秋发。”唐彦谦《小院》“小院无人夜,烟斜月转明。清宵易愁惆怅,不必有离情。”人们本无伤怀愁绪,但杨柳,清宵,薄暮等外物却撩拨起情思愁肠,正所谓触景生情,情因景生。
当然,起何情是由主体情绪、心境所界定。“观则同异于外,感则同异于内,”深者见深,浅者见浅,仁者见仁,智者见智。这决定于审美主体的心理构架、心理背景和审美心理定势。对审美客体的观照、审视不同,所激发的审美情感的高低,雅俗、美丑、深浅也不同。面对梅花,陆游“零落成泥辗作尘,只有香如故”(《咏梅》),抒发他孤高自许,孤芳自赏的情愫;林逋“众芳摇落独暄妍,占尽风情向小园”(《山园小梅》)寄寓他不与世俗同污,洁身自好的操行品性,王冕“不要人夸颜色好,只留清气满乾坤”(《画上题跋》)以梅自喻,昭示他崇高的民族气节;毛泽东“已是悬崖百丈冰,犹有花枝悄”(《卜算子·咏梅》)则表达了革命者的铮铮铁骨和坚强意志。由于审美主体各自的生活基础、社会地位、文化素养、心理背景的差异,产生了不同的审美感受。
应当指出的是,立普斯的移情说也有片面性的一面。在论述美感产生的原因时,他说:“审美欣赏的原因就在我自己或自我,也就是看到对象而感到欢乐或愉快的那个自我。”“从一方面说,审美的快感可以说简直没有对象,审美的欣赏并非对于一个对象的欣赏,而是对于一个自我的欣赏。”他以为美感产生的原因,不是审美对象,而是灌注于审美对象中的主体情感,主体生命,主体的直接价值感,对象本身并非引起审美知觉的客体,只是主体情感的载体,它与审美主体是同一东西,即自我。因而人们审美面临的自然实体,究其本质是一种主体自我的欣赏,移情的产生纯粹由审美主体决定,这就否认了审美对象的客观存在。
2014-12-25
王玉华(1962-),女,河北沧州市人,毕业于河北师范学院中文系,硕士,教授,主要研究西方悲剧.
I106.3
A
1672-4658(2015)01-0127-0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