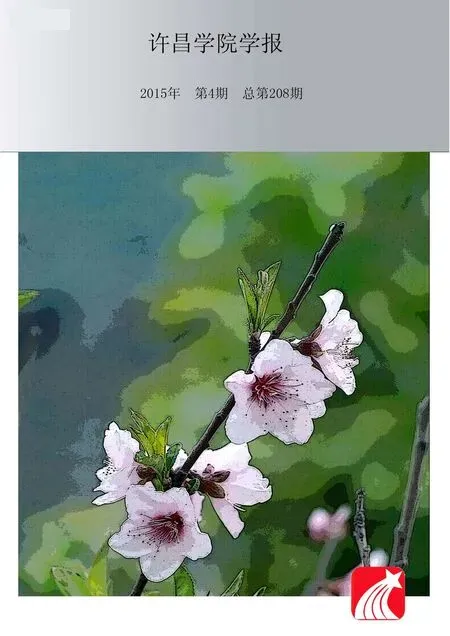领袖与个人:解读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2015-02-28叶君剑
叶 君 剑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00)
领袖与个人:解读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
叶 君 剑
(浙江大学 历史系,浙江 杭州 310000)
西安事变发生之初,面对“兵谏”,蒋介石内心感到屈辱与愤怒,表现出抗拒与不合作的态度。之后宋子文和宋美龄的到来,使蒋介石了解事态,改变态度,同意宋子文与中共会谈,并两次接见周恩来,口头保证不再“剿共”,从而为西安事变的和平解决奠定了基础。而在西安事变中,对于作为领袖与个人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属性下的蒋介石,我们可以有不同的解读。
西安事变;蒋介石;张学良;宋子文;宋美龄
1936年12月12日,张学良、杨虎城采取“兵谏”的方式,扣留了前来西安督剿红军的蒋介石,是为震惊中外的“西安事变”。对于身处漩涡中心的蒋介石来说,虽然他在事变解决过程中一直处于被软禁、被监视的不利地位,但其态度的变化却对事变的和平解决有着至为重要的作用。无论是中共、张(学良)杨(虎城),抑或是两宋(宋子文、宋美龄),各方之间角逐、谈判的最终目的无一不是指向蒋介石:或促其改变既有政策,或保其安全离陕。作为全国领袖,蒋在事变中的一言一行自然备受瞩目;同时作为个人而言,他在险境中又有着本能反应和情感需求。既往的研究成果大多强调蒋介石与西安事变的发生,蒋介石在西安事变中的态度转变以及西安事变对蒋介石国内政策的影响,较少从领袖与个人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属性来剖析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对于蒋介石来说,西安事变不仅是一次领袖地位危机,也是一次个人安全危机,因而蒋在事变中的言行既有作为领袖的考虑,也有出于个人的需要。本文即试图通过梳理、考察事变中蒋介石的言行以及蒋直接参与交涉的活动,从中解读其背后的身份属性差异。
西安事变解决后不久,蒋介石、宋美龄分别撰写了《西安半月记》①《西安半月记》实际由陈布雷代笔。和《西安事变回忆录》。但从文本本身来看,两者(尤其是《西安半月记》)更像是政治宣传品,并有意掩盖了一些事实。而到了21世纪,随着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收藏的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蒋介石日记》②本文所用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原稿用英文写成)由张俊义翻译,刊于《百年潮》,2004年第7期;《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系浙江大学历史系肖如平老师赠予,特此感谢。相继开放,使我们探讨西安事变中的蒋介石有了更多可以相互参照的文本,也为我们进一步分析兼具双重身份属性的蒋介石在事变中的表现提供了多样视角。
一、事变之初:“绝食”与抗拒
1936年12月4日,蒋介石从洛阳来到西安,以临潼华清池为行辕,亲自督促张学良、杨虎城围剿红军。12日清晨,当蒋介石起床披衣时,大门外响起了枪声,且连续不断。蒋随即意识到这是东北军的叛变,但初步怀疑“为一部之兵变,必系赤匪煽惑驻临潼部队暴动,而非汉卿有整个之计划。盖如东北军整个叛变,则必包围行辕外墙之四周;今前垣以外,尚无叛兵踪迹,可知为局部之变乱”。[1]7随着事态的迅速发展,蒋介石“局部叛乱”的设想被无情击碎。其实在事变发生的前一天,蒋已察觉到某些异样,这在《蒋介石日记》中有所记载:
早起在院中散步,见骊山上有二人向余对立者约十分,时心颇犹豫,及回厅前,见有军用汽车由西向东者甚多,心又疑虑。……晚,招张、杨、于与中央各将领来行辕会议进剿计划。杨、于不到,而张之行色匆忙,精神慌惚,甚觉有异,乃以为其今日来时,或彼听得余对黎天才训诫之言,使彼心不安;又以其为昨日闻余切训,使彼不乐而已。[2]1936.12.11
无论如何,蒋介石也不会将这些的异样情况同全面叛乱相联系,更何况这场叛乱的策划者之一还是张学良。因而,当蒋在躲藏的岩穴中被士兵抓获后,其内心的屈辱与愤怒便可想而知了。13日的蒋日记中有“生而辱,不如死而荣”一语;《西安半月记》中12日的蒋、张对话中不乏“厉声叱之”、“愤极”、“怒诘”等语。
至于如何宣泄心中的愤懑,《西安半月记》中记载蒋介石采取了绝食的方式。12日事变当天,蒋被拘禁在杨虎城所在的新城大楼。当张学良叫仆人端来食物时,蒋以“余生已五十年矣,今日使国家人民忧危至此,尚何颜再受人民汗血之供养而食国家之粟?况义不食敌人之食”回应,坚决拒食,并且整日未进食。[1]16-19次日,负责看管蒋介石的杨虎城部下宋文梅又劝蒋介石进食,并声明食物系其私人所购,并非出自公家,但蒋仍加以拒绝。[1]19-20
蒋的绝食亦能从相关人士的回忆录中得到印证。14日跟随端纳飞来西安了解情况的黄仁霖这样追忆:“一直在追询委员长的健康状况之后,张学良又开了话题说,委员长对于此次反抗行动,非常震怒。因此,他拒绝进食,拒绝和张学良谈话。……他看起来很苍白而疲倦。因为他已有二天二夜拒绝进食或饮水。”[3]103-104黄的叙述相当简短,而且也是间接得知,说服力显然不够。同样经历过西安事变的高崇民为我们提供了另外一种解释版本:
蒋在被扣之后,南京方面大肆宣传说,蒋已绝食了,实际是头两天,蒋因为一口假牙,在华清池仓皇逃跑时遗落在寝室的茶几上,(被一士兵拾到)口中无牙,不能咀嚼,无法吃饭,只好喝些流汁,到了第三天,经我们悬赏得到了假牙,蒋立即大吃而特吃。这说明念权怙势的人,是不会轻于自杀。[4]406
高崇民的文章写于1966年8月。撇开其中的政治立场和时代因素,它至少向我们揭示出蒋介石绝食的背后也有他本人难以启齿之处。《西安半月记》关于蒋绝食的描写只限于12日和13日,之后再无绝食之说,而这也与高所记相吻合。
不过,贴身看管蒋的宋文梅回忆:
我劝他入卧室稍憩,并劝他吃饭。我说:“这里的饭是干净的,不会有什么意外,如果因为没有牙齿,有麦片粥,吃点还是好的。”蒋不答也不吃。我再劝他:“今天所发生的事情,是国家大事,应平心静气,设法解决,不应意气用事。”蒋听了之后,说:“如果是你们自己做的饭,吃些也好。”我便叫西安绥靖公署的厨师,预备麦片粥,蒋才吃了些。……我问他喝水吗?他说,想喝些桔汁。我叫人买些桔子汁,盛了一玻璃杯给他,他一饮而尽,并且告诉我,他最喜欢喝桔汁。[5]253
根据宋文梅的叙述,蒋吃了麦片粥,根本没有绝食。另外值得注意的是《蒋介石日记》。在蒋的日记中,对于绝食这样的大事竟无只言片语,如果仅以漏记来解释,似乎太过勉强。日记属于私密文字,不对外示人,同时当事人也有更大的发挥空间;《西安半月记》则是公开出版物,需要树立领袖的正面光辉形象,因此,《西安半月记》中记载的蒋不仅需要“绝食”,而且“绝食”只能是因为愤怒和屈辱。但对于蒋个人来说,绝食之举并不存在,所以在事后补写日记时*有学者通过文本分析和实物参照,认为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的全部内容均非事变当时所写,而是事后补写。参见张天社:《蒋介石〈西安事变日记〉系事后补写》,《百年潮》,2014年第6期,第71-73页。,便无须提及这种子虚乌有之事。至于《西安半月记》,该书主要是出于宣传的需要,“绝食”就被高尚地包装起来了。
西安事变发生后,张学良、杨虎城随即通电全国,提出八项主张:(一)改组南京政府,容纳各党各派共同负责救国;(二)停止一切内战;(三)立即释放上海被捕之爱国领袖;(四)释放全国一切政治犯;(五)开放民众爱国运动;(六)保障人民集会结社一切之政治自由;(七)切实遵行孙总理遗嘱;(八)立即召开救国会议。[6]108那么,蒋介石是何时知道这些主张的呢?这其中还有一段插曲。如前所述,蒋被抓后,一度拘禁于新城大楼。张学良则希望蒋介石能够换住到他的宅邸,但为蒋所拒。13日又托邵力子相劝,让蒋迁到师长高桂滋的宅邸,亦被拒绝。无奈之下,13日半夜张学良派营长孙铭九前来,试图逼迫蒋移居,蒋仍不答应。在此僵局下,14日受宋美龄委托的端纳飞来西安,张学良遂以此为契机,终于劝动蒋迁居:
(端纳)即自请与余同住。余允之。端纳谓:“此间起居,实太不便,务请珍重身体,另迁一处。”其时张亦在侧,力白悔悟,意似颇诚,谓:“只要委员长俯允移居与端纳同住,则此后一切事,大家均可听命办理,并早日送委员长回京。”端纳亦坚请。余不忍拂之,遂以下午移居于高宅。[1]28-29
蒋在14日的日记中也曾提到迁居一事,但又有“余痛斥而深恨其无耻无信一至于此”一语,让人不明前因后果,无耻无信何从体现呢?15日的日记则作了补充解释,并与《西安半月记》相互印证:
十四夕移住张宅(注:实际是高宅)后,余欲其实行在新城所约之言,即移□□一切事大家皆听从委座之意办理,送余早日回京也。及至其家,彼食前言,并提出八条件,并言此事有红军亦参加其间,故须事事□决。[2]1936.12.15
如果张学良在蒋迁居前提出八项条件,那么蒋可能更加不会听从张的安排。所以,张学良先以早日送蒋回京为饵,诱蒋迁居,待蒋移居后,继之以八项条件作为交换条件。按此逻辑,蒋介石的“痛恨”则在情理之中了。作为回应,蒋声明如果他不先回京,那么任何条件或主张均不能谈,在这点上,蒋的态度是非常坚决的。
16日,南京国民政府下令讨伐张学良、杨虎城,任命何应钦为讨逆军总司令,向西安进军,并派飞机进行轰炸。在蒋不松口,前方又面临军事威胁的情况下,张学良委托蒋百里前来劝蒋介石。16日、17日,蒋百里两次来见蒋介石,希望蒋能够致函中央,暂缓军事行动。第一次会见时,蒋介石明确表示:“如有一期限送余回京,则余可致函中央,或能停止进攻。”[2]1936.12.17待到蒋百里第二次来时,转达了张学良同意以蒋介石三日内回京之意致函南京,并下令停止进攻,同时派蒋鼎文携信飞回洛阳,蒋介石这次同意了。虽然不久蒋介石即从张学良的谈话中揣测出张的口头保证并不能相信,但蒋已表现出相当坦然的心态了。
17日的日记蒋介石写下:“读圣贤书,受圣水礼,此时不树万世之楷模,其将何以对生我之天地与父母也。”[2]1936.12.1718日是西安事变一星期,蒋介石感觉“安危生死,所志已决,此心更觉泰然”。[1]4119日,三日停攻之约期已满,蒋更为豁达了:“鼎镬在前,刀锯在后,人生死亡不过五分钟而已。十字架之受难,余不承辱,谁复承受?……张并无任余回京之表示,余亦并无回京之希望。盖明知张之前日之约言为诈也。”[2]1936.12.19
19日晚,张学良来见蒋介石,并作出了一定的让步:
彼又言:“前所要求各件,最好能实行几条,以便速了此事。”余曰:“此八条件,如余不回京,任何一条皆不能行。”彼曰:“现在只须四条,无须八条。”余曰:“所删者何四条?”彼曰:“后四条皆可不谈。”……余始则骇然,继乃知彼等对第三国际请示之结果,不愿提此四条,以避去共党参加此事之嫌疑也。因此余乃更知苏俄之反对叛逆。彼等荒谬如此,无能为之助也。[2]1936.12.19
蒋介石已将个人生死置之度外,因此对于张的让步虽感惊异,但仍不妥协。如果蒋为求自保,答应张的让步条件,固然能够脱险,但对于一位领袖来说,不仅人格将受到质疑,而且威信也会一落千丈。蒋深知此点,故而他的期望便是无条件离陕回京。对于张学良等人来说,蒋如此愿望不啻是痴心妄想。在两者不可调和的情况下,迫切需要有人从中协商,而宋子文的到来正好弥补了这一缺憾。
二、情感慰藉:宋子文来陕
宋子文与张学良私交甚好,此时宋未在政府中担任要职,所以南京方面最终同意他以私人身份前往西安。20日上午,宋子文抵达西安,在见到张学良后,张称:
委员长17日已同意如下四项条件:一、改组国府、采纳抗日分子。二、废除塘沽何梅察北协定。三、发动抗日运动。四、释放被捕七人。但今晨委员长改变主意,谓其不会再胁迫下接受任何条件。[7]17
张学良的说法十分可疑。蒋介石在日记中并无提到上述17日之事,而且张学良自己在19日晚还作了一定让步,蒋也未妥协,又何来20日反悔之说呢?张的谎称,似乎是为了向宋子文暗示:只要蒋介石接受这四项条件,那么就极有可能安全回去。换言之,如果你要和我们谈判,这四项条件是基础。
宋子文见到蒋介石时,蒋再也无法压抑内心的情感了,因为此前他一再叫端纳让宋前来。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蒋当时“甚为感动,失声大泣。我对其安慰,告诉他,彼并未蒙羞,相反,整个世界均在关心他,同情他”。[7]17蒋日记中也记载道:
谁知子文不一时与端纳及张来见,余不知泪自何来。子文即□妻函交余,称:“如子文三日内不回,则妹必来陕与兄共生死也。”不觉咽呜,不忍出言者再。[2]1936.12.20
在宋、蒋两人的单独谈话中,宋子文明确指出:
军事上之成功并不能确保其性命之保全,即便西安被占,他们尚可退至接壤共区,惟国家将陷于分裂,内战四起。他(注:指蒋介石)的性命悠关整个国家之命运,并非其个人一己之事。他必须认识到,他的案件,不似一名将军遭一群有组织队伍捕获那么简单,只要捕捉者被迫作出退让,就可饶其性命。[7]17
宋的说法无疑在某种程度上触动了蒋。当日下午张学良在拜见蒋介石后,对宋子文说,自宋见了蒋之后,蒋的态度逐渐通情达理。蒋介石甚至答应张学良:(一)允其军队开往绥远;(二)召开大会讨论四项条件;(三)改组陕西省政府,由杨虎城提名人选。但在张学良、杨虎城看来,蒋介石仍旧避重就轻,因为1、3两点并不重要,关键是第2点,如果蒋个人同意,大会讨论只不过是形式。[7]18
21日,在协商无果且形势可能继续恶化的情况下,宋子文决定先回南京,并在离开前去拜见蒋介石。对于这次分别,宋子文日记记载寥寥,蒋介石日记却作了非常生动、细致地描写:
上午十一时许,余正在睡中,子文忽入门,余目犹迷雾,不辨其为子文也。少顷清醒,始识其真为子文,告余曰:“余即欲回去,后日或将再来。”余甚骇其回去之速。……彼不愿与余多言。余知其意,乃托二语曰:“尔切不再来。”以手势全力示以速即进兵;其次切嘱余妻,无论如何余不欲其来此地,务请转达。彼乃强应之。又曰:“我约后日回来。”……子文既出,仍回身向余曰:“余后日必回。”余知其不忍离舍之状,亦未有甚于此者也。[2]1936.12.21
从“后日或将再来”到“后日回来”,再到“后日必回”,与其说是宋的承诺渐重,毋宁说是蒋自己的情感步步加深。虽然当时的实际情况是否完全如蒋所叙述的那样,这点我们不得而知,但非常明显的是,宋子文来西安后,蒋介石心中的苦闷、孤独与委屈有了一次非常合适的宣泄,展现了其坚毅背后柔弱的一面;而宋子文转天即走,亲近之人的离去,又让蒋的精神寄托再度空虚,不免形单影只。
在与宋分别之际,蒋介石将三封分致国民、宋美龄及其二子之遗嘱交给宋*根据12月20日的《蒋介石日记》,蒋是在该日将遗嘱交予宋子文的。但宋子文的日记则显示是在21日得到蒋的遗嘱。两者孰是孰非,无从考证,笔者倾向于宋说。,但遗嘱被张学良扣下。其实早在16日黄仁霖来见蒋介石时,蒋就写了一封相当于遗嘱的信给宋美龄,并反复朗诵,希望黄仁霖至少能以口述的形式告知宋美龄,但不曾想黄仁霖本人被张学良扣留。宋子文答应后天必回,但严格来说并没有遵照约定,因为他翌日即回。而这一次与他同行的,正有蒋介石既想见又最不希望见到的那个人。
三、态度趋缓:宋美龄共难
西安事变发生时,宋美龄刚好在上海,开会讨论改组“全国航空建设会”一事。蒋介石被劫持的消息传来时,对宋来说无异于晴天霹雳。当她赶回南京后,主张和平解决事变。在宋美龄的委托下,端纳于14日飞抵西安一探究竟。*端纳在西安事变中的行程值得注意。13日傍晚,端纳(随行者黄仁霖)抵达洛阳。14日,端纳飞抵西安,并从西安发来电报。15日晨,端纳飞回洛阳,下午用长途电话告诉宋美龄西安状况。16日,端纳返回西安。通过对事变以及蒋介石状况的了解,宋美龄更加坚定了采用和平方式解决事变的态度。本来20日宋子文飞去西安时,宋美龄即打算一同前往,却不料被众多政府要员所阻。待到21日宋子文从西安回来后,宋美龄便坚持要在22日去西安,因为“当时余对西安事变已具一种感想:譬之造屋,端纳既奠其基,子文已树柱壁,至上梁盖顶完成之工作,实为余无可旁贷之责任矣”。[8]2822日,宋美龄、宋子文、端纳、蒋鼎文和戴笠一行到达西安。
22日是冬至日,蒋介石在清晨祷告完毕后,翻阅圣经,恰好看到“耶和华要做一件新事,即以女子护卫男子也”一句,岂不料下午即见到妻子宋美龄。关于夫妻相见时的情形,宋美龄这样描述:
余入吾夫室时,彼惊呼曰:“余妻真来耶?君入虎穴矣!”言既,愀然摇首,泪潸潸下。余强抑感情,持常态言曰:“我来视君耳。”盖余知此时当努力减低情绪之紧张。[8]32
对于宋美龄的到来,蒋介石在惊喜的同时,却增添了不少忧愁:
相见时悲痛不可名状。余切属子文劝妻万不可来西安,乃不料其竟冒万险而入此虎穴也。妻见余,强作欢颜,而余则更为之忧。以今后所作,乃须顾虑妻之安危,而本身之生死早已置之度外也。[2]1936.12.22
在蒋看来,西安事变本只是针对自己,幸好未殃及妻子宋美龄,但宋美龄为救夫君,竟然以身犯险。原本蒋将自己的生死已经看淡,这时却不得不面对夫妻二人共生死的局面。顾虑的因素一旦增多,原来的决心便可能动摇。反过来看,宋美龄的到来也不失为一个福音。一方面,宋美龄与张学良关系密切,宋的到来无疑对张产生了更大的压力;另一方面,17日中共代表周恩来等人已到达西安,但蒋介石一直不愿相见,宋美龄的到来恰好在蒋与中共、张杨之间架起了沟通的桥梁,她可作为蒋的私人代表与各方进行协商、谈判。
22日晚,宋子文前去拜见蒋介石,蒋同意宋子文与宋美龄一起去见中共代表周恩来,并且提出四点要求:(一)取消中华苏维埃政府;(二)取消红军名义;(三)放弃阶级斗争;(四)愿意服从委员长作为总司令的指挥。蒋还保证将于三个月内召集国民大会,并且在必要的情况下,可以让宋美龄签具一份保证书。[7]19由此不难看出,宋美龄的到来的确缓和了蒋的对抗情绪,为事变的和平解决打开了快速通道。但是,在谈判中首先登场的却是宋子文。
23日,蒋介石让宋子文与张学良一道去见周恩来,但主要是听周讲。在上午的会面中,周表示,中共原则上同意取消苏维埃政府及在中央政府的领导下作战,但希望保留自身的军事系统,并愿意支持蒋介石的抗日行动。而在下午张学良、杨虎城、周恩来与宋子文会面时,四人竟然开始讨论新内阁的人选问题。根据宋子文的汇报,蒋介石答复:(一)他将不再担任行政院院长,拟命孔博士担任。新内阁绝不会再有亲日派。(二)返回南京后,他将释放在上海被捕之七人。(三)1.设立西北行营主任,由张负责。2.同意将中央军调离陕、甘。3.中共军队应当易帜,改编为正规军某师之番号。4.中日一旦爆发战争,所有军队一视同仁。(四)1.派蒋鼎文将军去命令中央军停止进军。2.将与汉卿讨论双方共同撤军,在离开西安后,他将发布手令。[7]19-20
由于宋子文本人对中共抱有一定同情心,又和张学良私交不错,所以他们在会谈时并没有产生相当激烈的争论。又因蒋介石明确指示宋子文以听为主,故而可以肯定,在蒋的计划中,宋在23日主要是起到试探中共条件的作用。*但实际上在会谈中,宋子文并不仅仅局限于了解中共的主张或条件,他还提出了自己的解决方案。这点可以从12月23日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明显看出来。宋的做法显然不符合蒋的指示,根据杨奎松的研究,宋子文试图借西安事变重登政治舞台,实现政治抱负(参见杨奎松:《西安事变新探:张学良与中共关系之谜》,江苏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369-377页)。
但是,在宋子文向蒋介石汇报时,他真的会全面传达会谈情况吗?一方面,我们可以肯定的是,23日宋子文等人在会谈时,宋美龄并没有在其身边,这就为宋子文有保留的汇报提供了可能。根据宋子文日记的记载,蒋介石只是要求宋子文与周恩来相见,之后才跟宋美龄商量,而当天下午的会面,宋子文又明确提到是张、杨、周和他自己。宋美龄的不在场也可从蒋介石的日记中找到印证。在23日的日记中,蒋介石提到如果周恩来要求与自己会面时,可以让宋美龄代见,并约定明日十点。由此不难判断,23日宋美龄没有见到周恩来,进而可以得出宋子文与周恩来会谈时她并没有在场。另一方面,如果宋子文将23日下午讨论新内阁人选的意见汇报给蒋介石,那么蒋必定会勃然大怒。因为张、杨只是军官,周是中共代表,宋此时也没有身居要职,四人竟然密谋新内阁人选,岂非置蒋与中央的权威于不顾。而且,蒋介石的答复中只是保证新内阁中不会再有亲日派,可见宋子文并没有全面反馈当天下午的会谈情况,或许只是向蒋提出张、周等人要求新内阁中没有亲日派。*这一猜测,也可从周恩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得到某些印证。在12月23日的电报中,周有提及新内阁的具体人员问题;在12月25日的电报中,周只是说“孔、宋组行政院,宋负绝对责任保证组织满人意政府,肃清亲日派”,而当天谈判有宋美龄在场(参见《关于西安事变的三个电报》,《周恩来选集》(上卷),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70-73页)。当然,关于新内阁人选的讨论,也可视为宋子文向中共、张杨故意示好的表示,以便争取事变的早日解决,至于蒋介石知道与否,则无关紧要。
宋子文向蒋汇报的不可靠也能从蒋的日记中寻找到一些踪迹。24日的日记记载:
上午,共党对余忽提出七项条件,并声明中央军未撤退潼关以东,仍留余在西安,此与昨夜子文所谈者完全相反,余乃知其中另有其故。盖料此为张指使共党做黑面,而彼自可做红面,卖情讨好,以为将来谅解之地也。余乃嘱子文即将其条件退还,并言此条件不能示蒋先生也。子文照此进行,并声言如此只有决裂,以后不再谈判。未几,张果出而调解,并声称:“共党之无信义,只弄手段,如其作怪,我必对周反面云。”[2]1936.12.24
蒋的日记表明中共的态度是先要撤军,然后放蒋,而宋子文23日向他汇报时并非如此。蒋将中共的“变脸”视为是张学良暗中指使的结果。但周恩来在23日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提到:“宋提议由蒋下令撤兵,蒋即回京,到后再释爱国七领袖。我们坚持中央军先撤走,爱国领袖先释放。”[9]71两相对照,不难发现宋子文实际上并没有完全、准确地向蒋传达中共的意见,而是有所隐瞒或歪曲,以至于蒋在24日的日记中有如此记载。或许蒋在事变结束后得知了真实情况,因此后来对宋仍旧冷落,不予重用。
如果我们细看23日蒋介石的答复,不难发现蒋履行承诺的前提是先回南京。所以在张、杨24日召开的西安军事委员会会议上,多数人坚称在蒋介石离开西安前,若非全部、至少亦应履行部分条款。张、杨之间也爆发了激烈的争吵。24日是各方交涉非常频繁的一天,蒋介石却显得相当淡定:
此时之委员长,对于事件之开展,已不感关切,彼厌见周旋,厌闻辩难,尤厌倦于周遭疑虑之空气,出陕与否已不在彼顾虑之中。曾语余曰:“事态既继续如此,余决不作脱险之妄想,望吾妻亦不枉作匪夷所思矣。”[8]43
为尽快使局面明朗化,宋美龄终于与周恩来进行了会谈,进而创造了蒋介石与周恩来见面的条件。24日深夜,宋美龄带周恩来来见蒋介石,由于蒋已睡,所以双方并未多作交谈。*根据学者考证,在西安事变期间,周蒋之间曾两度会面。第一次是在12月24日晚上10时以后,由张学良、宋美龄陪同,此次会面因时间已晚并未多谈。第二次会面在25日上午10时许,由宋美龄、宋子文陪同,这次会面进行了较为深入的谈话。参见张天社:《西安事变期间周恩来蒋介石会面问题新证》,《抗日战争研究》,2009年第3期,第127-132页。虽然没有实质性结果,但蒋对中共代表从“不见”到“见”,这场简短的破冰之谈无疑凸显了宋美龄在软化蒋介石态度方面所起到的特殊作用。
对于那些反对送蒋回京的人来说,问题的焦点在于蒋介石不愿签字,因此他们日后的安全不能保证,这其中最重要的人物就是杨虎城。张学良其实已下定决心送蒋介石回京,但较之于杨虎城,他在西安并没有军事优势,故而他提出先将宋美龄送出城,然后蒋介石再化装混出城。这一提议被宋美龄否决。在僵持不下时,25日上午周恩来与蒋介石的再度会面为事变的最终解决奠定了坚实基础。蒋介石的日记记载:
十时许,周又来见余妻, 其事先为子文言曰:共党对蒋先生并无要求,但希望蒋先生对余面说一语“以后不剿共”是矣。余乃属妻找周来见余。余妻与子文求余强允之,否则甚难也。妻与子文在邻室先见。余及见周, 余谓周曰:“尔当知余平生之性情如何。”周答曰:“余自然知蒋先生之革命人格,故并不有所勉强。”余又曰:“尔既知余为人如此,则尔今日要求余说‘以后不剿共’一语,则此时余决不能说也。须知余平生所求者,为国家统一与全国军队之指挥,□□□□余革命之障碍而已。若尔等以后不再破坏统一, 且听命中央, 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则余不但不进剿,且与其他部队一视同仁。”周答曰:“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言至此,余乃曰:“此时不便多言。余事望与汉卿详谈可也。”周乃作别而去。子文属其再说虎城,使其赞成余今日回京。周乃允之。[2]1936.12.25
宋子文与宋美龄希望蒋介石能当面对周恩来说“以后不剿共”一语,以满足中共的要求。蒋介石内心不认同,所以在周恩来面前,他表示“以后不剿共”一语此时决不能说,除非中共“不再破坏统一,且听命中央,完全受余统一指挥”。周恩来顺势而为,答以“红军必受蒋先生之指挥,而且拥护中央之统一,决不破坏”。这句话虽然是绕了一个弯子,但也间接得到了蒋介石的许诺。周的爽快出乎蒋的意料,蒋也无可奈何,只好以“此时不便多言”来结束这场会谈。周恩来满意地离开,并在当日发给中共中央的电报中汇报了见面成果:
蒋已病,我见蒋,他表示:子、停止剿共,联红抗日,统一中国,受他指挥。丑、由宋、宋、张全权代表他与我解决一切(所谈如前)。寅、他回南京后,我可直接去谈判。[9]73
在得到了蒋介石的口头保证后,周恩来最终说服杨虎城放蒋回京。在离开西安前,蒋介石还特意召张学良、杨虎城训话。这次训话约半小时,以至于黄仁霖担心:
我可听到墙外委座告诫反叛将领们的尖锐而响亮的声音,责备他们鲁莽、反抗的举动,并且可能相反的,已使国家受到了打击。我感觉到这篇训话已经太长了些,而且恐怕张、杨二人会改变他们的决定,那末,所有一切不是都要成泡影了吗?[3]106
黄仁霖的担心并没有成为现实。训话完毕后,蒋介石在宋美龄和宋子文的搀扶下走上汽车,驱车前往机场。傍晚时分,蒋介石等人安全飞抵洛阳,26日中午,抵达南京。而少帅张学良不顾蒋的劝告,毅然陪同返京,从此翻开了人生的另一页。
结语
纵观西安事变,蒋介石的表现充分显露了他作为领袖与个人这样一种双重身份属性。领袖应强调纪律与形象,个人需注重情感与家庭。作为领袖,面对变乱,蒋在初期采取了抗拒的态度。因为如果蒋在危难中轻易承诺或签字,那么他的领袖权威就会严重受损。不管是出于宣传需要的“绝食”,无条件离陕的坚定态度,抑或是离开前对张、杨进行训话的做法,无不契合了领袖应有的身份地位。作为个人来说,蒋的性格中有着坚毅、刚强的一面,虽然他逐渐看淡生死,但在危机中也需要正常的情感慰藉,宋子文的到来无疑提供了一个非常好的契机。当妻子宋美龄来陕共赴危难后,蒋在领袖与个人之间的身份置换则显得相当矛盾。领袖应为全国榜样,威武不能屈;丈夫则需恪尽责任,保护妻子。而宋子文在向蒋介石汇报会谈情况时有所保留,反映出蒋在被动情形下信息获取的有限与不对称。所以蒋让宋美龄介入谈判,不失为是一种主动出击,既能全面了解会谈情况,体现领袖的存在感,也可以在一定程度上规避自己作为丈夫的责任。当然,对于蒋来说,事变的结局还算是圆满的:领袖不尽失颜面,反而威望大为提升;夫妻共生死,患难见真情。
[1] 蒋中正.西安半月记[M].南京:正中书局,1937.
[2] 蒋介石日记(手稿本),美国斯坦福大学胡佛研究所藏.
[3] 黄仁霖.黄仁霖回忆录[M].台北:传记文学出版社,1984.
[4] 高崇民诗文选集[G].沈阳:沈阳出版社,1991.
[5] 吴福章.西安事变亲历记[G].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86.
[6] 西北大学历史系中国现代史教研室等.西安事变资料选辑[G].1979.
[7] 张俊义.宋子文《西安事变日记》[J].百年潮,2004,(7):17-24.
[8] 蒋宋美龄.西安事变回忆录[M].南京:正中书局,1937.
[9] 周恩来选集(上卷)[G].北京:人民出版社,1980.
责任编辑:熊 伟
2015-01-27
叶君剑(1992—),男,浙江临海人,博士研究生,研究方向:中国近现代史。
K265.9
A
1671-9824(2015)04-0017-06