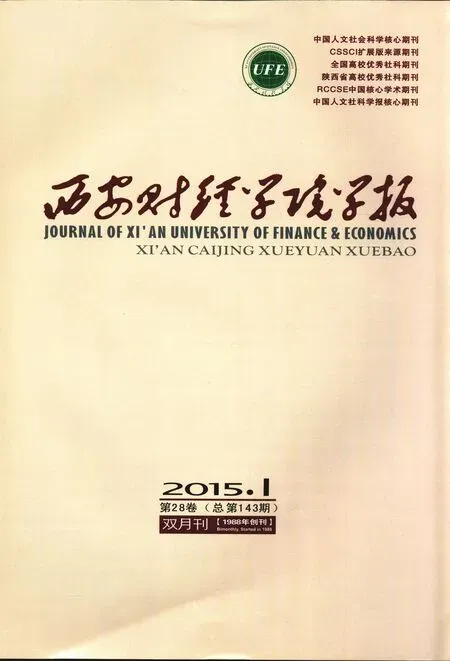《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
2015-02-28高旭
高 旭
(1.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淮南 232001;2.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淮南子》“秦始皇”观评议
高 旭1,2
(1.安徽理工大学, 安徽 淮南 232001;2.南开大学,天津 300071)
《淮南子》多次论及“秦始皇”,从社会经济、政治用人、现实战争及法治实践等方面,对其暴虐之政进行严厉批判。着眼于治术、治道及君道,《淮南子》从道、儒立场出发,深刻反思秦政之失,认为其根由在于秦始皇迷信法家的功利政治,并将其在实践上推向极端化,以致秦王朝缺失“民本”的正义性内涵,最终在纵欲残民、与民为仇中败亡。对秦始皇的暴政之失,《淮南子》试图让统治者深有借鉴,以此促使其在治国上民本为先、身国同治,延续清静无为、休养生息的汉初国策,推动西汉王朝实现“圣王”之治。
《淮南子》;秦始皇;法家;道家;儒家;民本
在西汉时期的“过秦”论中,关于秦始皇的政治认识及评价,始终是核心议题之一,为众多思想家所关注和探讨。虽然秦始皇“奋六世之余烈,振长策而御宇内,吞二周而亡诸侯,履至尊而制六合,执敲朴以鞭笞天下”[1]1963,在汉人看来,其继承先人遗业,攻灭六国,统一天下,最终建立秦王朝,这是前所未有的历史事件,但“至周末世,大为无道,以失天下。秦继其后,又益甚之。自古以来,未尝以乱济乱,大败天下如秦者也”[2]1032。汉人更认为秦始皇实乃秦王朝之暴政的始作俑者,“俗传秦始皇起罪恶,胡亥极,得其理矣”[1]293,因而对其普遍持批判和贬斥的政治态度。作为西汉前期“纪纲道德,经纬人事”[3]《要略》的思想巨著,《淮南子》对此也有着深刻反映。与其他思想家不同,《淮南子》论及“秦始皇”时,主要从黄老道家与儒家出发,尽管所言不多,但别具特色,有其精辟之处。由于《淮南子》为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所撰,成书于景、武之际,正值西汉王朝进入政治转型时期,所以在对“秦始皇”的批判中,《淮南子》不仅延续汉初的“过秦”主张,而且更为突显“言治乱之道,借秦为谕”[2]2327的反思意识,试图以“秦始皇”为鉴,促使统治者民本为先、身国同治,坚持休养生息的汉初国策,确保民众的现实生存与发展,以此夯实西汉王朝的“民本”根基,避免重蹈秦王朝的暴政覆辙,实现理想的“圣王”之治。
一、批判——《淮南子》论“秦始皇”的基本立场
作为“千古一帝”,秦始皇扫灭六国,统一天下,成为秦汉时期最具影响的专制君主,但其所创建的秦王朝,却并未能长久存在,而是在暴虐政治中,二世即亡,这使得秦始皇也成为西汉思想家深为批判和争议的历史人物。因秦王朝的统治,曾给广大士人及民众带来极大的现实灾难,所以汉人虽不抹杀秦始皇“蚕食天下,并吞战国,海内为一,功齐三代”[2]2799的政治功业,但从思想主流而言,却将其视为秦王朝暴政的始作俑者,认为“秦王置天下于法令刑罚,德泽亡一有,而怨毒盈于世,下憎恶之如仇雠,祸几及身,子孙诛绝”[2]2253,进行严厉批判,甚至彻底否定。这种政治认识与态度,在西汉前期的《淮南子》中,便有着显著表现。
淮南王刘安及其宾客,距离秦王朝的历史存在并不久远,对后者的残暴统治仍有切肤之感。故而《淮南子》在论及秦汉王朝之兴亡时,与汉初陆贾、贾谊、贾山等人一样,对“秦始皇”多有批判,认为秦王朝之所以速亡,在很大程度上,决定于秦始皇的治国理念及实践。正是秦始皇极欲好为、任法残民的政治局限,导致二世皇帝无法改弦易辙,最终在变本加厉的歧途上,促秦覆灭。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在不同的篇章中,对秦始皇展开多重批判,谴责其治国实践所具有的消极性,认为其虽然勤于为政,但所行偏差,终究难求良治。
其一,在社会经济上,《淮南子》认为秦始皇与民争利、罔顾民生,使得广大民众难以维持基本的生存和发展条件,致其走上变乱之路。
“夫民有余即让,不足则争,让则礼义生,争则暴乱起。”在《淮南子》看来,统治者只有积极发展社会经济,满足普通民众的生存需求,才能促其走向“礼义”之治,而非陷于“暴乱”之中,“故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3]《齐俗》。但秦始皇的治国实践却并非如此。“秦王之时,或人菹子,利不足也。”《淮南子》认为,始皇统治期间,好大喜功,穷兵黩武,非但无法实现“物丰则欲省,求澹则争止”的社会发展,反而造成“或人菹子”[3]《齐俗》的消极结果,这只能是“上好取而无量,下贪狼而无让,民贫苦而仇争,事力劳而无功,智诈萌兴,盗贼滋彰,上下相怨,号令不行”的“末世之政”[3]《主术》。事实上,始皇时期的这种虐民之政,不仅流毒其后,而且愈发剧烈。秦二世胡亥即位后,更是只知“纵耳目之欲,穷侈靡之变,不顾百姓之饥寒穷匮也。兴万乘之驾,而作阿房之宫,发闾左之戍,收太半之赋,百姓之随逮肆刑,挽辂首路死者,一旦不知千万之数”,以致“天下敖然若焦热,倾然若苦烈,上下不相宁,吏民不相憀”[3]《兵略》,终使秦王朝陷于土崩。对《淮南子》所言,汉代思想家也深有认同:“至于始皇,遂并天下,内兴功作,外攘夷狄,收泰半之赋,发闾左之戍。男子力耕不足粮饷,女子纺绩不足衣服。竭天下之资财以奉其政,犹未足以澹其欲也。海内愁怨,遂用溃畔。”[2]1126痛切批判秦始皇,斥责其使“贫民常衣牛马之衣,而食犬彘之食”[2]1137的暴虐之政。
其二,在政治用人上,《淮南子》认为秦始皇信用功利之臣,蔑弃利民德政,既无法真正获得广大民众的支持和拥护,也为秦王朝的二世而亡埋下隐患。
“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3]《人间》《淮南子》认为凡是历史上的贤良之臣,都深知“为政之本,务在于安民;安民之本,在于足用”[3]《诠言》的治国道理,能辅佐统治者施行利民之善政,从中获取人心,巩固王朝的统治根基,如“文王举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此举贤以立功也”[3]《泰族》。但是,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所用之臣,与此背道而驰。“秦任李斯、赵高而亡。”虽然李斯在秦汉历史上可谓“能臣”,甚至被汉高祖刘邦看作是“有善归主,有恶自与”的“忠臣”,但作为“千古一相”,“奋时务而要始皇”的李斯,在现实政治中“不务明政以补主上之缺”,只知“持爵禄之重,阿顺苟合,严威酷刑”[1]2563,加剧秦王朝的残民暴政。也正因其实乃重己之私的功利之臣,无法矫君之失,所以才会在始皇病故之际“听高邪说,废嫡立庶”,致使秦王朝积弊难返,沦于速亡。同李斯相比,赵高更是等而下之,不仅“以诈立胡亥”[2]2724,而且得势之后,“颛国主断”[2]1805,“以峻文决罪于内”,滥杀秦臣及宗室,严刑残民,造成“死者相枕席,刑者相望,百姓侧目重足,不寒而栗”[4]586的政治恶果,以致秦王朝后期“政治日乱,盗贼满山”[2]3162。由此,《淮南子》深刻指出:“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而“观其所举,而治乱可见也;察其党与,而贤不肖可论也。”[3]《泰族》言外之意,认为秦始皇的政治功业虽大,但根本上昧于王朝治乱之道,难成“圣主”贤君。“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秦始皇也因其所用之臣、所施之政,无法“布德施惠”于百姓,所以只能是积怨于民,难逃“兼吞天下而亡”[3]《人间》的悲惨结局。在此意义上,《淮南子》实际认为,始皇治国之失,首要在唯求功利,所用非贤。
其三,在现实战争上,《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兼并之行,并非正义之举,其穷兵黩武的战争所为,给广大民众造成严重灾难,乃至逼民而反。
“古之用兵者,非利土壤之广而贪金玉之略,将以存亡继绝,平天下之乱,而除万民之害也。”[3]《兵略》《淮南子》眼中的战争,必须具有内在的正义性,有利于民众和国家的现实发展,而非仅仅满足统治者的一己私欲。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时期的兼并战争,并不合乎“故兵者,所以讨暴,非所以为暴也”的战争原则,更缺少“用兵有术矣,而义为本”[3]《本经》的根本内涵,故秦王朝虽能经由剧烈的兼并战争而建立,但其“务广地侵壤,并兼无已”的不义性质,最终决定这样的战争实践不得人心,难以真正稳固王朝的统治基础。对秦王朝建立后,始皇发动的征匈奴、伐百越的对外战争,《淮南子》同样持批判态度。“秦皇挟录图,见其传曰:‘亡秦者,胡也。’因发卒五十万,使蒙公、杨翁子将,筑修城。西属流沙,北击辽水,东结朝鲜,中国内郡挽车而饷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齿、翡翠、珠玑,乃使尉屠睢发卒五十万,为五军……三年不解甲弛弩,使临禄无以转饷。又以卒凿渠而通粮道,以与越人战,杀西呕君译吁宋。而越人皆入丛薄中,与禽兽处,莫肯为秦虏。相置桀骏以为将,而夜攻秦人,大破之。杀尉屠睢,伏尸流血数十万,乃发谪戍以备之。”《淮南子》认为秦始皇这种出于贪欲、妄兴战事的政治行为,对已长期经历兼并战争的民众来说,无异于雪上加霜,使得“当此之时,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3]《人间》。正是在此极为严酷的生存条件下,始皇之黩武,最终迫使广大民众铤而走险,反抗和终结秦王朝的暴政统治,“于是陈胜起于大泽,奋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于戏。刘、项兴义兵随,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3]《人间》。《淮南子》认为,秦始皇因战而得天下,也由战而失天下。“欲知筑修城以备亡,不知筑修城之所以亡也。发谪戍以备越,而不知难之从中发也”,之所以如此,就在于“故秦之设备也,鸟鹊之智也”[3]《人间》。秦始皇根本不懂得战争所必需的正义性,好战伤民,毫无悯民意识,以致于“知备远难而忘近患”,丧尽民心,以战亡秦。
其四,在法治实践上,《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罔顾法度之义,只知严刑酷法以残民,极端推行法家的任“法”治国理念,酿成刑虐政乱的消极局面。
“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3]《主术》《淮南子》坚持认为,法律的制定与施行都应利于民众,合乎道义,而非相反。“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何者?力不足也。”[3]《齐俗》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的法治实践即是如此。“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3]《修务》秦始皇虽然勤于“决狱”,但事实上秦王朝的严苛法网,并未使其趋于稳定发展,相反却是“妄赏以随喜意,妄诛以快怒心,法令烦憯,刑罚暴酷,轻绝人命,身自射杀;天下寒心,莫安其处。奸邪之吏,乘其乱法,以成其威,狱官主断,生杀自恣。上下瓦解,各自为制”[2]2297。正如《淮南子》所言:“事愈烦而乱愈生。”基于此,《淮南子》明确指出:“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以为治也”,认为“位高者事不可以烦,民众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难治也,法烦难行也,求多难澹也”,进而强调:“故有道以统之,法虽少,足以化矣;无道以行之,法虽众,足以乱矣”[3]《泰族》。从中可见,《淮南子》对秦始皇的法治实践的局限性,实际上有着深刻的政治反思,理性认识到:“法之生也,以辅仁义,今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3]《泰族》
概言之,与汉初思想家一致,《淮南子》并未过多肯定“秦始皇”的政治功业,而是“主要围绕秦亡汉兴的历史经验教训”,展开对其治国局限的多重反思,显示出“浓烈的批判性”[5]662。对《淮南子》而言,不论在社会经济、政治用人上,抑或在现实战争、法治实践上,秦始皇都严重背离“治国有常,而利民为本”[3]《氾论》的根本原则,这促使秦王朝无法“布德施惠”于百姓,只能在残民暴政中愈行愈远,多行不义而自毙。若就此而论,秦始皇及其后继者,都可谓是“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的“贪主暴君”[3]《主术》。
二、反思——《淮南子》论“秦始皇”的政治理性
《淮南子》对“秦始皇”的多重批判,并非仅止于始皇之政的现实表象,而是着眼于王朝兴衰规律,深入反思其产生的治乱根由。《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政治实践,其失不在于治国用“法”,而在于奉行极端功利化的法家思想,及由此而生的迷信严刑峻法的暴力统治。这种法家治国路线,虽然基于“贪狼强力,寡义而趋利。可威以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劝以赏,而不可厉以名”的“秦国之俗”,从秦孝公以来便成为秦国的政治传统。“孝公欲以虎狼之势而吞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3]《要略》,且曾让秦国深受其益,“商鞅相孝公,为秦开帝业”[6]1153,促成日后秦始皇兼灭六国、统一天下的政治功业。但是,由于其唯功利是从,严重缺失“民本”内涵,致使秦王朝产生“以任刀笔之吏,争以亟疾苛察相高,其敝徒文具,亡恻隐之实”[2]2308的现实弊端,丧失其长久存在的正义性基础。因此,《淮南子》在论及“秦始皇”时,立足黄老道家,兼涉儒家,从治术、治道与君道三个方面,深刻反思其法家治国实践,批判始皇之政的内在局限性。
第一,治术反思。《淮南子》虽然肯定“法”作为“治术”所具有的治国效用,但坚决反对秦始皇将其过度功利化的政治实践,而是更为重视“法”的内蕴的正义性。法家主张:“国之所以治者三:一曰法,二曰信,三曰权”[7]82,“治国之有法术赏罚,犹若陆行之有犀车良马也,水行之有轻舟便楫也,乘之者遂得其成”[8]105。与之相同,《淮南子》也认为:“法者,天下之度量,而人主之准绳也”[3]《主术》,“故法制礼义者,治人之具也”[3]《氾论》,将“法”视为统治者治国理政的重要手段之一。但与前者相异,鉴于秦王朝以刑、法残民的历史教训,《淮南子》尤为强调:“法生于义,义生于众适,众适合于人心,此治之要也”[3]《主术》,突显以“义”制法的重要性,反对统治者滥用无“义”之法。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治国之“法”,其工具性已被极端的功利化,而其内在的正义性却严重萎缩,这使得始皇之“法”在工具性和正义性上彻底失衡,故而其现实效用虽能有所发挥,但却表现为惨酷少恩的法治实践,难以真正“适合于人心”,以致最终的消极性远甚于积极性。“夫峭法刻诛者,非霸王之业也;箠策繁用者,非致远之术也。”[3]《原道》《淮南子》认为,正是秦始皇的任“法”之失,根本上决定秦王朝之命运,其“法”虽能逞欲一时,但终难持久,绝非理想的治术。
第二,治道反思。“法”作为一种治国手段,在秦王朝的现实发展中,其消极性虽大,但毕竟有限,更为重要的是,作为一种治国模式的法家理念,事实上对秦王朝的政治兴衰产生决定作用。对始皇之政的深刻批判,《淮南子》不仅着眼于秦法在“治术”上的工具化歧误,而且从黄老和儒家出发,反思法家“治道”的根本局限性。秉持黄老立场,对秦始皇所遵奉的法家治国理念,《淮南子》痛加斥责和否定:“今若夫申、韩、商鞅之为治也,挬拔其根,芜弃其本,而不穷究其所由生,何以至此也。凿五刑,为刻削,乃背道德之本,而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而忻忻然常自以为治,是犹抱薪而救火,凿窦而出水。”[3]《览冥》《淮南子》认为,法家化“治道”存在着致命弊端,即:“凿五刑,为刻削”,“争于锥刀之末,斩艾百姓,殚尽太半”,完全溺于法本民末、刑重义轻的政治泥淖,极度缺乏应有的“民本”内涵及精神。在其看来,这种法家化“治道”对民众和王朝的现实发展,实际上都是弊大于利,有不如无,“若夫墨、杨、申、商之于治道,犹盖之无一橑,而轮之无一辐。有之可以备数,无之未有害于用也;己自以为独擅之,不通之于天地之情也”[3]《原道》。
受儒家思想影响,《淮南子》也认为:“故仁义者,为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并指出:“赵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3]《泰族》。《淮南子》强调,秦始皇所奉行的法家化“治道”,因其缺乏仁义、德政内涵,所以无法让秦王朝获取民心,长治久安。“水浊者鱼噞,令苛者民乱。”《淮南子》认为战国以来的秦政治已历史证明:统治者施行极端功利化的法家苛政,其结果必然适得其反,既有害于其自身,更无益于国家发展,“故商鞅立法而支解,吴起刻削而车裂”[3]《缪称》,“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3]《人间》。究其根由,便在于法家化“治道”实乃“物化的治道”,在政治上“认事不认人,认法不认人”,只“向着客观方面的共同事物之领域用心,而不向主观方面的个体(个人人格)用心”[9]36-41,严重轻忽广大民众的政治主体性,蔑视其对王朝发展所具有的决定作用,由此“刚毅戾深,事皆决於法,刻削毋仁恩和义”[1]238,走上任法滥刑的暴政歧途。正是基于以上的“治道”反思,《淮南子》明确指出:“今商鞅之启塞,申子之三符,韩非之孤愤,张仪、苏秦之从衡,皆掇取之权,一切之术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恒常,可博闻而世传者也”[3]《泰族》,将秦始皇所信奉的法家化“治道”,贬低为工具层次的“权”、“术”,指斥其并非“治之大本”。
第三,君道反思。“人主之术,处无为之事,而行不言之教。清静而不动,一度而不摇,因循而任下,责成而不劳。”[3]《主术》《淮南子》作为道家论著,在政治上反对统治者事必躬亲、有为而治,主张统治者应“漠然无为,而无不为也;澹然无治也,而无不治也”[3]《原道》,在政治上始终处于主动地位,能善于“听治”。“夫人主之听治也,虚心而弱志,清明而不暗。是故群臣辐凑并进,无愚智贤不肖,莫不尽其能者,则君得所以制臣,臣得所以事君,治国之道明矣。”[3]《主术》《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实践上只需明察善听、因循任下,便能让群臣各司其职、自负其责,而不必事无巨细、强力有为。因此,“厌文搔法,治官理民者,有司也,君无事焉,犹尊君也”[3]《诠言》,统治者应“无事”而自尊,不越俎代庖,干涉臣职。《淮南子》强调:“君臣异道则治,同道则乱。各得其宜,处其当,则上下有以相使也”[3]《主术》,但在其看来,秦始皇的治国实践恰恰与此相反。秦始皇并不懂得“立事者,贱者劳而贵者逸”[3]《泰族》的为君之道,在政治上权力欲惊人,“天下之事无小大皆决於上,上至以衡石量书日夜有呈,不中呈,不得休息”[1]258,凡事都要躬亲独断。对此,《淮南子》深为批判:“赵政昼决狱而夜理书,御史冠盖接于郡县,覆稽趋留,戍五岭以备越,筑修城以守胡,然奸邪萌生,盗贼群居,事愈烦而乱愈生。”认为始皇为君,虽勤于政事,但根本上昧于君道,无益于治。“人无为则治,有为则伤。”[3]《说山》在《淮南子》看来,秦始皇的法家治国实践,急于力治,功利太甚,其结果必然是“执政有司,不务反道矫拂其本,而事修其末,削薄其德,曾累其刑,而欲以为治,无以异于执弹而来鸟,捭棁而狎犬也。乱乃逾甚”[3]《主术》。显而易见,对秦始皇的这种君道反思,《淮南子》受到汉初陆贾的思想影响。后者就曾深切指出:“秦始皇设刑罚,为车裂之诛,以敛奸邪,筑长城于戎境,以备胡、越,征大吞小,威震天下,将帅横行,以服外国,蒙恬讨乱于外,李斯治法于内,事逾烦天下逾乱,法逾滋而天下逾炽,兵马益设而敌人逾多。秦非不欲治也,然失之者,乃举措太众、刑罚太极故也。”[10]71
利用张航等人研究的量子行为粒子群优化(Quantum PSO, QPSO)算法对微型飞行器进行三维路径规划[2],首先将三维坐标数据通过坐标变换和离散有限平面的方法化简为一维数据,然后建立新地图和粒子适应度函数,适应度函数决定了静态和动态壁障的适应值,最后通过QPSO算法获得一条全局最优路径,对UAV+RFID数据模型进行计算可以得到一条S到F点的最优路径,其中L2的长度为88.82。仿真结果如图6所示。
要之,对“秦始皇”及其治国实践,《淮南子》从黄老、儒家出发,不仅是严厉批判,更是深刻反思。这种反思同样具有多重的政治内涵,既涉及具体的“治术”、“君道”,也关系根本的“治道”,在很大程度上,充分反映出《淮南子》对“秦始皇”的特殊重视,以及对其治国之失深为借鉴的强烈意识。
三、镜鉴——《淮南子》论“秦始皇”的现实诉求
毋庸置疑,在《淮南子》眼中,秦始皇难以被称之为贤明之君,更无法被视为“圣王”楷模,相反,在很大程度上,《淮南子》实际将其视为“贪主暴君”、“无义之君”的历史典型。究其因由,便在于始皇之政既非《淮南子》所追求的道家“无为”之治,也非其有所肯定的儒家“仁义”之治,而是法家极端化的功利政治。“地以德广,君以德尊,上也;地以义广,君以义尊,次也;地以强广,君以强尊,下也。”[3]《缪称》《淮南子》认为秦始皇这种法家治国实践,根本上缺失“民本”内涵及精神,无法实现“安民”、“养民”的良好景象,只能是残民以法、虐民以暴,使广大民众陷于生存窘境。因此,《淮南子》对秦始皇及其治国实践进行深刻反思,试图促使统治者在治国上,深入镜鉴其民本之失、任法之失、用人之失和治身之失,以此推动西汉王朝良性发展,实现“圣王”之治。
首先,《淮南子》反对秦始皇崇尚功利的法家实践,主张西汉统治者应鉴其“民本”之失,在治国上“德”、“义”为重,夯实王朝的政治基础。
“秦王赵政兼吞天下而亡,智伯侵地而灭,商鞅支解,李斯车裂。三代种德而王,齐桓继绝而霸。故树黍者不获稷,树怨者无报德。”《淮南子》认为秦王朝的政治命运是“树怨者无报德”的必然结果,为君者如秦始皇,为臣者如商鞅、李斯,在治国实践上都是醉心兼并,任法残民,而无法“足本”以“安民”,让民众得以正常的生存和发展。“故乱国之君,务广其地而不务仁义,务高其位而不务道德。是释其所以存,而造其所以亡也。”[3]《诠言》《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法家治国实践,即是如此。正因“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当此之时,忠谏者谓之不祥,而道仁义者谓之狂”,最终促发“戍卒陈胜,兴于大泽,攘臂袒右,称为大楚,而天下响应”[3]《氾论》的农民大起义,导致秦王朝在始皇暴政的历史延续中自取灭亡。对秦王朝这种悲剧性的政治发展,《淮南子》立足黄老,深刻指出:“国之所以存者,道德也”,“存在得道,而不在于大也;亡在失道,而不在于小也”[3]《氾论》,贬斥秦始皇的功利政治。《淮南子》还着眼儒家,认为秦之失天下,也因其无“义”,故而“逮至高皇帝存亡继绝,举天下之大义,身自奋袂执锐,以为百姓请命于皇天”[3]《氾论》,西汉王朝能取秦而代之。可见,“国之所以存者,仁义是也”,“国无义,虽大必亡”[3]《主术》。在《淮南子》看来,“所谓有天下者,非谓其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也,言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3]《泰族》,秦始皇却与此相反,其虽能“履势位,受传籍,称尊号”,但在治国上却无法“运天下之力,而得天下之心”,最终同桀纣、楚灵王一样,在“外内搔动,百姓罢敝”中身丧国亡。因此,《淮南子》认为西汉统治者应以始皇为鉴,始终不忘秦政的“民本”之失,在“得民之与失民也”[3]《修务》中选择前者,夯实王朝统治所需的正义性基础,推动其走向良政善治。
“世治则小人守政,而利不能诱也;世乱则君子为奸,而法弗能禁也。”[3]《齐俗》《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在政治上不应片面强调“法”之施用,而是要着力发展社会经济,改善民众日常生活所需的物质条件,从根本上确保其能良善而“守政”,不“为奸”而犯法。始皇之政却极力于兼并,唯君欲是从,造成“或人菹子,利不足也”的消极结果,在此情势下,秦始皇非但不改弦易辙,兴民所利,反而用“法”日益深刻,严酷压制民众,最终以“商鞅之法亡秦”,其自身也因“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灭”。对秦始皇的用“法”之失,《淮南子》与陆贾、贾谊和晁错等人一样,都深为痛斥,认为这种法治实践无“义”可言,只是“察于刀笔之迹,而不知治乱之本也”。在《淮南子》看来,“治之所以为本者,仁义也;所以为末者,法度也”,因此“法之生也,以辅仁义”[3]《泰族》,而始皇之“法”却与之相悖,“重法而弃义,是贵其冠履而忘其头足也”,其结果必然是“不益其厚而张其广者毁,不广其基而增其高者覆”[3]《泰族》。“乱世之法,高为量而罪不及,重为任而罚不胜,危为禁而诛不敢。民困于三责,则饰智而诈上,犯邪而干免。故虽峭法严刑,不能禁其奸。”[3]《缪称》通过反思秦始皇在治国上的用“法”之弊,《淮南子》明确主张:“民不知礼义,法弗能正也;非崇善废丑,不向礼义。无法不可以为治也;不知礼义,不可以行法”[3]《泰族》,“府吏守法,君子制义,法而无义,亦府吏也,不足以为政”[3]《主术》,试图警醒西汉统治者,促其鉴秦之失,能在政治发展中教化为先、以“义”制法,充实“法”的正义内涵,做到“法令察而不苛”,发挥其有利于民众生存、国家发展的积极性。
再次,《淮南子》反对秦始皇以“功利”择臣,主张西汉统治者应鉴其用人之失,在政治上任人唯贤,推行利民善政,实现王朝的良好发展。
虽然《淮南子》中也有非贤之语,但一般而言,从治国出发,《淮南子》还是主张统治者能选贤而治,认为:“得其人则举,失其人则废”[3]《泰族》,“所任者得其人,则国家治,上下和,群臣亲,百姓附。所任非其人,则国家危,上下乖,群臣怨,百姓乱”,强调“人主之一举也,不可不慎也”[3]《主术》。在政治用人上,《淮南子》把“秦始皇”作为反面事例,痛切指出:“秦任李斯、赵高而亡。”在其看来,“故圣主者举贤以立功,不肖主举其所与同”,而秦始皇的用人实践便属于后者。李斯、赵高之辈,不可谓不“能”,但绝非“贤”臣,因为“忠臣者务崇君之德,谄臣者务广君之地”[3]《人间》。在李斯、赵高这种功利之臣的辅佐下,秦始皇虽能并六国、一天下,但却造成“男子不得修农亩,妇人不得剡麻考缕,羸弱服格于道,大夫箕会于衢,病者不得养,死者不得葬”的悲惨景象,使民众生存无依、苦不堪言,最终让秦王朝难逃“与民为仇”的覆灭结局。因此,在《淮南子》看来,秦政之败,首要在用人之失。“知人则无乱政矣”,鉴于秦始皇在用人上的历史教训,《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应擢用“兴治之臣”,推行“兴民之利”的仁治德政,实现西汉王朝君明臣贤、百姓拥护的良好局面。
最后,《淮南子》反对秦始皇的好大喜功、纵欲虐民,主张西汉统治者应鉴其治身之失,能节嗜欲、施善政,在身国同治中实现“圣王”之治。
《淮南子》认为,如若统治者“一日而有天下之富,处人主之势,则竭百姓之力,以奉耳目之欲,志专在于宫室台榭,陂池苑囿,猛兽熊罴,玩好珍怪”,那么现实政治必然出现“贫民糟糠不接于口,而虎狼熊罴厌刍豢;百姓短褐不完,而宫室衣锦绣”[3]《主术》的消极局面。因此,《淮南子》在政治上反对“人主急兹无用之功”,而是主张:“人主租敛于民也。必先计岁收,量民积聚,知饥馑有余不足之数,然后取车舆衣食供养其欲。”[3]《主术》就现实政治而言,《淮南子》认为,统治者如为“仁君明王”,则能“取下有节,自养有度,则得承受于天地,而不离饥寒之患矣”;反之,统治者若是“贪主暴君”,则必然“挠于其下,侵渔其民,以适无穷之欲”。“秦之时,高为台榭,大为苑囿,远为驰道,铸金人,发适戍,入刍槁,头会箕赋,输于少府。丁壮丈夫,西至临洮、狄道,东至会稽、浮石;南至豫章、桂林,北至飞狐、阳原,道路死人以沟量。”在《淮南子》看来,毋庸置疑,秦始皇的治国实践当属后者。事实上,不论任法黩武,抑或纵欲侈靡,秦始皇在秦汉时期都罕有其匹,归根结底,皆因其贪权多欲、懈于治身所致,而这与《淮南子》所言“古之立帝王者,非以奉养其欲也;圣人践位者,非以逸乐其身也”[3]《修务》,大相径庭。基于这种认识,《淮南子》深刻指出:“有以欲多而亡者,未有以无欲而危者也”[3]《诠言》,“省事之本,在于节欲;节欲之本,在于反性”[3]《泰族》,试图让西汉统治者对秦始皇的治身之失有所警戒,践行身治为先、身国同治的根本原则,在“自养得其节,则养民得其心矣”[3]《修务》中成为“圣王”,推动王朝政治更加合理化,走向理想之善治。
综上所述,对秦始皇及其治国实践,《淮南子》的认识深刻独到。在其眼中,秦始皇实难称之为“仁君明主”,更遑论“圣王”,只可谓为“贪主暴君”、“无义之君”。之所以如此,皆因始皇之政的内在弊端和局限性所决定。“国主之有民也,犹城之有基,木之有根。根深则本固,基美则上宁。”[3]《泰族》《淮南子》认为秦始皇的治国实践,完全背此而行。受法家极端功利化的治国理念影响,始皇之政严重缺失“民本”内涵,因此不论是具体的“治术”、“君道”,还是根本的“治道”,都无法彰显出“防民之所害,开民之所利”[3]《主术》的合理取向。秦始皇这种治国实践的严重局限,不仅成为导致秦王朝速亡的根由所在,而且使其自身成为汉人眼中的“暴君”典型,甚至被日益的政治符号化[5]658-672,转换成以《淮南子》为代表的汉代政论著作批判王朝暴政、反思君主政治的重要历史资源。在很大程度上,对《淮南子》而言,批判始皇之政,也内显出其对西汉王朝代秦而立的合法性的积极肯定;而深思始皇之失,则寄托着其对西汉统治者的政治警戒与期许,以及对西汉王朝实现“圣王”之治的理想追求。
[1] [西汉]司马迁.史记[M].北京:中华书局,1959.
[2] [东汉]班固.汉书[M].北京:中华书局,1962.
[3] 何宁.淮南子集释[M].北京:中华书局,1998.
[4] 王利器.盐铁论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1992.
[5] 张分田.秦始皇传[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3.
[6] 黄晖.论衡校释(附刘盼遂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0.
[7] 蒋礼鸿.商君书锥指[M].北京:中华书局,1986.
[8] [清]王先慎.韩非子集解[M].北京:中华书局,1998.
[9] 牟宗三.政道与治道[M].长春:吉林出版集团有限责任公司,2010.
[10] 王利器.新语校注[M].北京:中华书局,2012.
(责任编辑:高士荣)
Comment on Qin Shi Huang inHuaiNanZi
GAOXu
(1.Anhui University of Science and Technology,Huainan 232001, China;2.Nankai University,Tianjin 300071,China)
The political practice of Qin Shi Huang was criticises inHuaiNanZifor many times from social econmy, the talent of chooseing and using, mergers war and the rule of law practice. Based on Taoism and Confucianism point of view,HuaiNanZireflects the disadvantages and limitations of Qin Shi Huang’s political practice which includes the means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the wisdom of governing the country and leadership principle of the monarch.HuaiNanZithinks Qin Shi Huang despises the power of people and maintains the cruel rule abide by Legalism’s utilitarian thought so that Qin dynasty quickly come to perish. In order to achieve Han dynasty’s prosperity,HuaiNanZitries to urge the ruler of Han dynasty to draw and learn lessons of Qin Shi Huang.
HuaiNanZi; Qin Shi Huang; Legalism; Taoism; Confucianism; people-oriented thoughts
2014-09-18
安徽省教育厅人文社会科学一般项目“《淮南子》与法家思想研究”(2011SK142);安徽省社科联项目“《淮南子》与其成书背景的互动研究”(B2012001)
高旭(1979-),男,陕西延安人,安徽理工大学楚淮文化研究所所长,人文社科学院讲师,南开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生,研究方向为中国思想史。
K233
A
1672-2817(2015)01-0092-0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