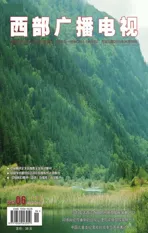90年代中国的法制题材电影探究
2015-02-27彭瑾
彭 瑾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90年代中国的法制题材电影探究
彭 瑾
(作者单位:贵州师范大学文学院)
上世纪80年代是法制电影宣告诞生的时期,由于改革开放与政策破冰的影响,一系列罗列法律事件、折射社会原貌的电影纷纷在这一时期问世:《法庭内外》(1980年)、《检察官》(1980年)、《第十个弹孔》(1980年)、《见习律师》(1982年)、《被控告的人》(1983年)、《少年犯》(1985年)等。它们被电影理论工作者命名为“法制片”。经历了80年代的探索期后,上世纪90年代初,中国的法制电影走入了多转型期。这一时期的法制题材代表电影有严浩的《天国逆子》、范元的《被告山杠爷》和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
《天国逆子》是香港著名导演严浩根据张成功小说《苦海中的泅渡》改编的法制题材电影。这是一个背负着法与情冲突的“母子”故事:在中国东北农村,男子关健在长大后多年,凭着记忆中的片段,向公安机关检举了亲生母亲蒲凤英曾杀死她的丈夫、关健的父亲。这是一个对传统儒家孝道文化挑战并反思的作品,也是对传统文化本质性的一次发问。因其透出的深刻人性与“法”“情”交织间的人性窥探,严浩在1994年东京国际电影节上获得了最佳导演奖。
片中一对母子关健和蒲凤英正是站在“法”与“情”天平两端的人。关健为了替生父讨回被杀的公道,在成长路上一直自学法律知识,并通过法律手段揭开真相。作为儿子,他同时爱着双亲,当母亲背叛父亲时,他从一个孩子与一个男人的角度选择了怀疑母亲、暗恨母亲背叛的叛逆者,进而演化为把母亲送进死囚房的道德“背叛者”。
关健的复仇武器是“法律的公正”,从人物出场的检举,到艰难求证的经过,到查不出证据后的情感转变,再到结局时的决裂,法律的理性一直是支撑其前进的动力。然则,他的行为是为维持法律的理性与公正吗?法律之于关健,与其说是正义,不如说是达成目的的手段。他不断追寻父亲死亡的真相,不惜对抗传统乡土社会的桎梏也要对抗母亲,抛弃家庭,做出开棺验尸的行为,实质却是在用法律的方式发泄童年伤害与拷问母亲心灵——在电影文本未直接告诉观众的真实层面里,关健一直不能容忍母亲为了追寻自己幸福坚定抵抗着传统社会对不平等夫妻关系的痛恨,即使母亲在与父亲的夫妻生活中始终扮演被侮辱与被损害的弱者。
因此,当法律作为理性与希望的象征支撑着关健支离破碎之心时,母子之情让他陷入煎熬,关健无数次追问母亲试图丢掉心理包袱。歌厅一夜,是他最大的真情流露,结局处他丢弃了母亲行刑前为他织的毛衣,想借此丢掉道德巨石,但弑母的悲剧无法随着毛衣一起丢弃,将永远压在自己心头。
以“情”主宰行为的母亲蒲凤英则是站在法律对面,被情欲与环境桎梏的女性形象。她是90年代乡土社会女性在父权、男权社会面前的无从抵抗的缩影。法律之于蒲凤英,只是“男人的武器”而非“理性的天平”。她不知道如何运用法律武器改变命运,只能靠杀死丈夫,飞蛾扑火地扑向情夫,又被情夫凶狠对待。杀夫改嫁后,她被同样代表男权社会话语权的儿子用法律送进天堂。法律在蒲凤英身上,一面主宰公平正义,一面微妙地成为男权社会摧毁女性的武器。
但严浩并没有因为蒲凤英处境的悲剧性与关健弑母的命运感而失去判断,《天国逆子》里,立场和情怀并无偏颇,每个人都有自己的不得已,但是情与法之间该有的天地正义应当遵守。法的正义宣判了应有的惩罚,情的纠葛也因为法的正义得以深沉。面对法与情,面对一切不得已,导演敢于直面,客观叙述,留有余地,又不阻碍叙事本身的动人心肠。
不过,《天国逆子》虽然拍了东北题材,其立场平衡却也跟严浩本身是香港导演有关。由于文化背景的不同,香港电影中的法制观、正义观和可涉及的层面与内地差别不少,许多大陆电影为了表现情而避重就轻之处,在香港电影里,则更理性地得以表现。
这种差别体现在了《被告山杠爷》中。《被告山杠爷》对传统与现代、人治与法治、农民与农村干部等关系进行了探讨、反思,这种反思却由于导演价值观而影响了影片本该传递的客观真相,成功的把“法”的问题转移重点到“情”上。
《被告山杠爷》中的堆堆坪是90年代中国真实乡村的缩影。法制的力量在这片土地上是一个遥远的名词,作用力微乎其微,几近于触不可及。乡村干部的公共形象是苦苦挣扎的,他们穷于应付中央和乡村社会的种种压力。
山杠爷是范元塑造的新中国电影史上经典形象:一个集合了可敬与可悲的典型农村基层干部形象。他靠着自身的清廉、处事的公正和公信力构建了一个非正式的法律制度。在他的带领下,堆堆坪兴修设施,治安太平,年年拿锦旗,人人心中都敬着山杠爷。村民信服他,因其动机在于为群众谋福利,并一直以身作则。由于他的决策,村庄在事实上完成了脱贫。
但山杠爷也是专制的。90年代的中国农村偏远地区与城市相互隔离,经济交通都不发达。法律法制维护着城市的环境,却难以渗透乡村和偏远地区。中国的农村社会是乡土性的,乡土性源于地域上的天然隔离和人口的静止,在当时,一定程度上加大了信息沟通的难度。
由于中国当时的环境下,当时的劳动人民靠着领袖与不成文的民间规则,传统道德和旧习俗在静止、孤立的社会中得以维持秩序和传承。
显然,山杠爷便是个“独裁领袖”,法律的公正仗着他自身的人格而维持。在他的独裁下,作为独立个体的村民人格在不符合乡规时,都成为了独裁下的牺牲品:私拆信件、关押村民、当众侮辱、捆绑游街……人们在“杠爷是为了大家好”的前提下予以默认和支持。
这些行为意在惩戒,本质上却是对独立人格和精神的践踏。本应被法律制裁者最终被道德观制裁。强英的自杀是这一行为的体现,她的死,让法律的公正真正意义上介入了山村,最终使山杠爷被法律制裁。
但影片至始至终,导演是同情山杠爷
的,影片表现出法与情难两全时,导演用煽情转移视线,营造了山杠爷的正面形象:村民和乡公安对他毕恭毕敬、结局处还全村百姓泪送山杠爷。与此同时,导演还设置了一位现代法治的代表人物——女检察官:一个从头到尾被闲置的符号化角色。女检察官在电影中的戏份除了机械重复法律禁令外,就是不断听村民们对山杠爷发自内心的颂扬。法律在电影中已不是重点。
影片的偏颇就像一种不自觉的斯德哥尔摩综合症。这不仅是导演本身的局限,也是当时中国社会普法情况的一个缩影。
张艺谋的《秋菊打官司》则讲述了一个发生于转型期现代农村的故事。秋菊丈夫万庆来与村长的矛盾源于一次“下辈子断子绝孙,还抱一窝母鸡”的口角。子嗣是农村成年男性延续香火、维持面子的根本。面子是中国传统农业文明时代,出现在民众之中的一种判别个人社会身份与被群体认可度的一个关键指数。对无子的村长而言,庆来的怒骂挑动了村长根植于农村的封建意识心态:男尊女卑。
秋菊的漫漫上告路是法制与人情二律悖反的缩影,也昭示着现代文明侵蚀下,90年代农民为逐步摆脱传统小农社会宗族等级制度束缚、追求自由平等的渴求。作为转型期新一代农民的代表,秋菊承袭了传统文化合理与不合理成分,又被植入了现代法律法制意识。她的行为本质是农村道德纠葛,但其不自觉采取的行为却趋向了现代法律手段。
对于秋菊不停打官司的行为,传统文化社会居民保持着反对态度。从村民,到秋菊丈夫,甚至到城市里法院的各种人物,对于秋菊都抱着围观、反对的心态。为了加强这一表达,张艺谋还设置了等待法院宣判的过程中,村长带人把大肚子秋菊连夜抬往医院助其生下儿子一场,让问题的核心从面子和儿子上得到解决。
所有矛盾向着皆大欢喜迈进之时,法院却带给了秋菊意料之外的判决,一切恩怨化为镜花水月。
法律制度和乡土社会规则之间的冲突体现了现代法治的成本,秋菊一次次从传统和人情的起点出发,向法制所在的城市探索、询问,最终徒劳回到起点的历程,是当代农村一个巨大的表意符码。张艺谋叙述了中国农民深受转型期文化困扰的心理状态,揭示了秋菊行为并不是彻底的法制行为,是对令人困惑的法制与人情二律悖反的话语陈述,并由此揭示由传统文化过度法制指称的现代文明转型的困难。
通过《被告山杠爷》和《秋菊打官司》这类经典电影,我们可以看到不同时期我国农民对法制的了解及变化,也在这类电影中明白成熟的法治社会的对维护社会的平衡与健康运转起着根本性的作用,作为影视从业人员,唯有不断挖掘生活中的法制精神,让其客观公正地融入到影片中,才能让法制电影得到更好的发展,让观众在观影中不断了解和学习法治文化。
参考文献:
[1]谈大正,沈栖.中外法制电影赏[M].上海:上海科学技术文献出版社,1991:1-2.
[2]苏国勋.理性化及其限制.韦伯思想引论[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8.
[3]李显杰.电影叙事学:理论和实例[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1990.
[4]马尔丹.电影语言[M].北京:中国电影出版社,200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