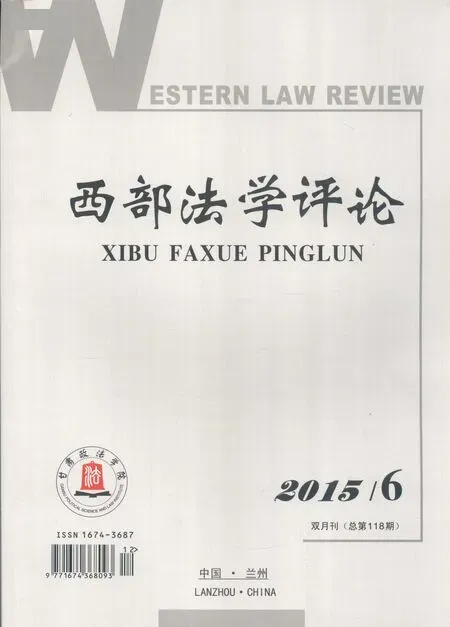《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2015-02-27田勇军
田勇军
《行政诉讼法》中“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之理论分析
田勇军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制度并没有随着其被明确写入我国 《行政诉讼法》而终止人们的争议。出庭应诉行为属于权利之性质决定了其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诉权平等原则要求对于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法院应该是保护而不是限制;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决定了其对行政权的监督要有边界,不能审查行政内部的日常自我管理行为;当前我国司法实践中,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仍面临诸多困境。不能以暂时的效果来评价制度的合理与否,不能将行政机关首长负责制之管理方式等同于凡事必须负责人亲躬。行政诉讼法对于诉讼参与双方的平衡是通过有针对性的对诉讼地位以及举证规则的调整,而不是程序性的权利义务之不对等。
起诉权 诉讼权利 诉讼地位平等 内部管理行为
引言
近年来,在我国 “民告官”类案件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并非是一个新话题。自从2004年国务院 《全面推进依法行政实施纲要》第28条要求行政机关在行政诉讼中要积极应诉、答辩以来,理论及实务界一直就该措施争议不断,盖基本观点有二:一种认为,该制度的合法性、合理性和必要性值得商榷,〔1〕参见汪成红:《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的合法性审视》,载 《江南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2007年第6期;徐健:《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实践与反思》,载 《长沙铁道学院学报》(社会科学版)2011年第4期;吕尚敏:《行政首长应当出庭应诉吗?》,载 《行政法学研究》2009年第4期。要客观、冷静地对待。另一种观点则是积极、乐观地支持建立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2〕参见黄学贤:《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机理分析与机制构建》,载 《法治研究》,2012年第10期;章志远:《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载 《法学杂志》2013年第03期;江必新:《积极推进行政机关负责人行政诉讼出庭应诉工作》,载《人民法院报》2011年7月13日第5版。当前,后一种观点成为主流。在司法实践中,则几乎是一边倒地积极倡导、宣传和力推之,而且该制度在此前实践中的效果也不错。2014年11月通过的《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以下简称 《行政诉讼法》)修订案,对这项在实践中已广为探索的 “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做了明确的规定。即 “被诉行政机关负责人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力图通过该项制度,改变行政诉讼面临的一些困境,并进一步推动当前的司法改革。实践中,各地实施的方式也千秋各异,如党委发文、政府自我规范、法院设定内部实施细则等,也有党委、政府和法院联合推行的,更多的是没有通过规范性文件,而是在实践中探索自己的方法,例如,有些法院在向被告行政主体送达起诉书时一并送达首长应诉通知,有些法院通过向行政主体提出司法建议形式,有些法院甚至规定,行政首长不应诉就不开庭〔3〕这是笔者在参加贵州全省九个市州中级法院的行政庭庭长座谈会时,有部分法官介绍自己的成功经验之一。等。这些措施被称为当前建设法治社会,推动司法改革的 “抓手”、“助推器”、“牛鼻子”。但是,由于法律规定过于笼统,如没有对负责人 “应当”出庭之 “应当”的标准或条件予以明确化,也没有对 “不能出庭的”之具体情况予以规定。因此,在现实中,很多法院是在 “摸着石头过河”、“跟着感觉走”。法院在其中应该扮演何种角色,其如何把握对该制度推行的力度和尺度?可否直接处分违法者,或是须依靠行政机关?这些问题尚没有满意的答案。故,写入法律并非是理论研究的使命已经完成,缺乏坚实理论支撑的制度犹如失去指引航标的航船。早期没有对该理论进行更为深入的分析,司法实践促使我们必须回头补课,对该制度中的一些根本理论问题进行分析和梳理,以便从根本上找到符合法治理念及法的逻辑的解决之道。
一、出庭应诉行为属于 (诉讼)权利——具有可自由处分属性
要判断司法权是否应当审查行政主体之选派出庭应诉人员事项,首先要明确该事项的 (权利或义务)属性,即其究竟是属于被诉行政主体的一项诉讼权利,还是必须履行的义务。如果是前者,则基于权利的可处分性当然要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如果是后者,方有必要进一步探究司法审查的深度,司法审查不能限制诉讼当事人的权利。
从法律的角度来看,社会主体之间的关系可以简化为权利和义务关系,但对于权利义务的准确定义是一件让人大伤脑筋的事情。费因伯格认为,给权利下一个 “正规的定义”是不可能的,应该把权利看作一个 “简单的、不可定义、不可分析的原初概念”,〔4〕JodFeniberg:“The Nature and values of Rights”,journal of Vaule Inquiry,4(1970),pp.243一244.但基于理论研究的需要还必须定义之。有人认为 “权利是为道德、法律或习俗所认定为正当的利益、主张、资格、力量或自由”,这其实是对权利属性的综合。基于不同的价值取向,人们对于权利有不同的认识。权利和义务是一对相对概念,从比较普遍的观点来看,权利具有主导性,义务具有受动性,个体的权利具有对世的原初性和对其他个体的主导性。义务具有次生性,没有无缘由的原初性义务,通常来说,权利的逾界行使侵害了他人利益所负担之不利后果,就是义务。“权利主要体现为自决权、自由权、豁免权……”〔5〕夏勇:《权利哲学的基本问题》,载 《法学研究》2004年第3期。之特性,其中,自决权当然包含选择权,即不被强制做某事的权利。“个人权利是个人手中的政治王牌。当由于某原因,一个集体目标不足以证成可以否认个人所希冀什么、享有什么和做什么时,或不足以证成可以强加于个人某些损失或损害时,个人便享有权利。”〔6〕Ronald Dworkin,Taking Rights Seriously,Introduction,Duck worth,1978,p.xi.此处的“个人”要做宽泛的理解,包括法人和其他组织,行政机关在诉讼程序中也是和普通诉讼主体 (即个体)具有同样的诉讼地位。所以,“法无禁止即权利”,不能无缘无故的剥夺某个人的权利,也不能毫无缘由的强加于某人义务。在法律上,权利的剥夺或义务的加于都必须有法定的理由。
从诉讼制度的性质而言,整个诉讼过程的目的在于查清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义务关系,诉讼程序具有工具性意义,由此决定了诉讼过程中当事人更多的是享有参与诉讼的各项权利,其最大的义务是履行最终确定的司法裁判之内容。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当事人只要不主动影响诉讼进程,法院不应处分当事人的实体权利,不应无缘由地强加其他程序性义务。一般说来,诉讼当事人的义务主要有两点,即①遵守诉讼秩序的义务;②履行生效法律文书的义务。〔7〕张卫平:《民事诉讼法》,法律出版社2004年版,第139页。依张卫平教授之观点,公民在法律上的义务还包括 “依法行使诉讼权利的义务”,对此作者不敢苟同,这是在混淆权利和义务,故不予采纳。对于遵守诉讼秩序的义务,我国 《行政诉讼法》第59条、《民事诉讼法》第110条、111条均明确规定了包括诉讼参与人在内的所有主体不得扰乱法庭秩序、妨害诉讼之义务;至于履行生效法律文书义务,这是每个诉讼当事人的当然义务,也是整个诉讼过程的目的。除却上述两项义务之外,诉讼参加人不应该再承担其他义务。〔8〕在我国 《民事诉讼法》第109条中,对于负有赡养、抚育、扶养义务和不到庭就无法查清案件事实的被告规定了出庭义务,这是基于原告和被告的特殊关系以及保护原告已较为确定的利益之需要。此时,诉讼程序的重心不是查清事实,因为事实基本清楚,更重要的是通过诉讼确定双方的权利义务关系并保障被告的义务切实得到履行。这种特例在行政诉讼中不存在,因为其中之被告一方属公法人组织,不会引发上述关系。那么,出庭应诉是一项权利,还是义务?
在行政诉讼中,行政相对人作为原告具有起诉权并以此启动对行政行为的司法审查程序,但这只是说明被诉行政行为存在违法之可能性,是否违法必须等待司法审查的结果才能评判,行政行为被起诉至法院之后,相关的行政主体并不因此而减损任何权利。与相对人起诉权对应的义务是审判权,义务主体是法院。作为诉讼武器对等的设置,与起诉人的诉权相呼应,应诉人理所应当被赋予应诉之权利。之所以说应诉是一种权利,是因为,首先,在判决确定前,行政主体并无任何行为被确定为违法,故不能无缘由的被施予义务;其次,行政主体作为被告出庭应诉除却具有为自身利益之原因,也有帮助法院查清事实的客观效果,如果诉讼各方均不予配合,则法院的审判权就失去了存在的意义,从这个意义上来说,司法权只能鼓励各方积极参与诉讼,而不能对此予以强制;再者,司法具有被动、中立、不告不理的谦抑本性,司法审判之机器的启动权不在于法院,法院的居间裁决应该中立,不能厚此薄彼,对原告赋予起诉权,而对于被告却强加于必须出庭的义务;司法的被动性不仅要求司法不宜主动启动审查权,还要求法院在审判过程中尊重当事人的诉讼参与权,其既可以积极参与诉讼,也可以有选择性的参与,又可以灵活地调整参与诉讼的投入成本和变换诉讼态度。法院只是根据双方提供的证据,依法进行裁判,哪怕是一方不予举证,法院也不能直接处分该行为,而只能针对该行为的结果,即提供的证据之质与量,依据证据规则进行裁判。与起诉权一样,出庭应诉权所对应的义务也是审判权,义务主体是审理法院。起诉权和应诉权属于当事人诉讼权利的内容之一,二者是相互对应的,而非对立,〔9〕“对应”是指一体系统中某一项在性质、作用、位置或数量上跟另一系统中某一项的相当,二者的存在是一种平衡、对称,例如,左和右,上和下、前与后;“对立”则指处于矛盾统一体中的相互依存、相互斗争的两个方面,例如输和赢、权利与义务。参见:《现代汉语词典》,商务印书馆2014年版,第330页。两种权利均属于潜在性权利,在行政相对人启动诉权并为法院所认可后,则对应行政机关的应诉权随即启动,因此,应诉权具有被动性和防御性。与此两种诉讼权利相对应的是法院的审判权,法院对此负有公平、公正裁判之义务。
诉讼权利是公民、法人或组织的一项基本的公法上之权利,没有诉讼权利就不可能有诉讼制度,诉讼权利包括起诉权、应诉权、答辩权、出庭权、质证辩论权、上诉权、申诉权等一系列程序性权利,程序权利保障当事人在诉讼中能够充分地表达自己的意志、展示自己的证据、攻击对方的证据。整个诉讼程序是为了给纠纷当事人提供一个非暴力的、相对公平的、文明方式解决纠纷之平台。在诉讼程序进行过程中,争议双方的诉讼地位是对等的。假如一方有起诉权,而另一方就必须有义务去应诉的话,那么如何避免起诉方故意拖累应诉方,使其耗费大量时间和精力于诉讼中之不义行为?
行政诉讼法是一个有机整体,各项制度之间具有相互的一致性和承接性,例如,我国行政诉讼法在2014年修订中,因为在目的方面废除了 “维护”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之追求,在判决类型中就要相应地废除 “维持判决”和 “确认合法或有效”判决。现行 《行政诉讼法》虽然没有从正面肯定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权利属性,但是,从第58条的缺席判决规定可以推导出:对于行政主体不出庭应诉,尚且没有明确的制裁措施,何况是行政主体选派何人之事,司法审查更不应过问。反过来,如果行政主体负责人出庭应诉是一项义务,那么,在其没有派负责人出庭情况下,法院应该依法拒绝非责任人的出庭,然后确定应出庭的负责人,接下来就是要对拒绝出庭者采用司法拘传措施,而不是缺席判决。由此可以推断,对于被诉行政主体来说,出庭应诉是一种权利。
当前,在我国司法实践中,法院向被告行政主体送达 《应诉通知书》中,已经明确告知当事人的诉讼权利,而且需列明内容,包括:原告有起诉权、被告有应诉权;有委托代理人进行诉讼、申请回避、提供证据、举证、质证和陈述最后意见的权利;有阅卷、申请补正法庭笔录和申请强制执行的权利;原告有放弃诉讼请求权利;不服一审裁判,有提起上诉权利。〔10〕我国当前的 《行政诉讼应诉通知书》的内容中,通常都有当事人诉权内容的告知。应诉通知书格式参见:http://wenku.baidu.com/link?url= KJUTNbIuKsIdTHQ0Fpy3kcA9ZfHxTiXcsRtKY6k _yohSPKY53y10aKZJl3wVPYDLBinAK5xVbeG-ZOD9ebT1ouKAzA3Bxt8QCPKlRdslIeG.2015年8月16日访问。其中,出庭应诉权包括选择是否出庭、选派何人出庭之权利。因为权利具有自决性,当事人可以选择行使权利的方式,对于是否选派负责人出庭应诉是被告主体的权利,此项自决权不应受到司法审查的限制。因此,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不应受到外部干预。
二、诉权平等原则——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应该保护而不是限制
凡事必有其因,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为什么近年来在我国被重视并获得较快的发展,直至写入法律?这是与我国当前 “民告官”制度的司法环境及其引起的公众认知分不开的。1990年我国 《行政诉讼法》开始实施,“民告官”才算是被正式的纳入了司法的轨道,实现了从无到有。但是,二十多年的实践中,行政机关在诉讼中难改傲慢的惯性,“不理睬、不应诉、不执行”现象屡见不鲜。公民告官不见官,法院裁判没底气,这与我国不断发展的法治进程显得格外不协调,因此,矫正行政诉讼中官民不对等现象成为人们的共识。正是由于我国行政权的强大及其对待诉讼的不重视,人们不自觉的就希望起码能在法庭上看到行政负责人,甚至有人认为把负责人拉到被告席上就是一种胜利,对行政主体也算是一种 “羞辱”,比较解气。而行政机关为了显示对于依法行政的决心和勇气,也不自觉的选择该项制度为突破口。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是人们最能直观感受得到的制度,所以,无论社会公众、行政机关以及法院都不约而同的找到了这个切入点,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非常符合人们的心理期盼。
由于社会现实中行政机关处于强势,行政相对人处于弱势,行政诉讼法的目的被定位为:保障公民权利、监督行政机关依法行政。因此,为了平衡诉讼双方当事人的地位,就要施予被告更多的义务。在行政诉讼法中,诉讼制度的设计就如同一个跷跷板装置,通过杠杆长短的调整,以保证诉讼结果的公平。但是此杠杆的设置应该符合诉讼的基本原理,不能为了迎合公众情绪上的满足而不顾及诉讼规律。应该限于行政诉讼中双方不平等的具体方面,有针对性、有尺度地调整行政主体的优势地位。首先,与相对人相比,行政主体最大的强势体现在其是具有国家做后盾的强制性公权,所以,在行政诉讼制度中,行政主体只做被告,不能做原告,也就是只能 “民告官”,不能 “官告民”,而且一旦进入诉讼程序行政主体就被贴上了 “被告”的标签,其身份变成了被告,并且其强制性公权力在整个诉讼程序中被 “冻结”,不能使用,行政机关就相当于普通的社会组织,且在整个诉讼过程中必须听从法院的安排。其次,将审理对象确定为 “行政行为的合法性”,法院只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相对人是否违法只是作为证明行政行为存在的证据。再者,行政机关必须在法定的举证时限内,向法院提交其行政行为合法的证据,否则就要承担举证不能之不利后果。再者,由于行政主体距离证据更近,且其使用国家资源进行举证的能力强于相对人,因此,行政诉讼的举证规则规定被告承担主要举证责任(俗称举证责任倒置),以此来平衡其与相对人在举证能力上的差距。
由上述可以看出,这些对于行政主体不利的制度设计都是有针对性的,除此之外,行政主体和行政相对人具有平等的诉讼权利,而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只是为了迎合人们的心理需求,对其进行司法审查并不具有合理性。在行政诉讼的程序性权利方面,被告和原告不应有任何的差别,除了原告启动诉讼的权利叫做起诉权,被告应诉的权利被称作应诉权,在随后参加庭审、举证、质证、上诉、再审申诉等权利方面,二者没有任何的区别。因此,在诉讼过程中,纠纷当事人的诉讼地位是平等的,如果把被告的应诉作为一项必须的义务,既有悖于诉讼平等原则,也不符合 “不能无故加于义务”的正当性。
行政诉讼脱胎于民事诉讼,从与民事诉讼的比较中也可以看出,除却在 “原、被告身份固定;举证责任分配;审判对象”等三方面有差异外,二者并无任何不同。在英美法系中,行政纠纷没有采用独立的行政诉讼程序,依然采用民事诉讼程序就说明了二者在诉讼程序方面并无质的差别。诉讼地位平等是诉讼制度中武器对等原则的基本要求。我国民事诉讼法第2条明确规定,“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任务,是保护当事人行使诉讼权利,……”,说明在诉讼过程中,审判权在实现查明争议事实、裁断纠纷任务的同时,也要保障公民在此过程中所享有的各项诉讼权利。不能为了追求结果的公正而造成对程序权利之侵害。同时,民事诉讼法第8条规定 “民事诉讼当事人有平等的诉讼权利。人民法院审理民事案件,应当保障和便利当事人行使诉讼”,行政诉讼法第8条也规定,“当事人在行政诉讼中的法律地位平等”。因此,在行政诉讼中,诉讼双方当事人的诉讼权利是平等的,对应于原告的起诉权,被告的应诉权同样应该受到尊重和保护。在被告应诉权内容中,行政机关选派应诉人是其中应有之义,法院应该尊重行政机关的自主选择权。
基于诉讼法律地位平等原则的要求,无论对于民事诉讼双方当事人,还是对于行政诉讼原告,并没有哪些法律对其选派出庭应诉者之事项作出限制,如果有规定,也是在诉讼资格不明确或无监护人愿意出庭情况下,而这种规定并不是对当事人的限制,反而是对其诉权的保护,〔11〕例如,在我国 《民法》第二章中,对于公民的民事权利能力和民事行为能力、监护、宣告失踪或死亡等情况,以及个体工商户、农村承包经营户及个人合伙等主体诉讼权利的规定,均是从保护其合法行使诉权的角度出发,而不是限制其权利及其行使的方式。是确保当事人因为客观原因无法亲自行使诉权时的保护措施。因此,在行政诉讼中,对行政主体出庭应诉权不应限制,相反,应该尊重和保护。
三、司法权监督行政的有限性——行政内部管理自治
一个政治发展成熟的社会,其公权力基本上是由立法权、行政权和司法权构成,这已经成为文明社会的基本选择和共识。此三种权力性质不同,功能也有别。立法权以充分汇聚和表达民意为己任,追求民主和参与,行政权以忠实执法、提供高效管理和服务为目的,司法权以公平、公正裁判为追求。此三种权力的不同性质决定了其功能各异,“舟行于水,车行于陆,各限其用”,〔12〕孔子:《论语全书》,思覆译注,中国华侨出版社2013年,第416页。任何一种制度的功能都是有限的,如果不顾及事物的性质,不按照事物固有的功能进行制度设计,必将因违背社会规律而受到制裁。因此,三权在配合与制衡的过程中,均有其界限,不能僭越。从性质上来说,司法权是一种裁判权,“裁”就是一刀两断地解决,“判”就是对事物作出是非黑白的评价和判断。〔13〕[日]兼子一:《裁判法》,有斐阁1956年版,第7页,转引自胡夏冰:《司法权:性质与构成的分析》,人民法院出版社2003年版,第198页。司法权实现的过程就是法官对于纠纷当事人所主张的事实问题及相关法律问题作出具有效力的判断的过程。司法即justice,亦有 “公正”之意,〔14〕《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7版),商务印书馆、牛津大学出版社2012年3月版,第1103页。故司法即公正,司法追求公正,也代表着公正。从整体来说,司法权具有程序性,是为解决实体权利义务纠纷服务的,司法裁判只是为了查明并判断实体权利义务之关系,并在此基础上矫正被打破的实体权利和义务的关系。〔15〕不排除司法权在运行过程中所产生的当事人的程序性权利,但这些是少量的、从属的。行政权是一种管理权、执行权。行政即administrative,亦有管理之意。〔16〕同前引 〔14〕,《牛津高级英汉双解词典》第25页。任何社会中都不存在不会违法的主体,行政主体也不例外,故,分权与制衡的宪政原则决定了司法权必须监督行政权,法治发达国家基本上都设置了对行政权的司法审查制度。同时,考虑到行政权的特性,这种审查有监督的时机、范围和审查深度等限制条件。从时机上来说,司法监督行政要遵循 “成熟原则”,即司法对于行政的审查,必须是该行政行为已经在行政外部形成为一个适宜司法审查的状态,且如果推迟可能会给当事人造成困难;从范围上来说,司法会排除那些不适宜其监督的内容,例如在我国 《行政诉讼法》第13条中所明列者;就司法审查的深度而言,其包括合法性审查和合理性审查,其中,合法性审查是主要内容,对合理性 (即行政自由裁量权)的审查应较为谨慎,我国 《行政诉讼法》中仅有第七十条 “(五)滥用职权的;(六)明显不当”等审查事项,而且在司法审判实践中很少被法官所采用。总之,行政系统具有其自身的专业性,有其内部纠错机制,而司法权因专业知识所限,以及司法资源的有限性等,其对行政权审查的深度是有限的。
由上可知,司法权监督行政权之范围和深度有限,这是因受司法权的功能和行政权相对自治特性之制约,那么,在行政系统内,行政主体选派出庭应诉人员事项,是否属于司法审查的范围呢?欲厘清该问题,需先解决一个前提性问题,即被诉行政主体应诉事项的另一种属性——行政外部行为或内部行为。
四、选派出庭人员是行政主体内部事务安排权——不受司法审查
司法权对行政事务的审查,在广义方面包括违宪审查和行政诉讼,狭义的仅指后者。在我国行政诉讼制度设计中,从司法权的角度来说,法院主要审查行政行为的合法性 (确切的说是不违法性)和有限的合理性 (即行政自由裁量)。从行政权的角度来看,行政行为内容繁杂,包括:哪些应当纳入司法审查、哪些是有限审查的,哪些是虽然侵犯他人利益但不宜审查的,哪些是不侵犯别人权利也不应进行司法审查的等。一个行政行为的可受司法审查性,一般须具备三个要素:1.须是拥有行政管理职权的机关、组织或个人实施,这一条件排除了立法机关、司法机关、检察机关、军事机关以及其他不拥有行政管理组织的行为。2.须是与行使行政职权有关的行为。3.须是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的行为。”〔17〕应松年袁曙宏:《走向法治政府:依法行政理论研究与实证调查》,法律出版社2001年版,第346-347页。以内部行政行为为样本,我们可依此条件来检验其是否可受司法审查。内部行政行为通常包括内部决定、内部处分行为,以及最常见的日常管理行为。其中,内部决定如果涉及内部人利益,可能会变成内部处分行为,我国 《行政诉讼法》第13条第 (三)明确将该种情形排除于司法审查之外。若内部决定行为涉及对外部人利益的处分,则有可能外化为外部行政行为从而变得可诉。行政日常管理行为,也是行政主体依职权作出的行为,由于这些行为不对公民、法人其他组织权利义务产生实际影响,故不符合司法审查之要件。
之所以行政机关日常管理行为不受司法审查,是因为其以维持行政机关正常运作为目的,不以影响或者改变他人的权利义务关系为目的,其具有过程性、程序性、工具性和非结果性的特点。如果把一个行政机关整体比作一个人的话,那么个人的行为就相当于整个行政机关的行为,而行政内部的日常管理行为就相当于一个人正常的进食、睡觉、身体活动 (如站、走、坐、思考)等,这是为了维持其物理性客体的正常运转。行政之日常管理行为纷繁复杂,如通知开会、文件归档、财务统计、登记造册、工作安排等。这些行为主观上不具有故意或过失的心态,客观上也不会对外界之利益产生影响。如果我们一定要说这些行为存在间接的影响他人利益之可能,也只是作为工具服务于行政主体的能够影响他人利益的行政行为,此时,司法审查的对象仍然是此后的行政行为,日常管理工作已经被该行政行为所覆盖或吸收。
从诉讼权利的角度,我们认为行政诉讼中被告选派出庭人员是一项诉讼权利,属于应诉权的内容。而从行政权的性质角度,我们可以把其看作是一项行政内部日常管理行为,因为其完全符合内部行为的特征。行政主体接到法院 《应诉通知书》,从中了解具体争议事项内容,然后就会对案件作出内心评估,从而决定是否应诉或派谁出庭应诉等事项。首先,应诉 “通知书”只是信息的传达、事项的告知,不是权利的剥夺,也不是义务的强加。否则,就不能叫做“通知”书。同时,通知书中也不应有被告主体必须派内部何种人员出庭应诉之义务要求。当然,法院可以根据案件需要,通过司法建议的形式对被告主体派何人 (通常是责任人)作出建议,但建议不具有强制性,也不属于必须履行之义务。在有些应诉通知书或传票中,法院会告知当事人如果不出庭可能会缺席判决,这间接地说明,法院既不能强制出庭,更不宜干涉派谁出庭。行政主体在接到法院的应诉通知或传票后,对于本单位是否出庭应诉及派谁出庭应诉,会根据内部的日常管理程序予以安排,无论是由某个领导、某内设机构 (如法制办),还是工作人员做出选派决定,这都是单位的 “私事”,该项日常工作安排对审判主体,即法院,并无任何影响,因为其居间裁决,无利益掺入,只是依据双方提供之证据及证据规则确定裁判结果。如果行政内部所安排人员应诉失当,其出庭应诉表现不佳,或因为诉讼技术的原因而败诉,这是被告主体的 “内部事务”,其只要承担败诉后果,法院对此不宜干涉。反过来,即使诉讼中最后被诉行政机关胜诉,只要其内部在安排出庭应诉人员时违反了内部相关规定,行政主体依然可以通过内部处分追究相关人员的责任。只有行政主体不执行确定裁判时,法院才能对行政主体进行处分,且即使处分了责任人,也是因为其不履行生效裁判之原因,而不是其委派应诉人员失当之责任。所以,选派出庭人员是行政主体内部事务安排权,不受司法审查。
反过来,假如对于行政内部的日常管理行为都要进行司法审查,那么,由此可以推演,还有哪种行政行为不能纳入法院审查的范畴?行政机关还有何自我管理、自由裁量空间可言?行政机关还有何专业性可言?司法对于行政的审查还谈什么 “成熟原则”呢?而且,如果这样的话,行政权难免会变得极为僵化,不敢越雷池一步,甚至变成司法权手中的皮影,司法权也会因陷入对浩瀚的行政事务之审查而改变了其自身的性质和职能,这是不可想象的。所以,司法审查必须止于行政内部管理事务。
五、司法干涉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所面临之困境
(一)理论上的难以自洽
一项制度的构建,必有先行之理论作为支撑,我国行政诉讼法中规定行政机关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也是有其理论背景的。对此支持观点大致有如下几个方面:①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维护司法权威和尊严,提高依法执政水平。〔18〕于海波:《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安徽大学宪法学与行政法学2014年硕士论文,第15-16页。②行政首长是行政行为的 “知情者”、“决断者”、“责任者”。〔19〕章志远:《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的理论基础探析》,载 《人民法院报》,2012年4月25日 (第6版)。③迎合我国 《宪法》上的首长负责制规定,即第86条规定:“国务院实行总理负责制。各部、各委员会实行部长、主任负责制。”第105条规定:“地方各级人民政府实行省长、市长、县长、区长、乡长、镇长负责制。”〔20〕同前引〔19〕。④实践中获得了很好的效果,很多地方政府也作出相应的规定,“目前,至少有超过153个地方相继通过颁发规范性文件的形式推行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该制度受到国务院和最高人民法院的高度认可。”〔21〕参见章志远、顾勤芳:《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立法面向问题研究》, 《学习论坛》2012年第10期。此数据是2012年统计的,可以预测,在2014年11月行政诉讼法修改中明确了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后,行政机关的相关规范文本必然会大幅度上升。
其实,这几点理由都是经不起推敲的:
在①和④中,所谓的及时有效化解行政争议,实践中的效果好。首先,这是一种由果推因的思维,以结果的好坏来评判制度的合理与否,不符合对司法制度检验的规则。司法制度的设计必须具有理论的自洽性、前瞻性和全局性,不能是一厢情愿的假设和试点效果的放大。司法审判是一种规则,以公平、公正为最高追求,所以,化解行政纠纷不仅是要 “及时、有效”,更重要的是 “依法”,且所谓 “及时、有效”的评判标准具有不确定性。同时,有很多行政机关自行制定规范性文件推行此制度,恰恰说明了这是行政机关的内部事务,由行政机关自我规制比较合理,以此反证司法机关不应干涉。反观法院系统,只有在2015年4月 《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 〈中华人民共和国行政诉讼法〉若干问题的解释》第5条对于 “行政机关负责人”,做了 “包括行政机关的正职和副职负责人”的说明,对于违反此规定者,与 《行政诉讼法》正文一样,并无任何处分之举措,其中第59条对于扰乱诉讼秩序之惩罚情形中,并无对被告派负责人出庭应诉不力甚至缺席有任何处罚。这也说明,司法裁判系统对于该项措施有可能是保持克制的态度,更有可能是无能为力。这也是制度缺乏理论支撑之必然现象。
理由②认为,行政首长是行政行为的 “知情者”、“决断者”、“责任者”,但是,这与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从理论上,行政首长对于本单位的所有事项,都是 “知情者”、“决断者”和 “责任者”,如果这样推论,不仅仅是出庭应诉事项,所有的行政活动都需要负责人亲临才是最佳。而且,诉讼的专业性、程序化、对抗性要求参与者属知晓相关法律制度和规则者,相比较而言,还有哪些人比具有专门知识的律师更为合适呢?常言道 “打官司就是打证据”,而且由于行政诉讼的证据规则、举证责任和审判对象等不同于常人理解的民事诉讼,更需要参与诉讼的人不仅要知晓案情、还需熟悉和恰当运用各项诉讼权利。正因为司法的公正性与司法的专业化程度存在高度的勾连,因此许多西方国家的行政诉讼都实行律师强制代理制度。〔22〕如 《联邦德国行政法院法》第67条第1款规定:“提出申请的参与人,必须委托律师或德国高校老师在联邦行政法院及高等行政法院作为其全权代理人。”参见 [德]平特纳:《德国普通行政法》,朱林译,中国政法大学出版社1999年版,第278页。确切的说,首长也未必总是 “知情者”,通常情况下,首长不是行政行为的一线执行者,而是通过间接的渠道,如听取汇报才 “知情”的;首长是 “决断者”没错,但是,这个决断是有程序和制度的,不是一言堂,也不是简单地当场拍板,行政决策通常是民主基础上的集中;首长是责任者,通常是指政治责任。如果行政首长常常在法庭上基于诉讼形势的变化,随时作出 “协调”(其实就是实质的调解),或者当场作出承诺、决定,像某位首长在庭审之后豪迈的放言,“回去整风”〔23〕案例:盐城某地工商局被告上法庭,开始是委托代理人出庭。几次庭审下来,矛盾激化,工商局长决定出庭应诉。庭审中,他才得知事情原委,意识到是执法人员行为过火,但委托代理人没跟他说实话。局长当场赔礼道歉,满足老百姓诉求,庭审后撂下一句话:“回去整风!”参见:http://www.jsfy.gov.cn/mtjj/sjmt/2011./05/17142553969.html.2015年8月25日访问。,这种家长式甚至山大王式的领导作风,是违背行政管理规律的。还有人认为:但凡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的 “民告官”案,大多不当庭宣判,以调解结案,且有时收获 “奇效”。〔24〕顾勤芳:《我国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载 《公法研究》2014年第1期,第87页。我们都知道,在行政诉讼中,基于 “公权力不可让渡”的原则,可供调解之案件种类极少。对被诉行政行为如果尚未作出合法与否的审理与判定就被调解结案了,那么,行政诉讼监督行政之目的如何实现,调解背后是否有拿国家利益为行政主体的违法行为隐性买单之嫌,〔25〕所谓隐性买单,就是指没有明确的法律文书对行政行为的违法或不当作出定性。而是在 “协调”过程中,拿国家的利益 (主要是经济上的)换取行政相对人对行政诉讼案件的撤诉、息诉。所以,这种 “奇效”是以违背行政诉讼的基本理论和牺牲社会长远利益换取的表面性疗效。
理由③的观点也经不起推敲额。我国 《宪法》上的首长负责制规定,意在确定行政体系不同于立法权的委员会制度和司法权上合议制的责任形式,责任通常是由权力引起且其承担方式受制于对应的权力之性质。因为行政系统是民主集中制的决策方式,所以,采用首长负责制有利于行政效率。而首长的负责与凡事必须由其亲躬没有必然的因果关系。如果这样类推,则行政机关的所有外事活动都要首长出面,若此,行政管理会陷入一种很荒唐的局面。
(二)现实中面临的困境
任何一项法律制度乃至每个法律条文的背后,都有理论作为支撑,凡是违背基本法理的制度在现实中必然会引起矛盾或造成不必要的成本增加甚至损害。当前,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在现实中已经被自觉不自觉的 “运动化”、“形式化”、“庸俗化”〔26〕章志远:《行政诉讼中的行政首长出庭应诉制度研究》,载 《法学杂志》2013年第3期。了,并且出现了一些并非人们期盼的后果。其实,我国 《立法法》第9条规定明确了 “司法”制度属于国家绝对保留事项,除法律有权制定规范外,其他任何机关都不能规定,〔27〕同前引〔24〕,第95页。其初衷就是防止对司法制度的改动过于随意,没有经过充分的论证不要轻易 “上马”。最高人民法院副院长江必新大法官曾指出 “对于行政首长出庭应诉”立法不应做出硬性的百分比的要求和比较僵硬的规定。〔28〕江必新:《不会硬性规定行政首长出庭应诉》,http://news.xinhuanet.com/legal/2008-03/11/content_7764905.htm.2015年8月5日访问。
司法实践中,有些地方法院甚至采取行政首长不来就不开庭的措施,这不但侵犯了被告的诉讼权利,干涉了行政内部事务,而且这种 “某人不来不能开席”的做法反而会进一步提升行政首长的家长地位,在人们的心中强化了行政 “一把手”的重要性,不利于行政内部的科学管理。而且,如果负责人出庭不出声,或者出庭不配合,甚至耍家长态度,蛮横,是否法律还须进一步规定负责人出庭后应该如何表现?再进一步,若对于出庭负责人的表现进行考核,依据什么标准,总不能依据案件的输赢或是否得到调解为标准吧!另外,对于违反出庭应诉制度的责任者,应该由谁作出处分?法院是不宜对其作出司法处分的,如果是采取拘传措施,拘传的前提是要确定具体责任人 (是负责安排出庭事项的领导、内设机构、还是被指派的出庭人员?),而这又要借助于行政机关协助方能确认,说明法院对行政的监督必须靠行政帮助才能进行,这岂不是陷入了悖论?再者,如果对责任者由行政机关进行处分的话,是本机关、行政监察机关、还是公安机关?这都是在实践种难以操作的。
因此,假如对违反该项规定的责任人进行处分,法院充其量只能对其作出司法建议,〔29〕我国 《行政诉讼法》第62条第二款规定 “人民法院对被告经传票传唤无正当理由拒不到庭,或者未经法庭许可中途退庭的,可以将被告拒不到庭或者中途退庭的情况予以公告,并可以向监察机关或者被告的上一级行政机关提出依法给予其主要负责人或者直接责任人员处分的司法建议。”该条文中包含了两个信息:一是针对的主体是 “拒不到庭或中途擅自退庭者”,而非针对 “出庭应诉是否为行政负责人”事项;其次是,通常来说 “公告”是一个项中性的行为,其并不具有惩罚性,但是,在此处,很显然具有 “羞辱”之功效。由此,对于行政机关没有派负责人出庭应诉事项,法院也不应适用 “公告”处罚。当然,这里并不禁止行政机关自我管理过程中适用 “公告”。最终能够做出处分的仍然是行政机关。这种违反司法制度要靠行政主体来处罚的现象,使得法院成为了 “没有牙齿的老虎”,出现了 “法院既要通过监督行政应诉行为应提高司法威信,但有必须依靠行政机关支持”之悖论,“靠行政机关的支持来提升司法的独立性和摆脱行政干预”之措施是无法实现当前司法改革中落实司法独立行使审判权,摆脱行政干预目的的。
其实,《行政诉讼法》中关于负责人出庭应诉的规定过于弹性,不具有拘束力,从其内容“被诉行政机关应当出庭应诉。不能出庭的,应当委托行政机关相应的工作人员出庭。”可以看出,虽然规定了 “应当”但是,并没有规定应当的条件,也没有规定 “不能出庭的”条件。推行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所有行政案件,无论简繁,均须有行政负责人出庭,既不现实亦无必要,但是如果设置出庭率的话,这个比例规定多少较为合理,由谁来定,如果是行政机关来定,各地是否会不一致?而且,出庭率由行政机关制定的话,这项制度其实又演化为了行政内部的裁量,等于把该项行政诉讼制度变相 “掏空”,法院依然无法进行监督。如果法院非要对此进行监督的话,只能向被告机关或其上级机关进行司法建议,但毕竟,建议不具有强制性,而且司法建议的内容也要受到司法审查的深度之限制,例如,只能建议对有关责任人进行行政处分,至于是党纪处分、行政处分以及行政处分的种类和轻重,这是行政内部事项,法院不宜过于具体化。
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必然带来行政活动成本的增加和一定行政资源的消耗。因为负责人通常是本单位各项工作安排和管理的主力,如果整天疲于应付诉讼,则必然会占用其对其他工作之时间和精力的投入。其次,负责人不一定擅长诉讼,律师或本单位专门的法治机构工作人员才是最佳选择。再者,没有证据证明,行政负责人一定就比其他人更为通情达理,有更强的诉讼参与能力。当前近乎运动式的推行该制度,是因为举国上下的重视从而出现很好的势头,但是,启动之后能否进入良性的常态化,对此我们不能盲目乐观。
结语
从实践上来看,行政诉讼中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无论是否与诉讼理论契合,在客观上的确是一次对行政机关的法治教育课,它有力地促进了行政机关依法行政,使行政机关对于行政诉讼制度空前的重视。同时,对于整个社会也是一次很好的普法活动。再者,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也在客观上提高了法院的威信。但是,诉讼毕竟是一套系统的理论,而且实践必须有理论的指导,没有理论作为指导的实践必然是盲目的、片面的。当前该项制度能有效运作是因为在党的领导下政府和司法机关联动的优势之结果,但是,这种现象毕竟不是常态,司法对行政的监督不可能会永远得到行政机关的配合,毕竟行政机关既不是不会犯错的上帝,也不是没有私利的组织,一旦行政主体不积极配合和支持,司法对该项制度的推行就会陷入尴尬。因此,法院系统对于该项制度要有一个清晰、准确的认识,要明确其理论缺陷所在,在适用过程中把握尺度,保持必要的谦抑,不要越界,更多的是通过鼓励措施和司法建议手段引导行政机关自身加强意识和完善内部监督制度。借助于当前建设法治国家的大好时机,发挥行政负责人出庭应诉制度的助推作用,使行政主体养成一种习惯,自觉地、尽可能地选派负责人出庭应诉,使该项制度成为一种常态,从而使硬性规定变得 “多余”,变成几乎不用的 “闲置”条款。当然,这种推理只是一种美好的假设,具有不确定性。解决该问题最为根本的措施毫无疑问是对于法院裁判的切实执行。只有确定裁判得到切实的实施,才能让诉讼参与各方从根本上认真对待诉讼权利、充分行使诉讼权利。相信,如果负责人出庭制度能够有好的效果的话,法院根本无需管问,行政机关就会从自身的利益出发自觉地作出该项行为。
田勇军,浙江大学光华法学院公法与比较法研究所博士后,中共贵州省委党校法学部副教授。
本文系中国博士后基金项目 《交通行政处罚中 “一事不再罚”之 “一事”认定问题研究》(项目编号:503000-X93103)之阶段性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