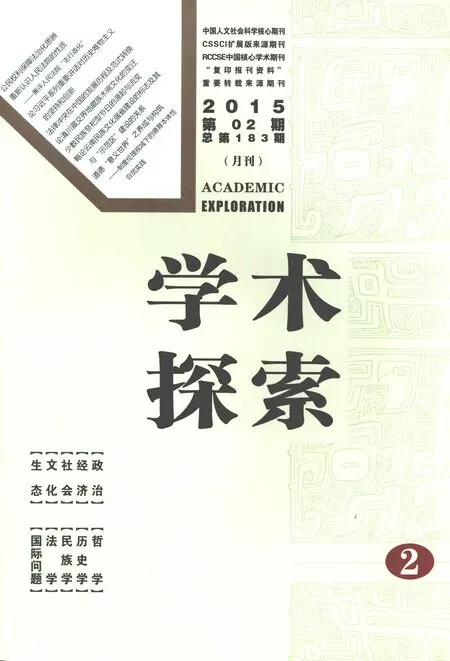叙事时间策略和叙事时间维度
——张爱玲的时间叙事
2015-02-26杨春
杨 春
(中华女子学院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101)
叙事时间策略和叙事时间维度
——张爱玲的时间叙事
杨 春
(中华女子学院 学报编辑部,北京 100101)
张爱玲对叙事时间以及叙事时间与人的关系有着深刻的理解和独到的掌控能力,张爱玲叙事时能充分地利用叙事时间中的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差异和对比,来达到表达自己对时间和人生的叙事主题。同时叙事时间呈现出几组张力: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之间的张力;个体时间和集体时间之间的张力;过去、现在和未来时间之间的张力。这几组张力使得张爱玲的作品展现了无穷的魅力。张爱玲的小说能够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转化和穿梭。而叙事时间的四个维度——世界时间、作品时间、作者时间和读者时间对张爱玲作品也产生了深刻的影响。
叙事时间;叙事时间张力;时空转化;叙事维度
一、故事时间和文本时间
张爱玲在叙事的时候充分地利用叙事时间中的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差异和对比,来达到表达自己的主题的效果。热奈特在《叙事话语》引用克里斯蒂安·麦茨的话来加以说明时说:“叙事是一组有两个时间的序列,被讲述的事情的时间和叙事的时间。这种双重性不仅使一切时间畸变成为可能,挑出叙事中的这些畸变是不足为奇的;更为根本的是,它要求我们确认叙事的功能之一是把一种时间兑现为另一种时间。”[1]热奈特将时间划分为“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故事时间指的是所述事件实际上发生所需的时间,话语时间指的是文本在叙述的时候用于叙述事件的时间,通常用文本叙述的过程中所使用的篇幅的长短来衡量和计算。故事时间是事物本身在时间的链条上的实际长短或发展轨迹的长短,而话语时间则是作者在叙事的篇幅上进行增加篇幅叙述或者缩短叙述,是对原始的实际时间的改造和利用,读者也可以通过阅读读者所陈述的篇幅的长短来领悟作者的思想和意图。这种差异性热奈特提出更为根本的研究方法,即“顺序”“时距”“频率”等一套标准的叙事时间研究术语。如果用这套研究方法来研究张爱玲的叙事时间的话,会发现她在时间上的艺术造诣。具体来说,主要表现为下面几个方面。
第一,叙事时序的使用。叙事时序指的是叙述故事时的时间顺序。叙事时间策略主要利用的是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排列关系的差异和不等同,文本的叙事时间可以按照故事发展的自然顺序,也可以按照叙述者讲述的时间,包括倒叙、插叙、回叙诸种手法,这些手段和方法在张爱玲的小说中都频繁出现。如《金锁记》的开头采用的是倒叙的手法。以老年人回忆开始,由当下的凄凉的昏暗的微带泪光的月亮联想到三十年前的铜钱大的欢愉的月亮。这种表达方式使张爱玲在故事时间与叙事时间之间自由来回,在叙事中以隐蔽的方式表达对过去事件的时间感受。这实际上是张爱玲利用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之间的反差和对比,采用非线性、立体的时间回溯的叙事方法,使得她取得了现在与过去的对话:使作者与读者和故事中的人物都保持了一定距离;也有效拉长阅读者的悬念、期待心理;又使故事回到“从前”,体验过去的时间和岁月,在强烈的时间差异和生活处境对比中体味沉重人生的苍凉。张爱玲在讲述中往往有意打破事件的自然秩序,按照叙事的需要重新排列。而小说中对曹七巧的来历则采用了插叙的方式,七巧在送走自己的哥嫂之后,插叙了一段对自己年轻时候的回忆,站在麻油店黑腻的柜台前卖麻油的穿着蓝夏布衫裤的俊俏的大姑娘七巧,常常会引来小伙子们的爱慕。这种叙事方式,具有非常强的时空掌控能力,时间由三十年前又向前推进到了曹七巧没有嫁进姜家之前的故事,增加了故事的容量;空间也由姜家转到了七巧做姑娘时娘家的麻油店。高宅大院的姜家与乡下的麻油店形成了鲜明的对比。因此,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叙事话语中的时间呈现出非线性的、立体的、并置的特征。这种时间表现上使作者可以自由地调用话语时间和空间,以达到能动地伸缩时空的艺术效果。《金锁记》中小说的叙事时序的时间错置,反映了七巧对往事生活的挥之不去和刻骨铭心的记忆。七巧的记忆过程就是对人编码、存储和提取过程,只有经过记忆深刻的时间在编码的信息过程中才能被记住。张爱玲选取七巧人生中最关键的信息进行编码、加工和改造的过程,使七巧的命运在叙事的表达效果上令人扼腕、令人叹息。
第二,叙事时频的使用。叙事时频的使用主要是形成时空的反复。频率实际上涉及的是“一个事件在故事中的次数与该事件出现在文本中的叙述(或提及)次数之间的关系”,[2](P18)时频在小说中可以反映作者创作的主次,时频在小说中主要表现为:单一频率(即讲述一次发生了一次的事件)、重复频率(即讲述数次只发生了一次的事件)、概述叙述(即指讲述一次发生数次的事件)。张爱玲在叙述一般的事件时,往往使用的是单一频率,而重大事件时,使用的是反复频率,如在《金锁记》中“哭声”非常多,故事中的女性几乎都哭过,而且贯穿整个文章的基调是哭泣。曹七巧、长安、芝寿、云泽都哭过,有的大声,有的小声,有的无声,构成了一曲哭声的交响曲。而小说中的优美的口琴声所形成的主旋律,也往往是在美好的事情即将逝去时回想起来的:一次是长安辞别学校的时候,独自偷偷吹响了口风琴:“‘Long,Long,Ago’的细小的调子在庞大的夜里袅袅漾开。”唯美地渲染了长安辞别学校美好生活时的怅惘和寂寥。一次是长安与童世舫结束爱情的时候:“长安悠悠忽忽听见了口琴的声音,迟钝地吹出了‘Long,Long,Ago’。”口琴声生动地抒发了长安对爱情的向往以及爱情离去时的依依不舍,呈现出优美逝去的感伤的情怀。这种频率的变化增加对女性生存空间的不同层次的认知,通过反复感知和认识,使女性哭诉和哭泣的生存状态的通过反反复复的强调和凸显,使“哭怨”的主题和原因得以实现,从而达到更大的时空涵盖和价值涵盖。而张爱玲在小说主题的重复上更是令人惊奇,如《半生缘》结尾就是对《十八春》的重写,致使两个文本叙述的苦难本质发生扭转。而两个文本均显示出对《普汉先生》的颠覆性重构,是同一故事的两种变奏。这种重复的书写暗示张爱玲五十年代采取的对抗、妥协双重叙事策略以及六十年代对自身创作立场的重申和回归。[3]而《金锁记》和《怨妇》的互文和重复书写重叠也展现了张爱玲对立场的回归和反复吟唱。
第三,叙事时距的使用。叙事时距利用的是故事实际延续的时间和叙述它们的文本长度之间的关系,张爱玲在作品中通过对不同叙事时距的灵活处理,得以呈现爱的短暂和悲哀等情感重心。张爱玲在小说中充分使用的时距包括省略、延缓、停顿、加速、减速和匀速等时距手段,在非关键处采用省略叙事(叙事篇幅很少)、在心理冲突处减缓和停顿叙事(叙述篇幅很多)、在高潮升华处停止叙事(叙述篇幅停止),时距处理堪称完美,省略、加速、减速、停顿、匀速等的变化使用和灵活组合使张爱玲的作品充满了跳跃和音乐般的旋律。在《金锁记》中曹七巧的一生,张爱玲主要采用场景叙事手段主要描写了几个场景:丫鬟凤箫和小双的夜间谈话侧面叙述了七巧嫁进姜家的过程;七巧给老太太请安的场景交代朱口细牙的七巧的为人和在姜家不被瞧起的卑微地位;与季泽的谈话场景表达了对病怏怏的丈夫的无奈和对青春活力的季泽的渴望;曹家舅爷探亲场景折射出她满腔幽恨、被欺负、被压抑的生活状态以及她嫁进姜家之后性格上的暴躁和疯疯傻傻的变化,等等。这种对场景的叙事交代了曹七巧的出身、性格、家庭地位及被扭曲变态的行为,解读了曹七巧一点点走向黑暗无望的生活的过程。张爱玲为刻画曹七巧等待爱情的焦虑与渴望以及她的渴望破灭后的心情,便对这些等待和破灭的故事时间在话语时间的时距上拉得很长,使话语时间明显远远大于故事时间,甚至在关键处和冲突处采取停顿叙述且精心刻画,在季泽的离去七巧的爱情破灭的高潮处戛然而止,使文本形成了一首流淌着、奔涌着的美丽的诗。然而对曹七巧其他生活的表现则采用了略写或概述的叙事时间手段,用笔省之又省。这种省略性叙事手段使文本情节快速推进,读者阅读时也是一晃而过,这一长一短就造成了阅读时的节奏感。从这种阅读的节奏感中读者也可以明显感受到张爱玲对女主人公的曹七巧女性生存境况和情感生活的关注和同情。
二、张爱玲小说时间的其他张力
本文在使用“故事时间”和“话语时间”的差异分析张爱玲的作品时,发现所展现的时空上的时间错乱、时间倒置、时间拼贴等,对于反映了张爱玲的独特的思维方式和心理体验,以及揭示女性的现实真相和人生遭际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同时,我们还会发现在张爱玲的作品中还展示了几组时间上的二元对立,故事正是在这几种张力中得以展示和刻画。时间意识既表现在表层结构上,又深植入深层结构里,表层的为显性时间,深层的为隐性时间,常常体现的是人与人或者人与社会之间的关系。这些二元对立形成的张力,对于张爱玲展现其艺术才华起着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
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之间的对立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展示了无穷的魅力,两种时间所形成的差异充分展示生活的感受和体验。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心理时间和现实时间往往是不同拍的,心理时间可以慢于实际的时间,如《倾城之恋》中白公馆的时间是十点钟而人家的时间是十一点,跟不上生命的节奏。心理感受的时间可以长于实际的时间,如《封锁》中的时间:对于整个上海来说,只是打了个盹,但对于宗桢和翠远来说却在这短暂的时间中经历了陌生—熟悉—恋爱—谈婚论嫁等人生中非常重要的阶段。心理感受的时间也可以短于实际的时间,如《半生缘》中描述沈世钧和顾曼桢相遇时的感慨,时间对于中年人,十年八年就像弹指间。对于年轻人,三年五载就是一生。也可以是现实的时间和心理感受的时间相吻合。如《爱》中“于千万人之中,遇见你要遇见的人。于千万年之中,时间无涯的荒野里,没有早一步,也没有迟一步,遇上了也只能轻轻地说一句:你也在这里吗?”这种心理时间和现实时间相和谐、相同一的时间是人生中最完美的时间。心理时间也可以停止不动,如《小团圆》中的“雨声潺潺,像住在溪边。宁愿天天下雨,以为你是因为下雨不来。”虽然物理现实时间在发生变化,但是对于心理来说还是希望时间没有发生变化。同一个现实时间可以生成不同的心理时间,如《红玫瑰与白玫瑰》中当振保和娇蕊要分手的时候,用钟摆来形容,虽然是同一个时间,却走着不同的路。长的现实时间变成短的描述时间。《花凋》墓碑上关于川嫦短短21岁生命的过程只进行了短暂的描写,只述说了川嫦一生中两个典型事迹——19岁毕业于宏济女中,21岁死于肺病。这些现实时间和心理时间呈现出的不同,具体来说表现为荒诞、滑稽的特点。张爱玲通过物理时间和心理时间之间的差异和对立,力图营造的是生命个体在历史的潮流中的深切的感受和体验,将物理时间在时间表达上加以逆向性或者差异性地分割、截取和组织,在“变异的、片段的、感受的”的心理时间上进行叙事和表达,充分传达出个体生存状态的差异和变异,从而表达了无法摆脱的苍凉感。这种心理时间的解构和建构,传达的是被压抑的复杂人性,揭示的是被隐埋于历史文本中的真实的人性,展现了人的生活核心精神和价值以及人的存在价值。
(二)个体时间和集体时间
个体时间和集体时间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充满着张力。集体性的时间,是有刻度的、不断流动的日常时间;个体时间是个体化了的时间,可以是停滞不前的,也可以是快速流动的,在没有时钟刻度感受时间刻度的时间完全取决于个体的感受。张爱玲对于两个时间的张力的充分利用,展示了人生是一袭华丽的袍子,里面爬满了虱子的荒芜的主题。对于叙事时间来说,通常故事的物理时间往往体现的是集体时间,而话语时间往往体现的是个体时间。故事时间是集体时间,体现的是一个国家和一个民族的历史的记忆。在张爱玲的小说中,底调是现实中的实际时间,这是小说叙事的基础,是故事开展的先决条件。个体时间是伴随着时代的背景和时代的信息的,个体的命运潜含着时代对人生的影响和作用,深刻理解集体时间可以深化对作品的理解。张爱玲生活的集体时间正是上海沦陷丧失主体和话语权的时代,也是一个主流话语暂时被悬置的空白时期,西方文化和古老中国思想冲撞,各种力量相互纠缠渗透,人们急于接受西方文明而又一时无法摆脱旧时陈旧观念束缚。在这个特殊历史时期,有着清醒而明晰认识的张爱玲,在小说中展现的是个体感受的时间,是对于时间和时代的个体感受。这种感受是独到和深刻的。个体时间所体现的这一深刻的生命体验形式,在张爱玲的潜意识中和小说的叙事中得到了尽情的发挥,凝聚了作家对世界、对人生、对生命的观照和感悟,是非常富有创造力的。《茉莉香片》中张爱玲在开篇就这段上海传奇的时间感受给定了苦的基调,华美而悲哀的香港就如沏好的茉莉香片茶一样的苦。而在小说中张爱玲则进一步介绍了这种时间的个体感受:“他们初从上海搬来的时候,满院子的花木。没两三年的工夫,枯的枯,死的死,砍掉的砍掉,太阳光晒着,满眼的荒凉。”《小艾》中的开篇的时间感受也是荒凉的:“下午的阳光照到一座红砖老式洋楼上。一只黄蜂被太阳照成金黄色,在那黑洞洞的窗前飞过。一切寂静无声。”展现了空洞、无聊、静止、暗淡的个体时间感受。张爱玲的个体时间是凝滞性、虚无的、荒芜的、瞬时性和象征性的。
(三)过去时间、现在时间和未来时间
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的记忆碎片,构成一段珍珠般的记忆。张爱玲的小说在过去时间和现在时间或未来的时间交替出现,这样的叙事表达有什么意义和价值呢?在时间的长河中“过去”与“现在”是既相互分离而又相互统一的,“过去”和“表现”为两种文化观念、价值趋向、审美情调等等的差异和对比,正是“现在”与“过去”的对话,构成叙事结构。“时间实际上是人的积极存在,它不仅是人的生命的尺度,而且是人的发展的空间。”[4](P532)这也就意味着时间结构就是人的存在方式,是生命成长的迹线。
张爱玲在过去的时间中与自己的以往进行对话,反思和窥视人物的成长和历史。利用“过去时”与“过去完成时”的组合,采取对过去的反思。《金锁记》中七巧回忆自己的过去那段很值得反思。“七巧立在房里……从前的事又回来了:临着碎石子街的馨香的麻油店……朝禄赶着叫她曹大姑娘。……她皱紧了眉毛。床上睡着的她的丈夫,那没有生命的肉体……”张爱玲在这段把人物从过去的时间更遥远的时间“过去的过去”,然后小说又从“过去的过去”拉回到过去,在闪回的镜头中,将时间进行不同的切割和重新组合,在主观视点和客观视点之间进行交叉组合,在重新组合的画面中,展示了七巧的主观灵魂的渴望与客观现实的不可能之间的矛盾,七巧年轻时的美好和目前不堪入目的状况形成对比。在回忆、梦境、想象、遐想、思索、潜意识中展现了曹七巧的心理成长过程。时间在七巧身上是重叠、交错的,既可以超前又可以倒流的。七巧都是以成熟、反思、忏悔或怀旧的眼光来“刷新”自己的记忆,而七巧的性格中多面的、矛盾的、复杂的等诸多层面的特性恰恰是随着时间向度的转换慢慢呈现的,时间关系或叙事结构的人物性格的内部的深层关系与社会的关系也得以展现。
过去和过去将来式的对话。过去将来式往往展示的是过去对未来的希望。《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罗杰与愫细举行婚礼时,罗杰产生了幸福的幻想,他梦见愫细在五彩缤纷的世界里变成了玫瑰色、蓝色和火红色。罗杰新婚的喜悦通过梦幻般的色彩被描写体现出来。“过去”与“过去的未来”的对话显性地表现在时间结构中,深层实际上体现的是人与人之间的人性结构关系,是一种意义关系。罗杰婚礼上对婚后美好生活的畅想,为后来愫细结婚当夜逃跑、罗杰离开学校、罗杰选择自杀等事件埋下了伏笔。张爱玲的小说就是通过书写“过去”来思考“现在”与“未来”,通过书写未来的美好来对比现实的不如意,来映照未来的理想与残酷的现实之间的不同一,以及自我与存在之间的关系,从而阐释人格分裂的原因。
张爱玲的过去、现在和未来在深层结构有着相同的内涵。《金锁记》中的“过去”对于七巧来说,是青春、活力、爱情、温馨和美好,“现实”对于七巧来说是苍老、病态、无爱、苍凉和安然。“未来”对于七巧来说,是无望。《沉香屑第二炉香》中的“过去”是罗杰爱愫细但是蜜秋儿太太故意不对愫细进行性教育,“现在”是愫细结婚当晚逃跑、罗杰失去了名誉、全香港的人都觉得罗杰是个性暴力者。“未来”也是无望的。所以在张爱玲的小说中,过去—现在—未来之间是有着内涵式的深层结构的,就是“过去”还是美好的,“现在”是残酷的,“未来”是无望的。时间与自我认知密不可分,自我是时间的持续存在,也是时间发生发展的过程。人们对自我存在的反思和探索是无穷无尽的。[5]自我存在于当下的同时,也会回顾过去和展望未来,研究时间维度上的自我有利于揭示自我的本质。过去、现在和将来的认知和态度会影响到心理健康和幸福感。[6]
三、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之间的转换
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是可以转化的。巴赫金这样写道:“在文学中的艺术时空体里,空间和时间标志融合在一个被认识了的具体的整体中。时间在这里浓缩、凝聚,变成艺术上可见的东西;空间则趋向紧张,被卷入时间、情节、历史的运动之中。时间的标志要展现在空间里,而空间则要通过时间来理解和衡量。这种不同系列的交叉和不同标志的融合,正是艺术时空体的特征所在。”[7](P274)罗曼·英伽登认为:“文学作品实际上拥有‘两个维度’:在一个维度中所有层次的总体贮存同时开展,在第二个维度中各部分相继开展。”[8]艾略特、庞德、乔伊斯和普鲁斯特等在研究叙事学时说,作品可以看作是“空间的”,它们用“同在性”取代“顺序”。试图通过“并置”来打破叙事时间顺序,使文学取得空间上的展示,使文学从空间上的理解代替时间顺序上的理解。弗兰克从叙事的三个侧面,即语言的空间形式、故事的物理空间和读者的心理空间分析了现代小说中的空间形式。[9]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中提出了“社会空间”的概念。他将空间分为三种:物理空间(自然)、心理空间(空间的话语建构)和社会空间(体验的、生活的空间)。[10]这些理论对于探讨叙事时间和叙事空间之间的转化具有非常重要的意义和价值。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封锁》可以说是时空转换的典范。《封锁》讲的是在上海的电车上,因突然发生的封锁事件,而使两个本不相干的人发生了爱情,但是伴随着封锁的解除,一切又都结束了。在《封锁》里,张爱玲把时间封锁起来,人为地让时间停滞或延长。小说故事发生的现实时间都很短,从封锁开始到封锁结束,也就相当于上海打了个盹的时间,但是小说充分地对物理空间、心理空间和社会空间进行时空转化,留给读者无限回味和余音绕梁的感受却是无限长的;在时间上做停顿叙事,通常小说的叙事策略有两种,一种是在空间上无限展开,一种是将瞬间的时间无限制地放大。
在瞬间的时间叙事上通过无限的物理空间叙事进行转换,从而使叙事时间无限扩大,这是张爱玲经常使用的办法。《封锁》刚开始时摇铃声实际上是一个短暂的时间段,只几下,“叮玲玲玲玲玲”,瞬间发生的事情,但是张爱玲却将每一个铃声都放大,切断了时间与空间,并在时间进行减速和延迟,在空间上进行扩展和延伸。这里作者巧妙地将细微空间无限放大,从而使时间无限制地放大。
瞬间的时间用社会空间进行多视角的并置来展示和刻画。《封锁》在一瞬间描写社会空间的种种人生百态:讨饭的山东乞丐、人事复杂的公事房里的办事员、为钱所困的中年夫妇、为了买到便宜包子不惜穿街走巷的银行的会计师、被逼急于结婚的女教员、孜孜修改一张人体骨骼的简图的医科学生,张爱玲通过将这些人物的并置,写出时代下人们窘困的生活状态,像一幅画面照出众生像,在时代的潮流下,虽然事事不如意,但仍是像那个医科学生那样的热爱生活。并置的社会空间无限制地延展了瞬间的时间。
瞬间的时间用心理空间进行延伸和扩展。张爱玲的心理停顿空间描写拉长叙事的空间。《封锁》对翠远的脸进行了细节描写,如淡水画上的盛开的白描牡丹花,两三根吹乱的短发如风中的花蕊,细腻、精致、繁杂而有震撼力。这种停顿的叙事方式把小的空间无限地放大。另外通过有着大段的心理空间叙事,扩展瞬间的时间空间。宗桢和翠远恋爱时的心理叙事:恋爱的男女的言谈的不同,男的爱说,女的爱听。恋爱中的女人,她懂你,宽宥你,为你心酸,为你微笑,像那团“白、稀薄、温热、冬天呵出来的一口气”,她是你的一部分。大量的情话和心理感受填写着文本的书写空间,大篇幅的文本的书写,描写出了男女主人公突破了日常的烦琐后所获得的恋爱的喜悦和快乐,心理空间将叙事空间无限拉长和加大。
时间叙事和空间叙事实际上是物理时间和感知时间之间的转化问题。物理时间相对的是主观时间。物理时间是用钟表等计量的时间,是瞬间的连续,具有客观性、顺序性、线性和持续性。感知时间是个体对时间的感知和反映,是瞬间的感知和记忆,具有主观性、感知性、意识性、交错性、立体性和相断性的特点,是相对物理时间的。空间叙事反映的是“知觉到的现在”,也就是说物理上发生几个事件,当在心理上被感知时,有时可以同时发生,即相断事件知觉在瞬间心理时间上构成相对同时发生的。[11]这就是时间叙事转化成空间叙事的基础。
在张爱玲的作品中,特别擅于使用凝聚时间概念和空间概念的意象,从而形成时间和空间的交错转化。张爱玲将各种不调和的时间背景、时代气氛,硬生生地掺糅地放在一起,造成时间和空间的交融和对话,从而形成一种奇幻的景观。如《金锁记》中新式洋房的姜家:堆花红砖大柱、巍峨的拱门,木板铺地的楼上的阳台、黄杨木阑干、晾着笋干的大篾篓子,使充满着敝旧的太阳的时空在姜家交错。《倾城之恋》中的白公馆:顺着高高下下堆着一排书箱的墙、刻着绿泥款识的紫檀匣子、机栝早坏了且停了多年珐蓝自鸣钟、闪着金色寿字团花两旁垂着朱红对联的堂屋,使虚飘飘的不落实地的时空在白公馆交错。《沉香屑第一炉香》中的葛薇龙看到姑母家的建筑和陈设的时空感受更是绝妙。在这里是不同时空的交错,屋顶上盖了一层仿古的碧色而却又呈现出流线型的类似最摩登的电影院的白房子、鸡油黄嵌一道窄红边框的绿的玻璃窗、鸡油黄的漆安着雕花铁栅栏,陈列着翡翠鼻烟壶与象牙观音像的炉台、围着斑竹小屏风的沙发,这里既有中国的时间历史的沉淀,也有西方文明的历史的映照。这是一个充满着矛盾的时空交错的空间:有立体化的西式布置,也有中国化雅俗共赏的摆设,有中国的风韵但也有美国南部早期的遗风,呈现的是西方人心目中的荒诞、精巧、滑稽、非驴非马的中国。《小艾》中的寂静无声的老式洋楼上:有静止不变的光线很阴暗的红砖,被太阳照成金黄色的黄蜂。又如《倾城之恋》中咿咿呀呀拉着的胡琴、《封锁》中关于铃声、《金锁记》中酸梅汤等等的叙事策略,这些浓缩着时间烙印重新拼接在一起的事物,占据着空间,同时在空间上也刻着时间的烙印。张爱玲的老事物上凝聚着的是过去的岁月,呈现的是颓废、没落和异化的味道,凸显的是她的时间和空间意识,承载的是当下与过去的衔接和演绎。这些都成为对张爱玲小说叙事的经典。像《色戒》中雪白且白得耀眼的光芒四射闪耀的一只只钻戒,也像《沉香屑第二炉香》堆着几百年的书散发着书卷的寒香图书馆的黄昏的一角,也有像单调与无聊、千年如一日神仙的洞府的白公馆,它们身上散发着年月的光芒,衔接着过去与现在,沟通着时间和空间,“张爱玲运用意象描述,成功地在直线进行的当下时间里,保留给过去一些容身的空间”。[12]个体的叙事时间实际上是有着“存在的瞬间”的哲学的基础的。张爱玲是十分擅长在某个瞬间以存在为形式向世界展现自己的存在的,非常重视心灵空间时间的个体感受的,特别擅长将变化多端、不可名状、难以界定、解说的内在精神痕迹展现出来。
四、叙事时间的维度——世界时间、作品时间、作者时间和读者时间
在解读张爱玲的作品的时候要充分地注意作品中的时间维度对张爱玲作品解读的影响。每一件叙事作品或者“每一件艺术品总是涉及四个点”,即作品、作者、世界、读者,否则这件作品就不能被称为完整。[13]对于文学的时间来说,则包括作品时间、作者时间、世界时间、读者时间。作品时间指的是文学作品中所记录的时间。作者时间指的是作者创作的时间和完成的时间。世界时间指的是故事的物理时间,是时钟等记录下的特殊事件的客观发生的真实的时间。读者的时间是读者读到作品的时间,是读者依据自己的亲身经验对作品感受和重新阐释解读的时间。列斐伏尔在《空间的生产》一书中指出:我们关注的空间有物质、精神、社会三种。[14](P487~502)因此,联系上文提到的时间和空间作为二维向度上的共存和互依,即时空的存在理应亦有物质、精神和社会三种。而这三种时空关系正隐含在每个完整的叙事作品或艺术品所要涉及的作品、作家、世界和读者“四个点”里。也就是说,一个完整的作品必然包含由这“四个点”分别形成的时空层面。这四个层面相互交错、相互渗透、相互重叠,则在对一个成功的完美的叙事作品的完成、塑造中呈现出非常强的影响力。
张爱玲的《色戒》的不同纬度的时间的展示就非常值得我们反思。《色戒》曾经因为由李安导演的电影,掀起了又一股张爱玲的热潮。人们在此部小说或电影中最热衷的是郑苹如、张爱玲、王佳芝三个女人的虚构与现实之间的关系,这种现象就非常值得我们深思。《色戒》是根据郑苹如刺杀丁默?事件的故事改写的,张爱玲一写就写了30年,小说承载了张爱玲“此情可待成追忆,只是当时已惘然了”爱情的感悟。胡兰成和张爱玲、郑苹如和丁默村、易先生和王佳芝三对人物之间的情感故事更使得这部作品的不同故事事件原型主人公与文本中的主人公之间的关系呈现出少见的扑朔迷离关系。郑苹如刺杀丁默村事件发生的时间是1939年,这是《色戒》故事素材发生的时间。郑苹如为了民族大义,为了苦难的中国,欲刺杀丁默?而未成,1940年在上海从容地牺牲。胡兰成和张爱玲开始交往的时间是1944年,两个人因为《封锁》而结缘,张爱玲从尘埃里开出花来,因为懂得,所以慈悲,但最终却因为胡兰成的多情和好色,两个人的情感以1947年6月胡兰成收到了张爱玲的诀别信而结束。这两个真实的故事发生的时间是世界的时间。而胡兰成因为是故事的素材的讲述人和原型主人公之一,而使这部作品更是倍加有争议。而《色戒》构思于1953年,成文于1978年4月11日《中国时报》的人间副刊,这是《色戒》作品创作的时间,而且张爱玲创作此作品用了30年的时间。1983年收录在《惘然记》中说:因为这篇小说的取材的惊喜和震动,一晃就写了30年。张爱玲对原来的故事采用偷梁换柱和移花接木的手法,安全颠覆了原故事,刺丁案为她提供的只是一个故事时间框架,而《色戒》的故事却负载着张爱玲的人性理解以及对女性“唯情感最大”的爱情的深切感叹。2007年电影《色戒》的拍摄,则重新引起对张爱玲的作品的广泛关注,这是读者关注的时间。《色戒》之所以会在21世纪初,在小说创作完成30年以后的时间里才在大陆引起共鸣,这与当下的人文环境是相吻合的。《色戒》那纠缠不清的,那无法控制的真性情的流露和展现,与当下读者状况的感受是相一致的,从而引起了深深的共鸣。也就是说在小说《色戒》的兴衰和成败中,交织了几个层面时间叙事:作者叙事行为时间和故事发生实际时间之间的时空交错,作者叙事行为时间和作品所展现的时间之间的时空交错,作品所展示的时间和读者感受及解读行为时间之间的时空交错,正是这几个时间层面的相互映射和相互影响,使《色戒》展示了充分的艺术张力。
文学是一面镜子,反映社会存在。叙事时间用以描述事件之间的顺序,叙事的时间问题不仅是哲学领域,也是文学领域恒久的主题。在热奈特的叙事学里,时间叙事已经建立了一个相对比较成体系的理论,使用这个时间体系分析张爱玲的作品,可以使我们更深刻地透视出张爱玲作品的独特性以及张爱玲使用时间张力的独特技巧,但是叙事学的时间还有很多问题值得我们进一步探索。比如叙事时间的结构、叙事的时间纬度、叙事的时间和空间转化等等,叙事学的研究仍任重而道远。
[1]热拉尔·热奈特.叙事话语.新叙事话语[M].王文融,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0.
[2]谭君强.叙事理论与审美对话[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2.
[3]窦苗.《十八春》《半生缘》《普汉先生》的文本互涉——从苦难叙事角度看张爱玲的叙事策略[J].参花(下),2013,(9).
[4]马克思,恩格斯.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47卷)[M].中共中央马克思恩格斯列宁斯大林著作编译局,译.北京:人民出版社,1979.
[5]陈莹.时间自我:过去我、现在我和将来我的一致与不一致[D].重庆:西南大学,2008.
[6]罗扬眉.时间自我态度的外显和内隐测量[D].重庆:西南大学,2011.
[7]巴赫金.巴赫金全集(第三卷)[M].钱中文,等译.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1998.
[8]罗曼·英伽登.对文学的艺术作品的认识[M].陈燕谷,等译.北京:中国文联出版公司,1998.
[9]程锡麟.叙事理论的空间转向——叙事空间理论概述[J].江西社会科学,2007,(11).
[10]Henri Lefebvre.The Production of Space.Trans.by Donald Nicholson Smith.Oxford,UK:Basil Blackwell Ltd.,1991.
[11]心理时间[EB/DL].http://baike.so.com/doc/6294660.html
[12]王百玲.论张爱玲小说的叙事时间与叙事空间[D].兰州:西北师范大学,2005.
[13]M.H.艾布拉姆斯.镜与灯——浪漫主义文论及批评传统[M].郦稚牛,张照进,童庆生,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9.
[14]朱立元.当代西方文艺理论[M].上海:华东师范大学出版社,2005.
The Strategy and Dimension of Narrative Time——The Narrative Tim e of Eileen Chang
YANG Chun
(Editorial Department of the Academic Journal,ChinaWomen′s University,Beijing,100101,China)
Eileen Chang had a deep understanding and unique ability to control the narrative time and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narrative time and human beings.She couldmake full use of the difference and contrastbetween the story time and narrative time to achieve her expression in narrative themesof timeand life.Thenarrative time shows several groups of tension:the tensionsbe tween real time and psychological time,between individual time and collective time,and between past,present and future,which makes herworks full of charm.And there is free space-time transformation in her narratives.In addition,Eileen Chang′s narrative time has four dimensions:world time,works time,author time and reader time,which had exerted a profound impact on her works.
narrative time;narrative tension;space-time transformation;narrative dimension
I206
A 文章编号:1006-723X(2015)02-0120-07
〔责任编辑:黎 玫〕
杨 春,女,中华女子学院学报编辑部副教授,主要从事女性文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