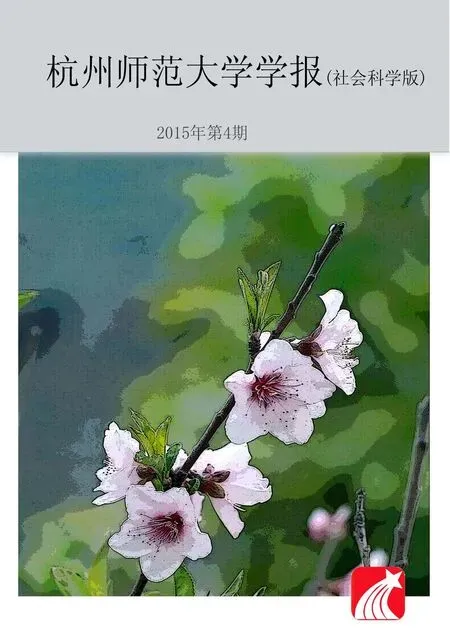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2015-02-25倪伟
倪 伟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新青年》时期钱玄同思想转变探因
倪伟
(复旦大学 中文系, 上海 200433)
摘要:在《新青年》倡导文学革命后,钱玄同迅速从原先的国粹主义立场转变为全盘的反传统主义。考察这一时期钱玄同的日记、书信和公开发表的文章,可以发现有三方面的原因推动他走向了激进的反传统主义,即他对今文经学古经辨伪之学的崇信,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兴趣,以及和鲁迅之间频繁而密切的思想交流。而在《新青年》同人的思想分歧公开化之后,尤其是在五四运动将政治革命提上议程之后,他出于对革命势将造成的破坏性后果的忧虑,又转向了保守的“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钱玄同前后思想的反复变化暴露了一种思想上的无根状态,这也是中国现代知识分子身上一种有代表性的精神特征。
关键词:钱玄同;《新青年》;新文化运动;无政府主义;今文经学
自1908年问学于章太炎后,钱玄同就成了一个头脑“比太炎先生还要顽固得多”的复古分子,不仅主张推翻满清以恢复汉族的文物制度,而且还认为应越过明朝和汉唐,“复于三代”。[1](P.113)他狂热地践行复古的主张,用小篆书写,行古代礼制,民初在浙江教育司供职时,还设计制作了一套深衣玄冠,穿戴着上班。[1](P.117)但胡适的《文学改良刍议》刚一发表,他却出乎意料地迅速响应,致书陈独秀,力挺文艺改良之议,并痛斥“选学”为妖孽,“桐城”是谬种。[2](P.1)作为国学大师章太炎的高足,钱玄同的反戈一击让陈独秀和胡适喜出望外。陈独秀恭维他:“以先生之声韵训诂学大家,而提倡通俗的新文学,何忧全国之不景从也。可为文学界浮一大白。”[3](P.296)尚在北美留学的胡适更是感到“受宠若惊”。[4](P.311)钱玄同从此变得十分活跃,不断在《新青年》“通信”栏发表长信,攻击包括古文、旧戏、儒道释乃至汉字在内的一切国粹,言辞之激烈令人侧目,他也藉此一跃成为《新青年》同人中举足轻重的人物。①在林纾的影射小说《荆生》中,浙人金心异(即钱玄同)与皖人田其美(陈独秀)、狄莫(胡适)三人放言欲力掊孔子,却为“伟丈夫”荆生所殴。钱与陈、胡二人并列,足见其影响之大。周作人认为《新青年》“毁灭古旧的偶像”的论调虽由胡适之、陈独秀首倡,但钱玄同“继之而起,最为激烈,有青出于蓝之概”。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文史资料选辑(合订本)》第32卷第94辑,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年,第94页。
钱玄同何以会从狂热的国粹主义转到全盘反传统的立场上?钱玄同自述是因受袁世凯复辟帝制之刺激:“自洪宪纪元,始如一个响霹雳震醒迷梦,始知国粹之万不可保存。”[5](P.281)②在1919年1月1日的日记中,钱玄同回顾说:“因为袁世凯造反做皇帝,并且议甚么郊庙的制度,于是复古思想为之大变”,“于是渐渐主张白话作文”,又“始知孔氏之道断断不适用二十世纪共和时代,而废汉文等等思想发生”。《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年,第336-337页。对这种说法很多人都深信不疑。周作人晚年谈到钱玄同,也认为是“民国初年的政教反动的空气”促使其转向了反复古。1915年的洪宪帝制和1917年的张勋复辟,“这两件事情的轰击”,使得“所有复古的空气乃全然归于消灭,结果发生了反复古”。[6](P.93)但事情似乎并不那么简单。
1914年9月28日,袁世凯率百官祭孔,意在为复辟帝制预演。钱玄同对此意兴甚浓,不仅索取了一本祭祀冠服图,还在日记中称“所定斟酌古今,虽未尽善,而较之用欧洲大礼服而犹愈乎!”[7](P.275)对袁氏遵行古礼似不无赞赏之意。1915年12月12日,袁世凯接受劝进正式登基,改国号为“中华帝国”,令人意外的是钱玄同日记中并无关于此事的记载。1916年元旦那天,钱玄同在马幼渔处见到官报,“乃知自今日始改称中华帝国洪宪元年,是民国历数尽于昨日。”下午他照常游玩中央公园并参观古物陈列所,晚上点阅廖平的《群经凡例》。[7](P.282)当天的日记语气平静,看不出他有多么愤怒。此后三天的日记均是读经论古,无一字提及袁氏称帝。1月5日日记中他又重弹用孔子纪年的老调,嘲笑“光复之后,浅人皆用民国前几年……至今则民国已成前代,吾不知彼等又将创为何种纪年?将曰帝国前几年乎?则自黄帝以迄清宣统四千余年中间,惟周称王,余悉帝国也。将称洪宪前几年乎?则洪宪之名,正如明之洪武,清之顺治,及日本之明治……”[7](PP.283-284)言语中既无亡民国的哀痛,亦无对袁氏倒行逆施的愤怒。
读他当时的日记,你的确感受不到袁氏复辟给他的刺激有多么强烈。印象更深的倒是他因个人生活不顺而不断发出的怨叹。1913年9月,他就任北京高等师范学校历史地理部及附属中学国文、经学教员,本想等来年秋天“收入稍丰”,接家眷来京,“不料为忌者排挤”,“所入不及百金”。同门马幼渔遂将自己的中学课程相让,但这样钱玄同每周的课时量就达到了19小时。[7](P.273)1915年后,他又兼任北京大学文字学教授,课时量更增加到每周27小时。[7](P.299)几乎每天都要上四五个小时的课,自然是劳顿不堪,他日记中便常有“甚惫”或“惫甚”的感叹。更不幸的是,家眷北来之后,病患不断,大人、孩子均先后染上白喉、猩红热等时疫,四子秉东夭折。在1917年1月8日日记中,他哀叹:“三月以来,心绪恶劣,至今尤不许我开展,且我自身亦难保此后竟不传染,思至此,愈觉闷闷不乐。”[7](P.300)没过几天,他家中又发生煤气中毒,“家中上下,人人患病”,三子秉弘和一女仆“人事不知,几濒于死”。[7](P.301)阖家诸般不顺,他心绪之恶劣可想而知。在1917年1月的日记中,他不断说些“人极无憀”(1月1日、23日、25日)或“余极无聊”(1月11日)之类的话,甚至对于平时所喜爱的逛厂甸这等乐事也“殊无兴趣”。[7](P.305)在1月13日的日记中他更声称“入都三年,心绪恶劣者三年”。[7](P.301)然而,正是在他最感侘傺无憀的时候,他却突然爆发了,在1917年2月1日出版的《新青年》第2卷第6号上发表了火力十足的第一篇“通信”。因为生活不顺利而淤积的愤懑和怨怼,似乎全都借此得到了宣泄。
转宗今文经学
钱玄同激烈地反传统当然不可能只是为了消个人胸中块垒,态度的转变必定有着内在的思想动因。读他1914年后的日记,不难发现其间的草蛇灰线。
1914年2月,钱玄同尊今文经学大师崔适为师,“以札问安”,自称“弟子”。[8](P.134)崔适的《春秋复始》、廖平的《群经凡例》等今文经学家的著作从此成为他日常研读的案头书。章太炎专宗古文,钱玄同却“‘背师’而宗今文家言”[9](P.225),其间暗含着什么消息呢?今文经学尊今抑古,探求先圣之微言大义,强调要经世致用,至廖平、康有为辈出,遂有孔子托古改制之说,这对于长期受经义束缚的中国读书人来说不啻是一种思想解放。今文经学家通过考据辨伪疑古的手段,对钱玄同震动极大,他自此笃信古文经乃为刘歆伪造。连千百年来士人奉若神明的古文经也因有作伪迹象而变得不可信,那“史”、“子”、“集”中的书就更不可信了。既然传统典籍皆不足征信,那么载于典册的古代思想和礼法当然也都不足信了。“古”已不真,还怎么复古呢?今文经学的辨伪之学因而从根本上动摇了钱玄同复古思想的根基。1917年后,钱玄同思想更趋激进,不仅视一切古文经为伪造,还进而“打破‘家法’观念,觉得‘今文家言’什九都不足信”[9](P.225)。此时适逢《新青年》举起反传统的旗帜,风云际会,他也便因疑古而转向了激烈的反传统。
美国汉学家艾尔曼在其关于清代常州今文学派的研究中指出:在中华帝国晚期,“经学研究被作为一种系统化的政治话语,成为一种为国家特权合法性辩护的具有意识形态封闭性、排他性的系统”[10](P.223),而今文经学则“代表着一个充满政治、社会、经济动乱的时代的新信仰,它倡导经世致用和必要的变革”,今文经学家们“求助于古典的重构来为现代授权,为将来立法”。[10](P.225)在此意义上,今文经学与其说是一套学术话语,不如说是在中华帝国晚期危机深重的时刻应运而生的一套新的政治话语,尽管它仍须以经学研究的面目出现,以谋求一种政治合法性。常州学派的庄存与、刘逢禄,以及后来的魏源、龚自珍和康有为,都十分强调经学经世致用的性质,对于他们来说,经学首先是可以用来变革社会的政治工具,而不是考据、辨伪之学。康有为提出“托古改制”的口号,更明确地表达了藉经学以变法的意图。钱玄同对今文经学的这一精神传统似乎缺乏认识,他对今文经学的兴趣几乎完全是知识性和学术性的。他非常推崇康有为的《新学伪经考》,赞其考证、辨伪的功夫都极精审,采用的正是“科学的方法”。[8](P.138)至于颇受非议的康有为“托古改制”的经说,他以为应与考证“分别评价”,《新学伪经考》在考证学上的价值,决不会因经说之是非而有增损。在他看来,“今文古文之不同,最重要的是篇卷之多少,次则文字之差异;至于经说,虽有种种异义,其实是不值得注意的。”[8](P.211)重考辨而轻经说,对今文经学家立论的方式及背后的问题意识更不加措意,这恰恰暴露了他思想上的短视:只能见其表而不能究其里。他一生思想多变,屡次翻转立场,即缘于这种缺乏思想根基的短视。
今文经学对古经的辨伪仍然是在儒学的政治框架内进行的,希望通过对经典的批判性清理和重构来激发儒家传统思想所固有的政治活力。今文经学家们始终相信儒家思想即使在当代社会中也仍然有着经世致用的价值。“对于他们来说,儒学仍是新的信仰和政治行为模式的起点和毋庸置疑的内容。”[10](P.226)今文经学对古经的辨伪与对儒学思想的全盘质疑完全是两回事,承认古文经有伪造的痕迹,决不等于说它们所阐述的儒家学说本身也因而丧失了其全部的正当性和合法性。然而钱玄同的逻辑却是:既然“经”是伪造的,那么“‘经’这样东西压根儿就是没有的,‘经’既没有,则所谓‘微言大义’也者自然是‘皮之不存,毛将焉附?’了”。[11](P.261)他据此认为“‘六经’的大部分固无信史的价值,亦无哲理和政论的价值”。[12](P.238)这种逻辑放在今天来看,自然是荒谬的,但在当时却的确为他转向全盘的非孔和反传统提供了知识的和思想的依据。
没有根基的无政府主义
在转宗今文经学后,钱玄同又对无政府主义重新产生了兴趣。早在东京求学时,他就曾受张继、刘师培的影响,一度信奉无政府主义,多次参加刘、张二人创办的社会主义讲习会。他曾与人激辩无政府主义有无实行之可能,认为断言无政府主义决不能实行,盖因误以为“无政府时代之制度与今制同”。[7](P.117)换句话说,就是决不能以今天的情势来推断将来,否定未来之可能性。他后来说服鲁迅起而呐喊,靠的也是这一逻辑。鲁迅认定“铁屋子”万难破毁,启蒙者的呼喊只能使少数被惊醒的人忍受“无可挽救的临终的苦楚”,钱玄同却相信既然有几个人起来,就不能说决无毁坏这铁屋子的希望。
在东京的时候,钱玄同尽管对当时无政府主义的两大重镇《新世纪》和《天义报》都有所不满*他认为《新世纪》那群人“学识太浅,而东方之学尤所未悉,故总有不衷于事实之处”(《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106页),且“每有不轨于理之言”。(同上,第105页)他更不能接受《新世纪》所提出的废除汉字、推广万国新语(世界语)的主张,曾大骂奏请废汉文、用“通字”的法部主事江某以及提倡用简体字的王照等为王八蛋(同上,第141页)。他虽然佩服刘师培“中国学问深邃”,但对刘“总主张进步说,因甚以《新世纪》为是,又谓世界语言必可统一云云”也颇为不满,认为其实在“难化”。(同上,第134页),但还是非常热心地阅读无政府主义的报刊。他对《新世纪》也不乏赞誉,认为它“打破阶级社会,破坏一切,固亦大有识见”[7](P.105);“要之大辂椎轮,于现今黑暗世界中不得谓非一线之光明也。”[7](P.106)无政府主义吸引他的究竟是什么呢?首先是无政府主义“排斥强权”的主张。他认为晚清以来国人崇拜功利之心日炽,认强权为文明,提倡无政府主义则能破此劣根性。[7](PP.114-116)他在1908年2月23日的日记中记录了刘师培在社会主义讲习会上的发言,刘批评了当时国内盛行的立宪论,嘲讽“功利主义之《天演论》几为家弦户诵之教科书。凡编教科书者皆以富强功利等说为主干”,无政府主义则正能“药其毒”。[7](P.117)他赞同刘师培的这一说法。其次是无政府主义的平等观。在他看来,无政府主义主张“人人平等,人人受同等之教育”,可以弥补因体格强弱和受教育程度差异而产生的不平等。[7](P.117)再次是无政府主义非功利的自我观。1908年2月28日的日记记载了他伦理课考试的答题内容:个人“对身体之义务无他,即求学以改良社会,使人道进化,非为祖国、功名利禄、一己之私等”,“今之伦理学,皆偏重个人(自私自利)、国家(强权功利)伦理,此极不然(反于进化)”。个人的自私自利和帝国主义的兴起其实有着内在一致的逻辑,“有自私自利心,而帝国主义乃兴”。“二十世纪之时代宜求社会的平民教育,如孔、孟之徒应排斥务尽,以绝忠君爱国之念。”尽管这些观点“皆捡《新世纪》之唾余”,“尚非尽善”,[7](PP.118-119)但他基本上还是认同的。上述三条,无论是非功利、反强权,还是人人平等、自我进化、趋于完善,其实都能在章太炎的思想中找到相应的论述。《五无论》《四惑论》《国家论》诸篇就阐发了无国家、有种族、非功利、否进化等观点,它们与无政府主义的确有着诸多相合之处。既然太炎先生的思想已大体包含有无政府主义的一些令人心动的议题,钱玄同自然就无需旁求了。这可能是他在1909年后不再谈论无政府主义的主要原因所在,而未必如其所言,是因为刘师培回国降了端方*在1917年9月12日的日记中,钱玄同称:刘师培归降,留日学生中的同盟会员皆以此为口实而诋毁无政府主义,他遂因此“亦渐渐不谈”无政府主义。《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315页。。
大约在1916年秋天,钱玄同又突然对无政府主义产生了浓厚兴趣。9月18日他“收到区佩刚寄来Anar之文印刷小册四种”,第二天又“寄书上海,购Anarismo书报数种”。9月20日,他购墨盒一,上镌“玄同”二字,[7](P.291)自此启用“钱玄同”之名。回到无政府主义,这和他复古思想的破灭直接相关。他在1917年1月11日日记中说:自己“自受洪宪天子之教训以来,弃保存国粹之心理已有大半年矣。今日思之,《新世纪》之报,即为吾国言Anarismo之元祖,且其主张新真理,针砭旧恶俗,实为一极有价值之报”[7](P.300)。他托蔡元培搜购《新世纪》旧刊,就是想从中寻找新的资源,以填补国粹主义破灭后的思想空虚。1916年10月4日的日记记载了他关于“毁家”的思考:“吾谓苟不毁家,人世快乐必不能遂,若谓毁家之后即视父母兄弟如路人,则尤为谬见,破坏家族正是兼爱之故,方欲不独亲其亲,子其子……”[7](P.293)这完全是复述了《新世纪》关于家庭革命的观点。*褚民谊在《普及革命》(《新世纪》第15、17、18、20、23期连载)一文中指出:“亲疏由于有家族,家族由于有男女配合而成,故欲破亲疏之习惯,必自破家庭始。欲破家庭,必自废婚姻始。婚姻既废,家族不得成,始人各无自私自利心。无亲无疏,互相扶助,四海一家,天下大同。无君臣、父子、夫妇、昆弟之别,只有朋友之爱,爱以是为博。”见张枬、王忍之编《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时论选集》第二卷下册,三联书店,1960年,第1038页。
事实上,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发表的激进言论基本都没有越出《新世纪》当年所讨论的议题。作为音韵文字学专家,他最关注的当然还是语言文字问题。他认为中国文字乃是“象形文字之末流,不足与欧西诸国之拼音文字立于同等之地位”,“断非新时代所适用”[13](P.99),因此主张应废汉文而用世界语。这是照搬了吴稚晖等人在《新世纪》上所发表的采用万国新语(即世界语)的言论。当年章太炎对《新世纪》认汉字为“野蛮之符号”一说曾大加痛诋,作《驳中国用万国新语说》力辩汉字之优长,并强调语言文字关乎历史文化传承,若盲目崇拜欧洲,欲废本国文字“以逐文明”,则会适得其反,“得其最野者”。[14](P.369)在这场笔仗中,钱玄同当然是站在老师这边的。他在1908年4月28日日记中说:《新世纪》“复有创中国新语者,其编造之字身、句身,以知字能识万国新语为目的”,此举不仅可笑,实乃发疯。[7](P.130)在9月27日日记中,还大骂奏请废汉文、用“通字”的法部主事江某以及提倡用简体字的王照等为王八蛋。[7](P.141)1910年,钱玄同协助章太炎创办《教育今语杂志》时,更明确宣称:“夫文字者,国民之表旗,此而拨弃,是自亡其国也。”[15](P.313)然而想不到的是,没过几年,他的态度就来了一个彻底的翻转,宣称“欲使中国不亡,欲使中国民族为二十世纪文明之民族,必以废孔学、灭道教为根本之解决,而废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汉文,尤为根本解决之根本解决。”[16](PP.166-167)昔日视汉文为民族文化精魂所在,今则视之如毒瘤,必欲去之而后快,只因他对汉文所承载的文化传统的看法发生了变化。既然汉文过去之历史,“千分之九百九十九为记载孔门学说及道教妖言之记号”,[16](P.166)那么要铲除孔教、道教的妖言,最彻底的解决办法就是将其载体汉字一并连根拔去。
对中国思想文化的全盘否定是钱玄同主张废汉文的思想前提。他认为,“二千年来用汉字写的书籍,无论哪一部,打开一看,不到半页,必有发昏做梦的话。”“经”是“教忠教孝之书”,“史”“不是大民贼的家谱,就是小民贼杀人放火的账簿”,“子”和“集”“大多数都是些‘王道圣功’、‘文以载道’的妄谈”。[16](P.163)总之,两千年的中国思想传统宣扬的不是“奴隶道德”就是“野蛮思想”,只能令人发昏。然而,他的全盘反传统却基本只停留在笼统而又僵硬的立场上,没有对中国文化传统中的一些基本的思想命题或价值准则作深入的批判性分析,所以其激进言论虽然有助于扩大新文化运动的影响,但在思想文化的推进方面却鲜有建设性的成绩。同样是激烈的反传统主义者,陈独秀的思想出发点不是无政府主义,他对传统思想文化的全盘性批判,是在个人主义的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中展开的,这种批判始终和他的政治革命理想联系在一起,并且最终从文化批判走向了政治行动。在鲁迅那里,这种个人主义伦理观与民族主义目标的张力同样也是存在的,只不过他不像陈独秀那样深信单单依靠政治革命就能从根本上改造社会。鲁迅对传统的看法无疑是更为复杂、更为幽暗的。
和陈独秀、鲁迅相比,钱玄同的反传统言论由于没有深刻的思想根基,不免有点肤浅,在思想的深度和论述的水平上都没能超越十年前的《新世纪》派。鲁迅曾评价钱玄同的文章“颇汪洋,而少含蓄,使读者览之了然,无所疑惑,故于表白意见,反为相宜,效力亦复很大”。[17](P.47)所谓“少含蓄”,根本是缘于思虑不深,或者观点竟非己出,只满足于表明立场,却不能看到问题对象的复杂性。
鲁迅的影响
在《呐喊·自序》里,鲁迅生动地记录了钱玄同为《新青年》向他约稿的情景,并委婉地表达了他们对启蒙事业的不同看法。在东京时两人同为章太炎门下,后来在北京亦不乏见面的机会,但多数是师门聚会*钱玄同在1915年1月31日、2月14日日记中均提到章门宴师会,这两次聚会鲁迅都参加了。《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第279、281页。,私下交往并不多*查鲁迅日记,在1917年8月以前,他与钱玄同见面次数不多,多是在朋友家偶遇或是朋友聚餐时碰见,偶尔也有书信往来。分别见1914年1月31日、6月13日、9月27日、12月31日以及1915年2月14日、3月8日、4月10日、6月20日、6月24日日记。另据周作人回忆,鲁迅和钱玄同在张勋复辟前“相见只有关于师友的事情可谈,否则骂一般士大夫的不通,没有多大兴趣,来往因此不多”。周作人《鲁迅的故家》,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02年,第353页。。1917年8月9日,钱玄同访鲁迅和周作人不值,下午又再次前往周氏兄弟借居的绍兴会馆,和他们一直谈到深夜十一点。*周作人此日日记载:“钱玄同君来访,不值。乃服规那丸。下午,钱君又来。留饭,剧谈至晚十一时去。夜颇热。”《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上),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年,第686页。此后钱玄同开始频繁登门拜访,且每次必谈到深夜十一点后始去。这种频繁的交往一直延续到1919年9月。*查鲁迅和周作人日记,1917年钱登门拜访9次,1918年达34次,1919年到9月为止共21次。
和鲁迅的长谈*周作人木讷寡言,远不如鲁迅健谈,所以钱玄同的谈话对手应是鲁迅。周作人日记中每记钱玄同来访,必标注其离去时间,最早十一时,深夜一时亦不在少数。在钱离去后,周作人往往还要抄写讲义,常常弄得夜不能寐。他似乎颇以此为苦。另据沈尹默回忆,“鲁迅善作长夜之谈,钱玄同是他座上常在之客。玄同健谈是大家所知道的,他们两位碰在一起,别人在旁只有洗耳恭听的份儿,是没有插嘴的余地的。”沈尹默《鲁迅生活中的一节》,《鲁迅回忆录》(散篇,上册),北京出版社,1999年,第248页。对钱玄同思想的影响恐怕是不能忽略的。和鲁迅频繁交往的这段时间,钱玄同思想极为活跃,在《新青年》上发表言论也最密集,他文章中的很多话题,可能就来自和鲁迅对谈的思想激发。从两人发表在《新青年》上的“随感录”看,议题就常有交集。钱玄同狠批上海的《灵学杂志》搞扶乩降神,并斥道教为“最野蛮的邪教”,所宣扬的是“上古极野蛮时代‘生殖器崇拜’之思想”;[18](PP.10-11)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四十二”、“五十三”以及杂文《我之节烈观》里对灵学派也有犀利的揭批,《随感录》“三十八”亦说儒道两派助成了中国人头脑的昏乱。钱玄同批中国旧戏,对“打脸”、男扮女极尽嘲讽(《随感录》之“十八”、“三二”);鲁迅在《随感录》“三十八”里同样嘲讽了“打脸”,《论照相之类》更是辛辣地称“中国的最伟大最永久的艺术是男人扮女人”[19](P.187)。钱玄同批中医不科学,说中医关于身体构造和病象的解释都是玄而又玄的(《随感录》之“五一”、“五二”);鲁迅在《随感录》“三十三”里同样讨论了医学和科学的问题,《从胡须说到牙齿》对中医也有尖锐的批评。至于钱玄同屡加痛斥的国粹和国粹派,自然也是鲁迅批驳的主要对象。在1918年7月5日致钱玄同的信里,鲁迅以钱玄同常用的那种“不雅驯的文笔”[20](P.373),大骂奉刘师培为祭酒的国粹派是“如何发昏、如何放屁、如何做梦”,并轻蔑地称他们是“老小昏虫”。[21](P.351)可见两人声气相通,在很多问题上都有比较接近的看法。
和鲁迅密切交往的这段时期,钱玄同的思想明显变得激进了,他对包括语言文字、戏曲小说在内的一切国粹都不遗余力地加以抨击,言辞之激烈让人难以相信他曾经是一个极其固执的国粹主义者。尽管在这个时期鲁迅的思想也非常激进,但他思想之深刻、头脑之冷静,却决非钱玄同可比。钱玄同在《新青年》上反复申说要废汉文以世界语代之,并声称“刘半农、唐俟*这是鲁迅在《新青年》上发表“随感录”等杂文时专用的笔名。、周启明、沈尹默诸先生……对于Esperanto,都不反对”[22](P.211)。鲁迅在给钱玄同的信中却说:自己对世界语固然不反对,但也不愿讨论。他赞成世界语,是因为觉得人类将来总当有一种共同的语言;不愿讨论,是因为将来有没有一种共通的语言,以及这共通的语言是不是世界语,并没有确凿的依据,所以这问题无从讨论也没有必要去讨论。他进一步指出:学世界语是一件事,学世界语的精神又是另一件事。“白话文学也是如此——倘若思想照旧,便仍然换牌不换货;才从‘四目仓圣’面前爬起,又向‘柴明华先师’脚下跪倒;无非反对人类进步的时候,从前是说no,现在是说ne;从前写作‘咈哉’,现在写作‘不行’罢了。”[23](PP.33-34)鲁迅的意思是:语言如同独木小舟或是汽船,只是传输思想的一种工具或载体,如果只关注工具本身,而忘掉了更为根本的思想改良,那么不管工具有多么新也依然无补于事。这对当时国内知识界对于世界语的拜物教似的膜拜,是一个必要的提醒。可惜钱玄同却不能领会鲁迅的深意,他在回信中糊里糊涂地说什么世界上万事万物都在进化,文字也不例外;象形文字改为拼音文字,也是进化之理,正如衣裳破了,自然要改做新衣一样。[24](P.246)
针对中国传统思想文化鲁迅也说过一些偏激的话,但他更重视的是分析中国传统思想文化中那些已成为结构性因素的痼疾,以及潜藏其间的病态精神人格和文化心理,如《随感录》中对国人“合群的爱国的自大”、对一切冷笑的犬儒心态以及作为“暴君治下的臣民的渴血的欲望”的揭示,都是极为深刻的。钱玄同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却从来没能达到这般深刻的地步,他总喜欢说一些耸人听闻的过头话,比如他认为传统中国的政治道德学术思想与现代民主科学均格格不入,应彻底铲除,[25](P.45)中国书籍充斥着“发昏做梦的话”,应“一概束之高阁”[16](PP.163-164)。类似这种极端的话,鲁迅从不曾说过。钱玄同批判旧传统甚至偏激到认为春节、端午、中秋、冬至这些传统节日都是“荒谬绝伦的规定”[26](P.29),这也是鲁迅决不能赞同的。早在《破恶声论》里,鲁迅就曾批驳那些以科学之名斥农民赛会为迷信且欲加禁止的所谓志士,并直指他们为“伪士”。[27](PP.29-30)鲁迅在年轻时虽也曾信奉文化复古主义,但他的主张复古,并非如钱玄同那般要恢复上古的制度,着古衣冠,行古礼,写篆字,而是强调要“取今复古,别立新宗”,“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潮流,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28](P.58)所“取”之“今”是对个性和精神的张扬,所“复”之“古”则是“朴素之民”的“纯白之心”。这是他一生坚执的信念。正因如此,无论是青年时代的复古,还是新文化运动中激烈的反传统,以及三十年代投身于左翼政治活动,鲁迅的思想言论始终有着内在的一致性。这和钱玄同的反复多变形成了鲜明的对照。
向“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的倒退
1919年9月后,钱玄同与鲁迅的交往明显减少了。从这年8月起,鲁迅虽一直忙于购买和整修八道湾住宅,但还不至于忙到摒交息游的地步。1919年11月21日,鲁迅与周作人全家迁入新居,两天后的星期天,朱逷先、沈尹默、马幼渔、刘半农及钱玄同的侄子钱稻孙等一干老友来贺,钱玄同却不曾露面。[29](P.355)11月30日又是一个星期天,鲁迅已定于次日南下接母亲北来,朱逷先、宋子佩、李遐卿来送行[29](P.356),钱玄同再次缺席。1920年1月4日,钱玄同来访,傍晚离去,[30](P.98)没有像以往惯常的那样作长夜之谈。时隔半年后的7月17日,钱玄同再次来访,于饭后离去。[30](P.137)第三次来访是年底的12月25日,这次是来代马衡还《孝堂山石刻》的,[29](P.385)并借了三十元钱,下午五点来,晚十时去。[30](P.164)

反省自己前两年过于情绪化的言论,这本来是好事,但无原则到了丢弃立场、不分是非、一团和气的地步,就有点糊涂了。把《新青年》同人的激进姿态与思想专制联系在一起,也是罔顾新文化、新思想在当时社会中实际上是处于弱势这一事实。钱玄同的反省所暴露出来的思想的大幅倒退令人吃惊。他强调的是辩论态度的正当性,应当理性而宽容,费厄泼来,对思想本身的内容及是非对错却不那么关心。在他看来,“中国人‘专制’‘一尊’的思想,用来讲孔教,讲皇帝,讲伦常……固然是要不得”,但用来讲德谟克拉西,讲布尔什维克,讲马克思,讲无政府主义,讲科学,也一样要不得。他主张要用“科学的精神(分析条理的精神),容纳的态度来讲东西”,那样不管讲的是德先生、赛先生,还是孔教、伦常,就都是好的。他还说:“我在近一年来时怀杞忧,看看‘中国列宁’*指陈独秀。的言论,真觉害怕,因为这不是ㄅㄛㄌㄕㄝㄞㄧㄎㄧ*此为布尔什维克的注音字母。,真是过激派;这条‘小河’,一旦‘洪水横流,泛滥于两岸’,则我等‘粟树’‘小草’们实在不免胆战心惊”。他最终得出的结论是:最好奉行“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中国人要是人人能实行它,便已泽及社会无穷矣”。[31](PP.74-76)
或许对“小河”的杞忧才是导致钱玄同思想立场迅速后撤的真正原因吧。在放言反孔教、废汉文的时候,他肯定没想到启蒙本身也是危险的事业,当沉默的大多数逐渐被唤醒,他们爆发出来的那股冲决一切的力量就让坐而论道的知识者惊悚不安了。《新青年》的启蒙事业迅速从文化运动转换为政治运动,这是钱玄同始料不及的,五四运动的席卷之势以及其后政治形势一日千里的突进,也不能不让他为势将到来的“小河”的泛滥而胆战心惊。追悔先前的鲁莽,用“各人自扫门前雪”主义取消社会运动乃至政治革命的必要性,说穿了就是一种软弱而感伤的自欺。
表面上,钱玄同坚持着自由、理性、宽容等自由主义的核心价值,实际上其思想却在迅速地向传统回归。1919年9月,钱玄同与马幼渔等北大同事商定编一部现代标点本的《中国学术论著集要》,作为学生用教材。[7](P.347)在此后两年时间里,点校古代典籍成为他的一项日常性工作。1919年9月24日他买了一部石印本《王阳明集》,读了王阳明的《大学问》;第二天又换购另一版本的《王阳明集》,并点校《大学问》;第三日开始读未收入《集要》的《传习录》。[7](P.350)虽然他不曾在日记中发表议论,但连续三天记载,大概是心有所动吧。《大学问》是阳明心学的教典,抉发格物致知、正心诚意之说,其中特别提到“为大人之学者,亦惟去其私欲之蔽,以自明其明德,复其天地万物一体之本然而已耳”。[32](P.968)这种说教对钱玄同似乎不无影响。在1920年9月19日致周作人信中,他说自己“近来大有‘绚烂之极归于平淡’之意”,不想“和人斗口”,觉得减除精神上良知上的痛苦才是唯一要义。[31](P.29)在1921年元旦的日记中,他检讨自己两三年前专发破坏之论是不对的,“杀机一启,决无好理”,要搞革新首先要化除“旧人偏窄忌克之心”,“万物并育而不相害,道并处而不相悖,方是正理”。[7](P.367)这就很像宋明理学家的口吻了。
但中国诡谲变幻的现实却让他没法安然地自扫门前雪。1922年后,“学衡派”突起,提出“昌明国粹,融化新知”的口号,连许地山“忽然也有提倡孔教之意”,这让他颇受到一点刺激,“烧毁中国书的偏谬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当年和周氏兄弟在绍兴会馆“院子中槐树底下所谈的偏激话的精神又渐有复活之象焉”。[31](P.59)在《语丝》时期他短暂地抖擞精神再来破坏传统,大概就是对这种刺激的反应吧。
钱玄同一生思想多变,常以今日之我否定昨日之我,且往往是那种大翻转式的变化。其多变、善变虽不能说是曲学阿世,却也并非缘于思想的不断精进。他终究还是没有一套从自己的生命经验中顽强生长出来、又经过艰苦的思考和反复的纠错而形成的想法,没有坚定的思想信念,更没有投身饲虎的勇气,就只能被时代潮流裹挟着东飘西荡了。当然,这么说并非要抹杀他在新文化运动中的功绩,因思想的简单而获得的自信和勇气让他很好地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为新文化运动的推进助了一臂之力。为实现废汉文的最终目标,他还积极参与了注音字母、国语罗马字、简体字等的制定和推广工作,这些实绩也许是更应当被铭记的。
参考文献:
[1]钱玄同.三十年来我对于满清的态度的变迁[M]//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钱玄同.赞文艺改良附论中国文学之分期[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陈独秀.答钱玄同[M]//陈独秀著作选编:第1卷.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唐德刚.胡适口述自传[M]//胡适全集:第18卷.合肥:安徽教育出版社,2003.
[5]钱玄同.保护眼珠与换回人眼[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6]周作人.钱玄同的复古与反复古[G]//文史资料选辑:第32卷.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2000.
[7]杨天石.钱玄同日记(整理本):上[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4.
[8]钱玄同.重论经今古文学问题(方国瑜标点本《新学伪经考》序)[M]//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9]钱玄同.论今古文经学及《辨伪丛书》书[M]//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0][美]艾尔曼.经学、政治和宗族——中华帝国晚期常州今文学派研究[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1998.
[11]钱玄同.春秋与孔子[M]//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2]钱玄同.答顾颉刚先生书[M]//钱玄同文集:第4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3]钱玄同.答陶履恭论Esperanto[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4]章太炎.章太炎全集·太炎文录初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14.
[15]钱玄同.刊行《教育今语杂志》之缘起[M]//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6]钱玄同.中国今后之文字问题[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7]鲁迅.两地书·一二[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8]钱玄同.随感录·八[M]//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19]鲁迅.鲁迅全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0]钱玄同.写白话与用国音[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1]鲁迅.致钱玄同[M]//鲁迅全集:第1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2]钱玄同.关于Esperanto讨论的两个附言[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3]鲁迅.渡河与引路[M]//鲁迅全集:第7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4]钱玄同.渡河与引路[M]//钱玄同文集:第1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5]吴锐.钱玄同评传[M].南昌:百花洲出版社,1996.
[26]钱玄同.陈百年《恭贺新禧》的附志[M]//钱玄同文集:第2卷.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27]鲁迅.破恶声论[M]//鲁迅全集:第8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8]鲁迅.文化偏至论[M]//鲁迅全集:第1卷.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29]鲁迅.鲁迅全集:第14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30]周作人.周作人日记(影印本):中[M].郑州:大象出版社,1996.
[31]钱玄同.钱玄同文集:第6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9.
[32]王阳明.王阳明全集:下[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92.
(责任编辑:吴芳)
An Exploration on Motivations of Qian Xuantong’s Ideological Change
during the Period of theNewYouth
NI Wei
(Department of Chinese Language and Literature, Fudan University, Shanghai 200433, China)
Abstract:Qian Xuantong changed his ideological position from original ethnic chauvinism to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when he joined theNewYouthin 1907. Through an exploration on Qian’s diaries, correspondences and published articles during this period, it can be found that there were three motivations which resulted in his move towards the radical anti-traditionalism, namely his admiration for the sophisticated text research methods of the new text Confucianism, the revival of his enthusiasm for anarchism, and his frequent exchange of ideas with Lu Xun. As the ideological disputes among theNewYouthcolleagues had been increasingly brought into open, especially after the May Fourth Movement had placed the political revolution on agenda, Qian gradually became anxious about the upcoming destructive effects of the revolution and moved again to a more conservative doctrine of being self-responsible and self-interest. The capriciousness of Qian’s ideological position reveals the rootlessness of the idea and the absence of conviction, which is actually the typical spiritual characteristic of some sort of modern Chinese intellectuals.
Key words:Qian Xuantong; theNewYouth; New Culture Movement; anarchism; new text Confucianism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05
中图分类号:I209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44-09
作者简介:倪伟(1968-),男,江苏江阴人,复旦大学中文系副教授,主要从事中国现当代文学及中国现代思想史研究。
收稿日期:2015-06-16
主题研讨二纪念《新青年》创刊100周年专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