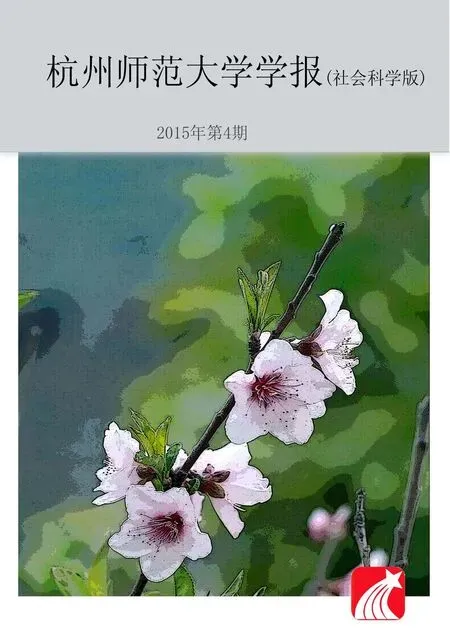切斯特顿随笔与共同体文化
2015-03-28胡强
胡 强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切斯特顿随笔与共同体文化
胡强
(湘潭大学 外国语学院, 湖南 湘潭 411105)
摘要:切斯特顿随笔对共同体的关注主要体现在传统与文化断裂、思考惰性与文化危机、教育与文化愿景这三个层面。传统的存留不仅是一个凝聚着社会关注的思想焦点,也是一个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社会问题。切斯特顿对传统的态度更多意味着一种充满辩证法的审慎与稳妥,体现了一种对既有秩序感的依恋,以及对共同体未来的文化忧思。在切斯特顿看来,思考的惰性与对进步概念的误读其核心是一种智识缺席,这种缺席不仅阻碍了社会进步,也危及了共同体文化的良性发展。切斯特顿对教育的关注不仅具有文化史研究的现实关怀,也以一种对话精神渗透着一种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愿景思考。
关键词:切斯特顿;共同体文化;传统;教育
在英国社会史家阿萨·勃里格斯看来,漫长的维多利亚时期可以分为早、中、晚三个阶段。早期以1851年举行的伦敦世博会为终点,而中晚期的分界点则在70年代,在这个分界点前后,英国社会呈现出了一种文化史意义上的分裂特质。这种分裂正如T.H.埃斯科特所言,“旧的分界线”正在消失,“思想和信念的老界碑在被移走,我们不久前所尊奉的偶像已被打碎”。[1](P.286)可以说,这种分裂也预示了一种社会转型的开始,这一独特的思想语境无疑给这一时期的英国散文打上了鲜明的时代印记。
英国散文在维多利亚时期“臻于全盛”,而到了20世纪初年,依旧“文运不衰”,再度呈现了“兴盛繁荣甚至更加崛起之势”。[2](P.9)切斯特顿出生于1874年,适逢维多利亚时代中晚期的交界点,卒于二战爆发前夕的1936年,一生见证了世纪之交英国社会的历史演进和文化变迁。在国内,切斯特顿多为人知的主要是他创作的《布朗神父》等侦探作品,读者对他的批评随笔关注不多,相关的学术研究也非常薄弱。在他的丰盛的随笔创作中,我们可以清晰地体会到一种对于英国社会共同体发展的文化忧思。
传统与共同体文化断裂
在切斯特顿生活的时代,传统的存留不仅是一个凝聚着社会关注的思想焦点,也是一个事关共同体文化发展的社会问题。爱德华·希尔斯指出,所谓实质性传统,既是指一种延续人类社会的“主要思想范型”,也意味着“崇尚过去的成就和智慧,崇尚蕴涵传统的制度,并把从过去继承下来的行为模式视为有效指南的思想倾向”。[3](“译序”,P.2)在此维度上,切斯特顿的随笔可以说具有了一种对传统和现实关系的辩证反思,这种反思的核心孕育着一种文化自省。在《维多利亚时代的遗产》一文中,切斯特顿指出,19世纪的英国虽然成就瞩目,但是在快速发展的过程中也犯了“重大的错误”,这种错误是一种选择性的“遗忘自己错误的错误”,其焦点就在于偏执地认为“不断向上、完美无瑕的社会进化永远是对的”。[4](P.136)比起对物质进步负面影响的关注,切斯特顿更为担心的是这种“自以为是”的思想所导致的“停滞不前”。[4](P.135)在他看来,如果在拥抱进步的同时,英国人也能以一种自我省思的心态看到“现代的种种弊端”,[4](P.136)那么共同体的发展就会更加平稳。切斯特顿特别强调,“在整改、重建、变革或拒绝变革之前”,走在发展快车道上英国人应该有足够的勇气“坦诚自身的过失”,如果面对种种“现代意识”所导致的“一连串的严重错误”,人们总是徘徊于“虚荣”与“尊严”之间而止步不前,那么“一切所谓的工业进步”都有可能把国人引上“从压迫走向毁灭的道路”。[4](PP.136-138)
在《英伦的美国化》中,切斯特顿批判了英国的“迅速美国化”,直言不讳地指出了美国商业文化对英国传统文化共同体的负面影响。在切斯特顿看来,英美都有着各自的“民族传统与价值观”。美国人自有他们“崇尚知识、创新,唾弃愚昧、怠惰”的优良品质,但也有其“金权政治”和“粗俗文化”的弊端,如果英国人“亦步亦趋”地跟在美国后面,那么共同体文化中的“民族记忆”和“民族认同”就会受到很大的冲击。[4](P.151)切斯特顿嘲讽了“把纽约移植到伦敦”的愚蠢念头,在他看来,照搬高楼与霓虹不难,难就难在让英伦文化传统中那种特有的“知性讽刺与幽默”保持一种独特的文化品性。[4](P.152)在共同体文化的演进过程之中,面对强势的美国商业文化的侵袭,切斯特顿忧虑的是英国文化竟然节节败退,面临“完全失语”的尴尬境地。[4](P.153)在他看来,带给民众快乐的“笑匠”是“功德无量的”,而“英国人的幽默比英国的法律更值得捍卫”,如果一个从乔叟延续至狄更斯的“独特而悠久的幽默传统”竟然“需要进口生涩难懂的美式笑话”来维系,那实在是一种文化上的“可悲”。[4](P.153)
在《英国乡间的布尔乔亚文化》中,切斯特顿以一个偏远乡村的传统集市的存废为题,敏锐地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摩登英国”与“快乐英国”之间的文化冲突。切斯特顿认为,势不可挡的工商业社会培育了一大批中产阶级,这个新兴阶级很多时候“似乎已经完全丧失了对乡土的那份自豪与热爱”,在“对传统文化的粗暴践踏”之中,他们让这个具有悠久历史的文化共同体“丧失了很多宝贵的遗产”。[4](PP.54-55)而传统之所以重要,不仅在于它延续了共同体的价值规范和道德理想,同时也赋予了现实生活某种具有超越性的精神特质。在切斯特顿看来,乡村牧师手上的圣像木雕不仅“记录了中世纪的故事”,也演绎成了一场联结过去与现在的“文化盛宴”。[4](P.55)如果说,30年前卡莱尔(Thomas Carlyle,1795-1881)忧虑的是“在机械生产制度的冲击之下,有机的人类共同体将会纷纷瓦解”的现实,[5](P.253)那么切斯特顿更为担忧的是一个面临分裂的社会中共同体文化的未来。在他眼中,“保守木讷、不苟言笑”的乡下人并不失“淳朴善良”,很多时候反而显现出一种“令人惊异的独立精神”,而那些“自视清高”、颇有“艺术修养”的中产阶级却总是“荒唐地”想要摆脱传统的束缚。[4](P.56)传统集市的存废看似小事,但从更深的层面来看却反映了工业化与城市化进程对共同体文化的影响,同时也折射了“貌似保守、实则新派”的“野叟村夫”和“外表新潮、内在保守”的“唯美派”之间在面对共同价值传统时的文化冲突。[4](P.57)
可以说,传统是一种共同体文化的精神沉淀,它不仅延续着一种“共有的习惯”(customs in common),也对现实社会始终散播着一种文化的感召力。面对社会转型所带来的种种变迁,切斯特顿提出了“维多利亚大断层”一说。[4](P.241)在《文化传统的遗失》一文中,他以“集体大合唱”的贬颂之争历陈此种文化断层对现实生活的种种负面影响。在他看来,传统习俗是“精神与情感的自然流露”,大合唱本来就是英国固有的传统,与英国宗教习俗相伴而生,绝非俄国革命之后强调集体主义的“苏俄的专利”。[4](P.240)而如今国人之所以对自己的宗教仪式和民间文化“感觉陌生”,心生隔膜,就在于“遗忘了一些最基本的规则”,放弃了一些“最具人性、最灵活”的共同体习惯。[4](P.241)对于共同体建设而言,传统的重要价值就在于如果人们不能“撷取丰赡的文化传统”,那么他们也就不可能“升华眼前的物质享乐”,从“更为丰富的历史记忆”中找到新的选择,从而不断推陈出新,点燃更多“自我更新的希望”。[4](P.209)
切斯特顿忧虑的是,英国人往往只看到美国的摩天大楼和广告牌,却看不到“越古老的国家反而越年轻”。其实任何面向未来的“精神需求”,总能“通过回归历史的记忆而获得满足”,[4](PP.208-209)而任何古老的文明,也能够通过延续传统的生命活力开创未来。在《群虻的喧嚣》中,切斯特顿提醒读者尤其要警惕一种“反传统的情绪”。[4](P.318)在他看来,这些“不经大脑的胡言乱语”已经“如蚊虻一般充斥于整个社会”,这些“零星的想法”和“琐碎的言语”渗透着一种“廉价的怀疑”,它们虽然“细小”和“不起眼”,但却“无孔不入”。[4](P.314)青年时期的切斯特顿倾向自由主义,后又转向保守主义立场,但是他的随笔对于种种新的思想和观点始终存有一份宽容,他真正希望国人警思的是那种宣泄着“怀疑、无望的情绪”,这种情绪以各种面目示人,或伪装深刻,或尖酸俏皮,但其实质指向的都是一种“言论思想的贬值”。[4](P.315)为什么“理想到处受到攻击?”“为什么连傻瓜都可以指手画脚、目中无人?”切斯特顿认为,在一个进步社会,如果连“美德”都被无端“仇视”,连传统都可以被随意抛弃,这实在让人“匪夷所思”。他一针见血地指出,“一只苍蝇并不起眼,但一群苍蝇却不可小视”,如果世人对这种看似“微不足道”的个人情绪不加以警惕,任其蓄积蔓延,那么就很有可能“侵蚀整个文化”,其对共同体的破坏远“比已经定型的异端邪说更为惊人”。[4](PP.315-316)
切斯特顿并不反对进步,他提醒国人警惕的是激进的进步。他的保守主义看似尖刻犀利,但其核心却充满着一种辩证思维的审慎与稳妥。他的批评回应了一个快速变迁时代人们内心的惶惑与焦虑,强调了共同体发展过程中人的精神自觉的重要意义。在这种批评中我们可以看到18世纪英国思想家伯克的影响痕迹。在1791年写给友人的信中,伯克说道:“人们能够享受自由的程度取决于他们是否愿意对自己的欲望套上道德的枷锁;取决于他们对正义之爱是否胜过他们的贪欲;取决于他们正常周全的判断力是否胜过他们的虚荣和放肆;取决于他们要听的是智者和仁者的忠告而不是奸佞的谄媚。除非有一种对意志和欲望的约束力,否则社会就无法存在。内在的约束力越弱,外在的约束力就必须越强。事务命定的性质就是如此,不知克制者不得自由。他们的激情铸就了他们的镣铐”。[6](P.35)可以说,切斯特顿继承了伯克的保守主义立场,体现了一种对既有秩序感的依恋,以及对于共同体未来的文化忧思。
“厌‘思’症”与共同体文化危机
在《改变就是进步》一文中,切斯特顿对进化论提出了自己的思考:“假设万物都在改变,包括人的心智,那么我们该如何辨别这变化到底是不是进步?”[4](P.266)比起进化论者在伦理观上的矛盾与纠结,切斯特顿更为关注的是在这些思潮背后“现代人的思考惰性”。[4](P.268)在切斯特顿看来,正是这种与“极端的进化论”相关联的“思考惰性”让很多现代人沦为了科学进步和物质财富的奴隶。在一个浸透着乐观主义精神的年代,最大的愚昧不是不识字,而是社会心态中的一种思考惰性。这种思考惰性以为“装上了机械眼,眼睛就不会再感到疲劳”,以为“装上了机械脑,人就不必再费心思考”。“一切看起来都不那么费力气”的惰性缘起于推崇自由竞争所取得的巨大物质进步,正是这种“不愿认清真相”的惰性,让英国社会在迈入了新世纪之后呈现了一种“停滞不前”。[4](P.268)
对于年轻人而言,这种惰性意味着不再“追问生存的意义”和“探求实物的本源”。[4](P.213)虽然相比前人,现代人已经获得了更多的“自由与独立”,但是这种“自由与独立”中有多少“思辨”的成分却的确存疑。切斯特顿指出,当下的英国社会如果真的存在某种“解体之虞”,那么这种危险或许来自“精神的崩溃”和“头脑的松垮”,而非“道德的沦丧”和“良心的僵硬”。[4](P.212)这种“崩溃”和“松垮”的内核是一种“辨别分析能力”的缺失。在切斯特顿看来,在维多利亚时代,英国面对的已经不是“有无思想自由的问题”,而是“愿不愿意思想的问题”。英国的年轻人习惯于享受物质进步,“满脑子真真假假的新思想,但大多都是囫囵吞枣、食而不化”,他们缺乏“通盘思考的能力”,“从不质问权威,也不查根究底,反正一切是天经地义、理所当然”。[4](PP.212-213)与切斯特顿同时期的作家康拉德(Joseph Conrad,1857-1924)在其《间谍》一书中曾经塑造了两位典型的“厌‘思’症”患者。维洛克夫人为人处世信奉“不必细察”。她对丈夫的营生一无所知,对家人也关心甚少。当她看到弟弟斯迪威因目睹社会不公而试图宣泄愤懑的时候,她对弟弟内心的苦痛根本不愿意“深究”。而当她的母亲为了保护弟弟斯迪威而做出自我牺牲,宁愿搬到济贫院去以减轻家庭负担时,她也无心体会“做母亲的心思”。她的人生“哲学”就是“不加深究”,因为“任何事物都经不起仔细推敲”,[7](P.157)而不必“深入了解事实的真相”,[7](P.136)这或许就是她维系“家庭和睦生活的基础”。[7](P.212)小说中的埃塞雷德爵士主管公共安全,位高权重,但同样也有不愿“深究”的习惯。当格林威治爆炸案发生,手下带着“深入调查”取得的成果向他汇报案情进展时,他多次以一句“我没有时间”傲慢地提醒对方讲话一定“要简明扼要”,特别注意“不要讲细节”。[7](P.121)维洛克夫人和埃塞雷德爵士“不予细察”的态度为切斯特顿的“厌思症”提供了一种时代语境的文学佐证。[8](PP.157-161)所谓“不愿细察”,既意味着一种对矛盾现实的含混和暧昧,也意味着一种对共同体核心价值观的认同懈怠与丧失。
在《现代人的思想惰性》一文中,切斯特顿不无忧虑地指出,现实世界日新月异,而唯有“人的头脑不见长进”。虽然与过去的时代相比,新世纪的英国人能够紧跟潮流与时俱进,能够从抽象的现代艺术中找寻到情感与精神的共鸣,但是,“一旦遭遇考验智识的问题”,现代英国人“大多远远逊色于他们的父辈”。[4](P.281)在切斯特顿看来,所谓“智识”,从本质而言就是一种“带着疑问、会思考”的心智成长。英国人在经历了财富的快速积累之后,已“不太热衷于去求证事情”,在种种新知的冲刷之下,那种“缜密的逻辑论证”和条分缕析的思辨判断能力已让位于“人性中非理性的部分”。在这样一个充满着“蛊惑”与“煽动”的时代,当人们一旦“厌倦了所有的思考”,人的思辨也只能最终退让于平庸之下的“轻松”、“省心”与“省力”,这种“智识”缺席的“思考惰性”不仅阻碍了社会的思想进步,也会对人性的道德成长产生深远的负面影响。[4](PP.281-284)
从当时社会心态来看,一方面是厌“思”症的蔓延,另一方面却弥散着一股对进步与速度的执迷。在切斯特顿看来,不断涌现的科学新发现似乎已经较少让人感到“激动”,而对于快速成功的膜拜却延续并扩大了一种思想的断裂。他以充满激情的句子写道:“如果一味盲目创新”,满头栽进“空无的未来”,“肆无忌惮地自夸现代与超强”,那么极有可能会“炮制更多的无聊与疲倦”。“人生苦短”,倘若我们只顾着“向前赶路”,“其结果必定和开车一样——速度虽然很快,却错过了窗外的风景”。[4](PP.246-247)在《成功指南》一文中,切斯特顿对这种思辨缺席的浮躁心理进行了深刻的剖析。在他看来,《成功指南》不知道会把这个社会“引向何方”?[4](P.36)这一类书籍充斥的都是些“史上最为愚蠢的文字”,之所以说它愚蠢,是因为它既没有骑士小说在夸张手法背后的“言之有物”,也没有宗教“经论”在枯燥讲述中的“有的放矢”,[4](P.32)它有的只是教人如何快速成功的所谓秘诀。“成功指南”的热销反映了物质时代人们对身份追求的迷失,也在社会心理学的层面折射了社会有机体的文化失范。切斯特顿指出,如果任由这种“恶俗的功利哲学”肆意发展,那么社会必将付出沉重的代价。这类成功学的故事之所以显得无聊而虚幻,其本质就在于推销了一种“可怕”而“神秘”的“金钱崇拜”。说它可怕,是因为这种“只想在百万富翁面前屈膝下跪”的“伪善势利”必将危及共同体文化的长远发展。而说它神秘,则是因为此类文字常常以一种“无形的存在”会让读者在“奉若神明”的精神麻醉中变得“更加痴迷”。[4](P.34)切斯特顿预言,这种“荒唐”的成功指南终将为读者所“鄙视和抛弃”,因为天下本就没有“所谓的成功”。[4](PP.32-36)
教育与共同体愿景
教育与共同体文化建设息息相关,切斯特顿的批评随笔在这一维度上也体现了一种极具文化史深度的现实关怀。在《历史教育》一文中,他指出,具体的国别史研究“只有放在世界史的视野内,才能了解得更充分、更透彻”。这种互为比照的历史观对当时英国的教育现状无疑具有一种超乎寻常的紧迫性。在切斯特顿看来,维多利亚晚期的英国已经成为世界强国,而迈入新世纪的英国如果要避免沦为一个“孤立的世界工厂”,避免“战争与饥荒的威胁”,首先就要让接受教育的孩子们明白,接受教育的目的是要培养“大写的人”,是要“以想象来开阔自身的经验”,而这种经验绝不仅仅是对地铁、电灯、汽车、潜水艇和飞机等物质进步与科学发现的热情拥抱,而是更应着力培养一种具有历史纵深感的思辨意识。在切斯特顿看来,这种思辨意识的核心无疑就是人的智识本身。比起随处可见的种种“物”的进步,真正让人感到隐忧的却是今天的老师已经“很少在课堂上提到人”。[4](P.157)在一个社会心态时时为“伟大成就”欢呼雀跃的年代,也正是这种“对人的不了解”所造成的局限极有可能让孩子们出现“认识的偏差”,而一旦孩子们的视野受到局限,他们就有可能出于对历史的无知而变成“岛上的蛮族”和“小镇上的愚人”。[4](PP.155-158)切斯特顿以历史教育作为切入话题,直面的是英国文化有机体发展的现实矛盾。维多利亚时代思想家卡莱尔曾用过“机械时代”一词表达了他对英国社会的批判。在卡莱尔看来,工业发展与科学进步的结果需用整体的眼光来辩证地加以把握。作为手段,机械提高了效率,创造了财富,但是人的智识一旦成为机械的附庸,那么这种机械的“习惯”则不仅会“支配了我们的行为方式”,而且也会“支配了我们的思想和感情方式”。[9](P.159)
从以上分析来看,只关注物质成就的取得而忽视人的因素,就有可能对社会有机体的良性发展产生负面的影响。人要避免成为物质异化的囚徒,必须提升智识与精神的层次。作为一种解决途径,切斯特顿对教育问题的思考和对功利主义的批评具有内在的逻辑一致性。在《完整教育和一半教育》中,切斯特顿批评了“舍本逐末的现代教育”,指出了它的危害与隐忧。在他看来,这种“偏离正轨”、“只关注成效与结果”的“一半教育”不仅是现代文化的一大病症,也是英国社会有机体发展的巨大障碍。现代英国之所以杂念喧嚣,人性浮躁,就在于人们往往“以务实功利为傲”,心中已经“容不下一个‘礼’字”。切斯特顿指出,对“礼”的重视不仅培养了古希腊人“超然的态度”和“求索的精神”,也塑造了中国以孔子为代表的“博大的文化”。所谓“礼”,不仅“关乎仪式、举止”,更包含着“道德的熏陶与教诲”。由此来看,真正的教育既是一种从“整体出发”和“明辨主次”的“全人教育”,也应该是一种“欣赏礼的艺术”。[4](PP.255-257)
在《识字不识字》一文中,切斯特顿更是把批评的矛头指向了社会有机体中教育与公共生活的交集维度。进入新世纪以来,英国人的受教育程度有了很大的提高,在国人为此感到兴奋的时候,切斯特顿却对英国人的公共文化生活提出了更高的期许。在他看来,教育并不简单地等同于识字,读写能力的提高更不一定就会“代表个人智慧的增长”和“社会自觉的进步”。[4](P.258)较之前人而言,今天读书看报已经变成“十分廉价的事情”,现代人的书的确也读得多了,但是文化素养的提升却并非仅指阅读量的单向增长,而更意味着阅读背后智识的提升与人性的成长。在一个科学理性与财富效率日渐成为社会主流话语的年代,切斯特顿以讽刺而犀利的文字提醒我们务必重新审视文学中的情感与想象力的重要作用。在他看来,人们虽然也会人云亦云地“宣称阅读的重要性”,但是他们却不再满怀情感地“阅读经典”。社会的进步让人愈觉自由,但是他们却“偷偷地逃避读书”。一方面是“文字越来越容易阅读”,另一方面却是想象力和思辨能力“总体水平的直落”。人人似乎都有“阅读的习惯”,但是“大众的阅读量却在递减”。他们“既读不懂连贯有意涵的文字”,也分不清“文章的主次轻重”。如果我们把有思想的文字比喻成照亮共同体的公共“光源”,那么实际上我们正在离这一光源“越来越远”。[4](PP.258-261)
进入20世纪以后,英国教育中急功近利的倾向愈演愈烈。在《职业教育观》中,切斯特顿指出,所谓商业化教育,也就是只注重培养“实用型人才”的教育。这种教育之所以“荒谬”,就在于“实用型人才”一旦面临一些“真正基本的、严重的”、事关社会发展的问题,就只能“哭诉,或祈求呼唤”那些“非实用型人才”。实用型人才往往只知道“如何操作机器”,而社会的发展往往更得益于一些“不可或缺的”、“非实用”的理论家。什么是教育?切斯特顿强调,“培养青年的谋生能力根本不算是真正的教育”,真正的教育是“培养公民”,而非“市民”,更不是什么“莫名其妙”的“城市精英”。[4](P.274)切斯特顿调侃自己是“怀抱旧式共和理想的遗老”,但是他的笔触时时渗透着一种与时俱进的批判锋芒。共同体要良性发展,教育责任重大。在他眼里,教育就是培养公民,其核心就是“培养批判者”。“教育的全部意义在于传授抽象、永恒的准则,使受教育者能够以此判断虚实真伪”。[4](P.274)而在商业社会中,教育之沦落就在于“智识的缺失”。这种缺失意味着“比较的能力”和“独立判断的能力”的缺失,意味着只教会了学生“用数字计算”,对哲学更是“一无所知”,不知道如何思考。[4](P.275)切斯特顿认为,“正当的数量概念本是商业活动的永恒基石”,但是一旦把这种概念放大为统摄全社会精神文化活动的思想主调,那么就无异于“膜拜邪神与怪物”。如果说,商业教育的弊端在于智识缺席,让人的“眼界愈发狭隘”,那么真正的教育就应是让人“拓宽视野、开阔心胸,尤其是要培养受教者批判和谴责这种狭隘的能力”。切斯特顿的随笔并非一味批评指责,而是始终贯穿着一种对话精神,渗透着一种事关共同体发展的愿景思考。在他看来,如果孩子们“太早参与这些体制的秘密运作”,并且把这些制度“视为圭臬”,那么他们就“永远不可能指陈这些制度的弊端”,而社会共同体也就“不会有改革自新的想法和主张”,其结果就只能是让“忙碌的商业活动”最终都变得“像化石一样僵死”。[4](PP.275-276)
切斯特顿生活的年代,英国国家实力处在鼎盛时期,但是危机也四处潜伏。正是在对这一历史语境的充分关联之中,他的随笔指向了一种纠缠着矛盾与困惑的公共生活,折射了社会心态与共同体意识的相互激荡,也反映了大众舆论与共同体形塑的思想关联。在自由党人约翰·摩里看来,“那些栖身在古代信念的塔楼里的人们,经常是怀着忧心忡忡和惊讶不已的心情来看待那些年代,使他们震惊的是,这些年代仿佛满头都是飞弹,一切都不可捉摸和令人举棋不定,人们只能战战兢兢地展望着未来”。[1](P.279)摩里所言形象地概括了切斯特顿写作的社会语境与思想背景。切斯特顿的随笔以悖论式修辞见长,对他而言,悖论不仅是语言形式,更是对现实的一种隐喻指涉。这种独特的文风因应着一种社会现实,也表达了一种公共知识分子的人文焦虑。在切斯特顿看来,正是由于有了悖论这一矛盾修辞,“散文才能在文学的殿堂里占有一席之地”。悖论看似不可调和,其实却蕴含着一种极具内在思想张力的辩证法,这种辩证法或许正如切氏自己所言,思想者犹如一位有信仰的旅人,“心里明白永远不会到达终点,却仍坚持踏上无望的旅途”。[4](PP.264-265)
参考文献:
[1]阿萨·勃里格斯.英国社会史[M].陈叔平,等译.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1.
[2]高健.英国散文精选[Z].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2010.
[3]爱德华·希尔斯.论传统[M].傅铿,吕乐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9.
[4]G.K.切斯特顿.改变就是进步[M].刘志刚译.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10.
[5]罗兰·斯特龙伯格.西方现代思想史[M].刘北成,赵国新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05.
[6]陆建德.麻雀啁啾[M].北京:三联书店,1996.
[7]康拉德.间谍[M].张健译.北京:外国文学出版社,2002.
[8]胡强.康拉德政治三部曲研究[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2008.
[9]阿伦·布洛克.西方人文主义传统[M].董乐山译.北京:三联书店,1997.
(责任编辑:吴芳)
Chesterton’s Essay and Community Culture
HU Qia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Xiangtan University, Xiangtan 411105, China)
Abstract:Chesterton’s essay on community mainly concentrates on three aspects: tradition and culture rupture, thinking inertia and cultural crisis, education and cultural vision. The persistence and abolition of tradition is a spiritual focus embodied with the social concern as well as a social problem concerning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hesterton’s attitude towards tradition has no more meaning than a dialectics full of prudence and reliability, which reflects his fixation of the existing order and gloomy thoughts on the future of community culture. In Chesterton's opinion, the spread of thinking inertia and a misreading of the concept of progress is an absence of intelligence, which not only hinders the social progress, but also jeopardizes the virtuous development of community culture. Chesterton’s concern with education not only testifies to an actual solicitude for the cultural history research, but also opens up a spiritual dialogue imbued with visional thinking on the cultural development of a community.
Key words:Chesterton; community culture; tradition; education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10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85-06
作者简介:胡强(1971-),男,河北深州人,湘潭大学外国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和湖南省教育厅重点项目“爱德华时代文学知识分子研究”(11A123)的研究成果。
文学研究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