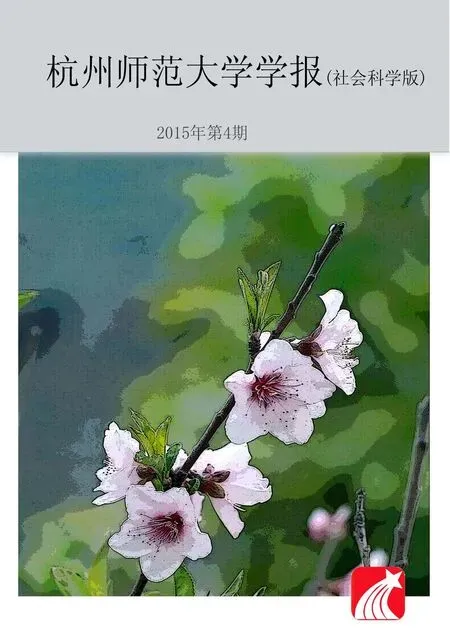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2015-03-28张继焦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建设、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
张继焦
(中国社会科学院 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 北京 100081)
摘要:在国内外一大批学者80多年的持续探索基础上,最近几年企业人类学已经在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学术活动、学术成果等各个方面,开展了许多开拓性探索,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可以说,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意味着人类学发展的局部突破,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作为一个国际性学科,企业人类学打通了中国与西方人类学的通道。从这个学科的发展现状与未来前景来看,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使其成为了企业人类学创新发展之地。中国学者应该可以基于本土的调查思考,提出本土的企业人类学新理论。
关键词:企业人类学;学科体系;发展现状;未来前景
在日常社会交往和国内外学术交流的过程中,我时常会遇到有人问:“企业人类学是什么?从人类学看企业,有什么特别之处?”身为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主席、中国企业人类学委员会秘书长,我有责任回答这个问题。从2009年起,我开始用中文和英文撰写企业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探索论文,①有关企业人类学学科建设方面的研究有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实证与应用研究》(《云南民族大学学报》,2009年第1期)、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关于“成功”的案例分析——对马来西亚28位华商和经理人的访谈及其分析》(《学术探索》,2009年第4期)、张继焦《企业人类学关注什么》(《管理学家》,2013年第9期)、Zhang Jijiao, 2011,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Review and Prospect”, in Zhang Jijiao and Voon Phin Keong(eds) ,EnterpriseAnthropology:AppliedResearchandCaseStudy, Beijing: Intellectual Property Publishing House, pp.1-12.特别是去年(2014)发表了一篇论文,回顾和总结了国际和国内企业人类学的发展历程和学科现状。[1]在本文中,笔者打算在前文的基础上,对企业人类学的学科体系进行一次初步的总结和提升,并分析其发展现状与未来发展前景。
一、企业人类学的“名”与“实”:学科名称的整合
(一)企业人类学之“名”
在一门学科的体系里,学科名称是最为基础性的,也是最为重要的。诞生于20世纪30年代的企业人类学,经过世界各国(主要是美国、中国、日本等三国)人类学者80多年的不懈探索,历经了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企业人类学等不同的发展阶段和相应的不同名称[2],到2009年7月在国际学术界被正式统称为“企业人类学”*2009年7月下旬,在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第十六届世界大会上,通过设立“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召开“第一届企业人类学国际论坛”、统一学科名称为“企业人类学”等三件事。企业人类学的国际学科地位得到了确立。参阅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年第4期。,是本学科有史以来的第一次整合性学术活动。
这不仅是学科名称的简单整合,而是学科的“名”与“实”演变发展的结果。最近一百多年来,中国学术界已经习惯了“西学东渐”、“西学为体,中学为用”。在企业人类学与其他各种名称(如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的相互关系和演进中,我们既看到了这门学科的知识从太平洋东岸的美国,传播到太平洋西岸的日本、中国的影子,也看到了太平洋东、西两岸的美国、日本、中国三国之间,也存在着各自独立发展的轨迹。
(二)企业人类学之“实”
企业人类学与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但是名称上的不同,它们的研究范围、研究对象和研究方法以及所处的学科发展阶段等也稍有不同。比如,工业人类学探究的主要是工业化问题和工业企业问题;工商人类学分析的是企业的盈利性经营活动;经营人类学强调的是企业的行政管理问题。进一步地说,企业人类学的研究对象和研究范围不但包括了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所分别探究的工业、组织、工商、经营等各个方面的具体事项,而且,与其他名称相比,企业人类学是一个更为概括和全面的名称。一方面,学科名称的整合,针对的是这个研究领域多年来存在着多个名称(如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的混乱局面,使得企业人类学的“名”与“实”达成了一致;另一方面,企业人类学这个名称是以中国学者为主导创立的,这在一定程度上超越了非西方(如中国、印度等)学者老是跟在西方学者后面亦步亦趋的治学方式。
(三)企业人类学之“名”与“实”
在人类学领域,各国学者都在考虑如何运用人类学的理论和方法研究企业这个问题。比如,世界各地的学者都不约而同地思考这样两个相关的问题:人们是为了搞好工商研究而利用人类学知识呢?还是为了促进人类学的发展而研究企业问题的?笔者认为,企业人类学,不但可以从人类学角度使企业研究兼顾企业的经济性和非经济性,也有利于研究“社会文化”的人类学家可以跟企业人士和企业研究者进行交往和交流,由此,打通了企业的“经济性”与“非经济性”之间的联系,或者说,在企业研究中的“经济性”与“非经济性”之间建立起了一个相互沟通的平台。
本质上,以企业人类学看企业,首先看到的是企业的社会性,接着才看到企业的经济性,接着就会兼顾企业的社会性和经济性。
二、从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看,企业人类学的国际性
一门学科是否具有国际性,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程度是两个重要考察指标。以下我们主要考察自2009年学科名称统一为企业人类学以来,其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的国际化情况。
(一)学术活动的国际性
自2009年企业人类学实现学科名称整合以来,到2015年这6年间,其学术活动已形成3个国际性系列会议、1个国内系列会议:始于2009年的“企业人类学国际论坛”,至今已办4次(昆明、安塔利亚、曼切斯特、千叶),今年7月将在泰国举办第5届(曼谷);始于2010年的“经营与人类学”国际会议(大阪、香港、北京、首尔),至今已办4次,明年将在日本办第5次会议(福冈);始于2012年的在国内举行的“国际工商人类学”研讨会(广州、上海、吉首、天津),至今已办4次;始于2012年的国内“企业人类学”研讨会(兰州、成都、大连),至今已办3次,今年9月将在贵州办第4届。[2]最近几年,企业人类学在国际和国内人类学与民族学界都是最为活跃的分支学科之一。
(二)学术成果的国际性
在2009-2015年六年时间里,企业人类学研究以东亚为主战场,在世界各个国家和地区得到了积极拓展,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涉及26个国家和地区。其中,亚洲和大洋洲有日本、澳大利亚、新加坡、泰国、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印度、中国大陆、中国香港等9个国家和地区,欧洲有西班牙、德国、英国、丹麦、荷兰、比利时、法国、瑞典、芬兰、波兰、葡萄牙、俄罗斯等12个国家,北美洲有美国、加拿大等2个国家,南美洲涉及阿根廷、秘鲁、古巴等3个国家。通过世界各国各地学者的共同努力,在国内外正式出版了中英文各类论著共13部(其中,4部英文论著、3部中英文双语论文集、4部中文著作、2部翻译作品等)以及一系列研究论文,取得了丰富的学术成果。[3]作为一门新兴的世界性前沿学科,企业人类学也是国际和国内人类学与民族学界中出版物最为丰硕的分支学科之一。
由上述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两方面的情况,我们可以看出企业人类学是一门国际化程度很高的学科。
三、研究范畴的不断扩展:从传统的到新兴的
几十年来,企业人类学在自身研究范畴(如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议题等)的不断扩展中,得以传播和发展。家庭企业是最具有社会性的企业类型,也是企业人类学的传统优势研究范畴,我们就从这里开始谈吧。
(一)家庭企业:企业人类学的传统研究范畴
在学科历史上,人类学和社会学对家庭婚姻、亲属称谓、亲属制度等有很多研究,自然而然地,当人类学和社会学关注商业经营、企业行为之类的事时,通常也会研究家庭与商业经营、企业行为之间的关系。
自20世纪50年代初以来的60多年时间里,很多人类学和社会学研究者都在解释海外华人经商致富的原因。他们大都将重视家庭或亲属纽带看作是华商成功的主要原因之一。持此论点的代表性人物是英国人类学家弗里德曼(Maurice Freedman,1920-1975)。弗里德曼于1946年结婚,并与妻子朱迪思·杰莫尔(Judith Djamour)一起进入伦敦经济学院攻读人类学,1948年获得硕士学位,其论文是《东南亚种族关系的社会学研究:以英属马来亚为例(The sociology of race relations on Southeast Asia with special reference to British Malaya)》。他的这篇论文对东南亚地区海外华人的家庭、婚姻、宗教和文化有较多的分析。1949年1月至1950年11月,受殖民地社会科学研究理事会(Colonial Social Science Research Council)委派,弗里德曼和夫人朱迪思·杰莫尔一起到新加坡,从事“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和“新加坡马来人的家庭结构”的田野调查工作。调查完成的两项报告——弗里德曼著的《新加坡华人的家庭与婚姻》和他夫人杰莫尔著的《新加坡马来亚人的亲属关系与婚姻》,分别于1957年和1959年出版。在此之前,1956年弗里德曼基于新加坡的调查资料写成了博士论文,并获得人类学博士学位。他有两部研究华南宗族的著作最有名。其一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1958年)。[4]他没有到过中国大陆,汉语水平也不高,但他通过对以新加坡为主的海外华人社区的考察,翻阅一些中国历史文献,加上阅读葛学溥、费孝通、林耀华、胡先缙、杨懋春、田汝康等人的有关作品,对华人宗族组织进行了深入而细致的剖析。其中,家户是独立的经济单位,家户之间的经济关系事实上或者在原则上受市场自由运作的调整。该书从福建、广东二地经济基础切入,细述了当地宗族的规模和组织结构,具体涉及宗族的房、支、户等各个层级以及不同层级在地方社区中的政治经济功能。他所得出的结论为:中国东南部(如福建、广东一带)大规模宗族组织得以存在的基础是高生产率的水利灌溉系统和稻作经济、共同财产、边疆社会、宗族精英与国家官僚之间的紧密连接*比如,土地的共同拥有在经济生活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主要是宗族和村落共同拥有土地(即:既是宗族的又是地域的群体)。在福建和广东,宗族和村落明显地重叠在一起。土地出卖受到两种不同权利的限制:1.土地要么只能在宗族范围内转让,要么在宗族成员选择之后才能转让给族外人;2.任何一个拥有土地的男人对他的儿子负有义务,任何土地的出卖都需要获得他们的一致同意。这两种限制也适用于许多租赁形式的土地所有,在田皮与田骨的权利之间作了区分。,由此分析宗族之间以及宗族与国家权力之间的关系。其二是《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与广东》(1966年)。[5]这本书虽然说是《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的续篇,但并未对前面著作所构建的宗族模型进行修正,也没有对其做出任何评论,只是依据后来掌握的某些材料对宗族的具体特性做了更细致的补充和进一步的说明,书中有大篇幅讨论了形成地方性群体的原因,试图从整体上把握中国宗族乃至社会全貌。这两本著作作为姊妹篇,一起使他的宗族理论显现出清晰的纹理,并赢得了相当多的追随者。*从20世纪80年代至今,从台湾地区到大陆,从美国到中国,不少人类学家对弗里德曼及其宗族理论进行了评述或反思。参阅Watson, L. James. 1982, “Chinese Kinship Reconsidered: Anthropological Perspective on Historical Research”, inChinaQuarterly, No.92;陈奕麟《重新思考Lineage Theory与中国社会》,《汉学研究》1984年第2卷第2期;陈其南《房与传统中国家族制度——兼论西方人类学的中国家族研究》,《汉学研究》1985年第3卷第1期;叶春荣《再思考Lineage theory:一个土著论述的批评》,《考古人类学学刊》1995年第50期;王铭铭《宗族、社会与国家——对弗里德曼理论的再思考》,《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年秋季卷总第16卷;常建华《20世纪的中国宗族研究》,《历史研究》1999年第5期;杨春宇、胡鸿保《弗里德曼及其汉人社会的人类学研究——兼评〈中国东南的宗族组织〉》,《开放时代》2001年第11期;张宏明《宗族的再思考——一种人类学的比较视野》,《社会学研究》2004年第6期;吴作富《弗里德曼中国宗族研究范式批判——兼论宗族研究范式的认同取向》,《南京大学学报(哲社版)》2008年第6期;杜靖《百年汉人宗族研究的基本范式——兼论汉人宗族生成的文化机制》,《民族研究》2010年第1期;师云蕊《古老异域的“迷思”——读弗里德曼〈中国宗族与社会:福建和广东〉及其他》,《社会学研究》2010年第2期。
弗里德曼对中国宗族的人类学研究,提出了一个颇类似于库恩(Thomas Kuhn)所界说的“范式”*范式就是一种公认的模型或模式,是人们所共同接受的一组假说、理论、准则和方法的总和。参阅Kuhn, Thomas Samuel,TheStructureofScientificRevolutions, Chicago: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2.。在他之前,福忒思(Meyer Fortes)对泰兰西人和埃文斯-普里查德(Evans-Pritchard)对努尔人的研究,提出了“裂变宗族制(the segmentary lineage system)”用以说明非洲的无政府、无国家社会。*在《非洲政治制度》一书中,埃文思-普里查德、福忒思等人已把社会分为两大类,一类是“A组社会”,即拥有中央化权威、行政机构与法律制度的社会,另一类是“B组社会”,即无政府统治的社会。无政府社会又分为两种,即政治结构与亲属制度完全融合的社会(社区)和所谓的“裂变宗族制”。参阅Fortes, M. & Evans-Pritchard, E. E., eds.AfricanPoliticalSystems. Oxford: 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40.弗里德曼认为,从非洲的“无文字社会”或“简单社会”中发展出来的模式,并不适用于中国,因为在中国这个文明古国中,既有中央集权式的制度,也存在着民间的宗族制度。他试图以对中国这个“文明社会”的实证研究,来反驳当时人类学界流行的范式。他的这种努力至今仍值得中国人类学家们借鉴。
很多社会学家和人类学家都以弗里德曼的亲缘理论为主要理论,探讨家庭及其亲缘关系对华人工商业经营、企业行为的影响。比如,施坚雅(G·William Skinner)于1960年比较分析了爪哇与泰国华人经济发展的异同[6];吴燕和(David Y·H·Wu)于1982年调查研究了巴布亚新几内亚华商[7];欧爱玲(Ellen Oxfeld Basu)基于对印度加尔各答华商的调查,1985-1992年间发表了一系列论文*Ellen Oxfeld Basu,1985,TheLimitsofEnterpreneurship:FamilyProcessandEthnicRoleAmongstChineseTannersofCalcuta, Ph.D. Dissertation, Department of Anthropology, Harvard University;1991a, The Sexual Division of Labor and the Organization of family and Firm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AmericanEthnologist, 18(4):700-7;1991b, Profit, Loss and Fate: The Entrepreneurial Ethnic and the Practice of Gambling in an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y, inModernChina17(2):227-259;1992,Individualism, Holism, and the Market Mentality: Notes on the Recollections of a Chinese Entrepreneur, inCulturalAnthropology,7(3):267-300。笔者2004年12月,曾到加尔各答郊区造访了这个华人(客家人)社区。,2013年在其正式面世的中文著作《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中,分析了第一、第二和第三代华人制革商的家庭和企业结构[8]等。尽管他们的观点各异,但在这一点上却是共同的,那就是都认为,家庭主义是华人成功的主要原因。首先,家庭或家族教导给个人价值观及社会行为的准则;其次,华人的同乡会、宗亲会等纽带维系着华人的亲缘网络。
美国家庭社会学家古德(William J. Goode)认为,由于中国有分家均产的习惯,家庭企业难以扩大规模。与中国相比,日本和英国的家庭企业可以把权力和财富都集中于长子身上。[9](P.266)古德的这个观点没有点到问题的要害。其实,日本经济以中小企业为主,30%以下的企业雇佣了日本全国总劳动力的70%;在美国,中小企业也雇佣了全国总劳动力的40%。[10](P.10)问题的实质应该是为什么家庭企业至今仍为家庭所有而没有发展成为由经理人管理的股份制公司。
美国社会学家科尔曼(James S. Coleman)认为,家庭企业挑选和聘用职员的范围,仅限于以家庭成员和亲属网络为基础的小圈子内,企业职工的平均质量不一定太高,很有可能会给企业带来一定的不良影响甚至损失。[11](P.121)毋庸置疑,企业只有在劳动力市场上按工作经验和工作能力选择和聘用职员,才能保证职员的质量和水平。然而,在更有效率的、更正规的聘用制度尚未形成之前,家庭及其亲缘关系依然是企业配置资源的重要方式。[12]
哈密尔顿(G. Hamilton)比较了西方和中国之后,指出:家庭企业及其亲缘网络是华人经济的基本单位。这些家庭企业网络的范围具有一定的伸缩弹性,可以根据不同的情境和需要调整自己关系网的范围,有时可以扩大,有时又可以缩小。[13]格林哈尔(S. Greenhalgh)[14]和迈克豪夫(T. Menkhoff)[15]等的研究都显示:华人商业成就和经济发展应归功于华裔的家庭伦理和家族企业。
在上文中,有鉴于以往经济学界较多地讨论的是家庭企业的消极面,为了改正一些不符合中国现阶段情况的看法,我们更多地讨论了家庭企业中的积极因素。[16]
(二)各类新兴企业:企业人类学的新型研究范畴
自人类学诞生之日起,一直以研究“简单社会”及其简单的社会组织为主。对人类学来说,现代社会是复杂的社会形态,企业组织是复杂的组织形态。
中国改革开放30多年以来,出现的各种类型的国内企业(如乡镇企业、私营或民营企业、股份制企业、少数民族企业等),各种中外合资企业和外国独资企业(如港资企业、侨资企业、跨国公司等),又在各个城市还留存着各种行业的百年老店和中华老字号(如全聚德、同仁堂)。人类学、民族学、社会学、民俗学、历史学等非经济管理类学科的学者,不满足于传统的家庭企业和家族企业研究,对上述各种新兴企业做了大量的调查和研究,形成了一大批有影响的学术成果。
第一,对农村社会兴起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改革开放初期,乡镇企业异军突起是中国经济腾飞中的一个重大现象。乡镇企业在中国大地的大江南北遍地开花。在乡镇企业的研究领域,中国和德国学者联合完成的一个研究项目值得注意*这个研究计划的主要成果是一套由山西经济出版社1996年推出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丛书”,如陈吉元和胡必亮主编的《当代中国的村庄经济与村落文化》、胡必亮和郑红亮的《中国乡镇企业与乡村发展》以及其它五本分别是关于中国五个不同省份的不同村庄的个案研究专著。。关于这些新兴企业的白手起家和兴旺发展,民间流传着各种版本的“传奇故事”。对分布于中国五个不同省份的五个不同村落的乡镇企业进行了调查和研究之后,胡必亮发现,几乎在每一个民间故事中,都可以看到乡镇企业的厂长、销售员或采购员,寻找、利用、编织、生产和再生产各种业务关系网的活动。[17]这些社会关系网的背后牵动着项目、批件、资金、设备、技术、原材料等各种稀缺的权力资源和经济资源。马戎、刘世定、邱泽奇等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取得了一批学术成果。*对乡镇企业的调查研究参见马戎、王汉生、刘世定主编《中国乡镇企业的发展历史与运行机制》,北京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戎、黄朝翰、王汉生、杨牧主编《九十年代中国乡镇企业调查》,香港:牛津大学出版社,1994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变迁研究》,华夏出版社,2000年。马戎、刘世定、邱泽奇主编《中国乡镇组织调查》,华夏出版社,2000年。邱泽奇著《城市集体企业个案调查》,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邱泽奇著《边区企业的发展历程》,天津人民出版社,1996年。他们指出,在依靠厂长的关系起家和发展的乡镇企业中,厂长的地位几乎是不可替代的。因为厂长私人掌握着这些特殊的人脉关系,是厂长个人的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撤换一个厂长,就意味着这个企业失去了“关系网”,损失了一批社会、经济和政治资源,甚至可能危及企业的存亡。李培林等从两个方面分析乡镇企业:一方面剖析了乡镇企业对外社会和经济交换的情况;另一方面,注意到在乡村社会中建立企业,可以将人们的特殊关系网络和乡村伦理道德套用在乡镇企业这种新型的企业组织形式上,虽然这有利于降低乡镇企业内部的组织成本,但却会增加乡镇企业对外的交易成本。[18](PP.64-77)
第二,关于国有企业社会成本的调查研究。20世纪90年代,李培林、张其仔、张翼、张海翔、杜发春等对国有企业展开调查研究,取得了一些成果。*对国有企业的调查研究参见李培林、姜晓星、张其仔著《转型中的中国企业》,山东人民出版社,1992年;张海翔、杜发春《民族地区县级国有企业改革研究》,《中央民族大学学报》1998年第2期。比较显著的成果是:2000年,李培林等运用国外近年来兴起的过密化理论,以社会成本为核心概念。此概念的内涵不同于科斯所谓的社会成本,它不是私人成本加上交易成本的总和,而是整个社会减去私人净收益所得的差,即国有企业用于承担非经济功能所付出的成本。作者基于对508家国有企业进行调查问卷,获得的大量鲜活资料,指出:国有企业亏损的主要原因之一就是它的社会成本巨大。作者通过对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的深入分析,找出了国有企业发展艰难的症结,从而寻求到了一条国有企业改革的合理道路。[19]笔者2010年对上海世博会进行了为期10多天的调查研究,发现:第一,世博会在上海举行,但其最高经营管理权不是上海市委市政府,而是中央政府;第二,世博会不是一个完全市场化的项目,而是一个政府主导的项目。由此,笔者从世博会的组织管理架构入手,分析了其运行目标和管理方式。*Zhang Jijiao, “‘Shanghai Expo’as a Nation-owned Enterprise——A Perspective of Enterprise Anthropology”,中牧弘允编《上海万博の经营人类学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番号:21242035),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12年3月,第91-108页。
第三,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全球500强跨国公司中,已经有近400家直接投资进入了中国市场。在北京,自1985年4月第一家投资性企业入京以来,到2002年底为止已有跨国公司119家。[20](P.153)到2003年底,跨国公司亚太地区或大中华地区总部设在北京的达到24家。2003年更多跨国公司和全球研发中心落户中国,20多家外企将其地区总部移到北京,40多家落户上海。[21](P.114)“狼”已经来了!加入WTO(简称“入世”),对于跨国企业来说已经不仅仅是机遇。当中国企业紧锣密鼓改造自己准备迎接入世挑战的同时,跨国公司也开始调整在华经营战略,力求尽快、大规模地融入中国经济与社会生活每个角落。跨国公司已经进一步把中国作为了自己的战略重点。笔者大约从18年前起开始接触跨国公司,即1997年第一次从事外资企业调查工作时,接触的对象是赫赫有名的跨国大公司——摩托罗拉。当时摩托罗拉在中国移动通信市场上处于遥遥领先的地位,在此种有利条件下,它对市场信息的高度重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后来,我又有幸为微软、惠普、通用电气、飞利浦、海德堡、爱普生、麦肯锡、美国乐泰等近10家国际知名企业提供过调查服务,陆陆续续地对IBM、西门子、思科、趋势软件、SAP、ABB、可口可乐、百事可乐、伊莱克斯、丰田汽车、通用汽车、壳牌、加德士、BP、美孚、爱索、爱森哲等近20家著名跨国公司,进行过研究分析,积累了一定的管理学、市场营销学、人力资源管理等与企业管理有关的理论和知识,出版了一系列管理学著作。*有关管理学研究参阅张继焦著《价值链管理:优化业务流程、提升企业综合竞争能力》,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张继焦、吕江辉编著《数字化管理:应对挑战,掌控未来》,中国物价出版社,2001年;张继焦、帅建淮编著《成功的品牌管理》,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张继焦、葛存山、帅建淮编著《分销链管理——分销渠道的设计、控制和管理创新》,中国物价出版社,2002年;张继焦编著《控制链管理:防范客户和应收账款风险》,中国物价出版社,2003年;G.德拉姆德和J.恩索尔著《战略营销:计划与控制》,张继焦、田永坡译,张继焦校,中国市场出版社,2004年。2003年,中国社科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将笔者主持的《外资企业的中国文化适应——对在华跨国公司行为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课题被列为所重点课题。与此同时,中国社会科学院青年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中心也将笔者主持的《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列为15个青年社会调研课题之一。所以,这项成果是笔者多年来从事“在华跨国公司”研究工作,写成的一份比较系统的研究专著。笔者认为,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的竞争,以1997年为分界线,可以把1978—1997年的竞争称为第一回合的竞争,从1998年开始的竞争称为第二回合的竞争。经过第一回合的竞争,跨国公司和中国企业在不同行业的竞争中,各有输赢。第二回合的竞争比第一回合的竞争更加残酷和激烈。有些行业,中国企业取得了优势的地位,比如,电视机、冰箱、空调、PC机等。但在另外一些行业,跨国公司占据了主导地位,最明显的是手机,然后是化妆品、洗涤剂、碳酸饮料等。2001年加入WTO之后,中国企业与跨国公司之间进入第三轮的竞争,即全方位的竞争。赢家必须是一个全能的冠军。无论研发、市场营销、生产管理、企业文化、资金、公关和行业知识等各方面都必须有很强的基础,有很强的竞争能力,才能在这一轮的竞争中形成优势。竞争中强者和胜者的核心在于世界优势加中国特色。跨国公司在产品研发、市场营销、全球经营体系支持、全面管理技能和雄厚的资金方面有强大的优势。而中国企业则在本地因素重要,行业比较成熟,技术相对稳定,或者可以从第三方获得这种核心技术的行业里取得比较大的优势。中国企业在本土化的产品设计、销售渠道、低廉的劳动力产品和本地政府关系方面享有一定的优势。总之,全面技能的提升和单项优势的迅速突破是中国企业下一步发展的必由之路。*张继焦主笔《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问题——对在华跨国公司行为的人类学调查与研究》,研究报告(18万字,184页),第175页。
第四,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及其接班人问题。多年来,社会学家张厚义、陈光金等对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进行了大量的调查研究,出版了一系列成果。*对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研究参见张厚义、陈光金主编《走向成熟的中国民营企业家》,经济管理出版社,2002年;张厚义、侯光明、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6)》,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4年;张厚义、明立志、梁传运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5)》,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3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4)》,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3)》,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2)》,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年;张厚义、明立志主编《中国私营企业发展报告(1)》,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9年。2010年在上海世博会上,中国民营企业联合馆由中国大陆16家在各领域内最具代表性的私营企业联合展出。*它们包括了中国最大的私营企业之一上海复星高科技有限公司、网络业龙头企业阿里巴巴公司、房地产大亨大连万达集团公司、家居业霸主之一的红星美凯龙国际家居连锁集团,影视业巨人华谊兄弟传媒股份有限公司,以及中国民生银行、苏宁电器有限公司、易居中国控股有限公司、上海美特斯邦威股份有限公司、浙江爱仕达电器股份有限公司等知名企业。此展出显现了改革开放后30多年来,私营企业成为中国由计划经济转为市场经济的开路先锋,是中国经济再度崛起的一股有生力量,具有惊人而旺盛的经营活力。笔者曾就私营企业问题分别于2012年3月在美国威廉与玛丽大学、2012年10月马来西亚拉曼学院等做了学术讲座,并以企业人类学的角度撰文向英语世界介绍中国的私营企业。[22]最近这些年以来,许多民企老总感到非常“头疼”的问题是“子女难承父业”。*比如,近些年万达董事长王健林对王思聪是否接班,充满着纠结:接班我不是一定要传给他。如果他出色,当然是最好的人选;如果不一定能担得起来,也不一定传给他,可以交给职业经理人。要看大家拥不拥护他,这帮老臣是跟了我的,如果传给他,这帮老臣能不能接受、能不能拥护?或是将来他要在我的公司慢慢培养他自己的权威,服众就传,不服众就不传。中国的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处于从“创一代”到“富二代”的交接班高峰期。企业领导人的接班问题已成为中国经济下一个十年的重要悬念。对此,不少华人学者认为:“富不过三代”是家族企业和民营企业的魔咒和怪圈,不仅是中国企业,而且是全世界华人企业发展的普遍规律。*我多次听到香港大学王向华教授阐述中国家族企业“富不过三代”的观点。比如,由国际企业人类学委员会和香港大学现代语言与文化学院联合主办的“企业与社会”工作坊,于2010年8月12-13日在香港大学举行。参阅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新探索:近些年的学术活动及其研究动态》,《创新》2015年第3期。目前,“富不过三代”既是民营家族企业发展壮大的烦恼,也是企业在经济新常态下转型升级亟待破解的难题。有没有化解“富不过三代”魔咒的良方和灵丹妙药呢?对于企业领导人交接班这个问题,相对而言,浙江商人的思考和探索比较多。[23](PP.123-132)[24](PP.284-294)在此,笔者试图从中国学者自己建立的“品牌企业案例库”中,找出清华池这个典型的百年“老字号”企业作为论据,进行企业人类学的案例分析。[25]
第五,对老字号现代转型的钻研。现代社会中的老字号,近些年成为了一些非经济管理学者关注对象。比如,民俗学家刘铁梁、董晓萍、王焯等对老字号的调查与思考*对老字号的研究参阅刘铁梁主编《中国民俗文化志:北京·宣武区卷》,第三章“繁华市井大栅栏”中有一节专门谈老字号,即第三节“老字号里的生活”,中央编译出版社,2006年;董晓萍等《现代商业的社会史研究:北京成文厚(1942—1952)》,《北京师范大学学报》2010年第2期;董晓萍《技术史的民间化——清宫造办处传统手工行业现代传承老字号的田野研究》,《辽宁大学学报》2013年第6期;王焯著《中国老字号的传承与变迁》,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年。,历史学家定宜庄等人对老字号的口述历史记录和分析*作者走访了乐曙青、沈芳畦、乐侠等同仁堂乐家后人,贾荫生、贾怀增、李建勋、李荣福等同仁堂的老药工、老领导,以及企业员工,并收集到乐家后人乐笃周从未公开发表过的自述手稿,通过口述史料与文献考证相结合的形式,生动地展现了同仁堂乃至北京中药业百年来的兴衰更迭,以及同仁堂在企业运作、制药理念、管理模式、主雇关系、生产营销等方面鲜为人知的故事。参阅定宜庄、张海燕、邢新欣著《个人叙述中的同仁堂历史》,北京出版社,2014年。。企业人类学以老字号研究为抓手,已建立起一支全国性的队伍:北京、上海、天津、广州、浙江、辽宁、重庆、云南、湖北、湖南、江苏、吉林、山东、广西、福建、河北等16个省市学术研究机构和大专院校的专业人才,与各地行业协会、企业近400余位从业人员保持适时互动。大家共同的关注点是:老字号企业的现代转型,即在激烈的市场竞争中(特别是在新一轮的经济危机当中),中华老字号、全国各地的省级和市级老字号,面对着严峻的挑战,如何重振昔日雄风。这个老字号研究团队的成果不断推出:2011年发布了第一部老字号蓝皮书[26],2013年继续发布了老字号绿皮书[27],一批以老字号为研究对象的论文陆续在《思想战线》*比如,《思想战线》先后发表的老字号论文:张继焦、李宇军《中国企业都“富不过三代”吗?——对“老字号”企业的长寿秘籍和发展前景的社会学分析》,《思想战线》2012年第4期;张继焦《从企业与政府的关系,看“中华老字号”企业的发展——对鹤年堂、同仁堂的比较研究》,《思想战线》2013年第3期。《广西民族大学学报》*比如,《广西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5年第2期发表了一组老字号论文:张继焦《“自上而下”的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老商街、老字号的分析》;殷鹏《企业社会责任的中国视角:对“老字号”企业的观察》;尉建文、刘波《“老字号”企业技术创新影响因素的实证分析》。《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比如,《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4年第4期上发表了一组三篇老字号研究论文:李宇军、张继焦《中国“老字号”企业的经营现状与发展前景》;赵巧艳、闫春《广西“老字号”发展建设研究报告》;陈阁《“老字号”品牌的文化保护与传承——以长沙老字号“火宫殿”为例》。2015年第1期上接着发表了一组两篇老字号研究论文:张继焦、李宇军《观察中国市场转型的一个新角度:地方政府与老字号企业的“伞式”关系》,陈丽红《北京西城区老字号品牌在建设世界城市中的作用》。《创新》《中国民族报》*比如,《创新》和《中国民族报》分别发表的老字号论文: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创新视角:老字号的研究现状、现实意义和学术价值》,南宁市社科院《创新》2015年第1期。张继焦《老字号、老商街如何重拾竞争力》,《中国民族报》2014年9月12日第6版整版。等期刊报纸和一些国外出版物*比如,张继焦《上海世博会:“老字号”企业的盛典性“事件营销”——以上海杏花楼为例》,中牧弘允编《上海万博の经营人类学研究》(研究成果报告书,课题番号:21242035),日本国立民族学博物馆,2012年3月,第141-154页;Zhang Jijiao, 2013,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Enterprise and Government: Case Study on Two “Chinese Old Brand” Companies (Heniantang, Tongrentang),JournalofChineseLiteratureandCulture, Vol. 1, No.2, November, Kuala Lumpur: University of Malaya, pp.1-24.上发表,案例分析和行业研究的内容丰富多彩,形成了系列性的老字号专题研究论文,极大地推进了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建设,提升了企业人类学的学科地位。
总之,与传统人类学主要研究简单社会组织不同,企业人类学对现代社会中的各种类型的企业,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老字号企业等复杂组织进行了调查研究,大大扩展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由此,企业人类学的研究内容和研究议题也相应地得到了丰富和发展,涉及到了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国有企业的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的接班人问题、老字号的现代转型等复杂的现代组织问题,扩充了企业人类学的研究范围。在很大程度上,对各类企业组织的研究夯实了人类学作为现代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不但增强了人类学研究当代组织的学术能力,而且强化了人类学与经济学、管理学等学科的对话能力。
四、研究方法的持续创新
一门学科要确立学科地位和获得长足发展,必须要有自己创新性的研究方法。然而,人类学用于研究简单社会组织的那些研究方法,在面对复杂的现代企业组织时,显得有些捉襟见肘,需要有所创新。
(一)整体论:从简单组织到现代复杂企业
整体论(holism)是很多学科都经常使用的分析视角。在人类学圈里,整体论被视为是本学科的一种独特的方法,[28]也是一种人类学界公认的、最常用的分析方法。但是,由于传统人类学主要研究的是传统的村落或简单的社会,所以,它所谓的整体观通常指的是对简单的社会或组织的整体观。
美国人类学家提出的“人际关系”理论*该学派早期理论的代表人物有原籍澳大利亚的美国人埃尔顿·梅奥(Elton Mayo)、美国的罗特利斯伯格(F J Roethlisherger)提出的“有效管理理论”。这种有效的管理,就是要了解人的行为,特别是劳动小组的行为。为此,要采用激励、劝告、领导、交流等处理人与人之间关系的技能,通过有效的传播活动达到管理的目的。,是人类学在研究企业时对古典整体论的发展。这个理论把社会科学的各种有关理论、方法和技术等,用来研究企业内部个人与个人之间的关系、企业中的正式组织和非正式组织,以及企业与外部社会环境的关系等。
在苏联、东欧等国家发生变革之前,支配西方社会科学界对这些社会主义国家的研究思路主要有两种研究范式:极权主义范式*极权社会有两个显著的特征:第一个特征涉及政党与其支持者之间纽带的性质。在作为资本主义另一极的极权主义看来,政党与支持者之间是一种意识形态性的,以意识形态为基础的关系。即使在革命成功以后,意识形态取向仍是社会动员的基本手段。第二个特征可以称为社会的原子化。这种社会不强调区别私人领域和公共领域的合法性,凡是直接妨碍执政目标实现的社会纽带均消失了。“原子化大众”的存在,不仅为维持权力所必须,而且可以确保毫无障碍地对群众进行总体性动员。和现代化范式*对于现代化范式,主要的观点认为,在社会主义革命以后,一旦政权得到巩固,社会主义社会就必然致力于经济发展。这种增长要求实现现代化和引进现代技术,而工业化和现代科学技术又要求有一套相应的现代价值观和制度,从而导致社会主义制度结构的变迁。现代化的过程将以自己的必然逻辑使社会主义国家按照西方发达国家的模式对自己进行重建。。然而,20世纪80年代以来,苏联、东欧发生了一系列的重大经济社会变革,这两种范式显然都没有足够的解释力。一般认为,影响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主要有两只手:一只是看得见的手——“政府”,另一只是看不见的手——“市场”。早在23年之前,1992年李培林首次提出了“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他认为,中国正处于一个社会结构的全面转型期,即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从乡村社会向城镇社会、从封闭半封闭社会向开放社会等的结构性转型。社会结构自身拥有相当大的活动空间和变动弹性,在发生社会结构性变动时,处于社会结构之中各种行为方式、风俗习惯、道德伦理、价值观念、利益格局和运行机制等,会形成一种巨大的推动力量。这“另一只看不见的手”作为一种资源配置的实际方式,不仅从整体上推动着社会发展,而且会从深层次上影响着产业结构的调整方向和经济体制的改革方向。*关于“社会结构转型理论”的基本命题,主要体现在被称为“社会结构转型三论”的三篇论文里:李培林《“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结构转型》,《中国社会科学》1992年第5期;李培林《再论“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社会学研究》1994年第1期;李培林《中国社会结构转型对资源配置方式的影响》,《中国社会科学》1995第1期。由中国学者提出的这一理论,推动了经典的整体论向前发展了一大步。它提倡从整个社会结构的角度看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对国内外社会科学界都有一定的影响。
在李培林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影响下,经过多年思考,笔者对中国的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先后创新性地提出了一对(两个)新概念:2014年提出的“伞式社会”,用于观察和分析政府主导的资源配置和经济社会发展[29];2015年提出了“蜂窝式社会”,用于观察和分析普通老百姓自我开展的资源配置方式和对经济社会发展的影响。[30]这两篇企业人类学论文,从社会结构和市场转型的整体性视角,探讨了中国经济崛起的内在动因和巨大的经济社会转型的结构性因素。
(二)研究范式的转变
对城市经济社会的有关研究,二分法是最为常用和基本的分析框架。社会学和经济学出现了不少经典的“传统—现代”二分法模式。比如,梅因(H. Maine)关于“身份社会”与“契约社会”的对立(1861)[31](p. 170),滕尼斯(F. Tonnies)关于“礼俗社会”与“法理社会”的对立(1887)*Tonnies, F. , 1887,GemeinschaftundGesellschaft(CommunityandSociety), Leipzig: Fues's Verlag, 2nd ed. 1912, 8th edition, Leipzig: Buske, 1935. translated and edited by Charles P. Loomis, 1957, The Michigan State University Press. pp. 223-231.,涂尔干(E. Durkheim)关于“机械团结”与“有机团结”的对立(1893)*Durkheim, E. ,1893,TheDivisionofLabourinSociety(French: De la division du travail social). Translated by W. D. Halls. 1997, New York: Free Press. Chapter II: Mechanical Solidarity, Or Solidarity by Similarities.,韦伯(M. Weber)关于“前现代社会”与“现代社会”、“实质合理性—形式合理性”和“传统性统治—合法性统治”的对立(1921-1922)*Weber, M. , 1922.WirtschaftundGesellschaft(EconomyandSociety), 2 volumes, Germany; Bendix, Reinhard. Max Weber, 1921-1922,TheTheoryofSocialandEconomicOrganization. Translated by Parsons together with Alexander Morell Henderson in 1947.,雷德菲尔德(R. Redfield)关于“俗民社会”与“都市社会”的对立(1947)[32],帕森斯(T. Parsons)关于“特殊价值”与“普遍价值”的对立(1951)[33],刘易斯(A. Lewis)关于“传统部门—资本主义部门”的对立(1954)[34]等,都体现了“传统—现代”处于两极的研究思路。
李培林针对“传统—现代”的二元对立分析模式,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他指出,在我们那些已经习以为常的二元对立(如私有企业和国有企业、乡村和都市、传统与现代等)之间,事实上都存在着“连续谱”的真实世界。[35]陈国贲和张齐娥也认为:城市移民并不是一个新的研究课题。但是,将移民与企业家精神联系起来,去认识移民如何随着时光的推移把自己改造为小商小贩、商人、企业家、实业家的过程却是相当新颖的。他们摆脱了原有的社会经济结构,得到了新的发展机遇,在城市中找到了新的生活,创造出了新的社会经济结构。*参阅该书的中英文版本:陈国贲和张齐娥著《出路——新加坡华裔企业家的成长》,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6年,第386-387页;Chan Kwok Bun & Claire Chiang See Ngoh,1994,SteppinOut:TheMakingofChineseEntreprenuers, Simon & Schuster(Asia) Ltd.
因此,对城市移民及其经济社会的研究,笔者超越“对立—同化”二分法,吸收了部分社会学家、人类学家提出的“并存”分析模式和部分经济学家、政治学家提出的“联结”分析模式,采用了“并存-联结”分析模式,简称“并联”分析模式。[36]由此,我们可以类推出,在中国少数民族新移民在城市中要转变或创建本民族的经济社会结构。民族企业是一个经济社会组织形式,是转变或创建本民族在城市中新的经济社会结构的社会基础,没有民族企业这个结构性的实体作为依托,新的经济社会结构将无立足之地。在民族企业这个实实在在的经济社会组织中,企业家可以运用本民族自身显著的家庭、民族价值观、文化特征、社区、社会关系网络等民族资源,获得创业资本、廉价劳动力、商业信用等,谋求民族企业和本民族新型经济社会结构的创立和发展。[37]
(三)“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视角相结合
人类学家通常喜欢选择弱势群体、少数民族、妇女儿童、底层百姓等作为研究对象,对弱者具有天生的同情心,其研究视角通常或者是非常草根,或者是“自上而下”的,很少有向上的研究或者“自上而下”的视角。
如何将学者们常用的“自下而上”研究思路与各级政府常用的“自上而下”工作思路两种视角,更好地结合起来?这是人类学界长久以来一直没有很好地解决的问题。笔者正在思考这个问题。比如,对老字号、老商街与城市竞争力三者之间的关系,笔者分别从“自下而上”的视角和“自上而下”的视角,各写了一篇文章:
“自下而上”的分析框架,大致分为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微观地对老字号经营方式的个案分析;第二个层次为中观地对城市局部地区(尤其是那些老字号集聚的老商街)的分析;第三个层次为宏观地对城市竞争力进行整体性分析。[38]
与“自下而上”的视角相反,“自上而下”分析框架的三个层次:第一个层次为宏观地对城市竞争力进行整体分析,主要表现为“城市发展规划”。在城市发展规划的顶层设计框架下,把老商街、老字号企业作为局部区域或个别企业放在其中。第二个层次为中观地对城市街区的分析,常见的表现为“商业街发展规划”、“城市商业发展规划”。老商街上的各家老字号企业,只是政府制订这两类发展规划时的参考性个案资料。第三个层次为对老字号企业个案的微观记录和描述,只是政府制订上述两种城市规划的个案性、基础性资料。[39]
由此,我们体会到:一方面,与“自上而下”的研究视角相比,“自下而上”的分析路径有些不足:有时候会“只见树木,不见森林”,只看到个别老字号企业、个别老商街,看不到整个城市发展的全貌;有时候会忽视城市政府的发展规划、老字号企业所在商街的发展状况。另一方面,老字号、老商街是一个值得不断挖掘的宝藏。与城市规划者和城市经济学者不同,企业人类学可以以老字号和老商街的实证研究为基础,来分析城市竞争力。城市规划者的城市商业分析和城市经济学者的城市竞争力分析,由于缺乏对老字号和老商街进行微观的、基础性研究,其城市商业分析和城市竞争力分析是不够深入和扎实的。
我们希望:越来越多的城市政府官员和城市规划者意识到,企业人类学者基于老商街和老字号的“自下而上”调查研究的学术价值和现实意义。老字号和老商街是城市发展的宝藏,如果能够不断挖掘老字号的经济资源和复兴老商街的商业活力,可以深化城市商业的分析,可以进一步增加城市竞争力。
总之,在一批学者的不断努力和尝试下,针对“传统—现代”二分法僵化研究模式,提出了“连续谱”的概念,实现了研究范式的转变;有些学者正在尝试着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视角相互结合;人类学的整体论从研究简单组织的视角,转变为了分析现代复杂企业的观点;李培林1992年首次提出的“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已被中国企业人类学奉为最为重要的理论源泉之一,大大提升了人类学对企业的分析能力和对经济社会转型的解释力。企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有了一定的创新和发展,其理论水平也上了一个台阶。
五、总结、思考和启示:企业人类学的兴起和未来发展前景
(一)总结:企业人类学的产生标志着人类学第四次革命
在人类学发展的100多年时间里,人们用人类学知识探讨了当今各类企业现象。当20世纪30年代企业人类学产生的时候,其名称为“工业人类学”,因其从属性太明显,尚未开启人类学真正意义的第四次革命。*人类学的第一次革命是对原始民族的研究,第二次革命是对农民社会的研究,第三次革命是对都市社会的研究,第四次革命是对现代各类企业的研究。其后经历了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同发展阶段,因其独立性都不太充分,只能算是为开启人类学第四次革命的不同准备过程。经过几十年的积累,到了2009年国际学术界正式统称为“企业人类学”,才真正开启了人类学的第四次革命。
由上述我们可以知道,在国内外一大批学者80多年来的持续探索基础上,2009年以来的六年间这个学科在学科名称、研究对象、研究范围、研究方法、学术活动、学术成果等各个方面,不但已有相当多的开拓性研究,而且已创新地形成了一套比较完整的学科体系,所以我们说,企业人类学是真正意义上人类学的第四次学科革命。换言之,与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相比,企业人类学才是名副其实的人类学第四次学科革命。
在研究范畴方面,企业人类学突破传统的家族企业研究模式,进入一些新兴的研究领域、研究对象、研究议题等。企业人类学克服了人类学侧重于研究简单社会组织学术传统的束缚,展开了对各种复杂企业(如乡镇企业、国有企业、跨国公司、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老字号企业等)的调查研究,大大扩展了人类学的研究对象。企业人类学好像注入了新鲜血液一样,其研究主题也相应地变得丰富起来,涉及到了一些现实经济社会中的重大议题,如乡镇企业兴起的原因和途径、国有企业运营的社会成本、跨国公司在中国的本土化、私营企业或民营企业未来发展的接班人问题、老字号企业在市场经济下的现代转型等复杂的现代组织问题,扩充了企业人类学的研究范围。这些对复杂企业组织的探索性研究,进一步夯实了人类学作为一个现代学科的基本研究范畴,不但增强了人类学研究当代各类企业组织的学术能力,而且强化了人类学与应用经济学、企业管理学等显性学科的对话能力。因此,我们可以说,称企业人类学开创了人类学第四次学科革命,是名正言顺的。
最近一些年,企业人类学的研究方法也有了明显的创新,其理论水平也登上了一个新的台阶。在国内外一些知名学者的学术倡导或理论引导下,“传统—现代”二分法这种被奉为经典的研究模式,得到了突破,研究范式实现了重大的转变;有的企业人类学者不但努力走出人类学“自下而上”研究视野的藩篱,提出了“自上而下”的新角度,而且正在尝试着将“自下而上”和“自上而下”两个不同的学术视角有机地结合起来;有的企业人类学者已经突破了整体论主要用于研究简单社会和简单组织的局面,已经使用整体论来分析复杂的现代企业;“社会结构转型”理论(或称“另一只看不见的手”理论)被中国企业人类学尊为最主要的理论源泉之一,极大地增强了人类学对复杂的企业的解析能力、对经济社会结构及其转型的解释能力。
近些年,企业人类学的学术活动已形成了比较制度化的学术交流机制,其学术成果比较丰富和体系化。在学术活动方面,已出现了一系列定期和不定期召开的国际学术会议和国内研讨会,已呈现了一套比较规范的国际或国内学术交流机制;在学术成果方面,已正式出版了10多部中、英文著作和一系列中英文论文。企业人类学研究者及其研究对象涉及五大洲(亚洲、大洋洲、欧洲、北美洲、南美洲)的26个国家和地区。简言之,企业人类学的学术活动和学术成果两方面的国际化程度都很高。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不只是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事,也是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一件大事。
总的来说,企业人类学虽然诞生于80多年前,但是,直到最近几年才在国际上完成了学科名称统合,并逐渐形成一门具有独特的研究范式、拥有比较完整知识体系的学科。从学理上特别是从学科知识体系上看,我们说企业人类学开创了人类学第四次革命,不是徒有虚名的,与工业人类学、组织人类学、工商人类学、经营人类学等不同名称相比较,这门学科基本实现了“名”与“实”相结合,真正称得上是“实至名归”的人类学第四次革命。
(二)思考:企业人类学的兴起意味着人类学发展的局部突破
最近一些年,人类学民族学研究议题呈现多元化和分散性,学科理论更新换代较少。*2014年11月,在日本大阪国立民族学博物馆参加一个会议期间,我当面请教黄树民教授:“当今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的发展状况如何?”黄树民教授认为:“当今的国际人类学民族学没有一种主导性的理论或主流的研究领域,呈现出分散性和多元化的特点。”笔者认为,无论是整个国际人类学民族学界,还是整个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界,都不可能出现全局性的、飞跃性的发展,只有可能出现个别或一些局部性的突破,如某个学科或某个研究领域在某些研究对象、研究方法等的尝试或创新。换言之,我们所期待的:全世界的或全中国的人类学民族学出现全面性的腾飞,只是一种奢望,这样全局性的学科繁荣不可能会出现。企业人类学的产生只是意味着人类学民族学发展的局部突破。
由于亚洲“四小龙”(韩国、新加坡、中国台湾、中国香港)的兴起、中国作为新兴经济体的崛起,特别是亚洲“四小龙”和中国发生了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的巨变过程[40],出现了各种类型的企业及整个经济社会结构的剧烈转型,整个学术市场出现了对各种类型企业研究的巨大需求,企业人类学在学术“需求—供应”驱动下应运而生,成为了整个人类学民族学停滞或缓慢发展中的局部突围,算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中新兴的学术增长点。
在目前的国际和国内学术背景下、在学术市场的“需求—供应”条件下,人类学民族学较为可行的发展路径有两条:其一,寻找新的发展空间,并通过努力获得新的学科发展增长点;其二,在传统的学科领域里,进行创新性的探索。以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现状来看,与企业人类学的情况类似,在非物质文化遗产、民族旅游、民族节日等几个方面,都找到了新的学术发展空间,都是人类学民族学发展出现局部突破的体现。相反,由于学术需求不强,欧美作为人类学民族学传统优势地区却出现了衰落。因此,企业人类学的兴起在一定程度上意味着人类学民族学在中国和亚洲的局部崛起。
(三)启示:中西方人类学的关系与企业人类学的未来发展
西方学术界之所以傲视我们非西方学术,是因为我们只有事实陈述而没有自己的理论,我们的研究只是为他们的理论提升提供原始材料。弗里德曼曾指出,人类学对中国社会的传统研究不乏事实材料,应该通过系统性的重组,将民族志和历史材料结合起来进行深入分析,形成一些表述清晰的理论观点。[41][42](PP.417-419)作为一个国际性学科,企业人类学不但打通了中国与西方人类学的通道,而且,由于最近30多年来中国和亚洲一些国家和地区的经济腾飞,使这些国家和地区成为了人类学民族学创新发展之地,实现了人类学民族学局部突围和学科转型。
笔者认为,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的研究不能只停留在悲情地事实描写或者愤青式揭露问题,中国各种类型企业的兴起及其引发的整个经济社会结构转型,必有自己的运行规律,值得我们提升到一定的理论。我们应该有中国人的理论自信,应该运用社会科学各种原理,分析各种类型企业两重性——经济性和社会性,应该也可以基于本土的调查思考,并提出本土的企业人类学新理论。希望本文能够抛砖引玉,激发起我们新一代学者的共同努力,一起形成中国特色的人类学理论和学派。
参考文献:
[1]张继焦.企业人类学:作为一门世界性的前沿学科[J].杭州师范大学学报(社会科学版),2014,(4).
[2]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新探索:近些年的学术活动及其研究动态[J].创新,2015,(3).
[3]张继焦.企业人类学:近些年的最新学术成果和研究进展[J].创新,2015,(4).
[4]Freedman, Maurice.LineageOrganizationinSoutheasternChina[M].London: The Athlone Press,1965,1958.
[5]Freedman, Maurice.ChineseLineageandSociety:FukienandKwangtung[M].New York: Humaniies Press,1966.
[6 ] William Skinner. Change and Persistence in Chinese Culture Overseas: A Comparison of Thailand and Java[J].theSouthSeasSociety,1960,16(1-2).
[7]David Y.H.Wu.TheChineseinPapuaNewGuinea,1880-1980[M].Hong Kong: Chinese University Press,1982.
[8][美]欧爱玲.血汗和麻将:一个海外华人社区的家庭与企业[M].吴元珍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3.
[9][美]威廉·J·古德.家庭[M].魏章玲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86.
[10]David Friedman.PoliticalChangeinJapan[M]. Ithaca: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1988.
[11][美]詹姆斯·科尔曼.社会理论的基础:上册[M].邓方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1992.
[12]张继焦.亲缘交往规则与家庭工业[J].中央民族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1998,(4).
[13]Hamilton, Gary G.BusinessNetworksandEconomicDevelopmentinEastandSoutheastAsia[M].Hong Kong: Centre for Asian Studies, University of Hong Kong,1990.
[14]Greenhalgh, S. Land Reform and Family Entrepreneurship in East Asia[J].PopulationandDevelopmentReview,1990,(15).
[15]Menkhoff, T.TradeRoutes,TrustandTradingNetwork:ChineseSmallEnterprisesinSingapore[M]. Saarbrucken Fort Lauterdale: Verlag Breitenbach Publishers,1993.
[16]张继焦.市场化过程中家庭和亲缘网络的资源配置功能——以海南琼海市汉族的家庭商业为例[J].思想战线,1998,(5).
[17]胡必亮.“关系”规则与资源配置——对湖北、山西、陕西、广东、浙江五省乡镇企业发展的典型研究[J].中国社会科学季刊(香港),1996,(16).
[18]李培林,王春光.新社会结构的生长点——乡镇企业社会交换论[M].济南:山东人民出版社,1993.
[19]李培林,张翼.国有企业社会成本分析[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0.
[20]王志乐.2002-2003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3.
[21]王志乐.2004年跨国公司在中国投资报告[R].北京:中国经济出版社,2004.
[22]Zhang Jijiao.China’s Private Enterprises: A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Perspective[J].AnthropologyNewsletterofNationalMuseumofEthnology, Osaka,2012,(34).
[23]张继焦.新一代商人群落的研究之一——从企业人类学角度,分析浙商的产生和群体特点[M]//企业和城市发展:并非全是经济的问题.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3.
[24]陈振铎.民营企业家的女性代际传承——浙江个案的企业人类学研究[M]//张继焦.新一轮的城市化、工业化、市场化、文化多元化:对全球化和现代化的探讨.北京:知识产权出版社,2015.
[25]张继焦.如何破解“富不过三代”的魔咒:百年老字号“清华池”案例的企业人类学分析[J].广西经济管理干部学院学报,2015,(2).
[26]张继焦,丁惠敏,黄忠彩.老字号蓝皮书——中国“老字号”企业发展报告No.1(2011)[R].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
[27]张继焦,刘卫华.老字号绿皮书——老字号企业案例及发展报告No.2(2013-2014)[R].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2013.
[28][美]高斯密.论人类学诸学科的整体性[J].张海洋译.中央民族大学学报,2000,(6).
[29]张继焦.“伞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结构转型的一个新概念[J].思想战线,2014,(4).
[30]张继焦.“蜂窝式社会”——观察中国经济社会转型的另一个新概念[J].思想战线,2015,(3).
[31]Maine, Henry James Sumner.AncientLaw,ItsConnectionwiththeEarlyHistoryofSociety,andItsRelationtoModernIdeas[M]. London: John Murray,1861.
[32]Redfield, Robert. The Folk Society[J].AmericanJournalofSociology,1947,( 52).
[33]Parsons, T.TheSocialSystem[M]. New York: The Free Press,1951.
[34]Lewis, W. Arthur. Economic Development with Unlimited Supplies of Labor[J].ManchesterSchoolofEconomicandSocialStudies,1954,(22).
[35]李培林.巨变:村落的终结[J].中国社会科学,2002,(1).
[36]张继焦.经济文化类型:从“原生态型”到“市场型”——对中国少数民族城市移民的新探讨[J].思想战线,2010,(1).
[37]张继焦.中国城市民族经济文化类型的形成——民族企业和民族企业家的作用[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0,(5).
[38]张继焦.老字号、老商街如何重拾竞争力[N].中国民族报,2014-09-12.
[39]张继焦.“自上而下”的视角:对城市竞争力、老商街、老字号的分析[J].广西民族大学学报,2015,(2).
[40]张继焦.企业人类学的角度:如何看待新一轮的工业化、市场化、城市化[J].创新,2015,(2).
[41]Freedman, Maurice. A Chinese Phase in Social Anthropology[J].BritishJournalofSociology,1963,14(1).
[42]Skinner, G. William.TheStudyofChineseSociety:EssaysbyMauriceFreedman[M].Stanford: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1979.
(责任编辑:吴芳)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Discipline System Construction,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ZHANG Ji-jiao
(Institute of Ethnology and Anthropology, Chinese Academy of Social Sciences, Beijing 100081, China)
Abstract:On the basis of 80-year work both at home and abroad, a great deal of explorative work has been done o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study from the following perspectives: discipline name, research subject, scope and method, academic activities and achievements, etc. As a result, a complete and systematic discipline framework has been innovatively established, which marks a partial breakthrough and the 4threvolution i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As an international discipline,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plays a role to connect the anthropology between China and western countries. As far as its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and future prospect are concerned, China and some countries and regions in Asia are supposed to be a promising place for the innovative development of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Therefore, based on their investigations and reflections from a local perspective, scholars in China should propose new theories on enterprise anthropology.
Key words:Enterprise anthropology; discipline system; current development situation; future prospect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13
中图分类号:C912.4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106-13
作者简介:张继焦(1966-),男,海南海口市人,中国社会科学院民族学与人类学研究所社会研究室主任、研究员,兼任国际人类学与民族学联合会专业委员会理事会代理理事长(相当于联合会副主席)、中国人类学民族学研究会副秘书长,主要从事社会人类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特别委托项目“21世纪初中国少数民族地区经济社会发展综合调查”(13@ZH001)和国家社会科学研究基金一般项目“我国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及其管理研究”(10BMZ006)的研究成果。
主题研讨三企业人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