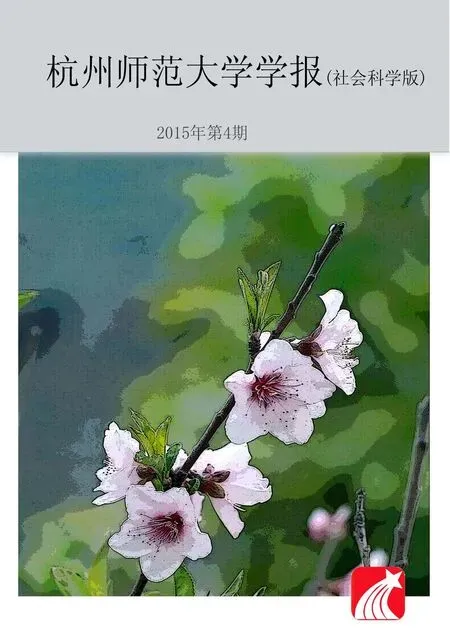知识共同体——维多利亚文人的智性探求
2015-03-28高晓玲
高晓玲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知识共同体——维多利亚文人的智性探求
高晓玲
(郑州大学 外语学院, 河南 郑州 450001)
摘要:没有哪个时代像维多利亚时代这样如此关注知识的本质问题。当时几乎所有重要的文人都在思考知识问题,探求人类智性的边界,反思认识活动带来的后果。尽管他们的学科领域看似泾渭分明,关注焦点也各有不同,然而细读和比较会让我们发现,他们的话语在深层处彼此交叠,相互渗透,形成了一个独特的知识共同体。这个共同体追求整体性而非分化的专业知识,看重健全心智而非职业人士的培养;他们把知识与道德价值和审美情趣紧密关联,成为动荡时代为大众提供精神导引的中坚力量。
关键词:维多利亚时代;文人;知识共同体;科学;文学
从维多利亚时代延续至今的科学与人文之争,常常由于评论者所持单方立场而被片面夸大,让读者误以为当时的科学家与文学家之间处于水火难容的紧张关系当中。这一观点在近年的维多利亚研究中得到了一定程度的反拨,很多评论家开始关注两者之间的共识共通之处。比如乔治·列文(George Levine)在《写实主义、伦理和世俗化:维多利亚文学与科学论集》中指出,人们夸大了赫胥黎和阿诺德之间的冲突,实际上两个人不仅是生活中的好朋友,即使在思想领域也是共识大于分歧,两人论争的文章中有不少轻松调侃的成分。他们的总体目标都是希望能够改变英国人过分狭隘和实用的思维方式,使他们的思想变得更加开放也更有温情。[1](P.124)劳拉·奥蒂斯(Laura Otis)在《十九世纪文学与科学选集》中也力图消解人们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误解。这个选集的编排方式沿袭了维多利亚时代的知识传播方式,把涉及同一话题的科学与文学作品杂糅在一起,互为参照。奥蒂斯指出,在维多利亚时代,科学和文学作品常常在同一期刊杂志中并行发表,科学家与文学家们互相引证以吸引或说服读者。因此,当时的文学与科学之间不存在所谓的“割裂或沟壑”,因此也不需要搭建什么“桥梁”。[2](P.2)苏珊·安杰(Suzy Anger)在《认识过去:维多利亚文学与文化》中也指出维多利亚研究的这些误区:对维多利亚时代的认识已经陷入了一种非此即彼的困境中,而在这中间是有其他可能性存在的。[3](P.1)以上这些评论的整合性思维方式显然比二元对立更能贴切地描述维多利亚时代的精神特质。本文所要讨论的便是这样一种可能性,进而探究科学家和文学家在“知识”问题上的话语交叠与融合,聆听维多利亚时代杂多语声中的和谐音符,即维多利亚文人构建的知识共同体。
之所以用“文人”(man of letters)概念,是因为该表达方式在维多利亚时代仍然具有鲜活的生命力,常常被用来统称“有学问的人或学者”。这个时期的文人不同于现代的专业人士,他们大多会对自己专业领域之外的问题抱有浓厚的兴趣,甚至有很深的造诣。换言之,不同学科的影响都会渗透并体现在文人的思想和文字当中。这个概念所暗示的模糊界限使其得以涵盖包括自然科学家、社会科学家和文学家等不同领域的思想者。用“共同体”来描述这个知识群体,则是基于德国社会学家滕尼斯(Ferdinand Tönnies,1855-1936)的“精神共同体”概念。在《共同体与公民社会》中滕尼斯除了提出血亲(community by blood)和地域(community of place)组成的“共同体”外,还提出了一种更具活力和凝聚力的共同体形式——“精神的共同体”(community of spirit)。他把“精神的共同体”界定成“为着同一目标一起努力的共同体”;“即便共同体中的人们各自分离,这种统一感依然存在,而且以多种形式存在,其共同特征是潜意识。”[4](P.22;P.27)本文认为,维多利亚文人对知识的共同关注把他们融聚在一个无形的精神共同体当中,他们通过人文、社会、科学等不同领域的话语界定知识,探究知识的界限,反思知识的问题。在此过程中,他们互相借鉴,彼此影响,产生了诸多交叉与契合之处,构成了一个具有典型时代特征的知识共同体。
一、知识话语的建构
维多利亚时代是公认的变革期和转型期,这不仅意味着政治经济生活领域的巨变,也意味着人们认识方式、思维框架和情感结构等精神领域的变革。人们认识世界和认识自身的渴望变得日益热切:地质学和考古学为自然去魅,宇宙的边界无限扩展,历史的起点不断向后推移;对人类自身认识的渴望促使包括社会学、人类学、心理学等多门新兴学科的诞生。知识的快速更新也促使既有知识传播方式的变革:各种知识普及学会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越来越多的科普读物和文学作品走进中下层民众的生活;专业性学术期刊日益增多。19世纪末学科分化发生之前,各种知识混杂交织在专业或非专业的期刊杂志中,不同学科之间的论辩与对话发生在正式或非正式的出版物上。文人们以各种形式就知识的本质问题展开思考:什么是真正的知识?如何更有效地传播知识?人类能否凭智性完全认识世界?这些成为维多利亚文人最为关注的话题。从小说家、诗人、教育家,到社会学家、政治经济学家、自然科学家,他们虽然从事不同领域,却无一不关注知识的本质问题,而且不约而同地共同关注并坚持“知识”的整体性。
诗人、评论家马修·阿诺德(Matthew Arnold,1822-1888)在《文化与无政府状态》中详细阐述并界定了他的“文化”概念,而这些定义基本上都以“知识”为核心展开。他一再强调,文化即“通过阅读、观察、思考等手段,得到当前世界上所能了解的最优秀的知识和思想,使我们能做到尽最大的可能接近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5](P.132)这个定义把思想和知识中所有最精华的部分作为文化的精髓,把认识“事物之坚实的可知的规律”或者说“看清事物之本相”作为文化人追求的目标。与此关联,阿诺德提出“完美”和“健全理智”的概念,倡导人类天赋秉性的均衡全面发展,即所有能力的整体和谐发展。这就要求人们脱离狭隘思维和低级趣味,寻求来自各种知识的滋养:“文化在寻求完美的内涵时,要参考人类经验就这个问题所发表的全部见解,不仅倾听宗教的声音,还要听艺术、科学、诗歌、哲学和历史的声音,如此才能使结论更充实,更明确。”[5](P.10)阿诺德话语中反复出现的“整体性”和“完整性”(totality)是他文化概念的基石,也构成了他知识观念的核心内容。
与阿诺德相似,教育家纽曼(John Henry Newman,1801-1890)同样强调知识的整体性。纽曼认为,既然是“大学”(university),就应该传授“全面知识”(universal knowledge),而非职业性技能。因为只有这样的知识,才能训练受益终生的心智习惯、培养出具有健全品格的人才,或者说真正的绅士。他的教育理念之所以被称为“博雅教育”,正是由于这样的教育以其自身为目的,摆脱了外在功利性诉求的奴役和束缚(他称之为servile knowledge),能够让人获得精神自由,由此才称其为“博雅知识”或“自由知识”(liberal knowledge)。[6](PP.66,110)不仅如此,纽曼还强调各学科知识的关联性。在他看来,正如真理之间不可能存在真正的冲突一样,不同学科之间也应该是互相勾连、和谐共存的关系。真正的知识并非对事实的孤立认识,而是对事实之间关系或者说对事实所组成的“体系”的认识。这个复合体就像一个蜘蛛网一样把事实勾连起来,成为一个整体。
政治经济学家穆勒(John Stuart Mill,1806-1873)和纽曼一样,把跨越学科界限的总体性知识置于职业性或专业性知识之上。他把个别的事实性知识和琐碎的信息性知识称为“浅表性知识”(superficial knowledge),把注重不同学科的关联性和整体性的知识称作“总体性知识”(general knowledge)。[7](P.24)穆勒把拥有总体性知识的人称为“有教养的知识分子”(cultivated intellects),他们不仅拥有某一专业领域的知识,而且对其他领域也有相当程度的了解,这足以使他们拥有一种理解力和独立的判断力,能够看到事物的多面性,不至于随波逐流,盲从某一学派或党派。穆勒的反派别主义与折中主义倾向大体上都基于对“局部真理”(half truth)的警惕和对总体性知识的追求。[8](P.4)
即便是极力推崇科学知识重要性的维多利亚文人,也很少将科学与其他领域的知识割裂开来看待。社会学家斯宾塞(Herbert Spencer,1820-1903)1857年7月在《威斯敏斯特评论》(WestminsterReview)发表题为《什么知识最有价值?》的文章,他指出最有价值的知识是“科学”。不过他的科学概念远非现代科学中去人格化的知识概念,而是与价值追求和审美趣味紧密相关、具有人文关怀的知识。如浪漫主义诗人华兹华斯一样,斯宾塞把科学与艺术紧密关联:“我们不只看出科学是为一切形式的艺术诗歌服务,而且看得正确的话,科学本身就富有诗意。”[9](P.37)在他看来,投身科学研究意味着一种信仰和价值追求,因为“对科学的忠诚就是一种无言的崇拜,默认所学事物的价值,即意味着崇拜事物的造因。……只有真正的科学家,才能真正知道那表现自然、生命、思维的宇宙全能是怎样完全超出人类知识和人类理解的范围的”。[9](P.41)斯宾塞通过把科学与审美、道德、信仰等领域的价值追求联系在一起,构建出一种能够推动人类精神发展的总体性知识话语。
被称为达尔文斗牛犬的赫胥黎(Thomas Huxley,1825-1895),同样以坚持科学教育闻名,然而正如列文所言,他与阿诺德的分歧并不是根本性的。赫胥黎在《科学与文化》中所坚持的科学教育并未完全否认古典人文教育的价值。他与阿诺德虽然各有侧重,然而都坚持全面均衡的知识理念,都坚持所有人类的思想精华都能够得到传播,并在学校课程中有较为合理平衡的安排。赫胥黎一方面强调科学在教育中的重要地位,同时也反复提醒人们,“科学必须避免的最大危险是那些从事科学的人的片面发展”。[10](P.20)他明确指出,“科学和文学不是两个东西,而是一个东西的两个方面”;“单纯的科学教育与单纯的文学教育意义,将会造成理智的扭曲。”[10](P.20)在倡导科学知识的价值时,无论是斯宾塞还是赫胥黎,均未把科学与其他精神追求分离开来孤立看待。恰恰相反,他们把科学与宗教信仰、与道德伦理、与审美趣味,甚至是个体的健全心智和社会责任联系在一起,从而使科学具有了无可争辩的社会价值和话语权威。
由以上的论述可以看出,无论是人文领域还是科学领域,无论文人使用怎样迥异的概念,他们都把认识问题作为核心内容和价值依托,把获取整体性知识看作人类社会进步的根本动力。在构建知识话语的过程中,他们的话语框架不断发生交叉和碰撞,催生出维多利亚时期文学与科学共有的微妙话语场域。
二、知识话语的交叉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常常借用文学技巧阐述复杂的科学概念。吉莉安·比尔(Gillian Beer)在《达尔文的情节》中详细分析了19世纪科学家,特别是达尔文科学话语的文学特质。通过分析《物种起源》中的论述结构、用词以及思维方式等,比尔发现,达尔文有意无意在模仿圣经或其他经典作品中的文学表现形式和叙事技巧。不仅是达尔文,当时很多科学家都有意无意借助文学的语汇或修辞策略来阐述读者认知模式之外的事物或构建作者的话语权威。比如,催眠师汤森德(Chauncy Hare Townsend,1798-1868)在论述“催眠术”时一边引用牛顿,一边引用柯尔律治,因为对他来说,两者具有同样的真理性。人种学家普里查德(James Cowles Prichard,1786-1848)在描述精神失常的病人时,运用了历史材料、人物特写以及小说人物叙事策略,使得读者如同了解《雾都孤儿》一样熟悉他笔下的病人。[11](PP.325,326)
奥蒂斯也分析了维多利亚科学家对文学话语的借鉴与吸收。她认为“在当时科学只是文学的一种变体”。[2](P.xvii)著名地质学家查尔斯·莱尔(Charles Lyell,1797-1875)以写作故事的方式记录了地质变迁的历史,并不断引用维吉尔、贺拉斯、莎士比亚、弥尔顿等诗人的经典诗句。奥蒂斯指出,莱尔的这种写作风格不仅使他的地质学著作引人入胜,成为畅销书籍,而且也让读者确信,地质学研究是合乎绅士身份的职业。[2](PP.2,236)
实际上,维多利亚科学家借鉴的不仅仅是文学作品的表现形式,甚至在科学原则问题上也受到文学思维的影响。以物理学家丁达尔(John Tyndall,1820-1893)为例,他非常看重想象力在科学探究活动中的重要作用,甚至曾专门撰写文章《想象力在科学中的应用》阐述自己以“想象力”为核心的科学原则。[12](P.127)他这样写道,“想象力是物理理论的设计师。没有了想象力的应用,我们对自然的认识将不过是对共存和序列的记录。力的概念将会消失,因果关系将会消失,随之把宇宙各部分联结为有机整体的科学也将消失不见。”[12](P.104)不仅仅是对“想象力”的强调让人联想到浪漫主义的影响,丁达尔对科学目标的描述更清晰地证明了这一点。在论述《物质与力》的科学论文中丁达尔指出,“科学的职能并非如人们以为的那样会让人们忘却宇宙的神奇和奥妙。恰恰相反,科学要揭示日常事物的神奇和奥妙之处。”[12](P.66)这与浪漫主义诗人的主张如出一辙。柯尔律治(Samuel Taylor Coleridge,1772-1834)在《文学生涯》(Biographia Literaria)中这样表述他和华兹华斯创作的共同目标:
给日常事物以新奇的魅力,唤醒人们对习俗的惰性的警觉,引导他们观察眼前世界的美丽和惊人的事物,以激起一种类似超自然的感觉;世界本是一个取之不尽、用之不竭的宝库,可是我们却视而不见,听若罔闻,虽有心灵,却既无感受,也不理解,这一切皆因我们对事物习以为常,还让私心蒙蔽了双眼。[13](P.63)
实际上,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无论是诗人还是科学家,尽管探究真理的方式不同,却有着相似的价值诉求。对于工业革命下日渐麻木和淡漠的人类心灵,他们深感焦虑,无论是诗歌创作还是科学研究,其目的均在于寻求留存生命活力与感受能力的方式与途径。
同样,文学家在创造性写作中也有意融入对科学问题的思考,探索科学发现的深层意义。以“变化”这一主题为例,无论是科学家、社会学家还是文学家,无不关注其对自然与人类社会的影响。无论是地质学中的渐变论、灾变论之争,还是生物学中的演化论,退化论和进化论之争,19世纪自然科学家大致都认同一点:一刻不停的变化是自然界和人类社会存在的基本形态。进化论的先驱、法国博物学家拉马克就曾这样写道:
在整个宇宙中存在一种没有任何原因却可以减弱的令人惊奇的活动,每一个存在的事物似乎都在不停地发生着必然的变化。……所有的存在只不过是一个永恒的变化过程中瞬间存在的各种特质和不稳定实体综合而成的巨流。[14](P.74)
对自然变化的意识引发了维多利亚文人对社会变化规律的探求。丁尼生一首早期的诗歌《一切都不会死去》(Nothing Will Die)可以被看作维多利亚人对变化的典型反应:
这世界从未完工,
它只有变化,永不消失,
所以,让风吹吧,
因为无论是夜晚还是早晨,
都将在永恒中延续。
没有什么已经诞生,
没有什么将会灭亡,
万物都在变化中。[15](P.283)
尽管这首诗以平淡无奇的方式白描出一幅自然画面,然而看似平静的诗行中间处处流露出毫无盼望的漠然。之所以这样说,是因为此诗的对诗《一切都会死去》中,尽管诗人慨叹没有什么能长久,“一切都会死去”,[15](P.284)然而从另一个角度看,正是由于他对世界存有热情和盼望,因此才会产生对死亡的恐惧。《一切都不会死去》看似否定了前诗,其情绪却并未因生的希望而有任何提升。恰恰相反,诗人反而陷入更深的绝望当中。如果说前诗表达出“死的恐惧”,那么后者则渗透着“生的绝望”。丁尼生的很多诗歌中都表达出类似的情绪,如不断苍老却无力死去的提托诺斯,渴望停止海上漂泊生活、甘食忘忧果的水手们。对他们而言,死亡是可怕的,然而比死亡更可怕的是那种看不到价值和意义的苟且人生。
维多利亚时代很多小说也生动地记录了人们对“变化”的心理体验和情感反应。狄更斯的小说中城市生活无不在变化的背景下展开。以《老古玩店》为例,老古玩商吐伦特破产后,与孙女小耐儿在陌生的城市乡间四处漂泊,无处归依,最终客死异乡。爷孙二人的行程中,乡村不再充满友善温情,处处潜伏着不可名状的危险;城市生活光怪陆离,瞬息万变,让他们常常不知身在何处。故事的结尾部分,在描述耐儿的朋友吉特带领他的孩子们回忆耐儿生前住处的情景时,狄更斯将浓墨重笔落在无可阻止的“变化”主题上面:
他有时把他们带到她曾经住过的大街;不过许多地方都改变了,没有原来的面貌了。那座老房子早已拆毁了,在它的地基上修建了一条又整齐又宽阔的大道。最初他还能用手杖在那里画出一块方地,指给他们房子就建在那里;但是不久之后他便捉摸不定那个地方了,只能说大约在那一带,他想,这些变化把他搞糊涂了。这便是几年以内发生的变化,许多事情也都是这样很快地过去了,就像是讲了一个故事一样
这段看似淡然的文字背后,充满了惶惑与感伤。时间的流逝不仅抹去了吐伦特和耐儿,就连他们曾经存在过的痕迹也被一同抹去,这所有的一切都会被忘记。小说最后一句把“故事”和事件做比,抹去了虚构与真实之间的界线,借此狄更斯似乎在告诉读者:随着小说叙事的结束,这些事情也终将被遗忘。个体的生死和存在都将被变化的大潮抹去,无处循迹。
乔治·爱略特也常常用洪流意象来描述变化对人类生活的影响和冲击,只是她对变化的反应更为复杂和微妙。在《弗洛斯河上的磨坊》的结局中,大洪水吞没了麦琪和汤姆,几年后又恢复了旧日的繁华模样,然而:
大自然弥补它的创伤,但是并没有全部弥补。连根拔起来的树木不再在土里生根,崩溃的山头留下了痕迹。如果新树生长出来,那么新的也和老的不同,绿叶覆盖下的山头还留着过去崩裂的痕迹。对那些曾经看到过往日情景的人们来说,并没有全部弥补。[17](P.654)
撇开洪水结局所包含的灾变论成分不说,这段话中所包含的新旧对比极为准确地表达了爱略特对变化的态度。她一方面相信不可摧毁的生命活力将在变化中留存和延续,另一方面也不无怀恋地回望逝去的旧时光。对于人类整体而言,一代代繁衍生息不停向前,然而,个体总是在回望中找寻自己存在的痕迹。
维多利亚时代的科学家们试图把握变化的规律,社会学家借助自然科学的视角审视人类社会的变化,而文学家则竭力捕捉变化进程中个体的心理反应。他们的文字交相呼应,从不同角度展示了他们对变革社会的认识和对恒常价值依托的追求。实际上,让维多利亚文人焦虑的不仅仅是瞬息万变的可见世界,还有那无法洞观其奥秘的不可见世界的存在。
三、对知识界限的意识
维多利亚时代的文人一方面为自己获得的关于地球以及地球生物的知识而倍感自豪,另一方面也不无遗憾地意识到了“不可知”世界的存在。最具代表性的便是“不可知论”(agnosticism)的出现。“不可知论”起初并非哲学概念,而是科学家赫胥黎为了划分可知与不可知的界线,于1869年自造的词汇。他宣称人的认识能力只限于感官经验和现象世界,这个范围之外的“第一因”(First Cause)是不可认识的。[18](P.120)
实际上,赫胥黎并非第一个提出“不可知”概念的维多利亚人。斯宾塞在1862年的《第一原则》中就已经提出了类似观点,他把这个不可认识的“第一因”称为“不可知”。他写道,“我们不断地追求知识,又不断地被阻隔在知识之外,使我们不得不相信,获取真知是不可能的任务。这让我们意识到,我们最高等的智慧和责任便是把万物赖以依存的那个存在看作‘不可知’。”[19](P.113)如果说赫胥黎把焦点放在物质世界以及科学知识的“真实性和确定性”上的话,那么斯宾塞的目的在于承认超验存在的可能性:
正如智力和意志超越了机械运动一样,不是有可能存在一种超越智力和意志的更高存在吗?我们的确没有能力完全认识这种高等存在。但这并不等于说我们可以因此就质疑它存在的真实性,应该是恰恰相反。难道我们还没有意识到我们的头脑在认识现象背后的终极存在方面是多么的无能为力吗?[19](P.109)
由此可以看出,斯宾塞提出不可知概念的目的并非如现代人理解的那样否定不可见世界的真实性,而在于承认人类智力在认识方面的软弱无力。他在《进步:其规律与起因》中满怀纠结地写道,“人类的智力既伟大又渺小……绝对的知识是不可能的;在万物之下,潜伏着一个永远无法洞悉的秘密。”[20](P.196)这种看似矛盾却真实的体验并非他和赫胥黎独有,而是当时许多科学家的共同感受。物理学家丁达尔不仅坦然承认科学的限度,而且对宇宙的奥秘充满了敬畏之情:
就知识而言,自然科学有两个极端。一方面它注定要认识一切;而另一方面它一无所知。科学认识我们现今称之为自然的一切事物,然而,对于自然的本源和未来命运,科学却一无所知。是谁创造了太阳?是谁赐予阳光以力量?是谁创造了物质的终极分子,并赐予它们各样神奇的互动力量?科学无法获知:尽管被搁置一旁,这个奥秘却始终无法被解开。[12](P.52)
哲学家和心理学家刘易斯(George Henry Lewes,1817-1878)也常常被称为不可知论者,不过他走得更远。在他看来,即便是可见的事物,我们也无法认识其本质。我们所能了解的无非是事物之间的“关系”:“对事物的认识即对其所处关系的认识。事物即其关系。”[21](P.58)他常常用“面纱”来描述人类与不可知世界之间的屏障:“万物奥秘的面纱(the veil of mystery)不可能被揭开。我们站在这个神秘面纱之前,思忖着隐藏其后的秘密,我们只能构筑体系,却永远无法看到真理。”[22](P.225)
与刘易斯同声相和的小说家爱略特在创作中也常常思考人类认识限度的问题。“面纱”、“迷宫”等意象在她的小说中频繁出现,暗示人物在认识方面的迷惑与纠结。《米德尔马契》中女主人公多萝西娅对婚姻的期待与知识相关。她觉得自己的生活“不过是在深山幽谷中徘徊,在曲折的小径间行走,而这些小径像迷宫一样,周围筑有高墙,不能通向广阔的世界”。[23](P.31)因此,她期待未来的丈夫能够像弥尔顿和帕斯卡尔那样带来智慧与指引,婚后却失望地发现,“她只是走进了阴暗的前室,在曲折的死胡同中打转,找不到出路。”[23](P.236)卡苏朋和利德盖特分别在神话和医学两个不同领域追求终极真理,却都无果而终,没有能够找到揭开存在之谜的终极“钥匙”或“线索”。在爱略特看来,无论是终极真理,还是他人的内心世界,对于人类有限的知觉而言,都是不可穷其奥妙的神秘疆域。如同叙事者在第20章中所言:
要是我们的视觉和知觉,对人生的一切寻常现象都那么敏感,那就好比我们能听到青草生长的声息和松鼠心脏的跳动,在我们本来认为沉寂无声的地方,突然出现了震耳欲聋的音响,这岂不会把我们吓死。事实正是如此,我们最敏感的人在生活中也往往是麻木不仁的。[23](P.234)
在那不可见、不可闻的静默表象背后,隐藏了我们粗陋感官所无法了解的世界。承认智性限度的时刻,也是对他人同情和宽容等情感发生的时刻。小说中多萝西娅的同情心使她能够超越个人痛苦,体察他人的苦难,促使她做出利他主义的抉择。这种包含着启示和洞察力的同情感受成为一种超越理性、更为强大的情感真理,无声地改变着这个世界。如爱略特在《米德尔马契》结尾所言:“你我的遭遇之所以不致如此悲惨,一半也得力于那些不求闻达,忠诚地度过一生,然后安息在无人凭吊的坟墓中的人们。”[23](P.981)
和爱略特小说中的人物一样,很多维多利亚文人在知识飞速扩展的时代意识到了理性的限度和情感的真理。这促使他们采取谦卑谨慎的科学态度,留存对自然的敬畏之心,在纷繁袭来的思潮中维系着知识与价值之间、头脑与心灵之间、进步与传统之间的和谐与平衡。
结语
没有一个静态的、稳定的维多利亚思想体系等待我们去揭示,去认识。它本身是一个变动不居、富于变化、充满张力的综合体。用任何单一标签来化约或界定它,都会使我们偏离真实图景。戴维斯对这个时代的总结深中肯綮:“这个时代没有明确的冲突,而是各种思潮的混合交织。”[24](P.50)这个时期的文人们有不同的关注和侧重,存在这样那样的歧见和纷争,然而他们在知识本质问题上,坚持大致相似的原则和共识,都倡导人类天性的全面和均衡发展。无论是阿诺德的批评家,穆勒的哲学家诗人,还是卡莱尔的文人英雄,纽曼的绅士,都在以“知识”和“真理”为导引,通过健全心智的培养,对抗由变革带来的思想无序状态。这个知识共同体为现代社会留下的,不仅仅是认识方式的变革,而且是迄今为止仍然珍贵的精神遗产。这份遗产的核心思想可以这样表述:知识群体不应拘囿于个人或个别阶层的利益,不应热衷于构建个别群体的权威地位;借用阿诺德的“文化”概念来说,要“不带偏见地”致力于人性与人类社会的和谐与整体发展。
参考文献:
[1]George Levine.Realism,EthicsandSecularism:EssaysonVictorianLiteratureandScience[M].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8.
[2]Laura Otis.LiteratureandScienceintheNineteenthCentury:AnAnthology[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3]Suzy Anger.KnowingthePast:VictorianLiteratureandCulture[M]. Ithaca, London: Cornell University Press, 2001.
[4]Ferdinand Tönnies.CommunityandCivilSociety[M]. Trans. Jose Harris, Margaret Hollis. Cambridg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1.
[5]马修·阿诺德.文化与无政府状态[M].韩敏中译.北京:三联书店,2008.
[6]约翰·亨利·纽曼.大学的理念:界定与诠释[M].高师宁译.贵阳:贵州教育出版社,2003.
[7]约翰·密尔.密尔论大学[M].孙传钊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3.
[8]约翰·穆勒.论自由[M].许宝骙译.北京:商务印书馆,2014.
[9]赫·斯宾塞.论教育[M].胡毅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1962.
[10]托·亨·赫胥黎.科学与教育[M].单中惠,平波译.北京:人民教育出版社,2013.
[11]Gillian Beer.Darwin’sPlots:EvolutionaryNarrativeinDarwin,GeorgeEliotandNineteenthCenturyFiction[M]. New York: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 2000.
[12]John Tyndall.FragmentsofScience[M]. London: Longmans, 1889.
[13]柯尔立治.文学生涯[M].刘若端译.十九世纪英国诗人论诗.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4.
[14]威廉·科尔曼.19世纪的生物学和人学[M].严晴燕译.上海:复旦大学出版社,2000.
[15]Alfred Tennyson. Nothing Will Die, All Things Will Die [M]. John Churton Collins. ed.TheEarlyPoemsofAlfredLordTennyson. London: Methuen, 1901.
[16]狄更斯.老古玩店[M].许君远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80.
[17]乔治·爱略特.弗洛斯河上的磨坊[M].祝庆英译.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1996.
[18]T. H. Huxley. Agnosticism [M]//Michael Goodwin. ed.NineteenthCenturyOpinion. Harmondsworth, Middlessex: Penguin Books, 1951.
[19]Herbert Spencer.FirstPrinciples[M]. London: Williams & Norgate, 1870.
[20]Hebert Spencer.EssaysonEducationandKindredSubjects[M]. Charles W. Eliot. ed.London: Dent,1963.
[21]George Henry Lewes.ProblemsofLifeandMind[M]. Boston, MA: James R. Osgood, 1874-18.
[22]George Henry Lewes.ThePhysiologyofCommonLife[M]. Edinburgh: Blackwood, 1859.
[23]乔治·爱略特.米德尔马契[M].项星耀译.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7.
[24]Philip Davis. 1830-1880:TheVictorians[M]. New York: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2002.
(责任编辑:吴芳)
Community of Knowledge——Victorian Men of Letters
and Their Intellectual Pursuit
GAO Xiao-ling
(School of Foreign Languages, Zhengzhou University, Zhengzhou 450001, China)
Abstract:Never has there been an age so much concerned about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as the Victorian age. Almost all celebrated men of letters of this period pondered on the nature of knowledge, the boundary of human intellect and consequences of intellectual pursuit. Although varied in field and scope, they overlapped and interpenetrated in discourse, through which they unconsciously constructed a unique community of knowledge. They sought wholesome rather than specialized knowledge, sound reason rather than professional training. Through the close link they sustained between the value of knowledge and that of ethics and aesthetics, this community functioned as a spiritual lighthouse in the age of turbulence.
Key words:Victorian Age; men of letters; community of knowledge; science; literature
DOI:10.3969/j.issn.1674-2338.2015.04.011
中图分类号:I106
文献标志码:A
文章编号:1674-2338(2015)04-0091-07
作者简介:高晓玲(1974-),女,河南郑州人,郑州大学外语学院副教授、硕士生导师,郑州大学英美文学研究中心研究员,主要从事英国文学研究。
基金项目: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文化观念流变中的英国文学典籍研究”(12&ZD172)的研究成果。
收稿日期:2015-05-19
文学研究英国文学中的“共同体”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