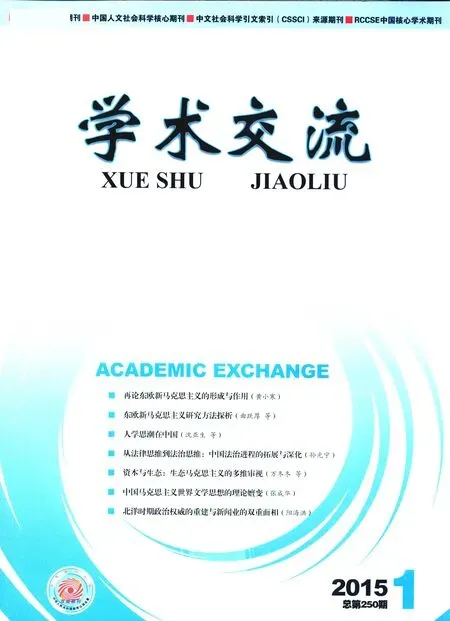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蜕变及其原因初探
2015-02-25张振亭张会娜
张振亭,张会娜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昌 330031)
新闻传播学研究
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上海《时报》的蜕变及其原因初探
张振亭,张会娜
(南昌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南昌 330031)
上海《时报》是旧上海三大民营报纸之一,初为康有为梁启超在国内的舆论喉舌,但终因宣传不力而与康梁决裂。后经历了两次重大蜕变:为文人所办的报纸,业务方面锐意革新,但政治上表现平庸;最后成了被称为“黄报”的商业大众化报纸,但连年亏损。上海《时报》可谓“党人报不党”“文人报不论政”“商人报不盈利”,这背后既有复杂的政治社会背景,又展现了一个多种形态的中国近现代报业构成。
上海《时报》;文人论政;大众化报刊
依办报主体分,党人报、文人报、商人报是我国近现代报刊史上最主要的报纸形态。一家报纸先后经历了这三种形态,实属罕见。上海《时报》就是这样一家报纸。它创刊于1904年6月,1939年9月停办,存续时间长达35年,经历了清末新政、民初共和、北洋政府、国民政府、日伪侵略等中国社会最激荡变迁的几个历史时期。在政治、经济、社会急遽转型的大背景下,《时报》被动或主动地作出了两次重大政治转折,对报纸内容以及经营方向进行了调整:从党人报(1904-1908)到文人报(1908-1921)再到商人报(1921-1939)。作为康有为、梁启超(以下简称康梁)在国内的舆论喉舌,却被认为“宣传不力”,为康梁所弃;之后,狄葆贤独立支撑起《时报》,变为民营,连同陈景韩、包天笑等几个知名文人在业务上锐意革新,但在政治上表现平平;地产商黄伯惠接办《时报》后,走大众化路线,被冠以“黄报”,但一直无法获得市场盈利,连年亏损。《时报》可谓“党人报不党”“文人报不论政”“商人报不盈利”。探究上述曲折转型的历程及背后的原因,既是《时报》研究的第一步,又可以揭示我国近现代报刊结构形态上的多样化,呈现一个多面、整体而真实的新闻史。
一、“党人报不党”:康梁国内的耳目喉舌及其夭折
戊戌变法失败后,康有为、梁启超等人逃亡国外,检讨变法失败原因,“咸认三年鼓吹为时短暂,未能唤醒国人一致支持。唯有再接再厉,冀有卷土重来之日,决心以言论为依归”[1]。海外流亡期间,康梁组建保皇会,创办了数十种报纸杂志,继续把报刊作为保皇会重要宣传工具,大张旗鼓进行保皇立宪宣传。但因其所在地区限制,受其影响者多为华侨,难以触及中国大陆和清廷。鉴于此,在1904年召开的保皇大会上,康梁决定在香港和内地创设言论机关,扩大宣传攻势。康梁计划在香港设《香港商报》、在广州设《羊城日报》、在上海设《时报》、在天津设《日日新报》、在汉口设《大江报》。结果,广州、天津、汉口的计划均未成功,只有香港和上海的计划得以实现。上海《时报》就成了康梁在内地所设唯一综合性大型宣传机关。
《时报》初创时为避开清政府干扰,由日本人宗方小太郎担任名义上的发行人,实际主持人为狄葆贤。关于创办资金的来源,张静庐称“系利用唐才常‘庚子之役’失败后之粮台余款作基金”[2]55,包天笑则回忆说“当时筹集资本时,大概康梁方面占十之三,狄氏占十之七”[3]591。康梁宣称为《时报》大约消耗二十万之巨。康有为曾写信给梁启超,言及保皇派援助《时报》资金:“时报除癸年(1903年)经拨七万外,甲年(l904年)拨捐款约二万(又借广智二万两),乙丙年(1905、1906年)皆过万,丁年(1907年)一万,计合十五万(墨银行代出五六万,苦极),外另代交息(三年)三万余,合共总在廿万左右,无年不请款。”[4]446梁启超也曾提及要将广智书局的资金一万元加股《时报》。[4]487因此,从资金来源上看,《时报》的所有权大部分为康梁所有,《时报》初创时是一家典型的党报。
在人事安排上,狄葆贤任总经理,罗孝高任总主笔。狄葆贤(字楚青,号平子)早年在政治上追随康有为,是康的弟子。1895年,康有为发起公车上书,狄葆贤名列其间。狄氏与梁启超、唐才常等人相交甚厚,引为“莫逆之交”。梁启超称其故交中“复生、铁樵之外,惟平子最有密切之关系。相爱相念,无日能忘”[5]5336。戊戌变法失败后,狄氏思想渐趋激进,曾寄望于武力革命。再遭失败后灰心革命,从此弃武从文,决心入言论界。狄葆贤参加了1904年的保皇大会,后被康有为派到上海筹办《时报》,同去的还有罗孝高。经过一番筹备,梁启超潜回上海“暗中支持”,并直接参与报纸的命名,撰写发刊词,确定报纸体例。不仅如此,《时报》初办时所登载的论说也多为梁启超从横滨寄稿而来。其后的一些重要报道如“争回粤汉铁路一案”的材料、稿件,也全赖梁氏谋划。[4]337罗孝高是广东人,康有为万木草堂时的嫡传弟子,主要负责审核、撰写论说。早期《时报》的社论多由罗孝高、冯挺之等人把关,竭力宣传保皇党立宪、爱国的主张。
从内容上看,《时报》是保皇党提倡立宪发展宪政的宣传工具,是梁启超新民说的支持者和鼓吹者,在重要社论主张和报道口径上都有鲜明体现。《时报》初创之时正值日俄战争,立宪小国日本战胜了专制帝国沙俄。《时报》将日本的胜利归结为明治维新的成功,又把明治维新的成功归结为日本天皇亲自下诏书,定国是,于是要求清政府“仿日本之故事,先行下诏,期以十年立宪”。时隔一年,迫于各方压力,清政府派五大臣出洋考察政治。清政府假立宪的小动作,《时报》从中看到的却是莫大的希望。清政府下诏“预备立宪”后,《时报》更是热情高涨,急于规划改革事宜,接连发文为清政府自上而下的立宪鼓与呼,以为“数千年间专制政体,将从此而为根本之改革”。及至官制改革方案公布,清政府假意立宪面目暴露,《时报》才大失所望,愤然其“唯汲汲以中央集权为诡计”,却也清醒地意识到对清政府寄予立宪希望,无异于“痴人说梦语”。
张謇所领导的江浙立宪派势力雄厚,颇有影响,海外保皇党有意拉拢,身在上海的狄葆贤被委以联络责任。不料多方接触之下,狄氏与张謇及其宪政公会的联系日趋紧密,而与海外保皇党渐行渐远。至1907年,康梁与狄氏之间的离心力已经形成。是年,梁启超组织政闻社,欲向中国内地发展,而《时报》所刊政闻社消息不多,舆论支持甚少。这令梁启超颇为不满,曾致函康有为指责狄葆贤“于党事种种不肯尽力,言论毫不一致,大损本党名誉”,愤然道“吾党费十余万金以办此报,今欲扩张党势于内地,而此报至不能为我机关,则要来何用”[4]432。1908年后狄葆贤逐渐疏远了康梁及保皇党。
对于《时报》,康梁不可谓不尽心,出钱出力,多方谋划,结果却事与愿违。《时报》与康梁的决裂,对于保皇党而言少了一个喉舌,而对于暗淡的晚清中国则多了一份真正有品质的民报。[6]84
二、“文人报不论政”:狄葆贤与文人办报的另一种模式
狄葆贤退还康梁所出资金后,开始独资经营《时报》。《时报》从党报蜕变为民营报纸,成了狄葆贤的个人事业,无论是在言论方向、业务以及编辑上都更加突显狄氏个人风格,开启了文人办报的新形态。
狄葆贤出身于江苏溧阳名门望族,工书擅画,笃好辞章,精于鉴赏,可谓中国传统文人的典型代表。他光绪二十年中举,但无意进取。狄氏“以满清腐败,甘受列强欺侮为恨”,几度东走日本,广交名士,汲取新知,呼号平等、自由、博爱,自名“平等阁主”,是一个吸纳了新思想的传统文人。狄氏致力维新,赞成改良,以改革者的姿态开报馆、办书局,被称为“文化界中第一人”[7]。创办《时报》时,狄葆贤尝言“吾之办此报,非为革新舆论,乃欲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8]134。正因为此,《时报》在版式编排、印刷、文体、专刊、小说、图画、多样化出版、集团化等方面均有革新,领一时风骚,“拖着望平街的老爷车向前进”[9]9,对当时报界及后来的报刊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开启了中国报学史的崭新一页。包天笑曾言,“狄氏的创设时报,在上海新闻界不为无功,那正是申、新两报暮色已深的当儿,无论如何,不肯有一些改革。时报出版,突然似放一异彩,虽然销数还远不及申、新两报,却大有‘新生之犊不畏虎’的意气”[10]424。
首先,在报纸外观上,《时报》首创对开版式,两面印刷,“始废弃书本式,而形式上发生一大变迁”[8]331。第一版报头“时报”二字用一号大字,特别醒目,下有英文报名“Eastern Times”。首版全版广告,以新书出版、学校招生类居多,“以首页刊广告,为一大胆之尝试,盖申、新等老资格报纸皆不如此”[1]。其次,在报纸内容与规范上,《时报》独创体裁,不随俗流。首办专电,创特约通讯,立时评专栏,辟副刊等,一时在上海与《申报》《新闻报》鼎立而三。其中,最为人乐道的当属陈景韩所创之时评。“时评”一词一语双关,含有时事评论以及《时报》的评论两层意思。这种文体,配合时事,抒发议论,短小精悍,令人耳目一新。[11]424“在这十七年来逐渐变成中国报界的公用文体,这就可见他们的用处与他们的魔力了。”[8]135其三,狄葆贤独具眼识,大力提倡小说。《时报》开创了上海大型日报刊载小说的先例。在上海众多的报纸中,《时报》登载的小说最多。《时报》在民国前登载的小说达223篇,高于《申报》的203篇,而《新闻报》和《中外时报》仅为35篇和50篇。[12]小说与报纸的销路大有关系,往往一种情节曲折、文笔优美的小说,可以抓住报纸的读者。[10]318《时报》能够迅速打开销路,跻身沪上三大报之列,与大量登载小说不无关系。其四,创办了一系列专业性副刊。1919-1924年,该报约创办过妇女、儿童、文艺、实业、英文、美术、学术、图画等十几个专刊。这些专刊颇具特色,引领当时报界风潮,不少专刊成为我国新闻史上的“第一”,为《申报》、《新闻报》所效仿。[13]最后,积极探索多样化出版和集团化经营。从1908年开始,狄葆贤主持下的上海《时报》逐渐形成了一个由书局、报纸、杂志、照相馆、印刷厂等构成的报刊出版集团,在内容、人才、资本、发行、广告等方面初步形成了一个集团架构,是我国民营大报集团化的最早实践者之一。[14]
上述业务方面的革新,是在狄葆贤擘画下,带领陈冷、包天笑、雷奋、史量才、黄远生、邵飘萍、戈公振等报馆骨干实现的。狄葆贤、陈景韩、包天笑等是典型的文人,《时报》蜕变为一家文人所办的报纸。自1874年王韬创办《循环日报》以来,“文人论政”就成了我国报界的传统。简言之,文人论政就是“论政而不参政,经营不为营利,以言论报国,代民众讲话”[15]。张季鸾认为,报纸是文人论政的机关而不是实业,这是我国报业的传统,既可以说它落后,也可以说是特长。[16]有趣的是,狄葆贤时期的《时报》,虽然办报的多是文人,但初衷并非为论政,在言论上表现平平,政治上无多大影响。可以说,狄葆贤时期的《时报》是一张文人所办但不论政的报纸。
辛亥革命前后,中国政治云谲波诡,《时报》报人的政论态度也是应时而生,随时而变。以袁世凯统治时期为例,《时报》的政论经历了拥袁、反袁的变化。南京临时政府成立之时,《时报》拥护袁世凯实行中央集权,反对革命派的“暴民政治”,公开宣扬开明专制说。[17]1913年宋教仁被刺,证据公布后,《时报》仍发文为袁开脱。直到袁世凯以《中华民国约法》取代《临时约法》,以参政院取代国会,并明文取消议会和地方自治,《时报》才认识到袁氏专制独裁甚于清政府,改而要求袁氏还“共和之实”。1915年12月袁世凯公开称帝,护国军兴起,战争爆发在即,《时报》清醒地认识到导致这场战争的祸根是帝制。等到袁世凯一死,《时报》撰文庆贺,态度发生180度大转弯。不管是对时局的认识,还是前后有变的立场,《时报》的政论都无一可足称道。
论政上并无建树的狄葆贤几乎参与了辛亥革命前后上海所有的重大活动,甚至冲在最前列,雷奋、陈冷等人也热心为各类政治活动奔走。1905年科举制废除,9月张謇、赵凤昌、狄葆贤等九人发起兴办新式学堂的倡议,得到全省学界的支持。10月,江苏学会成立大会举行。1906年7月,江苏学务总会更名为江苏教育总会。在张謇等人的领导下,通过杨廷栋、雷奋、狄葆贤等人的努力,江苏教育总会成了“政治性的江苏中心组织”[18]49。清廷宣布预备立宪后,民间宪政团体应运而生。1906年12月9日,宪政研究会召开成立大会,雷奋被选为副总干事。狄葆贤、陈冷、史量才等《时报》骨干几乎全部都是积极参与者,不少成员后来还参加了预备立宪公会,狄葆贤还是骨干成员、活跃分子。[19]1908年,狄葆贤更成为江苏咨议局议员。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江苏巡抚程德全在议员狄葆贤、雷奋等人的劝告下,宣告江苏独立。1916年,狄葆贤作为江苏咨议员积极参加了江苏的反袁独立运动。
该时期的《时报》,虽然业务上令人耳目一新,但市场盈利却乏善可陈,靠着有正书局的扶持,才勉强维持日常运营。这一点倒比较符合文人办报的特征。恰如包天笑所言:“在从前以一个文人,办点商业性质的事,终究是失败的多”[10]328。
狄葆贤先后参加了康梁领导的维新变法和唐才常组织的自立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深受打击,对政治有些心灰意冷。他决定沉潜下去“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因此,其所主导的《时报》,舆论上表现平庸,而业务上却颇有革新。辛亥革命前后,狄葆贤和《时报》同人,也直接参与了一些政治运动。因此,此时期的《时报》属于文人办的一家报纸,但论政无力,却直接参政,颠覆了“文人论政”的传统。如此,狄葆贤“革新代表舆论之报界”的目的算是初步实现了,只是没有给其足够的时间进而革新舆论本身。
陈景韩的出走、经营上的不力,加上丧子等家运不济、北洋军阀的干扰,狄葆贤无力支撑,萌生退意,最后不得不痛心割爱,于1921年以四万银元全部盘给黄伯惠。[20]
三、“商人报不盈利”:黄伯惠与《时报》的大众化
黄伯惠(名承恩),松江朱泾人,系黄公续长子。黄氏家族经营地产、钱庄等实业,家产丰厚,积累了大量财富,“在上海公共租界浙江路以及杨树浦一带也有不少房地产,是上海有名的富商之一”。接办《时报》前,黄伯惠是一个纯粹的商人,其时正在做橡皮股票生意,很是称心顺手,发了大财。[21]
关于黄伯惠的办报动机,曾任《时报》外勤记者的顾执中认为“最大的可能,是他眩惑于《新闻报》与《申报》的年年发大财,想要发财以此致富”[22]179。袁义勤提供的多则资料表明,黄伯惠接办《时报》起码不是为了致富,因为他本身已经很富有。退一步来说,在当时的中国办报亏本是常事,赚钱是例外。[23]另外,黄伯惠年少时常随父亲出入《时报》,对办报产生了浓厚兴趣。黄伯惠曾自费游历欧美、日本,考察机械、矿务及经济,尤其注意《伦敦时报》的设施,颇有归国办报之意。[24]165综合来看,黄伯惠接办《时报》是兴趣使然,盈利与否倒没有列为首先考虑的因素。
黄伯惠游历欧美期间,黄色新闻浪潮正迅速蔓延,大有席卷全球之势。20世纪初美国三分之一的大都市报刊都成为不折不扣的黄色报纸,其他报纸也都不同程度地受到了黄色新闻的污染。[25]289其时黄伯惠所特别注意的《伦敦时报》(即《泰晤士报》),恰好处于第二个巅峰时期,即北岩爵士主导下的大众化革新阶段。1908年,北岩爵士收购了面临破产境地的《泰晤士报》后,采取了一系列大众化的办报方针,使得报纸重新有了起色,一战期间销量一跃达到31.8万份,创该报创刊以来的最高纪录。[26]114
1929年,黄伯惠特意印赠的宣传册《时报敢请国人阅看之理由》公开宣布了《时报》的经营方针:“《时报》以改良报纸为目的,与任何团体机关营业不发生关系,专为读者有益无害而改良《时报》,现已完全改良印刷。凡阅《时报》者,老者不致费力,青年不致伤目;耳闻不如目见,《时报》提倡照相,记事中多插图片,并于每星期日、星期四刊有画报二张,每日刊《新光》一版。《时报》特将无关重要记事,冗长无味字句,一律删除。并将每篇记事重行编制,使阅者一目了然,既省光阴,又有无穷兴趣”[27]39。不论是“改良印刷”还是“无穷兴趣”,《时报》都与《伦敦时报》的大众化做法不谋而合。
如果说赫斯特是美国的黄色新闻大王,北岩是英国大众化报刊的代表,黄伯惠就是中国黄色新闻和大众化报刊的标志人物。黄伯惠主持下的《时报》轻政事而主要以消遣、娱乐内容来吸引读者,无论报道事件的选取还是报道手法,都以激发读者好奇心为第一要义,对于社会新闻的报道更是以“耸人听闻”著称,走的是模仿赫斯特的黄色新闻道路[28]191,再加上报馆主人姓黄,因而被冠以“黄报”。
在内容上,《时报》特别重视社会、体育新闻,大量刊登相关报道以吸引市民读者。在社会新闻方面,“黄报”力求视角独特,异于其他报纸。黄伯惠特别重视外勤采访,对跑社会新闻的记者有特别奖励,交通工具、稿费、特支费,无不从丰。[29]229犯罪与案件是黄色新闻最感兴趣的话题之一,黄伯惠曾对编辑部表示,只要是工部局或法院公开宣布的案件,一律刊登。[23]针对《申报》《新闻报》不太重视体育新闻的情况,黄伯惠特在《时报》辟体育专刊,凡国内外体育新闻,都派遣记者或物色特派员进行采访。1930年4月,全国运动会在杭州举行。黄伯惠不惜巨金,特向沪、杭、甬铁路局包下半节车厢装设暗房设备。每天在杭州开往上海的最后一班火车上,将当天所摄大会体育比赛的照片,在火车车厢暗房中冲洗,等火车一到站马上将照片送回报馆制版,次日早晨便可刊出,然后再以飞机送往杭州全运会会场发售。这令其他上海各报望尘莫及,杭州当地报纸也自叹弗如。《时报》还经常将报道的标题印成红色字体,几乎每天的报道都有一个整版,把体育新闻报道提到了与政治、经济、社会新闻同等的高度。[30]
“黄报”尤其注重新闻照片的刊登,图片数量多,且印制精良。“摄影迷”黄伯惠把自己的摄影爱好融入《时报》,特别重视图片的使用,鼓励记者多拍摄新闻图片。为此,报社购置了多架照相机,记者出门采访均可领用,同时发给软片一盒(12张),规定采用2张就可抵销一盒。[28]190《时报》组建了当时最为强大的摄影队伍,中国新闻史上第一个专职摄影记者郎静山曾在《时报》供职,摄影名家唐镜元任摄影部、制版部主任。《时报》在图片的选择上精益求精,“每天拍摄各类新闻照片一二百幅,报纸所用仅三五幅而已”[31]39。新闻照片在《时报》上刊出后,非常受读者欢迎,几乎每期有照片的《时报》销路就会多出一千余份。[32]
在印刷和版面编排上,《时报》采用最先进的印刷设备,印制极为精良,一改《时报》前期“一纸在手,翻阅未尽,十指尽黑”的窘态。[20]黄伯惠对印刷技术颇感兴趣,常在印刷机旁亲自与工人一起整修机器。他从德国花10多万银元购买了一套高速套色轮转印刷机,每小时印报纸可达162 000张,可套印红、黄、蓝三原色或其他颜色。他又向日本定制了铜模、电动铸字机、制版机等先进设备。1932年6月27日,《时报》特出《时报一万号》彩色纪念刊,以三色版套印一幅“威尼斯图”,在亚洲还是首次。在版面编排上,《时报》特别注重标题的编排制作,遇有重要新闻,以特大号的红绿字做标题,以至于上海通志馆在论及“黄报”时,认为其唯一特色就是在报头上印着大大的红字,《时报》卖的不是新闻,而是标题、大红字。
《时报》还采取了降低报价、赠送报纸附张等典型的大众化报刊的经营手段。得益于引人注意的内容、印刷精良的版面以及较低的售价,《时报》逐渐打开了销路,本埠销量曾一度超过《新闻报》。遗憾的是,黄伯惠的上述做法被当时报界耻笑为上不了台面,也没有为他带来经济利润。相反,他却为《时报》倾注了大半心血,耗费了大量资财。最主要的原因是他一味为了满足自己的癖好而不考虑投入产出比。一支规模大、待遇高、奖励优的外勤记者队伍,雄冠亚洲的高速、套色彩印设备,摄影人员、设备以及制版印刷,重大事件的大手笔操作都刺激了《时报》的销量,同时成本也迅速增大。在整体行业不景气、广告投放有限的背景下,销量的扩大不仅不能带来利润,反而要消耗大量资金。
1937年11月,日军侵入上海后,黄伯惠为维持报纸出版,甘愿(当然也有被迫的成分)接受日伪的新闻检查,骨气与品格俱毁。1939年5月,汪精卫一伙来到上海,酝酿劫夺《时报》。黄伯惠发觉后及时停刊,并向工部局请求立派探捕保护房产,9月《时报》正式停办。黄伯惠刻意避开政治,最终仍因政治而走向终结。黄伯惠对报纸的种种嗜好、想象得以梦想成真,但他关于民营报纸大众化的探索却宣告失败。
四、结语
我国近现代报刊的构成形态是多样而复杂的,不能将其简单化、标签化。惯常认为,党人所办报纸是政治集团的舆论喉舌,亦步亦趋;文人办报,论政而不参政,长于言论而疏于报纸本身业务革新;商人办报则意在逐利,将经营置于第一位。上海《时报》的蜕变经过,却向我们展现出不同于上述认知的另类形态:它由康梁创办,却宣传不力,无法有效充当耳目喉舌,最终与康梁分道扬镳;转为民营身份后的《时报》,在以狄葆贤为首的一帮文人经营下,极力革新报纸本身,引领报界风尚,却在言论上了无影响,甚至摇摆不定,报人自己也积极参与政治;对报纸抱有一腔热情的富商黄伯惠接办后,仿效欧美报界,走大众化路线,购置先进设备,改良印刷,赚够读者青睐,却无法实现经济上的赢利。最终,刻意回避政治的《时报》终逃不脱因政治而走向终结的命运。
造成这种结果的原因,最主要的是中国近现代以来复杂而又快速变换的政治生态,报刊缺少自主性,不允许有足够的时间和空间按照自身规律,根据中国本土实际来生长、发展、壮大。狄葆贤试图突破康梁把《时报》作为保皇党耳目喉舌的限定,办有品质的报纸,短短时间内声名鹊起,但还没来得及赢利就不得不转让出去。黄伯惠照搬欧美大众化报纸的做法,孜孜不倦,办得也算有声有色,发行量大增却连偌大家产都赔了进去,从反面证明了民营大众化报纸在中国是行不通的。狄葆贤弃康梁而亲近江浙立宪派,积极参与政治活动以及黄伯惠刻意避开政治最终还是为政治所累,无不表明民营报纸的生存空间极其狭小,生存发展异常曲折艰难也就不难理解了。
[1]张朋园.时报:维新派宣传机关之一[J].中央研究院近代史研究所集刊,1973,4(上).
[2]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上)[G].内部资料,1982.
[3]中国人民大学新闻系.中国近代报刊史参考资料(下)[G].内部资料,1980.
[4]丁文江,赵丰田.梁启超年谱长编[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3.
[5]梁启超.梁启超全集(第十八卷)[M].北京:北京出版社,1999.
[6]吴廷俊.中国新闻事业史[M].武汉:武汉大学出版社,2009.
[7]罗石.狄葆贤氏族的诗学传家和文学思想[D].苏州:苏州大学,2008.
[8]戈公振.中国报学史[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11.
[9]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1997.
[10]包天笑.钏影楼回忆录[M].香港:大华出版社,1971.
[11]刘圣清.中国新闻记录大全[M].广州:广州出版社,1998.
[12]刘永文.晚清报刊小说研究[D].上海:上海师范大学,2004.
[13]张振亭,尹婷.我国报纸创办专刊的最早尝试:上海《时报》专刊研究[J].郑州大学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3,(3).
[14]张振亭,赵庆.《时报》系及其集团效应初探[J].中国出版,2014,(22).
[15]吴廷俊.新记《大公报》史稿[M].武汉:武汉出版社,1994.
[16]张季鸾.本社同人的声明[N].大公报(重庆),1941-05-15.
[17]尚贤政治与平民政治[N].时报,1913-02-10.
[18]黄炎培.八十年来[M].北京: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
[19]章开沅.张汤交谊与辛亥革命[J].历史研究,2002,(1).
[20]邵翼之.我所知道的上海时报[J].报学(台北),1955,(8).
[21]朱颜.黄伯惠与时报[J].金山文史资料,1992,(11).
[22]顾执中.报人生涯[M].南京:江苏古籍出版社,1987.
[23]袁义勤.黄伯惠与《时报》[J].新闻大学,1995,(5).
[24]郑逸梅.清末民初文坛轶事[M].北京:中华书局,2005.
[25]李彬.全球新闻传播史[M].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05.
[26]刘笑盈.“窃听门”真相:默多克传媒帝国透视[M].北京:新华出版社,2011.
[27]王文彬.中国现代报史资料汇辑[G].重庆:重庆出版社,1996.
[28]方汉奇.中国新闻事业通史(第二卷)[M].北京: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1996.
[29]高拜石.新编古春风楼琐记(6)[M].北京:作家出版社,2005.
[30]董新英.黄伯惠时期《时报》特色研究[D].长春:吉林大学,2009.
[31]甘险峰.中国新闻摄影史[M].北京:中国摄影出版社,2008.
[32]陈祖民.郎静山重访上海滩[J].新闻记者,1994,(1).
〔责任编辑:曹金钟 王 巍〕
G219.29
A
1000-8284(2015)01-0191-06
2014-12-09
江西省高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项目“上海《时报》研究(1904-1939)”(XW1307)
张振亭(1979-),男,河南民权人,副教授,博士,从事新闻史论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