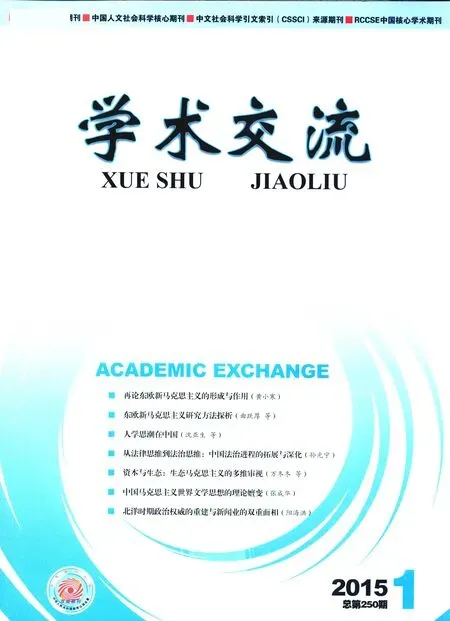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的理论嬗变
2015-02-25张成华
张成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241)
世界文学研究
·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专题·
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的理论嬗变
张成华
(华东师范大学中国语言文学博士后流动站,上海 200241)
世界文学不是固定不变的概念,它随着时代的变化改变自己的内涵和外延。五四时期,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人道主义和马克思主义结合,以人道主义为基础将世界文学构想为表现人性、国民性的文学的整体;五卅运动前后,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聚焦世界革命的时代精神,世界文学被构想为以阶级革命为基础的世界革命文学;抗日战争时期,世界文学被构想为围绕同一伟大理想的各民族高度发展的文学的集合。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对民族遗产的关注,中国的马克思主义者以“中-外”的视角看待中国和其他国家文学的并存和交流、以“东-西”对抗结构构想世界文学的体系。对我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的理论嬗变进行梳理,能够为我们在全球化时代提出合适的世界文学思想提供借鉴和支撑。
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理论嬗变
马克思和恩格斯在《共产党宣言》中指出:“资产阶级,由于开拓了世界市场,使一切国家的生产和消费都成为世界性的了……物质的生产是如此,精神的生产也是如此。各民族的精神产品成了公共的财产。民族的片面性和局限性日益成为不可能,于是由许多种民族的和地方的文学形成了一种世界的文学。”[1]今天,世界经济全球化的深入已经引起了人们对世界文学更为广泛的讨论。梳理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的发展和演变,一方面能够突显我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的独特性和创新性,另一方面能为经济全球化形势下参与世界文学讨论和提出我国自己的世界文学构想提供参照和支撑。
一、“世界主义”与“时代精神”统摄下整体的世界文学观和革命的世界文学观
清末民初,在外国侵略和各阶层寻求救亡图存的过程中,一些有识之士,开始具备一种“世界主义”的视野。在“五四”新文化运动中,这种“世界主义”视野成为反对文化保守主义和进行文化变革的基本导向。“于此而执特别历史国情之说,以冀抗此潮流,是犹有锁国之精神,而无世界之智识。国民而无世界智识,其国将何以图存于世界之中?”[2]同样,这种“世界主义”意识也深深嵌入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构想世界历史进程和解读阶级斗争的思想中。“我们要晓得一切过去的历史,都是靠我们本身具有的人力创造出来的,不是那个伟人、圣人给我们造的,亦不是上帝赐予我们。将来的历史,亦还是如此。现在已是我们世界的平民的时代了,我们应该自觉我们的势力,快赶[赶快]联合起来,应我们生活上的需要,创造一种世界的平民的新历史。”[3]221-222当然,中国早期的这种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内含着一种强烈的人道主义色彩。“由今以后的新生活、新社会,应是一种内容扩大的生活和社会——就是人类一体的生活,世界一家的社会。”[3]117“我们应该拿世界的生活作家庭的生活,我们应该承认爱人的运动比爱国的运动更重。”[3]13
在这种带有强烈人道主义色彩的“世界主义”意识统摄下,这时的马克思主义者往往以“人性”为根基构想世界文学。“翻开西洋的文学史来看……虽则其间很多参差不齐的论调……然而有一句总结是可以说的,就是这一步进一步的变化,无非欲使文学更能表现当代全体人类的生活,更能宣泄当代全体人类的情感,更能声诉当代全体人类的苦痛与期望,更能代替全体人类向不可知的运命作奋抗与呼吁。”[4]23-24当然,“现时种界国界以及语言差别尚未完全消灭以前,这个最终的目的不能骤然达到,因此现时的新文学运动都不免带有强烈的民族色彩”[4]24,“亦惟能表见(现)国民性之文艺能有真价值,能在世界的文学中占一席地”[4]22。可是,“所谓国民性并非指一国的风土民情,乃是指这一国国民共有的美的特性”,只有表现一个民族真善美的文学,“才是有价值的文学”,才能“在世界也生了绝大的影响”[4]28。这种以“人性”为根基构想世界文学的方式,在五四之后的一段时间相当流行。与茅盾同属文学研究会、中国最早系统论述世界文学的学者郑振铎认为,“世界的文学就是世界人类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5]68,“文学是人生的反映,人类全体的精神与情绪的反映。决不宜为地域或时代的见解所限,而应当视他们为一个整体,为一面反映全体人类的忧闷与痛苦与喜悦与微笑的镜子”[5]70。
中国早期的马克思主义者将人道主义与马克思主义并列,以人道主义纠正马克思主义阶级斗争“偏蔽”的做法使其能够以人道主义为根基构建一种总体的世界文学思想。“立足于‘全人类、全世界’而平等对待中外古今文学的态度,不仅做到了将‘文学定位于全人类价值’,而且做到了‘立足于本民族自身的传统’,将中国传统文学纳入了‘世界文学’的构架之内并给予其合理的定位,这充分显示出中国的‘世界文学’观念已经臻于成熟。”[6]可是,我们看到,对于马克思主义者来说,这种“成熟”的世界文学观念是以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的偏颇而获得的。随着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对马克思主义学说理解的深入,也随着中国社会政治局势的转变,这种世界文学思想必然会被抛弃和替代。
五卅前后,李大钊笔下的“世界的无产阶级”——“中国的农业经济挡不住国外的工业经济的压迫,中国的家庭产业挡不住国外的工厂产业的压迫,中国的手工产业挡不住国外的机械产业的压迫。国内的产业多被压倒,输入超过输出,全国民渐渐变成世界的无产阶级,一切生活,都露出困破不安的现象”[3]147——与一种久已存在的“时代精神”融合在一起。“像罗丹所雕刻的铜器时代的人一样,世界的无产者正从沉睡中醒来,应着时代的号声的宣召,奔赴历史所赋予他们的使命。从黑暗到光明,从苦痛到解除苦痛;这一个暴风雨的时代啊!正是从有人类历史以来最富有色彩、动作和音声的时代——一个大活剧的时代!”[7]这个“大活剧”的时代是革命的时代。“在现在的时代,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活泼些,光彩些?有什么东西能比革命还有趣些,还罗曼谛克些?倘若文学家的心灵不与革命混合起来……他取不出来艺术的创造力”[8]62。从“五卅”经过“革命文学”论争到“左联”时期,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总是浸润着这种激情澎湃的革命“时代精神”。这种“时代精神”将中国与世界历史的发展进程联系在一起——“我们的国民的或者民族的要求,归根是和他们资本主义国度下的无产阶级的要求完全一致”,也将中国文学与世界文学发展的历史进程联系在一起——“你们要晓得我们所要求的文学是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学,我们的要求已经和世界的要求是一致”[9]12。世界文学不再以表现全人类和服务全人类为目标。“从文学发展的史迹上看来,文学作品描写的对象是由全民众的而渐渐缩小至于特殊阶级的。”[4]85
这种革命“时代精神”挟裹下的世界文学理念,首先构想了以经济发展为基础的世界文学发展史。“某一时代经济发展的形式规定某一时代文化发展的程度:原始共产社会时代的文化是一样,封建制度时代的文化是别一样,而资本主义时代的文化更与前二者不同。”[8]139“无产阶级艺术这个名词正式引起世界文坛的注意,简直是最近最近的事!”[4]87以经济发展为基础构想的世界文学发展史是阶级文学斗争的历史,必然支持一种“进步文学”的取向。“在欧洲今日的新兴文艺,在精神上是彻底表同情于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艺,在形式上是彻底反对浪漫主义的写实主义的文艺。这种文艺,在我们现代要算是最新最进步的革命文学了。”[9]10其次,在“时代精神”上与世界阶级斗争的现实取得一致,促使中国文学的创作也要与世界文学的发展潮流取得一致。“中国的革命已经与世界的革命混合起来了,中国的劳苦群众已经登上了世界政治的舞台……倘若有人以国家主义的文学为革命文学,这也未免是时代的错误,根本与现代中国革命的意义相违背。”[8]172“中国的文学家不但要著作些东西给中国人看,并应努力攀登上世界文学的舞台,与世界的文学打成一片。”[8]156当然,对世界文学发展趋势的追逐要求中国文学打破“狭义”的国家民族界限。“我们的革命文学应极力暴露帝国主义的罪恶,应极力促进弱小民族之解放的斗争,因为这也是时代的任务,但同时应极力避免狭义的国家主义的倾向。”[8]173最后,在对旧文学的批判和斗争中,在对“狭义”的国家主义的突破中,这一世界文学理念带有强烈的否定中国民族文学的倾向。一方面,中国传统文学被以阶级属性进行划分和重新估价。精英式的文学形式被贴上“封建”“贵族”(中国传统士大夫文学)或“资产阶级”“新文言”(五四时期创作的白话文学)的标签而被否定,中国传统的文化精神被称为“青天白日主义”而成为斗争对象——“青天白日是所谓青天大老爷的主义。武侠和剑仙是一个青天大老爷,所谓祖国民族也是一个青天大老爷。宗法主义是这样,市侩主义也是这样,一切反革命的武断宣传都是这样”[10]。另一方面,“新”的能追赶世界文学潮流的无产阶级文学又并没有创造出来。“固然现代中国文学发展的阶段很快,但不能超出相当的限度。就拿现代中国文坛上几个著名的作家仔细地看一看,喂!哪一个能与西欧的大作家相比!只是幼稚,幼稚,幼稚而已……不革命的文学尚且如此地幼稚,那吗(么)所谓革命文学不过是近两三年来的事,既没有过去的传习,又没有长时期的发育,如何能免去幼稚的毛病呢?”[8]168
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时代精神”挟裹下的世界文学,是革命的世界文学。这种革命的世界文学反映世界无产阶级革命的现实,以无产阶级的阶级观念为基本价值取向,为世界无产阶级革命服务;进而,这种革命的世界文学又是斗争的文学:在国际上,它与资产阶级的文学形式进行斗争,在中国国内与士大夫文学和五四白话文学进行斗争。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往往以世界文学为支点批判本国的文学创作。在具体的事例上,是对原苏联文学典范地位的推崇。“俄罗斯不但给了世界以伟大的革命,而且在现今的时代给了世界以伟大的文学……似乎伟大的革命为文学开辟了一条伟大的路;顺着这条路走去,俄国文学的发展更有难以预料的伟大的将来。”[8]187事实上,直到新中国成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原苏联文学都被建构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潮流和趋势,是我国文学模仿的典范。对原苏联文学典范地位的确认勾勒了中国文学发展的方向,但同时也加强了对中国传统文学的否定。
二、“民族形式”讨论下以民族文学自我发展为基础的世界文学思想
随着日本帝国主义对中国侵略的日益加重,尤其是在1935年“华北事变”之后,中国文艺界为了统一抗日力量以实现民族救亡的现实需要而提出了“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两个口号。在围绕这两个口号展开的论争中,一方面,文学的大众取向更为明显,另一方面,文学与现实斗争形式联系得更加紧密。以对“国防文学”的界定为例:“‘国防文学’的任务,首先是认识和反映中国反帝斗争的情境和力量……‘国防文学’首先是中国劳动大众文学,可是在为着民族和社会解放的斗争上,它又是全中国民族的文学。”[11]32当然,“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都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文学,这两个口号在具体解释中都有很强的国际主义取向。它们往往将自身与弱小民族的反抗斗争联系起来以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为目标。“国防文学可以‘民族’为畴范而反对帝国主义的侵略,待得民族的自由解放,它的终极目的是全世界各个民族的自决。”[11]340因此,在“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口号下阐释的世界文学必然是以被压迫民族的解放为目标的“新人类”“真实人类”(被压迫民族、阶级)的文学。“我们的时代是广泛的大众的革命实践的时代,是诞生新人类的时代”[12]838,“国防文学的特殊性是跟着社会主义现实主义走的一个新阶段……是真实人类及其社会相互关系的艺术反映”[12]839。
在围绕着“国防文学”和“民族革命战争的大众文学”的论争中,虽然一直强调打破狭隘的民族国家主义界限,但还是隐含着一种民族文化自我认同的取向。“种族的低劣,人民的野蛮,都是‘白人的担子’,而‘开化’他们,也是‘肉弹三勇士’的神圣的荣耀。但是,我们的‘国防文学’,必然要谢绝这种‘开化’,请他们放下他们的‘担子’,虽然我们不是狭义的爱国主义者,但我们很明了自己的民族性并不低劣,我们不看轻人家,我们也不看轻自己,她更要使人家不能看轻自己。”[11]63-64中国传统的文学形式确实可能存在着许多缺陷和弱点,但是,对这些弱点和缺陷的纠正只能依靠本民族的特性而不是依靠白人的“开化”。只有在对民族性认同的基础上,我们才能创造出属于我们民族的、反映我们国家人民生活状况的、为我国人民大众所需要的文学。这种民族文学认同在延安时期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中逐渐与民族战争和阶级战争联系在一起,并进一步加强。
随着抗日战争的全面爆发和为了使文学更好地服务于抗战需要,在1939年左右,延安开始了关于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为什么今天要提起文学、艺术的‘民族形式’这一问题呢?我想,是因为这伟大的民族解放战争,它要求文学、艺术为它服务,而文学、艺术也自觉地起来为它服务了。”[13]604当然,关于“民族形式”的讨论并不是孤立的涉及本民族的解放斗争和单纯主张文学为战争服务。它以一种世界主义视角讨论中国的民族文化和文学,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理解世界文学的进程,以一种创新性的意愿引导本民族文学的发展和重建。
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中国革命是世界革命的一部分。因此,“在观念形态上反映政治革命和经济革命,并为它们服务的”文化革命,也具有这种世界性。[14]699“由于现时的中国革命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革命的一部分,因而现时的中国文化也是世界无产阶级社会主义新文化的一部分,是它的一个伟大的同盟军。”[14]705当然,当毛泽东以阶级革命为基础解释文化时,他必然会以一种发展的眼光看待本民族和世界文化。“在‘五四’以前,中国的新文化,是旧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在‘五四’以后,中国的新文化,却是新民主主义性质的文化,属于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的文化革命的一部分。”[14]698世界文化是发展的,其发展的路径由“世界资产阶级的资本主义”文化走向“世界无产阶级的社会主义”文化。在毛泽东关于中国文化与世界文化及二者关系的思想的统摄下,关于世界文学和文学的“民族形式”的讨论也具有一些独特性和创新性。
首先,世界文学是由围绕“同一伟大理想”的高度发展的民族文学组成的整体。“我们相信迟早会出现这样一个世界。这种世界性的文学艺术并不是抛弃了现有各民族文艺的成果而凭空建立起来的。恰恰相反,这是以同一伟大理想但是不同的社会现实为内容的各民族形式的文艺各自高度发展之后,互相影响溶化而得的结果。是故民族文学之更高的发展,适为世界文学之产生奠定了基础。”[13]648-649因此,“世界文学”是未来的理想,是文学发展的方向。之所以当时还不可能,是因为:其一,“同一伟大理想”的时代还没有到来。其二,民族文学发展的程度还不够。其三,民族之间闭塞,“互相影响溶化”还不可能。
其次,以“同一伟大理想”为基础的世界文学并不是要否认民族文学的特殊性。恰恰相反,世界文学是多样性民族文学的“相对的统一”。“至于艺术(无论它的内容或它的形式)的国际性,只是意味着它的相对的统一,不是绝对的统一……愈是强调艺术的国际性,愈是应该发扬民族性。在各个民族特色的发扬与相互渗透过程中,才能创造统一的国际性的艺术。”[13]625正是对组成世界文学的民族文学独特性的强调,才不至于失掉民族性和民族自信心,才能立足中国当时的社会现实进行文学创作,也才能显示中国文学在世界文学中的标识和贡献。“在世界文库里,要是找不出代表中国气派的文化成果来,那末,想研究中国文化的外国人,就一定会感到中国民族的空虚而长叹了。带特殊性的优秀的民族文化,恰足以帮助世界文化的发展。”[13]602
其三,正如世界文学只能指向未来一样,民族文学在当时也只被理解为一种构想,一种正在创造的成果。“因为民族形式的文艺,是意味着一种新生的尚待创造的东西,而不是一种既成的事物,尤其对于此意味中的新生事物的具体形态和特征,这是一个须待展开讨论的课题。”[13]623-624因此,对延安时期的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家来说,中国传统的民族形式是需要严格甄别的。“利用旧形式的方式,首先要酌量解放它的一些生硬不化的格律。凡是妨碍反映现实的规律都可以大胆地放弃。”[13]599“真正的”“新的”民族形式不仅是能够服务于民族解放战争的形式,更应该是反映人民大众生活、关注人民大众生活的形式。因此,能够利用的旧形式就不是中国传统的精英文学形式,而是存在于底层的民间形式。当然,这些民间形式只是“真正的”“新的”民族文学的资源和胚芽,还需要在具体的文学创作中进行创造性的运用,剔除其封建的残余成分,以求更好地反映人民大众的真实生活,反映人民大众当家做主的新时代。
总结新中国建立前中国马克思主义世界文学思想我们可以看到,以阶级属性为基础构想世界文学,必然会将世界文学看作是内部充满冲突和矛盾的场域——主要表现为无产阶级文学和资产阶级文学的冲突。同时,这一冲突暗示了无产阶级文学取代资产阶级文学的世界文学发展趋势,也暗示了本民族文学与世界文学一致的发展趋势。
三、民族遗产整理下“中-外”民族文学关系和“东-西”对抗的世界文学体系
新中国建立后的很长一段时间,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仍然以世界历史进步观和阶级斗争为基础构想世界文学。这主要延续于对原苏联文学的态度上。“对照着苏联文学艺术的繁荣兴盛,现代世界资产阶级的文学艺术正经历着堕落和解体的过程。很显然地,这正是新世界日益成长壮大,旧世界日益没落衰亡的反映。”[15]333原苏联文学被构想为世界文学发展的方向,是世界进步文学的中心。“苏联文学已成为整个世界进步文学运动的核心。中国有句古语:‘譬如北辰,居其所而众星拱之’,可以用来恰当地形容苏联文学与世界各国进步文学的关系。”[15]333
可是,新中国成立后,阶级斗争和民族战争基本结束,单纯以阶级斗争为视角看待中国民族文学和世界文学已不合时宜。新中国领导人和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开始反思之前对待旧文化、文学的态度和方法,并以更加积极的态度看待本民族文化和文学传统。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对中国传统文学遗产不再持总体的批判态度,而更关注其优秀成分和对文学创作的借鉴作用。“这就是说尊重古代文化,批判地吸收其精华,是相信自己的民族,爱护自己的祖国的不可少的条件……不要把封建时期的文学和资本主义时期的文学贴上个封条就算完了。”[15]13-14当以国家、民族为视角,而不是以(或纯粹以)阶级斗争为视角看待文化和文学时,他们也就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审视其他国家和民族的文化和文学传统。除了将原苏联文学看作世界文学的中心和发展方向外,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还突显出另外一种看待我国与其他国家文学的结构——“中-外”结构,以“中-外”的眼光处理中国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化和文学的关系。“文化遗产包括本国遗产和世界遗产。研究学问就要具备古今中外的知识。作为文化来源的古今中外。‘中’和‘今’应该是主要的,但只有‘今’没有‘古’不行,只有‘中’没有‘外’也不行。”[16]14以这一结构看待世界文学,自然能将世界文学看作各民族优秀文学的集合,也能以更加积极的态度吸取其他国家、民族的优秀文学成果。“近代文化,外国比我们高,要承认这一点。艺术是不是这样呢?中国某一点上有独特之处,在另一点上外国比我们高明。小说,外国是后起之秀,我们落后了。”[17]
当然,这时的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并没有完全放弃以阶级斗争为基础构建世界文学的方式,只不过是将这种方式进行了创造性挪用。自清末民初,“天朝上国”的美梦被打破,中国知识分子就往往将中国与弱小国家联系在一起。一直以来,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除了积极关注原苏联文学之外,另一个聚集的焦点是其他被压迫的弱小国家文学——北欧、印度等。随着新中国的成立和中苏关系的降温,中国以更加积极的姿态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联系。在加强与亚非拉国家的联系和反抗西方国家霸权的过程中,中国逐渐形成以“东-西”对抗为基本理念的处理国际事务的方式。这一理念同样渗透于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的世界文学思想中。周扬在《在亚非作家会议上的报告》中指出:“今天我们亚非两大洲的作家在这里讨论东西方文化的联系这个问题,这标志人类历史进入一个新的阶段,我们正在新的基础上发展东方各国人民之间以及东方和西方人民之间的友谊和文化交流。”[16]52以反对西方文化霸权和加强东西方文化交流为基础,周扬对歌德的“世界文学”构想进行了重新阐释。在歌德看来:“诗是人类共同的财产……‘民族文学’这个用语现在的意义已经不大了,‘世界文学’的时代快要到来了,我们每个人应该促使它的到来。”[16]56-57①此处为周扬自己的翻译。周扬对歌德这段话的理解是:“他(歌德)在这里不是否定‘民族文学’,而是否定那种把自己的民族文学当做世界上唯一文学的狭隘观念……他所说的‘世界文学’应该理解为世界各民族文学优秀产品的集合,因为它们是‘人类共同的财产’。”[16]57
中国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家处理世界文学的两种方式——以“中-外”视角处理我国文学与世界其他国家文学的并存和交流,以“东-西”对抗结构构想欧美文学对亚非拉文学的殖民和入侵——成为我们一直沿用的讨论世界文学的基本方法。这两种处理世界文学的方式不再以阶级斗争为基础,而是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它们将世界文学构想为一个平台,一个各民族国家文学相互对抗、交流的平台。正因为这两种方式都以民族国家为基础,在全球化的今天对我们构想世界文学理论仍有借鉴作用。
总之,世界文学是突显矛盾的结点,随着时代和政治形势的变化,中国马克思主义者不断以其突显出阶级、国家-民族、东西方之间的矛盾。我们也不应该将世界文学固定化和规范化,仅仅通过追溯歌德或马克思的世界文学思想确认其含义和价值。就像我们在中国马克思主义者关于世界文学的论述中所看到的,世界文学不仅显现为不同国家、民族文学的自我表现和汇聚,而且是一个对立统一的矛盾汇聚场所。尤其是在经济全球化的今天,世界文学是“中”“外”文学并存和交流的场所,“东”“西”文学对抗的领域。我们只有从矛盾论的视角看待世界文学,将其看作矛盾汇聚的一个结点,看作不同国家、民族文学在相互对立中寻求统一的共同交流的领域,才能突显和确认本民族文学的特质和对世界文学的独特贡献,才能提出符合当代文学发展趋势的世界文学理论。世界文学不单单意味着世界声誉——从世界声誉的角度理解世界文学会将世界文学内含的矛盾抹平,世界文学是矛盾汇聚的场所。
[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35.
[2]陈独秀.独秀文存[M].合肥:安徽人民出版社,1987:7.
[3]李大钊.李大钊全集(第3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2006.
[4]茅盾.茅盾选集(第5卷)[M].成都:四川文艺出版社,1982.
[5]郑振铎.文学的统一观[M].达姆罗什,刘洪涛,尹星.世界文学理论读本.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3.
[6]潘正文.中国近现代启蒙思潮与“世界文学”观念的发展[J].文艺研究,2007,(9):32-39.
[7]沈泽民.文学与革命的文学[N].民国时报(副刊·觉悟),1924-11-06.
[8]蒋光慈.蒋光慈文集(第4卷)[M].上海:上海文艺出版社,1988.
[9]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革命文学”论争资料选编(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1.
[10]瞿秋白.瞿秋白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475.
[11]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上)[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2]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现代文学研究室.“两个口号”论争资料选编(下)[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2.
[13]《延安文艺丛书》编委会.延安文艺丛书(第一卷·文艺理论卷)[M].长沙:湖南人民出版社,1984.
[14]毛泽东.毛泽东选集(第2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5]周扬.周扬文集(第2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6]周扬.周扬文集(第3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1985.
[17]毛泽东.毛泽东文集(第7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9:81.
〔责任编辑:曹金钟 孙 琦〕
I109.9
A
1000-8284(2015)01-0163-06
2014-10-18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国外马克思主义文论的本土化研究——以东欧马克思主义文论为重点”(12AZD091)
张成华(1985-),男,山东临沂人,博士后,从事澳大利亚马克思主义文学理论和文化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