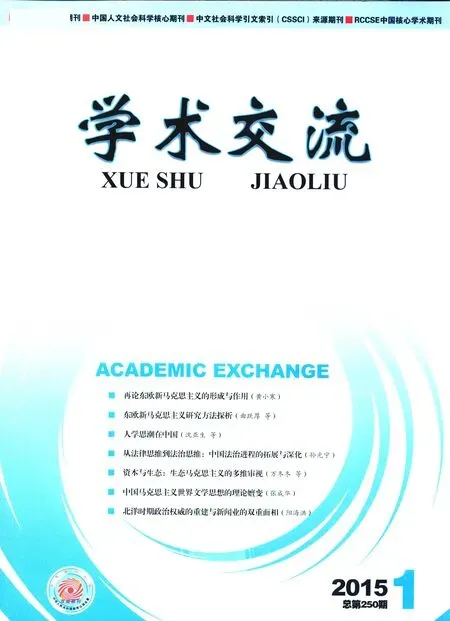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政治参与
2015-02-25赵春丽
赵春丽,郭 虹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政治理论研究
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政治参与
赵春丽,郭 虹
(北京工商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北京 100048)
微博消费主义影响下的政治参与日益凸显大众权威的解构力量,并以日常生活为重要的参与内容,以休闲狂欢作为主要的参与方式。这对于消解传统的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凸显大众的权威,激发民众参与热情,实现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向,都有所助益。然而,微博消费主义是商业化行为,它以利益为根本导向,其积极的政治功能并非主动为之,微博等新媒体也以各种方式进行着自我规制,对于开放的公共讨论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用消费主义的商业动机侵蚀着公共话语空间,以娱乐狂欢掀起民粹主义的涟漪。但是不管如何,新媒体与政治从来都不可能互相撇清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微博等新媒体仍然会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影响着公民参与、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
微博消费主义;政治参与;日常生活
随着市场经济的深入推进,消费主义的生活方式和文化观念日益为大众所接受。“消费主义”是法国著名社会学家波德里亚在其专著《消费社会》中所提出的概念,主要批判了西方社会消费至上的资本主义生活方式,“表面上以物品和享受为轴心和导向的消费行为实际上指向的是其他完全不同的目标:即对欲望进行曲折隐喻式表达的目标、通过区别符号来生产价值社会编码的目标”[1],这些对符号象征意义的追求满足了人们不断被刺激的心理欲望。市场化竞争的传媒为了自身利益不断迎合民众消费主义的追求,传媒和消费主义日益结合,形成了传媒消费主义。所谓传媒消费主义,主要是指:“传媒迎合受众的感官消遣和感性需求,以煽情和娱乐的角度处理表现内容和报道方式,营造一种具有普适性的消费文化,以浅层次的阅读指向唤醒受众的消费欲望,以此来达成收视率、发行量及广告收入的提升,并从中获取商业利润。”[2]媒介的消费主义倾向是当今世界各国媒介发展的重要现象之一。媒介与消费主义合谋已经深刻影响着人们的生活方式、价值观念和社会心理,甚至是政治生活。和其他媒介一样,媒介的消费主义在微博里也得到充分展现。与此同时,微博也是当前中国民众表达意见、诉求和进行舆论监督、参与公共事件的重要途径,是人们参与公共生活的又一重要载体。微博消费主义倾向和政治生活的相遇给政治参与带来新的特点和隐忧。
一、微博消费主义倾向的表征及动因
2009年以来,兼具博客和即时互动工具功能的微博作为互联网新的应用媒介获得蓬勃发展,它快速走进中国普通网民的视野。裹挟着商业动机的微博新媒介在消费主义的社会氛围中也逐渐向媒介消费主义迈进。“网络作为媒介,已经成为人们日常社会生活最具支配性和主宰性的力量之一,引领着人们的文化需求,刺激了人们的消费欲望,把网民一个个培养成显在或潜在的消费者,网络成了消费主义的兜售器。”[3]微博的碎片化、裂变病毒式传播又使得用户时时刻刻都被海量的爆炸性消费信息包围。微博里无时无刻不充斥着消费主义的气息,成为传媒消费主义又一典型的媒介通道。
1.商业广告蔓延和娱乐至上:微博消费主义的直接表征。消费广告和娱乐至上是微博消费主义的直接表征。在商业主义驱动下,微博的传播特性使得其成为商家进行广告营销的绝佳平台,微博里海量广告、嵌入式广告与事件营销、微博软文等比比皆是,处处是商业利益的弥漫。一些营销公司在微博空间里注册了大量僵尸微博,以主动关注微博里的用户、成为微博用户的粉丝来吸引用户注意力,从而赚取点击率,达到商业营销的目的。还有一些微博以大量发表人生哲理、逸闻趣事、搞笑幽默等内容为手段赢得大量粉丝;一些具有噱头的豪车美女新闻、奢侈品消费、奢靡生活方式也是微博媒介里大肆传播和炒作的信息,不断刺激着人们的眼球和消费欲望。大量商业广告、消费新闻的弥漫,为微博披上了浓厚的消费主义外衣。娱乐化是运营商经营微博的另一策略,也是微博消费主义的重要媒介内容和形式。在微博产生之初,为了微博的普及和运用,各大微博运营商邀请大量娱乐、时尚、体育明星开通微博,赢得粉丝和人气。当红歌星、影星、导演、电视节目主持人、体育明星在微博传播中普遍具有较高人气,在粉丝排名前十的微博大V中娱乐、时尚行业占据八位。①根据新浪微博2013年9月20日晚22:22分数据,粉丝数前十名分别为:陈坤(54701208个),林心如(52120013个),李开复(51372854个),郭德纲(51254525个),姚晨(51173149个),张小娴(46109872个),赵薇(45605717个),文章同学(39947632个),小P老师(39367881个),范玮琪(38098661个)。各大微博首页推荐话题也以大量娱乐信息为主,娱乐名人的隐私、消费与生活方式等娱乐信息充斥微博空间。正如有研究者评论道:当前的中国互联网空间呈现强烈的“人性娱乐化”功能,网络空间里造星运动、集体窥私、网络聊天、游戏上瘾、虚拟交往、网络另类狂欢等娱乐至死现象甚嚣尘上[4]。总之,商业广告、消费英雄和娱乐明星是微博海量信息的重要内容。
2.网络炒作与网络恶搞:微博消费主义的突出表征。除了赤裸裸的对人们消费欲望的不断刺激,网络本身也变成一种消费与消遣的工具,网络里的各种事件、新闻、人物、电影电视作品、信息符号等都成了人们的消费对象。各种“哥”、“姐”借助于网络推手的炒作,成为人们在网络空间高度关注和围观的话题人物,一夜之间迅速成为名人。这些看似违背常理、疯癫搞怪、不按常理出牌的人物却成为人们追捧和关注的对象,成为大众狂欢的消费品。网络炒作与恶搞借助微博传播成为重要的文化现象,消费主义从对现实的“物”的消费变成对一切对象的消费,不断刺激、满足着人们的欲望,也影响着人们的心理和思想以及价值判断。西方学者鲍曼曾提出消费主义“并不是指寻求和积累财富。它在本质上是指寻求刺激(不必然是快乐的刺激,至少不必然是凭自身能力得来的快乐刺激;它是对刺激的占有,甚至是希望获得被体验为快乐的新刺激)”[5]。在一定物质满足之下,当人们又无法追求更高的文化和精神体验时,感官的刺激就是人们的一种心理需要,网络世界里的炒作与恶搞正是满足了人们寻求新鲜刺激、颠覆惯常思维的心理需要。在对“物”的消费完成之后,除了接受新的消费欲望的刺激之外,人们开始消费人类自己,“对物的欲望和无休止的崇拜转移了人类对人本身的关注,人作为物的附属品,更多地以符号的形式存在于物与物的关系之中,而指向于人的欲望的物逐渐异化为控制人的物。在大众传媒尤其是低门槛、匿名的网络媒介的影响下,作为物的附属品的人也通过对符号的消费完成对物的消费的最彻底的感受,在布满物与符号的虚拟世界里,人的存在只剩下了眼睛、耳朵和点击鼠标的手指的存在。”[6]
网络炒作与恶搞盛行于微博,其根本动因就在于网络媒介的商业化利益导向。网络媒介以商业利益为最终的目标追求,微博上的“哥”、“姐”信息,各种恶搞文字、图片、视频被传播、被转发、被评论的次数越多,也就意味着信息的消费越多,也才能带来更多的流量消费和点击率,最终运营商和商业公司才可能获取更多的商业利润。“为了吸引观众以赢得广告费,媒体在新闻内容上不断增加隐私、冲突、丑闻、色情、搞笑、恐怖活动、政治腐败的内容,或者有意增减信息的内容以突出‘卖点’,或者制作有偿新闻等,以致传媒中的深度报道和评论节目纷纷让位给了那些煽情节目。”[7]商业利益主导下的网络空间似乎成为任何谋利者都可以肆意利用的营销手段与工具,只要去迎合和刺激网络受众的需要,任何东西都能被拿来消费,制造卖点,赢得点击率。“在消费社会中,由于利益的驱动,任何东西都能被卷入消费的洪流中。表面上网络恶搞似乎是网民的自娱自乐,其实质早就变为商家的营销工具和获利来源。”[8]在商业利益的驱动下,似乎任何文化人物、文化符号、精神偶像都成为人们的消遣消费的对象,网络媒介和一些商家可以将一切非娱乐的符号重新包装在微博空间里被人们点击和消费,在这个过程中,政治生活的娱乐化、消费化已不可避免,并成为网络政治生活中的重要内容。
二、微博消费主义倾向对政治生活的渗透
表面来看,微博的娱乐化不仅能够满足人们消费主义的心理欲望,而且能够诱使人们远离政治或者公共话题。不少研究者也担忧消费主义让人们免于政治参与,传媒消费主义话语的大行其道,会让政治领域、公共领域让位于私人领域。这一担忧不是毫无道理,然而,人们发现,随着媒介消费主义的兴起,新的话语形式和讨论空间随之出现,新传媒在传播消费主义导向的同时,不可避免地把对政治生活的讨论和参与挟裹进来,并以娱乐化的新型的话语形式与体系进行表达。
1.微博为消费主义话语向政治生活渗透提供了新的便捷的媒介形式。微博是“居间政治”的新中介,其传播特性进一步模糊了消费娱乐和新闻信息的界限。传统媒体中政治新闻和娱乐常常被人为地分割开来,在微博空间里,信息随时随地地传播,没有记者、官员、政策专家、理论家的把关,微博让新闻信息和一般信息同时发布于虚拟空间,普通民众具备了信息发布的权利,记者、政府宣传人员、专家等传统把关人缺失,新闻专业主义和政府宣传人员所把关的正统的新闻信息在新环境下与娱乐消费信息的差异变得越来越小。曾经被边缘化的群体成为新的话语力量,在设置和建构公众议程方面日益发挥重要作用。他们不是把关人,在信息发布时,没有新闻专业主义和政治宣传的约束,他们的信息混杂着新闻事实、花边故事、小道消息、似是而非的评论、爱憎分明的情感、不易把控的情绪以及消费与窥视的欲望。正是微博这样的新媒体,让普通人获取了更加自由的言说权利,使得消费娱乐信息和公共政治生活的话语深刻纠缠在一起,它们之间的边界越来越模糊。“原本高不可攀的‘政治’呈现出‘去隔离化状态’,即远离人们日常生活的政治外壳被打破了,‘可渗透的政治’变得无所不包,政治就是一切,对所有的传播模式开放。”[9]消费主义话语向政治生活渗透的倾向越来越明显,各种政治现象、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社会制度以及民主、自由、法治等等都变成了消费主义的猎物。
2.微博流行文化和娱乐精神本身承载着政治信息,对公共生活施加影响。置身于政治时代,政治主要是媒介化的经验,正如默里·埃德尔曼在《从艺术到政治》中所言,人们通过固有的观念和信仰对新的信息进行解读,政治态度和行为因而产生,而观念和信仰构筑于各种共享的文化渊源上。谁都无法否认艺术、流行文化、娱乐本身所承载着的政治信息和诉求,以娱乐和流行文化与艺术形式呈现的公共政治并不比直白的政治话语微弱,在微博等新媒体的媒介渠道中更能获得广泛传播。在特定情境中,新媒体传播的流行文化和娱乐符号的政治意义尤其会凸显。“消费的目的不是为了实际需要的满足,而是不断追求被制造出来、被刺激起来的欲望的满足。换言之,人们所消费的,不是商品和服务的使用价值,而是它们的符号象征意义。”[10]微博新媒介传播的后现代主义、流行文化、娱乐将符号象征意义转化为潜在的政治诉求与政治批判,暗含着对所追求的政治价值目标的聚积,逐渐影响受众,获取认可。微博里无限娱乐化和各种搞怪、嘲讽与自我嘲讽,又无不在表达对现实的讽刺、不满甚至抵抗的态度。娱乐渗透政治生活,而政治生活则以娱乐的方式走进民众日常生活。
3.微博消费主义不仅消费“物”、价值符号和意义,事实上它提出了所“需求”的政治。从一定意义上说,消费主义倡导的“需求”也并非单纯的娱乐或者是对个人喜好的表述,而是与其社会目的和社会利益问题相关,是人们对社会现状和公平和谐社会生活的期望。“需求”呈现了人们对社会资源占有的渴望,也在潜意识地提出社会应该提供象征性的或者物质性的资源以满足人们的需求。在消费主义的传媒话语中,抛开浮于表面的过度的需求,我们也能看到人们对于美好社会生活里社会财富和稀缺资源应该如何在不同阶层和群体之间分配的讨论,而无疑这些事关政治的制度安排和价值导向。微博空间的炫富女之所以被媒体用来炒作,被公众拿来消费,是因为其奢侈的生活方式不仅是对消费主义的引领,更容易点燃人们对利益分配、社会公平、贫富差距等问题的讨论,触动当前社会里公众敏感的神经,因而具有极高的卖点。炫富行为遭到无情批判,显然,人们不是批判奢侈品本身,普通民众也会渴望拥有“象征生活品位”的高端用品,人们批判的是炫富女背后的权色交易、腐败贪污和分配不公。显然,人们提出了关于社会资源分配、关于需求的正义问题。
三、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的政治参与
微博消费主义倾向是微博文化的重要方面,对微博发展产生重要影响。从政治参与的框架下审视,微博消费主义倾向既具有积极的意义,使政治参与朝着大众权威、日常生活、休闲娱乐的方向转变,呈现出“后现代政治”的特质,同时,也因其“后现代性”而冲击着政治参与的公共精神和价值追求。
1.大众权威的政治参与。微博消费主义的故事叙事和娱乐精神消解传统的政治权威。在消费主义的气氛中,官员也成为人们消费的对象,并在这一消费的过程中,逐渐瓦解传统政治权威,慢慢填平官员和民众的等级鸿沟,有助于民主平等意识的培育和传播。我们看到,在微博空间里,以娱乐的心态对话甚至挑战政府官员已经不是个案,政治人物与政治事件的娱乐化解读也是常态。对大多数人来说,在微博里去评论政治,与其说是关心政治、热衷政治参与,不如说是满足自己猎奇的心理,然而,不管动机如何,民众敢于利用微博直接与政府官员进行对话,不畏惧权威。在微博里,官员大小和现实权威等级没有直接相关性,微博面前人人平等。当记者、政府官员的权威日益受到大众挑战的时候,新媒体也正在解构传统的权力关系。在中国传统政治文化中,官本位的思想渗透于政治与社会生活,官员拥有较高的社会地位。这种传统政治文化的影响仍然存在于当代中国的大众政治文化心态之中。然而,由于互联网等新媒体的冲击,虚拟的媒介空间逐渐以新的话语方式打破这种政治文化心态。政府及其执政官员的权威在逐渐削弱,神秘而又威严的权力在消费主义、众人狂欢中的网络话语体系中一点一点地消解。科层制的等级结构也在娱乐狂欢、信息轰炸中被蚕食,尽管科层制仍然是当今政府的主要组织形式,但在微博等新媒体面前,政府机构、官员和民众被拉到同一个水平线上。在微博里,我们看到有越来越多的政府机构和官员选择与民众直接沟通和互动,不管深度如何,这已经是对传统科层制等级体系的挑战和冲击。微博政治参与中日益展现的是大众权威的参与力量及其对传统权威的解构。
2.日常生活的政治参与。随着社会的转型、微博的日益娱乐化和泛在化,加之传媒消费主义话语对政治生活的渗透,人们沉淀的政治参与热情在消费主义所关涉的日常生活领域里被日益激活。一个生活化“微笑”引起细腻和敏感的网友的批评,一块块奢侈手表、一座座高价房子引发微博里的舆论监督,源于人们对生活的关注。而各种消费维权、环保、拆迁公共事件在微博里发酵,更是人们对自身生活权益的追求与维护。微博里的参与和普通人的生活紧密相连,诸多民生议题,如教育、卫生、医疗、消费者权益保护等呈现在微博公共空间的讨论中,对弱势群体的慈善救助、地震救援的微博接力、柔弱个体的微博抗争、一次旅游中的不文明行为等等,都是微博热议和参与的公众议题。这就是今天的政治日益呈现微政治化的特点,它与人们的生活紧密结合。正如有学者所指出:“今天的政治已经与曾经很长时间主导人们政治生活的对理念、信仰、制度、权威等价值和相关命题的关切渐行渐远,而更多地表现为对民众日常生活的关注,或仅仅是对民众具体、细小甚至琐碎诉求和问题的回应。”[11]微博政治参与内容不仅同国家政治改革与发展等宏观议题相关,更与中观的公众生活甚至微观的公民细微生活、利益诉求密切相关。正如有研究者评论道:“与刚刚过去的历史相比,当前的政治样态已经发生了根本而剧烈的嬗变,传统一贯的政治概念与丰富生动的政治实践之间出现了‘抽离’脱层,愈难解释新领域、新方向上的趋势动态。……微政治借助信息传播的强劲力量,正以前所未见的速度,在经济结构、家庭关系、生活方式与交往模式、政治认同等诸多结构性要素方面,加速扩散并向深度演进。”[12]随着新媒体日益渗透和介入个人生活,并成为公民维权的有力工具,民众注意力越来越随着新媒体的传播而指向更为微小的公民生活世界,并把个体生活事件放大为公共事件,民众更加关注自身和他人的民生问题与命运。政治与民主的语境越来越与民众的日常生活和切身利益相关,事关每个公民的民生和利益。直接影响日常政治生活的微博媒介,并不是以国家权力为背景自上而下控制的中介,而是没有政治权力背景与后盾的来自草根民众的政治表达和政治参与,是生活的政治、民生的政治。
3.休闲狂欢式的政治参与。微博消费主义精神渗透进政治生活,形成微博空间里狂欢式的政治参与风暴,呈现休闲化与娱乐化的特点。“表哥”、“房姐”、“房叔”们之所以形成舆论风暴,所反映的恰恰就是狂欢的政治。人们在微博里以围观之姿进行广场式狂欢,进行集体窥视、话语狂暴,这与民众消费主义的狂欢心理需求是一致的。微博里对类似政治事件的新闻推送和信息传播也许并不是出于政治的动机,也许并不是想表达一个有责任的媒介机构或者博主的立场,而只是考虑到粉丝对奢侈手表、高房价、二奶和官员纠缠的浓厚兴趣,是受人气、利益驱动而进行的信息传播行为。各种网络意见的表达,政治时事的讨论、批评以及网络政治动员中,严肃、正式的政治话语被各种“体”式网络用语、网络恶搞、网络调侃以及网络幽默所代替,网络娱乐精神、大众娱乐心态渗透于政治叙事。民众在闲暇时刻的微博转发与评论,网络视频、网络图片的转发,一次不经意的微博直播,往往是完成了一次政治参与的过程,大量政治意见的发表、网络围观、网络签名等活动也是在休息娱乐、狂欢的状态中完成的。在新媒体造就的信息无限蔓延和无形外扩中,在新媒体商业和娱乐精神的侵染下,更多民众用轻松而不失关切、娱乐而不失追求、微小而影响巨大的精神,参与对国家政治和各级政府官员的讨论与监督,政治参与呈现出越来越休闲化的特点,政治不再那么严肃和“一本正经”,严肃的政治问题被轻松活泼的网络话语所消解。休闲化娱乐化的政治参与昭示着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向,普通民众娱乐政治,正显示着民众平等的政治地位和言论自由与表达的尺度,具有积极的意义:“在一个社会中,普通公民娱乐政治是一种健康的社会生态,它意味着一个人与他人、国家以及社会在宪法上和政治上形成平等的良性互动关系。”[13]
四、微博消费主义倾向下政治参与的隐忧
微博消费主义在给政治参与带来诸多不自觉的积极影响的同时,也呈现出一些消极因素:对于本来就是政治冷漠者来说,他们可能更加不关心政治,民众的公共精神也很难真正确立;消费主义狂欢下的大众参与也存在民粹主义的隐忧。
1.政治冷漠和公共精神的失落。在网络恶搞和娱乐至上的氛围中,微博的公共讨论和民主参与功能显然不足。人们的注意力总是有限的,在微博选择性推介信息的驱使下,置身于互联网信息的海洋里,微博里大量的公共信息可能被遮蔽。传媒“在遮蔽着社会中大量出现的公共问题的时候,也会使受众注意不到社会中诸多的问题,在把精力转向个人消费、体验享受快感的同时,也就麻醉着自己的神经,不再去思考看来与己无关的事情,对身边的世界变得越多冷漠。这样一来,公共性不可避免要被疏远”[14]。微博虽然激发了一部分群体的参政热情,但在微博文化中庸俗消极因素的影响下,消费主义和娱乐至上的民众更不关心政治、远离政治,人们只关心自己的生活,作为公民应有的责任感、公共精神、公民意识在不断萎缩,政治参与热情下降。达雷尔·M·韦斯特(Darrell M.West)在分析美国公民政府参与下降的媒介原因时指出:媒介更多地报道娱乐内容,让本来不关心政治的人更不去参与政治,媒介市场竞争的激烈让很多媒介越来越强调政治的娱乐价值,更多地强调政治的游戏性,在这种情况下,政治被简单化,记者们采用政治肥皂剧的叙事方式来吸引受众的注意力,好莱坞式的娱乐价值渗透进国家的政治讨论[15]。在消费主义文化的影响下,大众传媒渐渐将一切信息消费化、符号化和商品化,将文化和知识排斥在外,微博这一新型媒体也不例外,海量信息并未带来真正政治知识和优秀文化的增长。“事实可能已经证明,转向娱乐导致媒介的社会、政治和文化功能日益贫乏”[16],这也是一些学者所批判的:本来属于公共领域的、关注着公共事务的传媒,作为社会公器的传媒,越来越沦为商业利益的奴隶,甘愿服务于特定利益群体,诱惑人们的消费欲望,不再追求和关注社会的正义事业;网民受众则变成了消费者,变成了传媒自我消费的麻醉品,日渐丧失对公共性的感知和理性思考能力。
过度的娱乐化也使得公民在进行网络政治参与的时候以娱乐和游戏的心态进行,缺少了应有的严肃、认真和理性。消费至上、娱乐狂热的消费主义文化弥漫互联网空间,消弭了人们的理性和睿智思考。在泛商业化浪潮的冲击下,在激烈的媒介竞争环境下,一些互联网媒体形成以利润为中心的网络发展理念,以网民注意力、点击率为运营主轴,网络媒体缺少了应有的社会责任感和职业操守,新闻缺少深度和力度,变成一种娱乐叙事,以政治人物、政治事件的戏剧性的故事和来自底层民众的故事演绎换取了更多的点击率,但回避了一些严肃性的社会政治话题。“互联网中的政治更多的是在被消费主义者和自由贸易的选择模型所操控,而不再被讨论和思考的民主程序所左右。”[17]政治参与变成娱乐事件,人们只是满足自己猎奇的心理,津津乐道贪官究竟贪了多少钱、有几个情妇,贪官奢侈的生活是什么样子,他有什么后台,乃至对贪官在庭审时的表现评头品足,但更为深入的思考是匮乏的。大众化的微博媒介并不一定走向真正的民主:“随心所欲地谈论政治、不加思考地愤世嫉俗,在此意义上,他们并不具有真正意义上的‘政治的感觉’,他们津津乐道的仅仅是‘感觉的政治’。”[18]
2.民粹主义狂欢的隐忧。微博里的表达和参与,有利于政府相关部门去了解和收集最原始的民意诉求,去积极改进执政工作,有助于监督消极腐败现象,对于政府和执政党的民主执政有着积极的推动作用。微博里形成的舆论,既充满着正义的呐喊、人性的闪光,对弱者的同情,但也充满无知的偏见、非理性的泄愤、情感用事的谩骂、喋喋不休的牢骚、道德至上的傲慢、法治精神的缺失和民粹主义的隐忧。黑格尔曾指出,“公共舆论是人民表达他们意志和意见的无机方式……一切偶然性的意见,它的无知和曲解,以及错误的认识和判断也都出现了。”[19]所以,微博舆论和微博民意并不等于真实的民意,140字的空间让我们无法对事件做出深入思考,即时更新的速度让我们不断转移视野,大众在围观中迷失了自我。李普曼曾这样评价美国的公众舆论:“我们的公众舆论是间歇性地同各种情结发生着联系,同野心、经济利益、个人仇恨、种族偏见、阶级感情等等联系在一起,它们以各种方式歪曲着我们的看法、想法和言谈举止。”[20]在今天的微博狂欢中,政治参与的民粹性也在彰显。大众在微博狂欢中也夹杂着感情、偏见、非理性、个人愤怒等因素,也会歪曲事实真相,误导人们的看法与判断。民粹主义极端强调平民的价值和理想,把平民的主张和言论视为正确的,把平民舆论置于道德与法律的优势地位。在微博舆论监督中,这种民粹主义的狂欢,充分显示了其双刃性。在今天法治进程中,靠舆论来推动法治建设的进步似乎是不少民众的期望,在这一过程中,舆论对反腐败、对司法都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但同时也显示了舆论推动法治进程的边界问题。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发布的《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指出,微博反腐“误伤”情况时有发生。在2012年通过网络举报的24起反腐事件中,其中9起经调查确认为失实[21]。在微博民粹主义那里,人民的形象是高大的,只要是打着人民、人民利益的旗号就能获取同情;在微博群体事件里,只要是弱势方就是正确的。如拆迁案件,被拆户永远是道德高点占据者;城管与小贩的冲突,小贩永远是令人同情的对象,而城管则被各种网络语言妖魔化。这种网络民粹主义与现实空间的民粹思潮并无真正不同,却借助于微博等媒体引发更大的传播效应,容易混淆人们的判断。“民粹主义的危害在于其所暗含的非理性、反叛性集体行动逻辑会不断削弱社会发展的理性与自制机制,情绪化的大众自发地操纵政治议程,使得本来合理的利益诉求很容易变成一种破坏性的、非理性的极端政治宣泄,胁迫政府偏离正确的执政轨道,从而使社会退回到人治状态。”[22]
总之,在消费主义倾向的影响下,微博在政治参与方面呈现出一定的积极意义,对消解过度膨胀的政治权力,凸显大众权威,激发参与热情,实现政治生态的良性转向和推进民主进程都有所助益。然而,应该明确的是,微博的消费主义从根本上说来是商业化的行为,它以利益为根本导向,其积极的政治功能并非主动为之,相反,微博等新媒体也以删帖、禁言等方式进行自我规制,对于开放的公共讨论设置了一定的障碍,用消费主义的商业动机侵蚀着公共话语空间,以娱乐狂欢掀起民粹主义的涟漪。但是不管如何,新媒体与政治从来都不可能互相撇清关系,在未来的发展中,微博等新媒体仍然会在消费主义的浪潮下,以日常生活为切入,影响着公民参与、政治生态与政治发展。对普通民众而言,要对消费主义的诱惑和网络集体狂欢保持警觉,努力提升新媒体素养;对政府而言,对微博等新媒体的依法管理及其政治参与、社会管理功能的开发利用则是重中之重;对微博等新媒体自身而言,对商业利益的追逐应与社会公器的责任担当保持恰当平衡,自觉自律。
[1][法]让·波德里亚.消费社会[M].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1:69.
[2]王宇俊.我国传媒消费主义的文化语境和现实表征[J].创新,2009,(12):80.
[3]张品良.网络文化传播:一种后现代的状况[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7:142.
[4]东方尔.蒙面狂欢[M].北京:中国青年出版社,2007:20,207-248.
[5][英]齐格蒙特·鲍曼.被围困的社会[M].郇建立,译.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5:154.
[6]蚁畅.传媒消费主义与网络“哥”“姐”热现象[J].新闻爱好者,2010,(7):67.
[7]袁峰,等.网络社会的政府与政治[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151.
[8]宇泉锟.消费主义视域下网络恶搞的嬗变[J].东南传播,2013,(5):92.
[9][英]杰伊·G·布拉姆勒,米切尔·古尔维奇.对政治传播研究的再思考[A].[英]詹姆斯·库兰.大众媒介与社会[C].北京:华夏出版社,2006:156.
[10]陈昕.救赎与消费[M].南京:江苏人民出版社,2003:7.
[11]王丽萍.微政治——我们身边的政治文化演变[N].学习时报,2011-09-26(06).
[12]左广兵.“微政治”蔓延挑战中国治理生态[J].人民论坛,2012,(18):54.
[13]童大焕.政治娱乐化的两个基本面[J].领导文萃,2007,(2):107.
[14]贾广惠.论传媒消费主义对公共性的瓦解[A].中国传媒大学第二届全国新闻学与传播学博士生学术研讨会论文集[C].2008,(4):288.
[15]Darrell M West.What Accounts for Declining Political Participation?in Media,Profit and Politics—Competing Priorities in an Open Society[M].Kent&London:The Kent State University Press,2003:70-71.
[16][澳]格雷姆·特纳.普通人与媒介:民众化转向[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1:144.
[17][美]唐·斯莱特.政治话语与需求政治:数码空间美好生活的话语[A].兰斯·本奈特,罗伯特·M·恩特曼.媒介化政治:政治传播新论[C].董关鹏,译.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2011:91.
[18]范昀.论政治感[EB/OL].新浪博客,2013-10-19.
[19][德]黑格尔.法哲学原理[M].北京:商务印书馆,1961:332.
[20][美]沃尔特·李普曼.公众舆论[M].阎克文,江红,译.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2005:56.
[21]上海交通大学新媒体与社会研究中心,舆情网.2012年微博年度报告[R].中国青年报,2013-01-04(03).
[22]陈龙.网络民粹主义潜流的栖居空间——当前网络民粹主义新动向[J].人民论坛,2013,(6):69.
〔责任编辑:常延廷〕
D60
A
1000-8284(2015)01-0084-06
2014-04-14
国家社科基金青年项目“微博政治参与和社会主义民主建设研究”(12CKS015)
赵春丽(1982-),女,安徽太和人,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网络政治学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