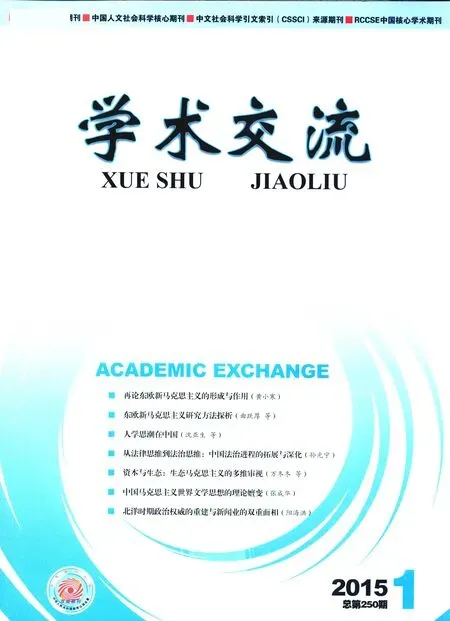五四宪法的民主政治渊源
2015-02-25薛剑符
薛剑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28)
政治理论研究
五四宪法的民主政治渊源
薛剑符
(中国社会科学院政治学所博士后流动站,北京 100028)
五四宪法是近百年来国人民主政治追求的理论升华。近代的君主立宪运动和民主共和实践完成了中国民主政治启蒙,给中国留下了关于宪法和法治的最初印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中国革命为五四宪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五四宪法铭记着国人为救亡、强国、民主和自由而前赴后继、浴血抗争的历史,夯实了社会主义民主和法治的根基。
五四宪法;君主立宪;民主共和;新民主主义革命
在中国,现代宪法的出现是与近代中国的救亡图存联系在一起的。鸦片战争以来,宪法一直承载着中国人强国富民的殷切希望,在封建与民主、专制与法治的博弈中,在一次又一次民主浪潮的涤荡下逐渐从虚幻走向真实。从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到资产阶级革命派的民主共和,再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中国的先进分子一路坎坷的民主政治追求终于在新中国成立后凝结成五四宪法。五四宪法肯定了中国共产党对中国革命和建设事业的领导,其所确立的人民民主和社会主义原则为改革开放后的八二宪法所继承和发展。在法治中国建设的进程中,回顾五四宪法的历史承载及其对社会主义法治开端的基础性贡献具有重要的理论价值和现实意义。
一、资产阶级改良派君主立宪的启蒙
近代中国关于法治与民主的思想启蒙是从清王朝走向没落开始的。西方列强崛起与晚清日渐贫弱的强烈对比迫使国人开始探寻西方富强的根本原因,其结果是发现了双方在政治法律方面存在的巨大差异,于是取法西方,维新变政以强国富民成为一些有识之士的梦想。甲午海战的惨败加剧了近代中国亡国灭种的危机,变法维新思潮开始从理论层面逐步演化为政治改良的实际行动,并在朝野之间产生了越来越大的影响。
早期改良派是在追随洋务派、服务于洋务运动的过程中了解到西方的议院制和君主立宪等政治制度的,最初他们是想通过效仿西方政治体制来促进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中法战争的不败而败使早期改良派清楚地认识到国家的强盛取决于政治法律制度的优劣,民族工商业的发展不足以挽回晚清的颓势,欲救亡图存则改政变制势在必行。改良派的先行者王韬指出:“君为主,则必尧、舜之君在上,而后可久安长治;民为主,则法制多纷更,心志难专一;穷其极,不无流弊。惟君民共治,上下相通,民隐得以上述,君惠亦得以下逮。”[1]这样的论证清晰地说明了君民共治的优越性。薛福成、郑观应持相同的观点,并做了类似的论证:“君民共主,无君主、民主偏重之弊,最为斟酌得中。”[2]“君主者权偏于上,民主者权偏于下,君民共主者权得其平。”[3]316通过对民主制、君主制和君民共主制等三种政治体制的认真比较,君民共主被认为是解决晚清政治问题的唯一方案。然而如何来实现君民共主呢?为此,陈炽和郑观应把西方议院制引进了人们的视野。陈炽认为设立议院,是“英美各邦所以强兵富国,纵横四海之根源也。”[4]245强调设议院“即可以民情不顺力拒坚持,合亿万人为一心,莫善于此。”[5]108在郑观应看来,议院是公议政事之处,议院制度有着显著的优势:“集众思,广众益,用人行政一秉至公,法诚良、意诚美矣。”[3]311在羡慕西方议院议事立法的同时,他们开始思考议院制在中国的实践前景。然而,建“议院之法”,实行君主立宪,在当时还没有成为广泛共识,这些思想深处的呐喊并未引起清王朝的重视,自然也无法真正付诸实践。至于议院如何具体组织和运行,宪法如何产生和运作,宪法的结构内容和精神实质是什么,这样的细节问题,早期改良者们还未做详细的考证。尽管如此,推崇君主立宪,提议开设议院等主张,已经表明早期改良派以逐渐清晰的改良主义政治倾向与崇尚“实业兴国”的洋务派区别开来,成为资产阶级改良派的思想先驱。
1895年,在《马关条约》的强烈刺激下,资产阶级维新派以康有为和梁启超为代表,开始大力宣传维新变法,积极推动实行君主立宪制。期间,康有为先后七次上书光绪皇帝,力陈君主立宪、变法图强。在维新派看来,制度设计与立宪是变法维新的首要措施。康有为分析指出:“中国败弱之由,百弊丛积,皆由体制尊隔之故”[5]219,认为君主专制,君权太专,下情不能上达,君民不能合为一体,这些政治体制之弊是中国贫弱的根源,中国的内忧外患,其根本原因都在于此。他把制定宪法视为维新改革的总纲领,强调:“变政全在定典章宪法,日本如此而成效大著,中国今欲大改法度,可采而用之。”他谏言光绪:“上师尧舜三代,外强国,立行宪法,大开国会,以庶政与国民共之,行三权鼎立之制,则中国之治强,可计日待也。”[5]337强调只有弃专制政体改行君主立宪,设议院开国会、制宪法、实行三权分立,才能实现国家富强。梁启超也说:“先生以为欲新中国,必以立宪法、改官制、定权限为第一要义。”[6]1898年6月11日,光绪帝终于接受维新派建议,于是就有了“戊戌变法”。维新变法的百日之内,国人获得了一定程度的言论、集会、出版、结社的自由,康梁大力鼓吹的“维新”“变法”产生了实际的社会影响。需要指出的是,维新变法仍然是在维护封建帝制的前提下,谋求现行政治体制的局部性改变,无法犁动封建专制的千年冻土,因而失败有其必然性。然而,维新运动的民主政治启蒙作用又是勿庸置疑的,它深刻地告诉人们“祖宗之法”亦可变,从而为近代中国民主与法治思想的发展奠定了初步基础。
1904年日俄战争的结果使专制与立宪之优劣更见分明,清政府进一步意识到政治法律制度改革的重要性。1905年受命出访美国、英国、日本等国家的载泽等五大臣,在考察了这些国家政治体制和法律制度之后,深刻认识到了通过立宪改革政治体制的重要性,归国即力陈立宪以固皇位、弭内乱、御外患。基于此,清政府先后于1908年、1911年制定了《钦定宪法大纲》和《十九信条》,寄希望于以些许的民主姿态来挽回颓势。风雨飘摇的晚清王朝竟然也制定了久违的宪法,且在宪法中除确认皇权外还规定了臣民权利,这无异于在专治之树上开出了民主之花。这两个宪法性文本拉开了颠覆中国封建法统的序幕,开启了近代中国迈向民主的艰难一步,而且《十九信条》清楚地规定“皇帝之权,以宪法所规定者为限”;“皇室经费之制定及培养,由国会决议”;“皇室大典不得与宪法相抵触”[7]359-360。中国帝制千年,皇权第一次受制于宪法!曾经傲视寰宇的大清帝国也不得不将宪法视为救命的稻草,这是宪法博弈专制的胜利,至少在观念上让国人产生了“宪法”还能够制约皇帝这样的兴奋抑或是置疑,宪法的作用由此彰显,关于其基本原则的思考在中国发端,中国人对宪法的认识空前地加深了。
二、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共和的鉴戒
在中国,民主共和这样的政治理念,是资产阶级革命派用鲜血和生命树立起来的。孙中山用他的三民主义理论和五权宪法思想诠释了资产阶级革命派对宪法的理解,一次次起义直至辛亥革命则是资产阶级革命派民主政治追求的实践表达。
孙中山在组织发起反清运动之初,就已将建立民主共和国作为明确的革命目标,即革命不仅仅是推翻清王朝,而且是要彻底铲除因循已久的封建帝制。从1894年创立兴中会的誓词“创立合众政府”到1905年提出“建立民国”的同盟会纲领,孙中山关于民主共和国的革命目标日渐清晰,民主共和观念深入人心。“三民主义”则是孙中山为建立民国而提出的革命纲领和理论体系,包含了国家独立、主权在民、平均地权和资本等内容。“三民主义”的核心是民权主义,即主张通过对封建专制主义的揭露和批判,经过“国民革命”的途径推翻封建帝制,建立“民主立宪”的共和制度。民权思想又直接派生出了权能分治理论。“政权在民”,或曰“民权”,分为选举权、罢免权、创制权、复决权四项,民权的真正实现即为“全民政治”;“治权在政府”,或曰“治权”,分为司法权、立法权、行政权、考试权和监察权,以此为基础设立相互独立运行的五院制“万能政府”;以“全民政治”来监督“万能政府”。在对民主共和的目标、理论基础、权力结构、制度安排做了一系列阐述之后,孙中山将民主共和的理想和实践最终寄托在宪法上,“今者由平民革命以建国民政府,凡为国民皆平等而有参政权,大总统由国民共举,议会以国民公举之议员构成之,制定中华民国宪法,人人共守,敢有帝制自为者,天下共击之。”[8]预期中的“中华民国宪法”被孙中山视为永久结束帝制,确立民国国体和政体,平等赋权给人民的重要依据。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最进步的救国方案,是“民主共和”最富时代意义的理论表述。直接民权、权能分治、五权分立是孙中山构建的五权宪法思想的集中体现。孙中山完整地规划了民国政治的“三阶段论”,其最终政治目标“是建立民主立宪的政体”[9],施行以宪法为基础的民主政治。
1911年10月,在一系列武装起义失败之后,武昌起义爆发,民主共和摧毁了封建帝制。1912年1月l日,孙中山在南京组织临时政府。为巩固革命党人用生命换来的革命成果——民主共和,临时政府的一个重要举措就是制定《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临时约法》是中国民主立宪的开端,它以根本法的姿态宣布封建皇权的终结,“人民”及其权利在宪法语境下正式出场,中国的政治体制由此而发生了根本性的变革:第一,《临时约法》以根本大法的形式确认了“主权在民”的原则。“中华民国之主权属于国民全体。”[7]366人民主权观念在《临时约法》中得到了正式体现,肯定了国家的一切权力来自人民,人民在国家政治生活中的地位历史性地获得了宪法的保障,这对于二千年封建皇权统治下的中国来说意义尤为重大。第二,《临时约法》将“人民”放在显要的位置,并以专章的规模凸显了人民权利的重要性。《临时约法》在第二章通过11个条文,详细规定了人民的权利和义务:明确了人民一律平等这一首要的原则;强调人民所应该享有的人身自由、家宅保护,以及保有财产、营业自由和集会结社、言论著作、书信秘密、居住迁徙、信教等各项自由权;明确规定人民有获得救济的相关权利,有选举及被选举权利,尤其是规定了考试权。《临时约法》关于人民权利义务的一系列规定,在中国近代以来宪法发展中的开创性意义是值得肯定的。这是旧民主主义革命时期资产阶级宪法的进步性体现。第三,《临时约法》以三权分立为原则确定国家机构的组成,构建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的政治框架。《临时约法》分专章规定了“参议院”“临时大总统副总统”“国务员”“法院”的产生、职权、运行机制及其相互关系,它用临时宪法的形式肯定了反抗封建专制的革命精神、民主精神,它的颁布标志着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制度的确立。
革除帝制,主权在民,权能分治,五权分立,以及民权、民主、自由、平等,这些激励资产阶级革命派浴血奋战的宪法理念融汇成《临时约法》,革命党人更直接的目标是寄希望于通过宪法性文件来限制袁世凯的专权。然而,袁世凯还是以军阀独裁复辟了帝制。孙中山精心缔造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在此时显现出了无法回避的局限性。孙中山的民主共和理论缺乏阶级分析方法,忽略了社会阶级力量对比和社会阶级矛盾是国家政治的基本问题,一厢情愿地将“人民”或“国民”视为整体;在权力结构设置上,“治权”一分为五,没有考虑相互之间的制衡和可能出现的扯皮推诿,为起协调作用的总统预留了可以发挥作用的空间。找不到自己的阶级基础和力量源泉的资产阶级民主共和注定了要接受失败的结局。尽管宪法与专制是无法相容的,但鉴于宪法的威力,此后的各种政治势力也都试图以立宪自证其合法性,《天坛宪草》流产后,《袁记约法》、《贿选宪法》和《中华民国宪法草案》相继出台,中国近代史上接连演绎了一幕幕假民主、真专制的立宪闹剧。可见,民主和法治观念的传播还是使军阀专政有了种种顾忌,宪法的威力、宪法于国于民的重要意义成为孙中山通过民主共和留给民国的最宝贵政治遗产。民主共和理论及其实践给中国共产党提供了深刻的鉴戒,即中国革命必须由中国社会的新生力量——无产阶级来领导,人民当家作主和革命法治是通向新中国的坦途。
三、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直接推动
在经历了君主立宪和民主共和的失败之后,中国依旧是“风雨如磐”。五四运动开始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思想启蒙,“民主不再是狭隘的资产阶级民主,而是指多数人的民主,劳动阶级为主体的民主。”[10]民主由此而被赋予了更深刻的内容,涵盖了主权独立、国家统一、反抗独裁、人民民主等基本要求,新民主主义革命从此而发端。
1.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最终目标是实现人民民主。近代中国,国家需要主权独立以抵御外侮,人民需要民主以反抗专制,在这样的一个历史主题面前革命是唯一途径,人民民主是最终目标。通过革命以实现民主是历史赋予中国共产党的政治使命。自1921年起,在建党后的一年时间里中国共产党就清楚地把握了革命形势,在中共二大上提出了党的最低纲领和最高纲领,主张建立“真正民主共和国”,赋予人民无限制的选举权、言论、出版、集会、结社和罢工自由,特别规定了女子的平等权。在争取人民民主的革命实践中,中国共产党深刻地认识到革命领导权和工农联盟的重要性,找到了适合中国国情的革命道路,采取了相应的政权组织形式和具体的战略策略措施。新民主主义革命的种种诉求,核心目标始终是赋予并捍卫人民真实而平等的民主权利,始终在强调“拥护工人农民的自身利益是我们不能一刻忽忘的”[11]。这清楚地表明,中国共产党所要保障的是劳动人民的权利,所追求的是贫苦农民和无产者等大多数劳苦大众的民主,即相对于封建地主和军阀割据势力的人民民主。人民民主——这一中国宪法的核心理念在中国共产党成立之初就已经确立了。
在人民民主目标的推动下,中国共产党广泛发动工农群众投入实际的革命斗争,参与国民革命并取得了北伐战争的胜利,开展土地革命挽救了大革命失败之后被蒋介石扼杀革命的危局。八年抗战,中国共产党和全国人民一同浴血奋战赢得了抗日战争的伟大胜利,三年的人民解放战争宣告了国民党集团的彻底失败,也标志着反帝反封建反官僚主义的中国革命的最终胜利。中国共产党人带领全国人民以巨大的牺牲换来了国家的独立、民族的解放,实现了人民民主。当家作主的中国人民首先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共同纲领》来记录这一伟大胜利,并在1954年新中国的第一部宪法中重申了中国革命历程,确立了人民民主这一重要的宪法原则。
2.革命法制实践为新中国制宪积累了经验。中国共产党在领导人民开展武装斗争的同时也十分重视法制建设,注重通过法制建设保障人民民主权利,指引和推进新民主主义革命的进程,从而为新中国制宪和法治建设的开展积累了丰富的实践经验。
1931年11月,《中华苏维埃共和国宪法大纲》的颁布是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的一个里程碑。作为中华苏维埃第一次代表大会正式颁布实施的第一个宪法性文件,《宪法大纲》对土地革命实践作了如下的宪法表达:第一,对革命政权的性质、任务、目的等作了清晰的规定。《宪法大纲》提出:“中国苏维埃政权所建立的是工人和农民的民主专政的国家。苏维埃政权是属于工人农民红军战士及一切劳苦民众的”;“中华苏维埃共和国之最高政权为全国工农兵会议(苏维埃)的大会。”[7]89-90第二,赋予苏维埃领域内人民广泛的权利。《宪法大纲》规定:根据地人民在法律面前平等;选举权和被选举权被平等地赋予十六岁以上公民;“制定劳动法,创立社会保险制度与国家的失业津贴”;“保证工农劳苦民众有言论出版集会结社的自由”[7]90-92。以政权的形式制宪来保证人民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民主权利,极大地鼓舞了根据地人民的革命斗志,也让国统区劳苦大众看到了希望。此外,《宪法大纲》也明确规定了“没收地主土地给农民”“土地国有”“限制资本主义”“取缔帝国主义一切特权”,以此来促进经济发展,调整和规范社会生活。《宪法大纲》是中国人民自己制定宪法的首次尝试,为根据地的民主政治建设提供了根本法的支撑,也为以后的人民制宪提供了极其宝贵的历史经验。
在全民抗战的推动下,各革命根据地一系列宪法性文件纷纷出台,比较有影响的有1939年的《陕甘宁边区抗战时期施政纲领》、1940年的《晋察冀边区目前施政纲领》、1941年的《晋冀鲁豫边区政府施政纲领》、1942年的《淮南苏皖边区施政纲领》、1943年的《山东战时施政纲领》等,这些宪法性文本一致规定了抗日军民普遍、平等地享有广泛的民主权利,保护抗日民众的人权、财产权利、政治权利,以及言论出版等表现权和居住与迁徙自由等其他权利。规定实行普遍、平等、直接、无记名投票选举制度,以及改进司法制度、厉行廉洁政治、减租减息以及有关婚姻家庭、民族、外交、侨务等各方面政策。不少根据地还进一步制定了有关保障人权、财产权的单行条例,如《冀鲁豫保障人民权利暂行条例》《晋西北保障人权条例》等。解放战争时期,《陕甘宁边区宪法原则》《东北各省市民主政府共同施政纲领》《内蒙古自治政府施政纲领》等,连同中国共产党和人民解放军发布的文告、宣言一起起到了规范各解放区人民民主政权建设的重要作用,促进了全国人民争取和平、追求民主的斗争。
总体看来,革命根据地法制建设中出台的这些宪法性文件具有以下共同特征:首先,规范了各级人民民主政权建设。这些宪法性文件都涉及了政权性质、组成形式、组织原则的规定,以及根据地基本政治制度框架、当前形势和具体任务,对各根据地政权建设的具体细节问题分别作了相关的规定。与此同时,往往以政策的形式对各根据地和解放区的社会经济生活进行调整。其次,以人民权利自由为核心,确认了人民应有的民主权利,构建起了革命民众基本民主权利体系,普遍强调政府对于人民权利实现所负有的责任。这种赋权并强调政权负有保障权利实现职能的积极权利模式对后来的《共同纲领》,尤其是对五四宪法产生了很大的影响。再次,这些宪法性文件在肯定革命成果、规划革命进程的同时,也充分表达了共产党人的法治诉求。在根据地法制建设中,中国共产党的领导是鲜明而普遍的特色,由此也强化了党在根据地法制建设中的作用。党的领导与人民当家作主一起成为中国革命法制建设的传统,深刻地影响着新中国制宪实践,为五四宪法乃至现行宪法所继承。
3.新型人民民主国家的构建奠定了五四宪法的政治基础。中国革命的胜利离不开时时以实现人民民主为己任的中国共产党。人民民主凝聚了来自人民的强大力量。在中国共产党的带领下,人民赢得了国民革命、土地革命、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的伟大胜利。
在革命战争进行的同时,中共产党人一直进行着人民民主国家的构建。从工农民主共和国到人民共和国,再到“三三制”抗日民主政权实践,中国共产党关于国家建设的脉络日渐清晰。“国体——各革命阶级联合专政。政体——民主集中制。”[12]677毛泽东早在1940年就提出了新民主主义革命的政治纲领,设计并论证了抗日战争胜利后中国的政治格局。在后续的演讲中毛泽东强调了这个政权的阶级构成、使命和特点:实行“几个革命阶级联合起来对于汉奸反动派的民主专政。”[12]733在1945年的中共七大报告中,毛泽东明确了建立民主联合政府的主张:无产阶级掌握领导权,“建立一个以全国绝对大多数人民为基础而在工人阶级领导之下的统一战线的民主联盟的国家制度”[13],采取民主集中制原则;在全国范围内保证人民平等地享有广泛而真实的权利和自由。联合政府的政治方案是对各民主党派团结抗日、共同革命事实的尊重,是在把握中国革命规律的基础上对共产党人民主政治追求的理论总结。
建国前夕,毛泽东在一系列论著中明确阐述了新中国的国体和政体,即以“工人阶级(经过共产党)领导的以工农联盟为基础的人民民主专政”[14]为国体,而政体则“采用民主集中制,而不采用资产阶级议会制。……我们提出开人民代表大会”[15]。至此,新中国的基本政治框架更加清晰。1949年10月1日,开国大典正式宣告了新中国的诞生,人民民主专政经过理论构建和实践检验,以临时宪法的形式被确立为新中国的国家制度,人民当家作主从此有了坚实的政治基础。建国后的三年时间里,新中国在国民经济恢复的同时,人民政权建设更加巩固,民众的组织程度和觉悟程度也有了显著提高,在这样的历史背景下,以《共同纲领》为基础,五四宪法经过科学审慎的人民制宪程序而正式诞生,新中国开启了自己的宪法时代。
近代以来不间断的改良与革命缔造了中国特殊的宪法发展进路,中国先进分子的民主政治理想与追求为五四宪法的形成提供了丰富的实践经验。资产阶级改良派的君主立宪运动开始了中国的民主政治启蒙,那时宪法是人们“师夷之长技以制夷”和救亡图存的工具;资产阶级革命派使封建帝制完败于民主共和,民主和法治观念深入人心,那时宪法是人们摆脱封建主义的奴役,获得自由、平等和人权的保障。中国共产党领导的新民主主义革命则饱含了人们对主权独立、民族解放和人民当家作主的强烈渴望。五四宪法从中国近现代历史走来,在中国宪法发展的进程中,它是具有承上启下作用的里程碑。五四宪法承载和回应了近百年来国人关于国家强盛和民主自由的各种诉求,它以人民当家作主和社会主义为基本原则,确认了中国共产党的领导,确立了新中国的政治制度框架,五四宪法实施给新中国法治建设留下了可资借鉴的经验教训,昭示了依法治国的重要性①参见薛剑符.五四宪法与中国民主政治模式的构建[J].东北师大学报:哲学社会科学版,2010,(3):13-17.。
[1]王韬.弢园文录外编[M].北京:中华书局,1959:23.
[2]丁凤麟,王欣之.薛福成选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7:606.
[3]夏东元.郑观应集(上册)[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
[4]陈炽.陈炽集[M].北京:中华书局,1997.
[5]汤志钧.康有为政论集(上册)[M].北京:中华书局,1981.
[6]张晋藩.鉴古明今,遵宪守法[J].中国政法大学学报,1983,(3):20.
[7]陈荷夫.中国宪法类编[M].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0.
[8]孙中山选集(上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56:69.
[9]孙中山全集(第一卷)[M].北京:中华书局,1981:325.
[10]胡绳.中国共产党的七十年[M].北京:中共党史出版社,1991.
[11]中共中央党校党史教研室资料组.中国共产党历次重要会议集[M].上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2:27.
[12]毛泽东选集(第二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
[13]毛泽东选集(第三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056.
[14]毛泽东选集(第四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1:1480.
[15]毛泽东文集(第五卷)[M].北京:人民出版社,1996:135-136.
〔责任编辑:常延廷 巨慧慧〕
D62
A
1000-8284(2015)01-0079-05
2014-10-31
黑龙江省社科基金项目“五四宪法与中国民主政治演进研究”(10C010);黑龙江省教育厅人文社科项目“法治民主的理论生成与实践路径研究”(12532418)
薛剑符(1973-),男,黑龙江讷河人,博士后研究人员,副教授,法学博士,从事法治与政治发展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