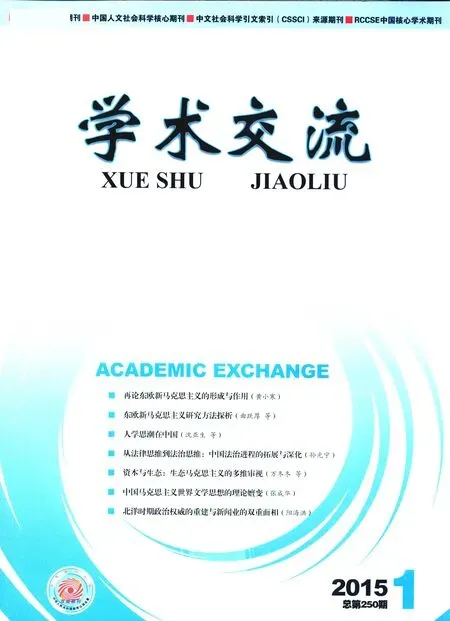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动因
2015-02-25苏淑民
苏淑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北京 100024)
政治理论研究
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蓬勃发展的动因
苏淑民
(北京第二外国语学院法政学院,北京 100024)
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世界舞台上民间外交蓬勃发展。全球化、信息化发展为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非国家行为体数量增多并且功能强化,是民间外交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网络形成,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空间;“全球治理”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信息公开化和便利的交流手段为非官方组织或个人参与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持。民间社会不仅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还是民间外交的力量源泉,在参与全球治理、保护弱势群体、抑制世界强权、治理“民主赤字”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现代外交的公开化、民主化趋势为民间外交大发展提供了前提条件。
民间外交;全球化;信息化;民间社会;外交民主化
民间外交是中国特色的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的重要组成部分,在增进中国人民与各国人民的友谊、创造我国发展所需的良好国际环境、推动国家间关系的健康发展等方面做了大量的卓有成效的工作,发挥了不可替代的重要作用。随着中国综合国力和国际影响力的不断提升,中国与世界的联系日益紧密,中国外交呈现出内外结合、官民并举、多方互动的立体化格局。在这种背景下,民间外交工作更加活跃,在服务国家总体外交、国家建设、祖国和平统一大业和促进世界和平等方面发挥了更大更重要的建设性作用。
当今世界,随着全球化趋势日益加强,国际社会行为体日益多元化,民间外交在世界范围内也得到了蓬勃发展。普通民众或公民团体纷纷涉足外交领域,他们在环保、安全、人道主义援助、经济和社会发展等各个领域,或致力于影响官方和政府间国际组织的外交决策,或致力于推动特定议题协商,使民间外交成为处理国家间关系的重要渠道,起到了政府间双边和多边外交无法替代的作用。跨国民间外交力量已作为一股强大的社会政治力量登上了世界政治舞台。
一、全球化与信息化发展为民间外交的蓬勃发展奠定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全球化与信息化相互渗透、相互促进,两者汇合成为21世纪世界经济社会发展的主流和方向。它们以强大的力量推进世界经济的大发展,改变人类的生产方式和生活方式,也重塑了当代世界政治的基本组织、规则和制度。全球化、信息化使得一定地域范围内人际交往所需的时间和距离伴随着交通与通讯技术的进步而缩短,真正实现了物质、信息、人员基本上共时性的全球流动。美国学者戴维·哈维将这一现象称为“时空压缩”(compression of time and space)[1]。在“时空压缩”的世界政治舞台上,民众参与外交事务的能力大大提升,民间外交的开展获得了坚实的物质基础。
1.非国家行为体的数量增多和功能强化,是民间外交主体发挥更大作用的前提
全球化的迅猛发展对民族国家提出了严峻挑战,国家的权力范围、权力形式、权力强度乃至权力的制度基础和观念都受到影响甚至削弱。赫尔德认为,在全球化进程中,国际关系中的独立能动者在制度层面上形成了模式化的或者有规则的活动交往网络[2]。除了国家之外,包括国际组织、跨国公司等一系列非国家行为体都是跨国网络政治中的成员。“这些非国家组织从不同角度和层面上或者分享着过去由国家控制的权力,或者创造着新的权力空间。”[3]242国家在法理上的完整性和独立性已很难在全球化的世界政治中发挥出来,它在国内政治舞台上越来越难于维护其绝对的权威性,在国际舞台上越来越难以保障主权的独立性。全球化时代的主权“不再是一种有明确领土界限的藩篱,而是一种在复杂的跨国网络政治中讨价还价的机制”[4]。
非国家行为体的多元与丰富,使国家权威出现了从中央政府向上、向下、向侧面分散的趋势:向上即向超国家层面、向下即向次国家层面、向侧面即向公共和私人的网络分散,而且这种分散比一切权力都被控制在中央政府手中更加有效。非国家行为体与国家行为体并存和互动,使国际社会的空间结构从一元的、等级的结构向多元的、网状的结构演变,这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广阔的空间。全球化使非国家行为体的功能日益多样化,包括:促进国家间联系与合作;协调国家间矛盾和冲突;制定规则;抵制个别国家的单方面行动(如绿色和平组织),向个别国家施加军事制裁、经济或道义压力,限制单个国家间的自私行为;为一些国家提供资金技术援助以及提供政策建议;宣传某种价值观念;影响个别国家的经济政策和经济布局(如跨国公司)等等[3]158。
2.复合相互依赖关系网络的形成,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更大的空间
在否定国际关系现实主义理论的基本假定基础上,美国学者罗伯特·基欧汉和约瑟夫·奈认为人类社会已进入“复合相互依赖的社会”。它的主要特征有三个:一是世界纷繁复杂,除了国家关系外,大量次国家和非国家行为体也直接参与世界政治,并日益发挥着重要作用,各种国际社会的行为体之间有着错综复杂的联系;二是外交与内政之间界限模糊,各种国际问题之间无明确等级之分,军事安全并不始终居于议事日程的首位;三是军事力量不再起决定性作用,武力并非有效的政策工具[5]。这也就是说,人类社会已连接成一个利害高度相关的有机整体。复合相互依赖关系体现在全部国际关系中,不仅在地区和全球范围内,而且在国际社会的各个行为体之间以及政治、经济、文化等社会发展的各个领域都有所体现。“蝴蝶效应”在世界各地进一步放大,而且国际事务中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国家力不从心或无能为力的领域,国界的“漏洞”越来越大,某些控制措施的实施变得越来越艰难[6],这为非国家行为体留下了争夺与填补的国际政治空间。
3.“全球治理”需要非国家行为体的积极参与,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创造了条件
全球化催生了全球问题的出现。20世纪60年代以来,环境污染、核威胁、恐怖主义等负面效应随着现代科技的发展逐渐显现,引发人们越来越多的关注。1972年,国际性民间团体罗马俱乐部发表了预言,即经济增长不可能无限地持续下去的研究报告《增长的极限》,使全球问题获得了世界性的关注。此后,全球问题的种类逐渐增多,涵盖了难民、粮食、人口、失业、债务、毒品、艾滋病、核扩散、南北关系、恐怖主义、国际人权等方方面面,既有科技文明的负面影响也有现代文明的消极后果。这些问题在全球范围的扩散和蔓延对人类的生存和发展造成了严重威胁,“全球治理”应运而生。
“全球治理”是一种涉及范围广泛的跨国治理形式,目的是解决全球性问题,弥补市场失灵和国家失效造成的世界秩序失范。美国学者詹姆斯·罗西瑙(James N.Rosenau)是全球治理理论的主要创始人之一,他认为治理不同于统治,治理以共同目标为支撑,无须依靠国家的强制力量来实现,这些管理活动的主体也未必是政府。除了国家和政府外,至少有十个与全球治理相关的术语已经得到人们的认可,即“非政府组织、非国家行为体、无主权行为体、议题网络(issue network)、政策协调网(policy network)、社会运动、全球民间社会、跨国联盟、跨国游说团体和知识共同体(epistemic community)”[7]。2000年联合国秘书长安南在千年报告中也谈到,改善治理就是要以非正式的政策网络来补充正式的体制机构,就意味着非国家行为体更多地参与,让民间社会和私营部门组织与国家政府、国际机构齐心协力追求共同的目标[8]。可见,全球治理的需要为民间外交活动的开展提供了更多的机会。
4.信息公开化和便利的交流手段为非官方组织或个人参与外交提供了技术支持
首先,网络民间外交的兴起具有技术上的必然性。随着数字化信息传播和网络技术的迅猛发展并走向大众化,网络这一新兴媒介迅速崛起并开始引起愈来愈多的关注。技术的兴起改变了社会形态。电脑网络创造了一个特殊的、虚拟的空间,即“网络空间”。借助于网络空间建立的社会就是“网络社会”。网络社会基本不受某一集中权力机构管制,能够自主运行,较少受到条条框框的约束[9]。因为网络传播具有廉价、实时、共享和高度扩张的特点,所以减少了信息传递的级层,提高了社会运行的透明度,并且能够动员广大网民掀起网络社会运动,其范围可以波及整个主权国家乃至全球。在这样的背景下,“网络外交”悄然兴起。而网络民间外交,即由国民个人和民间机构在网上进行的具有非官方外交性质和政治效用的对外交往活动,也必然会蓬勃发展。
其次,信息社会逐渐消解了现代民族国家造成的国内领域和对外领域的严格界限,也逐步瓦解了国家-社会-个人之间的壁垒,使得彼此的边界日益模糊。现代民族国家对内和对外事务的内容存在很大区别:对外事务基本上都是外交、军事和安全等“高级政治”事务,对内事务则主要是经济、文化和社会管理等“低级政治”事务,两者之间壁垒分明。然而,随着全球化的发展和国际网络空间的形成,国内事务跃出边界,成为对外事务的重要组成部分,此种状态从根本上决定着外交成为牵一发而动全身的事务,社会领域中的动向日益敏感地传递到外交事务之中。对于一些“低级政治”事务,政府必然要同那些非政府组织(包括私营跨国公司等私有部门)打交道,而且交往所依据的规则就不能完全按照政治和权力的逻辑进行,而是将市场机制引入到政治领域,通过平等的讨价还价和协商谈判来进行[10]。
最后,知识就是权力。信息革命使国际社会的权力结构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革,信息的可获得性掀起了政治平民化、国际关系民主化和外交公众化的浪潮。伴随着Web 2.0时代的到来,传播模式发生了改变,原来被动接受信息的网络用户逐步转化为信息制造者、传播者,用户的交流模式也从单纯的“读”向“写”及“共同建设”方向发展。网络用户不但常常为外交事务的议程设置提供思路,还往往会作出颇具批判意识的独立判断,主动参与到外交事务中来。
二、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为民间外交奠定了社会基础
全球化产生了以下重要的政治现象:全球意识的提升;市场力量的扩张;个人行为能力的增强;政治行为体的生长;国家权威的衰落等[11]。这些新现象的产生,极大地影响了传统民族国家框架下的国家与社会关系,其中引人注目的是民间社会力量的不断扩大。
民间社会指的是官方政治领域和市场经济领域之外的民间公共领域,由各种公民组织组成,这些组织介于政府与企业之间,又被称为“第三部门”(the third sector),包括社区组织、公民的志愿性社团、协会、非政府组织(NGO)、公民和利益团体自发组织起来的运动等。也就是说,民间社会是由民间的力量、媒体的力量、各种不同的职业团体的力量、宗教的力量、各种不同的草根性组织和民间社会运动等多种社会力量聚合而成的,它不由中央政府控制,却是能对政府形成压力又相对独立于政府的社会力量。
民间社会不仅为民间外交发挥作用提供了机会和舞台,还是民间外交的力量源泉。民间外交之所以发展强劲,就是因为它扎根于民间社会,代表了民间社会各种主体的利益。在国内层面,随着民间社会的进一步发展,民间力量的进一步壮大,非官方力量在国家的外交决策中发挥着越来越重要的作用。
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在参与全球治理、保护弱势群体、抑制世界强权等方面都发挥着积极作用。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兴起和成长,整合起游离于国家权力之外的众多行为体,强化了当代国际关系行为体的多元化趋势。20世纪90年代以来蓬勃发展的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已成为了国际舞台上无法忽视的力量之一。从现实来看,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生长扩大了非国家行为体的阵容,使国际体系的互动关系呈现出网络化和低政治化的态势,使得国际社会中国际制度和国际规范的不足得到一定程度的弥补,国际体系的制度化程度得到增强。
全球民间社会力量的发展使外交呈现出以人为本、以社会为基的走向,为民间外交发展奠定了社会基础。由于在制定政策、推进全球治理方面所做出的贡献,民间社会组织越来越受到各国政府和联合国的重视,它们采取措施扩大与民间人士及其组织进行磋商和合作的范围,为其提供更大的国际空间,吸收其作为伙伴,并帮助其完成政策的制定和实施。中国学者郭树勇指出:“在全球化与信息化的时代,民族国家内部的群众政治抗争或自发性民间外交所形成的直接或间接政治外交影响,与国际民间社会的发育发展有着耦合性与同步性,并以某种特殊的形式推动了全球社会与世界政治文明的进步。”[12]
三、民间外交顺应了现代外交民主化、公开化发展趋势与潮流
自威斯特伐利亚体系建立以来,现代外交就具有强烈的精英外交倾向,外交事务高度敏感,广大民众很少有机会介入到外交领域。然而,从19世纪中后期开始,外交民主化逐渐成为当今外交发展的方向,民族主义、民主主义和信息技术革命是这一进程中的主要推动力量[13]25。外交公开化原则在1899年和1907年召开的两次海牙国际和平会议上得到确认,并在后来成立的国际联盟和联合国中体现出来。日益增多的涉足原本神秘的外交事务领域的非国家行为体推动着外交民主化进程的发展。英国著名外交学家哈罗德·尼克松在20世纪中叶就指出,“尽管增加了复杂性,当今外交正逐渐要求‘开放’和公开解释,从老式外交的国际精英的小圈子向‘民主’‘公开’趋势转变”[14]。中国学者唐贤兴指出,“人在本能上是民主的。因此,所有的政治体系最终都必将走向民主化。也就是说,民主化必然要求把那些以往被排斥在外的社会成员纳入到政治生活中来,建立一个包容性的制度框架,实现世界主义民主的目标”[15]。人类社会的民主化发展,必然引起现代外交不可阻挡的民主化发展趋势。
第一,外交决策机制由高度集权向民主管理转变,为民间外交发展创造了前提条件。以前在“外交无小事”观念的影响下,外交决策权集中在国家最高领导人或少数政治精英手中,普通百姓不能过问外交事务。随着大众传媒的兴起,公众对外交事务越来越关心,而且国内政治的民主化赋予了民众以及他们的议会代表一定的外交权限。在一些国家,普通民众可以通过全民公决的方式决定国家的重大外交政策,如2005年法国和荷兰民众就是否批准欧盟宪法条约进行了全民公决。尽管政府间外交依然居于主导地位,但是构建国家与民间社会各构成主体间在内的协商外交制度越来越成为国家外交制度建设的主流。2004年,中国外交部下设公众外交处,就不仅体现了满足公众对外交事务关心和表达的诉求,也体现了政府决策民主化的需要,使外交部门掌握民情、了解民意,从而能最大限度地提高外交决策的科学性和透明度,这是外交政策凝聚和体现公众意志的重要举措之一。当今全球民间社会力量兴起后的一个客观趋势是,在外交议题设定、外交实施方案选择以及外交政策实施和评估的全过程中,大力加强一国专职外交机构与民间组织和团体之间的协商制度建设,已经越来越成为紧迫的议题被提上了各国议事日程。
在民主化时代,外交与内政的关系越来越密切。随着国家权力的流散、国家权威与决策机构的分散,下述两方面的变化在一国外交制度的设计上越来越需要体现出来:一是外交部门及其机构与其它政府部门之间的政策协调机制;二是外交部门及其机构与非政府组织、专家学者、社会公众等非官方主体形成的沟通与合作机制[16]。有的学者还认为外交变成了一个“双层博弈”的过程。美国学者罗伯特·帕特南的“双层博弈论”(two-level game)认为,外交与内政相关联,一国的谈判者总是处在相互缠绕的两个层次的博弈中:一是与其它国家的谈判者的博弈;二是获得国内各利害方批准的博弈[17]。美国学者玛格丽特·凯克(Margaret E.Keck)和凯瑟琳·辛金克(Kathryn Sikkink)在解释国际上一些非国家行为体的外交活动时,提出了“回飞镖模式”(boomerang pattern)理论:如果一个国家或政府对本国公众压力的反应迟缓或消极,国内的非政府组织或个人就会寻求国际盟友的支持,通过国外渠道对本国的决策者施加压力。在人权保护领域这种状况表现得最为明显[18]。中国学者赵可金指出,“在相当多的情形下,民间社会部门的这种活动开辟了一个广阔的外交空间,这一空间是任何国家行为体都无法完全控制的,外交活动成为‘多元外交的大合唱’”[19]。
第二,外交运行机制从政府垄断向社会多元开放转变,为民间外交发展开辟了道路。政府垄断外交权力的格局逐渐被打破,一些次国家行为体、超国家行为体以及跨国行为体纷纷走上前台,与中央政府分享权力。来自草根层面的民间外交活动及其倡议的运动逐渐被整合到国家总体外交的制度框架之中。
总之,在全球化、信息化飞速发展的时代,民间自由交往随着全球化的发展无可阻挡,政府垄断外交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无论是跨国公司、非政府组织以及广大民众在国际交往中逐渐构建起了新的国际网络,还是伴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社会新阶层的出现,国际交往主体逐渐增多,都表明政府要想控制外交事务变得越来越难以实现了。“一个国家的政府无法阻挡国际旅游、文化交流和社交往来,也无法阻挡跨国公司之间的交往。诸如肯德基、麦当劳、博雅公关公司、波音公司、国际禁雷运动和绿色和平组织等众多社会角色,尽管它们并不是一个国家政府的职业外交官,但同样具有代表国家行事的权利,很难说它们的影响力就比职业外交官小。”[13]34因此,在全球化时代,民间外交越来越受到外交界和学术界的高度重视,民间外交的发展方兴未艾。
[1]David Harvey.The Condition of Postmodernity[M].Oxford:Blackwell,1989.
[2][英]戴维·赫尔德,等.全球大变革:全球化时代的政治、经济与文化[M].杨雪冬,等,译.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1:23.
[3]杨雪冬.全球化·西方理论前沿[M].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02.
[4]Robert Keohane.Hobbes’s Dilemma and Institutional Change in World Politics:Sovereignty in International Society[M]//Holm H H,Sorenson G,eds.Whose World Order?Boulder:Westview Press,1995.
[5][美]罗伯特·基欧汉,约瑟夫·奈.权力与相互依赖[M].门洪华,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2:25-26.
[6][美]约瑟夫·奈,约翰·唐纳胡.全球化世界的治理[M].王勇,译.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2003:16.
[7][美]詹姆斯·罗西瑙.面向本体论的全球治理[M]//俞可平.中国学者看世界(全球治理卷).北京:新世界出版社,2007:16.
[8][加纳]科菲·安南.联合国秘书长千年报告(摘要)[J].当代世界,2000,(9):9.
[9][英]巴雷特.赛博族状态——因特网的文化、政治和经济[M]//刘文富.网络政治——网络社会与国家治理.北京:商务印书馆,2002:3.
[10]赵可金.公共外交的理论与实践[M].上海:上海辞书出版社,2007:47-49.
[11]庞金友.应对全球化:当代西方国家与社会关系理论的新趋向[J].教学与研究,2006,(6):70.
[12]郭树勇.试论“建构主义革命”对于当代中国外交研究的若干意义[J].国际观察,2009,(1):31-38.
[13]赵可金.试论现代外交的民主化趋势[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8,(1).
[14]Harold Nicolson.Diplomacy[M].London:Oxford University Press,1963:245.
[15]唐贤兴.国际关系民主化与全球新秩序:全球化视野下的考察[J].学习与探索,2003,(5):28.
[16]白云真.新中国外交制度的演变与创新[J].世界经济与政治,2009,(9):55.
[17]陈志敏,等.当代外交学[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8:39.
[18][美]玛格丽特·凯克,凯瑟琳·辛金克.跨越国界的活动家:国际政治中的倡议网络[M].韩昭颖,孙英丽,译.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5:13.
[19]赵可金.全球化时代现代外交制度的挑战与转型[J].外交评论,2006,(12):69-76.
〔责任编辑:崔家善 徐雪野〕
D812
A
1000-8284(2015)01-0069-05
2014-11-20
国家社科基金重点项目“中国特色民间外交理论与实践”(14AZZ014)
苏淑民(1966-),女,辽宁朝阳人,副教授,博士,从事外交学、英国政治、俄罗斯政治经济与外交研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