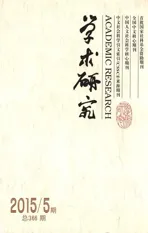王国维意境论与康德美学中国化*
2015-02-25蓝国桥
蓝国桥
王国维意境论与康德美学中国化*
蓝国桥
王国维提出文学意境论,在立论中融合了康德的思想。受中外文化的共同影响,王国维奉行知行并重原则,但在受影响的西学中,叔本华的知与行均有问题,而且知与行两相背离,而康德能做到知行合一,此是王国维告别叔本华,走向康德并视康德为精神导师的理由。王国维将意境的创造推给天才,天才创造的意境具有 “真 (所见者)—深 (所知者)”的两重性意蕴。康德美学中的天才,是美学理念的创造主体,它的机能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转化过来即是王国维意境 “真—深”的两重性意蕴。王国维的文学意境与康德的美学理念可以相通。康德是王国维西学的根基,其意境论的建构生成中融合了康德的思想,两者构成圆融一体的关系,足以表明康德对王国维精神世界的深刻影响。
意境论 “真—深” 两重性 康德美学 天才
王国维的意境论是中国近代以来影响最大的理论观点之一。他牢牢把握着的意境论,具体内涵究竟是什么,则似乎公说公有理、婆说婆有理。关于王国维意境论的理论来源厘定,学界更是出现了诸多的混乱与偏颇。不熟悉王国维西学背景的人,只就中国传统套路言说,充其量只带上一些佛教观念,甚至认定王国维的意境论完全是对传统的皈依,因而未能看清王国维意境论本应含有的现代性品格。而精通王国维西学背景的人,又错误地认为其意境论的理论来源是叔本华、柏拉图、席勒、尼采等人 (特别是叔本华)的学说,极少有人愿意将理论触角往康德哲学美学领地延伸,进而弄清王国维的意境论与康德美学理论的内在关连。有人尽管已注意到,康德哲学在王国维西学攻研中的根基作用,但却未肯轻易承认王国维的意境立论对康德美学的融摄,因而对康德哲学美学对王国维影响的充分性,也未能充分估量。王国维所创立的意境论,因其更多来源于康德美学,故而具有形而上学难以言说的特点。而康德美学中的天才,是不可解释的,故其产品也带有审美的不可解释性。
康德对王国维精神世界的影响作用,举足轻重。对叔本华产生深刻的质疑后,王国维不是走向对柏拉图、席勒、尼采诸家的攻读,而是把阅读、研究的热情、精力,集中在康德的著作上。其深层原因是个亟待深究、解决的问题。王国维在意境论建构中,如何使康德的思想作为有机组成部分而化合其中,同样是值得反思的大问题。问题一与问题二,是水乳交融的关系,绝不应像冯友兰、佛雏等学者那样,
将两者割裂开来,说他们虽承认康德的重要性,但却又否认康德与意境论之间有深层联系。
一、奉行知行并重原则:告别叔本华走向康德的理由
首先来看问题一,王国维 “别叔向康”的举措,原因究竟是什么。 “别叔向康”最根本的原因,是他以毕生精力坚守、奉行的知 (言)行并重原则。为了遵循此原则,他所付出的是血与泪的惨痛代价。
受时代风气影响,青年时期的王国维专治西学。因了解西学迫切,他接触的西方学说,有相当多是经日本学人转述而来的。日本新康德主义者桑木严翼所著的 《哲学概论》一书,以新康德主义的观念,概说整个西方哲学,引起王国维热情关注。该书于1900年在日本出版,王国维1902年即将之译为中文并刊行,足见他反应之迅速、关注之热切。桑木严翼在该书如此写到:“既有信仰,则不可不从而动。若所信而不能行,则其信则未至也。吾人屡有知而不行者。例如知慈惠之为善,而不能自减快乐以救贫民;知世间之无常,然犹缠着于名利,此皆知识存于其心而不移于行为者,此哲学者所当诫也。既如此,学说与实行不可分离,故学说又由实行而大受其影响。斐希台 (费希特)曰:‘哲学随哲学者之性行。’故斐希台之哲学示伦理的色彩,希哀林 (谢林)之哲学带审美的音调,叔本华以世界之根本在生活之意志,即烦恼也。而彼故烦恼家也。彼终身役役于不平之中,而不能实行其理想上之解脱。然如斯披诺若 (斯宾诺莎)以恬淡虚静为极致,自住此域,磨眼镜以糊其口,悠悠自适,如此者可谓信行一致之好模范也。”[1]桑木严翼对哲学者提出的严格要求,是他们的 “学说与实行不可分离”,希望他们 “存于其心”的知识能 “移于行为”,做到知 (学说、知识)与行 (实行、行为)一致。由他的要求引出的问题有二。其一、为做到知行合一,哲学者面对的学说、知识,需带有信仰品格,它们确切无疑、真实无妄。其二、以知行合一作为标准,去审视、考量哲学者及其学说、知识,便可以看出其成败、得失,以及到达境界的高低。作为中文译者,王国维对桑木严翼提出的问题,是能够心领神会、莫逆于心的。因为王国维在不同场合,对桑氏的知行合一原则,有程度不同的呼应,更有进一步的确认。
王国维之所以能够呼应新康德主义者桑木严翼,对哲学者提出的知行并重的要求,乃是因为他濡染的传统文化给他生成了回应的能力。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儒道两家学说,都非常重视行动。王国维深知,中国古人之为学包括知与行两方面。中国古人为学中的知识,是以现实人生的行动为皈依的。古人眼中的知是行之知,无行之知是概念的空谈,中国人对此的兴趣历来索然;而古人眼中的行是知之行,无知之行是浑浑噩噩,中国向来就忌讳,因它是与动物无别的行为。知指向行,行中有知,知行并重,是中国古学对人提出的严格要求,因而中国古学即是人学。儒学希望人能以德性仁心的训诫,引起现实的变动。理学家朱熹说:博学、审问、慎思、明辨、笃行,前四者博学、审问、慎思、明辨是深知,它指向最后的笃行,深知与笃行密不可分。心学家王阳明也很重视知行合一。道家则强调人心不为物累变得虚静明觉,人方可直面惨淡的人生,道家学说同样指向现实人生。王国维深知中国古人,为学中强调知(言)行并重的旨趣,他后来反思其师沈曾植的治学方法时,意味深长地指出,沈曾植 “忧世之深,有过于龚 (龚自珍)、魏 (魏源);而择术之慎,不后于戴 (戴震)、钱 (钱大昕)”,[2]“忧世”即忧虑民生社稷、民族存亡,“择术”即谨慎地选择能解救民族危亡、民生社稷的学术,而沈曾植治学的特点便是知与行双管齐下。王国维对沈曾植知行并重治学方法的归纳,是对知行并重原则进一步的强调。
王国维知行合一观念的生成,显然受中外两种力量的共同作用。中国传统文化强调知行并重,它是王国维知行合一观念形成之肥沃的精神土壤。桑木严翼对哲学者提出的知行并重要求,是点燃王国维知行合一观念的火苗。前后两者的共同作用,如此融合生成的知行并重观念,不但是王国维以血泪为代价竭力奉行的原则,而且是他衡量西方学者,特别是康德、叔本华得失成败的标尺。
哲学能否解答人生的问题,知与行能否相一致,最关键的环节是要看所获取的哲学知识是否确切可信。哲学知识越是确切可信,将之引向社会现实,以之来指导人的行为,使得言与行能够统一,就会变得越发有利。追求知识的确切性、可信性,对于真正的学者来说,必是责无旁贷、义无返顾的。随着王国维西学研究范围的扩大,他越来越惊奇地发现,新康德主义思想的导源地康德,能符合桑木严翼提出
的要求,与他内心的愿望相契合。康德之所以能如此,第一是由于康德能为他人的行为,提供相对确切的知识;第二则是因为康德本人,能做到言行并重、知行合一。前者是因后者则是果,前者与后者组合而成的,是因果性的联系。与此相反的情形是,不够确切的、可疑的知识,是难以导向行动的,因此在王国维心目中,疑窦丛生的叔本华学说,是不会占有重要地位的。
知识有见闻与德性之分。王国维凭借桑木严翼等人的研究知道,康德学说的伟大贡献,是把对象世界一分为二,区分出现象界与物自身。现象界与物自身,是对象对知识主体的不同显现。康德一再声言,主体面对的现象界是科学探索的区域,而在该区域内获得的科学知识,是真实可靠的。现象界是可知的,它需启用理论理性,它因而是见闻之知。科学探索的脚步必止于物自身面前,因为物自身不可知,在此无法形成科学知识,隶属物自身的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我们是无法知晓其真面目,理论理性无法穿越物自身的厚墙。面对可知的现象界,与不可知的物自身两者,王国维的态度是有所不同的。能形成科学知识的自然现象界,是由于人给自然立法,是源于人自身的能动力量,因而在王国维看来,它与休谟哲学只有程度的差异,而没有本质的区别,王国维不止一次地说到,康德与休谟本质上是一样的,都归属怀疑论的阵营。康德可靠的现象界知识,站在王国维的立场上,则是很值得怀疑的。而与此相反的情况是,在王国维眼中,康德不可知的物自身,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等超感性领域,若站在实践理性的范围内,它们都变得无比确切、可信。变得确切、可信的原因是,实践理性触及的物自身,与行为的道德性、价值性密切相关,唯有确信意志自由、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等学说,人的生活才有道德、才有价值,否则人的行为与动物无异。物自身的知识因而是德性之知。叔本华理解的理性是一种概念的能力,只关乎理论理性,而他眼中的康德的实践理性,与行为的道德性、神圣性是风马牛不相及的。王国维在 《释理》长文中,对叔本华的观点给予了驳斥。他的驳斥充分表明,他确信康德哲学中关乎德性的物自身知识。康德可靠的科学知识,到王国维那里却变得不可靠了,而康德不可知的物自身,到王国维那里却是可信的。应该说王国维对前者的理解,与康德的原意是不相符合的,而他对后者的领会则是准确的。由 “知识增时只益疑”的悟道诗句看,令他怀疑的是见闻之知,康德现象界的知识即是,使他坚信不疑的,是如康德的物自身那样,关乎德性的真知识。
德性的重要表现便是知 (言)与行一致。王国维眼中的康德,能做到知 (言)与行一致,是个极具道德修养的人。编译、刊行 《汗德 (康德)之事实及其著书》一文,使王国维知道,康德与斯宾诺莎都是言行一致的模范:“彼 (康德)素持严肃之人生观,又力践自己之义务,其好学不厌,诲人不倦,及其持躬之正直,皆出于尊重义务之心者也。彼晚年获至高之名誉,而仍不改其质素及冷淡之生活。”[3]属信仰的超感性存在,对科学知识而言是消极、有限制的,而对道德实践却能起到积极的促进作用。上帝存在、灵魂不朽、意志自由三者当中,最根本、最重要的是意志自由,因为意志自由是讨论上帝存在、灵魂不朽的前提,是行为绽放德性光芒的条件。当且仅当人行动的法则是由人的理性自行颁布,人的行动才是自由的、有道德的。康德深知成人的义务,知之深才能行之切,他能 “力践自己之义务”,康德的知 (深知)与行 (担当)是高度一致的。比起 “信 (言)行一致”的斯宾诺莎,康德有过之无不及!
康德是言行并重的模范,此印象在王国维后来的研究中得到进一步的强化。 “汗德不惟以学问有功于世也,其为人也,性格高尚,守正而笃实,尚质朴,食则蔬粝,居则斗室。严于自治,定读书作事之条规,日日奉行之,不稍间懈。方其为大学教授之时,天未明而兴,以二小时读书,二小时著讲义,既毕仍读书,午则食于肆。不论晴雨,食后必运动一小时,然后以二小时准备次日讲义,以余杂读各书。入夜九时而寝。三十年间,无日不如是。尝语人曰:‘有告予者,虽濒死必谢之。’”[4]康德不为名利所惑,行为高度自律,人格品性高洁,作息时间严格,康德乃做人的典范。历史上为人高尚无学问流于世者,芸芸众生中不乏其人,或有学问传于世而为人苟且者,古今学界多有所闻,如培根、卢梭、叔本华诸人即是,而达到学问与为人并重的,当非康德莫属:“言与人并足重,为百世之下所敬慕称道者,于汗德见之矣。”[5]康德言行并重印象的强化,使王国维更加推崇康德,并以之为西学的精神导师。
相比之下,叔本华则难以做到知行并重。王国维通过桑木严翼发现,叔本华终身陷于烦恼中,与他学说上倡导解脱说,实在是不相符合的,叔本华的知与行存在着背离。王国维关于叔本华,原先已有的不良印象,随着研究的纵深推进,得到了有力的强化。沿着知行合一的思路往前走,他在阅读叔本华著作的过程中,发现叔本华身上的缺陷实在不少。叔本华身上的缺陷,体现在两个方面,其一是他的学说经不起事实的推敲,他提供的是不确切的知识;其二则是他的知识与行动,存在着严重的不吻合。王氏既然已发现叔氏的为学与为人均存在着较大的缺陷,那么他若再以其为导师是不合常理的。
王国维学术取舍的标准,正是知行并重以及与此相关的,确信知识的有效提供。叔本华的哲学学说明显存在漏洞,叔本华的知 (言)与行,存在深刻的背离。而康德能提供可靠的知识,能做到言 (知)行一致。哲学家叔本华与康德,孰高孰低一望便知。王国维惜别他喜好的叔本华,自愿亲近他敬仰的康德,他西学取舍的全部秘密即在于此。青年王国维治西方哲学,第一宗师显然是康德,不是柏拉图、叔本华、席勒、尼采诸人。王国维西学的取舍既已如此,他倡导的意境论受康德影响应不会很浅。
二、意境 “真—深”的两重意蕴:康德美学观念的有机融入
再来看第二个问题,王国维是如何消融康德的美学思想,使其有效充当意境论有机组成部件的。王国维更急于追问的是意境究竟 “怎么样”,而不是忙于定义意境到底 “是什么”,王国维是在生动描述中使意境的意蕴灵动呈现出来的。王国维 《人间词话》的手稿与首刊稿,均对意境呈现出来的意蕴有着相对明确的描述、挑示手稿本写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百不失一,此余所以不免有北宋后无词之叹也。”[6]首刊稿则写到:“大家之作,其言情也必沁人心脾,其写景也必豁人耳目。其辞脱口而出,无矫揉装束之态。以其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诗词皆然。持此以衡古今之作者,可无大误矣。”[7]前者是125则手稿本的第7则,而后者位于64则首刊稿的第57则;前者是演绎性的,而后者是归纳性的,说的均是对 “古今之作者”的意境 (文学)创造,提出 “见者真”与 “知者深”之要求,带有总结性、概括性。不过,相比之下,后者比前者更简洁、明确、集中。王国维以词话的描述方式,想告诉我们意境是 “真 (所见者)—深 (所知者)”的两重性存在。
若具备相应的条件,意境的创造与欣赏中,会使我们目击到意境 “真—深”的两重性意蕴。意境的创造者要真,有自然的眼与舌,有自然的情与怀,他的存在需做到无蔽,他需对宇宙与人生有鲜活的感受体验。作为对象展现的作品,要自然而然能直观直感,而不矫揉造作扭捏作态。而欲创造深邃的意境,创作者需把灵虚的真际、不可捉摸的东西传达出来,使之感象化、具象化变得可以触摸。意境的感象、具象背后,应是令人琢磨不透欲罢不能,潜藏的意味韵味咀嚼不尽。如此一来,意境 “真—深”的两重性意蕴,便能在意境创造与欣赏中得到灵动显现。王国维对意境意蕴的描述,有时偏向于 “真”(不隔),有时则向 “深”(创意、言外之味、弦外之响)倾斜,有时则能两者兼及。偏重的情形不管如何,王国维倡导的意境,应是“真”中带有 “深”,而 “深”离不开 “真”,只有 “真”而没有 “深”(具体存在),或说只有 “深”而没有“真”(抽象存在),都成不了意境。作为两重性意蕴存在的 “新学语”,意境是中西观念融合的结果,而在中西观念融合的最深处,康德的影响始终是挥之不去的。
要求意境的创造者,沁人心脾地言情、豁人耳目地写景、脱口而出地说辞,即做到自然地书写。首先应具备的条件有二:创作需源于他真实的体验,心灵应不为功利所禁锢。意境创造所需要的诸多体验,最为刻骨铭心的,影响最大者莫过于痛苦。王国维对痛苦的艺术宣泄,以及相关的理论言说,由于有生命的痛苦体验作为基础,因而很容易产生共鸣,中国古典文学中的悲情书写、言说,叔本华和尼采对痛苦的理论说明,均是如此,康德也如此。康德的痛苦本体论深刻地影响着叔本华的学说。王国维治学有一特点,他的持论常经过多次综合方可定型,意境创造所需痛苦的真切体验之观念,同样经过多次综合。而在综合中,康德的因素是不可排除在外的。受桑木严翼 《哲学概论》关于康德痛苦论述的影响,王国维与叔本华一样,同样认同于康德的痛苦本体论。王国维坚持的无功利性审美原则,同样融摄
了康德的美学思想。痛苦的体验与摆脱功利的纠缠,都能体现出意境创造者及其作品存在的真。
创作者是真的存在,能做到自然地书写,意境即会达到 “能观”。王国维对意境提出的 “能观”要求,进而彰显其价值,与他接受的叔本华学说对直观的强调,以及他对此的消融,关系相当密切。不过,叔本华对康德甚是推崇,说读懂他著作、学说的前提,是了解康德的著作、思想,因而叔本华对直观的强调,与康德对他颖思智慧的激活有密切联系。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提出著名的审美四契机理论,四契机中 “量”与 “模态”的契机,都一致指出审美的直观本质,量的第二契机说的是审美无概念而普遍愉快,模态的第四契机则说,审美无概念而必然愉快。两个契机中的无概念即是直观,普遍、必然则与 “先天”的意义相当,两个契机合起来即是:审美判断属 “先天”的直观。钻研、消化 《判断力批判》观点后,王国维对其中的二、四契机,有如此简洁的表述:“优美及宏壮 (崇高)之判断为先天的判断,自汗德之 《判断力批评》后,殆无反对之者。此等判断既为先天的,故亦普遍的、必然的也。易言以明之,即一艺术家所视为美者,一切艺术家亦必视为美,此汗德之所以于其美学中预想一公共之感官者也。”[8]“美”遍及 “一切艺术家”说的是,审美判断是普遍的;而 “必视为美”强调的则是,审美判断是必然的。而康德所说的 “普遍”、“必然”,与 “先天”是可以互换的。由此看来,王国维对康德审美二、四契机的转述,是准确无误的,而审美二、四契机除了谈普遍、必然,还强调审美与无概念 (直观)的牵连,这才是康德的立足点。意境的 “能观”即是 “不隔”,而 “不隔”即是欣赏能达到“真”,王国维对此观念的提取,除了受叔本华等人的影响外,康德的影响同样不容忽视。
意境创作、欣赏中的 “真”与 “深”,水乳交融密不可分,王国维因此才断言,古今诗词作者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也”。由真之所见即能达深之所知者。真是深的前提,无真之深不是文学;深是真的升华,无深之真不是有意境的、杰出的文学,真者深也,反之亦然。在以意境为转动轴心的审美创造中,若以 “所见者真”为基础,能创造出 “所知者深”的作品,这是意境创造者必须完成的庄严使命。
王国维指出,有常人的意境 (境界)与诗人的意境 (境界)。常人之意境,所见者所感者有时也真,但常人却无法由之再往前有所推进迈进,他看山是山看水是水,眼前、当下即是他的全部,而诗人之意境不停留于眼前、当下,他的所见者所感者必不停留于表面,而是透过表面,直观到如其所是的面貌,他看山不是山看水不是水,即不是表面的山水,而是山水背后蕴藏的意义。 “山” “水”背后蕴藏意义的多寡,与创作者整个生命体验的深度、精神到达的高度,是有着内在、直接的联系的。创作者的整体生命存在,决定着意义赋予的面貌。生命的体验有深浅,精神的境界有高低,蕴藏的意义就有多寡,意境的创造也就有深浅。创作者以生命传达出悠扬、深远的韵味,是意境创造中甚为关键的环节。有意境,词作自成高格,而有深意境,词作规格更高。词作如此,文学亦然。词的创作史以及王氏自己的词作体验、理论接受,都能佐证这一点。王国维转向康德后,说文学艺术家神圣的使命、天职,就是要创造出意味隽永的有意境的作品。在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中他这样写到:“今夫人积年月之研究,而一旦豁然悟宇宙人生之真理,或以胸中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一旦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此固彼天赋之能力之发展,而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9]意境 “惝恍不可捉摸”,先存在于创作者的胸中,创作者若能将之传达出来,就会灵动地呈现于作品中。胸中 “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传达,需要 “天赋之能力之发展”。凭借 “天赋之能力”,“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得以 “表诸文字、绘画、雕刻之上”。意境以艺术方式表达,“此时之快乐,决非南面王之所能易者也”,创作者在其中获得的满足感,是溢于言表、无与伦比的。创造出意境深邃的作品,是创作者神圣的天职。
王国维对 “惝恍不可捉摸”(深)之意境,言之凿凿、感慨至深的评说,是对康德原著、原意的介绍、转译。康德在 《判断力批判》中,谈及美的艺术及其生成的天才创作时,有些表述:For in order to express what is ineffable in the mental state accompany presentation and to make it universally communicablewhether the expression consists in language or painting or plastic art-we need an ability[viz:spirit]to apprehend the imagination’s rapidly passing play and to unite it in a concept that can be communicated without the
constrain of rules.[10]王国维攻读叔本华的学说,已是叔氏著作的英译本,说明他有足够的能力读懂英文版的著作。王国维说他告别叔氏之后,在1905年以后将以数年的精力,来进一步钻研康德的著作,王国维恪守言行并重原则,他如此言说,必能如此行动。按照常理推算,他在1905年的春季已经大致弄懂 《纯粹理性批判》,之后迫切需要弄懂康德整体学说的他,马上阅读康德另外的伦理学、美学的著作,由此可以断定的事实是,王国维说他 “嗣是于汗德之 《纯理批评》外,兼及伦理学及美学”,是发生在1905年春季的事情。 《纯粹理性批判》甚为难懂,王国维在1903年的首次阅读,即是无功而返。他在1905年春既然已大致弄通甚为难懂的 《纯粹理性批判》,而他理解康德的 《判断力批判》必已不成问题。领会康德的美学观点之后,王国维写成 《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一文,刊行于1905年5月《教育世界》杂志上,他在该文中转译康德的美学观点,就变得容易理解了。诚然,王国维阅读的 “第三批判”,不一定出自Meredith之手,但英译本中的康德原意不会有很大改变,这是可以肯定的。
王国维的转述与康德观点的英译,有如下两个问题颇值得注意。其一,康德英译著作中的the mental state,王国维以汉语 “意境”翻译,而意境的 “惝恍不可捉摸”的特征、状貌,则与康德英译的ineffable对应。the mental state直译即是 “精神、思想的状态”,而ineffable的意思则是 “无法形容的、说不出来的”。ineffable in the mental state说的是 “无法形容、说不出来的” “精神、思想的状态”,而这种精神、思想的状态,在康德的著作里就是美学理念。王国维转译ineffable in the mental state时所说的“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与康德著作中的 “美学理念”是相对应的。如此的美学理念尽管不可名状,但是倘若能凭借 “天赋之能力”,就可将之表示于文字、或绘画、或雕刻之中。 “天赋之能力”即是康德所说的 “天才”,是表达美学理念的机能,正如王国维所说传达意境所需的 “天赋之能力”一样,两者的意思是一致的。依此可知,王国维之所以钟情于 “惝恍不可捉摸”之意境,与他对康德美学思想的接受、消化,是有深刻联系的。他的意境立论受康德学说的影响,当是不可诬的事实。而王国维对天才的无比推崇,与他对康德美学思想的融摄,彼此关联之深,在此也可得到确认。其二,传达美学理念所需要的 “天赋之能力”,是an ability[viz:spirit]to apprehend the imagination’s rapidly passing play and to unite it in a concept that can be communicated without the constrain of rules.翻译过来即是 “‘把握那快速而易逝一瞬即过的想像之游戏’的能力,并且也是那 ‘把这一瞬即过的想像之游戏统一于一概念中’之能力,这所统一之于一概念之概念即是那 ‘用不着任何规律之强制而即可被传通’的那概念”。康德所说的知性,是一种概念机能,而想象力的游戏是自由的,它属直观机能,知性的概念、定义与想象力的自由、直观,彼此相互协调,即是这种能力的适用场景。天才的机能,从它的内在构成来看,就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运转。在上述王国维的转译中,我们还无法看清,他对天才心意机能的把握、领会,只是在具体理论的阐述、运用中,他的把握、领会的状况才为我们辨识得到。
王国维对天才机能内在构造的把握、领会,可从他后来对天才人物,如屈原、辛弃疾等人的讨论中见出。他明确指出,中国的南北文学在诸多方面存在着差异,而屈原兼具南北文学的特点,屈子文学的精神,足以弥合南北文学的裂痕。真挚、深邃的情感是屈子文学的内容,它的形式则是瑰丽、丰富的想象力,两者缺一不可。王国维就形式说,屈子 “丰富的想像力,实与庄、列为近,《天问》、《远游》凿空之谈,求谬悠之语,庄语之不足,而继之以谐,于是思想之游戏更为自由矣”。思想是知性的事业,文学中的思想是自由的,如同想象力在文学中是自由的一样,知性、概念的思想与感性、直观的想象力双方在自由中 “游戏”,作为天才产品的屈子文学,就必然是想象力与知性彼此协调的产物。由屈子个案推而广之,王氏说诗歌乃至文学中 “想像的原质”,归根到底就是 “知力的原质”,[11]因为 “想像”与“知力”是协调一致的。 《人间词话》中有一则专评辛弃疾,足见辛弃疾在他心中分量之重:“稼轩 《中秋饮酒达旦,用 〈天问〉体作 〈木兰花慢〉以送月》,曰:‘可怜今夕月,向何处、去悠悠?是别有人间,那边才见,光景东头。’词人想像,直悟月轮绕地之理,与科学家密合,可谓神悟。”[12]《天问》体《木兰花慢》词,想象力异常丰富。神奇的地方就在于,想象力虽是直观的机能,词人凭借着它能与科
学上的知性功能相吻合。有学者指出,辛弃疾在当时,是不可能有 “月轮绕地之理”如此的科学发现的,与其说是他的 “神悟”,还不如说是王国维的 “神悟”,如此的疏证是有道理的。[13]若往深层里看,王国维 “神悟”心灵的开启,与他领悟过的康德美学,对想象力与知性谐和的强调,肯定不无联系。王国维的 “神悟”再次表明,他对天才人物的构成机能,即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谐和,是有深入领会的。
王国维的意境与康德的美学理念是可以相通的,康德把美学理念的传达推给天才,而王国维则指出,天才是意境真正的创造者,两者有异曲同工之妙,王国维已把康德的美学思想内化为自己的立论基础。我们知道,构成天才的心意机能,是想象力与知性的协调,既然意境的创造同样是天才担当的庄严使命,那么意境必表现为想象力与知性的谐和。王国维眼中的意境,带有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双重特性,并且他说,以此来衡量古今作者的优秀程度,大概是没有什么偏差的。想象力是直观的机能,它所承当的任务是 “所见者真”,而知性是概念的机能,它的基本职责是 “所知者深”,因而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构成的两重性,若转换成康德的语言,便是想象力与知性的谐和一致。王国维 “所见者真,所知者深”的表述,在 《人间词话》手稿与首刊稿中的位置,尽管有所不同,但带有总结性、概括性特点,倒是显而易见的,当中融合着的康德思想,只能理解为促使、推动他形成如此观念的,无疑是康德的学说。从意境创造到欣赏,由意境论的局部到整体,王国维都能使康德的观念融合其中。
三、结论:康德是王国维西学的精神导师
能创造出 “真—深”两重性意蕴之意境的,是天才。天才及其创造的作品除了存在之真与深,还具备德性品格。天才及其作品的德性凸显,使得王国维的意境论,必向人生现实敞开。对此王国维这样写到:“文学之事,其内足以摅己,而外足以感人,意与境二者而已。”[14]他想说的是,文学以创造意境为使命,而文学意境的功能大致有二,其一是 “摅己”,抒发、宣泄内心的苦痛,其二是 “感人”,使他人受到感动、得到变动,前者为己,后者为人,无论是为己,还是为人,意境都指向现实人生。王国维的意境论,因指向现实人生,他的意境论之言和知,与现实中的行和为,是不分须臾的。王国维的意境理论,同样体现着他知 (言)行并重的人生理想追求。[15]由此可以肯定,上文提到的问题一与问题二,绝不是割裂的关系。王国维在西学的治理中,以康德学说为根底,而他意境的理论生成,受康德的影响同样深刻,而前后两者不能割裂的更深层原因是,前后两个问题中,都能体现他知行并重的信念,而后者更是对前者的深化、提升。前后两者关系不能割裂,足以表明康德对王国维精神世界带来的深刻影响,绝非虚妄!不是叔本华更不是柏拉图、席勒、尼采,唯有康德才是王国维西学的精神导师!
[1]桑木严翼:《哲学概论》,王国维译,《王国维全集》(17),杭州、广州:浙江、广东教育出版社,2009年 (以下全集版本同此),第182-183页。
[2]王国维:《沈乙庵先生七十寿序》,《王国维全集》(8),第620页。
[3]王国维编译:《汗德之事实及其著书》,《王国维文集》(3),北京:中国文史出版社,1997年,第295页。
[4][5]王国维编译:《德国哲学大家汗德传》,《王国维文集》(3),第293、294页。
[6]王国维:《人间词话手稿》,《王国维全集》(1),第487页。
[7][12]王国维:《人间词话》,《王国维全集》(1),第477、474-475页。
[8]王国维:《古雅之在美学上之位置》,《王国维全集》(14),第109页。
[9]王国维:《论哲学家与美术家之天职》,《王国维全集》(1),第133页。
[10]Kant,A Critique of Judgment,Beijing:China Social Sciences Publishing House,1999,p.186.
[11]王国维:《屈子文学之精神》,《王国维全集》(14),第101页。
[13]彭玉平:《人间词话疏证》,北京:中华书局,2011年,第254页。
[14]王国维:《人间词乙稿序》,《王国维全集》(14),第682页。
[15]蓝国桥:《言行并重与王国维意境论的价值》,《人文杂志》2013年第6期。
责任编辑:陶原珂
B83-09
A
1000-7326(2015)05-0140-07
*本文系国家社科基金项目 “王国维与康德美学中国化研究”(12CZW018)的阶段性成果。
蓝国桥,广东岭南师范学院人文学院副教授、博士,复旦大学文学院博士后 (广东 湛江,52404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