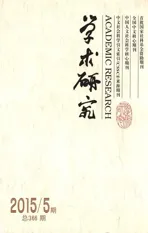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 (中)
2015-02-25周凡
周凡
在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
——对恩格斯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反思 (中)
周凡
1874年,俄国民粹主义的洪流终于冲开了历史的闸门,它咆哮怒号、倾泻而下,思想之流变成了塑造社会历史的激进运动。正是在这一历史时刻,它与那个时代早已震撼欧洲并试图影响整个世界的另一股思潮——马克思主义——发生了全方位的遭遇。这场遭遇战的先锋战将,马克思主义一方是老将恩格斯,俄国民粹派一方是小将特卡乔夫。恩格斯与特卡乔夫之间的这场较量使19世纪两种激进主义形态被迫开始了相互冲击、相互消磨、相互蚕食而又相互交融、相互吸收、相互塑造的痛苦过程。从一定意义上说,不了解这一痛苦过程,就不能理解马克思晚年阅读、思考、写作的微妙变化,就不能理解俄国革命民粹主义的内在冲动及其缺陷,就不能理解列宁主义的理论渊源的整个复杂性,就不能理解马克思主义的俄国效应及其在东方社会的存在与演变形态。本文尝试还原这场遭遇战的来龙去脉、前因后果及其进行过程中的诸多细节,希望借此为人们反思马克思主义与民粹主义之间的 “互构性”关系赋予一些激发性要素,同时也为人们审视当代 “后马克思主义”接合民粹主义逻辑的努力提供更加深远的背景。
马克思主义 民粹主义 特卡乔夫主义 巴枯宁主义 拉甫罗夫主义
五
拉甫罗夫指责恩格斯 “主写”的小册子,恩格斯自然不高兴,尽管他与拉甫罗夫是不错的朋友。或许正因为是朋友,恩格斯才更不高兴:既然是朋友,为什么偏偏为自己的敌人说话?当恩格斯第一次读到 《前进!》第2期上的 《工人运动年鉴》的时候,想必就动了反驳的念头,并且,恩格斯应该是在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争论之前就已经读了 《工人运动年鉴》。在1874年10月致洛帕廷的一封信中,恩格斯写道,“我在仔细阅读了 《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的小册子以后,确实不再由于我们的朋友对我们使用异常尖锐和毫无道理的言词而对他怀有任何怨恨”。[1]这就无意间透露出,恩格斯在读到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论战的小册子——《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之前确实由于拉甫罗夫在 《工人运动年鉴》中“使用异常尖锐和毫无道理的言词”而 “怨恨过”拉甫罗夫。只是在读了 《致俄国社会革命青年》之后,恩格斯才 “怨消气散”。为什么恩格斯满肚子怨气的时候,不去驳斥拉甫罗夫,而等 “怨消气散”之后,
却要撰文回应呢?
笔者判断,很可能是马克思劝阻了恩格斯即时的 “自卫还击”,理由有三个。第一,马克思对拉甫罗夫印象一直不错。长期以来,拉甫罗夫与马克思主义的关系被遮蔽了,在我们所能见到的马克思主义发展史或马克思主义哲学史教科书或种种学术著作上,鲜有人提及拉甫罗夫,而实际上,拉甫罗夫是马克思恩格斯十分看重的朋友,并且,在革命民粹主义理论家中,他的思想与马克思主义的兼容度最高。拉甫罗夫自1870年流亡欧洲以来,一直和马克思恩格斯保持着良好的个人关系,特别是1871年4月,他从巴黎来伦敦拜见马克思,向马克思汇报巴黎公社起义的经过,就像伊滕贝格所说,“拉甫罗夫是为马克思搜集到关于巴黎公社的完全可靠信息的为数不多的几个人中的一个”。[2]也有学者提出,马克思写作 《法兰西内战》时利用了拉甫罗夫的一些观点,特别是拉甫罗夫的反集权主义观念对 《法兰西内战》的民主思想产生了深刻影响。第二,正是由于马克思与巴枯宁的激烈斗争,才导致拉甫罗夫对马克思的抱怨与疏远,不过,在1874年,马克思自认为他在这场斗争中已经取得了明显的优势。1874年3月,《前进!》编辑部从苏黎世迁到伦敦不久,拉甫罗夫就拜访了马克思。马克思会把拉甫罗夫的拜访看做是自己与巴枯宁的斗争取得优势后附带产生的一个积极效应。既然拉甫罗夫离开了巴枯宁势力集结的瑞士,不远万里来到英国,来到伦敦之后,又不计前嫌,登门请教,就是看在共同的朋友洛帕廷的面子上,也不能对人家过于苛责。马克思也并不是一个彻底拒斥 “和为贵”的人,和不和,还是要看对象,跟一贯倡导和气的拉甫罗夫讲和,马克思还是乐意的。不管怎么说,拉甫罗夫的到访给两人缓和近两年来有点紧张的关系带来了转机。第三,马克思这个时候,正在加紧研究俄国社会问题,既然 《前进!》是俄文杂志,他也希望这个杂志能够给他提供更多的关于俄国社会问题的有价值的资料。再说,《前进!》迁到伦敦,也为马克思施加对于 《前进!》杂志的影响提供了机会。说不定,还可以把 《前进!》杂志朝着更正确的方向引导呢!好事找上门,为什么要往门外推呢?
也不排除有这样一种可能性:恩格斯读了 《前进!》第2期之后,按捺不住满腔怒火,立即着手撰文反驳,而当听了马克思的意见后,恩格斯写了一半就停了下来,这个已写出的一半就是后来发表的《流亡者文献 (三)》的第一部分。等恩格斯读了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各自所写的小册子之后,恩格斯才接着写 “第二部分”。如果真是这样的话,那么,后来续写的这个 “第二部分”就更显得奇妙了:它使本来不宜发表的第一部分变得可以向拉甫罗夫展示了,毋宁说,添加的这一部分改变了原有部分的性质。这正是 《流亡者文献 (三)》的奥妙之处:如果只有第一部分,而没有第二部分,那么,这篇文章就是一篇纯粹回击拉甫罗夫的文章,而有了第二部分,整个文章的意味就发生了微妙的变化:文章的重心不在于 “批判”而在于 “教育”。
1873年秋天,当拉甫罗夫读恩格斯的小册子时,心情无比沉重。1874年秋天的恩格斯则有着另一种情绪。坦白地说,笔者读 《流亡者文献 (三)》时,不知怎么的,脑子里多次蹦出杜甫的两句诗:两个黄鹂鸣翠柳,一行白鹭上青天。也许在潜意识里,笔者是把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当成两个鸣柳的黄鹂了,而恩格斯则仿佛是直冲云霄的白鹭。白鹭比两个黄鹂飞得高。据说,杜甫在写这首绝句的时候,蜀中战乱刚刚平定,加之听说故友严武还镇蓉城,所以心情异常喜悦。正是由于诗人心情舒畅,他才能妙笔生花,眼中才有 “窗含西岭千秋雪,门泊东吴万里船”那样窗含千秋、门纳万里的宏阔景观。恩格斯写作 《流亡者文献 (三)》时的心情大抵与杜甫一样欢快。当他读完拉甫罗夫的小册子时,他掩饰不住内心的喜悦,痛痛快快地说了一句:“现在我们可以满足了”。[3]此语既出,似乎意犹未尽,他又把拉甫罗夫所写的一段文字搬过来,略微改动了一下,以玩笑的形式来抒发心中的快意:
我们不知道,作者们如何看待所产生的效果。我们的大部分读者想必会像我们一样感到 “愉快”,我们就是怀着这种心情阅读这篇文章和为了履行史家的职责而在我们的刊物上披露这些 “特殊”现象的。[4]
不能简单地把恩格斯的愉快解读为他抓住拉甫罗夫的把柄之后的幸灾乐祸,在玩笑的背后,寄寓着
严肃的教诲。恩格斯此时,似乎正在向拉甫罗夫讲述一则寓言,情节则类似于 “农夫与蛇”或 “东郭先生与狼”,主人公就是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找到了这样生动的说教材料,恩格斯哪能不高兴呢:曾几何时,你拉甫罗夫说我不该写小册子,指责我不该在社会主义者之间挑起争论,现在,你为什么也印制小册子呢?你为什么要与特卡乔夫公开争论呢?你不是要我们宽容巴枯宁主义者吗?如今,特卡乔夫以巴枯宁主义者的姿态毫不宽容地向你发起了攻击,你又作何感想呢?你把自己弄得有苦难言,又能怪谁呢?好好想想吧!我的朋友,巴枯宁以及所有的巴枯宁主义者都是一些毒蛇,你敞开胸怀温暖它、挽救它,它反过来要一口咬死你。啊,可怜的拉甫罗夫!你这个受伤的黄鹂,你的遭遇已经够不幸了,我们也不好再多说什么,就是希望你能从中吸取教训!如果你老是督促别人学习,而自己却不善于学习,你永远也不明白为什么黄鹂不能 “上青天”而白鹭却能。至于那个特卡乔夫,那个与你一起 “鸣翠柳”的另一个黄鹂,实在乏善可陈,如果不是为了让你警醒,我提都懒得提他!
这就是恩格斯介入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争论的全部奥秘:它是一种非常奇特的介入,它好像是介入,又好像不是介入。说它是介入,因为可以断定,恩格斯是看了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各自的小册子之后,才动手写这篇文章,甚至可以说,如果没有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的争论,恩格斯就不会写这篇文章。说它不像是介入,是因为,从文章的内容看,恩格斯并没有分析争论双方理论上的异同,也没有明确赞同任何一方的论点。既不能说文章是为了批判拉甫罗夫主义而写,也不能说文章是为了批判特卡乔夫主义而写。德波拉·哈迪甚至认为,恩格斯这篇文章 “没有什么实质内容”。[5]从这个意义上说,它似乎算不上是对拉甫罗夫与特卡乔夫之间争论的一种介入。但是,一旦你试着感受一下恩格斯写作 《流亡者文献 (三)》时的情绪,你就会发现,《流亡者文献 (三)》又分明是对拉甫罗夫和特卡乔夫争论的一种偏向性的、干预性的介入。自1872年以来,拉甫罗夫与恩格斯几乎断绝了通讯联系,这与1870—1871年间两人频繁的书信交往形成了巨大的反差。 《流亡者文献 (三)》是破开友谊之河上的坚冰的信号。只不过,恩格斯对朋友的教诲是隐藏在批判性文字背后的,不明就里的洛帕廷一开始好像没有读懂,误以为恩格斯要与朋友彼得决裂,于是,恩格斯回信明言相告:“这根本不是我的意图。相反,我是在尽可能地使之缓和……无论什么时候,只要他能像我一样心平气和地对待所有这一切,那我随时都愿意和他握手”。[6]那个昔日的 “西多罗夫”①“西多罗夫”是拉甫罗夫的化名,恩格斯和拉甫罗夫通信时使用这个名字称呼拉甫罗夫。显然是读懂了恩格斯的这篇 “友爱的政治学”,他依稀听到了恩格斯隐藏在文字背后的友爱的召唤,所以,《流亡者文献 (三)》发表之后,他选择了沉默。但是,或许正是这种沉默,却预示着某种声音的出场。
六
1874年夏天,身在巴黎的特卡乔夫在读了拉甫罗夫的小册子后,想再写小册子予以反驳,可是,当初为他出版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的萨仁印刷所已经关闭。1874年6月21日,他致信拉甫罗夫,要求在 《前进!》杂志第3期上继续辩论,②特卡乔夫的这封信被鲍·尼古拉耶夫斯基 (Б.И.Николаевский,1887—1966)发表于 《在异国》1925年第10期。没想到,拉甫罗夫断然拒绝在他的杂志上刊登关于“流亡者文献的私人宣言”。[7]特卡乔夫一时失去了发表文章的渠道,他憋了一肚子反击拉甫罗夫的话,这些话像是更具杀伤力的子弹,只要找到机会,就朝拉甫罗夫身上更加猛烈地扫射过去,遗憾的是拉甫罗夫已无心再战。找不到对手的特卡乔夫闷闷不乐地离开法国重新回到瑞士。回到苏黎世不久,特卡乔夫在10月初 《人民国家报》上读到了恩格斯的 《流亡者文献 (三)》,在这篇主要批评拉甫罗夫的文章中,恩格斯顺便对特卡乔夫冷嘲热讽了一番,这令窝了一肚子火的特卡乔夫十分生气:我与拉甫罗夫争论,关您恩格斯什么事,您为什么横插一杠子?我又没招惹您老人家,您干吗在那儿说三道四?您对拉甫罗夫不满,尽管把火发到他身上,您凭什么拿我撒气?您说什么:顺便提了我一下名字,这一提却惹
起了我的可敬的愤怒。好像我是一个一听到别人提及自己的名字就会狂躁不已的精神病人似的!我对自己的名字一点都不过敏,您也不想想:您是怎样 “提”的?有您那样 “提”的么?您说我 “是一个幼稚的、极不成熟的中学生”,还把我比作德国幽默作家戴维·卡利希创造的一个浅学之徒、纨绔子弟的形象——小卡尔·米斯尼克,您的真正意图就是要把我们这些俄国流亡者滑稽可笑地介绍给德国读者。您不仅讥讽我 “胸怀壮志却一事无成”,而且,在您眼里,我向拉甫罗夫宣讲的道理竟成了 “幼稚的、枯燥的、矛盾的、翻来覆去喋喋不休的议论”,更可气的是,我关于俄国革命的言论中竟被您贬斥为一堆烦人的 “废话”。您向我们俄国人表示了您最深的蔑视。也太不给豆包当干粮了!盛怒之下的特卡乔夫,要向恩格斯开火了。本来,他的靶子是拉甫罗夫,谁知恩格斯这时冲了上来。于是,在1874年冬天,恩格斯要 “代友受过”了,这似乎是书写 “友爱的政治学”的一种代价。
但是,特卡乔夫明白,恩格斯毕竟不是拉甫罗夫,不能把恩格斯当做拉甫罗夫来批判,也不适宜把那些向拉甫罗夫说的话都讲给恩格斯听。因此,我们看到,《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不仅比 《给 〈前进!〉杂志编辑的信》要短得多,而且,它不是呈现为一种内部的争吵,而是要站在一般俄国革命者的立场上对怀疑俄国革命的 “外人”讲话,这正是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一个最重要的特色:它无意于突显特卡乔夫不同于其他俄国革命理论家的地方,而只是努力展示俄国民粹主义者所共有的信念,不妨说,这封冬天里的公开信具有一种摒弃前嫌、一致对外的气度。这不仅仅是特卡乔夫的应对策略,它也是那个时代俄国流亡者通常的做法,就像德波拉·哈迪所说的那样,“尽管俄国激进流亡者相互争吵不断,但是,他们尽量保持团结,正是在这个意义上,才可以正当地把他们称作在西欧形成的 ‘移民群体’。在瑞士,与在英国、法国一样,这些流亡者努力保持相互接触,并且,在外国人面前维持他们共同的身份”。[8]德波拉·哈迪举出了一个特别的例子:每当有俄国流亡者去世,那些曾与死者有过激烈争论的俄国侨民也往往会出席死者的葬礼,“在这样的时刻,昔日最严重的分歧在悲哀的死亡和为革命再献身的氛围中变得黯然失色”。[9]在1886年初,拉甫罗夫就参加了特卡乔夫的葬礼并在葬礼上发表了讲话。虽然特卡乔夫在1874年冬天不是面对某种死亡的悲哀,可是,他从恩格斯的 《流亡者文献 (三)》中俨然读到了比死亡更令他震撼与悲悯的东西,仿佛有一种最宝贵、最神圣的东西被剥夺、被亵渎了,一种巨大的丧失与沉痛紧紧攫住了他的心灵,正是这种情怀,使得特卡乔夫暂时抛开狭隘的 “小我”,主动地把自己融入到一个更大的群体之中。
恩格斯说,他连想都没有想到要把特卡乔夫看做是俄国革命者的代表,[10]这应该是真话;特卡乔夫的代表权确实非常有限,历史学家有大体一致的描述:特卡乔夫是一个内向而孤独的人,并且,他的一些独到的观点在他那个时代并没有得到大多数俄国革命者的认同。但是,我们不能由此否认特卡乔夫的革命者身份。我们不去讨论特卡乔夫是否有资格代表其他一些俄国革命者,我们只需关注特卡乔夫在公开信里是否提出了俄国革命民粹主义者在1870年代普遍思考的重大问题。答案无疑是肯定的。如果说,特卡乔夫的公开信有什么意义的话,那么,它的意义首先就在于,它比米海洛夫斯基1877年10月发表在 《祖国纪事》杂志上的 《卡尔·马克思在尤·茹柯夫斯基先生的法庭上》一文更早地提出了 “俄国能否走一条不同于西欧国家的独特革命道路”的问题。在特卡乔夫看来,恩格斯从来不愿意认真对待这一问题或者说干脆拒绝思考这一问题,并且,对于这一问题的提出及其解决,恩格斯是 “极端无知”的。特卡乔夫的公开信就是把恩格斯的这种 “无知”作为贡品奉献于俄国特有的 “革命”观念之前。具有讽刺意味的是,特卡乔夫用来对付恩格斯的方法恰恰是拉甫罗夫式的:拉甫罗夫不是主张学习吗?您恩格斯不是把他当做朋友吗?那么,最应该响应拉甫罗夫号召的就是您恩格斯,因为您习惯于用权威的口气向俄国革命者讲话,可是,您对于俄国社会却缺少必备的知识:
您在您的文章中主要是称赞德国革命工人党清楚俄国革命者的意图,以及给他们一些建议和最符合他们利益的实践指示。这是多么美好的目标!不幸的是,要达到这些目标,仅仅有良好的意愿是不够的,——还需要具备一些知识,而您缺少这些知识,因此,您的有益教训将在我们俄国人中
产生这样的感觉,也许您已经感受到了,就像一个偶尔学习德语但从未去过德国也从不关注德国文学的中国人或者日本人,如果突然在他头脑中出现一个奇特的想法,带着中国人或者日本人的傲视教导德国革命者应该怎么做,那么他会被拒绝。中国人的想法只是非常可笑但完全无害;而我们面临的完全是另一种情况。他们不仅是最可笑的, 而且还产生很大的害处,因为您以对我们最不利的色调来向德国工人描写俄国革命政党的国外代表、我们的意向和我们的著作,他们自身不够了解我们,必然相信以过于自信的权威口气说话的人,尤其是,他们认为这个人非常伟大。您用这样的方式描述我们,违反了国际工人协会纲领的基本原则。[11]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基本叙事任务就在于向恩格斯灌输关于俄国社会和俄国革命的基本知识。德波拉·哈迪指出,“特卡乔夫值得称赞的地方在于,他的答复超越了微不足道的谩骂,尽管这个年轻人一定知道恩格斯享有巨大的声望,但是,他并没有从争论中退缩。他的公开信几周之后就在苏黎世发表了,这封信虽然不是完全没有个人嘲讽,但是,它针对马克思主义者的观点对民粹主义立场进行了经典的辩护,也就是说,它捍卫了特卡乔夫这样一种认识:俄国具有特殊的国情,因此,它必然要走一条特殊的革命道路”。[12]特卡乔夫对恩格斯的主要指责在于,恩格斯只是盲目地让 “俄国人融入国际不可避免的命运”,即俄国的革命运动 “从今以后要在欧洲其余国家的面前并在它们的监督之下进行”,[13]可是,他不知道,“我们国家的情况是非常特殊的,它与西欧任何一个国家没有任何共同之处。西欧国家采取的斗争手段对于我们至少是不适用的”,[14]因此,他必须向恩格斯描述恩格斯没有看到的东西,即俄国不同于西欧国家的地方。
特卡乔夫迫不及待地告诉恩格斯,俄国之所以不能照搬西欧工人运动的模式,是由于俄国根本不具备西欧国家的工人进行社会主义革命斗争所具有的基本条件:
像你们在西方尤其在德国所具备的那些为革命服务的斗争手段,我们在俄国一样都不具备。我们没有城市无产阶级,没有出版自由,没有代表会议,总之,没有一件东西可使我们希望把无知识的劳动人民联合 (在现代经济情况下)在一个组织、纪律都很好的工会中——正是在这样的工会中,他们才能意识到自己的状况以及改善自己状况的方式。在我们这里,为工人出版书报是不可思议的,即使能出版,也不会有任何意义,因为我们的人民多数是文盲。个人对人民的影响未必有任何重要的长远的意义,即使它能带来真正的益处,它对于我们也是完全不可能的。根据不久前颁布的政府敕令,受过教育的阶级与 “愚昧”农民的任何接近都被视为犯罪。 “到人民中间去”只有在穿上别人的大衣和使用虚假的身份才是可能的。阁下,您一定同意,在这样的条件下把国际工人协会移植到俄国土地上来,这是幼稚的梦想。[15]
虽然俄国不具备这些条件,但这并不表明 “社会革命在俄国胜利比在西方更加值得怀疑、更加没有希望”。[16]你们西方有的,我们没有;可是,我们东方有的,你们西方也没有——正是因为俄国拥有西方所没有的这些东西,使得俄国不仅不会因为缺少西欧国家所具有的那些条件而与革命无缘,反而会比西方国家更容易爆发革命。(1)俄国没有城市无产阶级,但也没有资产阶级,这样革命就少了一层阻碍。(2)俄国人民是无知的,但是他们绝大多数都充满着公有制原则的精神,他们是本能的、传统的社会主义者。(3)俄国人民习惯于奴役和顺从,但是他们一直在反抗、在不断地反抗,他们是本能的革命者。(4)俄国的革命知识分子人数不多,但是他们有坚定的革命信仰,他们除了社会主义理想之外,没有任何其他理想。(5)俄国是专制主义国家,但是,它比西方国家更加薄弱。基于上述几方面的优势,特卡乔夫自信地说道:“我们相信社会革命在俄国最近实现的可能性,我们不是空洞的幻想家,不是幼稚的中学生,我们站在坚实的土地上,我们的信仰不是没有牢固的根基,它们多产是从我们熟知的俄国人民的生活条件中得出结论”。[17]
这显然是19世纪六七十年代俄国民粹主义各派观点的一般性综合,其实在每一个要点里面可能存在诸多的分歧,但特卡乔夫在公开信中尽量说得简略一点、模糊一点、笼统一点,以便塑造一个共同一
致的 “我们”的形象。挟民粹派之众以共御外侮,特卡乔夫好像在扮演一个思想盟主的角色。恩格斯显然看出了这一点,他随后发出的第一声抗议就是,“必须首先确定,‘俄国革命者’无论先前和现在都与这里的问题毫不相干,我们应当把特卡乔夫的 ‘我们’到处都读做 ‘我’”。[18]然而,在1874年冬天,孤独的特卡乔夫特别需要 “我们”。在与拉甫罗夫争吵之后,面对 “外人”对俄国革命的怀疑以及对俄国革命者的轻蔑,他好像是第一次深切地感受到了 “我们”的重要性,“我们的志同道合者越多,我们就越感到自己有力量”。[19]特卡乔夫就是要借用 “我们”的力量来围剿恩格斯,在他的这个总结陈词中,句句都有一个 “我们”,一个同仇敌忾的 “我们”。这是企图陷恩格斯于四面楚歌之中:您恩格斯反对我特卡乔夫,就等于是与所有俄国革命者为敌!最后,特卡乔夫也没有忘记对恩格斯使出他最狠的一招:“您忘记了,我们进行反对俄国政府的斗争,不仅是为了祖国的利益,而且是为了整个欧洲的利益,为了全部工人的利益,因此,这个共同的事业使我们成为您的同盟者。您忘记了,您嘲笑我们,就是为我们共同的敌人即俄罗斯国家很好地效劳”。[20]这与说拉甫罗夫 “为第三厅的利益和目的效劳”[21]没有什么两样,特卡乔夫终于解恨了:恩格斯已经孤苦伶仃地被一层又一层的 “我们”所包围,正遭受着真正革命者的质疑与拷问的目光。连恩格斯自己也感觉到,“卡尔这个孩子也开始威胁我了”。[22]其实,一点都不用怕,这通常是 “小卡尔”在自认为受到侵犯之后做出的一种虚张声势、故意吓人的滑稽姿态。
七
虽然特卡乔夫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竭力表现的是 “我们”,但是,在这个由特卡乔夫叙述的 “我们”中还是不可避免地夹杂着一些 “我”的痕迹。致恩格斯的公开信篇幅不大,其重点在于展示俄国民粹派的重叠共识,但是,说它一点也没有发出特卡乔夫主义的信号恐怕也是不真实的。与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相比,《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的一个最大理论贡献在于它对 “政治问题”的进一步阐述,这些阐述集中在三个方面:政治权力的优先性,激进主体的建构,东西方国家的结构性差异。这些方面要么围绕国家问题,要么涉及国家问题,因此,这封公开信表现出明显的 “国家—革命”论证逻辑:国家问题是革命问题的前提,只有清楚地说明俄国的国家状态与西欧国家不同,才能合乎逻辑地得出俄国可以走不同于西欧的道路这一结论。
首先,特卡乔夫以十分凝练的语言把他在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中关于 “政治优先性”原则的阐述又向前推进了一步。在与拉甫罗夫的论战中,特卡乔夫指出,“对你们来说,社会问题,即作为历史性的基本原则的一般经济原则,是首要问题,因此你们的杂志将特别注意与这些原则有最密切最直接的联系的事实,那些人民经济生活中的事实;至于那些只能间接地体现经济原则的事实,你们将不予以多大关注,把它们放到次要的地位”。[23]他强调,由于俄国经济生活对政治领域的影响并没有西欧那样更突出、更明显,所以,在俄国,摆在革命首位的不应该是经济问题而是政治问题——“即那个使我们大家都感到压抑的政治问题,专制制度的疯狂肆虐,残暴的政府的令人气愤的专横跋扈,我们的普遍的毫无法制,我们的可耻的奴隶制度”。[24]这一阐述代表着经济主义模式的普适性在俄国革命激进主义面前的崩溃瓦解并朝向以政治优先性为中心的新激进观念前进的一个关键点。其政治意蕴在于,革命性断裂不再被构想为单一的经济矛盾之展开的必然的、预定的点,而是取决于各种政治力量关系的霸权斗争。
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特卡乔夫将政治的优先性更直接更尖锐地概括为 “与政治权力作斗争”。[25]单从字面上看,很难说这就是典型的特卡乔夫主义表述,主张同政治权力作斗争,也是巴枯宁主义的诉求,但是,这一诉求在特卡乔夫那里还是呈现出了一些不同寻常的特征。(1)特卡乔夫明确把政治斗争分为相辅相成的两个方面:“一方面认为号召人民反抗现存政权是自己的责任,另一方面在自己的队伍中建立保证在几个地方同时起义的纪律与组织”,[26]其实,这就是他后来在 《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应当是什么》一文中所说的革命的双重目标:“革命破坏活动和革命建设活动”。[27]后一方面是特卡乔夫政治思想的重心所在,也是他不同于巴枯宁的地方。(2)特卡乔夫写作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之际,正值无政府主义国际布鲁塞尔大会召开不久,这次大会引起激烈争论的问题就是无产阶级革命是 “推翻国
家”还是 “夺取国家”的问题,拉甫罗夫后来在谈论这次大会的报告中概述了这一问题:
鉴于在某些国家 (特别是在英国和德国)中工人阶级有一种政治趋势,这种趋势的动力今天虽然是立宪主义的,但明天就可能是革命的,它的目的不是推翻自上而下组织起来的现有国家,而是夺取国家,并为了无产阶级解放的目的,而由国家利用高度的中央集权;鉴于这些国家中的任何一国在这件事上也许或可能引起别国的反应——我们就得好好追问一下,这种根据产业集团而进行的社会改组,这种从上而下实现的国家组织,是否不成为社会革命的起点和信号,是否不致引起它的多少还有些遥远的结果。[28]
特卡乔夫密切关注无政府主义国际布鲁塞尔大会关于国家问题的争论,他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不仅提到这次会议,而且在谈到俄国革命者关于社会变革的条件和方式的争论时,将这些争论的很多要点列举出来:比如,“政治家是否应该抛弃权力”,“是否利要用国家或完全拒绝它的支持”,“革命力量是否需要集中在唯一的集体领导之下”。[29]这些问题在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还没有提出来,在这封信中特卡乔夫不仅提出这些问题,而且强调他是按 “另一种方式提出并表述这些问题”。这等于暗示,他主张政治家不应该抛弃权力、要利用国家、革命力量要集中在唯一的集体领导之下,而这些 “建设性命题”正是特卡乔夫主义的鉴别性特征。如果把 “同政治权力作斗争”与之前的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的相关论述联系起来,就不难发现它的独特含义:同政治权力作斗争,并不是拒斥政治权力,而是通过斗争来改造它、利用它,就像特卡乔夫后来强调的,“社会革命的主要问题与其说是改变现存社会秩序的结构或形式倒不如说是改变它的内容”。[30]
其次,特卡乔夫以特有的方式表述了俄国革命的主体建构方式:围绕国家这个 “空能指 (empty signifier)”构造一个广泛的 “人民谱系 (genealogy of people)”。特卡乔夫不是以简单的阶级对抗关系来设想一种单一性的革命主体,在他看来,当时俄国阶级关系还没有充分分化,俄国只是为两个阶级 (地主阶级和资产阶级)的形成准备了条件,但是,它们毕竟还没有完全形成。所以革命并没有一个先验的主体,而是由具体的社会条件 “造就”出来,“一切受到专横暴虐的压迫的人民,遭到剥削者的痛苦折磨的人民,注定世代被迫以自己的血汗供养一撮游手好闲的寄生虫的人民,被经济奴役的锁链捆住手脚的人民,——一切这样的人民,由于他们所处的社会环境的条件本身的促使,都是革命者,他们随时都能够革命,他们始终愿意革命,他们随时准备投入革命”。[31]这些多元化的、处于各阶层的人民怎样才能形成一种统一的力量呢?有两个关键性策略,首要的是让这些人认识到他们有一个共同的敌人——即国家。围绕这个共同的 “对抗关系”形成一个 “等同链条 (an equivalential chain)”,一如拉克劳描述的那样,“一旦多样性诉求之间的等同关系超出了一定程度之后,我们就拥有了反对整个体制的广泛动员,我们在此也就见证了作为更普遍的历史行动者的人民的出现,其目标必然围绕一个作为政治认同的对象的空能指聚合而成”。[32]为了构建一个作为普遍主体的 “人民”,必须要把那个共同政治的对象虚化一个“空能指”:
我们的国家只有从远处看才是力量。实际上它的力量只是表面的、虚构的。它在人民的经济生活中没有任何根基,它自身并不体现任何阶层的利益。它压制所有社会阶级,所有人都憎恨它。他们容忍国家,他们完全冷漠地忍受它的野蛮专制。但是这种容忍,这种冷漠不应该使您产生错觉。它们只是欺骗的产物:社会创造了俄国的虚假实力,并且受到这种虚假的迷惑。[33]
紧密相关的另一策略是,革命必须要由少数勇敢、聪明、刚毅的革命知识分子来引导,正是由于他们的引导,人民内在的一切主动精神才能释放出来,他们才有勇气打破常规,才能克服相互间的隔阂与差异,形成一种统一的政治力量。即是说,破除俄国国家虚假性幻觉的,正是这些革命知识分子。普列汉诺夫曾经指出,特卡乔夫 “独到的思想”,[34]是他在 《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对少数革命知识分子的关键作用的描述:“只有当少数人不愿再等待而自己去认识自己的需要,并且下决心把这种认识可以说是强加于多数人的时候,只有当少数人促使一直埋藏在人民心中的对自己境遇的不满情绪爆发出来的时
候,暴力革命才发生”。[35]必须看到,上述关于 “国家的虚构性”的文字,是特卡乔夫在谈论革命知识分子的力量时引入的,因此,对这一段文字的理解应该把它放在革命主体建构条件的意义上加以把握,而不宜将之作为一种国家理论的实证性阐释。特卡乔夫不是不知道俄国的专制国家是 “最强大的敌人”,不是不知道 “它拥有军队和巨大的物质财富”,[36]但是,在动员人民进行革命的时候,为了构建一个敢于与这个强大敌人作斗争的 “大写的主体”,必须让人民感到人民比国家更有力量,在更强大的人民的面前,国家的力量是虚弱的。但是,人民的力量是潜在的、分散的,需要由革命精英来开发这一力量,来链接这一力量,来组织这一力量。因此,不能将特卡乔夫的论述仅仅看做是为了 “激发对现存制度的不满和憎恨情绪”的鼓动式宣传,更重要的是,应该把它看做特卡乔夫对革命知识分子 “建构人民 (constructing a People)”的能力的一种确信。似乎可以说,特卡乔夫在欧内斯托·拉克劳之前一百多年就已经明白:建构人民是激进政治的主要任务。[37]
不过,即便从国家结构的分析上,特卡乔夫的说法也可以在当代国家学说中找到某种呼应。一些政治理论家指出,在封建主义国家向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中,存在着一种 “专制主义过渡国家类型”——在这种国家中,中央的统治权已经不受任何封建意义的法则限制,但也不受资本主义经济关系的严格规定,这种过渡性国家一个结构性特征就是政治与经济环节相对独立,国家权威主要靠军队和官僚机构来维持,官僚机构的职能 “不再依靠它们同管辖区的一部分保持经济和政治联系,而在于它们执行国家政权,因此,执行这些职能不再视为实现掌权者的经济和政治利益,而是执行代表全体利益的国家职能”。[38]如果19世纪六七十年代的俄国属于这种过渡性国家类型,那么,特卡乔夫关于俄国专制国家 “不体现任何阶层利益”的说法不仅具有一定的合理性,而且较为成功展示了专制国家的一个结构性缺陷:国家与社会阶级的经济利益之间的关系是非对称的、失衡的,或者是错位的甚至是空位的——一些社会阶级可能在经济上具有实力而在政治上还没有上升到应有的地位,还有一些社会阶级可能经济上、政治上受到双重的剥夺与压迫。只要弄清楚,这里所说的 “任何阶层”并不包括参与国家管理的特权阶层,而所谓的 “社会阶级”也不包括统治阶级,我们就可以感受到特卡乔夫这种表达里蕴藏的愤怒情感:在俄国,人民的经济利益在政治权力体系中缺少一个应有的位置,所以,不是国家不代表阶级利益,而是阶级利益不被国家代表。这是站在 “人民”的立场——即民粹派的立场——对俄国专制国家 “草菅”社会层面广大民众利益的谴责。俄国的广大人民,他们的经济利益在国家这个层面没有得到基本的保障与维护,在国家与供养国家的人民之间存在巨大的断裂,而这个断裂带正是革命的温床。
八
最后,由专制国家的 “虚构性”过渡到东西方国家结构的比较,这显示出特卡乔夫在国家结构分析上操持灵活的 “双重模式”:就资本主义国家而言,他认可马克思的分析模式,而对于还没有达到资本主义国家的过渡性国家,他挪用黑格尔的分析模式。黑格尔国家学说的灵魂在于:国家不同于社会但又高于社会。特卡乔夫将这一 “灵魂之光”照进了俄国专制国家的内在机理,但同时,他又阉割了黑格尔的理性——国家中的 “客观精神”(即那要实现的 “普遍性”)却了无踪影,于是,只剩下一付高高在上的空壳,在革命激情的风暴中无力地摇曳:
在你们那里,国家不是虚构的力量。它用双脚站在资本上面;它本身体现着一定的经济利益。巩固它的不像我们这里只是军队和警察,资产阶级关系的整个制度都在巩固它。在没有消灭这个制度之前,战胜国家是难以想象的。在我们这里,则恰恰相反——我国社会形式本身的存在有赖于国家的存在,这个国家可以说是悬在空中的,它和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它的根基是过去,而不是现在。[39]
这里,我们再一次发现了 “普遍性”的三个不同版本:一个是黑格式的作为伦理实体的普遍性;一个是马克思式的作为特权阶级主体的虚假普遍性;一个是特卡乔夫式的阶级利益缺位的空洞普遍性。俄国激进理论家与马克思一样致力于否定黑格尔国家理念中的普遍性,但是,他们的处置方式迥然不同:
马克思通过颠倒国家与社会的关系把黑格尔所谓的 “绝对自在自为的理性”变成一种既非自在也非自为的存在,而俄国激进知识分子则通过扩大国家与社会的分离 (“它与现存的社会制度毫不相干”)来虚无化 “伦理实体”的客观性,这是民粹主义者藐视国家的学理依据。特卡乔夫的独特之处在于,他并不像巴枯宁那样任意地把 “国家对社会优先性”升格为一种普遍的国家哲学,而只是将其严格限定在 “不完备国家”的范围之内,因此,东、西方国家的区分不仅仅具有比较的意义,而且具有一种消解普遍性之僭越的形而上学批判功能。如果国家内在的 “普遍性”形态尚且具有非普遍性,那么,革命道路的普遍性无非就是神话。正由于秉持这样的信念,特卡乔夫才果敢地向恩格斯表白:“我们完全拥护欧洲工人党基本的社会主义原则,但不赞同它的策略,也不赞同而且也不应该赞同只能通过唯一的做法和革命斗争方式 (至少是以马克思和恩格斯先生为首的派别的方式)去实现这些原则”。[40]
追求马克思的目标,却不走马克思指定的道路。这令人想起,俄国十月革命胜利后不久,葛兰西提出的一个大胆的论断:布尔什维克革命是反对卡尔·马克思的 《资本论》的革命。葛兰西热情讴歌了布尔什维克对马克思 《资本论》的 “革命图式”的背离,“如果说布尔什维克否定了 《资本论》中的某些结论,但他们并没有抛弃它的富有生命力的内在思想。总之,这些人并不是 ‘马克思主义者’,他们并没有用这位大师的著作教条主义式地去编织一种容不得讨论的僵化理论,他们实践着马克思的思想——一种不朽的思想”。[41]不知葛兰西对布尔什维克革命这种看似矛盾的评述是否适用于特卡乔夫的革命主张?如果适用的话,我们不妨说,特卡乔夫才是历史上第一个构想 “反 《资本论》的革命”的革命家。
毫无疑问,特卡乔夫在叙述 “我们”时留下 “我”的记号。遗憾的是,恩格斯对此丝毫没有感知。恩格斯似乎是矛盾的:他一方面坚决主张特卡乔夫使用的代词 “我”不能代表作为俄国民粹派的 “我们”,另一方面又极力否认特卡乔夫的 “个我”的独特性。恩格斯声称,特卡乔夫的 “才能的光芒”在《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和 《给弗里德里希·恩格斯先生的公开信》中 “并没有放射出来”。[42]恩格斯之所以如此武断,无非是受到了马克思与巴枯宁在第一国际内部的斗争的余波的过度 “雕琢”。一如历史学家安德烈·瓦利基指出的,“特卡乔夫与恩格斯论战的背景与其说是俄国的还不如说是第一国际的——整个争论围绕着巴枯宁与马克思之间的意识形态分歧以及他们争夺第一国际的领导权的斗争问题而展开”。[43]恩格斯仅仅把特卡乔夫的观点置于第一国际内部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的斗争中来衡量,其关注的只是特卡乔夫与巴枯宁 “趋同”的地方,因而,那些 “存异”之处皆没有进入他的 “法眼”。
加达默尔曾说,“谁想理解,谁就一开始便不能因为想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而囿于他自己的偶然的前见中——直到本文的见解成为可听见的并取消了错误的理解为止”。[44]问题就在于,恩格斯从一开始并没有打算以一个 “诠释者”的身份对特卡乔夫的 “本文”做出一种开放性解读,所以,不是恩格斯没有眼光,而是某种历史性处境吞没了他发现特卡乔夫本文的 “另一种存在”的眼光。在 《流亡者文献 (四)》中,恩格斯斩钉截铁地说,“特卡乔夫先生想硬要我认真看待他的小册子,这当然是绝对办不到的”。[45]既然恩格斯发誓绝对不认真对待特卡乔夫的作品,他自然也就绝对看不出特卡乔夫的独特性。不过,纵使恩格斯确如加达默尔所说 “尽可能彻底地和顽固地不听本文的见解”,我们也不应该把恩格斯 “失察”的责任完全归咎于恩格斯本人。
必须看到,1874年,特卡乔夫在与拉甫罗夫的论战中,其核心任务是表明他与温和派的不同,还没有把区分行动派之间的不同观点与策略提到议事日程上来,因此,《俄国的革命宣传的任务》自然而然地表现出与巴枯宁的亲缘性。恩格斯根据这种亲缘关系而断言特卡乔夫使用了 “巴枯宁主义词句”,也不算过分。在那个时候,特卡乔夫刚刚进入国际舞台,他还没有确立自己 “一家之言”的地位,更没有自己的学派。德波拉·哈迪曾说,“如果特卡乔夫不从俄国流亡到国外,他可能根本不会取得与巴枯宁和拉甫罗夫平起平坐作为革命行动的主要理论家的地位”。[46]在1874年,特卡乔夫还没有达到与巴枯宁和拉甫罗夫平起平坐的地步,那时俄国民粹派还没有形成三足鼎立的局面,人们只知道行动派与温和派的对立,不知道行动派中间还有什么对立。行动派首当其冲的人物当然是巴枯宁,特卡乔夫在批驳拉甫
罗夫的 “等待主义”时,表达的是 “直接行动”的革命观念,所以把他的观点归属在巴枯宁主义名下是比较自然的事情。尽管如此,恩格斯在 《流亡者文献 (三)》中,还是留有一定余地的,他并没有一口咬定特卡乔夫是一个巴枯宁主义者——也许恩格斯心里是那么想的,但他毕竟没有那么说。
恩格斯只是在 《流亡者文献 (四)》中才开始明确地把特卡乔夫划入巴枯宁主义阵营。之所以会有如此的划定,在很大程度上是因为特卡乔夫本人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更加露骨地为巴枯宁辩护。在致恩格斯的公开信中,特卡乔夫不仅有意淡化自己个性化的立场,以经典民粹主义的一般性观点来对抗恩格斯,而且还坚定地宣称自己就是要站在巴枯宁一边。特卡乔夫似有点逆反心态——您不是说我使用“巴枯宁主义的词句”吗,我就是要为巴枯宁鸣冤:
您用尽一切骂人的话来攻击我,因为您在我的小册子里找到了目前为止我所不知的 “巴枯宁主义的词句”,您从中发现,我们的同情,正如大部分与我们同心协力的革命党人的同情,不是站在您这边,而是站在敢于举起义旗反对您和您的朋友的人那边,站在那个从现在起成为您的不共戴天的敌人和您的启示录的梦魇那边。[47]
特卡乔夫与拉甫罗夫一样表达了对恩格斯 “主写”的小册子——《社会主义民主同盟和国际工人协会》——的强烈不满:“您和您的朋友力图玷辱我们所处的这个革命时代最伟大和最富有自我牺牲精神的代表之一”。[48]在马克思主义与巴枯宁主义之间斗争处在你死我活不可调和的敌对状态下,特卡乔夫这样大张旗鼓地为巴枯宁呐喊助威,这样故意地在恩格斯眼前晃动着巴枯宁式的鬼脸,已经远远超出了恩格斯所能承受的底线,恩格斯必须表达自己的愤怒。难怪恩格斯在 《流亡者文献 (四)》中一而再、再而三地给特卡乔夫的脸打上巴枯宁主义者的烙印:“这一次他表明自己是一个真正的巴枯宁主义者”、[49]“这里在我们面前的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巴枯宁主义者”、[50]“特卡乔夫先生摆出一副无辜受辱者的德行高超的面孔,即摆出一副对一切巴枯宁主义者都是极为相称的面孔”。[51]《流亡者文献 (五)》发表之后,恩格斯仍然余怒未消,他在1875年5月为 《论俄国的社会问题》单行本所写的导言中再次明告天下:特卡乔夫致恩格斯的公开信是一个 “劣等作品”——“这篇劣等作品从形式到内容都带有一般的巴枯宁主义的烙印”。[52]
文秋瑞在其论述俄国民粹主义的不朽之作中说,“讨论恩格斯与特卡乔夫的争论是有趣的”,[53]文氏所说的 “有趣”无非是指:恩格斯与特卡乔夫决斗,一开始枪口明明指向特卡乔夫,可是,出人意料的是,最后中枪的却是巴枯宁。 “恩格斯把自己局限于攻击特卡乔夫的纲领中的巴枯宁主义因素,然而,这些东西并不是根本性的”。[54]这或许是历史理性的 “狡计”,它只让恩格斯隐约听到特卡乔夫的声音,却不让恩格斯一睹特卡乔夫的真容。历史把验明特卡乔夫 “真身”的重任留给了弗拉基米尔·伊里奇·乌里扬诺夫。一代人有一代人的使命,在1874—1875年,也许恩格斯只能那么看待特卡乔夫了。
[1][6]《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3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73年,第652页。
[2]B.S.Itenberg,Rossiiai Parizhskaia Kommuna,Moscow:Nauka,1971,p.123.
[3][4][10][13][18][22][42][45][49][50][51]《马克思恩格斯文集》第3卷,北京:人民出版社,2009年,第375、375、378、376、378-379、377、379、379、378、380、388页。
[5][12][46]Deborah Hardy,Petr Tkachev:The Critic as Jacobin,University of Washington Press,1977,p.204,204,186.
[7]Philip Pomper,Peter Lavrov and the Russian Revolutionary Movement,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p.158.
[8][9]Deborah Hardy,The Lonely Éigré:“Petr Tkachev and the Russian Colony in Switzerland”,Russian Review,vol.35, no.4(Oct.,1976),p.400,402.
[11][14][15][16][17][19][20][25][26][29][33][39][40][47][48]Революционный радикализм в России:век девятнадцатый. Документальная публикация./Под ред.Е.Л.Рудницкая.М.:Археографический центр,1997,С.336,336,337,337,339,342,343,337,341,343,338,339,336,343,343.
[21][23][24][31][35][36]特卡乔夫:《俄国革命的宣传任务:致 〈前进〉杂志编辑的信》,《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49、365、349、354、347、352页。
[27]特卡乔夫:《能实际达到的近期革命目标应当是什么》,《俄国民粹派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83年,第380页。
[28]斯切克洛夫:《第一国际》,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1974年,第299-300页。
[30]P.N.Tkachev,“Nakanuneinadrugoi den'revoliutsii”,Nabat,no.1-2(1877),p.18.
[32][37]Ernesto Laclau,“Why Constructing a People Is the Main Task of Radical Politics”,Critical Inquiry,Summer, 2006,vol.32,no.4,p.656,pp.646-680.
[34]普列汉诺夫:《我们的意见分歧》,北京:人民出版社,1955年,第64页。
[38]尼科斯·波朗查斯:《政治权力与社会阶级》,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82年,第177页。
[41]《葛兰西文选》,北京:人民出版社,1992年,第10页。
[43]Andrzej Walicki,The Controversy Over Capitalism:Studies in the Social Philosophy of the Russian Populists,University of Notre Dame Press,1989,p.142.
[44]加达默尔:《真理与方法》上卷,1999年,上海:上海译文出版社,第345页。
[52]《马克思恩格斯全集》第18卷,北京:人民出版社,1964年,第641页。
[53][54]Franco Venturi,Roots of Revolution:A History of the Populism and Socialist Movements in Nineteenth-Century Russia,The University of Chicago Press,1960,p.415.
责任编辑:罗 苹
A124
A
1000-7326(2015)05-0017-11
周凡,北京师范大学哲学学院教授 (北京,100875)。